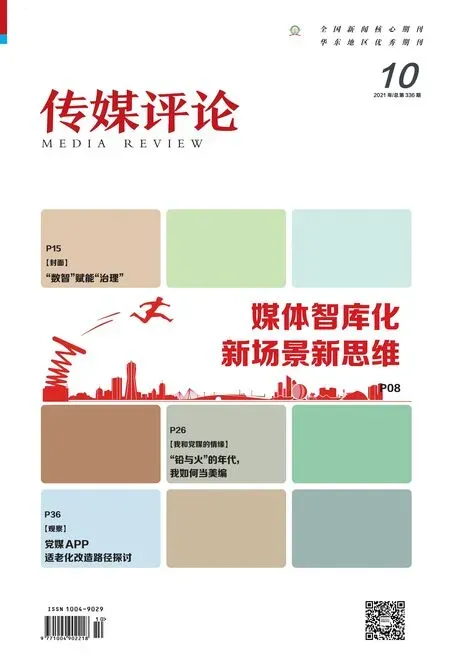回望来路 我心依依
——访《浙江日报》老记者黄云澍
2021-06-22文_高唯
文_高 唯

黄云澍,1934年11月出生,籍贯江苏常州。1958年9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进入浙江日报社工作。先后在《浙江日报》,浙报驻绍兴、金华记者站,以及《钱江晚报》工作。上世纪60年代初曾参与创办《浙江日报》文艺副刊《钱塘江》。1995年1月退休。2013年2月入党。
采访组成员:浙江传媒研究院 蒋卫阳
浙江日报全媒体编辑中心 高唯
浙江法制报 胡晓峰 陈骞
采访组:黄老,您好。您当了一辈子记者,这次有机会采访您,非常荣幸。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经历。
黄云澍:我与报纸的缘分,已经结了六七十年。
1934年,我出生在江苏常州农村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我祖父大字不识几个,却坚定地认为读书能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他每天早出晚归,勤劳耕种,一年只休息3天,和我父母一起,先后供养出我们家里4个大学生。
刚入学时,我作文写不好,老师把我列为“差典型”。为了提高作文水平,老师教我多看报纸。我看得最多的是《文汇报》,爱看查良铮(穆旦)的文章。我天天看报纸,学习写作方法。一个学期以后,我的作文水平突飞猛进,全年级第一。老师给我批语:作文好得很!后来我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1958年,我从南大毕业后,进入浙江日报社工作,是报社第一批非新闻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从此,我与报纸的缘分就落实到了《浙江日报》。
我在报社工作了30多年,其中在编辑部干了20多年、记者站干了10多年,一直到退休,在《浙江日报》《钱江晚报》都待过。
回首这30多年,如果要给自己打分,我认为只是及格而已,充其量超过分数线十来分。但这么多年工作,我尽心竭力,毫不马虎。
采访组:您在新闻领域工作了那么多年,哪些作品是您印象比较深的?
黄云澍:在报社工作了30多年,我写了大概六七十万字的各类报道,自己比较满意的是《茆山顶上的苍松》这篇通讯。
这是我进报社写的第三篇稿子,采访遂昌县一位名叫陈香兰的女烈士的事迹。她是为了不让突然倒伏的大树砸中其他村民,毫不犹豫地飞身抢险而壮烈牺牲的。当时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高铁,连火车快车都很少。我早晨从杭州出发,坐慢火车到龙游,在龙游住一晚,第二天一早再坐汽车去遂昌。遂昌是山区,当时从龙游到遂昌的公路都是砂石路,汽车要走3小时才能到。
到了遂昌,考验才开始,我听不懂当地方言啊!一开始县里有一位工作人员陪我同去,充当翻译,但他陪了我半天就有事回去了,可我后面还要采访好几天呢!采访年轻人还好,稍微能听懂一些,可面对年纪大的采访对象,我就一句也听不懂了。怎么办呢?我有办法,就让采访对象“演”给我看——用他们的动作,用肢体语言,来重现陈香兰烈士的故事。记得有一位老太太,说到陈香兰平时胆子也不大的时候,就“梆梆梆”地用手中的棍子敲地,连比带划地告诉我,陈香兰在队里开完会很晚才回家,因为怕黑,就用随身带着的一把开大门的老式铁钥匙沿途敲墙,发出响声,给自己壮胆。她这样一比划,我就明白了,陈香兰并不是一位胆大泼辣的女同志,但就是这样一个柔弱女子,在危险面前,却能奋不顾身保护同伴,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在他们的“表演”中,我似乎回到了陈香兰牺牲的那一夜。那天晚上,她因公事要出门,外甥女拉着她的手,让她不要走,要她陪自己,她只好骗外甥女说马上就回来。可谁想到,这一去,就是永别……
采访完,我在村里找了个地方,用完4根蜡烛,连夜写成初稿。第二天一早,起床后稍作修改,给县委办公室审了稿,就赶回了杭州。回到报社,我又把稿子改了一遍,交给了部主任张秉海。张主任翻了翻,就把稿子放到了抽屉里,没说任何话。这下我心里打起了鼓:难道稿子被“枪毙”了?

黄云澍的文章《茆山顶上的苍松》刊于1958年12月20日《浙江日报》第3版
等了个把月,1958年的12月20日,稿子突然见报了,占了不小的版面,还配了县委书记的文章。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报社为鼓励记者写好稿,正在酝酿评选“红旗稿”的制度。为了配合这一制度的推出,考虑要用一篇比较好的稿子“打头阵”,结果选中了我这篇稿子。于是,《茆山顶上的苍松》成为《浙江日报》第一篇“红旗稿”。报道还受到了当时省委宣传部和省委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的肯定,他们说:“稿子就是要写得有些文采,这样群众才爱看。”这篇文章后来还被收进浙江省省编中学语文课本,并被改编成连环画,这对那时还是年轻记者的我,真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还有一篇我比较满意的作品,就是报告文学《电脑厂长》。文章中的厂长,是改革开放初期打破“大锅饭”的一个典型。他所在的那个30多人的小厂,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造出了微机,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这篇稿子在采访过程中,因为涉及当时还有争议的打破“大锅饭”的问题,也遇到了不少阻力。但是我想,打破“大锅饭”,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阻挡不了的,因此我坚持跟踪采访了个把月,只要这位厂长回到浙江,我就去采访他。这个厂长可了不得,和卡车司机从深圳一路押货运到上海去销售,几十个小时风尘仆仆也不休息。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浙江企业家的精神在闪光。这篇报告文学,《人民日报》曾撰文推荐。
除了新闻报道,我在《浙江日报》以及其他刊物上还发表过不少报告文学、散文和诗歌。说到这,有一位领导不得不提,那就是当时的总编辑于冠西同志。我诗歌创作的激情被激发出来,是和他知人善任的领导艺术分不开的。
有一次,在温州楠溪江畔,我偶然看到有人用一个水碓在舂米。农民用水碓舂米,历史悠久,充满生活智慧,我看了很有感触。当地老人还介绍说,这水碓房当年还是游击队出没的地方。于是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一篇散文诗《水碓房》,寄回给《浙江日报》的《钱塘江》副刊。没想到还没到《钱塘江》副刊出刊的日子,这篇散文诗就在其他版面见报了。原来是于冠西同志看了这篇稿子后,觉得好,等不及《钱塘江》副刊出刊的日子,就安排到要闻版刊发了。后来我又得知他在一次谈版会上还专门提到这篇稿子,他说记者下去采访,不是只能写已经定了的题目,有其他“副产品”,比如像小黄写的这种有感而发、又有新意的诗歌,也是不错的。冠西同志对每个记者身上的闪光点,都能那么敏锐地发现,而且不吝于表扬。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为党的新闻事业奋斗一辈子的决心更坚定了。
采访组:您1958年就来到报社工作,那时《浙江日报》创刊还不到10年。能不能请您回忆一下,早期报社各方面的条件怎么样?是不是很艰苦?大家的工作状态又如何?
黄云澍:我刚进报社时被分配到政治组,张秉海同志是政治组主任。我是中文系毕业的,连新闻导语都不会写。张主任就对我说:“小黄,你是南大中文系毕业的,对新闻写作不熟悉,第一个星期,你就翻报纸。”我翻阅了一周报纸后,张主任给我派了第一个任务,让我写一篇关于人民公社的稿件。我写不出来,就又去翻了一个星期的报纸,可还是写不出来。张主任就和我说:“小黄,不为难你了,你出去采访吧。”
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去采访一位退休老工人、老模范,前后去了两次。稿子我用一个晚上就写出来了。这也是我的第一篇稿子,题目叫《走过胜利的道路,踏上崭新的起点》,老编辑给我编好后,登在1958年10月1日《浙江日报》2版头条位置。
没想到我第一次采访挺顺利,却在采写第二篇稿子时出了洋相。这次的任务是到海宁去采访农村青年在劳动中产生感情、谈恋爱的故事。去了以后,由于我没注意工作方法,当时大家的观念又比较保守,一听说我是来采访谈恋爱的事情的,好多小姑娘就笑着跑开了,躲得远远的。说实话,那时我心里真有点着急,担心自己如果一连几次都写不出稿子来,就会被调离《浙江日报》。幸好,我的第三篇文章,就是前面提到的《茆山顶上的苍松》顺利见报。
一开始,我对报社的夜班工作特别不习惯。上学时,我每天晚上9点多就睡了,可是在报社,晚上9点,正是灯火通明,才开始工作,经常要忙到凌晨一两点钟,周末、节假日也要召之即来。但我很快就习惯了。条件虽然艰苦,我的同事们都毫无怨言,乐此不疲。因为在党报工作,大家都有荣誉感,积极性很高。我孩子五六岁正上幼儿园,周末报社要加班,我就把他送到要好的同事家里。那时大部分编辑、记者都住集体宿舍。我上夜班,孩子不敢一个人睡觉,我也托同事照顾,等半夜下班后再去接回来。有时候出差,就整天把孩子寄放在同事家。那时大家都是这样的。没有奖金,也没有补休,上夜班能吃个夜宵,就很开心了。
采访组:您怎么看现在的青年新闻工作者,对他们有什么希望和寄托?
黄云澍:年轻人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国家发展的未来,我很羡慕他们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老同志只有向年轻人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我送他们4个字:敬业,奉献!拿我们那时候的话说,就是要干一行爱一行。我举个例子,我从记者站调回编辑部后,先在《钱江晚报》干了1年左右,然后到《浙江日报》工交财贸部。对我来说,财贸新闻从未涉足过,我就从头开始学习,后来在领导的支持下办了《今日市场》专栏,专门报道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从文化记者转型财贸记者,我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来学习入门知识,第3个月才有了一些成绩。后来又搞金融报道,办了《金融角》专栏,着力宣传金融对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的促进作用。我几乎访遍浙江所有的银行行长,在他们的支持下,我每个月都有几篇有特色的金融报道上一版,有的还是头条。从这个经历中我体会到,当记者,只要肯下功夫,多研究,总会开创出一个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