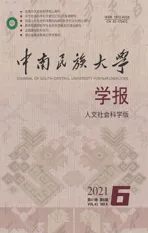鄂西“肉连响”与闽南“拍胸舞”的异同及成因
——基于舞蹈生态学视域下的比较分析
2021-06-16刘梦
刘 梦
(中南民族大学 音乐舞蹈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流行于鄂西利川地区的“肉连响”作为鄂西土家族代表性传统舞蹈,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不仅舞蹈形态独具魅力,而且拥有悠久的历史,是鄂西土家族舞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流行于闽南地区,尤其是泉州地区的“拍胸舞”是闽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舞蹈之一,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也在闽南传统舞蹈文化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肉连响”因其以男性舞者赤裸上身,手掌拍击身体的额、肩、臂、肘、肋、胯、腿等部位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具有其粗犷、洒脱、淳朴的舞蹈风格而备受舞蹈研究者的高度关注[1]。“拍胸舞”则以男性舞者赤裸上身,有节奏地拍击身体的胸、肘、肋、肩、掌等部位,形成粗犷、古朴、热烈的舞风。鄂西土家族民间舞蹈“肉连响”与闽南民间舞蹈“拍胸舞”在动作形态、风格特点、服装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相似性,由此形成鄂西舞蹈文化与闽南民间舞蹈文化遥相呼应的态势。早在1996年,就有学者在对“拍胸舞”源流的探究中提及与之极为相似的“肉连响”,但遗憾的是未对两者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2]。本文运用舞蹈生态学、舞蹈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在田野调查、文献查阅基础上对“肉连响”和“拍胸舞”的舞蹈形态典型性舞畴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表层形态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及其背后深层的舞蹈生态因素。
一、“肉连响”和“拍胸舞”舞蹈形态对比分析
(一)典型性舞畴因子分析
1. 基本节奏型。鄂西“肉连响”以拍击身体各部位并发出声响而得名,其拍击身体动作中发出的声响即为其最初的节奏,后又加入大鼓、锣鼓、木鱼、钹等伴奏乐器,其基本节奏型主要通过拍击身体发出的声响,同时伴以弹舌、弹指声以及大鼓击鼓声的节奏所体现。 “肉连响”拍击身体并伴以鼓舌、弹指,以欢快的2/4节奏为主,每小节包含一个重拍一个弱拍,根据手掌拍击身体部位的不同及拍击次数的不同,发出不同数量的声响,主要有“七拍”“十拍”“四拍”“三拍”。
七拍:2/4▎× × ▏× × ▏× × ▏× 0 ▎
十拍:2/4▎× × ▏× × ▏× × ▏× × ▏× × ▎
四拍:2/4▎× × ▏× × ▎
三拍:2/4▎× × ▏× 0 ▎
“肉连响”鼓伴奏节奏主要为:

“拍胸舞”又称“打七响”,本无伴奏,以手掌拍击、手肘夹击、脚下踩跺而发出声响作为舞动节奏,后逐渐加入闽南民间歌调及弦乐(南琶、洞箫、二胡、三弦)、打击乐(锣、鼓、钹、竹板、木鱼、响盏)等伴奏乐器产生音乐节奏[3]。通过对“拍胸舞”之“田间拍胸”“踩街拍胸”“醉酒拍胸”“乞丐拍胸”节奏型的梳理,笔者归纳出“拍胸舞”舞动的基本节奏型为稍快2/4节奏,每小节包含一个重拍一个弱拍,主要有“七拍”“八拍”“四拍”。
七拍:2/4▎× × ▏× × ▏× × ▏× 0 ▎
八拍:2/4▎× × ▏× × ▏× × ▏× × ▎
四拍:2/4▎× × ▏× × ▎
“拍胸舞”鼓伴奏节奏主要为:

2.典型性显要部位动作及其流程。根据对鄂西“肉连响”中“七响”“十响”“三响”“四响”舞畴序列的动作分解及动作频率统计,其典型性显要部位动作为:一是手臂的 “8”字划圆配合手部的掌击动作,例如掌击额头、掌击前胸、掌击大腿、穿手划8字掌击肩膀、穿手划8字双手胸前击掌和手臂平举划8字圆等等;二是以腰为轴带动上肢的拧转。手臂的“8”字画圆动作构成从肩部到手指尖的三维运动,属于外旋的转动型动作流程;以腰为轴带动上身的拧转中,腰部的“转”本为平圆运动,但“拧”即在上身的转动中呈现不同方位、不同程度的“倾”“仰”“躺”等非自然或反自然动态,形成三维运动,其运动流程也属于转动型。
根据对闽南“拍胸舞”中“七响”“八响”“四响”等舞畴序列的动作分解及动作频率统计,其典型性显要部位动作为:一是手部掌击和肘部夹肋动作,包括击掌、掌击前胸、掌击肩膀、掌击手肘、掌击大腿和夹击左肋、夹击右肋、双肘夹肋等等;二是以胯部横摆带动上身及头部的横摆动作。手部掌击身体各部位的动作需要大臂、小臂转动的配合,其动作流程属于转动型;胯部的横摆动作是双腿交替的重心移动中,盆骨臀肌左右交替的用力推动,形成胯关节及上身、头部的横向晃动,上身前后波浪式的“蛇腰”折动,形成折动型动作流程。
3.基本步伐。“肉连响”中配合其手臂的“8”字划圆、手部掌击动作和以腰为轴带动上肢拧转的典型性显要部位动作,脚下以膝盖弯曲、碎颤状态下的扭胯秧歌步和双腿交替的吸跳步为基本步伐。
“拍胸舞”中配合其典型性显要部位动作,脚下步伐是伴随身体横摆动律,屈膝状态下的双脚交替全脚踏跺步伐。
4.舞意。“肉连响”源于古代祭祀,后定型为一种乞丐行乞舞蹈,舞意为赢得他人欢心和同情获得施舍,有凄楚、悲凉的情感。随着社会的安定,人民生活的改善,“肉连响”舞意逐渐转变为表现一种热情欢快的情绪,营造一种热闹的气氛,表达土家人豁达豪爽的性格。
“拍胸舞”源自于古闽越族的祭祀活动,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成为民间乞讨舞蹈。近代以来,由于其粗犷古朴又诙谐热烈的舞风,广受泉州地区民众喜爱,又逐渐形成具有代表性的“田间拍胸舞”“踩街拍胸舞”“乞丐拍胸舞”和“酒醉拍胸舞”。“田间拍胸舞”展现田间劳动的场景,舞蹈豪爽有力又灵活欢快,充分表现闽南人豪爽豁达、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踩街拍胸舞”在民间迎神赛会或喜庆节日中表演,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表现出闽南人轻松、怡然的性格特点;“乞丐拍胸舞”原为乞丐卖艺行乞时所跳,动作徐缓,表现乞丐的可怜形象;“酒醉拍胸舞”为乞丐在破庙喝酒后,乘兴而舞,自由洒脱,怡然自得[4]。总体来看,“拍胸舞”其舞意展现闽南人祥和的生活图景和怡然洒脱的性格特点。
5.服饰。服饰作为舞蹈的伴同物是“舞体”在发生舞蹈行为时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不仅能够帮助舞体体现和增强舞蹈的审美效应,更能直接影响舞动中步伐的幅度及显要部位动作[5]110-111。“肉连响”的舞体均为男性,其服饰特点为:头部包黑或白色头巾,在近四十年中逐渐演变为系一条窄的红绑带或无头饰,上身赤裸、下身短裤或布条围裹,赤脚。
闽南“拍胸舞”舞体均为男性,服饰特点为头戴蛇形草编头圈、上身赤裸、下身短裤、赤足。
(二)典型性舞畴因子对比
通过对鄂西“肉连响”和闽南“拍胸舞”典型性舞畴因子的分析和对比,可以清晰看出两者在形态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1.基本节奏型。两者极为相似,都以中速偏快的2/4节奏型为主,节奏较为均匀,一拍一动,典型性舞畴多为7拍或8拍。
2.典型性显要部位动作。两者在相似中又显现出差异,相似在于两者都有手部的掌击动作及胯部的摆动动作。差异在于,“肉连响”的手部掌击动作多伴有手臂的 “8”字划圆,典型性显要部位动作还有以腰为轴带动上肢的拧转动作;“拍胸舞”则是肘关节的夹肋动作和胯部延伸至头部的横向左右晃动、上身前后波浪式的“蛇腰”折动。动作流程上,两者典型性显要部位动作的动作流程多为转动型,但有所区别的是“拍胸舞”的胯部横摆动和上身前后波浪式的“蛇腰”折动,属于折动型。
3.基本步伐。“肉连响”为下肢松弛、胯部扭动中的秧歌步伐和双腿交替的吸跳步伐;“拍胸舞”为伴随身体横摆,屈膝状态下的腿部用力全脚着地的踏跺步伐。
4.舞意。两者的舞意极为相似,都随历史的发展从乞讨卖艺最终成为表达一种轻松欢快的情绪,展现乐观豁达的性格。
5.服饰。两者服饰大致相同,仔细对比可发现细节的差别,“肉连响”曾在较长历史阶段以头巾包头呈圆形装饰,“拍胸舞”头饰则始终由草绳编成并呈现出立体蛇形。
二、“肉连响”与“拍胸舞”形态相似性的文化成因
通过上述比较研究,两者舞蹈形态典型性舞畴因子从形到意都呈现较高的相似度。笔者认为,构成两者相似形态的文化成因是其同属于我国连响文化圈。
文化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在某地区形成、发展并可能向其他地区移动,同时在不同地带,可能有与其相关联的文化成分形成文化圈的广阔地理分布表现[6]。基于“肉连响”和“拍胸舞”舞蹈形态典型性舞畴因子从形到意的相似性,从“数量的标准”可确定鄂西利川地区和闽南泉州地区同属于连响文化圈。舞蹈是人体动作的艺术,对动作的选择和运用影响着舞蹈的形态和风格,拉班人体动律学归纳出“砍、压、冲、扭、滑动、闪烁、点打、漂浮”八种动作元素。从“形的标准”来看,不论是“拍胸舞”,还是“肉连响”,选择赤裸身体以“点打”为元素的拍击身体部位为主要动作形态,并非舞蹈动作形态选择的唯一选项或必然选项。因此,作为不同地域的两种舞蹈,其相似性绝非巧合,两者之间有着历史的联系,是文化传播的结果。
历史上闽南与鄂西存在着文化的交流互动,使两地同属于连响文化圈。土家族本为巴人后裔,“肉连响”播布区鄂西清江流域,是巴文化的发源地。古代巴人俗喜歌舞,尤善男性武舞。“肉连响”虽不是由“巴渝舞”直接演化而来,但也继承了巴人舞蹈的粗犷古拙,体现出巴舞遗风。闽南地区自古为百越民族居地,越人以蛇为图腾。越与巴、濮同是南方民族,在许多地区交错杂居,先秦之前,越、濮两族也曾在今土家族地区活动。考古学者曾发现越文化很早曾到达巴人活动的中心地带,在商周遗址中采集到越人创造的几何印纹硬陶[7]。可见,两种文化之间必定有着交流互动,从而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影响。西汉灭闽越国后,武帝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为由,将闽越国官员及百姓迁徙到江淮一带,闽越人逐渐融合于汉人中[8]。此后,中原大规模人口南迁入闽: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林、黄、陈、郑、詹、邱、何、胡”八姓为主的人口南迁入闽;初唐,大批士族平乱入闽,开建漳州;唐末,大量义军入闽,创建闽国;北宋至南宋,中部乡民逃难入闽[9]。面对中原大规模的人口入闽,少数留居闽地的闽越人沦为贫民或乞丐,借助跳“拍胸舞”沿街乞讨以求生存[10]。形成于宋元时期的泉州梨园戏,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泉州地区丰富的南音、传说故事和民间歌舞,“拍胸舞”也被其吸纳其中。梨园戏《郑元和和李亚仙》“莲花落”一折中,书生郑元和穷困潦倒流落街头跳的就是“乞丐拍胸”。由此推断,“拍胸舞”在梨园戏产生之前已是泉州广泛流传的乞丐乞讨舞蹈,因而才会被吸纳入戏曲这一新的艺术形式中表现人物的身份和际遇。
从连响文化圈的功能来看,“肉连响”舞蹈形态在历史进程中曾以“泥神道”的形式和名称存在,形式上有以乞丐为主的舞体在舞蹈之前和在舞蹈拍击过程中将稀泥拍涂于身体和脸上的环节,其功能仍然是用于乞丐行乞,获得施舍。“肉连响”和“拍胸舞”的传统功能都为祭祀祈福,后用于乞丐沿街乞讨,以动作、声响吸引人群,通过交流情感获得施舍。直到近代,其舞蹈功能才转变为自娱和娱人,抒发自由洒脱、喜悦欢畅的情感。宋以后,连响文化经戏曲的加工提炼获得进一步发展,在湖北、江苏、福建等地区出现“莲湘”“莲香”“莲响”“打花棍”“打钱棍”等新的变化:加入代替双手击打身体的道具“莲湘”或“钱棍”,由一根竹竿制成,竹竿两端串铜钱或铁片,在击打中代替手掌拍击发出声响;吸收了戏剧表演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增加了戏曲伴奏音乐、改良了服装装饰;舞体逐渐不仅仅限于男性等。此外,曾有研究“拍胸舞”的学者在调研中发现,除闽南地区、鄂西土家族聚居区外,在海南黎族聚居区、台湾高山族聚居区都有“拍胸”舞蹈形象,由此,认为南方各地区的“拍胸”形象源自同一个曾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区域的民间舞种[11]。海南万宁县、东方县黎族流传的“钱串舞”“钱铃舞”,台湾台南、高雄等地由闽南人传入的“打七响”的加入,进一步扩大了我国连响文化圈的地理范围和文化内涵,各地域因民族交融时期和程度的不同,呈现出连响文化多层次的样貌。
三、“肉连响”与“拍胸舞”形态差异性的文化成因
(一)自然生活因素
吴晓邦、于平曾在舞蹈形态学的相关研究中指出,构成舞蹈原生形态的人体动态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由自然生态促成的少有意识渗透却沉淀有意识行为的自然动态,即“习惯的动”;另一部分是由社会生态促成的“练习的动”。其中,“习惯的动”能充分反映出运动人体的生态烙印[12]284-285。对舞体产生影响的自然生活因素包含生理机能、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各因素之间又互相关联形成链条,使舞体的生理产生变化促成“习惯的动”[13],进而对舞蹈的形态产生影响。生理机能的差异特别关注两性,不同性别特征决定体态差异并导致人体运动方式的差异,因“肉连响”和“拍胸舞”均是由男性舞体表演完成,因此不在差异性研究所涉范围中。笔者认为,导致两者在显要部位动作、基本步伐和体态重心上形成差异的原因,主要为自然生活因素中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及生活习俗的差异。
1.生存环境的影响。生存环境作为自然生态因素之一,具有先在性和潜在性。利川位于东经108°北纬30°左右,地处鄂、渝交汇处,境内重峦叠嶂,北部为利中盆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南部山高坡陡、沟谷幽深。该地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无酷暑、雨量充沛、终年湿润,四季分明[14]。 “肉连响”主要流行区域在鄂西利川北部盆地的都亭、汪营、南坪一带。闽南泉州地区,位于北纬25°东经117°,依山面海,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阶梯状下降,形成由中低山向丘陵、台地至平原次变的地形地貌。泉州地区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终年温暖湿润,四季如春[15]。 “拍胸舞”的主要流行区域在泉州东南部平原的鲤城区及岛屿金门县等地。有学者对中国传统民俗舞蹈的研究发现,体态重心和运动部位受到纬度高低的影响,呈现南北的差异,通常情况下纬度越高,气温越低,舞蹈动态的重心和运动部位越高[16]。例如汉族民俗舞中,随着舞蹈所属地区纬度由低到高,从云南花灯胯关节的“扭”—安徽花鼓灯腰部的“晃”—东北秧歌肋部的“提”,体态的重心从“胯”到“腰”再到“肋”,呈现随纬度升高,重心越高的特点。因此,不难理解“肉连响”与“拍胸舞”在显要部位动作的差异上,由于前者所在地纬度高,所以是高重心的腰部的“扭拧”,后者所在地纬度低则更突出低重心的胯部的“横摆”。此外,体态重心的高低差异进一步影响到大腿的屈伸幅度,在基本步伐上,“肉连响”吸跳步伐是主力腿半脚尖跳跃、动力腿吸腿及半脚尖先落地,“拍胸舞”为屈膝的全脚掌踏跺。前者腿部动作幅度大,动力腿大腿带动小腿完成吸腿,同时半脚尖的落地方式提高身体的重心;而后者屈膝,腿部动作幅度较小,并在全脚掌的踏跺中强调重心的下沉。“肉连响”与“拍胸舞”的显要部位动作、体态重心及基本步伐所显现的差异性,反映出鄂西与闽南两地生存环境中纬度的不同对舞体动作形态的影响。
2.生产方式的影响。生产方式是人顺应并改造生存环境的产物,是人类在生存、进化中最强烈、最持久、最直观的身体运动,它在下意识中促成人体运动的动力定型,在舞蹈活动中出现劳动动态本身[16]。鄂西“肉连响”流行地区由于拥有充沛的降雨、湿润的气候和利中盆地肥沃的土地,形成农耕为主,畜牧、捕捞为辅的多种生产方式。以农业劳动为主的生产方式,使得土家人在劳动中形成习惯成自然的人体动态,在农业种植中形成腰部的扭转动态,在田埂间行走中形成脚下左前、右前、左后、右后交替方位、移动重心的步伐动态,在泥泞的乡间小路行走中形成抬脚拔泥、交替吸腿、身体重心上提、主力腿半脚尖跳跃的步伐动态。这些“习惯的动”反应在“肉连响”中,即形成腰部扭拧的显要部位动作及秧歌步、吸跳步的基本步伐。闽南泉州“拍胸舞”主要流行区域位于闽南沿海平原,渔业与农业在此地并存。闽南人自古就开始了对海洋的探险之旅,宋元时期更是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频繁的海上生活,使闽南人在船上行走、劳作中逐渐形成屈膝蹲裆状态下胯部的左右交替,以及有助于保持平衡稳定的强度向下动势的踏步跺脚动态。这些“习惯的动”反映在“拍胸舞”中,即体现为胯部横摆的显要部位动作及屈膝蹲裆的踏跺基本步伐。
3.生活习俗的影响。生活习俗是生产方式的自然延伸,生活习俗对人体动态影响最为直接和显著的莫过于衣饰习俗,能够给予运动人体某种限制或某种炫耀[12]288。服饰的裸露部位往往影响着舞动的显要动作部位[5]110-111。“肉连响”与“拍胸舞”在服饰上都以上身赤膊、下身短裤和赤脚为服饰特点,因此,在舞动中都伴有对身体裸露部位的夹击或拍打。但二者在服饰中的重要区别在于, “肉连响”头饰原为土家族头巾,后逐渐省略头饰,而“拍胸舞”头饰为蛇形草编头圈,并延续至今。20世纪80年代,“肉连响”舞者还以传统的土家族日常生活头巾为头饰,而随着头巾在日常生活中的消失,现在头巾已不再是其舞蹈服饰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简化为一条细细的红绑带或无任何头饰。而“拍胸舞”,不论是其“准自然”形态、“衍生”形态或“再生”形态,蛇形草编头圈都是不可或缺的头饰。相比较而言,“拍胸舞”的蛇形草编头圈更为重要,极具装饰性和造型性,因此,“拍胸舞”头部的横摆晃动成为区别于“肉连响”的显要部位动作之一。
(二)社会人文因素
于平认为,舞蹈动态中经由人对自我身体动态的意识修正产生的规范化、典型化的非自然人体动态,以及经过自觉操练的有意识行为,即“练习的动”,主要受到社会生态因素的影响,包括社会心态中文化样态(社会文化心理对舞蹈的选择)和文化流态(舞者对文化交流中不同文化的选择)的影响[13]。资华筠在《舞蹈生态学》中也提出,舞蹈与生态之间的交互作用是通过心理机制来实现的[5]108-110。社会文化生态中的图腾崇拜、宗教信仰、文化构成,通过对人的审美思维方式、审美心理、审美选择产生影响和制约,进而影响舞蹈的形态。
1.黑、白头巾与土家族服饰审美。服饰及头饰不仅是影响人体动态的生活习俗的重要体现,更是作为舞蹈的伴同物直接参与舞蹈审美活动,它的色泽、花纹、样式是舞体审美心理的写照。鄂西土家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服饰特点。土家族男式服饰的基本特色为:上衣“琵琶襟”,后来逐渐穿对襟短衫和无领满襟短衣,缠腰布带;裤子肥大,裤脚大而短,皆为青、蓝布色,多打绑腿;头包青丝帕或五六尺长的白布,绑成“人”字形或绑成圈形盘在双耳上方,露出头顶,巾头向下留于左边;脚穿偏耳草鞋、满耳草鞋、布鞋或钉鞋[17]。土家族服饰崇尚简朴,色彩简单大方,多选用给人以稳重、敦厚之感的黑(青)色,表达了土家人质朴醇厚、简朴素净的自然美学观。“肉连响”舞者在较长的历史阶段中以黑、白头巾包头,正是土家族的服饰特征及其自然美学观念的深刻体现。
2.蛇形草编头绳与古闽越族蛇图腾崇拜。闽越先民常年生活的闽地,古为蛮荒之地,河海相交、多雨阴湿、瘴雾弥漫,是毒蛇猛兽频繁出没的区域。蛇既能脱皮蜕变,又能窜突腾跃,水陆两栖,来去无踪,具有毒杀猛兽甚至有吞食人畜的威力。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闽越先民赋予蛇思维意识和超人的力量,把自身的生死祸福同蛇神联系起来,祈求蛇神灵的恩赐庇护,对蛇的恐惧心理自然而然演变为敬畏,逐渐形成了古闽越人以蛇为图腾的图腾崇拜[18]13-19。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阐释“閩”曰:“閩,东南越,蛇种。”[19]即东南方以蛇为图腾的部族。从闽地先秦时期的蛇形岩画和石刻、汉代有蛇形图案的瓦当和铜铎残片、宋代墓葬中的人首蛇身动物俑,到清代福建妇女黑蛇蟠卷状发髻和蛇昂首状的蛇簪[20],再到如今闽地漳州村民仍将蛇尊称为“侍公者”顶礼膜拜,以及南平地区至今保留“蛇王庙”、农历七月初七的“崇蛇节”,都是古闽越蛇图腾崇拜的遗风。蛇图腾崇拜深深融入了闽南民风和地域文化之中,并在闽南民间舞蹈中生动呈现。“拍胸舞”头饰蛇形草编头绳的传统制作方法是,将一条红色细布条与草混合编在一起形成一个圈为蛇身,额头前端立起昂首向上的蛇头,红色布条于蛇头中间露出,如蛇之吐信。康纳顿认为,服饰不仅能传递可被解码的信息,它实际也有助于通过影响身体的运动塑造性格[21]。 “拍胸舞”中头部装饰形态逼真的蛇形草箍,即是对自身身体形态的加工和修饰。“当宗教思想孕育了‘神’的概念时,舞蹈则用符号表示了祈求,宣布誓言,发出挑战与表示和解。”[22]舞者以头戴蛇形草箍配合身体胯关节及上身、头部的横向晃动,上身前后波浪式的“蛇腰”折动身体形态模仿蛇的形象以祈求神灵的保护,不仅以此加强祈拜的气氛,同时也强化其蛇图腾崇拜的文化认同,从而使蛇形草箍头饰具有了象征意义。
3.转动型“8”字圆与动态循环的简朴哲学思想。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艺术特性源自先秦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体系所塑造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23]。因此,可以说鄂西“肉连响”中手臂的“8”字划圆及腰部扭拧的划圆,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思想在舞蹈形态上的体现。发轫于农耕文化的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思想,主张天人合一,尚和谐、主平衡,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阴阳两面,阴阳的互相作用形成无所不在的运动态势。“8”字划圆的手臂动作及腰部扭拧,在对称平衡中一来一回,自然流转,形成一种“圆而返、返而圆”的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动势。“8”字划圆的运动路线建立在阴阳双方的互相作用所达到的渗透中,体现出一种互存互补、相辅相成的和谐统一之美,隐喻着“天人合一”、“和谐圆满”的哲学思想,与中国古代朴素哲学思想一脉相承。
4.折动型横摆与异域舞蹈文化。闽南“拍胸舞”以胯部横摆为主延伸至头部的横向晃动、上身前后波浪式的“蛇腰”折动的折动型动作流程,不仅体现了古闽越族蛇图腾的崇拜心理和人类的模仿本能、表现冲动,同时也与异域舞蹈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代,闽南泉州已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四大贸易港口之一;宋元时期,闽南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海上丝绸之路”带来了丰富的异域文化,多元宗教文化在泉州共存。其中,丰富的印度舞蹈文化作为印度教的伴同物随之传入闽南,与闽南民间舞蹈发生互动与融合。曾有考古学者发现,早在秦汉之前泉州已有婆罗门教遗物“大独石柱”[24],在泉州港口附近存在印度教祭坛遗址、奉祀婆罗门神的寺庙遗址和石刻[25]。泉州开元寺内有24幅浮雕图像,描绘了9个古印度教神话故事[26]。印度舞蹈善以“诸神”的意义起舞,开元寺大雄宝殿上更是供奉有翩翩起舞的“迦陵频伽”妙音鸟女神。印度舞蹈以腿部跨开、屈膝、出胯为特色,例如印度古典舞流派中的“‘奥迪西舞’,其著名的‘三道弯’和演员舞动时腰部的左右摆动”[27],强调出胯、横摆形成“三道弯”的体态特征,强调身体重心向下以及腰部和胯部的自然松弛,注重整个身体的协调表现力[28],这与“拍胸舞”中的重心下沉至髋关节的胯部横摆,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此外,“拍胸舞”上身前后波浪式的“蛇腰”折动动态,更是与印度古典美学中强调的线条美和运动中的体态美相一致[18]33。
综上所述,鄂西“肉连响”与闽南“拍胸舞”在基本节奏型、典型性显要部位动作及动作流程、舞意、服饰等典型性舞畴因子上相似中又存在差异,两者同属于我国连响文化圈,有着悠久的历史延续及相同的舞蹈功能,但由于播布区自然生活及社会人文因素的不同,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呈现出带有地域文化色彩的形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