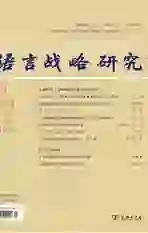汉语研究的当代观和全球观
2021-06-01游汝杰



提 要 改革开放以来的汉语可以称为“当代汉语”,当代汉语在语音、造词法、词类、句式和语言功能等方面与所谓“现代汉语”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全国各地还出现了大量“无方言族”。在当代汉语阶段,海外各地华人的民系结构及语言种类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汉语国际化的历史进程大大加快,同时由于海内外华人和华语互相接触、交流空前频繁,海外的汉语方言与国内一样,呈萎缩的趋势,世界各地华语差异逐渐缩小,有互相融合的趋势。研究汉语和制订语言政策和语言规范的视野也应该更加开阔,应扩大到全球各地的汉语及其方言。今后的汉语研究须有当代观和全球观。
关键词 现代汉语;当代汉语;海外华语;汉语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21)03-0086-11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307
Contemporary and Global Outlook of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You Rujie
Abstract Since the adop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Chinese language has seen many changes in its phonetics, vocabulary, grammar, syntax and social function. Chinese language during this period can be called Contemporary Chinese, which is different in many aspects from other periods. One of predominant changes in terms of its speakers is that a large number of them are speakers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 variety without any regional accent. In the perio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ructural change has happened in regionalects and hometown of Chinese diasporas across the world, speeding up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ese language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an unprecedent pace. Meanwhile, due to the unseen frequency of 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overseas Chinese, making various regionalects previously seen in different Chinese diasporas shrink even more rapid as what happened to dialects within China. All of these have caused eventual disappearing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languages spoken in different ethno-linguistical communities across the world, which signifies a tendency towards integration. In view of this, we should adopt a broader prospective in study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drawing up language planning policies such as standardization. We should include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ir dialects in the future vision and opt for contemporary and global outlook of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contemporary Chinese; overseas Chines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近年來对改革开放以来海内外汉语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大类。一是新词语词典,主要有:《新华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当代汉语词典》(中华书局,2009),邹嘉彦、游汝杰编著《全球华语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0),亢世勇、刘海润主编《新世纪新词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李宇明主编《全球华语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16)。二是综合研究,主要有:刁晏斌《新时期大陆汉语的发展与变革》(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新时期新语法现象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陈晓锦《东南亚华人社区汉语方言概要》(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三是有关“当代汉语”的定义、内涵和研究价值的专题讨论,主要有:游汝杰《当代汉语国际观》(“汉语国际化的契机和挑战国际研讨会”论文,2012,香港教育学院),刁晏斌《试论“当代汉语”》(《河北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还有些在研或已经结项的科研项目也涉及海内外当代汉语研究,主要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邢福义主持的《全球华语语法研究》(2011)、陈晓锦主持的《海外华人社区汉语方言与文化研究》(2014),国家语委科研项目:游汝杰主持的《海内外汉语使用情况调查》(2011)。这些项目都已有单篇论文发表。
上述成果为研究当代汉语打下了初步基础。笔者进一步思考这一课题,基本借助“中文各地共时语料库”(LIVAC),提出一些新观点,论述汉语研究不仅应有当代观,而且还应有全球观。
关于“华语”的定义和内涵,学界尚未形成明确的共识,故不宜单独使用“华语”这一名称。本文所谓“海内外汉语”相当于“全球华语”,包括普通话、地方普通话、台湾的“国语”、海内外各种汉语方言、新加坡的“华语”和海外其他华人社区的“华语”。
一、汉语研究的当代观
通常认为汉语的历史可以分为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三大时期,现代汉语以五四运动为起点,一直延续到今天。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的汉语可以称为“当代汉语”,当代汉语是汉语历史发展的新阶段。1979年是中国国运大转变之年,也可以说是当代汉语的开局之年。
当代汉语在语音、造词法、词类、句式和语言功能等方面有许多与所谓“现代汉语”不同的特点。
(一)新生的语音现象
1.零声母合口呼读唇齿音声母。如:新闻[v-]、为[v-]了、微[v-]笑。这3个字的声母,按原有的规范是读零声母的。《汉语拼音方案》虽然也有v声母,但规定只用于拼写外来词。此音是唇齿微触的摩擦音,用宽式音标记,即是[v],用汉语拼音标记只能是v。关于v声母,20世纪80年代曾有调查报告,但v声母大量出现是在近二三十年。
2.因外来词输入产生新的声母及音节。例如使用频率很高的常用词“拜拜”(bye-bye,再见)。《全球华语大词典》(第35页)注音为báibái[pai35pai35],但在口语实际读音中,声母读为双唇浊塞音[b]。普通话本来没有浊音声母[b],只有清音声母[p]。“拜拜”中的声母读作浊音[b],主要是受英语影响,是语言接触的结果,不限于方言母语就有浊音[b]的吴语区人。
3.用英文字母读音替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字母读音。《汉语拼音方案》的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不同于英文字母的读音,但基本不用。除n读“恩”外,其他字母一般都采用英文字母读音。
4.所谓“字母词”的读音也采用英文字母的读音。《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在给“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注解时说“在汉语中西文字母一般是按西文的音读的”(见1761页脚注),如:MBA、NBA、CCTV、VIP、B股。即使是汉语拼音缩写,如GB(國标)、HSK(汉语水平考试),也是“按西文的音读”。
新生的语音现象改变汉语的音系,例如新增[v]声母和来自英文的浊声母[b],这两个声母都是普通话所没有的。如果考虑字母词和汉语拼音字母通常采用英语读音,汉语音系的变化更是翻天覆地。英文字母读音中许多辅音、元音和音节都是普通话前所未见的。
(二)造词法的变化
1.许多社区词或方言词进入普通话,例如:
物业、按揭、打的、写字楼、企稳、高企、减肥(来自香港)
愿景、爆红、飙车、卡哇伊、蓝营、绿营(来自台湾)
打烊、头寸、黄牛、牛轧糖(来自上海)
忽悠、嘚瑟(来自东北官话)
粉丝、点赞、蛮拼、菜鸟(来自网络)
社区词是指仅在海内外某一地或几地华人社区流通的一类词汇,它们既不是普通话词汇,也不是方言词汇,是介乎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词汇(田小琳2007)。例如上海的“平改坡”(楼房平顶改为斜顶),仅用于上海地区,但不是上海方言词,上海地区的居民不管方言母语是不是上海话,都能听懂并使用这个词。目前上海居民中有约40%是外地人,他们的方言母语不是上海话。社区词有3个特点。一是社区词的使用不受方言母语的限制。同一社区的居民方言母语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但是大家都能听懂或使用社区词。二是用普通汉字而不是方言字书写,有相对固定的书面形式,通常见于当地媒体。三是大多是新词。网络是虚拟的社区,近年来大量产生的网络词,也可以说是社区词。美国华人社区词举例:洗笼(laundry洗衣店)、康斗(condo共有公寓)、布菲(buffet)、车拼(carpool)、分租(subdivision)、摩铁(motel汽车旅馆)、半土库(上半高于地面的地下室)。
2.用港台词替换原有词,或与原有词并用,例如:
公共汽车→巴士 奶酪→芝士 宇宙→太空
结账→埋单 李子→布冧 菠萝→凤梨
(→前是原有词,→后是港台词)
改革开放初期新词有近一半来自港台。不过近年来从内地产出的新词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多地被其他华语地区吸纳,如“忽悠、短信、博客、手机、互联网、山寨”,其情况与改革开放初期大不一样。
3.字母词大增,包括西文来源的,如B超、pose机、VIP、logo、WTO、CEO,和汉语拼音来源的,如HSK(汉语水平考试)、RMB(人民币)。《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所收“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有237个。实际上现有字母词多达1000多个。
4.新产生的外来词,倾向于音译,而非意译,如:丁克(dink)、克隆(clone)、优盘(USB)、博客(blog)、蹦极(bungee)、迷你(mini)、推特(Twitter)、美刀(U. S. dollar)。
5.出现一批新的构词后缀,例如:
族:上班族、月光族、傍老族、低头族
吧:书吧、陶吧、氧吧、话吧、网吧
秀:脱口秀、时装秀、达人秀、模仿秀
门:水门、电话门、翻译门、虐囚门、特工门
控:手机控、游戏控、零食控、收藏控
“门、秀”来自英语gate、show,“控”来自日语。作为构词成分“族”本来仅用于“水族、民族、种族”,“吧”仅用于“酒吧”,当年都还不是后缀。
(三)词类转化加剧
1.副词修饰名词,或名词形容词化,如“室内装饰很中国”“下午六点是最高峰”“这种牛奶很营养”。“中国、高峰、营养”原是名词,原有的规范是副词不能修饰名词。
2.名词动词化,如“病情严重,立即住院手术”“谁来一起午餐”。“手术”和“午餐”原是名词,按原有的规范不能直接做谓语。
3.形容词动词化,如“清洁城市,人人有责”“被高速(不得不乘坐高速动车)”。“清洁”和“高速”原是形容词,按原有的规范不能带宾语,或后置于“被”构成动词的被动态。
4.不及物动词及物化,如“联系我”“服务大众”。“联系”和“服务”原是不及物动词,不能带宾语,可能是受英语影响有了及物的用法,contact和serve在英语里是及物动词。例如:
contact(联系、接触):contact me;contact him by phone
serve(服务):serve my country;serve the people
汉语自古以来就有词类兼用现象,例如名词“书”可兼用作动词:“奋笔疾书,大书特书”,名词“树”可兼用作动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本文所说的是当代汉语新出现的词类兼用现象。初始阶段可能还只是临时活用现象,渐渐固化,并且词语搭配范围也渐渐扩大,成为词类兼用。例如“牛”本来是名词,或活用作形容词,只有“牛气、牛脾气”两词,现在可以单用,或词语搭配范围扩大,兼用作形容词:“他打败了所有对手,太牛了”“他是本行业的牛人”“牛市”“牛股”;“垃圾”本来是典型的名词,现在普遍兼用作形容词:“这人很垃圾”“垃圾食品”“垃圾邮件”。
(四)新生的句式
1.来源于粤语、闽语和南部吴语的“有+ VP”句式大行其是。例如:“他有说过这句话”“各大百货公司有售”“我昨天有喝茶”“你有没有去过世博会?有去过。”“饮料有需要吗?有。”。蔡瑱(2009)曾在上海大学生中调查过这样的句式可否接受,结论是“有+ VP”句在上海高校已广泛流行,具有一定影响,但还未达到盛行程度;其接受度、使用频率与年龄成反比,年龄越小的被调查者可接受程度越高;此外,答句中的“有+ VP”可接受的程度更高。
2.来源于南方方言的“V +不+ VO”已成惯用的句式。例如:
你吃不吃饭?/舒不舒服?
你知不知道?/喜不喜欢?
这种句式本来被认为是不规范的,规范的句式是“VO +不+ VO”,例如“吃饭不吃饭”。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新出现的语法现象,很可能是汉语与越来越普及的英语的语言接触的结果。例如前置于动词的“被”,原来倾向用于消极语义:“大树被台风刮倒了”,现在越来越多地用于中性或积极语义:“他被调去担任店长”“他被选为班长”。在英语里,被动语态在语义上是不分积极和消极的。
(五)语言能力和语言功能的变化
普通话和方言双语人已占全国人口大多数。普通话在社会生活中的高层语言地位确立,方言呈衰落态势,方言原有的特征减弱,方言的使用频率下降,方言人口萎缩。方言渐成仅用于私人场合的低层语言。
据调查,江苏江阴老中青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仅使用普通话的占22.68%,其中青年人占比最高,达33.38%。老中青居民总平均使用江阴话的比率为53%,而使用普通话或普通话和江阴话兼用的比率高达47%。同时语言态度的调查结果表明,江阴人喜爱普通话的程度远远大于江阴话(刘俐李,侯超2013)。
我们曾在上海一所中学做过抽样调查,调查的对象是初一年级学生,共45人。调查结果发现,在学校里,70%~80%的学生只使用普通话,不讲上海话,15%~20%的学生上海话和普通话都使用,没有只说上海话不说普通话的学生;在家里,50%~60%的学生兼用上海话和普通话,仅20%~30%的学生只使用上海话,10%的学生使用普通话或其他方言。
在上海这个言语社区里,目前的现实是:普通话是通用语言,也是高层语体(high variety),通用于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领域,如公务会议、公文、学校教学、学术会议、电视新闻、出版物、公共交通、高级商务等;上海话则是低层语体(low variety),一般用于市民日常生活和家庭生活,在确认对方会讲上海话的情景下也可能使用。
配对变语调查(matched guise technique)结果表明,上海人对普通话的印象分比方言高,不管性别、地点和项目如何,结果都一样。这说明上海人的语言态度比较倾向于讲普通话,换言之,现在普通话的地位在上海人的心目中比上海话高(钟雯晶,等2009)。上海的大中学生认为上海话好听或比较好听也仅占51%(蒋冰冰2006)。
(六)无方言族形成
当代出现了不少普通话母语人,即从小只会说普通话,不说任何一种方言,可以称他们为“无方言族”。无方言族是一个新的语言群体,最初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当年的中国大陆处于工业化的初期,全国各地出现许多新兴的大型工矿企业和工业区,职工大多来自外地,甚至全国各地,他们各自的方言与本地方言及普通话互相接触,逐渐形成在本企业或本地通用的普通话的变种,这种混合型的语言定型之后,传给下一代,就形成最初的无方言族。例如,杨晋毅曾调查研究过河南洛阳工业化初期的語言接触(杨晋毅2007),洛阳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等工厂的职工即是无方言族。部队家属大院、高校家属宿舍区等言语社区也是无方言族诞生的温床。
不过无方言族的大量产生,还是在最近二三十年。由于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大规模流动、普通话强势普及、方言渐趋衰微,无方言族在各大城市大量产生。无方言族的自然母语是地方普通话。所谓“地方普通话”,旧称“蓝青官话”,由来已久,它是各地方言与普通话接触的产物,是带有方言色彩的普通话。地方普通话在初期只是人们学习目标语(普通话)的中介语,不是人们的自然母语。但是近二三十年来,它渐渐成为许多青少年的自然母语或最初学会的语言。例如,2007年对394位南昌人的一个抽样调查表明,自然母语为普通话的青少年,高达68.2%(胡松柏,张向阳2007);2012年对124位太原人的一个抽样调查表明,自然母语为普通话的青少年高达83.9%(劲松,马璇2012)。
各地无方言族的语言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第一,群体性。无方言族的语言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一群人共同使用的内部系统一致的语言。例如方言区某一个城市的大部分青少年。
第二,世代传承性。无方言族语言不同于在言语交际中临时使用的语言,如洋泾浜语、中介语,而是无方言族的自然母语,具有世代传承性。以前的地方普通话是在某些场合临时使用的语言,没有世代传承的特点,世代传承的还是方言母语。
第三,集体偏误性。无方言族的语言是方言与普通话接触并混合后形成的带有方言特点的普通话,是使用某种方言的人学习普通话过程中集体偏误的结果。例如太原市无方言族的语言特点如下:普通话[t?]组声母读[ts];普通话[?u]韵母读[u];古入声字读太原话入声的21调;普通话的前鼻音韵尾[-n]读后鼻音[-?];普通话零声母读[?-]或[?-];普通话合口[u-]读[v-];普通话高平调(阴平)读低平调(劲松,马璇2012)。
最典型的无方言族语言是台湾的“国语”。台湾的“国语”是带有闽语和吴语特征的普通话,已经传承了好几代。据笔者对385位台北大学生的调查,在家庭聚餐时有85.94%的人最常用的语言是“国语”(游汝杰2015b)。据20世纪90年代对267位台湾人的抽样调查结果,有71.5%的人最先学会“国语”,同时有85.7%的人的自然母语是“国语”(黄宣范1995)。它有如下特点:少卷舌音;少儿化音;少轻声;普通话声母[f]常读成[h];用“有+动词”表示经历体或过去时;有大量不见于普通话的词,约5000条。
无方言族的语言具有地方普通话的性质。地方普通话兼有普通话和方言的特点,但我们认为它是普通话的变体,而不是方言的变体。它的音系结构是普通话的,而非方言的。从可懂度来看也很明显,例如,一个人可以听懂广东普通话,但完全听不懂广东话。
第四,社会方言性。地方普通话虽然有地域方言的色彩,但它不是语言分化造成的地域方言,而是标准语和地域方言混合的结果。在地理分布上,与地域方言的境界线不一定重合,例如台湾的主要方言有闽南话和客家话,它们各自分布在不同区域,而台湾的“国语”使用于整个台湾岛,与闽客方言的境界线无关。在大陆,目前地方普通话主要在大中城市使用。总之,地方普通话是一种社会方言。
地方普通话是一个总称,各地的地方普通话,往往可以用“地名+普通话”称之,例如“广东普通话”“上海普通话”;有的地方普通话已有专有的名称,例如武汉的“弯管子普通话”、台湾的“国语”、新加坡的“华语”。
就世界范围来看,从15世纪开始,历史语言学的谱系树分化模式就基本中止了,此后弱势语言陆续大量消亡,或被强势语言取代,这是不可避免的(Dixon 1997)。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当代中国许多语言或方言几乎已经消亡或处于濒危状态,例如满语、畲话。由于普通话的强势推广和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推进,普通话正在逐渐代替方言,成为很多地区居民的自然母语。据1999年统计,全国已有8%的居民以普通话为自然母语。
自15世纪以后,就不再有因语言分化而产生的新语言,新语言都是因语言接触而产生的。目前大家提到的这些新语言有以下几种:混合语、混合方言、过渡方言、变异方言、柯因内语、克里奥尔语等。那么,作为地方普通话的无方言族语言属于哪一种呢?
地方普通话最初是各地方言使用者学习普通话的中介语,是学习普通话过程中集体偏误的结果,在语音结构上处于方言母语和普通话目的语的中间状态。一旦定型并且成为一群人的自然母语,它就不再是中介语,而是一种新的语言变体。其情况与众多海外英语相似,例如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最初也是学习英语的中介语,经世代传承,已经成为因语言接触形成的新的英语变体,现在不会有人称之为中介语。
地方普通话是标准语和各地方言混合而成的,它不是标准的普通话,也不是方言,更不是混合型方言。所谓混合语或克里奥尔语是由不同语言混合而成的,故与地方普通话无关。
二、汉语研究的全球观
“汉语研究的全球观”意谓从“汉语国际化”的观点来观察和研究汉语。“汉语国际化”是指汉语从中国本土走向海外、国外,乃至全球。汉语国际化主要有三大途径:一是华人的海外移民运动;二是汉语与外语的接触;三是汉语的国际教学与传播。
汉语国际化由来已久,近几十年来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一历史进程大大加快了。近20年来海外的汉语教学蓬勃发展,包括兴办越来越多的孔子学院,也使汉语国际化如虎添翼。
长期以来,对于“现代汉语”研究,许多学者的眼光仅仅局限于中国大陆的普通话。例如大陆高等学校中文系所使用的各种《现代汉语》教材,几乎都只是相当于普通话教材,其内容不包括汉语方言和海外汉语及其方言,或者甚少涉及。我们认为,从国际化的观点来看,当代汉语应包括海内外各地的汉语及其方言。研究的视野也应扩大到全球各地的汉语及其方言,特别要加强海外汉语及其方言的本体研究和使用研究。其研究成果将对语言接触、双语现象、语言教学等多个领域大有学术价值。
(一)海外华人社区分布及其民系结构变化
海外各地华人的民系结构及语言种类40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非广东人、福建人和客家人近30年来大量移民海外,改变了海外华人人口的民系结构。
据198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朗文出版社),汉语分布于全球五大洲(亚洲、大洋洲、美洲、欧洲、非洲)近200个华人社区,华人人口2300多万,其中讲粤方言者最多,约1100万。改革開放以来大量中国人移居海外,海外汉语人口数量、民系、语言种类、共同语、社区等又有了很大的变化。据维基百科(Wikipedia)2016年的资料,海外华人总数为40 777 447。增加了许多新的华人社区,例如意大利中部的普拉托(Prato),是温州人聚居的城市,他们绝大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新移民。而许多老的华埠,人口和语言也处于消长变化的过程中。以纽约为例,据维基百科2012年的统计,其华人的总人口为735 019,最大的3个华人聚居区是法拉盛(Flushing)、布碌仑(Brooklin)和曼哈顿(Manhattan);法拉盛华人人口已经超过曼哈顿,成为全美最大的华人聚居地。纽约华人原来以台湾人为主,香港人次之,近年来大陆人数量已超过港台人。
(二)海外华人语言种类结构的变化
广东话传统上是美国华人聚居区占统治地位的语言,但近年来受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共同语——普通话的挤压,有边缘化倾向。在海外各地都有普通话替代粤方言、闽方言、客家话等成为强势语言,并进一步成为海外华人社区的共同语的倾向。改革开放以来移居海外的中国大陆居民,把普通话带到海外,极大改变了海外华人的人口结构和语言种类。海外华人社区没有语言文字政策,普通话与各种方言和当地语言自由竞争,普通话在华人中的共同语地位越来越明显。简体字与繁体字自由竞争,简体字渐趋流行,但是目前还是繁体字占优势,竞争结果如何,还有待时日。
海外华人的语言使用情况,总的趋势是汉语方言母语使用频率缩减,渐趋衰落,华人后代多以当地语言为母语。但不同的社区情况也不尽相同。例如,据我们的抽样调查,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所谓ABC,American born Chinese),其第一语言为英语的比率高达61.97%;粤方言已缩减到17.61%;普通话的比率为16.20%,与粤方言相差无几。在泰国,华人使用的汉语主要是潮州话,但不管哪一代华裔,泰语的使用频率都大大超过潮州话,世代越久,使用潮州话的频率越低。全家在一起吃饭时最常用的语言是泰语,占79.64%,比潮州话的12.57%要高得多。即使在同乡会聚会时,潮州话的使用频率也只有29.58%,而泰语的使用频率高达50.83%。这是因为有很多华人已经不会说潮州话,只能说泰语(游汝杰2015a)。
(三)海内外汉语有互相融合的倾向
华语文及其背后的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千姿百态。因为受不同文化背景和政治实体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较少交流,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华语文。
海外华人社区汉语的方言口语以粤方言、闽方言、客家话和官话为大宗。口头上的标准语,所谓“华语”,是以这些方言为底层的普通话(或“国语”),相当于“地方普通话”。而书面语在遣词造句和语言风格上,除港澳外,大都类似台湾华语文。海外汉语标准语可以分为三大类型。
第一,香港型,即港式普通话,在北美称为“广东国语”。港式普通话是以粤方言为底层的普通话,不仅流行于香港,也流行于以广东籍华裔为主的华人社区,例如北美和欧洲。这些地区发行的中文报纸,如《星岛日报》,也有港式普通話的特点。
第二,台湾型,即台湾华语文。台湾华语文不仅流行于台湾,也流行于以闽方言华裔为主的华人社区,分布于东南亚等地,例如泰国,尤其是泰国北部。泰国的中文报纸也属台湾华语文风格,如“秉上将承诺参加公宴”。又如常用大陆已不用或少用的词,如“眷属、幼稚园、英乐(泰国前总理英拉)”。台湾型的华语文可以在海外发行的《世界日报》为代表。
第三,新加坡型,即新加坡华语。新加坡华语也是以闽方言为底层的普通话,不仅通行于新加坡,也可能流行于马来西亚。相比之下,新加坡的华语文不仅采用简体字,而且在遣词造句和语言风格上比较接近中国大陆的普通话,而台湾华语文有更大的独立性。在口语上,因受多元语言环境特别是英语环境的影响,新加坡华语水平普遍不及台湾,并且青少年有较多华语和英语夹杂现象。这与台湾和大陆不同,而与香港型较接近。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海内外的华人和华语互相接触、交流空前频繁。不同地区的汉语,特别是词汇,不仅互相竞争,同时也加速互相融合。
以下的定量分析基于一个语料库和两本新词词典:“中文各地共时语料库”(LIVAC,邹嘉彦主持研制),此语料库从1995年开始,每周定期采录北京、上海、香港、澳门、台北和新加坡六地主要报刊的语料;《21世纪华语新词语词典》(邹嘉彦,游汝杰2007),收录2000~2006年的新词1539条;《全球华语新词语词典》(邹嘉彦,游汝杰2010),收录2000~2008年的新词1602条,其中单义词1450条,多义词152条。
这些新词在各地区的使用频率见表1。
“各地通用”占36.5%,在8类中百分比是最高的,而“各地通用”的新词最初几乎都只是仅仅流行于一两个地区,逐渐变成各地通用。这说明各地华语新词有互相融合的倾向。例如“方便面”最初在各地共有7个相对应的词:方便面、即食面、泡面、快熟面、速食面、熟泡面、公仔面。到了2008年,“方便面”已成为北京、上海、澳门、台北的最常用词,香港、新加坡的次常用词。
单用百分比最高的是“大陆”,占28.0%,这说明大陆内部的一致性比较高。大陆和香港合用的占11.5%,高于大陆和台湾的合用率7.0%,这说明大陆与香港的融合度高于大陆与台湾的融合度,也间接说明当前香港的社会生活比台湾更接近大陆。仅在某一地使用的新词,除大陆外,以台湾最多,占总数7.5%,高于香港的5.6%和新加坡的3.0%。这说明在各地华语中,台湾的独立性最强,融合度最低。地区词合计占63.5%。
以下以“手机”和“互联网”为例,进一步详细说明各地新词逐年互相融合的倾向。
“mobile phone”1995年以来在各地一共有10种说法,即流动电话、手提电话、行动电话、随身电话、移动电话、无线电话、大哥大、手机、手持电话、携带电话。在2001年之前,这10种说法都还是地区词;从2002年开始,各地最常用词则都以“手机”占绝对优势,从而进入民族共同语词汇。见表2。
Internet在各地共有9个对应词:国际联网、网际网路、互联网络、互联网、信息网、交互网、网际网络、递讯网、因特网。每一个词都用于两个以上地区。这9个词互相竞争的结果,是“互联网”取得明显优势,在各地出现的频率逐年提高,从2000年开始,除台湾仍坚持使用“网际网路”外,其他地区的最常用词己趋于一致使用“互联网”,京沪两地“互联网”与“因特网”的使用比率也从6∶4,渐变为7∶3和8∶2。到2001年,“互联网”在北京、上海、香港、澳门和新加坡5地都已高居首位,只有台北“网际网络”最常用,“互联网”是次常用词。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2005年。见表3。
blog大陆历年来只用“博客”一词。台湾译名“部落格”历年来为台湾最常用词,但从2005年开始,“博客”就已成为台湾的次常用词。“博客”也是香港和新加坡的最常用词。类似的还有“电邮、短信、给力、达人、山寨、超女”等从大陆扩散到海外各华人地区。与改革开放初期比较,当代华语新词原创地有北移的趋势。
我们曾在上海、香港、台北和美国东部四地抽样调查30多组外来词的使用情况,调查结果表明外来词也有互相融合的趋势。
从对香港外来词的调查结果来看,与大陆有融合倾向,例如:salad原称“沙律”,今又称“色拉”,占22.5%;sandwich原称“三文治”,今又称“三明治”,占36.5%;chocolate原称“朱古力”,今又称“巧克力”,占39.9%;ice-cream原称“雪糕”,今又称“冰淇淋”,占35.0%。这些词的原称为“最常用”,今称为“次常用”。与大陆、港澳和北美比较,台湾的外来词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也有与大陆、香港融合的趋势,例如“手机”在各地都是最常用的,“迪士尼”在港台都是最常用的。台湾次常用词与香港最常用词相同的有:的士、菲林、沙律、高球;次常用词与大陆最常用词相同的有:奔驰、光盘、迪斯科、摩托车、迪士尼、程序、服务器、黑客、博客、宇航员。
四地最常用和次常用外来词的使用频率互相接近率见表4。计算方法如下:列出每两地每一个外来词的最常用和次常用形式,计算它们在每一地的使用频率的平均值,將每两地的平均值相加,除以2,即得出这两地的接近率。
从上表看,美国东部与上海的接近率是最高的,达到45.87%;其次是与台北的接近率,为43.54%。从美国东部看,中国大陆的外来词形式具有更强势的地位。美国东部和中国大陆都是最常用的有:停车(park)、光盘、迪斯科、摩托车、胶卷、奔驰(Benz)、服务器、黑客、博客、快递、高尔夫、网络电话、短信、优盘。
当代汉语阶段,社会变革剧烈,普通话媒体高度发达,人口流动频繁,包括方言区内部的人口迁移和跨方言区的人口大规模流动,这些因素造成普通话越来越强势,方言向普通话靠拢,方言的原有特征减弱,使用频率骤降,不同方言趋同,方言的地理界线渐趋模糊。这种种现象都显示汉语正在经历急剧的变化。研究急剧变化中的语言,除了可以使用传统的方法之外,更需要采用社会语言学的多人次采样调查方法、定量分析方法,来研究语言变异和语言使用情况,研究海内外汉语都应该如此。
三、结 语
语言的演变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社会的剧烈变革会引起语言的急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汉语及其使用功能和全民的语言生活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汉语的发展史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汉语可以称为当代汉语。当代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语言功能等方面都有不同于现代汉语的发展变化。
在当代汉语阶段,汉语国际化的历史进程大大加快了。海外的汉语方言与国内一样,呈萎缩的趋势。
在当代汉语阶段,世界各地汉语差异逐渐缩小,同时又有互相融合的趋势。
研究汉语和制订语言政策和语言规范的视野也应该更加开阔,应扩大到全球各地的汉语及其方言。
总之,今后的汉语研究须有当代观和全球观。
参考文献
蔡 瑱 2009 《上海高校学生“有+ VP”句使用情况调查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胡松柏,张向阳 2007 《南昌市“普通话母语学生”的语言状况调查》,《中国社会语言学》第2期。
黄宣范 1995 《语言、社会与族群意识》,台北:文鹤出版有限公司。
蒋冰冰 2006 《上海市中小幼学生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分析》,《中国社会语言学》第1期。
劲 松,马 璇 2012 《“非方言族”对本地方言使用和发展的影响》,《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
刘俐李,侯 超 2013 《江阴方言新探》,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田小琳 2007 《规范词语、社区词语、方言词语》,《修辞研究》第1期。
杨晋毅 2007 《中国工业化初期的语言接触和语言选择——以洛阳市的语言使用情况为例》,载《中国首届人类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游汝杰 2015a 《泰国潮州籍华裔语言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海外华文教育》第1期。
游汝杰 2015b 《台湾大学生语言使用状况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
钟雯晶,许纯晓,徐媛媛 2009 《上海市民语言态度的配对变语调查》,载《语文论丛》第9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邹嘉彦,游汝杰 2003 《当代汉语新词的多元化倾向和地区竞争》,《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邹嘉彦,游汝杰 2007 《21世纪华语新词语词典》,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邹嘉彦,游汝杰 2010 《全球华语新词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Dixon, R. M. W. 1997. The Rise and Fall of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王 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