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不进文章的事儿”
2021-05-30谢其章
谢其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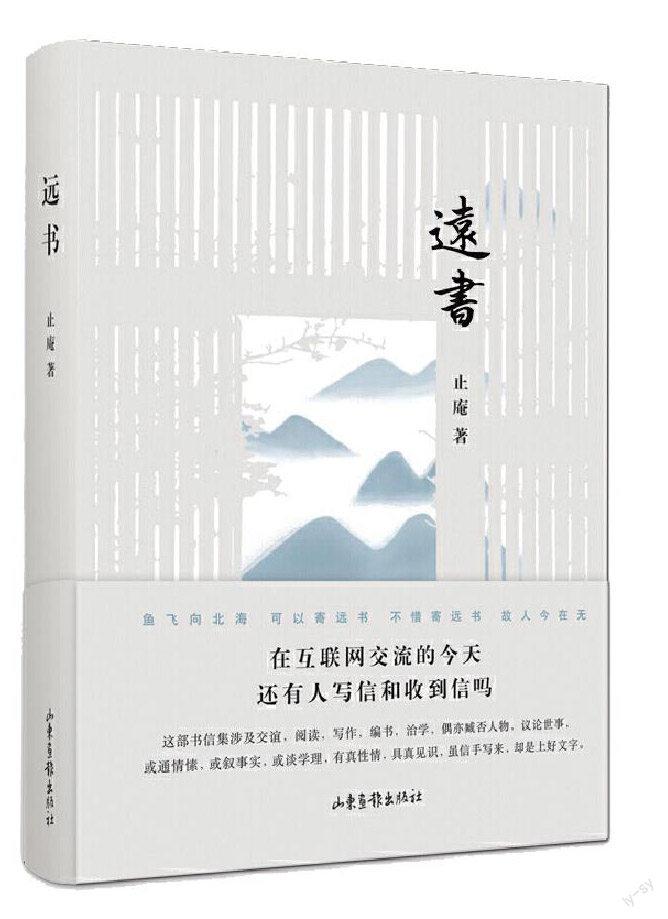
这几天在读止庵增订版《远书》,收获颇多感想。谈正事之前先来说说“我与信”的一些小故事。
平生写第一封信的时候约八岁,小学生,信是写给远在青海工作的父亲,记得第一句是:“爸爸,您好。我现在是在家里的写字桌靠左边的那个角上给您写信。”十八岁去农村插队之后.写信成了经常的事。我是天生拘谨的性格,可是写起信来似乎换了个性情,真的见了面,又回归到不会说话的样子。有一回给表哥写信,满纸热情洋溢,二弟在一旁说,别写得那么热闹,回头见了面又不知说什么了。常言“文如其人”,也许有道理,可是若说“信如其人”,在我这就通不过。
家书之外还有一种信(情书),现在自己可以交待一二。情书分两种,一种是鲁迅许广平那样的“你有情我有意”式,还有一种是单相思式的吧。现在来说说后一种,其实前一种我也写过,但是后一种更需要勇气。返城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服务行业,总店下辖十几个分店,每个分店都有一两个模样俊俏的姑娘,当然逃不过“男大当婚”的我们在背后有关“环肥燕瘦”的议论。我中意的一位与我不是一个店的,一句话也没说过,偶尔在食堂相遇,也没有搭讪的勇气。有一天,不知哪里来的一股邪胆,奋笔疾书,听着《在那遥远的地方》,写就一纸情书。第二天中午,骑着自行车,来到她的店,她正和几个店员在后面休息,我叫了一声“赵华”,就把信当着众人的面递给了她,然后扭头就走。那十几秒钟永远定格在我惨淡无华的青春上边。
后来怎么着了,结果呢?你我都不要忘了那可是上世纪70年代,风气未开,搁现在屁事儿不是的情书,“赵华”竟然像舒芜似的“上交信件”了!灰头土脸的我,经受住了沉重一击,两年后在本店交到桃花运,如今和“店花”已逾“珊瑚婚”。可笑的是,当年老妻和“赵华”人家都说长得很像,经常被混为一人。我成家之后,某年在三里河碰到了“赵华”,她带着孩子过马路,她孩子长得比我闺女可差远了。到了这把岁数,风清月朗之夜,回首往事,无端想象“赵华”会不会后悔“上交信件”?她看到电视上后来的我,也许早认不出来了。
止庵致史航信中说到舒芜,“随着时间流逝,大家印象中‘舒芜在胡风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似乎只剩下‘上交信件了,然而他在文章中对这些私人信件所做的摘录、分类、编排、注釋、解说,一并构成完整、周密、足以致人死地的构陷,这才是我们更不应当忽略或遗忘的东西。”“我平生尝与某些人趣味不合,意见不合,乃至笔墨相讥,但唯一对一人深感恐惧,且极厌恶,那就是舒芜。“(2018年4月19日)
这两段话,第一段可以写进公开发表的文章里,第二段不宜写进文章里,这就是书信的特殊作用。止庵深谙此道,《远书》里处处运用自如,存乎一心。致谷林信中有云:“张中行写赵丽雅的文章早读过,私心不甚以为然,不过也是人各有其特色。我虽作文多年,但平生最不喜文人习气。”(1997年9月4日)“张中行亦为我所尊敬,然稍嫌写得多了些,出书更多,书中篇目一再重复,为我这种爱买书的人所不免惋惜。”(1996年3月30日)致李君维信中有云:“余斌著书早已早已看过,即如先生所说,当得起严肃认真之评。只是有关《传奇》一章较为肤浅。后来重印,似乎未改。关于张、胡关系,目前所见资料,皆为胡氏提供,大家引述之后,反倒再来骂他,此点于理难通。须得另找旁证才行。”(2002年2月27日)面对谷林李君维二老前辈,看得出止庵的措词使字还是留有余地的,如“不免惋惜”之类。
《远书》里有句话很厉害,“我不满的是如今‘左已不时髦,而其犹持‘左论。”对于这观点笔者另有看法,前辈左不左事小,后生代左不左事大。请看这位后生才俊的一番话:“关于其装帧,也略有文人意趣,我唯一不满的是《立春前后》的封面,用了山人的一株老梅。八大是不与新朝合作的遗民,梅是传统上高洁的象征,我不是要纠缠于知堂的附逆,但总不能把这幅画给他吧。"(2005年3月23日致谷林)读了这番怪论,我真的很蒙圈,很想对才俊说,您还不如直来直去“纠缠”知堂呢。八大山人三百多年前随手画了一枝梅,图书美编三百多年后随手用在封面上,这就好比八大穿越时空赠梅给知堂,知堂“知惭愧”,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
另一位才俊也有一番与上一位才俊异曲同工的妙论,“承示《南方都市报》上《周作人佚文〈庸报新年志感〉》一文,粗读一过,作者对于周氏以及当时情形多强不知以为知,如云:‘须知江朝宗时任伪北平市长,表达了日伪政权对周作人这篇文章的重视。……这样的‘微言大义,自然要受到日伪政权的重视,无怪乎伪北平市长江朝宗也不免亲为此文题名,大张其鼓地刊印于版面头条了。按,周氏发表此文的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江朝宗旱已不是北平市长,一九三八年初该职务即由余晋龢接替,此后北平也改称北京了。”(2017年8月2日致老谢)“强不知以为知”也就是大白话“不懂装懂”,是一种化了妆的左论。
有的地方,我嫌止庵过于“掰开了揉碎了”,甚或执意“乃‘泰行耳”也不愿“输一东道”。如这封信里的一段,“序言:‘周作人因为许寿裳回忆文的偏向鲁迅而对其心怀不满,这才有意歪曲许寿裳文意,止庵先生不察,完全接受了周作人的歪曲,恐怕难免也有感情因素在起作用。按,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一节说法,多有错谬,我在传记的注释和别的文章中都曾指出。此处用‘外宾,无论如何是不对的——借用先生的话,这里倒是许氏‘恐怕难免也有感情因素在起作用——其引起当事人之一的反感,亦属难免。”(2009年6月20日致汪成法)
又如,“对于您的批评,我想略作解释,虽然不无自我辩解之嫌,请您谅解好了。其一,关于‘言必称知堂。我写文章,不外几项内容(其他的不懂,或仅一知半解,故不谈),其中只是涉及思想与文章者,偶尔引述知堂的话而已。……其二.关于‘好像越来越只重理趣一路,完全舍却了情趣一路。盖年龄渐长,有此变化,或亦属正常。”(2004年10月24日致江慎)“言必称知堂”与上信“恐怕难免也有感情因素在起作用”均属胡猜乱疑,这顶帽子也不妨扣往“言必称张爱玲”的陈子善、“言必称老舍先生”的舒乙,乃至天下所有“言必称某某”者头上。
又如,“承赐下大作一束,已拜读。吾兄勤奋好学,弟颇感佩服。惟有时下断语稍过,如:‘石民恐怕一般读者都已经不知道了,他的著作现在也见不到了。'(《想起被遗忘的诗人石民》)‘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学者恐怕都不知道朱英诞是谁,作为一个诗人,这是他的悲哀。(《记住诗人朱英诞》)皆是也。”(2008年5月21日致眉睫)“一般的读者”有必要知道或记住连“学者”都不知道的诗人么?古往今来人们只知道李白杜甫那么几个诗人,其余万千诗人只有“悲乎哀哉”一途。许许多多现代文学研究者们,特别喜欢用这种题目和这种句式,像传染了重感冒,吃啥药也不管用,除非不干这一行。
读《远书》,要说令人舒心痛快,还要数止庵那几通“立此存照”(“昔日鲁迅以‘立此存照为题写过几组文章,素所爱读,不妨效仿先贤,费神抄与老兄。”)如止庵抄了《南渡北归》里令人绝倒的一段,“就在彼此打得难解难分,成一团麻花时,蹲在白山黑水间的奉系军阀张学良,在蒋介石夫人,绝色美人宋美龄亲往其密所摇动三寸香舌和施展周身招数连番规劝、蛊惑、利诱下,张氏原本因吸食大麻而蔫儿吧唧的身子骨儿,如同每日注射的杜冷丁药力发作,突然稀里咔嚓响了起来,屁股开始由发热到发烫,随着脉管血液喷流蹿腾,密布的毛孔迅速扩张炸裂,细黄的汗毛如同霜打茅草在酷寒的夕阳中根根直竖。阵阵香风吹拂中,张学良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澎湃如涛的激情,在蒋介石与阎冯联军双方死伤达到30余万仍难决胜负的关键时刻,突然‘嗷叫一声蹦跳而起,于宋美龄放情的大笑与秋波含情的迷人眼神幻影中,抽刀拔剑,亲率20万东北军携枪架炮以虎狼之势入关助蒋。”张学良真够走背字的,生前,被马君武摆了一道,“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哀沈阳》其二)死后,又被岳南码了一道,诸如“绝色美人宋美龄”“三寸香舌”“秋波含情”“阵阵香风”云云,可谓前有胡蝶后有宋美龄,少帅多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