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斐多篇》与《圆觉经》浅谈柏拉图与释迦牟尼灵肉观之共性
2021-05-28方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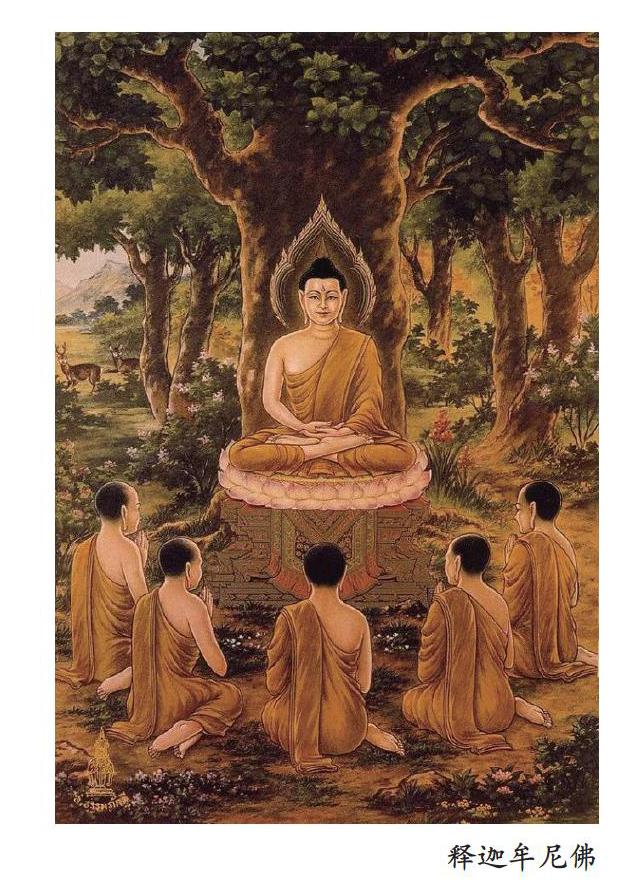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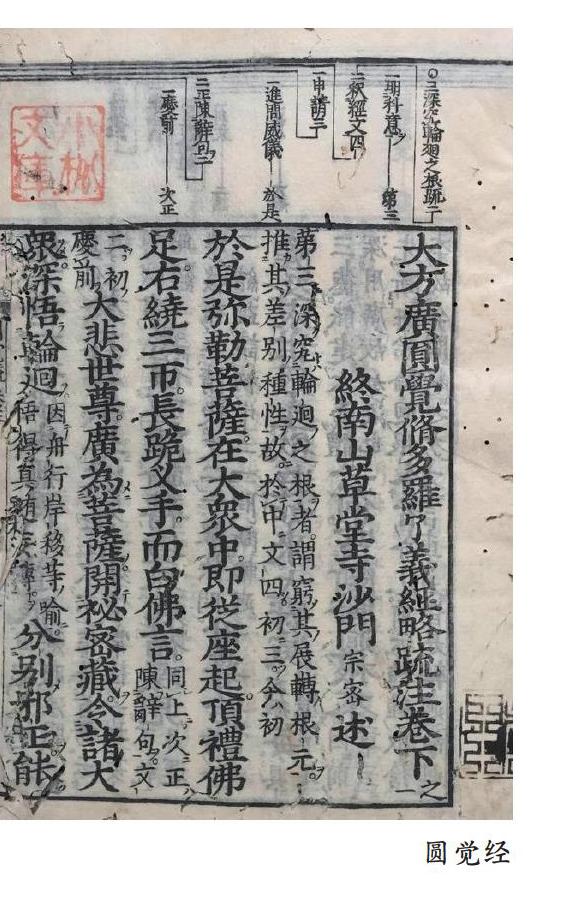
摘 要:《斐多篇》是古希腊哲学家、伦理学家柏拉图早期重要著作之一,而《圆觉经》则是大乘佛教的经典著作。两部作品虽然在时间、空间上都相距甚远,但在理念上也颇有一些共通之处。《斐多篇》讲述了亲历苏格拉底之死的斐多,向厄刻克拉底讲述苏格拉底死亡时的情景。文中出场人物虽多,但核心主要为苏格拉底与西米亚斯、克贝之间的问与答,从而对死亡、轮回、灵魂等问题进行论辩。《圆觉经》则采用释迦牟尼答十二位菩萨问的形式,对生起死灭、轮回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而又简明扼要的阐述。二者都以问答对话的形式为脉络,以举例例证的方式将难以捉摸的哲学难题化入到一个个形象的例证之中,以小例而见大理。而通过对比《斐多篇》与《圆觉经》的种种例证可见,二者灵肉理念都体现出由肉体所产生的诸种欲望与轮回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柏拉图;释迦摩尼;斐多篇;圆觉经
一
灵魂与肉体是柏拉图“二元论”世界的一部分。柏拉图认为,组成人的灵魂与肉体看似合为一体,实则彼此是一种相对立的存在,即“灵魂与身体的结合是一种‘堕落”。柏拉图在《斐多篇》中特别强调了灵魂的单纯性。当人的生命步入终点时,肉体会腐蚀消亡,而灵魂是不朽而永恒的。“灵魂不朽说”是柏拉图哲学中一个重要的理念。而由“灵魂不朽”则推论出“灵魂轮回”的学说。柏拉图在《斐多篇》中,为了说服人们追求净化灵魂的德性生活,避免因为贪恋肉体享乐所生出的诸种欲望而导致“堕落”,根据善恶相报的原则,创造了灵魂轮回的神话。那些理性而高尚的追求智慧的哲学家们,其死后灵魂必然能进入另一个圣洁之世界,与神灵以及其他的伟大灵魂共度美妙的时光;而那些只“关心肉体,爱这个肉体,迷恋着肉体,也迷恋着肉体的欲望和享乐”[1]54,在生的时候刻意回避那些无形无状,却需要理智、凭借哲学方能理解的理念世界,那么当他灵魂离开肉体的时候,就无法避免被玷污的结局[2]。《斐多篇》指出,世间冲突乃至战争的根源都是出于肉体和肉体的贪欲:“为了赚钱,引发了战争;为了肉体的享用,又不得不挣钱。我们都成了这类事情的奴隶了。因此我们便没时间研究哲学了。”[1]22柏拉图把肉体看作是灵魂的“牢笼”,“为了他们生前的罪过,罚他们的灵魂在那些地方徘徊。他们徘徊又徘徊,缠绵着物质的欲念,直到这个欲念引他们又投入肉体的牢笼”[1]55。这样的无尽“徘徊”,便生出轮回。由于欲念的污染,其生前为怎样的人,来世便转化为同样性质的东西,诸如狂荡不止口欲之人化为骡马、专横狂暴者化为鹰和狼等。因此柏拉图在《斐多篇》里多次论及,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是不会畏惧死亡的,因为高洁的灵魂终将与神灵共舞;反观那些被欲望玷污的灵魂,则“永远带着肉体的污染。马上又投胎转生,就像撒下的种子,生出来还是一个肮脏的灵魂”[1]59。这种欲望的轮回,便无始无终、无尽无休,不可解脱了。
在《圆觉经》里,释迦牟尼对欲望与轮回的关系也有着与柏拉图十分相似的阐述:“当知轮回,爱为根本。由有诸欲,助发爱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续。欲因爱生,命因欲有,众生爱命,还依欲本。爱欲为因,爱命为果。由于欲境,起诸违顺。境背爱心,而生憎嫉,造种种业,是故复生地狱、饿鬼。”[3]90-91释迦牟尼认为,一切众生都从无始际开始,“圆觉”本为众生之本性,但由“妄想执有我、人、众生及与寿命。任四颠倒为实我体”[3]50-51,于是生出如“空中华”的“我相”并执着于此,这个“我相”便会生出“妄心”,“妄心”而生出“爱”。当然释迦牟尼所说的“爱”,并不是狭义的情爱,而是爱“人”之爱,爱“物”之爱的广义之爱。而这种“爱”,便会生出诸种欲望,从而像眼中生翳一般被“幻”所蒙蔽,迷恋沉沦在各种欲中,导致贪恋肉体,贪爱生命,产生种种的贪、嗔、痴、慢、疑之“五毒心”,进一步生出许多业障。如果这些妄念前后相继而不断绝,便会循环往复永不停止,永远流转于生死轮回之中。“爱”生“欲”,“欲”导致“无明”而坠入无尽轮回。因此释迦牟尼认为,“爱”是轮回产生的根本,这和柏拉图的轮回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
在生与死的观念上,柏拉图认为,哲学家不会畏惧死亡,并且“真正的哲学家一直在练习死”。施杜里希在《世界哲学史》也提出,柏拉图的伦理学是从至善的观念中得出结论,不死的灵魂是人身上的那种能够使人参与到理念世界中去的东西。而人的目的就是通过使自己上升到超感觉的世界从而达到至善。至于“肉体和感性是阻碍人们达到至善的桎梏,用柏拉圖的话说就是:‘soma,sema(肉体是灵魂的坟墓)”。“德行是灵魂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灵魂接近于这个目标。”[4]柏拉图在《斐多篇》对此提出了一个形象的例证,即把苦与乐看作钉子,而这枚钉子把灵魂和肉体紧密地钉在了一起,使灵魂带上了肉体的欲望。因此,“凡是肉体认为真实的,灵魂也认为真实。灵魂和肉体有了相同的信念和喜好,就不由自主,也和肉体有同样的习惯、同样的生活方法了”[1]59。如果灵魂受到欢乐、惧怕、忧虑、肉欲等强烈吸引,把这些可以“感觉”得到的东西奉为真实。这种情况下所孕育出的灵魂,由于这类灵魂把“可见”错误的当做为真,并执着于这种“真实”,那么这种灵魂便带着肉欲无法分离,则无望和神圣、纯洁、绝对的本质进行交往。
而由于“可见”的错误认识所导致灵魂被肉体欲望玷污而无法解脱的结果,在《圆觉经》里也有重要的阐述:“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犹如迷人,四方易处。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譬彼病目见空中华及第二月。”“空实无华,病者妄执。由妄执故,非唯惑此虚空自性,亦复迷彼实华生处。由此妄有轮转生死,故名无明。”[3]35-37释迦牟尼常把“空中华”作为指代谬误的例证,提出“肉身”的东西,本就是地、水、火、风四大元素以及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相互合和形成的虚妄之物,而这虚妄的肉体由于“妄有缘气”,凭着这股“气”而生出“妄心”。由于这种妄心幻执,进而不仅把空中华当做虚空的自根或者本质,而且还看不出产生空中华错误的根源究竟在何处。把人世的可以看见、可以触及的事物当做真实的,由此衍生出种种欲望,从而无法脱离轮回,无法达到清静圆满的境界。
因此《斐多篇》里,在论及“真正的哲学家不会畏惧死亡”时提出,如果一个人恐惧死亡,并在临死感到愁苦,就证明他爱的并非智慧,而是肉体以及钱财权欲之类。而一般人的“自我节制”的修行行为,其节制并非出于灵魂上的追求,而是因为怕错失自己贪图的享乐,正如爱体面、爱权欲的人惧怕做了恶事被人发现而损失声誉,爱钱财的人惧怕贫苦而不去挥霍,这样的“节制”在本质上是:“他们放弃某些享乐,因为他们贪图着另一种享乐,身不由己呢。”柏拉图借书中苏格拉底之口对这种所谓“节制的修行”进行了驳斥。柏拉图认为,当人们把“美德”作为交易品时,舍掉小的利益,而用为此营造出来的所谓美德去换取更多的利益,这种“美德”,既“不健全”也“不真实”,实质就是奴性,这种充斥功利性的“修行”,其灵魂不会得到解脱,而真实是“清除了这种虚假而得到的净化”。因此《斐多篇》里提出,一切美德都只能用一件东西来交易,“这是一切交易的标准货币。这就是智慧”[1]27。
而《圆觉经》中释迦牟尼阐释修行中的谬误时,其理念竟然与《斐多篇》的观点高度契合。《圆觉经·净诸业障品》里,释迦牟尼解答净诸业障菩萨为何众生修行时,十分勤苦又经历诸多磨难,但还是无法得到“圣果”:
“何以故?认一切我为涅槃故;有证有悟名成就故。譬如有人,认贼为子,其家财宝,终不成就。何以故?有我爱者,亦爱涅槃,伏我爱根为涅槃相。有憎我者,亦憎生死,不知爱者真生死故,别憎生死名不解脱。”[3]161-162释迦牟尼解释为何众生难以成佛,就是因为“我相”。
南怀瑾在《圆觉经略说》对此有着深刻的解析:“你那清净境界、空境界、光明境界都是‘我所变的,我是什么变的?业所变的,业是心所变的,心是一念无明所变的,把这一念无明所变的我认为是涅槃,把我所变的清净认为是成佛的境界。”一旦修行者“认为一念不生清净境界就是道,这种看法就是贼,这正是‘业力的根本,永远不能成就”[5]311-312。由于执着于“我相”,便认为世间一切都为虚妄,唯有修行才是“真”,这种强行压制住肉体欲念的行为,实际上就犯了“修行四病”中的“止病”。看似是止住了欲念,实际上迷执于“涅槃”本身就是一种欲念,这和《斐多篇》的“美德交易”的论点遥相呼应:当人节制自身欲望而渴求涅槃,实际上是把修行当做一个交易的砝码,试图通过舍弃小欲交换终极目标的“商品”——“涅槃”。这样的修行者看似是克制了欲望,实际上心里怀着更大的妄欲,当修行者怀有这样的功利心时,便也落入“邪见”的桎梏,更罔谈得到圆觉正果。
三
由于肉体与灵魂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如何处理灵肉关系而得到诸如“去往另一个福岛安享极乐”“修成圆觉清静之境”一类的“解脱”,对于哲学家与圣贤也是一个挑战。《斐多篇》里阐述到,由于灵魂是不朽的,那么作恶之人即便肉体消灭,也不可能甩掉罪孽、逃避邪恶,也不能由其它任何方法得救,因此人们必须爱护自己的灵魂,“不仅今生今世该爱护,永生永世都该爱护”。而对于如何去爱护灵魂、拯救灵魂,《斐多篇》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那就是“爱智慧”,唯有智慧才能引导灵魂超脱出肉体所生的多种欲望。这是因为人的欲望把肉体与灵魂牢牢钉在一起,灵魂正沉溺于极端的愚昧的状态中。因此当热爱知识的人开始受哲学引导的时候,便会发现自己的灵魂完全是焊接在肉体上的。即便其灵魂渴望追寻真实,“却不能自由观看,只能透过肉体来看,好比从监狱的栏杆里张望”。
而通过哲学便会让人开明,认识到灵魂受监禁是为了肉欲,哲学会给灵魂鼓励与指示,并告知灵魂不要被肉体诸如眼耳等感官的感受所产生的欲望掌控而误入歧途。因此灵魂若要得到超脱,就要透过囚禁灵魂的肉体去分辨何为实体的假与抽象的真,“尽量离弃感觉,凝静自守,一心依靠自己,只相信自己抽象思索里的那个抽象的实体;其它一切感觉到的形形色色都不真实,因为种种色相都是看得见的,都是由感觉得到的;至于看不见而由理智去领会的呢,唯有灵魂自己能看见”[1]58。唯有这样,灵魂便可以摆脱污浊的浸染,回归福岛境界,与神灵相伴。
《斐多篇》里灵魂是被囚禁在肉体的牢笼里,唯有智慧能使灵魂超脱这个例证,在《圆觉经》也有着与之颇为相似的例证。释迦牟尼解威德自在菩萨的如何“定慧等持”之惑时,则提出了“器中锽”的理念:“了知身心皆为挂碍,无知绝明,不依诸碍,永得超过碍无碍境,受用世界及与身心。相在尘域,如器中锽,声出其外,烦恼涅槃不相留碍。”[5]189身体如器物,而“圆觉”则如一口钟被身体这个器物给牢牢拘禁着。因此,必须要通过觉悟心去进行思辨,“不取幻化,及诸静相”,不摄取诸种幻相和清静寂静的心相,便不会被这些迷障异引思维,就会永远超越障碍,明白何为“空”、何为“幻”,进入“碍而无碍”的境界。此时虽然身相与心相仍留在尘镜的“器”中,看似无法脱离而出,然而囚在“器”里的大钟所发出的激荡之声是可以超越“器”的禁锢而传到外界,“自他身心所不能及”而超越那人世间,进入“绝妙顺遂寂灭境界”之中。由此可以看到,《斐多篇》与《圆觉经》对于灵与肉所存在着不少具有相通性的理念,这对于我们研究“人”的学问,思辨哲学的终极三问等,颇具有启发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柏拉图.斐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M].杨绛,譯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2]冷桥勋,张慧.灵魂与统治 柏拉图政治哲学研究[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67.
[3]太虚大师讲述.圆觉经略释[M].台北:财团法人佛院教育基金会,2002.
[4]施杜里希.世界哲学史[M].吕淑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45.
[5]南怀瑾.圆觉经略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11-312.
作者简介:方馨,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写作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