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阿慧《大地的云朵》
2021-05-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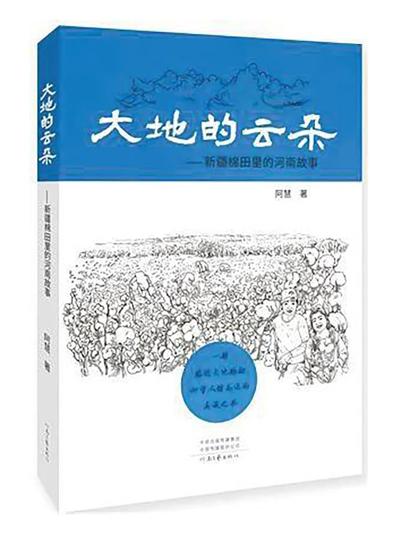
异乡劳动者的声音
刘大先
对于幸福生活不懈追求的信念无疑是人性中最为令人动容的部分。怀抱对于美好未来的向往,对于自我价值的实现,或者仅仅就是改善现状的冲动,驱使人们远离故土,行走在大地之上,寻找适合的机会,无论何种艰辛与苦难都无法磨灭与阻挡他们前行的步伐与行动的热情,从而显现出令人尊敬的崇高底质。这是一种生命意志的体现,不惟为精英阶层所拥有,而是体现于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上。
只是很多时候,那些身处生活底层的民众并没有机会在文字中呈现他们不屈不挠、顽强坚忍的品质,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泥土飞溅的大地上劳作,奉献出精力与收获,却面目模糊,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阿慧《大地的云朵——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就凸显出其难能可贵的价值:这个来自河南周口的作家,在2014年10月孤身前往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北疆棉区,从农六师新湖农场的四场八连,辗转到了六场二十八连,又雪夜奔赴玛纳斯六户地,深入到棉地之中,走访她来此务工拾棉的乡亲,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从而让那个无声的群体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那些异乡劳动者的声音不仅仅是河南的一个个鲜活个体的生命记忆,同时也表征着转型时代里的人们带有普遍性的生活旅程。
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阿慧采取了沉浸式的方式,即她将自己置入拾棉民工的生活之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参与式的观察与倾听中,记录下自己与书写对象的亲历亲闻与所想所感。这个过程中,她经历了从矫情和外来者的眼光向同情共感的局内人视野的转变,而没有变化的则是那敏感而开放的胸怀。这一点让她同那些走马观花的采风者区别开来,尽管整个采访的时间与旅程并不算长,但整个身心的投入却是真诚而深沉的。我们经常说作家要深入生活,不仅要身入,还要心入、情入,这个作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作者并没有避讳自己起初的无知和好奇,但是在与采访对象的接触中不断修正自己的看法与立场,最终与对象形成兄弟姐妹般的情感,而唯有如此才能打开彼此的心门。
正如阿慧在后记中写下的:“写作者要想获取生活的直接经验,必须把自己放置于他人的生活之中。”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它需要作者顶着烈日的暴晒,经受饥渴的煎熬,忍受冰雪中的苦楚,还要能忍耐不洁的气味、恶劣的环境,体验劳动的艰苦与对他人遭遇的情感折磨。在写法上,她以一个人的行走为线索,通过与不同人物的交往将他们的故事串联起来,与不同人物结识与交流的过程,也是作者本人认识与体悟逐渐深化的过程。
阿慧实地采访了五十六人,写到书中则有三十多人,无论性别,她都用一朵朵花对他们进行命名。他们有“微弱而不卑微,惜财而不拜金”、一心想抓钱的母亲,有屡遭情感挫折但心中仍未放弃的光棍男人,有一起出门打拼的新婚小夫妻,有相濡以沫打散工的患难夫妻,也有备受家暴而背井离乡的家庭妇女……这些普通人的生命史遍布著曲折离奇的经历、低回婉转的情愫,也不乏惊心动魄的情节,让人感同身受,意识到每一张普通的面孔背后都有着难以一言以蔽之的身世出处与恩怨情仇,每一个平凡的人物身后都负载着错综复杂的生活网络。读者无法对他们轻易地进行道德判断,他们“高贵而富裕的友善”也很难不让人产生情感上的触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拾棉民工以女性为主,阿慧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能够更为贴切地感受到女性更为艰难的处境,从而使得她们的人生故事有着社会问题的呈现。诸如留守儿童、拐卖妇女、“互助”男女、家庭危机……这些因为季节性劳动而漂泊异乡的女性各自携带着自身的遭遇,同时也是转型时代性别歧视、情感结构和伦理关系逐渐发生微妙变化的表征,尤其引发出对于更广泛层面社会问题的思考。
女性与底层的共同体验,让书中的人物形成了体恤互助的情感共同体:“深夜的星星为什么这么明亮呢?”“因为走夜路的孤苦人,需要它的温暖和照亮啊!”这是一种饱含温情的升华。这是这部作品不同于苦情哀歌与伤痕叙事的地方,它更着眼于劳动者的尊严与乐观积极的精神风貌的表现。“日子到跟前了,人不能躲,扛上日子走”,没有悲情,只有理解,没有哀怨,只有努力生活的欲望,在那种最基本的追求里有着中国普通民众务实而踏实的认知和实践。本书取名为《大地的云朵》实在是最恰切不过,他们如同云朵般随着生活的狂风飘移,但始终没有脱离对于大地的深情,对于劳动改变命运的信仰与执着,正是这种心怀梦想而又脚踏实地,用勤劳的双手耕耘生活的奋斗,才构成了中国大地稳健的基质。
作者在2015年到2018年又陆续回访了其中的一些采访对象,他们的生活大部分都发生了变化,从中原远赴边疆拾棉的日子即将一去不返,因为大部分地区都在逐渐实现机械化作业。作为一种异乡零工形态,人工拾棉不久就将完全不复存在,《大地的云朵》因此就带有了见证意味和时代文献的色彩,从社会学角度而言也有其价值。
但是,《大地的云朵》不仅局限于一部纪实文学或鉴证实录,它的文学性体现于将河南民工的故事升华为一种生命形态,一种不断流动的形态。书中写到一位“追梦女”,当北疆的棉田不再需要民工的时候,她秋季去南疆喀什拾棉花,春天去浙江安吉采茶叶,夏天到大连穿牙签海带卷,冬天再回到故乡。这几乎构成了一个当代社会的隐喻:当代社会是不断流动变易,人们从原先的共同体中脱嵌出来,加入到迁徙的行列之中,四季流转于大地的不同角落,只为铸造自己安顿身心的家园。阿慧用自己的笔墨让这些异乡劳动者讲述自己的故事,也让自我与他人的声音合奏为一曲当代底层民众的颂歌与咏叹。
最美的云朵
张洁方
必须写点什么,不然,对不起这本书,更对不起这本书一次又一次带给我的感动。
读完阿慧的《大地的云朵》后,这一意念立马从头脑中冒出,初始,如解冻后的第一滴河水,只叮咚一声,接着,大河开始奔涌,不能自禁。
我是从河南文艺出版社张娟老师的微信朋友圈知道这本书的,这本纪实文学,写的是河南农民远赴新疆釆棉的事情,并获得“2020年度十大好书”之首,立马决定买一本读读。
之所以迫切地想读这本书,是因为我有过新疆生活的经历。曾经,我在南疆的阿克苏市喀拉塔勒镇抚弄枣园。我的枣园四周,便有大片大片的棉田。进入九十月,棉桃次第开放,如云似雪,以一种任性的白回报土地的希冀。此时,会有大批的釆棉工进入棉田,排开阵势,一寸寸地清扫“积雪”。闲暇之余,我会趁着地老板给他们送饭之机,与他们攀谈几句。有次,我走进一块地头,看见二三十个釆棉工刚吃过饭,就上前与他们打招呼。一听说是河南老乡,呼啦一下围过十几个人。这些人中,有一个年龄最长的,问:吃饭冇?我说吃了,并问大姐是哪里人,大姐说是商丘的。我看她满头白发,像顶了一头棉花,就问她多大岁数,大姐说七十二了。我说,这么大岁数,还出来挣钱,儿女们不管你吗?她说,管,儿女们都孝顺着哩,只是都没本事,吾身顾不上吾身,我出来挣俩钱,自己花着方便。我问,你出这么远的门,儿女们放心吗?她说,不放心,瞅,老大也跟来了。大姐扭扭头,下巴抬了抬,我顺着大姐抬下巴的方向,看到人群的后边,蹲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支奓着,胡子支奓着,像撂荒的山包。他见我看他,便不好意思冲我笑笑,瞬时红了眼圈,杵下头去。就在他杵下头的那刻,我看见,有一颗东西从他的眼中滴落……每年,都有釆完棉花一时买不到车票回家的釆棉工,到我的枣园找活干。有一年,我回老家有事,去阿克苏车站买火车票,阿克苏的购票大厅候车大厅被人和大包小包挤得落不下脚。许多人买到两天、三天、五天后的车票,却舍不得花钱住店,把编织袋铺在站前广场,展开被褥,穿着臃肿的棉袄,蜷缩在广场上过夜。10月底的新疆之夜,哈气可以成霜,没到过新疆的人,是没有办法体会的。望着那些衣衫褴褛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望着一年一度的新疆镜头特写,我热泪奔涌,胸堵喉哽。那一刻,我冒出了写写他们的冲动。然,冲动终究是冲动,一直没有行动,一是因由生活所迫,二是我的长篇《天浴》写到半道,无法旁顾。如今,见了这方面的信息,怎能不一睹为快呢!同时,也想看看阿慧老师是从什么角度来写这本书的。
展卷,只读两页,就被灵动的语言牢牢吸引。众所周知,文学作品给人的直觉观感,首推语言。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无不在语言上下足了功夫。什么是好的语言?贾平凹先生说过六个字:鲜活,生动,准确。阿慧老师用自己的文字,对贾平凹的六字箴言作了强有力的注解。她写农民,用的是农民语言,譬如第一页,“呼咚咚上来三个中年女人,大包小包的行李,连同毫无掩饰的说笑,顷刻间填满了整个车厢。”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字比“呼咚咚”更鲜活,灵动!这些鲜活灵动的文字,自始至终在她的作品中闪耀,犹似跌进湖里的星,犹似隐在草丛的花。许多作家,在强调语境的同时,多多少少会陷入一个语言误区,认为叙述的语言可以更“文学”一点,只要人物对话符合人物身份就行了。阿慧没有陷入这个误区。她不会给一个犁地的老农穿诗人的外衣。农民与土地紧密相连,从骨子到衣裳,都散发着土地、田野、庄稼的气息。“三个女工老乡,头顶着头大声说话。短发女人说:今年南疆的棉花好,比咱北疆的强,抓一把是一把,俺娘家嫂子这回可抓住钱了,比我多挣两千多哩。烫发女人举着一根指头说:咦,你这媳妇挣得还少啊,一万多块哦,啧啧!管再养个男人了。”“大妹子魏桂花端起饭碗正要吃,发现筷子不见了,她在编织袋改制的包里翻了翻,没有找见,可能是漏到棉花地里了。我正替她发愁,她啪啪折了两根棉花秆,一双天然的筷子就有了,又从布袋里抓起两个馍,吧唧吧唧吃起来。我也从看不清颜色的布袋里,抓了一个馍。这馍比我的脸还大一圈……”这样的句子,质朴而清新,处处散发着土地的气息,棉田的气息。
必须承认,阿慧是一个具有相当才情的作家,她的才情,不仅仅体现在语言功力上,还体现在结构布局上。众所周知,在一众文学体裁中,纪实文学是最难写的一种,它不像小说,可以虚构,可以设置悬念,可以一个包袱压一个包袱,怎么抓人怎么写;不像诗歌,可以抽象思维,可以天马行空,一脚泰山一脚华山,一脚人间一脚地狱。纪实文学重在纪实,故在表现手法上会受到诸多限制。然而,阿慧在《大地的云朵》里,糅进了小说的悬妙,散文的优美,把一群河南釆棉工的故事讲得活色生香。全书写了三十二个人物,这些人物中,除了个别地主、基层工作者外,大部分是釆棉工。她以一朵花来命名人物,共三十二朵花,这个命名就很巧妙。但是,如果仅把釆集的三十二朵花扎成一束,插进花瓶,虽然美丽,却缺少了生命的鲜活。阿慧的精明就在于,她把自己变成一株棉棵主干,又生出许多枝杈,让三十二朵花摇曳上棉棵的枝头。掩卷良久,我还为阿慧的匠心独运击掌。
任何一朵花的盛放,都经历过凄风苦雨。阿慧笔下的三十二朵花也不例外,甚或比别的花经历得更多,这些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远涉万里到新疆挣钱的农民,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捧辛酸泪:一朵花,“财迷女”魏桂花,为了从结婚时公公给她盖的“趴趴着的破鸡窝”走出来,住上新房;二朵花,“酒窝姐”瞿美娟,为了“不给儿女增加负担……老伴吃药打针、柴米油盐,不伸手给儿女们要”……但凡生活过得去的人,谁愿意抛家别舍、背井离乡来这遥远的地方吃苦受累,况且,他们吃的苦,不是一般的苦……读《大地的云朵》,禁不住一次次泪奔。许多时候,三十二朵花,在我的眼中幻化成三十二滴泪珠,而阿慧,正是串起这些泪珠的雨线。这样的行文结构,弥补了纪实文学枯燥的不足。
著名作家铁凝在文代会上要求作家要“腿勤、手勤、眼勤、笔勤”。具体到阿慧身上,还多了一勤——心勤。她是用心、用情在写作。一个弱女子,跋涉几千公里,到一个艰苦的、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去釆访,拒绝场部领导的特意安排,坚持要与釆棉工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劳动;她不嫌弃拥挤的大铺,不嫌弃女工们因由四十多天不洗澡身上散发出来的异味和皮芽子(洋葱)味;视釆棉工为自己的兄弟姐妹,悲伤着他们的悲伤,快乐着他们的快乐。我想,这才是《大地的云朵》带给我一次次感动的真正原因。阿慧用行动告诉我,作家,只有扎根土地,扎根人民,才能写出具有生命力、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么,纪实散文,应該是历史的素描。我这人读书有个毛病:读时,不爱先读序,尽管为书写序的多是名家,《大地的云朵》是刘庆邦老师作的序。刘庆邦老师是我十分崇拜的大家之一,特别喜欢他的小说。然,我还是跳过序,先读正文。我始终认为,先读序,影响了我对一部作品的欣赏与判断。我是在读完这本书两天后,才勾回头读序的。读了之后,竟然发现我的认知与刘庆邦老师有许多相近的地方,最起码,我是认同刘庆邦老师对这部书的评价的:“每一个生命的个体,都承载着历史和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疆或许不再需要人工釆摘棉花了,改为机器收釆;棉田或许不再是棉田了,可能会变成油田,变成城市,变成历史。如果没有人把河南人去新疆拾棉花的故事记录下来,若干年后,很可能是落花流水,了无痕迹。幸好,富有使命感的阿慧,用她的笔,她的文字,她的心,深情地、细节化地、生动地记述了这些故事,并使这些故事有了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生命价值、审美价值和文学价值。”
使命感。阿慧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者。
新疆10月棉田的风是粗粝的。粗粝的风,削尖阿慧的笔。祝阿慧老师写出更多的好作品,为时代而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