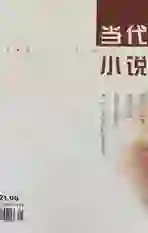口技
2021-05-27程相崧
程相崧
1
这次家长会,男孩终于可以通知爸爸参加。他从镇上回来的时候,跑得很快,感觉脚下有“呼呼”的风响。他后背上的书包不停地颠簸起来,打着他的屁股。两只鞋子也被他脱了下来,提在手里。这样可以跑得快些。在他的两旁,是枯黄的玉米秸,还有黑褐色的棉花棵。成熟的玉米有的已经被人掰了,有的僵硬地侧立在秸秆上,收获他们的人还没有回来。棉花也一样,有的已经摘干净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秸秆,有的还有些白色的散花。男孩听到,天地间都是秋天田野里的声音,让他熟悉,让他心里舒坦。麻雀在谷地的田埂上“唧唧喳喳”,蟋蟀在草丛中的巢穴门口弹琴,树上的枯叶在风中发出金属般的响声。
他一边跑,一边胡乱喊着什么,也许是胡乱唱着什么。至于是什么内容,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准确说,那更像是一些奇怪的音节。随着奔跑姿势的变化,孩子嘴巴里发出的声音也变化着。先是摩托车的声音,“嘟嘟嘟”,“嘟嘟嘟”。这时,他的两只胳膊架在胸前,双腿不停搅拌着,像是两个飞速旋转的轮子。接着,他的两臂变得一前一后,脚下也颠簸起来,整个人都像是骑在马背上,嘴里也发出了欢快的马的嘶鸣声,还有急促而紧张的马蹄声。他这样骑着骏马奔跑了一阵,终于气喘吁吁地停歇下来。在勒住马缰绳停下脚步的时候,他的嘴里发出了一阵“咴咴”的马的叫声。
他学完马的叫声,又似乎忍不住,学了两声驴鸣。这是草驴的叫声,男孩儿心里想着,接着又学了几声公驴的叫声。这两种叫声一高一低,一抑一扬,饶有趣味。接着,它们你一声我一声,像是越来越近,越来越熟,最终耳鬓厮磨,变得难解难分。这样突然出现的场景,把他自己逗乐了。他轻轻地嘘出一口气,放慢脚步,有节奏地朝前走着,嘴里发出汽车轮子从公路上迅速碾过的声音。接着,汽车紧急制动,喷出尾气,停在了他们家的门口。车门打开,是皮鞋轻轻敲打在地面上的声音。男孩模拟的是爸爸那天从外面回到家里来的场景。从他刚刚记事起,爸爸就在外打工,他的模样,好多村里人已经记不起了。他回来了,这真是一件大事情。男孩儿这样想着,走进村子的时候,嘴巴里不由自主地发出了黄鹂的鸣叫。那声音清脆婉转,有些欢快,就连他自己都怀疑不是自己发出的,而是附近树梢上传来的叫声。
口技这项本领,男孩是从爷爷那里学来的。爸爸和妈妈一直在外地打工,分别在不同的城市。后来,妈妈跟爸爸离了婚,再也没有回来过。爸爸也是在春节的时候,才会回来看看他们。男孩的童年几乎都是在爷爷身边度过的。爷爷沉默寡言,看上去像一根木头。只是逢年过节,或者有人家举办红白喜事,被请去表演的时候,才会突然变得欢快起来。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声音,爷爷都会模仿。动物、植物,器物,都惟妙惟肖。猪羊狗马驴,这些在村子里常见的动物不用说了,就连躲在山林里的狼豺虎豹,爷爷也能模仿得出来。
在那些短暂的时刻,他跟爷爷都没有了烦恼。爷爷的脸上泛着红光,他则躲在人群中,陶醉地望着爷爷。这样开心的日子,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短暂了。在更加漫长的日子里,他和村子里其他男孩一样,每天都要去镇上上学。那学校对村子来说有些远,很多孩子都是家长接送。在一开始,爷爷执意接送他。可是过了半个学期,他就不让爷爷接送了。他一个人走着来回。男孩在学校几乎不怎么说话,课外活动也不参加,体育课也不上。有同学主动跟他聊天时,他也只是简单地点点头,或者摇摇头,能不吭声就不吭声。这样时间久了,大家便几乎要把他当成哑巴了。
但是,男孩儿并不是哑巴。他不但会说话,还跟爷爷一样,天生一张巧嘴。在没有人的时候,例如从食堂里吃了饭,经过那条甬道去宿舍楼的路上,他就会鼓弄着嘴,学两条狗咬架。狗咬架往往有一个过程,一开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甚至你挨挨我我碰碰你,接着就因为一根骨头产生摩擦,呲牙咧嘴,剑拔弩张,不停地朝着对方咆哮。最后,往往是身体高大强健的占了上风,而弱小的一方就只能躲在一边,一边舔舐伤口,一边委屈地望着对方大快朵颐,眼睛里露出可怜巴巴的神色。
这样,一场战争结束,他也就从食堂走到了宿舍。他一到宿舍又变回了沉默寡言的样子,把餐具放在桌子上,爬到床上便蒙上了被子。有时候,他在走廊上洗衣服,也会发出黄鹂的叫声,或者布谷鸟的叫声。这样的情景,一般不会引起同伴们的怀疑。顶多,会有人望着窗外,脸上露出诧异的神色。而男孩儿则会装作若无其事,一边继续洗着衣服,一边窃喜。
爷爷的那个小院儿,在村子的中央,那里被他称为“老家”。而那处平常不住的父母的新房,则被他们称为“新家”。那个新家,在村头的路边。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那里都是铁将军把守。男孩和爷爷都不常到那里去,只在春节之前爸爸将要回来的时候,爷爷才会去一趟,把那里打扫一下。这一次,男孩儿要到新家去。爸爸回来了,他要把开家长会儿的消息告诉爸爸。男孩觉得有些不习惯。在以前,好几个学期,家里都没人给他去开家长会。爷爷已经好几年没有参加了。不是爷爷不愿意去,而是他不愿意告诉爷爷。如果告诉,他肯定会去的。
他不想让爷爷去,因为在一年级下学期,爷爷去参加家长会的时候,穿了一双下雨天穿的胶鞋。那鞋子上的泥巴弄脏了教室里的水磨石地面。这让爷爷和爷爷身后的他遭受了很多鄙夷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他便决定不让爷爷去了。为参加家长会的事儿,班主任曾经严厉批评过他,他一声不吭,用沉默进行抵抗。班主任暴跳如雷,最后却也无可奈何,随他去了。他不知道,如果这一次爸爸去参加了他的家长会,老师和同学们会怎样看他。他觉得,在去的那一天,一定要让爸爸穿上那双皮鞋,最好再扎上领带。他会骄傲地跟在爸爸身后,让他们都看一看这一对父子。
男孩儿来到村口新家的时候,却很诧异地看到了门前挂着的铁锁。今天,爸爸没有像前些天一样,做好了饭,打开院门,在家里等他。爸爸今天出门去了。男孩有些惆怅地扣了几下门环,里面的门栓似乎有些腐朽了,轻轻一推,门便打开了。男孩看到,院子里一片狼藉,比爸爸回来之前还要更加凌乱一些。横七竖八地堆在墙角的农具,随意地丢在院子中央的洗脸盆、搓衣板和半舊凉席。男孩推开房门,走进屋里,眼前的情景也让他吸了一口凉气。那张红褐色的破旧沙发不再是靠墙放着,而是斜摆在房中,沿着客厅的对角线。地下是凌乱地丢弃的衣物,没有吃完的半袋方便面,还有沾着污物的啤酒瓶。男孩疾步走进卧室,床上的被褥没有了,露着残缺不全的金黄色草席。床一侧的衣橱也没有了,写字台也没有了。这个家像是遭了贼,不!贼也不会弄得这样凌乱。应该说像是遭遇了一伙儿强盗,或者干脆说是遭遇了一场战争。
这样的场景,让男孩惊讶地站在那里,呆若木鸡。他在迈进家门的时候,嘴巴里正在发出一阵黄鹂和夜莺的鸣叫,这时,黄鹂和夜莺也停止了自己的喉咙。他有些恍惚地想着,昨天,爸爸还坐在这张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喝着啤酒。他偎依在爸爸身边,看着因为信号不好满是雪花的电视。现在,他站在房子中央,看着几个啤酒瓶子堆在墙角,电视机没有了,连放电视的桌子也没有了。男孩正在纳闷的时候,发现爷爷正站在门口。他一惊,不知道爷爷是什么时候跟着进来的。他轻轻叫了一声“爷爷”,带着些哭腔。爷爷站在门口,仍旧像从前一样,忧心忡忡地望着他。爷爷说:孩子,你又到这里来了!你醒醒吧,这座房子空无一人,已经闲置了好多年了。你总说爸爸回来了,到这座房子里来找爸爸。可是,你爸爸并没有回来,他还在外地打工。你说的一切,都是你想象出来的,包括你的爸爸,包括你跟爸爸在这屋子里的情景。这里并没有你的爸爸!你要相信,爸爸会回来的,但不是今天!你病得像是更严重了,得赶紧回家吃药,你得了臆想症。
2
这时候,男孩儿才忽然清醒过来,紧走几步,扑到爷爷怀里哭了。这样的情景,已经不是第一次,爸爸是他想象出来的,整个房子里跟爸爸在一起的场景,都是他想象出来的。实际上,这座房子还是跟从前一样荒凉、破败,没有人气。一切都是冷冰冰的,只有爷爷的身体是暖的。男孩紧紧地抱着爷爷,喉咙里哽咽着,眼泪顺着脸庞流进脖子里,把他的衣领都弄湿了。他感到爷爷把他抱得紧紧的,苍老的大手轻轻抚摸着他的后背,抚摸着他短短的根根直立的头发。
这时候,男孩却又听到了爸爸的声音。那是一阵汽车轮子碾压在路上的声音。那车就停他们家大门口。接着,脚步越来越近,男孩嗅到了爸爸身上的烟草味道,还有挥之不去的汽油味。这些年,爸爸是在北京的一家大型汽修厂工作。爸爸从电话里说过,挣足了钱就接他去北京。爸爸的脚步近了,他穿的是一双骆驼牌的皮鞋,皮鞋底儿上的花纹已经磨平,所以走在路上,发出的声音并不清脆响亮,而是有些拖沓。爸爸的左腿比右腿稍微长一些,他自己感觉不到,但男孩儿听出来了。因为走在地上,脚步声一轻一重。男孩甚至听到了爸爸因为长期抽烟,患着咽炎,喉咙里发出的“咕咕”的响声,像是鸽子喉咙里发出的轻轻的鸣叫。
男孩从爷爷怀里挣脱出来,转过头望向门口,那里却没有爸爸。他摸了摸自己的嘴唇,发觉自己的嘴唇在动。爷爷说得没错,这一切都是他的臆想。至于他听到的声音,都是他自己的嘴巴里发出来的。这些天来,他和爸爸一起坐在这间新屋里看电视,聊天儿,聊他在学校里的事情,聊他跟同学和老师之间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一切都并不存在,只是他自己跟自己聊天。他望着那张秃了皮的沙发,望着那扔在垃圾里的废弃暖水瓶,还有歪倒在地上掉了一条腿的小板凳,终于明白过来,那一切都是自己的臆想。他感到有些惊讶,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脑袋。天呐,他说,我的天哪。
我不信!男孩叫道。
你不信,你就看看嘛。爷爷说。
男孩儿知道,爷爷说得没错,一定又是自己在犯糊涂。他恍惚地记得,这些天自己一直在吃一种药。那是有一次爸爸带他去市里看病,一位年轻的大夫开给他的。他觉得带他去看病的是爸爸,不用说也是他的臆想。真正带他去看病的,一定不是爸爸,而是爷爷。男孩吃了一次之后,心跳起来没有以前那样慌了,但是偶尔眼前还是会出现一些记忆中的画面。比如爷爷,比如爸爸,比如妈妈。他记得,妈妈离开家的时候,穿的是一件蓝色的连衣裙,脚上是一双红色的皮鞋。那双皮鞋细长细长,像是两只红色的狐狸。
他跑过去紧紧抓住妈妈的裙摆,妈妈拖着他,艰难地向前拖了一阵。他用牙咬住了妈妈的裙角,紧紧地咬着。你松开嘴,你个小狼,几十块钱一条的新裙子,都让你给咬烂了!他听到妈妈气急败坏地说。那时候,妈妈在南方打工,在一所玩具厂里,跟在北京的爸爸常年分居。据说,妈妈是跟他们厂里的一个质检员好上了。他们办理了离婚之后,爸爸又去北京打工了。那时候他还很小,整整哭了一夜。后来,在他睡不着的夜晚,爷爷都会让他闭上眼睛,躺在床上,用口技来哄他。
现在,每当他的眼前出现臆想出来的情景时,爷爷都会痛心疾首。爷爷将这一切归咎为在孙子小的时候,自己用口技的方法哄他。爷爷说,男孩之所以这样,是自己当年给他种下的病根。
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晚上,男孩想父母,想得厉害。爷爷睡在床的那头,便让他闭上眼睛,仔细地听。慢慢地,男孩耳边先是有了小村每天都能听到的声音:人的脚步声,小声说话声,赶着羊从门前走过的声音,羊屎蛋落在地上的声音,公羊发情不停追着母羊叫唤的声音。接着,门口有了摩托车声,然后是鸡鸭乱叫,爸爸回来了。显然,爸爸在外面挣了钱,是衣锦还乡。爸爸坐在沙发上,用打火机抽烟,打开了新买回来的电视机。电视里播放着《西游记》,猴王出世的声音,接着是村里小孩子们挤在屋子里,看电视的声音。爸爸不仅买来了电视,还有洗衣机。洗衣机里的衣物“咕噜咕噜”地搅拌着,搅拌一阵,水管“哗哗”地朝下放水。
同时,厨房里热闹了起来。杀鸡的声音,宰羊的声音,锅碗瓢盆相互碰撞发出的声音。风箱“哐当哐当”地来回拉着,锅里的水先是发出“嗞嗞啦啦”的微小响声,接着“咕嘟咕嘟”地像是开了。在这个大锅烧着开水的时候,另一口锅里却被泼进了一勺子油,“嗞啦”一声,接着是什么东西“哔哔啵啵”地响成一团。男孩猜测,是葱花姜末蒜末都倒进了油里。这样响了一阵,刚刚小了下去,又是一声嘈杂的爆响,是土豆或者鸡块倒进锅里去了。锅盖马上被盖到了锅上,声音很快小了下去。
这时候,爷爷差不多就会发现,男孩眼睛渐渐闭上了。他呼吸均匀,小鼻翼一张一合,小胸脯一起一伏。他进入了梦乡,梦中似乎还嗅到了油花的香味,嘴角弯上去,露出笑容。
这样的节目,爷爷不知表演了多少次。每一次表演,男孩都是听得津津有味,兴致盎然。他还给这个节目起了一个名字,就叫《回家》。后来,爷爷说够了,提议说表演个新的吧,说个二狗咬架,要不就二马爭槽。男孩总不同意,他最喜欢的还是这一段儿。当然,这个节目,爷爷表演时也会稍有变化。比如爸爸回来的时间,有时是下雨天,有时候又是有大风沙的晚上。那样的话,男孩便总会瞪大眼睛,呼吸紧张,小心脏不停地跳着。当然,虽然遇到种种困难,每一次爸爸总能平安归来。有时回来,还会朝他脸腮上亲上一下。爸爸亲他时,他都会装作睡着,紧紧闭着眼睛。他怕一睁眼,爸爸就会离开。这样沉沉地睡下,直到第二天一早,他的嘴角都是笑着。
3
其实,男孩知道这都是假的,但是,他还是愿意相信。那些年,他没有什么玩伴,村里有一些跟他一样大人常年在外打工的孩子,他也不愿意跟他们玩儿。他除去上学,最愿意跟爷爷待在一起。
当然,这并不是最初的情景。
在爸爸妈妈刚刚出去的时候,男孩甚至不愿意搬出那座房子,不愿搬到爷爷那里去。他一个人住在那座空荡荡的大房子里,白天也关着大门。直到有一天夜里,他听到有什么人进了他们的院子。男孩听到很大的響声,就在鸡圈那个地方。他起了床,拉开了屋子里的三盏电灯和外面走廊上的一盏电灯。电灯在漆黑的夜色中发出昏黄的光,让他的胆子壮了一些,但身子还是瑟瑟发抖。他紧紧地抱着手电筒,盯着已经从里面锁上的房门,直担心会有人破门而入。
男孩用手电照着院子里,大声喊着:“你是谁,你要干什么?”院子里再没有什么动静,只有“沙沙”的风响。他照上一阵,就坐在床上,打一阵盹儿。这样一直坚持着,男孩一夜没睡。直到黎明时分,五点来钟吧,他听到有人拍打院门。他听出是爷爷的声音。他浑身颤抖着,赤着脚跑出去,给爷爷打开院门,猛地扑在爷爷的怀里。他喊了一声爷爷,听到自己因为喊了一夜,声音都已经嘶哑了。
从那之后,男孩搬到了爷爷那里。爷爷那里是两间土屋,没有这里条件好。但是,爷爷在那里住惯了,不想搬到他们这里来。男孩从来没有见过奶奶,后来才听说,爷爷这辈子没有讨过女人,爷爷是个光棍。爸爸是被人丢在集市上的一个孤儿,爷爷捡来,一口一口养大。爷爷在做农活上不大在行,甚至在村里人的眼里有些懒散,有些不务正业。但是,神奇的是,爷爷却有口技的天赋。小村里出现的每种声音,他都能学得惟妙惟肖。在搬到爷爷那里之后,男孩仔细观察过爷爷的那张嘴。爷爷的那张嘴并不好看,嘴唇偏薄,似乎比一般人还要大些。但是,那里面却能发出各种鸟、昆虫和动物的叫声。在跟爷爷住在一起的头些天里,爷爷教会了他火车的声音——启动时威风的汽笛声,还有行走起来“咔哒咔哒”的铁轨声音。
男孩在那样的声音里,仿佛跟总是不辞而别的爸爸和妈妈,进行了一次告别。随着那一声汽笛,男孩的心也绞拧在了一块儿,甚至猛地疼了一下。他站在高高的月台上,看着火车缓缓前行,随之疯狂地挥舞着手臂。他看到有好多人在随着火车奔跑,像有些电视剧上演的那样。男孩也跟着大家跑了起来,朝着父母离开的方向,朝着火车离去的方向。那样一连好多天,他天天早晨都会哭醒。
再后来,爷爷就不再给他学汽笛和铁轨的声音了,而是很多其他的声音。什么鸡叫啊,鸭叫啊,羊叫啊,猪叫啊,驴叫啊。总之,是农村从前常见的动物。这些动物里,有些男孩不仅见过,叫声也熟悉,例如鸡和鸭子。有些他见过但没有注意到过的叫声,例如羊和猪。还有些像驴子,他从小就没有见过,更不用说叫声了。爷爷总是惟妙惟肖地给他演示,并叫他试着学习。他一开始不学,说我学那些干什么呢?爷爷笑笑说,技多不压身,等爷爷死了,你如果考不上学,或许能有一项吃饭的本领。
是的,要说口技,爷爷才是他见过的真正的行家。爷爷给他演示得很细,例如鸡的叫声,就分公鸡母鸡和小鸡仔。公鸡里面,还有打鸣的公鸡、追求母鸡的公鸡、请求交配的公鸡,交配之后的公鸡等等。猪里面,有公猪母猪猪崽,饥饿时候的猪、吃饱之后的猪、拱地时候的猪、发情时候的猪、挨刀时候的猪、让人挠痒痒时候的猪,等等。爷爷教给他的时候,还要配上动作,并让他也跟着自己学习。男孩不好意思,每次都羞红了脸。可是爷爷严肃地说,就像演员演戏,要揣摩角色,才能演得惟妙惟肖。学鸡鸭猪狗叫唤,也要设身处地,体会它们此时此刻的感觉,才能模仿得形神兼备。
这样的教学,其实也只是祖孙之间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是老人为了给孙子去愁解闷想出来的方法。爷爷最大的期望,当然不是让孙子掌握口技,而是以后能够考上大学,至少也得考上一所技术学校。所以,爷爷省吃俭用,供孩子上学。这样隔三差五的,孩子学到的口技,只能算是一些皮毛。爷爷的口技在十里八村小有名气,所以,在过年过节或者哪里有红白事的时候,他们也会花些小钱,请爷爷到那里去演出。
每次去,爷爷总会带上男孩。爷爷有一套演出服,是一身中山装,不管冬夏都是穿着它。演出一般在简陋的舞台进行,一般有一个主持人跟爷爷站在一起,插科打诨。在主持人的要求下,爷爷分别学出鸡叫、鸭叫、狗叫、驴叫等等。这时候,下面的人好奇地看着,听着,哄哄闹闹。爷爷的演出总是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等他学出公驴发情,母驴迎合,两驴交欢的情形时候,下面的男人都会哄笑起来,女人们则都别过脸去,“呸呸”地捂着脸骂,有认识的,还会提着爷爷的名字。
除了二驴交欢,爷爷最拿手的,还有让人挠痒痒的母猪、被杀的公猪、发情过程中的公鸡、看电视时突然遭遇停电的老两口等。爷爷声音惟妙惟肖,再加上动作,更是让人忍俊不禁。例如,在模仿公鸡发情的时候,爷爷总是会金鸡独立,然后还不停转着圈子,单腿跳来跳去。模仿被杀的公猪的时候,爷爷会一边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一边旁若无人地突然躺在地上,身子不停颤抖,就像一头挨了刀之后的猪。
每次,男孩跟爷爷出来,都是躲在人群中,跟其他人一样看着爷爷的表演。他不说话,有时候也跟着人家笑。有的人看出他不是那村里的孩子,却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有在演出完毕,吃饭的时候,爷爷才会把他领到席上,打一次牙祭。有几次,在乡人的怂恿下,爷爷要他上台配戏,但他坚决不从。但是,在没有人的时候,例如上学放学的路上,他却试过自己的本事。他觉得,爷爷会的东西,他已经学到了八九不离十。学归学,可是,他不想给人表演。
那样的事儿,这些年,他只在班级联欢会上干过一次。那一次,他鼓起勇气,表演了一段自编的口技。他给节目取了一个名字,叫《放学》。他表演的,是城里的学校打了下课铃,放学之后,那些走读的学生纷纷涌出校门,孩子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来到学校大门口,接他们回家的情景。男孩表演得惟妙惟肖,脚步声、说话声、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
他的节目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孩子们似乎并不满足。因为,那些都是他们平常的生活,大家并不感到稀奇。最后,男孩不得不表演了猪和驴子的叫声,他们才算满意。在表演被杀的猪时,他像爷爷一样,一边哀叫,一边蜷缩着身子,还慢慢躺在了教室的地上。
他的那个样子,真的像是被杀的猪。男生都笑得前仰后合,不停地拍着桌子,女生们都笑得喘不过气来,弯下的腰半天也没抬起来。
4
这一次,男孩站在院子里,心里又一次被彻底的失望紧紧地包裹住了。
这一切都是臆想,爸爸并没有回来,正如爷爷所说。他隐隐想起来,这些天,他一直在吃一种药丸。自己病了,自己的精神出了问题。虽然爷爷并没有这样说过,但他此刻才意识到了这一点。男孩抬头望了爷爷一眼,看到了爷爷微微责备的眼神。他觉得,自己有些对不住爷爷。爷爷瘦了,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但是,他还是让爷爷操心。男孩记得,前些天的时候,爷爷甚至病得卧床不起,把村里支书都惹来了。村支书给外地打工的爸爸打了电话,但几天过去了,爸爸也还是没有回来。那些日子,男孩真的担心,爷爷说不定哪天就会头一歪去了。最终,爷爷还是挺过来了,又站在了他的身旁。在爷爷责备的目光里,男孩低头不语,他觉得懊悔不已。
在男孩清醒下来之后,才渐渐明白过来,爸爸回来了,这种事儿他原本就不该轻易相信。他想起来,在二年级的时候,同学们已经学会相互攀比着过生日。在生日来临的前两天,他背着爷爷,给爸爸打了电话。爸爸明白他的意思之后,声音很冲,不但没回来给他过生日,还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
因此,他曾经恨过爸爸一阵子。但是,不知为什么,他还是不争气,还是很快就开始想他了。后来有一次,班里一个叫小光的孩子因为打架,班主任叫了他的家长。大家都看到,小光的爸爸来了,在办公室门口挨训。据说,他是从广东坐高铁专门赶来的。从这件事儿上,男孩似乎又看到了希望。这样过了几天,宿舍里熄灯之后,他便在床上学起了驴子叫。在夜色里,整个宿舍的孩子们都沸腾了。男孩们拍着床板,连邻近宿舍的孩子也起起哄来。这样过了不久,宿管员老师就听到了动静,过来镇压下去了。在第二天,这事儿便被报告给了班主任。真实情境很快水落石出,班主任老师把男孩喊到走廊上,让他打电话叫家长。男孩把爸爸的电话给了老师,老师打长途打给爸爸,爸爸也并没有回来。
男孩不知道,他这边出了什么事儿,才能够惊动爸爸。后来有一次,他心情不好,早晨躲在床下,没有去上课。在上午第二节课的时候,老师发现缺了一个学生。班主任慌了,发动了全班同学,满校园地找他。食堂里、操场上、洗手间里,都找遍了。班主任亲自到宿舍来查看,他缩在床下,用一个大纸箱子挡住自己,成功躲过了所有人的眼睛。他听到班主任在走廊上给爸爸打电话,声音都变成了哭腔。可是,就是这样,爸爸也没有回来。
男孩觉得爷爷说得不错,爸爸只是他的一个臆想,爸爸不会回来的。男孩失望地跌坐在沙发上,望着凌乱的屋子,这屋子似乎还留有爸爸的气息。但是,就连这气息,也应该是他的臆想。男孩最终站起身来,朝着门口大步走去。这一年的家长会,没有任何惊喜,也没有任何异常。老师和同学都会像以前一样,见怪不怪,习惯了他的家长的缺席。这一天,男孩会躲在家里,谁也不见,这样就等于是放了一天的假。甚至可以说,对他来说,这一天根本就没存在过。
在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却又看到了爸爸。爸爸迎着他,从外面走了进来。爸爸走过他的时候,用一只手摸了摸他的脑袋。爸爸没有说话,但手掌暖暖的,对他的态度很温和。
男孩回过头来,看到爸爸手里提着一把芹菜,还有一包猪肚。他踢着脚下凌乱的垃圾,走进了里面临时用作厨房的一间小屋。爸爸像是要给他做饭了。男孩定了定神,站在那里,远远地望着爸爸。他对着他的背影轻轻说了一句:你是假的。
男孩看到爸爸在刷锅,铁丝球跟锅摩擦,发出“沙沙”的响声。然后,里面的污水被“哗啦”倒在一边的水桶里,最后,他听到了葱花扔在锅里的热油里,“啪啪”爆锅的声音。
这些声音,真的值得怀疑。男孩摸了摸自己的嘴巴,果然,他发觉自己的嘴巴在动。他刚才简直相信了眼前的情景,这时候才沮丧透顶地发现,这一切其实都是他的幻象。他轻轻骂了一句,该死,又是口技,这一切又都是我自己的口技。
男孩刚才唇角还因为欣慰而轻轻扬起,这时候瞬间沮丧下来,假的,的确是假的。他忽然发作,像是一头发了疯的狮子,将厨房桌子上的东西猛地扒拉到了地上。他听到了巨大的声响,看到两只不锈钢盘子、筷子和菜板、菜刀、西瓜刀都滚到地上。他看到,这声音吓了爸爸一跳,爸爸回过头来,满眼温柔的神色。爸爸显得那样温柔,即使男孩这样发脾气,他也没有训斥。爸爸望了他一眼,慢慢蹲下身子,表情甚至还带着些内疚,将那些东西一件件捡起来,又放在桌子上。
这时候,男孩知道,把这些东西重新捡起来的,或许只是他自己。整个屋子里,没有别人,只是他自己。这个温柔的父亲,说白了,只是一团空气罢了。男孩摇了摇脑袋,狠狠地闭上眼睛,然后又猛地睁开。他还是没有将爸爸的幻影从眼前成功驱散开去。他绝望地喊了一声什么,感觉里面似乎有两只手要把脑壳撑开。
你又没有按时吃药?那个男人回过头问。
这话让男孩轻蔑地笑了一下,说:你快消失!你是假的,赶紧给我消失!
爸爸无奈地摇着头,想要说什么,却又闭上了嘴巴,随之叹了口气。
这跟现实一样的幻象,折磨得男孩实在厉害。他冲过去,顺手抓起桌子上的一把水果刀,轻轻地朝着那个影子刺去。他聽到“噗”的一声,刀子似乎扎进了一个棉花包。男孩站在那里,看到血从爸爸肚子上流出来,沿着刀刃和刀柄滴到地上。
你赶紧消失,刚才爷爷告诉我了,你只是个幻影,只是我的臆想!我的爸爸不会回来的,他无论怎样,都不会回来!
男孩喊完这些,看见爸爸佝偻着身子,一只膝盖弓着,一只膝盖猛地跪在了地上。他看到爸爸的嘴巴艰难地一张一合,发出轻微的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孩子,爸爸知道,你跟爷爷相依为命。但是,在几个月前,你爷爷死了。从你爷爷死后,你便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刚刚正要告诉你的是,你的爷爷已经去世了,你看到的爷爷的样子,才是你自己的臆想!
这时候,从窗子外面传来一阵秋风吹过田野的声音,枯黄的叶子在同样枯黄的秸秆上,打着旋儿,发出“泠泠”的响声。屋檐下的两只麻雀探出小脑袋,惊恐地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男孩听到了几百里外那座小火车站老式火车启动,发出的沉重的汽笛,还有铁轨咔嗒咔嗒的声音。
这屋子里的家具,我上午找人暂时收拾出去了,所以,这里才会这样凌乱,凌乱得像是遭了贼。我这样做,为的是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孩子,我们要重新开始。无论我还是你,都要重新开始。
这时候,男孩听到,随着爸爸微弱的声音,他的血“汩汩”流淌出来。男孩又摸了摸自己的嘴巴,他确定自己的嘴巴这一会儿一直闭着。他走过去,用手指轻轻摸了摸流到地上的那些血,然后把手掌举到脸前,看到了自己手上湿润的红色的东西。那东西带着一些温度,泛出一种奇怪的气味。
这时候,男孩才慢慢想起来了:这一次,爸爸是真的回来了,回来给爷爷送葬。男孩想把事情想得更清楚一些,可是他的脑袋还是疼得厉害。虽然有些事还没弄清楚,但最关键的一些东西,还是在瞬间都明白了。男孩感到浑身颤抖,惊慌失措地扑到爸爸身边,跪在地上,抱住了不停抽搐的爸爸。
他的喉咙里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接着,那尖叫慢慢慢慢形成一种调子,有些像是救护车远远从村外公路上驶过的声音。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