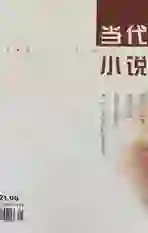生花妙笔绘人生百态
2021-05-27杨心怡
杨心怡
弗洛姆在《人的境遇》中说:“人是唯一意识到自己生存问题的动物,对他来说,自己的生存是他无法躲避而必须加以解决的大事。”无论是纪实还是虚构,乡土小说还是城市书写,描绘现实还是追忆历史,人物的生存状态始终是作家关注和描绘的焦点。本期所选小说,刻画了不同环境下人物的奋斗、挣扎与彷徨,向我们展示了现实的广度与人性的深度。
孙频的中篇小说《天物墟》(《十月》2021年单月号第2期)运用第一人称限制性视角,讲述了“我”回老家磁窑时被文物收藏者老元偶然选中,协助他整理书稿的故事。“我”是一个单身,失业,与父母关系冷淡的中年男子。父亲去世,“我”决定将其骨灰带回老家安葬。小说由此展开了主人公主动出走的书写。在老家,“我”接受了独居老人老元的邀请,留下成为了他写书的助手。老元重视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文物成为了他生命的寄托。将一辈子所收集的资料整理成书,是老元的夙愿。有时,“我”载着老元在山里闲逛,也去逛神秘的“鬼市”。在与老元的相处中,“我”得知了当地村民靠盗墓与倒卖文物为生,开始理解父亲生前常让“我”回老家看看的用意。老元对文物的敬畏使“我”明白了器物与人是相互滋养和成全的关系,文物所存的魂魄与时间超越任何的金钱价值。最终“我”将父亲留给我的玉璧埋在其坟旁,完成了与父亲的和解。与此同时,山间整理书稿的过程也是“我”与自我和解的过程。这一工作有着传承与守护文物的意义,使“我”找回了某种尊严感。在游历岭底村时,“我”惊讶地发现,老元曾用一个难以证实的谎言,让一个凋敝的村庄生机勃勃。原来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人的,很大程度上不是别人,而正是自己。整篇小说,是“我”的回乡记,更是“我”的一次精神救赎。最终“我”得到解脱,体现了作者对于小人物的关怀和怜悯。
李约热的短篇小说《家事》(《花城》2021年第2期)通过赵美珠的家事,反映出两代农民人生的无奈。广东打工回来的赵美珠和丈夫在八度屯本过着平静的日子,然而,这一生活因为丈夫的意外身亡被打破。从农村到城市,由城市再回到农村,第一代农人没有摆脱农村的生活,依旧在农村的土地上受苦。儿子赵拉浪是城市的打工者,勉强维持生计。他娶了同样在城市打工谋生的女人,婚后贫穷的生活激起了女人的不满。最终,女人生下孩子后和城市男人老宋跑了。第二代农人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生活,他们难以摆脱农民的烙印,作为最底层的人,在城市里继续受苦。平静、节制的叙述中,小说呈现出农人们渴望摆脱贫困又不得不在其中挣扎的生存窘境。与此同时,小说还向我们展现了当道德与生存在现实的环境中相互冲突时,人物面临的困境和抉择。女人是恶的,她想要过上好日子,只将赵拉浪当做一棵暂时的救命稻草。但在勾搭上老宋后,她本可以很早地一走了之,却因想为美珠家留个后代而与婆婆一起回到农村,直至诞下孩子才离开。赵拉浪一向人好、老实,能够包容妻子的缺点与任性,但在小说最后,为了留住女人,竟串通医生给妻子做了结扎。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苦难面前人性的复杂性。世界是善恶并存的灰色地带,每个人都有缺陷,每个人都有苦衷。在小说所塑造出的这些立体人物形象背后,流露出作者的同情与批判。
王大进的中篇小说《逆风》(《江南》2021年第2期)讲述的是男主人公赵烨发掘杨青谜团,并逐渐走入杨青母女生活的故事。小说力图展现现代都市青年慢慢融入城市的心理历程。农村学子赵烨在名校毕业后留在城市。他虽有体面的工作,但只能满足简单的生存。经济条件不足之外,使他更难以忍受的是与城市的疏离而带来的精神上的焦虑。赵烨因此产生了辞职回乡的想法。与神秘富豪女子杨青约会时,他阴差阳错成为了杨青女儿的家庭教师。通过一年多的相处,他与杨欣欣、何小武成为了朋友,从中找寻到了属于这座城市的存在感,对这座城市不再感到陌生,最终扎下根来。小说的题目出现在文章结尾逆风骑行的何小武处,象征着现代底层都市青年的生存状态。以赵烨和何小武为代表,他们都来自穷苦家庭,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去学习与打拼,才能在城市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和生来富贵的杨欣欣相比,他们在城市的生存有着巨大的阻力,就像逆风而行。留在大城市奋斗,还是回老家生活?这是多数外来学子苦恼的问题。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附着了当下城市生活的切实经验,将这一问题引向纵深,透过主人公赵烨,呈现出现代都市青年在物质、权力、金钱欲望之外,由身份焦虑而引发的精神困境,探寻当代青年的精神出路。
范小青的中篇小说《我们服了魏红霞》(《芙蓉》2021年第1期)讲述了凡事都要与人比,凡事都要比别人强的小人物魏红霞的一生。魏红霞在与姐姐比较的环境中长大。长大后,她不仅拿自己跟姐姐比,还开始拿自己跟同事、邻居和朋友们比,且比较的范围也从小时候的身高、长相和成绩扩大到了人生的方方面面。在小说的前半段,魏红霞的比较使其不断进取,在学业和工作上表现优秀,这是好的一面。但在这之后,魏红霞开始比结婚、比女儿,甚至于比离婚,比较的对象逐渐违背常理。故事最后,魏红霞与同事比三高的行为几乎接近于一场荒诞的闹剧。每一个人物都是历史与时代合谋的产物。魏红霞作为矛盾集合体,是当下社会问题影响下的典型人物。她在比较中丧失了自我,以别人的生活为标准,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思考与追求。除了自身外,她對下一代的消极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女儿王瑾萱在母亲没完没了的“比较”中长大,优秀却没有主见,无论是工作还是婚姻,都听凭母亲安排,活得如同一个牵线木偶。小说平铺直叙娓娓道来,读者在作者的指引下一步步地走进魏红霞的世界,蓦然发现她身上的这些可爱与可恨之处竟也在自己身上顽固地存在着。因此反观自身,实现一种对现实生存状态的超越。
王季明的中篇小说《大年夜》(《朔方》2021年第2期)是有关九十多岁的独居老太太意外死亡的故事。题目取自故事发生的时间大年夜,这本是一个阖家团圆、喜气洋洋的日子,却因为林老太的突然死亡而改变。与老太太有生活关联的各色人物来到她的家中,各怀鬼胎,上演了一场关于财产纠纷的闹剧。最后,女儿甚至声称不查出钱的下落,就不处理老人的尸体。这一反差极具讽刺意味,金钱之下人与人之间脆弱的关系,人性的贪婪与丑恶在其中显露无遗。小说采用多重式聚焦叙述手法,让林老太、女儿、听壁脚老王、里弄张医生、一条龙、老克勒小齐、儿子和户籍警小毛共八个人物依次出场进行叙述,打破时空限制,聚焦人物内心独白和变化,不仅给读者提供了有关这一事件的鲜为人知的细节和材料,还清晰表现了他们与死者间的现实关系。整篇小说很接地气,耐人寻味。我们从中能看到社会上常见的作为冷漠看客或是爱嚼舌根的邻居、利益面前针锋相对的亲人、忘恩负义的情人、圆滑机灵的生意人、热心尽职的医生和警察等各色人物形象。
陈仓的中篇小说《通灵时间》(《芒种》2021年第3期)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讲述了失恋者与聋哑人短暂相恋,最终因不在一个世界而含恨离别的故事。题目《通灵时间》指男女主人公通过“书写”互相交流的这段时间。书写作为表达的一种方式,比语言来得更加慎重也更加缓慢。当男主人公沉浸于书写行为时,他处于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能获得一种做神仙的陶醉感,从而达到所谓“通灵”的境界。这是一个有关声音的故事。从女主人公的角度看,小说展现了聋哑人群体在城市的困境,他们处于边缘地位,难以融入健全人的生活。他们遭到排斥,被恶意揣测,并未受到平等对待,没有得到足够的包容和同情。从男主人公角度看,小说提出了关于说话的问题。大城市是嘈杂而喧哗的,我们每天都在不停地说话,制造声音也吸收外界的种种声音。可是,任何两个物体碰撞都会发出声音,制造声音只是自然界万物最基本的能力。那些我们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它们除了起到制造声音的作用外,不会在世界上留下任何痕迹。与其浪费时间在无意义的说话中,我们不如保持沉默,冷静地观察与思考这个世界。正如主人公两次拜访静安寺的法师,得到的答案都是沉默。大师说:“说话前你是话的主人,说话后你是话的奴仆。”此外,小说也呈现出了在大移民时代,人与人之间存在无形的隔阂,他们彼此防范,缺少有效的沟通,从而导致关系破裂的问题。
苑楠的小说《倒立的云朵》(《山西文学》2021年第2期)用女性第一人称写作,将一段平凡而残酷的人生在读者面前缓缓展开。梦想与现实错位造成的矛盾感贯穿于小说的叙事。作为工地上唯一的大专毕业生,“我”不甘心一辈子待在家乡,曾多次想要逃离,却都以失败告终。尽管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家乡的土地上,但“我”却是一个精神上的“异乡人”。在内心中,“我”将长期与自己生活的父亲和丈夫拒之门外,从未真正了解和关心过他们。“我”曾多次梦到最初想要带自己走的那个男人,夢到倒立的云朵。那是一个与“我”的现实生活全然颠倒的世界,轻盈、幸福、自在。正如兰波所言,“生活在别处”,这个梦象征着“我”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和幻想。最终,“我”永远地留在了家乡的土地上,但依旧和这里的其他人不同,因为“我”并没有完全麻木于既定的生活。“世界上真正的英雄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改变既定命运是我们所渴望的,但当现实不足以实现这一愿望时,我们仍应坦然面对,保持热爱,努力将理想与之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