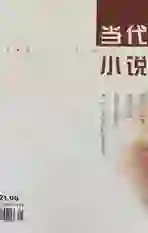像一记右刺拳
2021-05-27邱力
邱力
1
我没有想到,和莫贵生再次联系上,是十三年后一个不寻常的下午。
这天下午,我关上出租屋,准备出门。楼道里,手机微信的提示音响了起来。
“我是莫贵生。”
点开通讯录,新的朋友在向我打招呼。“莫贵生”这三个字来得很突兀,像一记刺拳,从一个我意想不到的角度,对着我被愤怒和绝望填满了的脑袋凌空一击,记忆深处那潭死水泛起波澜……一个小个子少年穿过岁月的雾霭,精瘦的身躯逐渐清晰,他提着与身体不般配的大拳头,向我走来。他挥舞着拳头,虎虎生风,那些阻挡在路上的雾障和尘埃,一击即溃。
你已添加了莫贵生,现在可以开始聊天了。
对方发来一张全国拳击冠军赛的广告宣传图片。比赛时间是晚七点,地点在六边门体育馆。这会儿,天色正在逐渐变暗。冬天里的一场雨将如期而至,街面上行人神色匆匆。我怀揣着一把被捂得发烫的蒙古刀,计划赶往南岸新区。那里,1.3万一平米的南湖豪庭内,居住着我的前女友晓芳和她的现任男友。我没有别的意思,活着真是没意思透了,有些事情你根本就没法说清楚。
加了莫贵生微信后,我站在街口,一时不知何去何从。这时候,大雨如注,如同不久前我在失去晓芳和工作后,烂醉如泥的一场呕吐。我甚至闻到了大雨中的酒臭味。雨雾弥漫,我回想起了那段热气腾腾的少年时光,回想起了在那片松树林里和莫贵生上拳击课的情景。我很想知道,这么多年不见,过去那个酷爱拳击的小矮子莫贵生如今变成什么样了?
现在是下午五时许,离拳击赛开赛时间还早。犹豫片刻,我转道前往去六边门体育馆的公交车站。
2
第一次见到莫贵生,是那年初三下学期。
莫贵生一进教室,就引起哄笑。他和高且胖的班主任并列讲台,对比强烈。他太矮了,甚至都够不上黑板的下沿,跟侏儒差不多。班主任简短介绍了几句,说他是插班生,从另一个镇来。让他自我介绍,他吞吞吐吐的,说出含糊其辞的姓名,后排有同学接话道:“哦,是魔鬼生同学,难怪啊!”又是一阵哄笑。班主任安排他跟我坐第一排。因为我贪吃,吃得浑身滚圆,又总是梦想有一天能将家中带来的馒头变成面包,同学们就叫我面包。这个小矮子跟我同桌,不是更加让我惹人耻笑吗?莫贵生小心翼翼地挨着课桌坐下,身上发出股汗馊味,撸头发时,白色的头皮屑和一些黑色的粉末纷纷落下。我嫌恶地往边上避。他露出讨好的笑,用脏旧的衣袖迅速拂拭桌面,然后掏出书本文具排列整齐。他双手和眼珠奇大,转动灵活自如,让我印象深刻。整节课我都在开小差,心情郁闷,想自己怎么这样倒霉,和一个奇形怪状的小矮子同桌?放学后,同学们大多骑着自行车,潇洒地疾驰而过,而我独自走着。不是爹妈不给我买自行车,是我笨,老是不会骑,一跨上去就摇晃着惊叫,顶多晃个一两米便人仰车翻。我对自己的愚笨失望透顶。走在路上,发现莫贵生始终尾随在我身后,我心头顿时火起,冲他吼道:“你到底想搞啥子嘛?鬼头鬼脑的。”莫贵生紧走两步:“我们是同路,我家就住在拱桥巷里。”我脑袋一下子又大了一圈,这个小矮子不仅和我同校同班同桌,还同住一条巷子。
之后,在学校我基本上不和莫贵生讲话。他也识相,清楚大家对他另眼相看,就闷头听课做作业,不和人交流来往,对大家当面背后的闲话也全当耳边风。一放学,就迅速往家赶。好几次,我看见他帮着老莫在巷口推木板车。老莫是个老矮子,但嗓音洪亮,爱骂人,骂声贯穿街头巷尾。看见老莫,你就会明白莫贵生怎么会长成了侏儒,遗传基因真是强大。老莫用木板车给镇子里的人家拉蜂窝煤和块煤,还推着辆载重自行车走街串巷收废品,车子左右两边挂着箩筐。老莫最让镇子上的人们感兴趣的一句骂语是:“个卵崽,找死!上坡不推下坡推,你要推老子去见你妈啊?”这句骂语印证了人们关于老莫没有老婆的猜测是准确无误的。莫贵生有个妹妹,读初二,长得娇小玲珑,干净俏丽,性格活泼,唱起戏来有板有眼,在学校人缘和成绩一样好。看得出来,老莫和莫贵生把妹妹当成公主来侍候。
我和莫贵生成为朋友,是在他教我学会骑自行车后。
那天下午,莫贵生骑着老莫那辆载重自行车,汇入放学的车流中。他的骑姿怪异,右腿斜穿过车子大杠,屁股和车垫不沾边。骑起来,一扭一拐,忽高忽低。尽管如此,他的速度和灵巧却丝毫不逊于其他同学,在车流中如同一尾怪鱼,悠然自得。我看呆了,心里越发瞧不起自己。在巷子口,莫贵生支着车,见我走近,就拍打着车垫说:“我这种先天不足的半残废都会骑,你也肯定会。走吧,我陪你练。”我心头一热,接过自行车车把,和莫贵生往巷外走去。那里的松树林边有块空地,清静无人。那天下午我一直练,不停地摔倒,爬起,摔倒,爬起。车链条被摔掉好几次,莫贵生两三下就把它重装上去。他扶着车身,嘴里喊着:“平衡,抬头……把稳方向……你肯定行……不要慌……”月亮升起来,月光朗朗,照在松树林里的两个少年身上,像舞台上明亮的追光灯。我终于可以平穩骑行了,并且大着胆子,放开了双手,我仰望星空,大声喊道:“我飞起来了!我飞起来了!”
次年,进入镇中学,我拥有了第一辆属于自己的“凤凰牌”自行车,那盏红色车尾灯让我脸上很有光彩。莫贵生经常和我互换着骑。他还是老样子,矮小得像个小学生,命运过早地终止了他的发育生长。但手臂和胸部比初见时长了明显的肌肉,我以为是他常常帮老莫干粗活的结果,却不知从初中时起,莫贵生就悄悄开始练拳了。老莫干活时,经常遭受袭击,袭击者多是镇上的地痞无赖,后来一些顽童也加入其中。他们将泥块瓦砾仔细瞄准老莫,像发射子弹一样射出,然后站在原地笑着观望,等候老莫叫骂或追赶。他们把袭击老莫当成了别开生面的娱乐节目。看到老莫别着一双短腿,努力奔跑的滑稽样,就如同到了节目的高潮部分。莫贵生也跟老莫追打过几回,可努力追打的结果往往是被袭击者摁倒在地上痛殴。看到莫贵生鼻青脸肿的可怜样,我劝他以后看见那些人躲远点,免得被人家当猴耍。莫贵生恨得咬牙切齿:“总有一天,老子要揍得这些狗日的哭爹喊娘。”我从他瞪圆的眼睛里看到了愤怒和仇恨。
3
我们学校旁边有个拳击馆,民办的,校长兼教练姓苏,拳头了得,黑白两道都要给他几分薄面,镇上人管他叫苏教头。要进苏教头的学校不容易,不是你交几个学费就进得了的,得苏教头亲自挑选。苏教头选中的学员,十有八九能闯出名堂。有的闯到县城或省城的体校去深造,有的闯到其他地方自立门户,开馆收徒。这在我们尚武成风的小镇着实荣光。苏教头每年都要来我们学校选学员。高一那年,周末最后一节课,苏教头又来了。我们班正在上体育课,其实也就是拿两个篮球、两把乒乓球拍自由活动。体育老师在一旁抽烟,或者到别的班去逗女老师。见到苏教头,体育老师赶紧吹哨,集合,点名。我们按高矮排成几溜。我跟莫贵生自然是排到最后一溜。苏教头在体育老师陪同下,像电视上首长检阅部队,边走边看。对个别同学,苏教头还用手捏捏肩头,让其跳跃几下。走到我和小矮子莫贵生跟前,苏教头眯着眼,上下扫视莫贵生。他让莫贵生伸展臂膀,出列,在操场上来回跑了一趟。最后,对莫贵生点点头,又摇摇头,一句话没说,走了。
第二天,传来消息,说是我们班上只有周大宝被苏教头选中。另有消息说,周大宝被选中主要是因为他爹是苏教头的师兄,还因为周大宝他爹是镇派出所所长。也就是从这时开始,落选的莫贵生自己上起了拳击课。
地点在拱桥巷外那片松树林里。
莫贵生在两棵松树间架根竹子,一块不知从哪儿捡来的帆布被改装成了沙袋,吊在竹子下,沉甸甸的,让人担心随时会折断竹子,坠落于地。地上散乱放着拳击手套、跳绳、哑铃。我作为唯一被邀请参观莫贵生拳击课的人,乍一见这种阵势,荣幸之余,也情不自禁地跳过去,朝沙袋挥出两拳。也不知莫贵生的练拳方法是如何琢磨出来的,除了朝沙袋挥一顿乱拳,就是绕着几棵松树打,好像松树成了他的对手,且越打越快。在莫贵生怂恿下,更是为了减肥强身,我跟着莫贵生练起了拳。我们商量好,悄悄练,等练出名堂再去找苏教头,当面演示给他看,让他后悔。这堂学校之外的拳击课,成了我和莫贵生共同守护的秘密。
我们这个秘密仅仅守了不到三个月,就被人发现了。同样守不住秘密的是莫妹和周大宝,他们早恋,并且莫妹日益挺凸的肚皮使他们的秘密彻底败露。
学校的高音喇叭响起来时,我们都意识到,有大事发生了。紧急集合,操场上都是黑压压的人头,大家小声交头接耳,猜测到底出了啥事。当教导主任领着莫妹和周大宝走上主席台时,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到了他们身上。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件当众宣布的大事竟是勒令莫妹和周大宝退学。校长念完学校的处分决定后,教导主任仿佛为了证实学校的决定是英明的,点着莫妹的头,叫她向台前走。莫妹走得很艰难,一步一挪,挪到台边。教导主任用右手食指点着莫妹的肚皮,痛心疾首地对我们说:“同学们,你们看看,成何体统,都五个月了。像啥子话嘛!”莫妹像被判了刑的犯人,低下头,浓密的头发遮住了脸。台下,莫贵生高昂着头,双拳紧握,两眼通红。
莫妹坠了胎,在家中闭门不出。一个多月后,周大宝重返校园,若无其事一般。莫妹再次出现在镇上时,挥舞着一方红纱巾,唱着戏词。那时,暮色如群鸦纷飞,漫卷全镇。她舞着唱着,一路脚步飘摇,似乎是戏子在舞台上表演。镇上有认得她的熟人,就喊莫妹莫妹,但莫妹入戏太深,对所有人置若罔闻。她舞到镇派出所时,人们这才听清楚,莫妹唱的是《天仙配》选段。只是原本男女二人的唱腔,莫妹一个人全包了。她还将唱词里的“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改编成了“大宝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大宝浇园”。就这两句,她站在派出所红砖楼前反复吟唱,声情并茂,如泣如诉。人们明白,莫妹这是唱给居住在楼后平房的周大宝听,顺便也唱给即将下班的周所长听。正唱得人心慌乱,周所长披着警服踱出来,叼着烟,乜斜着眼,一挥手:
“滚!老子X你妈的,疯了?!”
莫妹真的疯了。
她是我们镇上最年轻漂亮的女疯子。她最喜欢去的地方,一个是我们学校,一个是镇派出所,最百唱不厌的两句就是:“大宝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大宝浇园。”起初,人们都还很感兴趣,对莫妹的唱腔和仪态品头论足,久之,便不胜其烦,烦的是莫妹那种执着和忘乎所以。于是,莫妹在学校和派出所,也遭受到了泥块瓦砾的袭击,也经常鼻青脸肿。老莫变得愈发苍老。他带着莫贵生去找过校方,甚至在派出所楼前下跪,乞求周大宝能出来和莫妹见面,送几句软话给莫妹。但这一切都是徒劳。
这时,我和莫贵生一度中断的拳击课又重新开始了。
莫贵生将周大宝、周所长、校长和教导主任等人的姓名用圆珠笔写在沙袋上,用小刀刻在树上。他戴着拳击手套打,后来干脆脱了手套,直接用一对裸拳去打。他提起铁锤般大小的拳头,双目圆睁,两腿微蹲,气沉丹田,面向沙袋和树,左一拳右一拳,打着打着,我看见他两只大眼睛里泪水夺眶而出。时间长了,沙袋和树上留下斑斑血迹。松树被击打得枝叶乱颤,照耀在枝叶上的阳光被击打得支离破碎,刻在树身上的姓名被击打得模糊不清,我们镇上部分群众被击打得失魂落魄。这响彻全镇的拳擊声,如同丧钟一般。
莫贵生要我也找几个仇恨的人,写在沙袋上痛打。我使劲想了想,实在想不出值得我这样做的人。我担心再这样打下去,莫贵生也要疯掉。莫贵生有时候一连几天不见踪影,不知跑哪儿去了。空荡荡的松树林里,只有孤独的拳击沙袋在风中晃动,说不出的寂静。
4
事情发生时,我不在场。这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遗憾的事之一。我那天摸底考试考砸了,班主任把我留下来,用诲人不倦的语调重申为高考做最后冲刺的重要性。我明白,班主任这是拿我死马当活马医了。这时候的莫贵生已连续一周不来学校上课了,大家似乎已经逐渐将他遗忘。
莫贵生在和周大宝斗拳,莫贵生赢了。
这事我是听鸡精说的。鸡精是苏教头拳击馆的学员、周大宝的师弟。我离开学校时,天色已晚,快走到巷口时,见一伙人围着鸡精正闲扯淡。隐约听到“小矮子莫贵生”、“没想到打趴在地下的是周大宝”等语句,就停下脚步,凑过去,央求鸡精再说一遍。我说了一箩筐恭维话,还搭上一包“红塔山”,鸡精才满脸不屑地看了我一眼,重述了这场赛事。
“……都是他妈周大宝自找的,这个憨卵,这下糗大了……丢自己脸面是次要的,把苏教头的脸和他爹的脸都丢尽了……还硬拉我们去助阵,说是小矮子莫贵生天天揍他一家人的名字,他爹肺都气炸了,不教训教训这狗日的,真不晓得锅儿是铁铸的……我们把莫贵生喊到拳击馆来,嘿,都以为他打的是野拳,上不了台面,他妈的一上来,那拳法、腿法、防守、进攻,特别是刺拳,速度和角度又快又刁,完全是受过正规专业训练的嘛……”
我插话道:“莫贵生打拳全靠自学,我可以作证。”
“自学?自学能把我们拳馆第一高手KO了?哄鬼吧你!”
“那他跟谁学呢?苏教头又不收他。”
“鬼晓得啊,你到底还听不听?不听拉倒。”
“听,听,听,你是专业人士,讲详细点行不?”我赶紧给鸡精点上第二支红塔山。
“……一开始,就看得出来,莫贵生是有备而来,周大宝轻敌了。连续几个回合,莫贵生都在挨打中防守。你别看他个子小,抗打能力相当强,肯定是作了针对性训练。猛打猛拼中,消耗了周大宝大量体能……莫贵生看准机会,一个后手重拳打中了周大宝的面部,周大宝的左眉弓被打开花了,血流不止。涂了凡士林,又打。最后,周大宝被莫贵生逼得越打越乱,莫贵生一个右刺拳直接打掉了周大宝嘴里的牙套……”
说实在话,鸡精口才的确好,绘声绘色,还不时出拳比划一番,一会儿扮演莫贵生,一会儿扮演周大宝,让人如同身临其境。
第二天傍晚,我在松树林里见到莫贵生。他正在收拾练拳的器具。我问他昨天和周大宝斗拳的事情,他不说。问急了,他答非所问地说:“我一会儿就走,离开这里。周大宝一家不会放过我的。”
我说:“去哪里呢?不高考了?”
他说:“我不能讲,都联系好了。高考不是为我这种人准备的。”
我说:“你在外面拿啥子生活?”
他说:“打拳挣钱。”
翌年,我出人意料地考上了三本,录取学校是一所省外的职业学院。爹妈比我还兴奋,以为从此以后,我将交上好运,离开小镇,在广阔天地间翱翔。此时,莫贵生已于我先行离开小镇有半年之久。不知他去了哪儿。毕业后,我随着几个熟识的同乡去省城闯荡,这也是爹妈的意思。他们希望我像其他有出息的年轻人一样,扎根在大城市里,工作娶妻生子,然后逢年过节携妻带子大包小包地回来,在镇上人面前挣得足够的脸面。他们不知道,我在省城已是四处碰壁走投无路了。夜深人静,在还没有喝得不省人事时,我躺在出租屋阴暗的角落里,脑海里时常浮现出那片松树林,那属于我和莫贵生的拳击课。黑暗中,那连续不断的拳击声击打在我颓废绝望的心房上。我想把那些欺负我的人的姓名写在墙壁上,或者买个拳击沙袋来,写在沙袋上,吊在屋子里,每天痛打一顿,发泄心头仇恨。期间,我也回过几次家。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太适应小镇的生活方式,而省城的生活又没着没落的,就待在家中,不想出门。听爹妈闲聊,聊到莫贵生,引起了我的兴趣。
有一年,莫贵生独自回来。他右手戴着一副漆黑的手套,始终不见取下来。有人猜测他的右手残了,有人猜测他是在练什么厉害的拳术。莫贵生身子骨变得壮实,目光很凶,好像和全镇人有仇似的。见到我爹妈,还晓得主动问个好,姨和叔地喊,还问过我在省城的情况。镇上人都觉得要出大事。隔天,周所长就发出邀请,请莫贵生去吃饭,在镇上最高档的狮子楼。周所长退了休,但大家仍称他周所长。递请帖的人竟是苏教头。苏教头的拳击馆已经易了主。新馆长是周大宝。大名鼎鼎的苏教头在我们学校附近租了间小门面,专门兜售一些假冒伪劣的小商品。莫贵生二话不说,孤身赴宴。当晚,狮子楼被周家包了场。拳馆的人将整个楼把守得密不透风。至于这个宴席是怎么吃的?席上客人有哪些?这些人又在宴席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镇上人一概不知。让人们大失所望的是,狮子楼里并未血流成河。但第二天一早,莫贵生、老莫、莫妹以及苏教头从此竟然消失无踪。
5
半个月前,我和女友晓芳分了手,顺带着和打了一年工的公司也分了手。事情真是糟透了。这几年,我的女友和工作总是换来换去,像每天面对冰冷的电脑,进入既定程序,身不由己地用鼠标去点击“下一步”。我现在进退两难。如果早几年,我把自命不凡的脸面掖在胳肢窝里,离开这个让我遍体鳞伤的城市,回到小镇,过庸常的生活,不再奔跑,不再梦想,那该多好。晓芳的离开,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这年头,哪个傻逼愿意跟你成天挤在出租屋里,虚构美好生活,回忆陈年旧事?我曾经和晓芳聊过莫贵生的故事,晓芳问我莫贵生后来怎样了?我开玩笑说,莫贵生也许加入了黑社会,也许正在被人追杀亡命天涯,反正像他这种人,日子好不到哪里去。
晓芳提出分手的时候,我倒没怎么激动,但发现她竟然跟我现任老板好上了,我不得不愤怒。那天,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在省城滚打的这些年,开始时我还听得到各种声音,车流声、键盘声、低语声、脚步声、门窗声,后来,所有的声音都无影无踪——不是我听觉出现障碍,是它们融化在空气中,或者隐藏在我的身体内部了。
“不弄出点响声,我他妈比死了还难受。”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知怎么,当时,我脑海里不时闪现出莫贵生打拳的模样,那拳头呼呼有声,带着一种疯狂的愤怒。没有任何人理睬我。
我的右手在颤抖,看来非弄出点响声来不可。我径直走到公司进出口的玻璃门前,朝它挥出一记漂亮的右刺拳,就像那时候在那片树林里,和莫贵生练拳时的招式一样。玻璃门应声而碎,唏哩哗啦,动静挺大。碎片像寒冬腊月的雪花铺满我的脚边,看上去很暖和,我为终于完成一个心愿而感到高兴。我不明白到底怎么了,竟然会朝一扇玻璃门发脾气。玻璃门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这个世界是无辜的,那谁来为这一地的玻璃碎片负责?办公室里所有人都一起看着我,脖子伸得长长的,像一群引颈待宰的鹅。我虚张声势地啐了一口,冲出办公室,把死一样的寂静扔在脑后。一路上,那响亮的破碎声仍在耳畔萦绕,也许会经久不息,也许这是我几年来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了。
公交车在大雨中前行。
透过被雨水打湿的车窗,模糊中,那些不断浮现的少年时光随着车轮向后隐退。车子在夜晚的雨水中缓缓前行。车至六边门,雨水越发稠密。天地喧哗,空气清爽。我忘了带雨伞,一直麻木的身体,被雨水刺激得苏醒了过来。雨水渗透衣服,将原本发烫的蒙古刀浸得凉润。体育馆门前,聚集了一群人,灯光璀璨中,这伙拳迷的脸庞和声调兴奋异常。门的两侧,立着相对着的几张巨幅喷绘的拳赛宣传画,进口处的上方悬挂了一幅面积更大的喷绘。画面上,两个拳击男人摆出一副很酷的出拳和防守姿势。其中出拳的那位戴黑色拳击手套,赤裸的上身闪着光,肌肉紧绷,两腿微屈。我认出是莫贵生,他打出的是一记右刺拳,带着穿破黑夜的风声。莫贵生原本矮小的身形被放大数倍后,俨然成了巨人,须仰视才能看清全貌。我随着人流朝前走。我看到,在另一幅画中,有莫贵生和苏教头的合影。莫贵生右臂搭在苏教头左肩上,苏教头左臂搭在莫贵生右肩上,兩人同时向前伸出大拇指。他们微笑着望着我。他们师徒情深,又情同父子。
责任编辑:王玉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