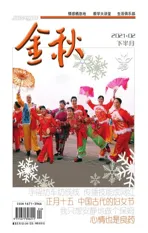樱花盛开又落下
——沉樱与梁宗岱的爱情
2021-05-27潘彩霞
◎文/潘彩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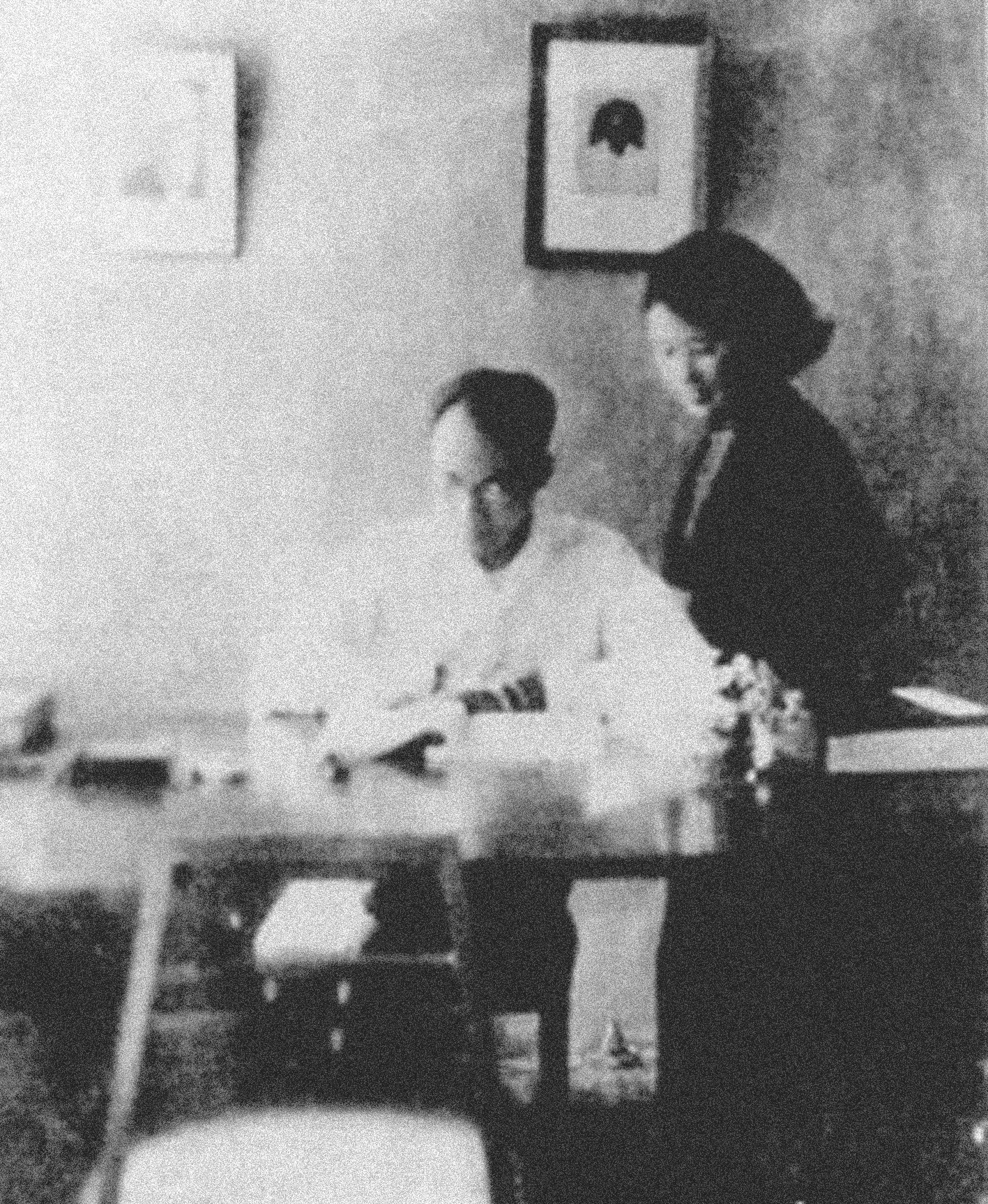
1931年,因丈夫移情别恋,24岁的沉樱结束了一段短暂的婚姻。她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那时已是文坛耀眼的明星,出版过三部小说集,茅盾和沈从文都曾对她大加赞赏。
离婚后,沉樱迁居北平,慈慧殿三号是她最常去的地方。朱光潜和他的留法好友、28岁的北京大学法文系教授梁宗岱住在那里,他们办的“读诗会”吸引了大批文艺青年来此切磋。那一年,梁宗岱刚刚回国不久。他自幼才气过人,16岁就被誉为“南国诗人”,又在欧洲留学多年,精通多国语言,在文学、翻译上有极高造诣。
频繁的相处中,他与沉樱惺惺相惜,相爱了。那电光火石的一瞬,后来被梁宗岱写进诗里:“我不能忘记那一天/我们互相认识了/伊低头赧然微笑地走过/我也低头赧然微笑地走过……”
1934年,梁宗岱去日本,沉樱陪他。红袖添香,岁月静好,在叶山一间精致可爱的小屋里,梁宗岱安静地写作、翻译。在给法国诗人瓦莱里的信中,他说:“我精神比任何时候更加活跃,更加一心孜孜于自我完善的求索。”
笑靥洋溢在眉梢眼角,得知巴金想来日本时,他们多次在信中热情邀他同住。几个月后,巴金真的来了,他目睹了他们的快乐:“在松林中的安静生活里,他们夫妇在幸福中沉醉了。我在他那所精致的小屋里亲眼看见了这一切。”
宁静温馨的一年中,梁宗岱翻译了歌德、瓦莱里等众多名家的诗作,后结集为《一切的峰顶》。朝夕相处中,他的阅读习惯、翻译风格和思想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沉樱。1935年5月底,他们返回北平,正式结婚。
婚后,梁宗岱应邀到南开大学任教,沉樱继续小说创作,巴金约她写一本《叶山札记》,她欣然应允。可是陷于家务,又兼孩子出生,写作的脚步不得不慢下来。
抗战爆发后,一家人辗转到重庆,住在郊外的北温泉,梁宗岱完成了著名的十四行诗《我们底幸福在夕阳里红》。然而这幸福,是以沉樱的牺牲为代价的,两三年过去了,巴金的约稿,她一个字也没有写。在信中,她讲述了自己的日常:“天天为换佣人操心,难得一刻清静,文章的事虽然时刻惦记在心里,但几次勉强去写,身心都不允许写下去。总之,我的文章不能交卷,现在是定了。万分的对不起,请接受我的道歉吧。”
困于生活琐务,早已没有了写作的心境,只是偶尔,也会怀念伏案的日子,郁闷之余,免不了冲梁宗岱发发脾气。可他既不理解,也不谦让,再加上爱吹嘘的性格,于是有了吵架。二女儿出生后,沉樱更加忙碌了。
1943年,战争中本就不平静的生活又迎来惊涛骇浪——梁宗岱回广西百色处理亡父遗产事宜时,竟然移情粤剧演员甘少苏,不仅多次为她写诗,还倾囊助她赎身,明知这样做会伤害沉樱,仍大张旗鼓宣告结婚。
“合欢花下立,双双笑语融融”已成过去。没有声讨,没有控诉,沉樱带着两个女儿搬到了重庆南岸海棠溪四妹的住处。几个月后,儿子思明出生。
回到重庆后,梁宗岱想求得谅解,不时去找沉樱,有一次还亲自牵着一只奶羊步行送过去。在三妻四妾合法的社会里,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错。可是自尊心极强、又受过“五四”洗礼的沉樱,绝不接受这样的“三人行”。正值蒋介石招安,梁宗岱不愿卷入政治,他辞掉教职回到百色定居。
抗战胜利后,沉樱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上海任教。得知消息后,梁宗岱随后赶来,希望接他们去广州同住,沉樱拒绝了。阅读、教书、育儿,她有勇气和底气独自面对生活。受好友赵清阁之约,辍笔八年后,她欣然执笔,写了短篇小说《洋娃娃》,风采不减当年。这是她在大陆最后的作品。
1948年,带着三个稚龄儿女,怀着一颗痛苦的心,沉樱跟着母亲、弟弟去了台湾。临行前,她对赵清阁说:“要走得远远的,永世不再见到梁宗岱!”可是她的行李中,不多的几本书中,其中就有梁宗岱的《一切的峰顶》。
既恨,也爱。多年后,沉樱这样解释分开的原因:“和他分开,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他很有钱,是一个有双重性格的人。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则,我是很难脱身的。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决不顺着他,大概这也算山东人的脾气吧。”
盟约既毁,她便走得毅然决然。
到台湾后,沉樱在乡下的一所私立中学教书。环境清幽,生活安定,“精神之舒畅前所未有”。教书理家之余,她把兴趣转向了英文小说的阅读和翻译。夜晚的灯光下,母亲静坐念佛,三个小儿女并头酣睡,沉樱自己则“伏案执笔乱涂细改”,那是她向往的小快乐。
然而终是异乡,每每看到盛开的杜鹃花,耳边便响起杜鹃“不如归去”的啼声。随着两岸局势紧张,和大陆的通信彻底中断。靠着一份教职和业余写作,她以一己之力承担了三个孩子的生活和教育。
译著不断发表,沉樱意识到,她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对文字的运用,包括爱引用蒙田的句子,无一不受着梁宗岱的影响。
他的印记无法抹去,孩子们相继赴美留学、工作后,孤独中,尘封的情感重又启动。1963年除夕,沉樱给在美国的女儿写信:“‘一夜乡心五处同’。此刻我想起这些千古名句,深深体会着往昔那种音讯不通、生离近似死别的凄惨……”
除去母子四人,这第五处,便是梁宗岱。转瞬十年,不思量,自难忘。离开时,他们并未正式离婚,她仍是“梁太太”。在与台湾朋友们的通信中,她的落款始终是“梁陈瑛”。她不经意写在纸上的,常常是他写给她的那些缠绵文字。
退休后,沉樱动了自己印书、送朋友做纪念的念头。就这样,译著《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面世了,谁料竟如彗星般照亮了文学的天空,一版再版,仍供不应求。受到鼓舞,她一鼓作气出版了译著系列《蒲公英丛书》。得益于在婚姻中汲取的养分,二十年后,她终于与翻译家梁宗岱殊途同归。
性格棱角已被时间磨去。二女儿思清回大陆探亲,见了父亲后,带回一些梁宗岱手稿。翻看着熟悉的笔迹,沉樱心潮起伏。那一刻,怨恨灰飞烟灭,她提笔给他写信:“时光的留痕那么显明,真使人悚然一惊。现在盛年早已过去,实在不应再继以老年的顽固。在这老友无多的晚年,我们总可称为故人的。我常对孩子们说,在夫妻关系上,我们是怨藕,而在文学方面,你却是影响我最深的老师,至今在读和写两方面的趣味还是不脱你当年的藩篱。”
“藕”通“偶”,个中滋味,难以言表。通信恢复后,字里行间不乏温情,聊到儿子时,她说:“不服输的毛病(像你),遇事过于和善迷糊(像我),”完全是亲昵夫妻的口吻。隔着时间与空间,他们再次触摸到甜蜜与温馨。
71岁时,沉樱赴美与儿女团聚,那时,她已被“帕金森”病折磨。老病相催,更加思念故土。1982年,阔别三十多年后,她终于回到大陆。逗留的几个月里,老友欢聚一堂,梁宗岱赶到北京多次求见,她却没有答应。也许,她情愿让记忆停留在青春岁月,那时,容颜未改,那时,情感依旧。
回到美国第二年,传来梁宗岱去世的消息。遗憾总是有的,当林海音因编书需要,向她要几张和梁宗岱的合照时,她催促儿女:“赶快找出来挂号寄去!”当有个晚辈说,在复旦读书曾师从梁宗岱,所以应称她“师母”时,她“双颊微红,微微笑了一下”;听到梁宗岱去上课,他饲养的山羊跟在身后亦步亦趋的趣事时,病中的她饶有兴味,笑眯眯地说:“他就是那德性!”
爱与恨,都付笑谈中。1988年4月,樱花飘落时节,沉樱在大洋彼岸去世。如她留下的文字一样,爱与人生,干干净净,璀璨又隽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