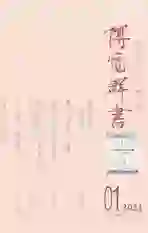《小说月报》为什么如此“译介”
2021-04-27高志强
高志强
五四时期,俄国革命的巨大变化吸引了探索民族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瞿秋白说:“大家要追溯他的原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研究俄国社会和文化,一时之间成为知识界的风气。对俄国文学的译介高潮也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勃然兴起,出现了一大批热心译介和研究俄国文学的翻译家、学者,俄国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被大量引进,种数之多,迅速超过英法等国,极一时之盛,而这与《小说月报》的大力倡导鼓吹分不开。俄国文学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是《小说月报》在革新的第一年、以专号形式最先聚焦的对象。
从1921年到1931年,《小说月报》的翻译文学以俄国数量为最多,并远远超出次之的法、英、日等国。仅从1921年到1923年这三年来看,除了《被损害文学专号》外,其他各期都有俄国翻译文学,绝大多数时候(仅有一两次例外)数量都居当期译作之首,极为引人注目。1921年9月,革新第一年的《小说月报》推出的第一个号外,就是《俄国文学研究》,分为论文、译丛、附录和插图四个部分,对俄国文学作了全面的介绍。号外发表了20篇论文,如郑振铎《俄国文学的启源时代》、沙洛维甫著、耿济之译《19世纪俄国文学的背景》、沈雁冰《近代俄国文学家三十人合传》、鲁迅《阿尔志跋绥甫》、郭绍虞《俄国美论与其文艺》、沈泽民《俄国的叙事诗歌》等,涉及文学史、文艺理论、作家研究、作品分析、文类研究、艺术批评等多方面内容;选译了29篇作品,上自普希金,下迄高尔基,其中还包括赤色诗歌(《国际歌》)和三篇赤色小说。这样大规模的翻译介绍,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是可想而知的。1923年,《小说月报》14卷5至9号连载了郑振铎著《俄国文学史略》,共14章,后整理成书,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体例严谨,脉络清晰,资料翔实,书目完备,是国内最早的一本俄国文学史专著。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小说月报》的翻译活动中,对俄国文学的译介占据了最为重要的位置。
《小说月报》为什么如此重视俄国文学的译介呢?最主要的原因有两点。
其一,国情相似性所引起的情感共鸣和思想暗示。周作人在《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一文中谈到:
我的本意只是想说明俄国文学的背景有许多与中国相似,所以他的文学发达情形与思想的内容在中国也最可以注意研究。
…… ……
他(俄国文学)的特色是社会的、人生的。俄国的文艺批评家自别林斯奇以至托尔斯泰,多是主张人生的艺术。……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将来的新兴文学,当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
俄国也是一个古老的国度,和中国一样,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也经历了长期的集权专制时期,同样是晚近时期才受到西方文明影响,开始近代转型。在西方中心话语中,俄国也是被打上“落后”“不发达”烙印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处于被压迫民族的弱势地位。而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社会也是处在苦苦探索出路、各种矛盾尖锐冲突、各种思潮激烈震荡的时期,就俄罗斯的民族精神而言,也同样充满了苦难和沉重的记忆。这些特点都与中国的情形相似,特别是同处于被压迫地位,容易激起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共鸣,而俄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其在社会变革、民族文学建设等方面取得的经验,特别是19世纪俄国文学所取得的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也会对中国知识者形成一种思想暗示,使后者获得鼓舞,看到希望,相信被压迫民族也一样能产生伟大的文学和精神,并从而振兴民族。鲁迅在1932年写道:
15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壇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上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予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
…… ……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对《小说月报》同人来说,文学从来就不是独立于民族国家现实之外的,而俄国文学基于上述种种社会历史原因,显然比西欧诸国文学更能为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文学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小说月报》译者对俄国文学情有独钟,也就很自然了。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俄国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特点,与文学研究会和《小说月报》“为人生”的文学观正相印合。鲁迅曾说,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具体而言,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为人生”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深广的社会性。他们始终怀着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关注俄国现实,批判社会,批判国民性。在《小说月报》同人看来,西欧现实主义作家笔下尽管也有对社会的批判,但往往着重批判社会的一个方面,对社会作整体性的批判反思的作品并不多,而很多俄国作家则总是力图把自己的关注对象扩大到整个社会和民族性的广度和高度,例如果戈理在谈到他的《死魂灵》就说:“我想在这部小说里至少从一个侧面表现全俄罗斯”,“全俄罗斯都将包括在那里面”。这样的视野胸怀使得俄国作家的作品常常具有一种洞察社会与人生的深刻力量,在反映社会人生的广度和深度上也具有一种雄浑的气势。沈雁冰在《近代俄国文学杂谈》一文中对此曾有明确的评价。“为人生”的另一落实点就是俄罗斯文学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传统,从普希金的《驿站长》、果戈理的《外套》,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到契诃夫的小说……俄国作家始终关注底层“小人物”的命运,满怀同情地描写他们的不幸和挣扎,表现他们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生命运,所以周作人在《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一文中指出:
俄国的文人都爱那些“被侮辱与损害的人”,因为——如安特来夫所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不幸,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伽尔洵,科罗连珂,戈尔奇,安特来夫都是如此。
沈雁冰比较西欧和俄国现实主义作家时也说:
英国作家狄更思未尝不会描写下流社会的苦况,但我们看了,显然觉得这是上流人代下流人写的,其故在缺乏真挚浓厚的感情。俄国文学家便不然了。他们描写到下流社会人的苦况,便令读者肃然如见此辈可怜虫,耳听得他们压在最下层的悲声透上来,即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那样出身高贵的人,我们看了他们的著作,如同亲听污泥里的人说的话一般,决不信是上流人代说的。
很显然,《小说月报》同人敏锐地把握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最突出的特点,并自觉地将其与西欧现实主义进行比较,既指出它们都具有关注现实、细致描写的共性特点,也强调俄国现实主义的独特之处。与西欧现实主义作品相比,俄国文学这种鲜明的“为人生”特点显然更能使那些关注现实人生、怀有强烈使命感的中国作家产生“心有戚戚焉”的感受,因此,毫不奇怪,作为成熟的“为人生”的文学范本,俄国文学成为《小说月报》最重要的译介对象。鲁迅后来回忆道:
为人生,这一种思想,在大约20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绍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出现于文字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那时组织的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会,也将他们算作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
至此,我们已经不难了解,正是国情相似性引起的情感共鸣和思想暗示,以及“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特点所激发的观念应和,构成了《小说月报》译介者高度青睐俄国文学的时代背景。
此外,《小说月报》对于被损害民族文学的译介也是其翻译文学的重要内容和特色之一。1921年,在推出“俄国文学专号”的同一年,《小说月报》12卷10号推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包括引言一篇,介绍波兰、捷克、塞尔维亚、芬兰、新犹太、小俄罗斯等国文学的论文七篇,波兰、希腊、芬兰、保加利亚、捷克、塞尔维亚、乌克兰等国的小说十篇和诗作十篇,等等。
对于被压迫民族文学的关注,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是从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开始的,当时收录了短篇小说16篇,童话寓言若干,重点介绍了北欧和东欧弱小民族国家的作品。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回忆:
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所求的作品叫喊和反抗,勢必至于倾向于东欧。
很显然,译者意图在于引起同样遭受侵略压迫的国人的心理共鸣,激起他们的反抗和斗争。但是由于当时中国译界的整体风气是,从作品选择而言倾向西欧强国,从翻译策略而言采用意译,而周氏兄弟选择弱小民族文学作品,提倡直译,虽有开风气之功,但在当时的读者中却反响不大。这也说明,在翻译文学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中,接受环境同样是相当重要的一环。五四时期弱小民族文学能够产生影响,和时代与社会的整体氛围、读者素质的普遍提高、译界风气的根本转变等因素是分不开的。
对于为什么要研究和译介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小说月报》编者是这样说的:
一民族的文学是他民族性的表现,……要了解一民族之真正的内在的精神,从他的文学作品里就看得出。
…… ……
凡被损害的民族的求正义求公道的呼声是真的正义真的公道。……他们中被损害而向下的灵魂感动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亦悲伤我们同是不合理的传统思想与制度的牺牲者;他们中被损害而仍旧向上的灵魂更感动我们,因为由此我们更确信人性的沙砾里有精金,更确信前途的黑暗背后就是光明!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编者推出这样一个专号,和当年的周氏兄弟有着同样的思路:通过被损害民族与中国同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国情相似性,激起人们的心理共鸣,或是因其不幸而同情,或是因其奋发而振作。不久之后,沈雁冰在《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更进一步明确地阐发了自己的意图:
我鉴于世界上许多被损害的民族,如犹太如波兰如捷克,虽曾失却政治上的独立,然而一个个都有不朽的人的艺术,使我敢确信中华民族哪怕将来到了财政破产强国共管的厄境,也一定要有,而且必有不朽的人的艺术!而且是这“艺术之花”滋养我再生我中华民族的精神,使他从衰老回到少壮,从颓丧回到奋发,从灰色转到鲜明,从枯朽力爆出新芽来!在国际——如果将来还有什么“国际”——抬出头来!
结合这两段话,《小说月报》大力译介被损害民族文学的动机和目的就非常清晰了。编者希望,或者说相信,首先,相似的国情可以激发人们对于被损害民族文学的接受兴趣;其次,其他被损害民族文学的成就,可以带给中国读者强烈的心理暗示,激励国人建设新文学;再次,文学可以振作民族精神,最终实现强国理想。可以看出,《小说月报》同人的基本理路是:弱小民族的现实—其民族性—其文学—中国文学—中国民族性—中国现实,而其最基本的前提仍然是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在这样的接受前提下,《小说月报》对于弱小民族的译介,显然不是从艺术性标准出发,因此技巧的选择在其次,而现实的因素则是重要的标准了。同时也应指出,有关“被压迫民族”的话语就其本质而言,实际上是对东北欧弱小民族的一种想象性认同,它反映着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在现实危机中的某种自我认定。归根到底,是出于迫切的现实需求而产生的文学和翻译策略。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