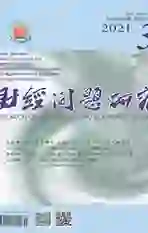智能绿色增长、生活方式与社会—政治范式的重构
2021-04-25杨虎涛
杨虎涛
摘 要:从传统增长模式向智能绿色增长模式转型,是使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能源和材料的“节约”以及新的绿色经济部门的“创造”,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和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技术,使绿色与增长的“兼容”成为可能。但新技术只构成智能绿色增长的供给侧力量,要将技术内蕴的绿色增长潜能得以充分释放,还需要生活方式的重构,从而在需求侧引导新部门创造,通过规模引致创新,促进智能绿色技术的生产率提升。但无论是技术本身的发展,还是生活方式的重构,都需要社会—政治范式的协同。
关键词:智能绿色增长;高质量发展;生活方式;社会—政治范式;技术—经济范式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1)03000310
一、引 言
继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等重要论断之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首次提出“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2019年11月到2020年3月的四个月时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文简称“发改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下文简称“工信部”)等部委又联合出台了《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总体方案》和《关于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法规政策体系的意见》等重要政策。党中央和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是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成为普遍形态”这一理念的反映,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绿色发展之路的坚定信心。绿色成为普遍形态,是对中国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经济结构到发展方式的长期要求。其中的“普遍形态”意味着从最终目的而言,创新、协调、开放和共享都要最終汇聚于是否实现、承载和助推了绿色。
但是,应当认识到,脱离增长谈绿色,或者脱离绿色谈增长,都是对高质量发展理念的误读。高质量发展并不是不要增长,高质量发展强调的只是质量要求更高、目标更为多元的增长。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绿色不是要放弃、停止或缩减生产活动,而是要强调绿色的维系、创造和修复本身就是一种财富创造,是要强调生产、消费、流通在生态意义上的可持续。因此,不仅绿色,而且绿色增长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
绿色能否、以及如何与增长兼容?基于对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智能制造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以及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前景,以Perez和Mathew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认为,智能绿色增长(Smart Green Growth)将是同时解决西方经济长期停滞、新兴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增长和落后国家发展需要的终极方案。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1]。新技术只提供了绿色增长供给侧的可能性,要将其转换为现实,不仅需要来自需求侧的生活方式的变革,而且还需要发展方式的观念革命。技术—经济范式的潜能不会自然释放,只有通过适当的社会—政治范式引导,智能绿色增长才能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底色。
二、从稳态经济到智能绿色增长:供给侧的革命性变化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能源和环境问题发起了广泛的讨论,增长的极限和罗马俱乐部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这场讨论对后续环境与生态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其中,尤具代表性的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根、博尔丁和戴利为代表的稳态经济观(Steady State)。
所谓稳态经济,即一个人口和商品库存维持在恒定水平的物质和能量流通率最小的经济体系。博尔丁称之为“宇宙飞船经济”。稳态经济意味着两个系统之间的平衡,第一个系统是物质财富系统,第二个系统是人口系统,这两个系统不会自我恒定,只有两者都处于低的流通率时,可持续的稳态才会出现。对于人口系统,低流通率意味着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对于财富系统,低流通率意味着使用期限更长或商品的耐用性更好,以及花费在生产上的时间更少而获得更多的休闲时间。稳态经济的本质是没有增长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这样的措词只有在被理解成没有增长的发展时,对经济才有意义——即在地球生态系统生成和吸收能力许可的范围内,一个由物质—能量产生所支持的持续稳定的物质经济基础和质量改善”[2]。
稳态经济建立在罗根的低熵稀缺理论基础之上。按照低熵稀缺理论,太阳是人类社会低熵的唯一来源,虽然太阳低熵存量充裕,但地球捕获的太阳低熵流量有限。由于低熵向高熵转换的过程不可逆,因而低熵稀缺成为最终约束。而工业化生产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消耗低熵和生产高熵废弃物。按照热力学定律,物质和能量只能被转换,而不能被创造。在纯物理的意义上,经济过程仅仅是把自然资源(低熵)转换为废弃物(高熵)的过程,是一个利用低熵产出高熵的过程,经济效率的本质是低熵使用的效率。而任何技术都要用物质去获取能量和利用能量,并以此消耗更多的物质,不能回收利用的能量和不能百分百回收的物质只可能给人类造成废热污染,由于生命过程和气候现象都是由温度调节的,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也正因如此,稳态经济就成为唯一可行的选择。
按照稳态经济观,只有低消费、低生产和低人口增长率的经济才是可持续和可接受的。Roegen[3]就此提出了八点具体建议,即彻底禁止武器生产而将生产能力用在建设性目的上、资助不发达国家、控制人口增长使之在有机农业的可维持水平上、避免能源浪费、放弃奢侈品生产、摒弃时尚、使商品耐用、重新平衡休闲和工作时间。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稳态经济观及其政策建议无论是对于还处在黄金三十年余温中的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对于迫切希望通过工业化实现赶超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显然都是不可接受的,稳态经济被普遍视为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尽管如此,罗根等将经济社会系统和自然环境系统视为一个整体巨系统的思路,一反长期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的自然—社会二分法,成为后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生态问题的出发点。
在英国苏赛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SPRU)1973年集结出版的“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A Critique of‘The Limits to Growth”(《思考未来:对“增长的极限”的批判》)一书中,以Freeman为代表的SPRU学者们首先否定了稳态经济理论。在Freeman等看来,不加遏制地浪费资源的确将是灾难性的,但问题不在于停止增长,而是在于调整增长的方向,稳态经济的倡议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不负责任[4]。1992年,Freeman[5]又进一步提出了绿色技术—经济范式(Green Techno Economic Paradigm),他认为,信息通讯技术革命使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两者可以兼容,原因在于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建立在廉价能源和材料的基础上,但信息通讯技术改变了传统技术—经济范式的关键特征,灵活的生产模式可以实现能源和材料的节约。在信息通讯技术条件下,浪费不仅是可以避免的,甚至对浪费的遏制本身也可以成为新的财富来源。而要实现这种绿色和增长的兼容,关键在于重新定位研发体系,改变旧的技术—经济范式导向下的创新,将其引导到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轨迹上来。
2014年,Perez又在Freeman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智能绿色增长”(Smart Green Growth)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增加无形资产在国内生产总值和生活方式中的比例,同时将全球变暖的威胁和资源限制转化为新的消费和生产模式的机会”[6],相较于Freeman仅基于信息化技术的绿色技术—经济范式,Perez更为详细地论证了3D打印、纳米材料和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对智能绿色增长的重要意义,认为随着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逐步展开,尤其是智能化生产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的进步,经济有可能实现去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在Perez看来,智能绿色增长必将带来又一次类似战后黄金时代的长期增长,环保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可以同时拯救地球、恢复发达国家的就业和促进全球全面发展。
如果说罗根等的稳态经济只是一个良好愿望的话,Freeman的绿色技术—经济范式和Perez的智能绿色增长则更多地建立在对新一代技术革命的技术—经济特征判断的基础上。从经济的角度而言,绿色和增长的兼容源于新技术的绿色创造效应和绿色修复效应。所谓“绿色创造效应”,即新技术本身可以创造出新的绿色经济领域和经济形态,如生物材料、医疗保健、数字化娱乐和教育培训等产业,以及本地生产、创意经济、共享经济等低能耗经济形态等;所谓“绿色修复效应”,即新一代技术可以通过对传统高能耗、污染型产业的升级改造或对环境的修复,重新创造出新的部门分工,如新型建筑材料对传统建筑材料的升级替换等。通过绿色创造效应和绿色修复效应,不仅可以创造出新的产业部门,带来就业和经济增长,也可以实现新的使用价值类型的扩展。简言之,不仅绿色的存在就是财富本身,而且围绕着绿色存在而展开的一系列修复、维修和分享等活动本身也是财富创造过程。
从技术的角度而言,智能绿色增长之所以可行是因为新一代数字经济改变了罗根等对稳态经济的基本前提:其一,稳态经济建立在低熵稀缺这一核心假设基础上,而低熵稀缺源于罗根时代人类捕获、固定和再分配低熵流量的技术能力严重不足,且成本较高;但随着材料科学和能源领域的不断进步,人类已经可以以新的、廉价的低熵流量捕获、固定和分配方式提供能源。2010年,風能和太阳能仅占全球发电量的4%,而到2019年,这一比重增加到了18%左右,2010—2019年的10年中,太阳能光伏发电平均电力成本下降了81%,陆上风能成本下降了46%,海上风能成本下降了44%[7]。其二,稳态经济以福特主义时期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为转型起点,在这一体系基础上,要实现从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发展模式到以文化、娱乐和创意生活为主的“重新平衡休闲与工作时间”的服务型经济,需同时解决就业上的工业“压缩”和服务“膨胀”,但在罗根时代,这种技术条件并不具备,而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而带来的制造业服务化(Servicification of Manufacturing),正是制造业“压缩”和生产性服务业“膨胀”的典型表现,“重新平衡休闲与工作时间”正在成为现实。
简言之,从罗根等近乎乌托邦幻想的稳态经济观,到Perez等的智能绿色增长构想,关键在于技术进步在供给侧所取得的革命性进展。数字经济在使产品设计和生产精度日益提高的同时,改变了福特主义的生产流程和供应链模式,从而减少了能源和材料的使用;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不仅降低了能源的生产成本,也通过能源的智能化分配实现了能源使用过程的经济化;新的经济组织形态,如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租赁和合作经济等,使闲置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制造体系将改变传统工业时代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模式,取而代之的将是更为灵活和更具耐用性的多元化生产和个性化消费。所有的这些变化,都使“绿色”与“增长”双重目标的兼容成为可能。
三、生活方式变革:智能绿色发展的需求侧力量
基于智能制造和清洁能源等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相当一部分学者,尤其是以Perez和Mathews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对智能绿色增长的前景充满自信。Mathews[8]认为,继第五次以信息通讯技术为基础的技术—经济范式之后,以第六次技术—经济范式必然是以清洁能源(Renewable Energies ,REs)为基础的。早在2013年,Mathews就预测,按照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导入期必有金融泡沫这一规律,2015—2020年会出现一次可再生能源的投机性金融泡沫的破裂,而之后就会迎来一个生产性资本而非金融资本主导的可持续发展时期。
Mathews的判断基于两点理由:其一,清洁能源的发展轨迹符合关键投入的全部特征——相对成本快速下降、供应近乎无限和巨大的应用潜力,Freeman和Perez认为,“关键生产要素”是技术—经济范式中的“一个特定投入或一组投入”,它可能表现为某种重要的资源或工业制成品,决定着技术—经济范式的特征并成为划分不同类型的技术—经济范式的依据。“关键生产要素”需满足三个条件:使生产成本具有明显下降的能力,在很长时期内有无限供应能力,广泛被应用和易于扩散的能力[9]。因此,清洁能源将与历史上的芯片、石油等关键投入一样,构成引爆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关键因素。而2010年之后,风能等清洁能源的价格急剧下降,预计2015年即可实现新旧能源的电网平价,从而具备了替换旧能源体系的可能性。其二,以信息通讯技术为代表的第五次技术—经济范式与第四次以石油、钢铁为代表的技术—经济范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基于化石燃料(石油、天然气、煤炭)的大规模工业经济向以信息和数据为关键投入要素的数字经济转型,存在强大的工业惯性和碳锁定力量的阻碍;但以清洁能源、纳米材料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六次技术—经济范式与第五次技术—经济范式之间不存在冲突,前者是后者的拓展和深度应用,属于Mathews “通讯+能源”模式的新组合,其典型代表就是信息通讯技术在绿色生产和智能电网中的应用。
从兼顾绿色和增长双重目标而言,Mathews的预判显然有些过于乐观。一方面,经济绿色化仍然任重道远,尽管清洁能源技术在飞速发展,2019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报告》显示,2010—2019年全球新增燃煤电厂(产能)仍超過500千兆瓦,推高了整个电力系统的碳排放量[7]。而要实现《巴黎协定》中的将21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这一目标,到2050年还需要减排80%以上(与2010年的水平相比),能源转型不可能短期实现[10];另一方面,尽管绿色领域投资、生态产业规模在不断增长,但新部门的增长并未带来从国内生产总值到劳动生产率的系统性高增长,以美国为例,尽管2010年以来美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持续增长,但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仍然从1970—2006年的3.17%降至2006—2016年的1.35%[11]。这意味着,虽然绿色经济部门本身在快速增长,但在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作为新引擎的智能绿色部门的“净创造效应”还不够强劲。
要释放智能绿色技术的潜在增长效能,并使其从潜在的产出变成现实的增长绩效,还需要来自需求侧,尤其是生活方式变革的拉动作用。生活方式所释放出的需求力量与新的技术革命浪潮所内蕴的供给潜能结合,才会形成新熊彼特学派所称的“发展的巨浪”(Great Surges of Development)。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和煤铁时代所对应的是围绕城市建设而展开的维多利亚生活方式,城市化构成的巨大需求对应了这一时期的工业产出——大量廉价而耐用的纺织用品和建筑材料。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时代,即以集中分布式电力能源、钢铁和重型工程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则形成了欧洲的美好时代(Belle poque)生活方式与美国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的生活方式,这一时期的生活方式重新定义了维多利亚时期的风格,“巨型”——从建筑到轮船,均成为钢铁和机械制品需求的主要来源,凡勃仑的炫耀性消费正是对这一时期的典型写照。而在以石油和汽车为代表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中,郊区化运动和以舒适度为导向的美国生活方式则成为新的潮流,这种生活方式不仅与大规模、标准化制造的福特主义相对应,也使战后黄金三十年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基于大规模群众消费的积累模式”。
生活方式的变革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它是技术—经济范式变迁过程中新部门创造(Creation of New Sectors)的催化剂。按照Earl[12]的定义,生活方式是一个由相关资产和经济活动选择组成的系统,这些资产和活动的选择受消费者感知世界的认知系统所约束。生活方式涵盖了收入约束下广泛的资产形式与消费活动的选择组合,是一个认知导向下经济选择的网络化、结构化、可拓展体系,生活方式的变革意味着这一体系的更替。在体系更替中,会产生一系列对应的新效用集合类型,由此而带来不同的需求组合。产品和服务供给一旦与生活方式的变革相对应,就意味着生产和服务供给从规模到结构的系统性变化。生活方式的变革越是彻底,新的效用类型也就越广泛,对应的新部门创生和经济的结构性变迁也就越强烈,净创造效应和增长效能也就越强劲。
通过基于效用类型扩展的新部门创造,生活方式的变革与技术革命两者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侧形成了一种自强化的协同作用。生活方式通过需求拉动、偏好显示和诱导,对提高产业部门生产率、诱导产业分工起着重要的作用。每一次新技术革命初期,新技术都提供了一系列新的生活必需品和服务,它们最初只是以独特的利基市场(Niche Market)形式出现,但这些初始的、带有实验性的利基市场却是生活方式转变的关键。随着生活方式变革的范围逐渐扩大,巨大的需求就会带来规模经济,使新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呈良性循环下降趋势,从而推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逐步取代旧的技术—经济范式;而在生活方式变革,即消费者选择集合系统性转换的过程中,企业又能通过机会空间的感知,规划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方向,进而使对应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部门被“裂变”出来,分工裂变又进一步产生产业间和产业内的协同效应。因此,技术创新和生活方式变革的协同过程,就是一次技术革命及其范式在整个经济中得以传播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面产生出结构性变化,而且也在社会中产生深刻的质的变化” [13]。
生活方式的变革所带来的新部门创造,集中体现在引致部门(Induced Branches)的催生作用上。在新熊彼特学派的理论体系中,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对应着三种不同的部门:生产关键生产要素的动力部门(Motive Branches)、使用关键生产要素的支柱部门(Carrier Branches)、围绕着动力部门和支柱部门而展开的引致部门(Induced Branches)。真正的新技术载体一般是动力部门和支柱部门,如石油、电力、汽车和铁路等。这些部门具有陡峭的学习曲线,具备强烈的生产率溢出效应,但吸纳就业最为广泛的则是引致部门。“新产业对提高生产率至关重要,但并不是创造就业的主力军,是新的生活方式引致的新的服务需求创造了大量的新工作”[14]。以郊区化和美国生活方式为例,汽车一旦成为生活必需品,引发的产品创新就不仅仅局限于汽车产业本身,加油站、汽车维修、保险和交通电台就会成为相应的引致部门。引致部门的扩张不仅为技术革命浪潮提供了产业协同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是吸纳就业、缓解新技术革命破坏效应的缓冲器。在每一次发展的巨浪中,尽管技术革命所对应的标志性技术、产品和部门都相对有限,但其对应的使用价值类型具有极大的延展性,从而可以使对应的引致部门得到极大拓展,而这种拓展根植于生活方式的变革。
因此,从生活方式的角度而言,绿色或绿色增长就不仅仅指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或开发更环保的产品,作为高质量发展方向的“绿色成为普遍形态”也并不局限于能源行业或少数经济领域。就像维多利亚生活方式、进步时代不是针对单一行业或一组行业一样,智能绿色增长是一个从生产体系到消费模式的系统性转换,它不仅意味着生产方式的变革,也包括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重大转变,而这种转变相应地带来了从材料、能源到产品设计以及生活服务业内容和方式的根本转变。易言之,一方面,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能够为生产方式绿色化提供持续的需求基础,从需求侧倒逼产业结构的绿色化发展;另一方面,生活方式的绿色化也能真实有效地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和对能源、材料的消耗。生活方式的变革对于促进智能绿色增长、实现“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具有极为重要的需求侧拉动意义。
四、社会—政治范式变革——智能绿色增长的制度保障
尽管新一代数字技术以及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所留下的遗产——从基础设施到经济结构转型,都有助于实现智能绿色增长,且绿色生活方式的变革对智能绿色增长的促进作用不仅显而易见,也已初露端倪,但无论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还是生活方式的变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生产方式的转变不仅需要彰显智能绿色生产的成本优势,还需要克服传统生产方式的碳锁定和利益集团的阻碍,更需要重塑研发方向;而生活方式的转变本质上是一场观念的革命,作为一个网络化的选择系统,它涉及到无数行为主体的偏好重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Lundvall[15]指出的那样,任何技术—经济范式都不可能孤立发挥作用,要发挥既有技术—经济范式的潜力,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社会—政治范式(Socio-Political Paradigm)。
Lundvall并未对社会—政治范式进行精确的定义,他只是强调技术革命浪潮的效能释放受到社会结构、社会—政治观念、治理形式、政治制度和相关政策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在社会—政治范式广泛的外延中,Lundvall尤其强调治理,他认为:“政治和新的治理形式对于最终的、持续的经济增长来说,比经济和技术更重要。对于我这样一个终生从事创新经济学研究的人来说,这个结论似乎不合适,甚至令人惊讶”[15]。在Lundvall看来,社会—政治范式是否有利于一个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与展开,在于其是否能在最大程度释放新技术的经济效能的同时,也实现技术进步红利的共享。作为技术—经济范式的对应概念,我们可以将社会—政治范式概念理解为“一个最佳惯行做法的治理模式,它由一套普遍的、通用的社会—政治观念和政策原则所构成,它决定和影响着代表着一场特定的技术革命得以运用的最有效方式能否产生”,以与Perez的“技术—经济范式是一个最佳惯行做法的模式,它由一套普遍的、通用的技术原则和组织原则所构成,代表着一场特定的技术革命得以运用的最有效方式”[13]这一概念相对应。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从镀金时代到进步时代的转型过程,就是一次典型的社会—政治范式的重构。从国家治理体系到社会价值观的改变,不仅为进步时代,也为战后黄金三十年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镀金时代的极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大市场小政府的导向,不仅使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激化,也使政府公共支出严重匮乏。相对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而言,这种社会—政治范式只会更快地导致生产过剩的矛盾,而无法起到继续释放技术潜能和引导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效果。而进步时代不仅是一个国家制度建构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阶层力量调整和社会价值观重塑的过程,美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与构建,包括预算制度、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等一系列财政制度的改革,工会组织和集体谈判制度以及消費主义文化的盛行,从本质上而言都是一种适应特定技术—经济范式的社会—政治范式调整。
单纯从生产方式的变革而言,Perez对智能绿色增长的前景判断是正确的。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与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冲突,的确要弱于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与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之间的矛盾。在从基于化石能源的大规模工业制造经济体系到以数据、信息为基础的去物质化经济体系的转变过程中,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已经提供了一次缓冲。从技术特征上而言,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是缓冲之后的发展,是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升级和延伸,其升级主要体现为从机—机互联网到万物互联的物联网,从生产的信息化和数据化到数据生产的实体化和智能化,即从数字经济1.0到数字经济2.0;其延伸主要体现为技术革命从信息通讯技术延伸到能源和材料革命,从而具备了里夫金的完整工业革命的全部特征,具有更强的产业裂变和协同效应。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认为,“通讯革命和能源革命的结合”是历次工业革命爆发的标志或原因。在里夫金看来,能源和通讯的组合变化,构成了工业革命进程不断展开和深入的标志。新能源的出现让复杂的文明社会成为可能,通过劳动分工整合成大的经济体,这同时对新的通讯方式提出了要求,而通讯革命又可以用来组织和管理新能源革命。可见,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是“互联网+能源”。
但是,正如Mathews [8]很早就指出的那样,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留下了一个坏遗产——金融化,而这正是遏制生产方式变革的主要障碍。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时代的红利首先体现在金融业,因为信息通讯技术的独有特征更适合开发和交易一些复杂的金融产品,其更具流动性,也更易于逃避监管,由此才兴起了“金融科技”这个行业。按照马伦和哈维等左翼学者的观点,是华尔街使信息通讯技术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而不是信息通讯技术促进了华尔街的崛起。从技术进步的偏向性而言,信息通讯技术不仅是偏资本的,更是偏金融资本的。信息通讯技术使金融业的交易成本、交易效率和交易对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借助金融产品的变化,金融业也更易于去监管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业和信息通讯技术在自由化政策导向下的协同发展,强化了整个经济生活的金融化——从企业金融化到个人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其结果之一就是诱导经济剩余趋向于非生产性活动,阻碍了技术革命浪潮潜在生产力的进一步释放。事实上,经过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强化,金融业已经习惯了短期的“赌场模式”,相当一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利润率与投资率背离的怪状。Kotz[16]的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利润率和积累率之间逐渐脱钩,利润率不再决定积累率,这一特征在2008年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美国私人企业利润率在2009年后反弹至长期高点,但积累率和经济增长率却一直呈下降趋势。
生活方式的变革同样面临着诸多困难:其一,生活方式是一个选择的系统性组合,这种系统性决定了生活方式缺乏灵活性,也正是缺乏灵活性,才赋予了个人生活方式的个性特征。而生活方式的变革必须完成系统性的观念变革,“消费模式的巨大转变不能基于内疚、恐惧或自我否定,而只能是基于欲望和渴望”[14]。这种偏好体系的变化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变革本身就是一个渐进的、波动的过程。其二,生活方式的变革具有从上到下的示范效应,它首先源于社会顶层或少数群体,其扩散遵从由上至下的方向[17]。但是,在从维多利亚生活方式向进步时代生活方式以及美国生活方式的变迁中,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由上至下的扩散过程,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拥有和使用财富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长的过程。它们之所以能最终完成由上至下的扩散,并最终能成为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降低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使新的生活方式成为大众性的。但智能绿色增长对应的生活方式与之前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有本质的不同,它要求的不是占有,而是获得、参与和创造,“智能绿色生活注重健康、营养、锻炼、创造力、体验、参与和获取(共享或租赁),而不是拥有”[6]。因此,这一生活方式变迁对应的是从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到发展需要的升级,在一个《绿色成为普遍形态》的生活方式中,绿色作为一种社会共同需要,具有不可分割性和一致性特征,但这一社会共同需要的满足,同时又需要无数社会个体将其具有差异性与分散性特征的个人需要完成聚焦[18]。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的障碍,只有通过社会—政治范式的重构才能得以克服。社会—政治范式的重构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政策,而是从社会治理到政治观念的变迁。正如战后黄金三十年的积累体制并不仅限于税收政策和竞争政策一样,包容性的社会妥协、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体系、基于生产率增长的工资指数化、对接近充分就业的政治承诺以及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大力宣传,同样为“基于大规模群众消费的积累模式”的形成具有基础性的作用。由于智能绿色增长所要求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要将“节约”“去物质化”转化为增长,要将占有(Possession)转换为获得(Access),这与之前任何一次技术革命浪潮时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观念和发展模式上都有着本质的差异,因此,社会—政治范式的重构也更为复杂和艰难。
从适应和促进智能绿色增长的角度而言,当前的社会—政治范式仍存在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具体可概况为:
第一,当前的社会—政治范式仍然主要集中于经济激励,但对社会—政治范式的其他方面重视不足,如声誉激励机制、社会规范和社会治理、多中心社会治理等方面。事实上,大量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研究都已经表明,无论是绿色生产还是绿色生活,绿色本身具有很强的利他主义性质,而货币激励基于传统经济学的利己假设,其绿色激励效果远不如道德约束、声誉标签等方式。由于绿色行为本身所带来的身份效用具有更强的内在激励效果,在社会规范、共同体意识能对身份进行更强的声誉租金“赋予”效果的社会环境中,行为主体具有一种更强的亲环境自我意识。为了将精神不适降到最低,会自发寻求更为符合其绿色身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关于绿色的激励方式差异性的实证分析,可参见Bolderdijk等[19]、Corner等[20]以及Hornsey等[21]。关于通过行为经济学轻推诱导绿色行为的激励,理论部分可参见理泰勒和桑斯坦[22]。因此,通过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建构,和通过打造环境共同体来形成身份约束,以及利用行为经济学的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ture)去诱导行为主体产生实质性环境行动主义行为,远比货币激励和信息提供等传统激励方式更为有效。
第二,当前的经济激励主要以税收激励为主,但这种传统的激励方式对于绿色增长而言存在双重偏差:一方面,由于缺乏社会治理和社会监督的协同,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技术的不确定性因素等多种原因,税收激励下的技术驱动有可能形成未经证实的“负排放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即一种看起来有助于减排、循环的绿色技术可能带来长期不可预期的降解风险,或成为一地减排异地增排的格局,给未来的绿色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环境成本[23];另一方面,由于绿色经济的特殊性,传统经济激励的领域和方式应有所改变,要使绿色增长摆脱金融化的负面遗产,使投资和创新集中于长期生产性活动中,政府有责任调整金融方向并为绿色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创造条件。同时,税收和研发的指向性要有所改变,Perez提议,应当取消传统的增值税,而对能源、材料和运输环节征税,而Mazzucato[24]则认为,通过税收政策来激励创新和投资的方式力度有限,政府应当通过开发银行直接提供资金来启动绿色项目,并加大政府对研发投资的力度。
第三,在生活方式的引导方面,忽视了绿色的普惠性要求,缺乏对应的社会政策支撑。以极简、健康和精神生活为内容的新生活方式仍然属于昂贵的精英主义生活方式,绿色与增长之间存在着社会阶层的不对称。隐藏在共享、租赁和本地化生产等绿色经济形态背后的,是零工经济、数字涡轮主义和日益恶化的工作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将更少人的绿色生活建立在更多人的生存状态恶化的基础之上,缺乏普惠性的收入和就业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绿色不仅不能成為普遍形态,而且会对增长产生负面作用,影响其可持续性,同时还会导致绿色财富的“极化”,形成另一种新的不平等。事实上,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可支配收入更高的人被认为更有能力、也更有可能关心环境,国民收入水平与环保贡献的可能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家庭层面的能源使用实证调查却显示,排放范围实际上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增加实际上促进了更多对环境有害的行为,对绿色的态度和行为之间存在着反向背离。“绿色”和“棕色”消费者的生态足迹几乎是一样的[25-26]。
第四,当前的社会—政治范式构建仍然缺乏有效的全球性制衡机制:一方面,不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排放和环保方面承担着与之财富、能力和历史责任不对称的责任;另一方面,大量实证研究仍然表明,全球贸易、能源和排放强度趋势仍然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Hypothesis of Pollution Haven) [27]。由于发展中国家仍然追求以工作换取排放的长期战略,环境负担始终在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发展中国家;发达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之间排放强度的不对称性仍在加剧。从《京都议定书》到坎昆世界气候大会和《巴黎协定》,围绕着绿色发展的全球性责权利分配与目标—措施—实施之间的困局和摇摆始终存在。曾一度被视为国际气候行动的重要初始步骤的《巴黎协定》一经签订,就开始了反对的浪潮,不仅温度控制目标和表述方式备受指责,而且普遍认为,《巴黎协定》“没有行动,只有承诺”,是一种“建设性模糊” [28]。
五、结语:智能绿色增长如何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中国一直在为绿色发展做着巨大的努力。近二十年来,中国新增植被覆盖面积约占全球新增植被覆盖面积总量的25%,居全球首位。2019年各类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8%,提前实现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的到2020年保护地面积达到17%的目标[29]。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趋势报告》显示,2010—2019年世界清洁能源产能投资达到2.6万亿美元,而中国是最大的投资国。2010年初到2019年年中,中国的投资7 580亿美元,超过整个欧洲的投资6 980亿美元和美国的投资3 560亿美元[7]。2017年中国提前三年完成了相关气候目标,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约46%,已超过2020年碳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第七十三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埃斯皮诺萨指出,在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方面,中国走在世界的前列[30]。
中国的绿色发展,尤其是近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建立在法律制度保障和相关政策规定的基础上。2015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引入了按日连续罚款、查封扣押、限产停产、行政拘留、公益诉讼等措施,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同年又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成为绿色发展的里程碑。2017年,党的十九大又将建设生态文明、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入了报告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推进绿色生活方式、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政策力度明显加快,继2019年11月发改委印发《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总体方案》之后,2020年3月,发改委又与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法规政策体系的意见》并明确提出,到2025年,进一步健全绿色生产和消费相关的法规、标准、政策,基本建立激励约束到位的制度框架的制度建设目标。
但是,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资源较为贫乏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实现绿色成为普遍形态这一目标上还有漫长而艰难的道路要走。目前,尽管人均碳排放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2019年能源生产结构中,原煤占比仍高达68.8%,原油占比6.9%,天然气占比5.9%,水电、核电、风电等占比18.4%[31]。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上,中国面临着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难度和挑战。从生产方式的变革上,我们要实现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制造业的智能绿色转型,将面临着更大的碳锁定强度;从生活方式的变革上,我们要实现一个人均GDP和人均GNI都刚刚超过1万美元,地区、城乡差距较大的14亿人的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转变,将面临着更大的观念阻力和调整压力。但辩证地看,这种巨大的挑战又是一种机遇:作为产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无论是从绿色创造效应还是绿色修复效应而言,都具有更强的产业协同基础;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生活方式转变所释放出的巨大需求,对智能绿色增长的实现又具有巨大的拉动力量。尤其是,在一个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党领导下,适应新一轮技术—经济范式的社会—政治范式在共享、普惠与绿色理念的落实上有根本性的制度保障。
在生产方式的变革上,重点在于抓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一着力点[32]。在智能绿色增长导向下,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智能绿色制造(Smart Green Manufacturing)。智能绿色制造既是生产目的指向的绿色化,又是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其实现不仅依赖于清洁能源、新型材料、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协同发展,更依赖于发展观念的深刻转变。其二,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制造业服务化(Servicification of Manufacturing)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新业态,也是制造业去物质化的必由之路。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绿色+智能”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是绿色智能增长的动力保障。
在生活方式的变革上,要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财富形态观与“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新发展理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各种有效的、绿色和可持续的方式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性特征,而只有美好生活需要建立在绿色财富形态基础上,才能使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在具体措施上,一方面,需要通过供给侧的改革,改变消费者的可选择集合,如绿色出行、绿色建筑等;另一方面,需要通过营造社会的绿色氛围,如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等,改变共同体的绿色意识和环境观念,使绿色选择成为一种自我激励、自我驱动的行为方式,通过外在选择集合的约束和内在自我激励机制的共同作用,推动绿色消费,促进绿色发展。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EB/OL].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103/c416126-29743660.html,2017-05-26.
[2] 赫尔曼·E.戴利.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M].马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01-302.
[3] Roegen,G.Energy and Economic Myths[M].New York: Permagon Press,1976.3-36.
[4] Cole, H.S.D., Freeman, C., Jahoda, M.,et al.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A Critique of ‘The Limits to Growth[M].London: Chatto & Wi ndus for Sussex University Press,1973.
[5] Freeman,C.A Green Techno Economic Paradigm for the World Economy[A].Heaton,G.The Economics of Hope: Essays on Technical Change,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C].London: Pinter Publishers,1992.190-211.
[6] Freeman,C.Second Machine Age or Fifth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Lead to Different Recommendations [EB/OL].http://www.carlotaperez.org/,1992.
[7] Global Trends in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2019[R].http://www.fs-unep-centre.org,2019.
[8] Mathews,J.A .The Renewable Energies Technology Surge: A New Techno-Economic Paradigm in the Making?[J].Futures,2013,46(2):10-22.
[9] G·多西,C·弗里曼,R·纳尔逊,等.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M].钟学义,沈利生,陈平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58-74.
[10] Antal,M.,Van Den Bergh,J.C.M.Green Growth and Climate Change: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Considerations[J].Climate Policy,2016,16(1-4):165-177.
[11] Gordon,R.J.Why Has Economic Growth Slowed When Innovation Appears to Be Accelerating? [J].NBER Working Paper No.24554,2018.
[12] Earl,P.E .Lifestyle Changes and the Lifestyle Selection Process[J].Journal of Bioeconomics,2017,19(1):97-114.
[13] 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M].田方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5.
[14] Perez,C.,Leach,T.M.A Smart Green ‘European Way of Life: The Path for Growth,Jobs and Wellbeing[EB/OL].http://beyondthetechrevolution.com/wp-content/uploads/2014/10/BTTR_WP_2018-1.pdf,2018-03.
[15] Lundvall,B.A .Is There a Technological Fix for the Current Global Stagnation? A Response to Daniele Archibugi,Blade Runner Economics: Will Innovation Lead the Economic Recovery?[J].Research Policy,2017,46(3):544-549.
[16] Kotz,D.M.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Marxist Theory,and System Transformation[J].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2017,49(4):534-542.
[17] Geels, F.W.Technological Transitions as Evolutionary Reconfiguration Processes:A Multi-Level Perspective and a CaseStudy[J].Research Policy,2002,31(8-9):1257-1274.
[18] 胡乐明.生活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11):56-68.
[19] Bolderdijk,J.W.,Steg,L.,Geller,E.S.,et al.Compa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Versus Moral Motives in Environmental Campaigning[J].Nature Climate Change,2013,3(4):413-416.
[20] Corner,A.,Markowitz ,E.,Pidgeon,N .Public Engagement With Climate Change: The Role of Human Values[J].Wiley Interdiplinary Reviews Climate Change,2014,5(3):411-422.
[21] Hornsey,M.J.,Harris,E.A.,Bain,P.G.,et al. Meta-Analyses of the Determinants and Outcomes of Belief in Climate Change[J].Nature Climate Change,2016,6(6): 622-627.
[22] 理查德·泰勒,卡斯·桑斯坦.助推:如何做出有关健康财富和幸福的更优决策[M].刘宁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
[23] Smith,P.,Davis,S.J.,Creutzig,F.,et al.Biophysical and Economiclimits to Negative CO2 Emissions[J].Nature Climate Change,2015,6(1): 42-50.
[24] Mazzucato,M.Directorate General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European Commission Missionoriented Research & Innov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A Problem Solving Approach to Fuel Innovationled Growth[EB/OL].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5b2811d1-16bE11e8-9253-01aa75ed71a1/languagEen,2018-02-21.
[25] Lo,A.Y .National Income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 Observations From 35 Countries[J].Public Underst,2016,25(7):873-890.
[26] Csutora,M .One More Awareness Gap? The Behaviour-Impact Gap Problem[J].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2012,35(1):145-163.
[27] Savona,M.,Ciarli,T.Structural Changes and Sustainability:A Selected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Evidence[T].SPRU Working Paper Series,2019.
[28] Schellnhuber,H.J.,Rahmstorf,S.,Winkelmann,R .Why the Right Climate Target Was Agreed in Paris[J].Nature Climate Change,2016,6(7):649-653.
[29] 高敬.回顧70年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EB/OL].http://www.chinanews.com/gn/2019/09-29/8968917.shtml,2019-09-29.
[30] 新华社.中国减排成就举世瞩目[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12-05.
[31] 中国能源大数据报告(2020)——能源综合篇(3) [EB/OL].http://shoudian.bjx.com.cn/html/20200521/1074226-3.shtml,2020-05-21.
[32]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22.
(责任编辑:徐雅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