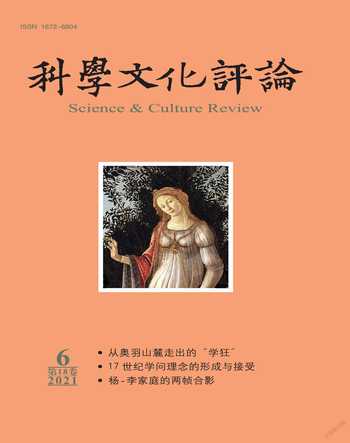科学革命论17世纪学问理念的形成与接受
2021-04-23佐佐木力

作者简介:佐佐木力(1947—2020),日本宫城县人。曾任东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是数学史,数学哲学,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科学史和跨文化科学哲学。
本文为《近代学问理念的诞生》(中文版)的序章,该书将于202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李梁教授惠允本刊发表,以资纪念。
编者按 这篇译文是已故日本著名科学史家佐佐木力教授(1947—2020)名著《近代學问理念的诞生》(以下简称“此著”)提纲挈领的序章。此著1992年10月初版由日本著名书肆老铺岩波书店发行,翌年便获得在日本学界极负盛誉的1993年度三得利文化财团历史、思想部门颁发的“三得利学艺奖”。正如此奖选评人代表中埜肇教授(时为冈崎学园国际短期大学学长,京都大学名誉教授,黑格尔专家)在获奖推荐辞中所言“此一力作,在科学(特别是数学和力学)以及学问论的领域上,乃研究极为精深,水平极高的成果”。他在此书中,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而展开的博雅探讨,并未停留于单纯的历史性叙述,同时在鲜明的现代性文明论问题意识引导下,批判性地审视存在于近代科学根底的志向性,并通过此一途经,尝试理性地重新评价近代性其本身(无论是肯定抑或否定)。而且,他摆脱了科学史家身上常有的单面性,依据复眼式思考而深入展开讨论。在佐佐木氏复眼性视角下,科学与历史这一乍见对立的概念得以融为一体,从而开启了探讨近代性的途径。这恐怕就是所谓“自然科学理论的妥当性常常是地平线似的”这一定说之意味,这种观点也与库恩的理论重叠,佐佐木氏依据文献资料,精致而又有说服力地阐释这一观点。李梁译。
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识码 A
我大凡如此以为,习惯是第二的自然,而此自然自身难道不就是第一习惯么?
——布莱兹·帕斯卡《思想录》[1,2]
一 近代自然观的本末倒置
在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ēs Laertius,约活跃于公元3世纪)《希腊哲学者列传》第七卷第一章里有关基提翁的芝诺(Zeno of Citium,公元前334—262)的轶闻里,有如下一段内容:
他(芝诺)有一天,正在鞭笞一个偷窃的奴仆,那个奴仆辩解道:“我是命中注定要偷盗的!”他回呛道:“那么,你受鞭笞也一样(是命中注定)的。”[3,4]
在近代版希腊语文本里,此轶闻是一不足两行的简短文字。但这一古代的知见,1880年在埃米尔·杜布瓦-雷蒙(Emil Heinrich du Bois-Reymond,1818—1896)为反驳近代机械决定论所作的题为“宇宙之七大谜题”的演讲里曾被复述关于这几个演讲的思想史背景与反响,请参见以下文献:Maurice Mandelbaum, History, Man & Reason: 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thought (Baltimore,1971), 14. “Ignoramus, Ignorabimus: The Positivist Strand.” pp.289—310。[5, 6]。杜布瓦-雷蒙的这场演讲是在1872年德国自然研究者医学者大会上,因“关于自然认识的局限”的演讲而引发的“Ignorabimus”(我们现在不知道,将来也不知道)争论正酣时,为增强自己论点的正确性而作的。毋庸赘言,“关于自然认识的局限”乃因将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1749—1827)决定论世界观里蕴含的原理上的可疑性,概念化为“拉普拉斯妖”而广为人知。
或许对生活于20世纪末我们来说,围绕古希腊斯多葛学派鼻祖的史话,以及杜布瓦-雷蒙的两个演讲都无不颇感陌生,仿佛名副其实就是他人之事。然而,如果当我们得知围绕此决定论的讨论,与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20世纪数学方向的、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在第二届国际数学者会议(巴黎,1900年)所作的演讲“数学的诸问题”有关的话,那么,此一哲学上的位相空间,无疑便会忽然变得亲近起来。实际上,希尔伯特在巴黎演讲的前言中,为了给数学家们鼓气,阐述在数学诸问题中的一切问题或肯定或否定都是解决可能的,数学中决不存在“Ignorabimus”[7,8]。在此,我们清楚地听到了抗拒杜布瓦-雷蒙哲学讨论之结论、即“Ignorabimus”式新实证主义之声。嗣后,希尔伯特通过将数学与逻辑学还原为记号的机械性操作,力图证明数学体系的无矛盾性,从而整合了现代数学中最有影响力的形式主义学派。正如后来明示的那样,在希尔伯特的研究计划案的根底部,包含着芝诺巧妙地暴露出的宿命论的二律背反性,以及类似“拉普拉斯妖”的逆说(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对此解释的反论也为可能。但是,这种解释,广义地来看待希尔伯特的研究方案,相当歪曲了希尔伯特历史的“意识形态性”。参见:E. g. Michael Detlefsen, Hilberts Program: An essay on mathematical instrumentalism (Dordrecht, 1986) ; Idem, “On Interpreting Gdels Second Theorem,” in S. G. Shanker, ed., Gdels Theorem in Focus (London-New York-Sydney,1988), pp.131—154。。让我们来更为仔细地来研讨一番基提翁的芝诺与奴仆之间的对话吧。奴仆行盗,作为辩解,他诉说他的行为乃由某种法则规定,企图免罪。对此,芝诺以同样的逻辑反驳,说他鞭笞奴仆的行为也由某种法则规定,以主张其鞭笞的正当性。在这里,或可想见有种与人们日常生活之意味有关的世界,即超越了生活世界的惯用性法则的网眼,在二者虽各说各话,以便使各自行为合理化的行为里,出现了二律背反现象。
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趣话太过简短,并未说明两个登场人物所依据的决定论是何种性格的东西。为此,我们将与此决定论类似的法则置于近代自然科学之中来考察一番。根据现代分子生物学所示,我们的遗传特质,乃是由局限于细胞核染色体内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来传达,1953年,发现了此DNA具有二重螺旋的结构,但化学家们并未满足于对这一生物学上的知见,而着手探究为什么DNA具有这样一种化学结构;物理学家则更不满足,他们研究起构成DNA诸元素的基本粒子论的组成结构,进而探究构成基本粒子的夸克的性质,这无疑是在尝试构筑物理学的一般性理论。而一旁的数学家们,或许可在数学上阐释夸克的组合结构。
在此,不妨思考一番,蓦然浮现于我们心中的现代自然观,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对我们来说,这一自然观是种有着更实在的、更现实意味的自然世界,并带有一种持续不断地向被认为是更根源性自然世界还原的倾向,形成生物学的世界、化学的世界、物理学的世界这样一种重层结构。因而,倘若将我们的整体世界统统全都还原为物理学的存在(比如基本粒子或者夸克)及其法则性,进而实体性地/决定论地来解释物理学的法则性(不依循哥本哈根学派,而是仿效爱因斯坦)的话,则或可以想见我们的生活世界,也将被埋没在物理学的世界之中,由此可见,只需稍加必要的变更,芝诺与奴仆之间对话里的二律背反现象,在近代世界里也是很容易再现可能的。
然而,这种物理学存在的实在性世界,若将自然世界里前述的中间阶段统统拆掉的话,虽可预想到构成我们的生活世界,也将意识到其仅仅只是(为表示对古希腊人的敬意而用他们的词汇来表达的话)在“无为地”(μτην)运动着而已。这种物理学的还原主义,即便不用援引前述的逆说,也难免不成为一桩“蠢事”(μτη)。本来,被看作理应为一切自然存在构成物的夸克,本身就是一种出于为基本粒子论整序目的而设想出的存在。进一步说,基本粒子也是为定义其上位的原子这一物理学存在而厘定的概念。并且,这些原子也都不外就是为了统一地说明化学性分子而设想出来的存在。或也可设想,譬如基本粒子是一种没有任何中间阶梯的直接存在物,在此情形下,在基于近代科技的理论性,在工具性的眼光审视下,其存在才得以在物理学者间获得认定。DNA的二重螺旋分子结构,虽也有可能被看作为原子或基本粒子的集合体,但如果这时不预先与DNA的生物学意义机能一起把握这一集合体,则基本粒子集合体其自身不外就是一种单纯的混沌性存在。这种分子结构,在与遗传这一更为上位的、即与存在于更为具体性生活世界的意义机能的关联上,可承认其为某种理念性意义形成态、或作为一种格式塔而存在。要之,在与被视为更加根源性存在结构(比如原子或基本粒子)的关联上,来理解自然世界中的存在(比如DNA),此举一方面会使我们的生活世界的意味更为丰富多彩,但另一方面,却因还原主义,即因忘却与隐蔽生活世界之为背理而发生逆说现象。基本粒子也好,夸克也罢,作为其自体乃一种混沌性存在,日常的生活世界,才是赋予了意味的宇宙空间。
不过,这种认识在今天已经司空见惯。如果是指出上述逆说其自身的问题所在的话,即便是一个想象力平庸的分析哲学家也能做到,并且,如果仅仅只是作为机械论自然观的代替选项,提出與其相对照的万物有灵论自然观这种程度之事的话,则甚至连敏于时流的作家也能做到。重要的是,近代自然观的这种本末倒置,错误理解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如何才能阐明其机制?不这样做,则这种错误理解还会不断继续再生产下去。而为说明这一本末倒置,必不可或缺的思想性作为,正是科学史角度的科学论。
曾有过提出这种尝试重要性的先驱者。最先提示不具历史性省察而来把握自然观念乃为一种悖论的,之所以是詹巴蒂斯·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并非没有理由(详细请参照本书第四章)。维柯在其《新科学》里,指责那种只是专注于自然世界的研究,却对人类社会史不屑一顾的哲学家乃是本末倒置。并且,黑格尔也在《逻辑学》中说道,数学以及数理学(物理学)所使用的概念,相对而言颇为空泛,而关于化学、生物学甚或人类精神的概念,则较前者更为丰满,并且越到后来就变得益发丰腴起来。虽然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各种议论的时代错置确难掩饰,但其全体逻辑展开的结构仍极为厚重,迄无出其右者。而从根本上批判观念的本末倒置,错误理解,并揭示了思想上的逻辑意义的,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开头的商品论。无论何种思想家,与其说是企图单纯地以其他的概念来置换观念的本末倒置,毋宁说是倡导将其发生以及僵化的历史性机制收入视野,试图阐明这一历史性思考之重要性的人们,要更引人注目。倘若将这种念头存储于心,则我们对近代科学思想里居支配性地位的独断论进行批判的方法,与这些思想家们所揭橥的历史性方法之必然性究竟程度如何,无疑便可理解。
二 科学史科学论之必然性
在展开我们的科学革命论之前,先且确定一下,对科学论而言,科学史考察将起到怎样一种作用的问题。可以说,给予近代科学的独断论式理解认真而细致的批判的,是由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开其先河。康德在此书中认为,夸耀已经把握了近代数学自然学的自然因果法则,决非寓于自然对象自身里的存在,而是出自赋予进行自然认识的人类知性判断作用之特征的诸范畴之中。根据康德的这种“哥白尼式革命”论,在指出自然科学中的革命,是起因于针对知性自然的自我抑制性的追问这一点上,乃为一具有划时代意义之举。然而,此种批判作为批判而言,并不十分周洽。因为,认识主体的知性作用自身,依然是先验性的存在,即为以一种永恒的存在为前提的。
承续康德的洞见,并竭力主张有必要历史地重新理解康德所厘定的“纯粹悟性概念”之先验性的,是《科学理性批判》的著者科尔特·修布纳(Kurt K. R. Hübner,1921—2013)。修布纳在试图提炼并纯化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1922—1996)于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构造》中首倡的科学论的同时,也试图历史主义地修正康德的思想。其时,修布纳作为飞跃的跳板而利用的,正是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1861—1916)的科学论。
迪昂在1906年刊行的《物理学理论——其目的与结构》中,讨论了光粒子说与波动说的历史性对立问题,贬斥了朴素的单纯举例式归纳主义。在迪昂看来,求真的物理学理论,为包摄并说明中枢性物理学诸现象而设定的各种假说,即便在历经了正当的手续验证了这些假说各自的妥当性之后,仍须是具有生命力的。不过,根据实验而揭示某一假说的矛盾时,并非就预示了其他某一假说的正确性。因为,哪儿也没有这些个假说已经悉数举例完毕的保证。迪昂说——“物理学家决不能保证穷竟了一切想象可能的各种假说(supposititions imaginable)。因为,某一物理理论的真理性,并不能像翻硬币那样以表里来决定是否”[9, 10]。因而迪昂认为,通常要归属于培根的“决定实验”(experimentum crucis),在原理上是不可能的。物理学理论的妥当性,并不能仅仅依靠经验的成分来决定。然而,作为物理学家,迪昂事实上支持某一特定的理论。在经验性成分以外,作为支撑物理学理论的成分,他加上了“良识”(Bon Sans),并认为此良识可通过科学史研究而获得。一般认为,构成科学理论的经验性成分以外的要素,超越了经验,而在作为一种促使经验、认识成立的前提性机构而发挥机能,因而或可将之命名为超越论性之成分。这样一来,迪昂不就是在说,通过科学史研究而培育出来的良识,正是构成超越论性的要素。
修布纳正是在迪昂迫不得已而导入的“良识”里看到了迪昂式科学论的破绽。因此,修布纳发挥康德般的想象力,试图重新厘定迪昂不得不用良识这一用语来处理的其科学理论的构成要素。仿效康德,修布纳认为这一超越论的成分由种种范畴交织而成,但修布纳并未像康德那样援用先验性的范畴,而是采用了别的用语,试图克服先验主义。修布纳以为,构成科学理论的超越论成分的,是科学工作者在一定期间内被迫应该守护的“诸定律(各种约定)”(Festsetzungen),并且这些彻头彻尾是间主观性的、历史性的[11, 12]。不难看出,修布纳在尝试将库恩的科学论纳入自己的概念装置之中。在科学家共同体里起到规范性定律作用的,是类似于库恩的范式概念,事实上,修布纳就是将往往被看作似乎超越了历史定律本身的变化称之为科学革命。
因而,修布纳将康德式科学论历史地动态化,与对迪昂同样,对修布纳来说,科学史是必须的作为——因为,构成科学理论的超越论成分的正是科学史的缘故。修布纳通过修正这种康德的科学论,试图说明围绕笛卡儿与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1629—1695)之间的冲突论,以及围绕爱因斯坦与玻尔(Niels Bohr,1885—1962)之间关于量子力学完全性的对立。在修布纳看来,彼此之所以抗衡不下,在许多场合,乃是因为论敌双方并未站在同一定律群的擂台上一决胜负的缘故。
虽然,修布纳的议论或可获得一定程度的评价,但在其根源性科学论里却并存有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巨大缺点。也即是说,因为他完全没有说明科学工作者为什么必须在一定期间内保持特定的定律,以及这一定律的转换,即科学革命是如何发生的问题。正是在此,存在未能摆脱康德主义认识论的修布纳的根本性的弱点。然而,反过来想想,这果然就是修布纳哲学上的缺陷么?难道这不就是哲学性讨论本身的局限吗?或许,修布纳会这样回答道——回答上述提问者,应是科学史家。我们将作为真挚的哲学性省察的成果,全面地接受这一结论。这样,作为一种周全的科学论,我们的科学革命论必须从科学史的角度展开。
三 17世纪学问理念的特质——有用性与确定性
可以认为,科学理论乃由经验的成分与超越论的定律所构成。而且,超越论的定律并非能先验地理解的东西,而是必须借助科学史的省察才有理解之可能。这一见解,或也可定式化为:仅依据四维度的物理学“只能不充分地决定”(underdetemination)科学理论,因而必须要有另一五维度的科学史考察。
因此,当从哲学、以及历史学的角度来讨论科学革命时,对近代科学工作者而言,确定一般认为不言自明的、先验性的超越论定律究竟为何,便十分重要。在此确定作业的基础上,必须批判性地、歷史性地阐述这些定律是产生于怎样一种历史性脉络之中。历史性阐释的特异性,忌讳那种仿佛观念或思想是超越性地从天而降似的说明,而矢志于彻底地作为在历史本身之中生成并消失的概念来加以说明。
那么,让我们来尝试粗略地整理并理念化自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刊行之年的1543年,到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诸原理》发刊之年的1687年之间的科学革命论。我们可以指出,16世纪依据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理论化的直观性、日常性的世界观发生剧烈动摇,濒临崩溃的危机之际,在提示了新的世界观的思想家们之身,普遍存在一个共通的指标信念。这一信念即是,这个现实的日常世界是假象的世界,表面的现象,而在理念型影子的彼岸,存在着建设与真正的世界有关的某种学问的可能性。这一信念具有多重变奏性。伽利略以文艺复兴期技术者的认识论为轴心,试图将阿基米得式的手法扩展到位置运动论之中。并且还借助望远镜,试图观察超越日常性感觉的世界。在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看来,亚里士多德的世界只是幻想,应取而代之的选项是伊壁鸠鲁的哲学体系。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提供了更深层次地说明呈现于感觉世界的手段。笛卡儿将讨论日常两义性世界的工具辩证法(逻辑学)看作无用之物,认为数学记述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自然学应该彻底几何学化。在此,我们也得以看到与这种自然观的转换相应而起的、令人瞩目的思想运动。即作为一种整统合日常语言、逻辑学、数学以及中世文艺复兴期盛极一时的记忆术学科而正在形成的“普遍记号法”(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这一思想运动。此运动的代表者,当然是莱布尼茨。无论在何种场合,都显示了一种试图从深层结构来阐释日常性现实的共同动机。依据这样一种观点来观察17世纪的思想革命的话,则这一革命的推进者们自我认定的新定律为何,就不言而谕了。
此新定律,直截了当地讲,可以说即是一种“有用性”(utilitas)与“确定性”(certituto)关于此点科学史的详细讨论,请参照《科学革命の歴史構造》第一章《17世紀的危機與科学革命》、第二章《伽利略·加利萊—近代技術的学知射程》,岩波书店,1985年。。当然,我们作为理想型来厘定这些概念。主要依靠托马斯·阿奎那的努力而奠定于13世纪的中世性世界观,是作为一种赋予了自然世界、人的世界阶层性秩序而被静态地全盘接受的,并借助以这一秩序为前提的人们献身性道德的发扬而建构起一种基督教爱的共同体。由于中世后期的疫病灾祸,及其后文艺复兴期人的探索性的、奔放的乌托邦激进主义,这种中世的宇宙观遭到破坏。然而,近世市民的定律,并非以在16世纪初期至17世纪前半,往往与新教伦理融为一体的形式出现的激进的否定精神那种形态而得以成立,而是从16世纪的对立与混沌之中,通过追求一种新的世界观的综合而形成的。毫不夸张地说,近代学问的定律,正如近代性的个人主义、民主主义的政治原理那样,肇始于围绕欧洲宗教性霸权而进行了最为激烈战斗的法国。
16世纪法国宗教战争正酣之际,最为激进地试图破坏中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思想代辩者是彼得吕斯·拉米斯(Petrus Ramus,1515—1572)。他几乎无视学术的严密性,在教育上重新编排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以及欧几里得的数学,企图使之变革为当时新兴的市民阶级明白易懂的东西。拉米斯学问上的定律是实用性。可是,拉米斯的这种学问理念,并未能原封不动地为17世纪思想家们所接受。激烈的宗教性对立时代过后,在波旁朝绝对主义确立前后不久,影响力日见增大的,是哲学史家理查德·波普金(Richard Henry Popkin,1923—2005)所认为的对近代哲学原理之形成至为重要的思想运动怀疑主义[13, 14]。这种怀疑主义指斥把藉由人的感觉知识误认为关于事物本性知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一种独断论。皮埃尔·伽桑狄将这种怀疑主义作为自己认识论上的原理,饶有兴味地尝试了批判旧有学问。伽桑狄的思想,在如实地揭示什么是近代学问构造须备的基本定律这一点上诚为重要。伽桑狄学术处女作是《针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逆说性研究》,他构想以全部7卷本的构成来写作此著作,但生前刊行的仅为第1卷(1624年刊)。第二卷虽以草稿的形式而为数人阅读过,但终见付梓却是死后1658年的事。中断自著的刊行,乃因伽桑狄自觉到自己批判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激进性,判断将难免招致悲剧性结果而为之[15]。此处伽桑狄的信条,正是皮浪式的“一无所知”(Nihil sciri)[16],这一原理,或可推测受到葡萄牙怀疑论哲学家弗朗西斯科·桑切斯(Francisco Sanches,1550—1623)著作Franciscus Sanchez, Quod nihil scitur(Lyon, 1581). 此著作的现代版,与英译本同时发行。Francisco Sanches, That Nothing Is Known, ed by E. Limbrick & D.F.S. Thomson(Cambridge, 1988).的影响。在伽桑狄看来,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基于绝对性根据的学问;因为我们是依靠轻易蒙骗我们的感觉和语言来认识的,所以我们能够认识的不过是假象,而不是事物的本质;因此,把假象错误理解为本质的本质主义亚里士多德学问体系不过是幻想而已。如果是到此为止的话,则议论仅仅是片面性的,破坏性的,但伽桑狄与桑切斯同样,并未在此停止思考。那么,将知识的根据置于何处为宜呢?即便说伽桑狄认为我们的知识的对象只不过是假象,充其量也不过是盖然性的东西,但还是可以想见从对象与我们相关的方式,譬如在实验和观察当中,获得某种实用性的知识。如果说学问存在的话,则只要对当下人的实践有用就大可满足了。
伽桑狄向前更迈进了一步,虽说认识并非是关于事物本身的东西,却毫无理由要去忖度。如果不是关于事物本性的知识,而是对人的实践性生活有用的知识的话,则自然研究大可奖励。对伽桑狄而言,鼓舞从事这种自然研究绝好的哲学体系,正是伊壁鸠鲁体系。试图系统性地再兴古代伊壁鸠鲁学说的伽桑狄的设想,十分具有战略性——因为他把伊壁鸠鲁视作对决亚里士多德主义独断论的战斗的同盟者而臣服于他,最终使伽桑狄下定决心复兴伊壁鸠鲁的,是与荷兰原子论者,比笛卡儿年长的友人以撒·贝克曼的邂逅参见:Jones, Op. Cit. (n. 10), p.27.。这发生在伽桑狄1628—1629年的荷兰旅行。
在17世纪的前半叶,伊壁鸠鲁以及原子论并非完全不为人知。中世纪时即有过原子论的提倡者关于中性原子论、原子论批判,参见:John E. Murdoch(translations, introductions and annota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Criticism of Atomism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 E. Grant(translations and annotation), “On Interstitial Vacua,” in Grant, ed., A Source Book in Medieval Science(Cambridge, Mass., 1974), pp.312—324 & 350—360, respectively; J. E. Murdoch, “Naissance et Devéloppement de Iatomisme au bas moyen ge Latin,”Cahiers dEtudes Médiévales, t.Ⅱ(1974), pp.11—32; Idem, “Atomism and Motion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in E. Mendelsohn,ed., Transformation and Tradition in the Sciences(Cambridge, 1984), pp.45—66。。比如,有藉由批判亞里士多德的原子论,反而成为了原子论支持者的人。异端神学家、哲学家奥特考特的尼古拉斯(Nicolaus de Autricuria,1299—1369)即为其中之一。1517年,由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发现了著名的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约公元前99—约前55)《物性论》(De rerum natura)的写本。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希腊哲学家列传》第10卷伊壁鸠鲁传,也于15世纪以各种拉丁文译本而广为人知。伽桑狄从人文主义的观点出发致力于复兴伊壁鸠鲁以下著作,描绘了驱使古典文献的手法试图重新构筑古代原子论世界观的伽桑狄的形象。参见:Lynn Sumida Joy, Gassandi the Atomist: Advocate of History in an Age of Science(Cambridge, 1987)。,他并不是仅仅单纯出于古典文献学的兴趣而企图复兴伊壁鸠鲁,而是试图唤醒活着的伊壁鸠鲁,使之成为自己怀疑主义的同盟军。早在1629年,他就完成了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伊壁鸠鲁传的拉丁文新译本,但此经加以扩充,并以《第欧根尼·拉尔修第十卷所见》(Animadversiones in Decimum Librum Diogenis Laertii)的标题而出版,却是在1649年。因而,在伽桑狄自身哲学体系《哲学集成》里为自然研究而做的草案,自然是依据伊壁鸠鲁原子论的东西。
在伽桑狄看来,伊壁鸠鲁的原子论里,提供了足以取代亚里士多德式世界观的整体性哲学基础。《哲学集成》第二部“自然学”,充溢着预示了洛克《人类知性论》中有名的一次性质——二次性质这种对概念的粒子论见解参见:Barry Brundell, Pierre Gassendi: From aristotelianism to a New Natural Philosophy(Dordrecht, 1987),此书描述了构思取代亚里士多德主义选项的伽桑狄科学哲学的全貌。。原子论不仅可以从更深层的结构上来为我们说明感觉性认识,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为有用的知识而设的研究假说发挥功能。即使遵循了这种原子论,而从词语的严密意义来看,不变的事实是既不能洞悉事物的本性,知识也依然是概然性的东西。不过对人们来说,知识只要是清晰明了的,那就足够了。例如,在当时自然科学研究者间逐渐成为爱用工具的望远镜、显微镜,便为伽桑狄提供了诸如这种程度上的明了的知识。光学器械(spec.)即为怀疑主义者(spec.)的建设性工具关于这点,以下的论稿有所论及:《微小世界を探る-顕微镜がもたらしたもの」》,刊于《镜とレンズ-无限を测る》、周刊朝日百科《世界の歴史》八〇号(1990)。。
在加深这种认识论考察的同时,伽桑狄自我进化成了一个建设性的怀疑主义者。看来到此为止,关于事物的本性,我们还是一无所知,而知识的定律是有用便足矣。《哲学集成》的第一部“逻辑学”告诉我们:“与其一无所知,不如有所知晓附带性的事情更好。”satius est, supervacua scire, quam nihil.[17]
伽桑狄的原子论里另一尤为令人印象深刻处,是将古代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改变成可与基督教教义两立可能的状态——比如说,像原子也是由上帝创造的,因而必须遵循上帝制定的法则来运动。因而伽桑狄说到:“因此,从这点来看,或许便可以这样假设,上帝一开始便尽可能多地创造了大量为形成全世界所需原子。”参见:Ibid., “Physica,” Sectio I, Liber Ⅲ, p.280b.
伽桑狄的粒子哲学,经由17世纪中叶的法国,以及瓦尔特·查尔顿(Walter Charleton,1619—1707)的解说[18],而在清教革命下的英格兰广为传播。可以认为,其思想曾深刻影响到了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牛頓甚至莱布尼茨(Gottfried W. Leibniz,1646—1716)[19]。伽桑狄决非试图构筑一种独断性知识体系。毫无疑问,可以想见,例如与波义耳同样,他也认为即便研究无法企及终极真理,也应不断地持续进行,并以从这一研究中能够获得有用的知识而感到满足。
一般认为,比伽桑狄年轻四岁的笛卡儿在学问上的扬帆启航,与伽桑狄颇有相通之处。对笛卡儿来说,有用性也是重要的学问论上的定律。而且,笛卡儿也保有可说是其独自的粒子哲学的自然学。在阅读过1637年出版的《方法序说》(作为试论,包含“屈折光学”“气象学”“几何学”)的某一读者便认为:笛卡儿的学说里,有类似德谟克利特以及伊壁鸠鲁哲学的东西参见:“Descatrs Huygens [mars-avril 1638],” Correspondance, t. Ⅱ, (Euvres de Descartes, éd. Par Ch. Adam& P. Tannery (Paris,1969), p.51;Correspondance, publiée par Ch. Adam & G.Milhaud, t. Ⅱ (Paris,1939), p.170; “Descartes Mersenne, 11 octobre 1638,”(Euvres, Ⅱ,p.396 ; Correspondance, t.Ⅲ (Paris, 1941), p.90。。
但不同于伽桑狄,因为笛卡儿干脆利落地与皮浪式怀疑主义作了诀别,并主张延长(extensio)不外即几何学空间,哲学里有一个谁都无可置疑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Je pense,donc je suis.,参照本书第一章)。伽桑狄虽然认识到数学的重要性(他曾任法兰西学院的数学教授,担任天文学),但由于认为自然世界并不是由物质性的最小存在(原子)以及数学的点所构成,且又仍保持前述那种经验主义的原则[20],因而没能到达笛卡儿的那种确信的程度。另方面,在笛卡儿这边,依然尊重自青年时代便开始沉迷其中的数学的确定性,进而通过发现“我思”这一形而上学的真理,认识到学问里必须有一个基准,即与有用性并立的确定性。笛卡儿之所以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是体悟到近代学问构造里的两个定律,即有用性与确定性的最早的思想家。“世界的机械化”这种17世纪学问理念的基础,便这样被夯实起来了。
然而,历史性地来看,对近代的学问而言,这种笛卡儿的“成功”果然就是桩喜庆之事么?在伽桑狄看来,笛卡儿的“见识”似乎含有某种敷衍了事的成分。因为他认为在笛卡儿克服皮浪主义里似有欺瞒性。笛卡儿对自己哲学上诸原理拥有自信,并将其向同时代的指导性思想家们广为宣讲时,伽桑狄反驳了笛卡儿关于确定性的信条。“我也同意您要将精神从一切先入观(praejudicium)中解放出来的意图,但仅以下一点,我却不太明白”。在伽桑狄来看,似乎笛卡儿到达确定性的步骤,“岂止消除旧的先入观,不啻接受了新的先入观”[21—23]。在这点上,继承了笛卡儿重视数学立场的莱布尼茨,也不得不承认伽桑狄论点的剀切性。莱布尼茨在《对笛卡儿诸原理一般部分的所见》(1691年执笔)中说到,“在这一点上,他(笛卡儿)其实并非是要消除先入观,而是试图替换之”[24]。
恐怕伽桑狄、莱布尼茨的观察是正确的。的确,笛卡儿高高地揭橥了取代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定律。一般来说,往往某种思想之所以为后世所接受,与其说由于这一思想内容的高迈性,不如说是由于其主张的声音之大,或明确的体系性所致。伽桑狄果然拒绝了这种体系性,而没有接受笛卡儿确实性的信条参见:Howard T. Egan, Gassendis View of Knowledge: A Study of the Epistemological Basis of His Logic(Lanham-Newyork-London, 1984), pp.155。在此不禁令我们想起尼采的《偶像的黄昏》(1889年刊)中的一节。“我对所有的体系家抱有不信,避开他们。对体系的意志,缺乏知性的诚实性”(箴言與矢·26)。西尾幹二、生野幸吉译《ニーチェ全集》Ⅱ·四,白水社,1987年,23页。。17世纪前半叶,在一边试图克服怀疑主义,一边为拥护近代科学的价值而斗争的思想家们例如伽桑狄、马兰·梅森(Marin Mersenne,1588—1648)。的最前沿,当我们读到其现象主义的、实用主义性观点时,不禁有种十分惊奇新鲜感,即其论据绝不是独断性的,而往往是由一种谦逊的、自我抑制性的音调贯穿始终。这一经验,或许能与阅读经验批判论的思想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1838—1916)著作时的感觉略相仿佛。
不管怎么说,近代科学以有用性与确定性为定律而予以了大力推进。然而,立于这一定律根基上的学问、数学以及机械论自然学,虽说成功地给近代人留存了许多的卓识,但决没有最终证明这些定律对整个学问都是全面有效的。因为这些定律并不是由超越性的、彼岸性的最高裁判所制定的。而此岸性的历史条件,才是使人相信特定的定律是先验性的存在,并有可能使之存继下去的东西。眼下我们必须质问的,正是有可能使之存继下去的历史性因素。
四 17世纪学问理念的接受与僵化
近代的数学自然科学为我们带来了令人惊叹的成果。可是,如果冷静地反省一番这些成果,则会意识到在近代科学肇始之初即嵌入学问之中的意图,与我们关于近代科学的思考方法、获得的成果乃大相异趣。被视为诸如此类科学成果的事物效用,除了为涵养科学批判精神的训练因素以外,若大胆地单纯化来看,或可将其总结为以下两点:利用了科学的技术所带来的富庶、生活的改善,以及有法则性地预测世界。可是,即便说预测世界的未来,却不是事先绘尽人类的未来。特定的天体,比如哈雷彗星向地球的接近,也仅仅是在哈雷彗星保持不变的物理性运动的前提上,才能预测。若以“拉普拉斯妖”式的法则来假设的话,则只会出现逆说性情况。
在阿基米德的方法论理念的基础上,推进了科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们,例如伽利略、惠更斯以及牛顿等在改良技术,确定自然法则领域留下了巨大的足迹。当然,他们不一定能永远发现正确的自然法则。例如,牛顿关于重力的数学理论,到了20世纪,便不由分说地由爱因斯坦的一般相对性理论予以了根本性的重新解释、以及改变。因此,一部分论者,如W·斯蒂克缪勒(Wolfgang Stegmüller,1923—1991)以及I. B. 科恩(I. Bernard Cohen,1914—2003)申诉说,剥脱了科学理论意涵的形式主义的句法论经久不变。必须承认,这一主张虽确有某种(科学内的)说服力,可是,以科学观的形式,必须是与其意义内容紧密相连为论据,也即显示了其主张不能获得全面性支持,最终,其不外即是原封不动地被弃置不顾的结果[25,26]。形式主义者的研究案,归根到底不过就是场黄粱一梦。科学观念的妥当性,不外就是一种平均性的、可谬性的妥当性,并且从科学史家的立场来看,即其作为一种“妥当现象”而成为历史考察的素材。这是科学无法规避地具有的超越论要素的必然归结。
17世纪的科学革命,大致以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诸原理》为标志达到了巅峰。这部著作,似乎给予我们这样一种印象,即在数学上彻底地阐释了天上和地上一切物体的运动法则。然而,在牛顿范式无法涵盖的惠更斯以及莱布尼茨来看,牛顿的万有引力说似乎不无某种“隐在性”参见:E. J. Dijksterhuis, The Mechanization of the World Picture, tr. by C. Dikhoorn (Oxford, 1961), pp.479。在17世纪,关于“隐在的性质”具有何种意味,参见以下文献:Keith Hutchison, “What Happened to Occult Qualities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Isis, 1982, 73, pp.233—253. 关于牛顿的讨论,在第250—253页。。实际上,牛顿自己就并不认为自己所提示的法则,对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来说是十全十美的。在增写进《自然哲学的数学诸原理》第二版(1713年刊)上的“一般性批注”里,就曾坦率地承认了这点。“然而,实际上从现象中推导重力的这些特性的根据,我迄今并未能做到。但是我并不捏造假说。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无法从现象里推导出的究竟是什么本身,就应被称作为假说的缘故。”[27,28]这样,未能完全满足实验哲学(科学)工作的牛顿,为寻求上述根据(ratio),没有停止神学和哲学性探索的步伐关于把牛顿解释为今日专业科学家乃是错误的看法,请参照下村寅大郎《ニュートンの蔵書目録》,刊于《精神紀要》1977年第35卷;《哲学者ニュートン》,刊于《ニュートン》,朝日出版社·科学の名著,1981年《月報》。——当然是空泛无果地。
支持万有引力论的18世纪诸理论(地球形状论,月球运动论,哈雷彗星回归的预言等)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牛顿的疑虑。毋宁说,正是构成科学理论的超越论因素本身,使探寻根据的行为变得没有必要。被视为因怀疑论的自我抑制而无法声张其未来权力的观念,却因这一超越论因素的变化而转化为了“教条”——俨然就像再也没有一个胆敢指出国王是赤身裸体的臣下了那样在此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商品论的以下箴言“譬如,这个人之所以为国王,不外就是因为别的人们对他取臣下之态。然而,正因为他是国王,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臣子”。参见:K. Marx, Das Kapital, Bd. 1 (1867; Berlin, 1969), p.72, Funote 21,资本论翻译委员会译,第一卷,新日本出版社,1982年,99页。。
那么,这种超越论的因素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东西呢?牛顿的思想,在17世纪末的英格兰思想界中,并非一种单纯的自然观,而是作为一种整体的世界观被接受,并制度化的。在牛顿的世界体系中,物质无论在天上还是地下,其自身都是毫无生气、死寂般的存在,是有规则地、被动地受到外部非物质性(精神性)力量才被驱动的存在。并且,在数学上被严格地定式化了的这一法则,丝毫不为周围的状况而有所变动。在牛顿著作第二版的“一般性批注”中,关于法则的主宰者,他说道:
这一至上的存在统治所有的事物。并非作为世界灵魂,而是作为万物之主。并由于这种支配的缘故,常常被称为上帝,普遍的帝王(παυτοκρτωρ)。上帝是相对性称号,乃是与仆从有关的缘故。所谓神性,即是将上帝视为世界灵魂所梦想的那样,上帝的支配并非及于上帝自身的身体,而是及于仆从之身的緣故。这至尊至上的上帝,是永恒的、无限的、绝对完全的存在参见:Nwton, Op.Cit. (n. 29), p760.日译,562页。。
牛顿这种多半含有社会性隐喻的世界体系的说明,作为与1688年的名誉革命相呼应的、党派性的意识形态而受到大肆宣扬。其一方面,成为邀击谋划反革命阴谋的天主教的恰好的论据。牛顿唯意志论的上帝,是远超天主教的“此世”的支配体制,上帝观念的新教式的超越神。在另方面,又是反驳并试图将内乱期导致英格兰陷入混乱的清教徒以及地方绅士阶层激进的、浪漫主义的自然观置于支配之下的理论根据。之所以这么说,因为置于牛顿的上帝(在此要读为英国的教会!)之下的物质(在此要读为英格兰臣下!)几无生气,只是应被安排在上帝的法则之下顺从地运动而已。牛顿的世界观,为应对国外思想上、政治上的敌对势力而被动员为一种意识形态,日臻洗炼。有名的牛顿派与莱布尼茨的争论,即应顾及到这样一种背景而加以重新考究[29, 30]。
这样,牛顿的理论范式便在1690年以后的皇家学会里稳稳地扎下了根,成了宫廷辉格派公认的神学性哲学思想而被制度化于英格兰社会。
然而,伴随这种制度化,牛顿的科学,即当初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所从事的知性活动,却被奇异地矮化为一种数学上、实验性的形态。这一制度化的形态,其自身却毫无疑念地被社会所接受并不断发挥着作用。这样一来,连牛顿自身的自制也已经成了无用之物,18世纪的启蒙主义,从某种意义上看,似乎可以特征化为一种把科学看作毋需任何正当化行为的思想运动,或说超越论因素的僵化运动参照本书第三章。[31]。
而法国也一样,在路易十四绝对王政体制下,将笛卡儿的理论范式改编成适合体制的思想并制度化的一种思想运动,则以巴黎皇家科学院为中心而广泛展开。其理念的代表者为惠更斯、马勒伯朗士(Nicolas de Malebranche,1638—1715)以及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1657—1757)。在17世纪后半叶的法国上流社会里,近代科学成为公认的思想关于17世纪法国上流社会中支配性科学思想的变迁,参见:G. V. Sutton, “A Science for a Polite Society: Cartesian Natural Philosophy in Paris during the Reigns of Louis XIII and XIV” (Princeton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1982)。此外,以下的文稿,以伦敦皇家学会与巴黎王立科学院为舞台,讨论了关于自17世纪后半到18世纪,为何近代科学制度化了的问题。参见《ふたつの科学アカデミー-国家威信をかけた近代科学の振興》,刊于《宮殿とアカデミー》;週刊朝日百科《世界の歴史》1990年第82号。,并眼见着其在法国革命后的拿破仑科学体制下受到大力宣扬,预想的拉普拉斯决定论的科学主义教条时代来临了关于法国科学思想的特质,请参见拙作《科学革命の歴史構造》第三章“フランス革命と科学思想”第四节“決定論的宇宙像の夢と現実”。。
五 二律背反的消除——历史性生活世界的复活
在此序论的开头,我论述了将近代科学自然观还原主义地实体化观念是多么地违反常理,进而揭示了这一看法,事实上是随着科学理论的超越论因素的僵化而历史地生成的结果。今天,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把17世纪的学问理念从其生成以及僵化的历史过程中解放出来,通过这种途径,给予重新阐释,确定其思想的辐射范围。
那么,近代学问的两个理念,究竟是产生于一种怎样的时代背景下呢?17世纪所谓的有用性,首先不外就是对饥饿和存续最原始物质性生命的有用性,进而就是对资本主义富裕的积累的有用性,而这与对个体生命的创造性发展,以及共同体社会中诸个体的联合互助的有用性概念,可谓相去甚远。另外,确定性这一定律,也不无17世纪的语境意味。笛卡儿对数学确定性的重视,在具有尊重对度量关心度增大这一技术考虑的同时,对16世纪法国宗教意识形态非妥协性对立之后酿成的思想性危机,还具有一种予之以如“渔夫之利”似解决方法的意味。笛卡儿哲学的批判性继承者莱布尼茨,也为消除迄至17世纪中叶欧洲宗教上,政治上的对立而构想了独自的确定性、调和的哲学。在莱布尼茨的构想里,丝毫不怀疑为了解决欧洲内部的矛盾,由统一的欧洲对非欧洲国家的侵略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一企图在很久以后,由拿破仑以一种被歪曲了的方式变为了事实(埃及远征)。
恰如试图逃离某种特定恐怖的人,在逃离过程中其脑中只有此恐怖的原因一样,17世纪的思想家们,一心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在头脑中描绘着有效的学问理念,总之试图用尽全力逃离危机发生的源头。正因为此故,在未经验过斗争的后一世代,发生了超越论因素的僵化现象,取代旧教条的新教条固定下来了。教条并不是单纯的教条,而是有其理由受到信奉。但是,在教条转化为桎梏,丧失了权威的时代的思想工作者,将教条作为教条来暴露其实体,以谋求改变定律,这些无疑也正是其历史职责。
在此,让我们将这种改变定律的要求存储于心头,再来考察一番第欧根尼·拉尔修所报告的芝诺与奴仆之间的二律背反现象吧。行盗的仆役对芝诺辩解说“我是命中注定要偷盗的”。对此芝诺回答道:“我鞭笞你也一样啊!”也许哲学家芝诺,是意在与奴仆的陈述一起宣告命运论的无效而这样回答的。可是,如果我们一旦离开此一哲学性意图来看的话,奴仆的陈述果然完全是胡诌么?完全没有作为借口的权利么?难道不是芝诺将奴仆陈述中的“命中注定”做了太过有利于己的解释吗?“命中注定”(ειματο,μειρομαι的过去完成式)如果更柔性地解释的话,也能理解为“由于某种原因、理由而不得不造成如此这般的结果”,并且,其理由也许是别人也能深信不疑的。因为倘若奴仆上述陈述,由于附加了有说服力的附带理由,也许可以辩解说偷盗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受到他人脅迫,或为了濒死的病人不得已而为之等。辩解的对方如果不是一个头脑顽固的哲学家的话,或许能减轻罪过,甚至或许会小事化了,根本就不会问罪。
反过来说,根据同样的论据,尽管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无法正当化,但并非近代科学的研究全都变得毫无意义。最关键的是科学陈述的姿态问题。在这一点上,康德批判实体主义因果概念的意图,可谓正中鹄的,1872年反驳了拉普拉斯机械决定论,高唱“我们现在不知道,将来也不知道”的杜布瓦·雷蒙自身,在柏林大学校长任上,也可以被看作为是一个具有某种实证主义心情的杰出近代科学家,不,甚至还是推进了生理学数学化的人。他只是再次提起了伽桑狄式的自我抑制(的理论)。在拥有了能够批判哥白尼以后物理学客观主义的自信后,胡塞尔也于1934年,这样写道:
恐怕可以认为,现象学颠覆了哥白尼的天体物理学——但是进而,也颠覆了认为上帝把地球固定在空间某一位置的反哥白尼主义。恐怕以现象学的水平可以說的是,遵从了哥白尼的天体物理学的计算和各种数学理论,并且正由于此故,物理学整体仅管有以上的问题,在其界限之内,保有某种权利。[32]
总之,即便不遵守从17世纪到19世纪为止支撑欧洲科学的客观主义定律,科学研究活动,经由必要的变更,依然是有意义的。犹如芝诺面对奴仆的陈述可以恢复其意义一样。
对现代的我们而言,最为关键的是,要断然拒绝近代科学自然观的实体化,在阐释其与生活世界关联的基础上,将导致实体化=物象化的历史机制呈现于光天化日之下。仅像哥德尔(Kurt Gdel,1906—1978)和海森伯(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那样打破17世纪确定性定律并不充分,以及像胡塞尔那样,仅在观念论的层面上谋求哲学观点的转换,同样也并不充分。维柯曾试图道破的事实是,自然虽然是上帝创造的,但数学自然学却是由市民社会创造出来的。然而,今天上帝已经不在了,不,而上帝这一超越性存在的一部分,模仿马克思—涂尔干(mile Durkheim,1858—1917)的口吻来说的话,即不外是奠基于自然环境之社会。从某种意义来说,上帝即是社会最高定律的别称。
我们不能像上帝那样创造自然,或者说也不能与自然其自身一体化。但却能以与独断性解释的数学自然科学方法不同的新方法来与自然和睦相处。这一新方法的摸索,正是今日社会最高定律所要求的行为。因此,首先探索解决现行矛盾的途径,我们认为,正当“上帝死了”后的时代,以维柯为鼻祖的批判史学,特别是社会史学性科学史应在批判科学教条主义中起到核心性作用。同时也不能忘记,这一历史性考察将进一步深化过去与现在的理解,也是旨在谋求解决现代社会矛盾的知性活动。我们之所以在将应依据的批判性科学史学,特意冠上“批判性”这一形容词,正是为了对此忘却事先发出警告。
参考文献
[1] Blasé Pascal. Pensées[M]. Paris, 1963. 514.
[2] 松川信三郎译. パスカル全集: 三[C]. 人文书院, 1959. 81.
[3] Diageni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vol. Ⅱ)[M]. ed. R. D. Hicks. London, 1925. 134.
[4] 加来彰俊译. ギリシア哲学者列伝(希腊哲学者列传·中)[M].岩波文库, 1989. 224.
[5] Emil Du Bois-Reymond. ber die Grenze des Naturerkennens und die Sieben Weltrthsel: Zwei Vortge[M]. Leipzig, 1882. 85—86.
[6] 坂田徳男译. 自然認識の限界について·宇宙の七つの謎[M].岩波文库, 1928. 99.
[7] David Hilbert. Mathematische Problem (1901)[A].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Bd. Ⅲ[C]. Berlin, 1935. 298.
[8] 松信译. 数学の問題[A]. 現代数学の系譜[C]. 共立出版, 1969. 10.
[9] Pierre Duhem. La Théorie Physique: Son objet-sa structure [M].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1997.
[10] 小林道夫等译. 物理理論の目的と構造[M]. 劲草书房, 1990. 256.
[11] Kurt Hübner. Kritik der wissenschaftlichen Vernunft[M]. Freiburg-München, 1979. Ⅳ.
[12] 科尔特·修布纳. 科学的理性批判[M]. 神野慧一郎等译. 法政大学出版局, 1992. 52—74.
[13] Richard H, Popkin. The Histroy of Scepticism from Erasmus to Spinoza[M]. Berkeley-Los Angeles, 1979.
[14] 野口又夫·岩坪紹夫译. 懐疑——近世哲学の源流[M].纪伊国屋书店, 1981.
[15] Howard Jones. Pierre Gassendi (1592—1655):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M]. Graaf, 1981. 22.
[16] P. Gassendi. Exercitationes Paradoxicae adversus Aristoteleos (1624)[M].éd. par Bernard Rochot. Paris, 1954. Praefatio.
[17] Gassendi. Syntagma philosophicum: OPera Omnia, t. I[M]. Lyon, 1658. 86a.
[18] Walter Charlton. Physiologia Epicuro-Gassendo-Charltoniana or a Fabrick of Science Natural upon the Hypothesis of Atoms[M]. London: Tho. Newcomb for Thomas Heath, 1654.
[19] Olivier Rene Bloch. La Philosophie de Gassendi: Nominalisme, materialisme et metaphysique[M]. La Haye, 1971. 493.
[20] B. Rochot. Gassendi et mathématiques[J].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t. 1957, X: 69—78.
[21] Gassendi. Objectiones quintae[A]. Descartes. 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hpia(1641): Euvre de Descartes, t. Ⅶ [C]. Paris, 1973. 257—258.
[22] 所雄章等译. 省察および反論と答弁[A]. デカルト著作権2[C]. 白水社, 1973. 310.
[23] Gassendi. Disquisitio Metaphysica seu Dubitationes et Instantiae adversus Renati Cartesii Metaphysicam et Responsa(1644)[A]. Texte établi, traduit et annoté par B. Rochot[C]. Paris, 1962. 31.
[24] Leipniz. Animadversiones in partem generalem Principiorum Cartesianotum[A]. Die 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 von[C]. G. W. Leipniz, hrsg, von C. I. Gerhardt, Bd. 4. Berlin, 1880. 356.
[25] K. Hübner. Kritik an der Sneed-Stegmüllerschen Theorie wissenschaftlicher Prozesse und des wissenschaftlichen Fortschritts[R]. 291—303.
[26] Zev Bechler. Introduction: Some Issues of Newtonian Historiography[A]. Z. Bechler. Contemporary Newtonian Research[C]. D. Reidel Pub. Co.: Sold and distributed in the U. S. A. and Canada, 1982. 1—20.
[27] Isaac Newton. 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cipia mathematica (1726)[A]. ed. by A. Koyré, I. B. Cohen. Scholium Generale(Vol. II)[M].Cambridge, Mass., 1972. 764.
[28] 河辺六男译. ニュートン[A]. 世界の名著[C]. 中央论新社, 1971. 564.
[29] Steven Shapin. Licking Leibniz[J]. History of Science, 1981, 19: 293—305.
[30] Of Gods and Kings: Natur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 the Leibniz-Clark Disputes[J]. Isis, 1981, 72: 93—139.
[31] S. Shapin. Social Uses of Science[A]. G. S. Rousseau& Roy Porter. The Ferment of Knowledge: Studie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Eighteenth-Century Science[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93—139.
[32] 胡賽爾. 自然の空間性の現象學的起源に関する基礎研究——コペルニクス説の転覆[A]. 新田義弘, 村田純一訳. 現象学と現代思想、講座《現象学》(3)[C]. 弘文堂, 1980. 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