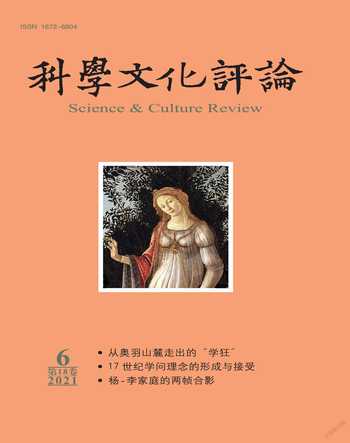从奥羽山麓走出的“学狂”纪念佐佐木力先生(1947—2020)
2021-04-23李梁



摘 要 将日本科学史,尤其是数学史研究“一举推上了国际性水准高度”的佐佐木力教授,是当代日本著名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科学史家。本文回顾作者与佐佐木力教授长达20年的亲切交往过程,并在参阅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描述佐佐木力教授学术以及社会思想的心历路程,概述佐佐木力教授的思想特质,彰显当代日本一位杰出左翼知识人丰富多彩的学术人生,垂范后世。
关键词 自然哲学 马克思主义科学观 笛卡尔 反原子能思想 庄子
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21-11-15
作者简介:李梁,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弘前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近世、近现代东亚思想史,受佐佐木力教授引导,近年关心经由耶稣会的西学东渐问题研究。
引 言
一般而言,“学狂”一词,不符汉语习惯。在此主要拟以日本江户后期著名浮世绘画家,毕生以“师法自然而画尽森罗万象”为宗旨,晚岁自号“画狂老人”的葛饰北斋(1760—1849)来类比2020年岁末遽归道山的著名科学史家佐佐木力先生(1947—2020,以下简称“佐师”,图1)。二人虽时代睽隔,专业领域迥异,但彼此毕生倾注于画或于学(问)上堪称“狂”的热情和心血,可谓毫无二致。故明知汉语中不够雅驯,仍以“学狂”称之。
二战结束两年后的1947年3月7日,佐师出生在日本东北位于雄大的奥羽山脉尾麓,仙台平原西北部的宫城县古川市(现为大崎市)加美郡(现为加美町)小野田村一户普通人家。生父因手艺高超而为远近闻名的建筑木工,生母则为工厂普通纺织女工,佐师本来为排行老五,是家中幺子,但因唯一的姐姐不到二岁便夭折,所以他实际成了四兄弟中排行老四的末子。靠父母工作养家,虽无冻饿之虞,但基本上一家过着较为清贫的生活。这或许可说是佐师一生除了在购买书籍或其他研究相关的资料以外,养成极俭生活习惯的主要原因。总之,佐师在家乡小野田读完小学到中学,到距家近20公里远的古川市读高中。古川素以出了位日本近代思想家——即曾任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师,后任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法学教授,并为大正德谟克拉西运动旗手的吉野作造(1878—1933)——而闻名吉野作造纪念馆就建于古川,佐师生前也不无自视为继吉野之后的当代古川名人的情结!,这些且不多论。总之,古川高中也以“大崎大学”的昵称而广受周围年轻学子的青睐。佐师数学才能的开花,以及在学问上刻苦钻研的精神,可以说便是在校训为“质实刚健”“尊重学问”“自主自律”的古川高中时代养成的。这从以下两件事,也可略见一斑。
其一,高中三年,无论严冬还是酷暑,佐师每天须很早起床,赶乘一个多小时公交车前去古川上学。三年里,从未旷过一次课。这对一个小小个头,体格又远算不上强健的少年,的确是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但少年佐师做到了,可见其毅力之不同凡响。据佐师自称,当年往往因睡眠不足而脸色青白。另外,或许因为与担任班主任的高桥秀夫老师极为投契,恰好高桥老师又是专任数学的教员。或因此,佐师对数学的兴趣与才能,可谓与日俱增,很快就被周围誉为数学神童。据高桥老师的回忆:“我第一次见到他(佐佐木力)是昭和三十七年(1962年)4月,在刚结束入学式后的一年级六班的教室。虽然他个头稍小,但却长得眉清目秀。……在学校,对任何学科都极为热心,尤其是对数学,更是付诸了非同一般的专注与热情。似乎他大凡都是在假期里自修好了教科书的内容,日后到课堂上,只是确认一下自修内容而已。三年级时,一到休息时间,便拿出数学问题集尝试着手开始解题。……他的座位在南边窗户第二排,至今犹记得他不时一动不动地凝视窗外天空在思索的样子。也许这时他正在思考着问题的别解方式吧。后来曾让他把笔记本给我看过,数字、图表、图形、文字等包括别解方式写得一清二楚,令人十分惊叹。这五本笔记本,他毕业时留给了我,因为我想以之为激励后辈们的材料。”高桥秀夫,“追悼热爱古高与数学的佐佐木力君”,2021年3月27日传阅。佐师终生保持着与高桥老师的联系,笔者与几位同学以及后辈一起,整理佐师书籍以及遗物时,便见到不少高桥老师的信函以及时令问候致意的明信片。
总之,有一天,佐师偶然读到法国天才数学家、革命家埃瓦里斯特·伽罗瓦事迹,深为之感动,并立志将来要成为一名数学家。正是在此意志的驱动下,本来大学要报考东北大学工学部的佐师,临到关头,毅然改为报考东北大学理学部数学专业,准备走向专业数学家的道路。据说,此举既令打算将来让佐师接自己班的父亲失望;同时却又令班主任高桥老师深感欣慰。
一 从“小野田山猿”到“国际主义者”
佐师生前不止一次公开声称,虽然自己一般不喜以日本人自称,但不仅毫不忌讳出生在日本东北乡下的事实,而且处处以故乡(宫城县加美町小野田村)为荣。先生成年后,随着思想、学术水准的升华和成熟,更喜以“最硬派的左翼国际主义者”自居。这与早期左翼运动的思想家们一样,大凡都以超越国界民族的国际主义者自许相仿。但在我看来,佐佐木先生自始至终都是个地道的东北人。更直白地说,是一个十足的东北“乡下人”(这里没有任何褒贬含义,仅就一般性情耿直或日语的“马鹿真面目”而言)。这从先生一辈子乡音未改(尤其在着急时)上也可略见一斑。比如先生东北大学的晚辈,以及学友野家启一教授(著名哲学家,东北大学荣休教授)在一篇题为“三题噺”的随笔[1]中,便描绘了在普林斯顿亲历的令人莞尔的一幕:佐老师因小野田口音影响而将自己居所地址里的“King street”发音成“Tchingue street”(东北口音往往将辅音K讹化成Tch),以致与书店店员之间,累说不通。急得佐老师最后不得不高声喊道:“Tchingue street, that is the husband of Queen street!”其實,早在古川念高中时,有数学神童之誉的佐师就因浓重的小野田口音而被同学戏称为“小野田山猿”。实际上,位于奥羽山脉之麓,仙台平原西北部的小野田,是风景绮丽的山乡。2002年秋,应先生之邀,曾与先生弟子周程(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人文学院院长),赵建海(目前为上海天文台延聘研究员)一起,有过一次难忘的小野田之行。
我从弘前驱车至古川车站与先生一行合流,然后一起前往小野田。如同司空见惯的日本地方城市一般,大崎市及其周边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瞩目的地方或说景点,但当车行至加美町时,风景为之一变:峰峦叠嶂之间,片片农田鳞次栉比,金黄色的稻穗低垂,随风似闻阵阵稻谷飘香。此景此境,我不禁对先生半玩笑地说道:“中国有句俚语说穷山恶水出刁民,而先生老家却是青山绿水,良田遍地,所以养就了先生这样一个高人了!”先生闻言大笑,可惜至今已经不太记得先生是如何回应了我的噱头话,不知在场的周、赵二兄是否有印象?
但话说回来,小野田位于北纬38度以上,又因坐落在雄伟的奥羽山脉之麓,周遭青山怀抱,湖沼森林点在,属于典型的日本东北气候地带。如所周知,日本的东北冬季漫长,冰雪封冻期长达半年之久。严冬漫长凄寒的气候,铸就了东北人朴实、木讷而又坚强执著的性格。在佐师身上,便十分明显地体现了这些性格特征。先生的中小学同学笠松幸一氏(日本大学荣休教授)回忆道:“生长于苦苦待春的风土里的佐佐木氏,性格坚毅,耽于思索,往往喜爱彻底沉浸于自己兴味盎然的事物之中。(冬日)依偎在父母以及四个兄弟之间,因是家中老小,在最受宠爱之中等待春天的到来。”笠松幸一,《托洛茨基与美国的实用主义》,参见[1]。再比如读书钻研学问时,先生从不为外界天气冷热或蚊蝇叮咬而有所影响。佐佐木先生有一独特的作息时间表,一直坚持到晚年后期——即在晚饭后,出外散步思考一番,回家小睡一阵,近午夜再起来读书写作,直至清晨再休息。他几十年如一日,几乎从未改变过。先生那接通古今,学贯西东的汪洋恣肆般的知识储备,以及庞大的著作群,便是在这种状态中产生的佐师曾自豪地说起过:在日本,没有比我读书更多的人!我曾多次伴佐师在国内外旅行过,令人难忘的是,每次他定要背上一、二十本书负重而行,有时书读得快,还要去当地书店购买,可见佐老师所言不虚,名副其实就是个硕大的书虫子。。记得我曾问过先生:“那您上午上课怎么办?”先生斩钉截铁般地笑答道:“打死我也不干!(死んでもやらない)我的课一般都是安排在午后!”闻言不由暗自思忖道:到底是大先生啊!
我曾有几次受邀访问过先生位于横滨港湾之畔32层之上的公寓,据说购得之前,为东京瓦斯公司所有,曾专门用作干部研修的场所。乃因先生是东大教授,东京瓦斯公司才肯售予他。那是偌大的复式建构公寓空间,几乎所有走廊上的书架和前所有者作研修用的硕大长方形大桌上,到处都堆满了书。可以说屋内除了书,就还是书。书是先生家中最显眼的东西,也是最大的特征。除了书,我甚至没看到一件像样的家具,连有没有电视,至今也不甚了了(不过从先生文章可知,先生还是看电视的)。毫不夸张地说,一见可知,此屋内住人显然是个极无生活感之人。
不过,先生的公寓里却有一令人难忘的生活乐趣之处,这里有一个大阳台,可将横滨湾铁桥(Yokohama Bay Bridge)尽收眼底。每年夏季,横滨湾都有大型焰火晚会。届时,在阳台上放上几把桌椅,边喝着冰啤,边欣赏夜空中璀璨的焰火,师徒们高谈阔论,该是多么惬意!可惜,我虽然确与先生有此约定,却时序不巧,始终没有抓到机会享受到这份快意之事。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先生在东大驹场的许多弟子,曾多次有过共享这份快乐时光的经历!
二 相遇相知
说起我与佐佐木先生从相遇到相交,似有必要交代一下其前因后果。
学生时代,在爱读的月刊《思想》(岩波书店发行)里,经常能读到并令我印象深刻的,即有佐佐木力大名的文论。但当时除了知道佐師是东大教授之外,对他是哪个学部、何专业的教授,我并没有刻意去确认。
2000年8月6—13日,有历史学奥林匹克大会之誉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19届)在挪威奥斯陆大学召开。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欧诸国,素为自己未曾踏足过的向往之地,加之当时参加学科共同科研项目有笔旅费可用,因而便有了一次北欧之旅。事后得知,大会上佐师在科技组,与我所在的历史组分属不同地点开会,因而我们在会上并没机会见面。但会议期间,会议组安排了各种娱乐活动。我报名加入了去卑尔根参观峡湾(Fjord)的活动。8月里的某日一早,我按时来到奥斯陆码头集合等待登船,正是在此地,迎面撞见到胸前挂着名牌的佐师。见状我忍不住用日语问道:“是东大的佐佐木先生吗?”佐师乍似一惊,待确认我会日语后,便热烈地攀谈起来。从奥斯陆至卑尔根须轮船火车轮番改乘,来回要一整天。这一天里,我与佐师形影不离,无话不谈,极为投契。大有他乡遇故知的味道(图2)。
大会结束时,我们约好回日本再联系,佐佐木先生旋即返日,我则开始了独自一人的北欧诸国之旅,直至8月底才返日。
回到日本,我才发现佐佐木先生已经数次来信询问我的归期,似有责怨我迟迟未归的语气,称希望尽早见面。若干时日后,我与佐佐木先生在东京重逢。记得他颇为欣喜地告诉我说,目前门下有好几位“中华系”的学生,希望我有机会与他们认识。
其后,与佐佐木先生之间,频有书信和实际的往来。至今许多往来之时之事,大多都未刻意记录,至今已无法确考。仍可稽考的几件,据存有资料及追忆如下:
在东京与先生重逢时,获先生赠送出版不久的《科学技术与现代政治》(筑摩新书)一书,阅后为此书明晰而有力的逻辑性,以及强烈的社会关怀精神所打动,为此特撰一短评,刊于《周刊读书人》(2000年12月1日)。此实构成我与先生的思想发生强烈共鸣的契机。我素来钦慕那种既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又有深沉的人文关怀与社会担当的学者。尽管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与佐师交往仍浅,但有时候对某些人,你却可以几句话即知可交与否。佐师即是那种几句话,即知是值得交往之人。尤其在其后不久,又拜读到先生的《活着的托洛茨基》《近代学问理念的诞生》,以及《科学革命的历史构造》等著作后,我坚信佐师正是这样一位令人憧憬的大先生。事实上,在其后的岁月里,我都自觉不自觉地被佐师那强大的磁场所吸引,随着先生磁场的磁力而转向定位。不夸张地说,关注陈独秀及其国际共运研究,尤其转向明清耶稣会与西学科学思想东传的研究,都是强大的佐佐木力磁场所发生的效应。
三 思想共鸣的媒介人——安藤昌益、陈独秀
2001年9月25—28日,我邀请佐师前来我当时所在的大学讲学,先生做了题为“科学技术与近代东亚”的连续讲座。讲学结束后,我驱车领先生游览世界自然遗产白神山地,记得行驶在蜿蜒数十公里的崎岖山道时,汽车颠簸,先生仍能酣然而睡,顿使我感到先生内心定力之强大!其后又前往毗邻弘前的大馆(属秋田县)参观安藤昌益遗迹,再南下鹿角参观内藤湖南纪念馆(对外称“乡土贤人馆”)。此举令先生极为兴奋,先生关注到安藤昌益以及内藤湖南的思想及其学术。在其后的岁月里,佐佐木先生曾认真翻读《安藤昌益全集》,以及内藤湖南有关中国史论断的重要著作。先生十分推崇安藤昌益,大有以引安藤为其思想同道的架势。甚至就在2020年7月初,先生还计划与前述芳川氏一道,再访大馆安藤昌益遗迹及其纪念馆(在八户市),说是为拍摄安藤昌益纪念碑,墓碑等照片,放入他正在撰写的有关自然论的新著里。并来信邀我前去晤谈。遗憾为疫情所阻,此行两度延期,竟成了永远也无法实现的旅行。先生最晚年的一篇题为“新自由主义范式资本主义的终结——面对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之时”(2020年5月12日传阅)的时政文里,阐述安藤昌益的思想价值写道:
昌益的思想奠基于作为治病救人的医生这一基本立场。基于此立场,通过正确地理解自然样态而织导出其独特的自然哲学,练就了一双尖锐批判社会的眼力,最终成为了一个“社会的医师”。他的环境思想甚至远超同时代西欧的让·雅克·卢梭。可以说,他本来是一位儒医,不仅治愈人的身体,同时也要治愈自然生态,进而要治愈社会的疾病。
昌益学问批判的志向,是将其激烈的批判之刃挥向以朱子学为顶点的中国宋学的学问体系整体。在此,似有必要重温一番内藤湖南提出的近世中国始自北宋的中国史观,同时也须认识到朱子学是以古代儒学为核心,揉合了老庄思想以及中国佛教的一种综合性的学问体系。昌益医学的基础是在京都学到的后世方医。但他通过批判此流派基于《黄帝内经》的医学观,发展到从总体上批判同时代近世日本的学问传统,进而到达重新审问政治经济样态的境地。
这里似有必要啰嗦一下我与安藤昌益的因缘。1982年初,因一偶然机缘,我受邀参加了同年秋天在北京香山召开的全中国日本哲学研究会大会,在一位同道的怂恿下,很偶然地选择了“被遗忘的思想家”安藤昌益作为主题,最后以“试论安藤昌益的自然哲学及其社会思想”一文与会。算是与安藤昌益结上了缘。意料不到的是,十几年后,我却因缘际会地来到与安藤生地大馆毗邻的弘前大学工作。其后在每年暑假里,我都会亲自开车带领几位学生由弘前出发去大馆,参拜安藤昌益遗迹后,再南下鹿角参观内藤湖南纪念馆后返弘。可以说这是我每年一度带学生寓学于乐的黄金路线。因此,联想到佐师的环境主义思想与安藤昌益的环境思想及其批判精神的共振,安藤昌益实际上成了我与佐师思想发生共鸣的媒介人。
引起与佐师思想共鸣的另一媒介人,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即赫赫有名的陈独秀。
大概是2001年5月下旬,佐佐木先生要求我陪同他访问中国,至浙江温州参加“陈独秀晚年思想学术研讨会”。此行是我比较深入了解先生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的开端。此行不仅结识了中国国内研究陈独秀的众多学者如社科院近史所的陈铁建、唐宝林等研究员,还得以见到几位温州本地的“托派”老人。这三位老人以及唐宝林教授一行四人,曾于2004年秋,应日本陈独秀研究会之邀,访问了日本,分别在东大驹场和慶应大学日吉校区参加了陈独秀研讨会详细可参见长堀祐造《佐佐木力氏与鲁迅·中国托派之事等》一文,见[1]。。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5月27—29日,我又与先生以及庆应大学的长堀祐造教授共赴南京大学,参加了“陈独秀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会议开幕是5月27日(陈独秀的忌日),大会会场宣布日本陈独秀研究会正式成立,先生自任会长,长堀教授为事务局长,我则忝列创始会员。
由此开始了与佐佐木先生合作研究陈独秀及其中国托派思想的计划,主要是计划合作撰写日文版《陈独秀传》以及翻译陈独秀的主要论著。我至今保存了一封日期为2003年3月24日佐师的来函。先生写道:
……
前日很高兴拜听了你对中国近况的介绍,非常感谢。
今送上谈话中提及的横山宏章《陈独秀》(朝日选书)一书的复印件。其他的汉语书籍,在去年《思想》上的论文注释⑴里已有列举。我原则上几乎所有的都有收藏。先生手头没有的,我可以通过宅急便送上,请指说。预定不日后,即会将《陈独秀传》的出版计划书提交给东京大学出版会的编辑,请务必推进执笔计划。
反击布什愚劣的战争行动弘前进行得如何?东北托派的劳动者们,正站在先头奋斗之中。
今秋乃至明春,让我们邀请中国的托派老人们来日吧!
我将于4月2号到9号,再度访弘。今天仅此要事,余言后述。
笔者注:绘马是日本寺院特有的祈愿木牌,上的绘画与名称不一定一致。因无特定译名,权且直接用日文汉字称作绘马而已。所以画的虽然是牛,但仍称绘马。
图3. 挂在佐佐木先生寓所玄关的瓷板陈独秀像及其诗句,瓷板画乃笔者通过友人请江西景德镇的名陶工绘制而成。注意遮住篆体诗句“行无愧怍心长坦,身处艰难气若虹”上部的绘马①,乃先生购自主祭神为菅原道真的防府天满宫(在山口县)。先生晚年的心态,由此也可见一斑(芳川良一氏供图)。
然而,显然佐师的计划书未能通过东大出版会的编辑会议,尤其是其后不久先生驹场遭厄事件的发生,打乱了所有研究计划,最后是无果而终。而与力卫兄等业已着手的陈著翻译工作,则随着长堀祐造教授等的《陈独秀文集》1—3卷(平凡社,2016—2017)的问世戛然而止。先生那种不时显露的热情有余,筹划不精的“乐天性”,由此也可见一斑(图3)。
如果说陈独秀研究跟我近代思想研究的专业勉强还可以挂上钩的话,那么明清耶稣会及其西学东渐的研究,则是与我从来的专业相去甚远的全新领域。
大约是2003年秋,我在东大驹场参加“佐佐木力科学史三部作完成纪念研讨会”后的一天,先生要求我考察一番中国的耶稣会史研究现状,并在他与伊东俊太郎教授主持的“阅读数学文献之会”(会场设在共立出版社)上做一次报告。为此我开始着手调查此领域的研究状况,甚至还利用回国出差机会,拜访了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结识其弟子李天纲教授,获得他们不少的指教以及资料馈赠。日后我如期在“阅读数学文献会”上做完报告。记得会后便当餐叙时,伊东教授亲切询问起我的学历出自,颇为鼓励有嘉。
2005年8月,佐师又邀请我参加在东大驹场数理科大楼召开的“第六届数学史及汉字圈数学教育国际研讨会”。佐师特意在会议期间,安排了一次饭局,引介耶稣会科学史研究的世界性权威,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乌戈·巴尔蒂尼(Ugo Baldini)教授与我认识。日后我在罗马做资料调研时,曾蒙巴尔蒂尼襄助,我们约好在教皇宗座大学(Pontificia Universitas)大楼大厅内的一家咖啡店见面,巴尔蒂尼教授亲切地为我讲解了一个多小时我欲调查资料的收藏情况,最后还开车将我送到耶稣会公文书館附近。在罗马的另一案内人,即为孙江兄介绍的宋黎明博士,他是轰动一时的《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的作者。
大约在此前后,佐师又交给我一个任务,他希望我把利玛窦、徐光启译《几何原本》中的引言与跋语译为日语,此任务最后因故大半由爱知大学的葛谷登氏完成。并将内蒙古大学莫德教授馈赠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研究论文集》[2]一书交给我,要我在中文资料调研方面,协助参与他的《几何原本》的翻译研究等。其后不久,佐师更将其从比利时搜求到手的《几何原本》的翻译底本,即利玛窦之师“丁先生”(Christopher Clavius,1538—1612)注释的15卷本拉丁文原版著作Elementorum LibriXV.(电子版)交给我,说让我先看看,日后再寻机为我讲读其内容。佐师期望通过将利玛窦,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与“丁先生”的15卷拉丁文底本加以比较研究,“以便彰显东西数学思想邂逅的微妙之处”([3],自序)。
佐师还强调说:利、徐合译的《几何原本》里,对概念的翻译仅止于概念本身,而丁先生对概念所做大量解释,内中含有丰富的神学思想,利、徐的《几何原本》都未予翻译;如果能完成这一研究,将会是件极有意义的事情。总之,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古希腊公理数学的代表性著作,《几何原本》仅次于《圣经》,是世界上被翻译成异国文字最多的古典文献。而由定义、公理以及证明演化的精密演绎思想体系,对后世欧陆乃至世界的文明走向影响可谓既深且巨。在康德哲学及近代宪法(政)思想里的深部,都有这一源于古希腊公理数学的演绎思想的影响。受先生鼓励,日后在我初浅的研究里,主要将着力点放在阐明《几何原本》几何概念的翻译及其思想在东亚各国的传播、接受这一问题之上。
佐师的专业是数学史,尤其是专究笛卡儿的数学思想。先生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增改而成的大著《笛卡儿数学思想》[4]里,开门见山便劈有专章论述“笛卡儿与耶稣会的数学教育”以及“克拉维乌斯的数学思想”等。而青少年时期的笛卡儿,正是在位于法国西部卢瓦尔(Loir)河畔著名的耶稣会学校拉·佛莱谢(La Flèche)度过了极为关键的七八年光阴。由此可见,佐佐木先生关注耶稣会史及其数学教育思想,并由此关注到经由耶稣会的西学东传问题,既是其专业所需,也是其探索眼光日益回望东亚的必然结果。邀请我协助研究的内在逻辑,或许在此。
话说回来,先生的门下,曾聚集了众多的各国俊英,为何先生不去找其弟子共同研究?比如说周程兄等,就远比我更适应这项研究工作。思来想去,也并非我有啥特殊能耐,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相较术有专攻的弟子们比如周程兄的博士论文《福泽谕吉与陈独秀:东亚近代科学启蒙思想的黎明》(东京大学出版会,2010)当然有浓厚的乃师思想的痕迹,但着重探讨的是陈的科学观或科学启蒙思想,较少涉其政治思想。,我与先生之间,是亦师亦友的状态,因而可以轻松自由地选择研究课题。还有一点,或许更为重要,即极有可能是出于佐师的苦心,借助共同研究,或可刺激一下怠惰而又漫心不专的我努力精进,各方面更上一层楼。而妙的是那段期间,我的相关研究计划,也“不幸”连续多年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的科学研究课题资助,由此也迫使我不得不亦步亦趋地滑入西学东渐这一“万劫不复”的研究之中,离原来的专业渐行渐远,竟至游骑无归(图4为佐师馈赠给笔者的部分著作)!
2005年10月与2007年6月,在弘前大学举办了两次研讨会,佐师都积极参与,分别做了“笛卡儿,莱布尼茨与东亚”以及“克拉维乌斯,笛卡儿,利玛窦与东亚——耶稣会的世界战略与数学教育”的报告。这两次会议,前后力卫、继东、孙江、少阳、阎小妹等“以文会”的兄弟姊妹都曾参加,也是佐师与以文会诸友结缘的契机。佐师晚岁最为热心参与的,便是以文会,最感亲切的人与事,即是与以文会诸友的恳亲会(图5—6)。每思及于此,我心中不禁涌起少许慰籍。
四 “东北月沉原”的武者修行与思想升华
在日本中部大学的学术刊物ARENA的2018年特辑里,有篇题为“从奥羽山脉之麓到东北大学——佐佐木力通往学问的旅程”。实际上是先生最后几年在中部大学做特任教授时,回答几位年轻同事提问的自传体随笔。以下引用未注明出处的,都出自此文。先生戚戚叹道:“但愿通过阅读这篇自传体随笔,我虽微不足道,或许多少能增加几个承认我作为人的存在(Existence)这一事实吧。”
在此仅就先生进入东北大学后的专业修行,以及关心并参与时政引发思想升华,略加叙说而已。
如前所述,还在高中时代,佐师就因读到夭折的法国天才数学家革命家埃瓦里斯特·伽罗瓦事迹而深为感动,并立志将来要成为一名数学家。从先生晚年的《伽罗瓦正传》(筑摩学艺文库,2011)一书可知,此书当为市井三郎译《诸神宠爱的人——埃瓦里斯特·伽罗瓦的故事》。在这一志向的驱动下,1965年,先生考进东北大学理学部数学科,专攻高等数学,直至修完博士课程,转向科学史专业。
东北大学的前身是近代日本继东京帝大,京都帝大之后设立的第三所帝国大学。战前便是在数学教育与研究上堪与东京帝大并驾齐驱的名校。东北帝大的理科大学(在二战前日本,文理科大学即文理学部的意味)素有“东北月沉原”的谐称,乃因数学科草创期的教授们,大多都曾留学过同时期德国自然科学与数学研究的中心之地哥廷根大学的缘故。哥廷根的日语发音“ゲッティンゲン”,在东北方言里被念成“ゲッチンゲン”,据此音配上几个颇富诗意的汉字即为月沉原。我国著名数学家、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教授,即毕业于此“东北月沉原”。记得有一年在上海,佐师曾以十分崇敬的口吻提到过这位大先辈。
关于佐师在“东北月沉原”的武者(数学)修行的详细状况,在此仅点一下先生的硕士论文“关于线型代数群的分类理论”,仅就其方法论方面,略谈几点感想。
首先是对哲学的偏好。佐师在前述自传体随笔里自称,自己最初阅读的正儿八经的哲学著作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但在学问方法论上起震耳发聩作用并终生受惠的,是现象学大师埃德蒙德·胡塞尔的《欧洲诸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先生写道:“虽是数学专攻的大学院生,却热心地阅读哲学书籍。因不满足希尔伯特的形式主义,相当聚精会神地阅读了赫尔曼·威尔。在此延长线上,系统地精读了埃德蒙德·胡塞尔的著作。在现象学与托洛茨基主义的交叉点上矗立着莫里斯·梅洛·庞蒂,我至今也极为推崇他的哲学。”
学问方法论上另一值得一提的,是先生的语学准备或者说语言训练。早在古川高中一年级时,德语就几乎是必修课。而大学时对理学部生中希望进入数学学科者,则被要求履修法语。博士课程时,佐师“虽是主修数学的学生,却往往踏入数学科大楼对面的文学部大楼,参加哲学专业细谷贞雄教授讲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等德语原典的研讨班,也热心地出席为本科生开设的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等课,上希腊语课时,将许多词尾变化写在笔记本上,最后跟随生地竹朗老师通读了以《俄狄浦斯王》为素材的教科书”。
近代日本,无论文理,专业训练的同时,必附有语学训练或要求,这是近代以降的一个优良学术传统。这不仅在大学,在旧制高中里也是如此。比如弘前大学的前身旧制弘前高校,分文理二科。文科再分甲类,乙类。甲类主修英文,乙类则主修德语。著名作家太宰治就是甲类学生,主修英文;而与太宰同窗却关系微妙的石上玄一郎(此公经历不凡,颇值一究!)则为乙类学生,主修德语。训练方法大多是略加基础语法讲解后,便开始专业书籍的阅读,通过阅读原著(典)培养读解能力。数年下来,学生大都能读通所学语言的原著,且酿成一种普遍风气,大有读不了原著非好汉的架势(原典を読まないと本物じゃない!)。
佐师在东大驹场,除了惊人的学术成果为人称道外,另一令人称羡的,即其多种语言能力。他精通英语,以及数学史专业必须的古希腊语,拉丁语。除日耳曼语系的德语外,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等皆属所谓罗曼斯语系,在词根以及动词词尾的变位变格上大同小异,有类似规则可循,故有“一通百通”的夸张之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不仅精熟欧洲数学思想史,而且欧洲古今历史与哲学思想都造诣深厚的先生来说,能读通读懂这些语种的原典著作,自是极为自然的事为纪念佐师,最近笔者正在翻译其代表作之一《近代学问理念的诞生》一书,对此点更是深有感触。。比如先生的论著,凡征引部分,哪怕是有日译本,也同时一定要附上原著的出处页码,上村真男与佐佐木力译自拉丁语的维科《论我们时代的学问方法》[5]等,都是明证。顺便多言一句,佐师在近代科学论上,十分推崇维科的观点。
此外,先生还粗通俄语(当与其古典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关),晚年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任教四年,因研究中国数学史以及《庄子》所需,苦读中文。据先生自称,借助字典,他已经大致能读懂数学专业以及一般性中文论著的内容。鉴于中世阿拉伯世界的辉煌对欧陆文明的巨大影响(所谓“12世纪的文艺复兴”),先生曾跟随伊东俊太郎教授学习过一年阿拉伯语,同时在学的另一位同学,即为后来因翻译了《恶魔的诗人》而在筑波大学校园遭到暗杀的五十岚一副教授,此事至今仍为悬案。不过,记得佐师曾亲口对我说起过,遗憾年轻时没好好学会阿拉伯语。
不难想见,超群的语言功夫,加之天道酬勤,先生的科学史研究硕果累累。而在青春多感的时代,因投身世界性反越战运动,积极思考时事政治,融学问与政治运动为一体而获得的思想升华,则不仅使得先生的研究以及思想不断持续地向一种哲学思辨的高度提升,而且具有了一种紧密关怀社会的恢弘格局(或说气概)。这方面的委细动向,在先生的先辈同学织田胜也氏(《环境社会主义通信》主编)的随笔“1968年前后的东北大学新闻社与佐佐木力氏”以及前述笠松幸一氏的文章里都有详细描述。这里仅就我的理解,略谈一点感受。
1968年的巴黎“五月革命”,被视为现代世界的重要转换点。一般认为,“五月革命”本身,或多或少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但其时代意义并不在此。真正具有时代性意义的,则是如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那样,以独立思考的知识人身份介入社会公共事务,如反战、环保、乃至欧共体走向等,并对当今西方社会的“现代性主体危机”进行建设性批判,力求维持社会正义,保障人权以及自由(思想)传统。
高中时“对自己生活的时代几乎不具任何政治性意识”的佐師,到了大学高年级,适逢上述风起云涌的时代风潮,自然难以置身事外。“我正是在那个月份里,自觉到自己成为了一个明确的托派马克思主义者。但并非‘五月革命的影响,而是前叙一连的读书与同时代的经验改变了我。”
佐师的读书经验,首先是其时岩波书店刚出版的《资本论》(向坂逸郎译,3卷4册版),以及《资本论》普及版性质的《工资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当然也有专业方面的读书,如《户坂润全集》等。如他所言:正是在时代转换的1968年,通读艾萨克·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极大地改变了我”。这里所谓“极大地改变”,自然是指自己真正成为一个托派马克思主义者的意味。“在与仙台的托派系工人、学生并肩共斗之际,不断加深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因密切关注现实的动向,或多或少也接触到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譬如比利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埃卢内斯特·曼德尔的著作《卡尔·马克思——从〈经哲草稿〉到〈资本论〉》,1971年甫自河出书房新社翻译出版,即热心翻读。我认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师即是曼德尔先生。”
其实,佐师虽称思想上最后与之诀别,但不难看出他的另一位马克思主义之师,实为战后日本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思想家广松涉(1933—1994)(图7为广松涉编校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书影)。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60年代末,佐师读到广松涉精湛的《恩格斯论》,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为此特撰一书评刊载于《东北大学新闻》(1969年2月5日号)。书评刊载后,佐师不仅为周围人戏称为“仙台的恩格斯”,且辗转为广松所知,从此开始了他与广松氏的“蜜月”交往期。佐师以战后最年少作者(23岁时)登坛岩波《思想》杂志,即为广松氏怂恿的结果。23岁的佐师在《思想》(第558号,1970年12月)上发表的首篇论文标题是“近代科学的认识构造——阐明近代科学意味的视角”。神奇的是,先生人生最后一篇论文“恩格斯未完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项目”,也刊载于《思想》(2020年12月号)之上。遗憾的是,佐师永远也无法读到刊有其文的这期《思想》了。不过,这是他在旧稿基础上修订的新版,其实早在七年前,我曾应佐师之求,将旧稿译成中文,刊载在《自然辩证法通讯》(2013年4月号)之上,标题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构思辨析——未完的研究课题”[6]。我以为,这既是我与佐师的一次学术因缘,也是我进一步了解其理论思辨力,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把握之精之全能力的难得之机。
可以说,佐师著述里呈现出的那种高度的哲学思辨性,缜密的逻辑性,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尤其那“诗意般的华丽笔致”(野家启一语),便是在前述激荡的时代里,藉读书思考,以及奋笔写作锤炼而成的。在火热的20世纪60年代末期,佐师称:“我在反战这一原则上毫不妥协,因而支持旗帜鲜明的反帝与反战的学生们。”“我虽然帮忙刷过反战标语牌,但却与学生活动家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并非一个有着心情伦理思想的人。然而,对责任伦理,却严格要求。换言之,我不为单纯的激进主义心情所动,其他同年代学生常见的那样,一从基础部进入专业学年,便从原先的激进主义运动中脱身而出,从此‘洗手不干,与此不同,我偏偏是选择了与之截然相反的途径,或许正是为这种责任伦理感所然吧。”总之,这种参与现实政治的实践经验引致的思想升华,不仅使他成为一个始终不渝的古典马克思主义者,更使佐师其后的研究与思索,未囿于狭隘的成果主义窠臼,总是那么清新脱俗,呈现出一种逻辑缜密、气势澎湃而又极接地气之风格[7]。可以说,无论在思想高度,还是学术精度,乃至社会关怀上,佐师周围鲜有可匹敌者。
五 关于“孤高的美”——佐佐木力美意识试论
在前述ARENA的2018年特辑里,有篇佐师为一位北海道的无名画家山内龙雄(1950—2013)写的画评,标题即“孤高的美”。我觉得这句话,其实用于描绘佐佐老师自身,同样恰如其分。笔者想就佐佐老师的日常生活中呈现的美意识,或者说美学思想试作申论,这对了解佐佐老师之为学、为人都至为重要。
笔者在与佐师20年的交往之中,虽然实际上是聚少离多,但借助网络,却有种长相往来的感觉。佐师每有新作新论,几乎总要寄给我。有时论及有关中国或东亚问题时,还要不耻下问地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或看法。无论是实际见面,还是在网络的假想空间里,佐师予我的印象,恰如他自称的那样,不折不扣就是一个“惟热心学问之道而几无兴趣的野生学者”。所谓“努力做出一种山野上‘花草般野生的学问”,乃佐师的理想之境。
“野生”既是佐师精神性象征,也是其非主流意志的宣示。进而言之,也即其东北人特有的心理特质象征。这一特质的形成,不仅与出生日本东北寒村的自然环境有关,也与他做建筑木工的父亲,以及工厂女工的母亲这一家庭环境密不可分。我明显感到,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佐师的视线里,始终会有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他这种对社会最底层民众的关注、同情,我以为正是他的古典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本出发点。比如好几次在谈到当年在中国烧杀抢虐的日本兵时,他总会说道:“这些人其实大多都是些贫穷的农家子弟。”反战的佐师,当然是站在谴责日帝对中国侵略的立场,但指出士兵做国家鹰犬的同时也是受害者的事实,可见他视线的与众不同。
终身未娶的佐师,日常生活中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饮食也十分简素。我曾好奇问过佐师一日三餐如何解决,佐师的回答令我难忘。他说,很简单,基本上就是喜做味噌酱汤煮山(野)菜、烤鱼而已。不难想见,佐师肯定没有时间和心思花在烹调美食之上。他从未吸过烟(据说遵守社会主义者不可吸烟的戒律!),进大学前也从未喝过酒。日后与我们同饮共餐时,虽颇显酒量,但从无痛饮放歌至醉之事。此外,我注意到先生着衣尚黑,这或许既是其精神性,也是其美意识的具现。黑色有种种象征意义,但我大胆猜测,佐师或仅取其简朴,纯粹之意而为之。
这与佐老师少有的兴趣之一,即在古典音乐中,对巴赫情有独钟类似。巴赫的音乐,尤其是平均律与纯粹数学有相通之处,数学出身的佐师喜爱巴赫当是顺理成章之事。事实上佐老师就曾写有“巴赫的音乐与数学”一文。这也同时令人想起毕达哥拉斯美在数字之中的名言。据说,佐师最喜欢一边听着巴赫的《马太受难曲》(Matthuspassion),一边读书写作。
佐师极为推崇山内绘画(图8),但我对佐師接触并欣赏山内绘画的起始经纬不甚了了。就佐师购得并悬挂在其横滨寓所的一幅自题为“云 孤高”的绘画而言,佐师写道:“我以为这幅艺术作品的神髓,即为其中小小的横向长方形被围在画框全体的纵向长方形里的宽阔的空间。这一空间的形状与色彩,秀逸无比。色彩乃为拒绝语言表述的暗蓝色,恰似造访奈良斑鸠之里即映入眼帘的,彷佛一种昭告古代日本高尚精神的觉醒般的、无以言表的美。”我不懂画,不知佐师的画评是否恰如其分。不过,从山内氏以几何学意味的简洁、纯粹的暗褐色和线条,勾勒的纵横长方形形状所呈现的“难以言表的内省之美”看,似与佐师作为数学史家的简洁、沉静的美意识,十分契合。因而佐师极力嘉勉画家摆脱商业主义的羁绊,继续研磨色彩,雕琢形状,向更高境界提升。我以为,这篇画评,看似佐师在点评山内画作,也是佐师的自画像。可以说是理解佐师美学思想不可或缺的文字。行文至此,忍不住要提到一篇佐师的未发表论考,即“基于艺道论观点所见的纯粹数学”一文(收于ARENA的2018年特辑)。此文极其鲜明地呈现了佐师的美意识,或说美学观。
自称几无趣味的佐师其实也未必毫无爱好。除了钟爱巴赫音乐外,佐师还是一位“无类的观能爱好者”。虽然自谦只是作为一般“好事家”(dilettante)似的爱好,未必是能的行家里手。那么,对佐师来说,“能”的魅力何在呢?老师写道:
或许是因为能的抽象性与单纯性,“脱俗”的精神贵族性,其彻底的乡土味在某种意义上与纯粹数学相似而喜爱。另外,诚如细尾实在《道元与世阿弥》中指出的那样,能乐的集大成者世阿弥的思想背景存在着曹洞禅。因为我是一个“大大的道元崇拜者”的缘故。……在前近代的日本知识人当中,我特别喜欢空海与道元。在寒冷气候的贫瘠的东北地方,也许若非如曹洞宗那样体恤“土民”的佛教,则很难生根开花的缘故。
在此,我们有必要跨越这种感性阶段,来看看佐师如何将世阿弥能乐理论的代表作《花镜》《拾玉得花》中展现的艺道论适用于数学论。在世阿弥艺道论注释中,佐师特别推崇能势朝次的《世阿弥十六部集评释》,认为其最详细地注释了“九位”之艺道论。在能势的注释本中,“九位”作为“九位次第”收录其中。能势分为上三花与中三花的能,基于世阿弥的“幽玄风”。中三位的能,努力一把,即可表演。对能势设置的上三位与中三位的区别,佐老师深感兴趣。他认为,中三位是伎艺的世界、锻炼的世界,到达那儿是“达者”的境地。至此境地,努力一把或即可企及,只要是一个还算可以的表演者完全即可表演。与此相较,上三花则存在一非单纯的伎艺训练而能逾越的鸿沟。不管怎么说,那即是正位,是“心”,是“悟性”之位。是惟有天赋禀异者才能到达的“名人”的境地。
佐师说,能势对世阿弥能乐理论的以下解释,更富哲理性。“把玩伎艺者不能仅满足于伎艺本身,搞学问者也不能仅满足于搞出点学问来。必通过其伎艺,以及学问打开自己的心扉,获得作为人的证悟之后,伎艺才得以灵动展现,学艺才富有生命力。”
总之,追究能乐,恰似一般艺术那样,不外即是追究“美”。因为纯粹数学理论,其第一要义全然没有实用性之必要。而是“花”,理论追求的是“美”。
或许可以说,佐师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贵族式的孤高的美,然而正是这种孤高,对理解并欣赏的人来说,可将其看作一种“美”;反之,则往往或被看作“孤傲”,甚至“狷介无礼”。曲高和寡,顽固劲,马鹿真面目,尽管精神上追求孤高的美,因性子急,现实中老师身边却不时生起各种不谐和音。比如无论平地还是山路,走起路来行如风,往往令同行人跟不上,做起事来一往直前,我行我素,以致目中无人,难免不时招致误会、甚至怨恨,引起矛盾、带来麻烦。佐师写道:
我极少称赞人,在未发自内心首肯之前从不点头称是。反躬自身,这一顽固劲自从懂事以来一贯未变,或说此即在铸造了自身的西欧流批判精神的环境中经长年累月发酵而成,似更近真实。我讨厌靠嘴皮子来奉承人。这在充满和之气的日本不时引起麻烦。(“孤高的美”)
而佐师也在世纪之初遇到了人生最大的麻烦,困扰着他的晚年。笔者对事件的详细经纬所知有限,佐师作有狮子吼的大著《东京大学学问论——学道的劣化》[8],本文无须多言。所幸,以司马迁、菅原道真(845—903)为榜样的先生,并未被上述厄难所压倒。而是如菅原道真那样,仍“在艰难中治学”,并“未因学问上的嫉妒被剥夺了社会性身份而愁眉苦叹,通过学问的再生与提高锤炼自身,为后世的学徒们锤炼学术,裨益世间,岂非对社会的最好回报。……学问思想上乐天主义者的我,或可斗胆地许诺一番,尝试做个“新的学问之神”也未尚不可。”
佐师在艰难之中治学的成果,即可谓佐师数学史研究集大成的煌煌大著《数学史》[3]。
六 “世界大的数学史”
值得庆贺的是,2010年3月4日,佐师63岁生日的三天前,也是最终将从任教30年的东京大学退休的大半个月前之时,先生数学史研究的集大成之著《数学史》由日本极负盛名老铺书肆岩波书店出版发行。
对佐师而言,前述科学史三部作,即《科学革命的历史结构》(1985)[9]、《近代学问理念的诞生》(1992)以及《笛卡儿的数学思想》(2003)不过是自己数学史研究“助跑”阶段的成果而已。而横跨东西贯通古今上下五千年的《数学史》,恰似司马迁的《史记》一般,名副其实是在艰难困厄之中,倾注了浑身力量的“发愤之作”。也是先生创成“世界大数学史”(oecumenical history of mathematics)的宏大构想的结晶。先生在《数学史》序论中写道:
若从我自身的数学史研究的旅程来看,我曾深受雅各布·克莱因的《希腊计算法与代数学的成立》的刺激。我与晚年的克莱因曾有书信往来,其后并通过列昂·斯特劳斯,得知他的著作刺激了近代政治学史的成立研究。([3],序论,页20)
晚年的佐师多次强调,他是“激越的库恩粉”,自己“学问上的教父”就是库恩。因此,佐师说:
我的数学史,乃是将库恩科学革命的概念数学性地植入一种“历史性的·数学的哲学”的学问课题之中,与此同时,并在此基础上,归根到底谋求到达“世界大的数学史”之境地。在此意义上,期待我来自东亚的视点,得以肯定地发扬光大。……与李约瑟倡导东西科学思想的统一而获得的“普遍性科学”不同,毋宁说我是企图通过多样的科学思想的多元主义的结合,构筑一种“世界大的科学史”。([3],序论,页14)
全面论述先生的《数学史》,既非我力所能及,也绝非我的任务,值得欣慰的是《数学史》的姊妹篇,也是精研中国数学史成果的《日本数学史》已经出版,此举足可慰先生的在天之灵,裨益世间后世学徒《日本数学史》将于2022年2月由岩波书店出版。。
七 从“环境社会主义”到反原子能的自然哲学——另一种意义的“不断革命论”
2015年春,在樱花盛开的季节,笔者收到佐师发自北京的电子信,有二事相告:第一,希望《科学论入门》的中译本能找到适当的出版社出版。其时正好与北大出版社的周雁翎氏交流过此事。得知周氏与我认识(几年前经周程兄介绍),希望我也从旁撮合一番。或可在北大出版社出版。第二,他在《近代学问理念》的基础上,正在构思写作反原子能的自然哲学。并强调自己的原点还是17世纪思想,要反复阅读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同年年末,佐师返日休假。多年来,佐师与我们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每年年末或年初,都要跟力卫兄及我设一席,聚会欢谈。除偶尔在外面店里外,大多在力卫兄家。2015年的年末,也约好在力卫兄家聚会。可是待到了约定的那天,才知佐师因写作渐入佳境,很少有地取消了约会!2016年6月由未来社出版的《反原子能的自然哲學》[9],即其时奋笔疾书的成果。
借用野家先生的话来说,此书的出发点乃在继承了“市民科学家”高木仁三郎(此书扉页上即有追忆高木仁三郎之献辞),以及“希望的诗人”栗原贞子等反原子能意志的基础上,并在空间上、地理上发展了恩师库恩的范式论而形成的跨文化视野中的科学哲学的构想(“文化相关的科学哲学”,intercultu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用佐师自己的话来说:“即不仅仅从数学史方面将库恩科学哲学的思考扩张到东亚的科学史,而且政治上,更强调其根源性。”([10],序言)
这里政治上更彻底性,根源性,或许即先生在序言里强调如下看法:
然而,稍加回顾,难道不是再清楚不过,虽然经历了广岛、长崎、福岛这种科学技术史上的历史性大事件,而日本的思想家们却并未尝试作科学思想上,乃至自然哲学上的反省思考。([10],序言)
佐师有鉴于上述这一现状下的思考,可以说是他融学术研究与现实社会关怀一体的思想的一贯的逻辑演化。其思想脉络如下:即从倡导内含科学技术的“环境资源论式轮回”的“环境社会主义”思想,到达反对基于培根式机械论自然哲学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极致形态,即坠入“反自然”状态的原子能的发现及其利用(尤其是原子弹的研制等军事利用)的现实。
必须指出,佐师反原子能思想的发展深化,与其在中科院大学四年任教的经验密不可分。
其一,鉴于日本广岛、长崎和福岛的原子能带来的惨痛教训,佐师对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原子能发电的国策深感忧虑,为此来信(2016年6月28日)告诉我以“中国人的老朋友”的立场,撰写了“原子能的科学考察”一文,婉告中国人民。并同信发来此文的中、日文版,希望我校阅一下中文译文(乌云其其格女士译)。其后此文以“没有卫生间的高级公寓—原子能的隐忧”为题刊发在《读书》[11]上。其二,也极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任教的经验,加之佐师利用各种假期有目的地到中国各地走访旅行的实际体验,他心中酝酿已久的一个理念喷薄而出:即力图从东亚,尤其是古代中国思想中,发掘并提炼出一种迥异于西洋机械论自然哲学的有机的自然哲学思想。佐师锁定的目标为庄子与传统中医学。2015年3月28日,佐师在给我和力卫兄同发的电邮里,称正在为《庄子》齐物论第二篇的解释而费神。针对“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一句中的“两行”作何解,参阅金谷治与池田之久的解释。前者释作“虽为对立的两者,却圆润无碍地流淌”,后者则根据王先谦的注,释作“批驳否定此思想的圣人,及依此而立定的齐同世界这两者皆得以体现之谓”。池田教授明显在批判金谷说。因此佐师意欲征求我和力卫兄的看法。虽然,如力卫兄在回复佐师的信中所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曾是池田教授的直弟子,但实际上一开始就游离秦汉,根本就没有学得皮毛。因此,我仅将目前日本立于中国思想研究最前线者之一的汤浅邦弘教授(大阪大学)的同一处的注解扫描送给了佐师而已。不过,佐师显然极为推崇池田教授的庄子解释。
佐师企图自古代中国思想里提炼的关于东亚独自的传统自然哲学的思考,浓缩于《反原子能的自然哲学》的第四章“东亚传统自然哲学的可能性”之中。通过三读《庄子》,惊喜地发现庄子的自然主义思想,即“无以人灭天”的“天钧”思想外,倾注了极大的精力考察了传统中医学(汉方本草医学)及其自然哲学基础,阐述了作为“治愈之术”的传统中医学与日本汉方医中的相承关系及其在东亚各国医学中的存在意义。最后佐师作结到:
我认为,适合于重视环境的自然哲学的医学,即为中医学与日本的汉方医学。以我的科学哲学的词汇换言之,存在于医疗根底的自然哲学的范式多样化为宜。不,理应多样化。倘若以为惟有近代西洋的机械论自然哲学才能创生有效的医疗实践,则乃性急而极为狭隘。我坚信,关于现代中国医疗制度体系的理念,即现代西洋医学与传统中医学并行不悖,各自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中西医结合医疗的多种形态。([10],页333)
在此,提桩不无黄婆卖瓜之嫌的事,也许佐师正是基于上述理念,因而在他任中部大学特任教授时做的一件大事,即2018年10月在中部大学组织的一场大型国际研讨会“寻求新的科学的思考方式——东亚科学文化的未来”上(图9),给我出的与会课题即为“中国·日本本草学的传统与近代西洋科学”。门外汉的我,恶战苦斗大半年,总算勉强交了差,并获佐师“力作”的谬奖,好歹又圆了场与佐师的学术之缘,幸甚。
八 尾声——为纪念的翻译
前年岁末,佐师遽归道山的噩耗震惊了吾辈,自不待言,痛定思痛之余,吾辈一个共同的看法,即是佐师太过信,太大意了。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佐师还有那么多写作计划,再活个十年甚至二十几年,也未必不可能。思之,真是令人遗憾莫能,悲叹不已。据说佐师11月17日入院手术,之所以28日即匆匆出院,甚至当夜还喜悦不禁地告诉自己乡里晚辈芳川氏说,为选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日出院而喜悦不已!纵观佐师的一生,似乎可以说,生而为恩格斯之徒,死而为恩格斯之鬼魂也!呜呼,多么纯粹可爱的乡党啊!
开篇以之比拟佐师的葛饰北斋临终之际,据说曾作夫子自道:“天若再假吾十年光阴……”稍停片刻后又接着喃喃自语道:“不,再假吾五年光阴,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画家了!”说罢气绝而逝。以此揆之佐师,天若再假他十年,五年光阴,满腹著作素案的佐师,定会给我们留下更多也更为圆熟,更为精致而富有洞察力的鸿篇巨制!呜呼,天命难违,徒呼奈何!惟愿佐师的学问精神,他的精致遗著,惠泽日中学林。
在此顺告二事。其一,为纪念佐师,眼下笔者正在戮力翻译佐师代表作之一《近代学问理念之诞生》。一切顺利的话,中文版可望明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二,包括古代丢番图以及帕普斯的珍稀拉丁文原著,D. T. 怀特塞德编辑的8卷本完整的《艾萨克·牛顿数学论文集》,以及莱布尼茨、笛卡尔原版全集在内的佐佐木教授长年收集的近3000册拉丁、意、法、德、英、希腊、甚至少部阿拉伯语的珍贵专业图书,目前书籍整理、书目制作工作已经完毕,等待海运通关后,将落户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馆,祈愿“佐佐木力文库”挂牌揭幕的那天早日到来,嘉惠我国学林,激励莘莘后来学子,精益求精,日新進步,不断向世界学术高峰攀爬!
最后引用佐师生前爱用的古希腊“医学之父”科斯岛的希波克拉底的箴言结束本文,笔者以为,这句话也精确地概括了佐师的一生,并且似亦暗合佐师晚岁十分痴迷的庄子“生有涯而知无涯”之意。此即:
人生短暂,学无止境!(Vita brevis, ars longa)
参考文献
[1] 中部大学研究推进机构编辑. 学问史的世界——佐佐木力与科学史·科学·哲学[A]. ARENA, 2018年特辑[R]. 2018年11月.
[2] 莫德, 朱恩宽主编. 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研究论文集[M]. 呼和浩特: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6.
[3] 佐佐木力. 数学史[M]. 岩波书店, 2010.
[4] 佐佐木力. 笛卡尔的数学思想[R]. 东京大学出版会, 2003.
[5] 维科. 论我们时代的学问方法[M]. 上村真男, 佐佐木力译. 岩波新书, 1987.
[6] 佐佐木力, 李梁.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构思辨析——未完的研究课题[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3,(4).
[7] 佐佐木力. 马克思主义科学论[M]. 美玲书房, 1997.
[8] 佐佐木力. 东京大学学问论-学道的劣化[M]. 作品社, 2014.
[9] 佐佐木力. 科学革命的历史构造(上、下)[M]. 讲谈社, 1995.
[10] 佐佐木力. 反原子力の自然哲学[M]. 未来社, 2016.
[11] 佐佐木力. “沒有卫生间的高级公寓”——原子能的隐忧[J]. 读书, 2016,(11).
The Sciential Enthusiast from Mt.Ou
In commemoration of Prof.Chikara Sasaki
LI Liang
Abstract: Prof. Chikara Sasaki is renowned to have raised the Japanese history of science,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mathematical studies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by the Trilogy of History of Science, which consists of The Historical Structure of Science Revolution(Iwanami shoten, 1985 first ed.), Birth of Modern Thoughts of Scientia (Iwanami syoten, 1992) and Descartess Mathematic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2003). This commemorative essay depicts the life of Prof.Chikara Sasaki through various topics to highlight his brilliant thought in both academic field and in Society.
Keywords:natural philosophy, Marxist science theory, Descartes, anti-Nuclear thought, Zhuangz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