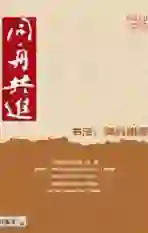说杜甫的《蜀相》
2021-04-20黄天骥
黄天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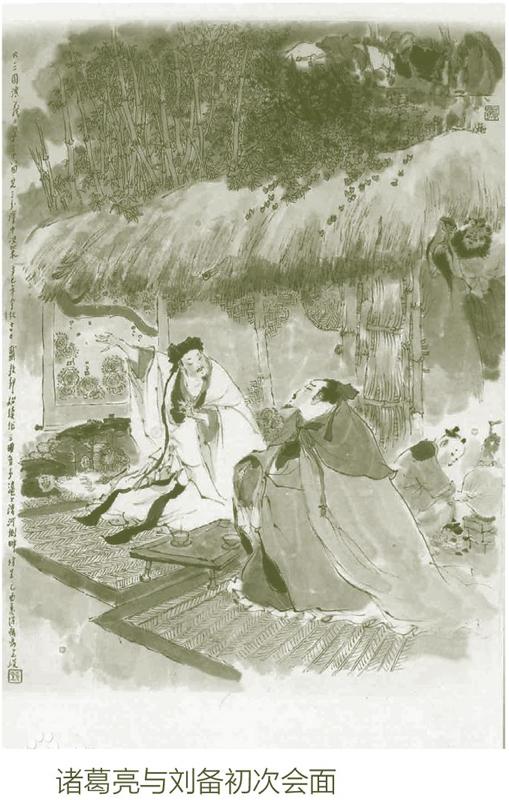

【咏史诗:托往事以抒怀】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我国历史悠久,不知发生过多少值得回味和深思的历史事件,产生过多少可歌可泣、可咎可誉的历史人物。这一份丰厚的遗产,为诗人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所以咏史之作在诗坛上蔚然成风。被誉为“诗圣”的杜甫,除了写过许多直面现实、描绘天宝年间人民疾苦的诗作外,也写过不少“咏史诗”。其中,《蜀相》是最为脍炙人口的一首。
历史是时间长河的记录。它像是万花筒,五颜六色,稍稍挪动便会出现新的图形;它又像是回音壁,这一头发出的声音,会在另一头产生回响。尽管时空的隧道遥不可及,但反响会惊人地相似。当诗人进入历史的画廊,会在历史的留影中,影影绰绰地看到现实,甚至看到自己也在时光的黑洞中,载浮载沉,载欣载奔。因古今之兴会,托往事以抒怀,便成为咏史诗这一体裁的功能。
杜甫的《蜀相》,写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的春天。那时,他初到成都,经历过“安史之乱”,看到了人民乱离的苦难,看到了唐王朝的昏庸腐朽。他虽然曾有满腔热情,希望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这理想始终无法实现。在唐玄宗当政的时代,他参加过科举考试,却名落孙山。唐肃宗取代唐玄宗后,杜甫经历千辛万苦去投奔他,但肃宗对他根本不重视,只让他当个芝麻绿豆般的小角色。现实的政局和个人的遭际,让他苦闷感怀,也让他知道自己很难再有所作为。
杜甫曾感慨地说:“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意为不再希冀有周公孔子那样的圣人出现,只是希望有英雄人物,能够站出来洗涤污垢、扫荡乾坤。所谓“吕”,指的是吕尚,即辅助周武王灭商的姜子牙;“葛”,正是三国时期的蜀相——诸葛亮。诸葛亮辅佐刘备,立足西川,与曹魏、孙吴鼎足三分,点燃了统一天下的希望的火炬。杜甫到达成都,那里曾是诸葛亮运筹帷幄的政治中心,抚今追昔,自然想去祭祀诸葛亮的武侯祠瞻仰一番,于是就有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咏史诗。
诗作的首句“丞相祠堂何处寻”,诗人以提问的方式喝起,一下子就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其实,杜甫当然知道武侯祠的位置,提出“何处寻”,意在表现他对武侯祠急切的向往之情。所以,接着他说“锦官城外柏森森”。锦官城,是四川成都的别称,他告诉自己,也告诉读者,诸葛亮的祠堂,就在成都郊外那長满密茂柏树的去处。有意思的是,这自问自答的方式,杜甫在一些作品中也运用过。像《望岳》一诗,开首两句是:“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这种句式,颇能表达出诗人对审美客体虔诚景仰的情态。
杜甫特别写武侯祠在长满柏树的地方,用意是深刻的。
在文学理论中,有“符号学”的说法。所谓符号,是指在同一文化范围中,人们对一些事物的形象,经过概括和抽象化,将其凝聚为符号。在同一文化系统中生活的人,对符号的内涵有着共同的认知。约定俗成后,人们便可以从一个简练的符号中,感悟到它背后蕴涵的特定而丰富的意义。例如,牡丹的形象,人们除了感受到它的美丽外,还会知道它有富贵荣华的内涵。又如诗文中出现的竹的形象,作为符号,人们会联想到它坚韧与清高的个性。因此,在文学作品里,适当选择并使用人们共同认知的符号,可以事半功倍且形象地展现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按照我国的民俗习惯,长期以来,松和柏都被人们视为品格坚强的象征。《论语·子罕》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特别是柏树,更被人们视为坚贞不屈的符号。《诗经》里便提到:“泛彼柏舟,亦泛其流。”(《邶风》)“泛彼柏舟,在彼中流。”(《墉风》)人们认为使用柏木制造的船,分外坚固。因此,诗人在诗句中选用“柏”的形象,便不仅仅指它是一种乔木,而是透过它启示其深层的社会性特质。
【“一石二鸟”的艺术效果】
据知,诸葛亮死于公元234年,与杜甫创作这首七律的时候,相隔有500多年的岁月。在唐代,环绕着武侯祠周遭的树丛,是否真的只有柏树?我们不得而知。但为什么杜甫不用“树森森”或“木森森”“柏松森”之类的字眼,只单单挑出柏树,这显然是有独特用意的。他是要借用柏树坚贞的意象,作为对诸葛亮人格的衬托。所以,这两句在字里行间,已渗透着诗人对诸葛亮无比敬仰的感情。
- 四两句,杜甫写他进入武侯祠:“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当杜甫踏进祠堂的石阶,发现里面有着秀美的景色。他写自己向前望,看到的是石阶下碧青的草色;向上望,树梢上黄鹂在歌唱,整个祠堂的氛围清幽而宁谧。
但是,杜甫在这两句诗中,又各下一“自”字和“空”字,可见眼前的景色,触发了他灵魂深处的共鸣——愈是看到景色的秀雅,心情也愈低落。正像金圣叹所说:“三、四,碧草春色,黄鹂好音,入一‘自字、‘空字,便凄清之极。”(《杜诗解》)
杜甫进入丞相祠堂,首先注目于青草。青草,文坛上常把它视为象征事物默默更替的符号,像李后主说: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别来春半》)白居易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赋得古原草送别》)人们习惯把青草的生生不息,和时间的不断消长联系起来。武侯祠内芳草萋萋,说明了春秋代序,岁月如流,但加上了“自”字,这一来,那和石阶相伴的碧草,年复一年,只能顾影自怜,显得冷清寂寞。在欣欣向荣的碧草面前,英雄人物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它所展现的春色,显得失去了意义。细看杜甫的许多诗作,不难发现,他常以草木的茂盛与心情作反衬,像“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和“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武侯庙》),都是如此。也可以说,反衬手法的多次运用,恰好是他心情矛盾的写照。
同样,杜甫写他听到黄鹂在隔叶歌唱,美妙得很。黄鹂的嘤鸣,常被视为知音求友的象征,宋代黄庭坚也说:“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清平乐·春归何处》)杜甫写黄鹂隔叶啼鸣,欢快得很。而加一“空”字,则唱者自唱,斯人已殁,庭台寂寞,有谁还去欣赏?有谁知道它嘤鸣求友寻找相知的心意?显然,杜甫选用这些具有符号性意义的意象,有助于读者领悟其中的喻意。
表面看来,三、四两句,杜甫无疑是在描写武侯祠里景色,但由于作者怀着既崇敬又伤感的心情来瞻仰武候祠,怀着将军一去,大树飘零的感慨来思念诸葛亮,于是,这里的景色愈鲜活,反让他益增惆怅。正如王夫之所说:“以哀景写乐,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乐。”杜甫说:“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所谓“诗律细”,我想,不只是对诗歌格律更作严格要求的问题,而且是对用词遣句以及细节描写,更加注意严格的筛选。《蜀相》一诗,属于杜甫晚期的作品。本来,在武侯祠他可以看到种种的景色,而他只选择了柏树、碧草、黄鹂的形象,这既展现了武侯祠的风貌,又透露出自己对诸葛亮和武侯祠的态度,从而收到“一石二鸟”的艺术效果。
有人说,这首诗以《蜀相》为题,但前四句写的是诸葛亮的祠堂,并非写“蜀相”,这不是离题了吗?不错,但从杜甫对祠堂景色的选取中,无一不包含对诸葛亮的追忆景仰之情。可见,他先写寻访武侯祠看到的客观环境,均与诸葛亮有关。换言之,《蜀相》的前面四句,诗人无非是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他心目中“蜀相”的形象。清人范大士在他所辑的《历代诗发》中提出:这诗“前四句伤其人之不可见,后四句叹其功之不能成”,可见他也看到,《蜀相》整首诗,都是环绕着以诸葛亮为中心开展的。
【扼要全面地概括诸葛亮的一生】
杜甫直接描寫诸葛亮的功勋,是“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两句。
“频烦”,是频频劳烦的意思,是“频烦三顾”的倒装。史载,刘备曾三访诸葛亮,诚心向他请教如何对付当时战局的方略。诸葛亮在给刘禅的《前出师表》中也提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当时,诸葛亮根据当时的天下形势,根据他的政治理念,向刘备全盘提出逐鹿中原、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即西取巴蜀,北拒曹操,东连孙吴。杜甫写他进入武侯祠后,让他肃然起敬的是诸葛亮的雄才大略与他纵横捭阖、指挥若定的军事才能。同时,杜甫也感慨刘备和诸葛亮两人关系的融洽。在上句,诗人不是写到黄鹂嘤鸣的意象吗?这和引出他对君臣遇合的向往,不无关系。
“两朝开济老臣心”。开济,是开创和有效地辅佐的意思。“两朝开济”,也是开济两朝的倒装。这句中,杜甫盛赞诸葛亮忠于蜀国的坚贞,他指导刘备开创蜀国的功勋,载入了史册。本来,刘备没有地盘,势单力薄,但诸葛亮劝谏他凭借“天府之国”的富足和地势的险要,建立了“刘蜀”。刘备死后,作为老臣,他又尽心尽力辅佐后主刘禅,延续蜀国的统治。诸葛亮忠心耿耿的品格,让杜甫十分景仰。
在魏、蜀、吴三国的对立中,史称魏得“天时”,吴得“地利”,蜀得“人和”。所谓“人和”,是指上下团结一心之意。蜀之所以得“人和”,很重要的方面,在于诸葛亮对刘备父子的一片忠心。刘禅本来庸碌无能,对于这一点,诸葛亮是知道的,刘备也是清楚的。所以,刘备在永安病笃,临终前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白:‘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刘备的这番话,也许出自对蜀国大局的考虑,也许有试探的性质;而诸葛亮说的则是肺腑之言。
如果不是对刘蜀的忠诚,既然刘备有言在先,诸葛亮确是可以顺水推舟,废了阿斗,省得许多掣肘的。但是,他始终不敢遵照“永安遗命”。封建时代儒家“忠君”的理念,捆住了他的手脚,当然也最终断送了蜀国的江山。对诸葛亮的忠心,离杜甫创作《蜀相》近千年后的清代诗人纳兰性德,还颇有看法。他在《咏史》一诗中写道“劳苦西南事可哀,也知刘禅本庸才;永安遗命分明在,谁禁先生自取来?”出身于贵胄的纳兰性德,受到明代以来异端思想的影响,对忠君的态度分明不同于诸葛亮,也不同于杜甫了。
从政治和伦理思想发展的轨迹看,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在“安史之乱”前后,看不惯许多主政者各怀目的,为争夺个人私利不择手段,因而高度肯定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责任心,肯定他坚贞顽强的斗志。这在唐代,有着深刻的现实的意义。杜甫着意点染武侯祠外森然挺立的柏树,不就是诸葛亮坚持实现统一中原理想的映照么。
第五、六句,一写诸葛亮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一写诸葛亮坚贞忠义的优秀品德,这是杜甫对这位历史人物的一生,作的最扼要、全面的概括。仇兆鳌说:“‘天下计,见匡时雄略;‘老臣心,见报国苦衷。”(《杜诗详注》)仇兆鳌很准确地把握住这两句诗所要表达的内容。
我们知道,在四川,杜甫还写了多首赞扬诸葛亮的诗,常被人传诵的有《八阵图》:
功盖三分国,名高八阵图。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以及《咏怀古迹(其五)》: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这两首诗,也都对诸葛亮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但它们只着眼于评论其相才与军功,反不及《蜀相》那样,能够全面地称颂其才略与品德。所以,就杜甫所写有关评价诸葛亮的作品而言,我认为《蜀相》的艺术水平最高。
【“沉雄顿挫”的创作风格】
杜甫在高度赞赏诸葛亮后,忽然笔锋一转,写下了让人震撼的两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这十四个字振聋发聩,成为杜甫这首咏史诗最感人、最经典的诗句。
史载,刘备死后,诸葛亮为完成统一中原的愿望,率兵六出祁山,多次讨伐魏国,在陕西一带与魏军对垒。而指挥魏军的司马懿,就是筑寨修垒,坚守不出。蜀兵则后劲不继,军心涣散,诸葛亮也操劳过度,不幸在五丈原病逝。可惜这盖世无双的英豪,出师未捷,赍志以殁。这永恒的遗憾,感动了世世代代的历史人物,包括像杜甫在内的壮志未酬之人。
在中外古今的历史上,有多少英雄人物,同样满怀理想,期望鞠躬尽瘁、匡时救世。但他们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或郁郁而终,或功败垂成;他们仰视孔明,感怀身世,只能满襟涕泪,同声一哭。在唐顺宗时期,提倡改革时弊、推行新政的王叔文,因触动了宦官的利益,被宦官集团反击,终于失败。据《旧唐书·王叔文》记,当他得悉回天乏力时,“但吟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末句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因歔欷泣下”。仇兆鳌也说:《蜀相》这诗,“结(句)作痛心酸鼻语,方有精神。宋宗忠简公临殁时诵此二语,千载英雄有同感也。”“宗忠简公”即宋代的爱国名臣宗泽。他力主抗击南下侵扰的金兵,多次领兵取得战斗的胜利,他极力反对“主和派”的投降主张,可是遭到多次阻挠。后来他不幸患上背疽,临终前悲愤地吟诵杜甫的这两句诗。
杜甫《蜀相》的这两句,之所以影响深远,感人肺腑,正由于它概括了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的共同心态,道出许多人想要表达而又未能准确表达的感情,因此,它成为具有典型价值的历史名句。
杜甫从寻访武侯祠入手,概括描写和评价历史人物,这当然是咏史诗。至于怎样写咏史诗,袁枚认为,咏史有三体,“一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一为隐括其事,而以咏叹出之”。(袁枚所说的另一体,实际上是用典的问题,兹不赘。)这样的区分,无论科学与否,但他指出,诗人无论是“借古人往事以抒发怀抱”,还是“隐括其事”即只就一时一事而咏叹之,都必须注入诗人自已的情感。如果咏史之作只是罗列往事,“便成《廿一史弹词》,虽着议论,无隽永之味,又似史赞一派,俱非诗也”。(《随园诗话》卷二)吴乔也说:“古人咏史,但叙事而不出己意,则史也,非诗也。”(《围炉诗话》卷三)他们的见解,很有参考价值。
杜甫的《蜀相》,之所以饮誉诗坛,成为咏史诗的典范,就在于他在追怀诸葛亮的时候,倾注了满腔情感。当然,诸葛亮是经过历史波涛的淘洗后,留下来的千古英雄人物。杜甫虽然被称为“诗圣”,在文坛上有着极高地位,而平生则穷困潦倒。区区一个“左拾遗”,没有留下一丝政绩,与“功盖三分国”“万古云霄一羽毛”的诸葛亮,实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杜甫自信,他是有理想和能力的,本来是可以“致君尧舜上”的。在《望岳》一诗中,他不就表达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概么?说到底,他是认为自己可以和诸葛亮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可惜的是,命运之神始终没有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他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后来混得个小官,又逢安史之乱。他也像诸葛亮对刘蜀那样,对朝廷矢志不移、忠心耿耿,但始终无济于事。后来还因为营救房琯,触怒了肃宗,又遭贬谪。当他在武侯祠凭吊诸葛亮的时候,何尝不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严羽说:“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何谓雄浑?司空图认为:“反虛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二十四诗品》)杜甫在创作的时候,很自然地把内心真实感情的律动,与历史和现实广阔深远的时空融为一体,于是,作品便呈现出“横绝太空”的雄浑之气。若就他个人创作风格而言,我认为,用“沉雄顿挫”四字来概括,似乎更准确一些。其中,《蜀相》便很能展示他诗作的这种创作风格。
所谓“沉雄”,包括诗风既深挚沉郁,又眼界开阔、胸怀古今。综观杜甫的诗作,不难发现,他的视野从不狭窄。在创作中,他往往把个人的苦难和忧伤,放置在广阔的时空背景里。像《登岳阳楼》,把自己“老病有孤舟”的凄凉境遇,与“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宏大背景结合起来;像《旅夜书怀》,把自己的“危樯独夜舟”和“天地一沙鸥”的孤苦伶仃,放在“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视野中;像《登高》,又以“风急天高猿啸哀”等景象空旷辽远的四句,衬托他自己“百年多病独登台”的苦况。《蜀相》中区区几句,便高度浓缩了诸葛亮的一生和他的高贵品德,但杜甫的目光,又不仅只注视在诸葛亮一个人的身上,而是放眼古今,看到了许多英雄人物的命运。显然,对现实生活的切身感受和对历史深邃的思考,让他的目光显得阔大而沉郁。
所谓“顿挫”,是指作品中所展现的意象和语言的节奏不断起伏变化,跌宕不定。这实际上是作者感情激动和内心矛盾的外化。就《蜀相》而言,杜甫在第一、二句,写自己怀着恳切崇敬的心情寻访武侯祠。第三、四句写进入祠堂,看到清幽的景色,想到人去祠空,落寞之情,油然而生。这一来,热切切的期盼,跌落冷清清的怀抱中,感情出现了转折。第五、六句,诗人从思绪萦回中,想到了诸葛亮卓越的功勋和忠贞的品格,诗的情韵出了新的变化。但是,杜甫又从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立刻想到他无力回天的结局,更联想到历史上多少英雄人物的遭遇,于是,对诸葛亮无限景仰之情,呈现为大幅度转折。整首诗的韵味忽抑忽扬,忽起忽落,作者情感的曲折变化,在诗歌语调和节奏上,呈现出顿挫跌宕的韵味。
“沉雄顿挫”,是杜甫对待人生的态度以及思想的矛盾综合在诗歌作品中,从而显示出的独特风格,它在盛唐的诗坛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本刊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