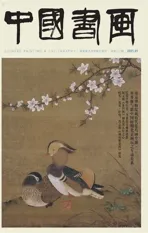古代书画论今注今译中的讹误举隅
——以潘运告编著《元代书画论》中《衍极并注》的注译为例
2021-04-18吴建权
◇ 吴建权
从汉至清,各种书论、画论可谓卷帙浩繁,而古文与今文的差异也给那些不熟悉古文者在阅读古代书画论时带来了障碍。幸赖当代一些学者为古代书画论作了今注今译,对我们阅读和研究古代书画论都大有裨益。其中,潘运告编著的《中国书画论丛书(十四册)》是今天较为全面的古代书画论译注著作。该丛书收录了古代书画论的大量名篇,并一一作了较为详尽的今注今译,在古代书画论译注著作中颇具代表性。但该书也存在着诸多讹误之处,且这些讹误在古代书画论译注著作中也较为典型。本文以《元代书画论》中的《衍极并注》注译为切入点,对其中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讹误进行举例说明,以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古代书画论译注中所存在的典型问题,以在今后的译注中加以避免。
一、因未详查文献来源而导致的张冠李戴
古人著书也常常引用前人文献,这与今人著书并无明显差别,不同的是,今人著书在引用时一般会注明文献来源,而古人并无此严格的规定。因此,在我们阅读古书时,就难以分辨书中哪些是“旧说”、哪些是作者“自说”,在未分辨清楚的情况下,我们对古书的理解和阐释就容易出现一定程度的偏颇。且古书由于时间久远而辗转流传,其原本面貌一般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改变,今人在为古书作今注今译时若不详加辨别,便会导致以讹传讹。而对于书中的那些属于“旧说”的部分,我们若仔细考察了其原始文献,或许这种以讹传讹便可以避免,这于《衍极并注》中的按赵明诚,字德甫(一字德父),将刘有定所引“赵德夫”语与《金石录》对比可知,刘有定所谓的“赵德夫曰”后的句子明显就是引自赵明诚《金石录》,此处之“赵德夫”必指赵明诚,而非赵不弃。盖德甫、德父、德夫均可相通,也有可能是刘有定或刊刻者将德甫(德父)误为德夫。潘氏将赵德夫释为赵不弃,盖未详查文献来源之故。

潘运告编著《中国书画论丛书·元代书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出版
再如,《衍极卷二·书要篇》的“隶之八分变而飞白、行草”条下,刘有定有注云:
曰反左书,梁东宫学士孔敬通所作。当时坐上酬答无有识者,庾元规见而识之,遂呼为众中清闲法。(潘运告编著《元代书画论》,第53页)
潘运告在对此条作注释时说:“庾元规:即庾亮,字元规。”(潘运告编著《元代书画论》,第55页)这也是由于未查文献来源而导致的张冠李戴。通过查阅南朝梁的书学文献可知,该句并非出自庾亮之口,而是出自庾元威。庾元威《论书》:
反左书者,大同中,东宫学士孔敬通所创,余见而达之,于是座上酬答,诸君无有识者,遂呼为“众中清闲法”。
将两则文献对比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刘有定提到的所谓“庾元规”乃是“庾元威”,应是刘有定或后世刊刻之误。而潘运告在注释时由于未查文献来源,导致以讹传讹,应该予以纠正。引用文献就可见一斑。
《衍极并注》不仅以其理论内涵而著名,而且还“以注的博深而享誉书法理论史”。(姜寿田主编《中国书法批评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刘有定的注释,并非仅限于对郑枃之语的简单解释,而是有许多自己的阐发。然而,通过仔细阅读《衍极并注》,不难发现,刘有定的注释虽然文字多、篇幅长,但出于刘有定自己之口的话语其实在注中并不占主要,而是包含了大量前人之语。但在刘注中也并非所有引用前人之语都注明了来源,如余绍宋所说“又注中于出处或出或不出,遂致旧说与自说猝难辨别”(余绍宋著《书画书录解题》,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这样就给我们认识《衍极并注》带来了一定困扰。并且,也正因为这种未注明出处的情况,后人对文本作注释和校勘时,若遇刊刻有误之处,便不容易得到纠正。在《衍极卷二·书要篇》谈到《诅楚文》时,刘有定注曰:
赵德夫曰:“秦《诅楚文》,余家所藏凡有三本,其一祀巫咸,旧在凤翔府廨,今归御府,此本是也;其一祀大沈久湫,藏于南京蔡氏;其一祀亚驼,藏于洛阳刘氏。”(潘运告编著《元代书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潘运告在对此条作注释时说:“赵德夫:宋太宗后裔,名不弃,字德夫,南宋人,敷文阁直学士。”(潘运告编著《元代书画论》,第62页)按刘有定在注中所引的所谓“赵德夫”语,实际上并非出自赵不弃之口,翻阅古籍可知,该句引文实乃来源于赵明诚《金石录》:
右秦《诅楚文》,余所藏凡有三本,其一祀巫咸,旧在凤翔府廨,今归御府,此本是也;其一祀大沈久湫,藏于南京蔡氏;其一祀亚驼,藏于洛阳刘氏。
二、因不详作者世系而导致的释义模糊
古代学者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这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因此,他们在著述时也难免带有一定的家学影子,甚至直接引述其先祖的语句和观点,这在《衍极并注》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若要对这些著述加以详细的了解,对其世系的考察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在《衍极并注》中,刘有定多次提到夹漈山人、郑回溪、郑肯亭等人,但在潘运告的注释中,仅仅指出了夹漈山人是郑樵,而对郑回溪则没有相关注释,在对郑肯亭的注释下更是直接写道“不详其人”(潘运告编著《元代书画论》,第61页)。查郑惠元修《南湖郑氏大宗谱》便可知郑回溪、郑肯亭乃何许人:
侨,宋禧次子,字惠叔,号回溪。
寅,原名守寅,字子敬,号肯亭。
由《南湖郑氏大宗谱》可知郑回溪本名为郑侨,郑肯亭本名为郑寅。郑侨和郑寅与郑枃的关系如何?郑岳《莆阳文献列传》载:
枃字子经,侨之玄孙,寅之曾孙,与陈旅为文字友。
通过上述文献可知,郑回溪即郑侨,乃郑枃之高祖,而郑肯亭即郑寅,原名郑守寅,字子敬,号肯亭,是郑枃之曾祖。可见,若对郑枃的世系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便不至于在注释时“不详其人”。并且,我们不难发现《衍极并注》中对郑樵、郑侨、郑寅的推崇之至,因此也只有弄清楚了郑枃的世系,才能清楚地认识到“家学”在《衍极并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才能更好地解释《衍极并注》。
三、因未仔细校勘文本而导致的释义偏差
古代书籍经过长时间的辗转流传,难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讹变,且存世的不同版本之间也往往会存在诸多差别。今人在对古书作注译时,在未能对文本进行详细的校勘时,便会遇到有些语句无法顺译的情况,甚至在注译时会出现许多讹误。
在《衍极卷二·书要篇》中,刘有定在“《乐毅论》,旧本希见于世,宋初王侍书别写混之”条下作注云:
宋太宗留心翰墨,摹求善书,许自言于宫车。(潘运告编著《元代书画论》,第68页)
此句若作直译,“摹”应是“摹写”之意,前半句好像是在说宋太宗自己摹写善本法书,但其中的“求”字似乎又无法顺译。并且,后半句的“许自言于宫车”,又不知是许何人言于“宫车”。“宫车”本指帝王后妃所乘车辆,虽后来也可用来指代帝王,但此句仍然难以合理释读。按此句或许本来不应如此,查阅前代文献可知,此句应是根据朱长文《续书断》而来,《续书断》:
(太宗)始即位之后,募求善书者,许自言于公车。
可以发现,在朱长文的原句中,释读并无困难,应是说宋太宗即位之后,招募了一大批善书者,并且允许他们直接上书进言,“公车”便是掌管征诏的官署之称。但因刘有定注中将“募”变成了“摹”,将“公”误为了“宫”,便使得该句难以释读。而在潘运告的《元代书画论》中,则在未经查阅原始文献及校勘文本的情况下,直接根据有误的文本进行直译,将“宫车”直译为“帝王后妃所乘的车辆。此借指帝王”,将“许自言”释为“宋太宗时人”(潘运告编著《元代书画论》,第69页),实在有些荒谬。可见,查阅原始文献和仔细校勘文本在注译时是至关重要的。
四、句读错误
古书无标点而今书有之,我们在为古代书画论作今注今译时不可能只作注译而不加标点。因此,准确的句读在注译时也十分必要。尤其作者若明确注明了引述前人文献,在加引号时就有必要仔细查阅前人文献,以准确区分文中的“旧说”与“新说”。
在潘运告编著的《元代书画论》收录的《衍极卷五·天五篇》中,刘有定有注云:
欧阳永叔曰:“石鼓在岐阳,初不见称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称之。”而韦应物以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诗尔。韩退之直以为宣王之鼓。在今凤翔孔子庙中,鼓有十,先时散弃于野,郑馀庆置于庙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传师求于民间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磨灭不可识者过半。古之文者莫先于此,然传记不载,不知韦、韩二君何据而知为文、宣之鼓?然至于字画,亦非史籀不能作也。(潘运告编著《元代书画论》,第217页)

诅楚文(拓本)
从潘运告在“欧阳永叔曰”后加的引号可知,潘氏应认为此段只有“石鼓在岐阳,初不见称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称之”是刘有定引欧阳修之语,其余则是刘有定自撰。但是,查阅欧阳修《集古录》可知,欧阳修的原话并不仅仅只有这一句,《集古录》:
右《石鼓文》。岐阳石鼓初不见称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称之,而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一有“至”字)宣王刻诗(一有“尔”字),韩退之直以为宣王之鼓。在今凤翔孔子庙中,鼓有十,先时散弃于野,郑余庆置于庙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传师求于民间得之,(一有“十鼓”)乃足。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一有“磨灭”)不可识者过半。余所集录,文之古者,莫先于此……前世传记所载古远奇怪之事,类多虚诞而难信,况传记不载,不知韦、韩二君何据而知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书籍粗备,岂当时犹有所见,而今不见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为信尔。至于字画,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从《集古录》与《衍极并注》的相似文字来看,刘有定引欧阳修的话应从“石鼓在岐阳”始,至“亦非史籀不能作也”止,“欧阳永叔曰”后的后引号也应加于“亦非史籀不能作也”之后,而非如潘氏加在“始唐人始称之”之后。
余论
由于古文与今文之间现实存在的距离,为古代书画论作今注今译应是当代学者应有的责任和担当。而在为古代书画论作注译时,也应在古书的文献来源、作者的生平世系、文本的流传与校勘、句读等方面加以深入的考察。潘运告编著《中国书画论丛书》作为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古代书画论译注著作,仅从其《衍极并注》一篇的译注就可发现其中所呈现的各种典型讹误,且这些讹误也的确广泛存在于其他各种古代书画论译注之中,古代书画论译注的现状可见一斑。这些问题也是影响理解和研究古代书画论时的典型问题,若这些问题长期存在,那必将导致以讹传讹。因此,虽然我们今天对古代书画已经陆续展开了各方面的研究,但古代书画论的整理和注译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