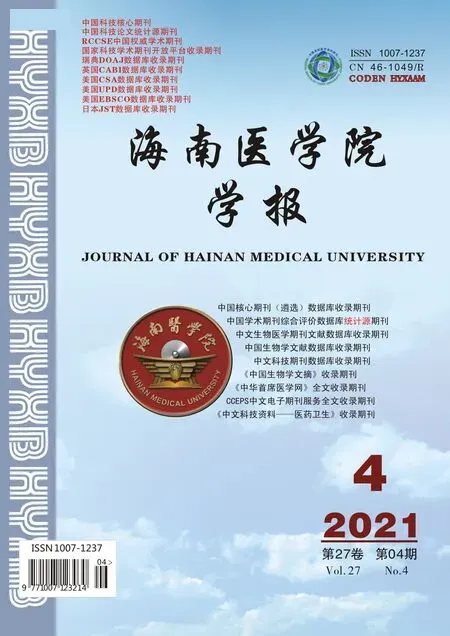“药食同治”思想在顽固性功能性便秘治疗中的应用
2021-04-17王慧静贠张君彭红叶龙思丹王一冲姚树坤
王慧静,贠张君,彭红叶,龙思丹,王一冲,姚树坤,刘 瑜
(1.北京中医药大学,2.中日友好医院消化内科,3.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脾胃病科,北京 100029)
顽固性功能性便秘是功能性便秘(functional constipation ,FC)的一种临床类型,简称顽固性FC。其病因复杂、病程较长,现代医学多采用促胃肠动力药、泻剂、灌肠、外科手术等方法治疗[1],虽能缓解症状但极易复发,且易产生赖药性,甚至导致肠道神经末梢损害,从而加重病情,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2]。近年来,随着对FC病因病机研究的不断深入, 中医药和饮食干预在减少不良反应、降低复发率、提高疗效等方面显示出巨大优势[3,4]。
姚树坤教授从医40余年,临床经验甚丰,在诊疗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药食同治”思想[5-7]。所谓“药食同治”,是指将辨证论治与饮食干预有机结合,使二者相得益彰。本文旨在为中西医诊治顽固性FC及其相关疾病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以期对临床有所启发。
1 古今病因,霄壤之别
中医学并无FC一说,但早在《内经》中就提到了“大便难”、“不便”,《伤寒论》中有“阴结”、“阳结”、“脾约”、“燥屎”等记载。根据FC临床表现,从中医学角度可将其归于“大便难”、“后不利”、“脾约”、“便秘”等范畴。对FC病因病机的认识,《素问·举痛论篇》中提到“热气流于小肠,肠中痛,瘅热焦渴,则坚干不得出,故痛而闭不通矣”,认为便秘为热结于肠所致。《景岳全书·秘结》中提到“秘结者,凡属老人、虚人、阴脏人及产后、病后、多汗后,或小水过多,或亡血失血、大吐大泻之后,多有病为燥结者。盖此非气血之亏,即津液之耗”,认为便秘为气血津液虚损所致。《东垣十书》云:“若饥饱失节,劳役过度,损伤胃气,及食辛热味厚之物,而助火邪,伏于血中,耗散真阴,津液亏少,故大便结燥。”《证治汇补》又言:“饮食失节,或恣饮酒浆,多食辛辣,饮食之火,起于脾胃……以致火盛水亏,传送失常,渐成燥结之症。”指出饮食不节,过食肥甘厚味或辛辣刺激炙煿之品均可导致便秘。
正所谓“继承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姚树坤教授认为要用与时俱进的眼光看待疾病的变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以五谷杂粮为主的低脂低蛋白饮食模式,转变为当下以肉、蛋、奶类为主的高脂高蛋白饮食模式[8,9]。此外,人们的体质和疾病谱也随饮食结构的变化而改变,从中医角度来看,人们的体质由之前以多虚、多寒为主转变为现在以多湿、多热为主,由原来的以虚证、寒证为主转变为当下的以实证、热证、虚实夹杂证为主;从西医角度来看,居民营养过剩状况明显,肥胖问题严重,慢性代谢性疾病与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明显增加[10-12]。顽固性FC原发致病因子在于饮食失节,因此应特别强调调整患者饮食结构,以达到治疗目的。
2 整体观念,辨证论治
在诊断时,首先辨病。姚教授认为诊断顽固性FC时,应在罗马Ⅳ标准的基础上格外强调其特征性临床表现,即持续性便秘、通便药依赖和(或)通便药治疗无效。此外,要从系统生物学角度出发,整体把握,很多消化系统疾病不仅与消化系统相关,还受内分泌等其他系统的影响,例如甲状腺功能低下也可诱发便秘。故诊断时,应重视甲状腺功能相关检查以排除其它系统疾病。其次辩证。顽固性FC大致可分为虚秘、实秘和其他兼夹证型3大类[13]。结合当下人们饮食结构、生活方式及体质变化,临床上以实秘和兼夹证型较为多见。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言“膏粱之变,足生大丁”,过食肥甘厚味, 易于生湿助热,热蒸湿动,日久则炼液为痰[14,15],进而阻滞气机,气滞则血瘀。临床最常见的证型为湿热夹瘀证,治宜清热化湿、理气祛瘀。其中,热重于湿者,多大便数日一行,干结难解;湿重于热者,多排出不畅,便后不爽。
3 对症治标,对因治本
3.1 清热降逆,祛湿化瘀
对症治疗,以“清热降逆,祛湿化瘀”为主要治法,多根据患者临床症状灵活选用清热、祛湿、化瘀类药物。姚教授自拟经验方:黄芩10~15 g,龙胆草6~12 g,金钱草60~90 g,旋覆花15~20 g,代赭石30~40 g,三棱12~15 g,莪术12~15 g,云苓15~30 g,薏苡仁30~60 g,陈皮10~15 g,醋香附10~15 g,枳实10~15 g,生甘草6 g。其中黄芩、龙胆草、金钱草清热燥湿合清热利湿,一扫三焦湿热。“诸花皆升,旋覆独降”,旋覆花味苦、辛、咸,归肺、脾胃、大肠经,善下气。“赭石之重,以镇逆气”,代赭石味苦性寒,归肝、心经,重坠降逆,善于震摄肝胃之逆气,可助旋覆花降逆下气。腑气以通为用,以降为顺,二者相伍,共奏降逆化痰、宣通肠腑气机之效[16]。云苓、薏苡仁健脾祛湿,中正平和,顾护脾胃正气。陈皮、醋香附、枳实疏肝理气和胃,畅达三焦气机。生甘草既清热解毒又调和诸药。诸药配伍,一来祛湿化瘀,二来宣畅肠腑气机、清热降逆,肠腑气机调畅,则糟粕得以下行、大便得以顺通。
姚教授强调,对于湿热型顽固性FC,治疗时切忌一味求快而攻伐壅补。正如《叶氏医案存真》所言“热从湿中而起,湿不去则热不除也”,湿邪本就黏腻厚浊,滞留体内胶着不化,热处湿中,更是如油裹面,病势缠绵,故应逐步加大药物用量,有章有法,循序渐进,做到缓清而不伤正。此外,临床处方时还应灵活权变,随证加减。湿热兼见关节不利时,加忍冬藤;胆草清热燥湿之力强于黄芩,湿热痰瘀减轻时则去胆草;患者有阴虚症状时,宜选用北沙参、知母等滋阴而不助热之药;睡眠不佳者,加莲子芯。必要时加用菌群调节药、福松或莫沙必利,获得良效。
3.2 正本清源,药食同治
《千金要方》有言:“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强调了食治的重要地位。《素问·痹论》言“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指出饮食失节、厚味过度会对肠胃造成伤害;薛生白《湿热病篇》又言“湿热之邪,由表伤者,十之一二,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指出湿热之邪与饮食的相关性。姚教授认为,一切生命都处于积极运动状态,有机体作为一个系统能够保持动态稳定是系统向环境充分开放,获得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结果[17],而饮食因素作为物质,携带能量与信息,首先影响消化系统,与消化道疾病密切相关。
所谓“药食同治”,即将饮食干预与药物治疗并重,使二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18-20]。而姚教授强调的饮食干预主要是指高危饮食限制。正如《内经》所言“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临床中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剔除高危饮食以消除病因。姚教授临床中对顽固性FC患者高危饮食干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按照食物种类划分,禁食或少食肉、蛋、奶类等肥甘之品,《黄帝内经》曰“五谷为养,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五果为助”,即健康养生的饮食模式应以五谷杂粮为主,肉食果蔬为辅,而不应荤素失调[21];按照性味划分,禁食或少食辛辣刺激性,如辣椒、胡椒等厚味之食,正如《养性延命录》所言“百病横夭,多由饮食,饮食之患过于声色”,清淡平和、顺应自然,食用应季果蔬,才能杜绝百病横夭;按照加工方式划分,禁食或少食烧烤、油炸、干炒等高温加工类炙煿之物。相关研究表明,食物的高温加工会诱导晚期糖基化终产物(AGEs)的形成,长期高AGE饮食和(或)高热量饮食会导致胰岛素抵抗的发生,诱导机体过氧化损伤和炎症反应[22],这也是诸如顽固性FC此类慢性病高发的主要原因。此外,还应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规律作息,调畅情志,适度运动,戒烟酒,避免浓茶、咖啡等。
4 验案举隅
患者李某,女,62岁。便秘20余年,反复发作。大便干硬,块状便,每周自发排便次数(有便意且成功排出,未使用泻药或手法辅助排便)1~2次,排便费力,排便不尽感,时伴腹胀、嗳气。询之平素喜食辛辣刺激之品,嗜食肉蛋奶类。既往甲状腺结节、2型糖尿病病史。舌质暗红,舌边瘀斑,舌苔黄厚腻,脉弦滑。结肠镜检查未见明显异常。辨病为顽固性功能性便秘、甲状腺结节、2型糖尿病,辩证为湿热夹瘀证。初诊处方:黄芩15 g、金钱草90 g、桃仁30 g、刘寄奴15 g、石见穿15 g、旋覆花15 g、代赭石30 g、柿蒂15 g、云苓30 g、枳实12 g、生甘草6 g。并嘱患者严格控制饮食,切忌肥甘、厚味、炙煿之品。服药14剂后二诊,大便干硬程度较前缓解,1次/d,排便不费力,无排便不尽感,腹胀嗳气较前缓解,舌暗红,舌边浅瘀点,苔黄较厚,脉沉弦,上方金钱草改120 g,加黄柏12 g、苦参12 g,继续服用14剂,饮食禁忌同前。按语:该患者中老年女性,平素过食肥甘厚味,以致体内湿热蕴结,困阻肠腑气机,大肠传导失司,故出现大便难、排便费力等;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故舌暗红、舌边瘀斑。首先辨证用药,脉症合参,该患者为湿热夹瘀证,治以清热降逆、祛湿化瘀。处方中以黄芩、金钱草清利湿热;桃仁、刘寄奴、石见穿活血化瘀;旋覆花、代赭石下气降逆、宣畅肠腑气机;云苓健脾祛湿;柿蒂降气,枳实破气消积、化痰散痞;生甘草调和诸药。二诊时患者各项症状均较前有所缓解,根据舌脉提示,体内湿热之邪仍在,故加大金钱草用量以增清热利湿之效,加用黄柏、苦参以增清热燥湿之功。全方配伍无一味虎狼之药,剂量增减循序渐进,真正做到缓清而不伤正。其次注重饮食干预,嘱患者祛除肥甘、厚味、炙煿之品等高危饮食以对因治疗,使饮食干预与药物治疗有机配合,则药物得饮食干预相助,效力更佳,逐步将体内湿热之邪清出体外。
作者贡献度声明:
王慧静负责论文选题、论文书写;贠张君、彭红叶、王一冲负责病案整理、分析;龙思丹、刘瑜负责后期文章语法修订、中英文核对等审校工作;姚树坤负责写作指导、整体把握。
本文内容不涉及相关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