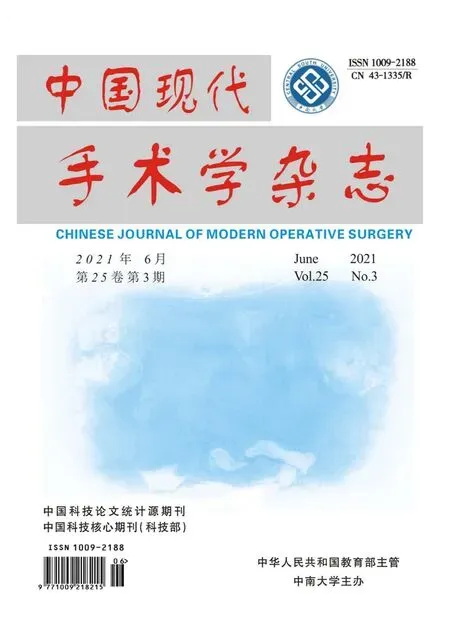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切口感染的影响因素及预防
2021-04-17孔祥可姜丽程晓娇李斯博许军
孔祥可,姜丽,程晓娇,李斯博,许军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腔镜外科,黑龙江哈尔滨 150000)
[提要] 单孔腹腔镜技术的兴起推动微创理念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经脐置入带有多个操作孔道的单孔装置,通过操作孔道引入手术器械完成手术,手术标本经脐部切口取出。脐部存在环境潮湿、清洁困难等特点,有利于细菌生长繁殖,可能会增加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发生切口感染的风险。为减少切口感染的发生,应对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切口感染的影响因素及预防加以重视。
手术部位感染(surgical site infection,SSI)是外科术后常见并发症,几项前瞻性研究显示腹部手术SSI的发生率较高,约为15%~25%[1-3]。SSI与患者术后死亡率、无计划再次入院以及术后护理费用和住院时间的增加密切相关[4-7]。目前关于单孔腹腔镜手术(single-incision laparoscopic surgery, SILS)切口感染的相关研究虽少,但却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为减少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transumbilical single-incision laparoscopic surgery,TU-SILS)切口感染的发生,本文就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术后切口感染的影响因素及预防进行简要阐述,以期为临床医生提供参考。
1 经自然腔道内镜手术
经自然腔道内镜手术(natural orifice transluminal endoscopic surgery,NOTES)是使用内镜通过人体自然腔道(食管、胃、阴道、直肠等)进入手术操作部位而完成诊断或治疗的一项新兴技术[8-9]。与传统开腹手术和腹腔镜手术相比,NOTES具有体表“无瘢痕”,术后疼痛轻,住院时间短以及避免体表切口发生相关并发症等优势[10]。但是由于设备、手术技术的限制,术中空间定位存在困难,以及在入路切口的闭合、预防感染等方面亟待优化,NOTES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并未在临床广泛应用[10]。
脐部作为出生时遗留的“自然孔道”,既能够达到隐藏腹部瘢痕的效果,又避免了经胃、阴道或直肠所产生的感染问题,还可以使用常规腹腔器械,因此,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是现阶段能保持经自然腔道内镜手术微创、美观等初衷并且较为安全、可行的一种手术方式。
2 经脐单孔纵切口入路手术
单孔腹腔镜手术根据手术部位、手术类型、手术方式的不同可在腹壁选取合适的切口位置进行操作。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选取脐部天然“瘢痕”处,由头侧至尾侧沿腹正中线纵向切开腹壁后置入单孔腹腔镜操作平台进行手术操作。国内许军教授团队自2011年开始由易至难相继完成了经脐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11]、经脐单孔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12]、经脐单孔腹腔镜胃癌D2根治术[13]、经脐单孔腹腔镜十二指肠乳头肿瘤局部切除术[14]、经脐单孔腹腔镜脾切除联合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15-17]及经脐单孔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18]等术式,证明了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在上述术式中的安全性及可行性。
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中,经脐纵切口相较于脐下缘切口能更充分的利用脐部这一天然“瘢痕”,其优势在于脐部位置隐蔽,切口愈合后可被皱褶的皮肤掩盖。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在优化切口美容效果、减少手术创伤、减轻术后疼痛等方面的优势相比于传统腹腔镜手术更加突出[19-22],但由于脐部特有的生理结构,其切口安全性亟待讨论。
3 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切口感染的影响因素
导致手术部位感染的危险因素有很多,包括手术方式、手术时间、伤口污染类别、切口长度、患者年龄、BMI、是否合并糖尿病、急诊手术、术中细菌负荷等因素[23-25]。然而,目前尚未见有关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后脐部切口感染发生率的前瞻性研究。综合相关文献,脐部切口感染的发生可能与如下因素相关。
3.1 脐部微生态
皮肤微生态是皮肤微生物、宿主皮肤与环境三者之间相互制约, 相互协调, 保持动态平衡所共同构成的统一体,并与皮肤自身的物理屏障及免疫功能共同构成人体的第一道防御体系,其中微生物是维持皮肤微生态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26]。微生物广泛存在于人的体表及体内,其数量是人体细胞的10倍,微生物基因的数量是人类的100倍[27]。微生物及其遗传物质在皮肤炎症、免疫反应及伤口愈合等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28-29]。Lai等[29]研究发现葡萄球菌产物脂磷壁酸(lipoteichoic acid,LTA)可通过Toll样受体-3(Toll-like receptor 3,TLR3)选择性作用于角质细胞来抑制损伤后的炎症反应。Byrd等[30]研究显示皮肤微生态结构的改变与慢性伤口愈合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Grice等[31]根据皮肤的生理特点及所处环境将皮肤分为油性区、湿润区及干性区,脐部位于湿润区,以葡萄球菌属(staphylococcus)和棒状杆菌属(corynebacterium)为主。Hamzaoglu等[32]对造成腹腔镜术后切口感染的病原体进行研究,发现切口感染处分离的最常见细菌为黏质沙雷菌(serratia marcescens)(50%),其次是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25%),与脐部消毒前分离的细菌不一致,证明脐部菌群不是造成腹腔镜术后切口感染的原因。TU-SILS术后对脐部进行了消毒和重建,打破了脐部原有的生态环境,其微生物种类可能会改变。然而,TU-SILS术后脐部微生物种类构成如何改变,变化后的微生态环境与切口感染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等目前尚未证实,仍需进一步探究。
3.2 切口长度
传统腹腔镜手术通常需要三到五个戳卡孔和一个额外用来取标本的切口,每个切口都存在感染的风险。Weiss等[33]研究发现,在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中较长的皮肤切口术后发生切口感染的概率较高((3.77±1.62)cm VS (2.96±1.06)cm,P=0.012)。因此应合理选取切口长度,降低切口处的张力,以保证组织良好的血运,减少切口感染的发生。
3.3 手术时间
Weiss等[33]研究表明,单孔腹腔镜术后切口并发症的发生与手术时间无关((75.22±50.47)min VS (81.46±54.86)min,P=0.425),但不难看出发生切口并发症组的手术时间较长。手术时间的延长可造成术中失血量的增加、切口暴露时间延长及局部组织抗生素浓度下降等问题,这些因素均可增加切口感染的风险。开展单孔腹腔镜的前期,器械的“筷子效应”及术者经验的缺乏都会延长手术时间,增加切口感染的风险。Hoyuela等[22]研究指出在克服学习曲线、熟练操作之后,单孔腹腔镜手术时间与传统腹腔镜相比并无明显差异。经脐单孔腹腔镜技术应用的前期及在复杂手术中所需的手术时间势必会延长,但相信程序化、规范化之后的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在手术时间上对切口感染的威胁将会降低。
4 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切口感染的预防
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绝大多数为择期手术,可通过合理规范地制定术前、术中及术后的预防策略来减少切口感染的发生。排除术前应纠正的营养不良、糖尿病等危险因素外,以下措施也可预防脐部切口感染的发生。
4.1 温暖、湿化的CO2使用
低温会导致皮下血管收缩、血流量减少,而伤口部位皮下氧张力降低可增加手术部位感染的风险[34]。同时低温会降低白细胞迁移、产生抗体和吞噬的能力,对宿主的免疫反应能力产生不利影响[35],进而导致发生手术部位感染的风险升高。Mason等[34]的一项回顾性研究共纳入246名患者,其中实验组采用温暖、 湿化的CO2建立气腹, 对照组采用常温干燥的CO2建立气腹,结果显示实验组术后体温过低的发生率显著降低 (OR=0.10, 95% CI 0.04~0.23),同时发现低温患者发生手术部位感染的风险增加(OR=4.0, 95%CI 1.25~12.9),在上述研究中使用温暖、湿化的CO2气体显著降低了66%的手术部位感染发生率(P=0.04)。
因此,在有条件的医疗机构中使用温暖的、湿化的CO2建立气腹可维持患者术中体温,保持切口部位的氧张力,降低切口感染的风险,促进切口的愈合。
4.2 目标导向液体治疗
目标导向液体治疗(goal-directed fluid therapy,GDFT)以改善组织灌注、优化组织氧供氧耗为目标,是一种根据围手术期心输出量、血压等类似参数来指导静脉输液和肌力治疗,进而达到调整血流动力学的液体疗法[36-37]。充足的血容量是组织灌注的重要保障,对维持组织的氧合也发挥重要作用。在低血容量和高血容量等非平衡状态下组织氧合受损可能会增加手术部位感染的风险[38]。
2016年WHO专家组[39]对14个临床研究进行荟萃分析后认为:与标准的术中液体处理相比,术中行GDFT与SSI发生率的降低显著相关(OR=0.56,95% CI 0.35~0.88)。Pearse等[36]研究显示在普通外科中术后行GDFT的患者切口感染的发生率较低(44% VS 68%,P=0.003, RR=0.63,95% CI 0.46~0.87)。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时间较长,术中和术后维持充足的血容量,保持合理的组织灌注对减少术后切口感染的发生尤为重要,有待进一步的相关研究来规范目标导向液体治疗,建立可靠的容量评估方法,更好的指导围手术期液体管理,减少切口感染的发生。
4.3 预防性切口负压治疗
预防性切口负压治疗(negative pressure wound therapy, NPWT) 可将创面边缘聚拢进行机械支持, 还能清除创面微环境中的多余液体, 减少组织水肿和细菌等微生物负荷, 增加组织灌注和刺激血管生成,进而促进创面愈合、减少切口感染[40-41]。Li等[42]的一项Meta分析评估了NPWT对SSI的影响,证实NPWT减少了SSI的发生(RR 0.58,95% CI 0.49-0.69),大大降低了高风险手术患者发生SSI的风险(32 RCTs; RR 0.60; 95%CI 0.50-0.73;I2=23%),与手术类型无关。
在TU-SILS中预防性应用NPWT可对重建的脐部切口起到机械支持作用,营造良好的组织生长微环境,减少切口感染的发生。此外,仍需要进一步研究评估最优的NPWT策略及手术创面管理的最佳策略,如负压的压力值、持续时间和换药频率等。
4.4 抗菌涂层缝线
缝线可以作为细菌进入手术切口的载体,切口越长,细菌随缝线进入切口的概率越高,其发生感染的风险也会增高。具有抗菌性能的缝线可减少缝线材料上细菌的定植,降低切口感染的风险。我国专家组[43]对18项临床研究进行荟萃分析后证明,抗菌涂层缝线能够显著降低SSI的发生率(RCT:OR=0.72, 95% CI:0.59~0.88;OBS:OR=0.58, 95% CI:0.40~0.83),并建议在任何术式中均可使用抗菌涂层缝线以降低SSI的发生率。
伤口敷料可对切口提供物理支持、保护和吸收渗出液。Dumville等[44]研究发现,没有任何敷料能完全降低手术部位感染的风险,也没有任何敷料在降低手术部位感染上表现更佳。《中国手术部位感染预防指南》[43]不建议以预防SSI为目的使用特殊敷料,也不推荐因存在切口引流或以预防SSI为目的而延长围手术期预防性抗生素的使用。
5 结 语
综上所述,脐部的微生态环境、脐部切口的长度及手术时间都可能是造成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脐部切口感染的危险因素。为了避免切口感染带来的不利影响,临床上可采取多种措施如使用温暖、湿化的CO2,术中、术后进行目标导向液体治疗,预防性切口负压治疗,使用抗菌涂层缝线等来预防、减少经脐单孔腹腔镜脐部切口感染的发生。作为人体的天然“瘢痕”,脐部可作为单孔腹腔镜手术的必备入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