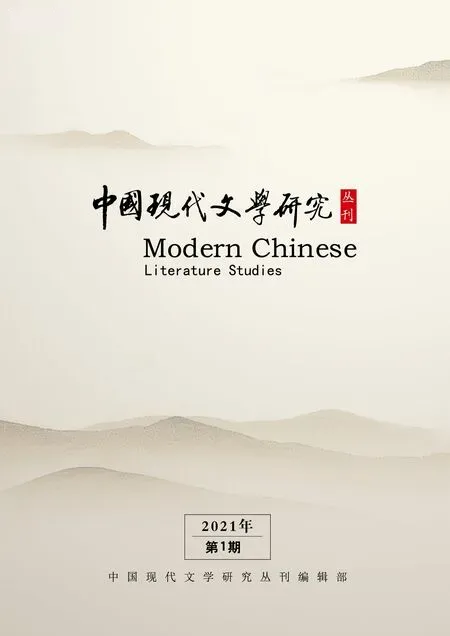陈铨《死灰》表现的中德青年之恋及其文化意涵①
2021-04-17叶隽
叶 隽
内容提要:本文以陈铨《死灰》为文本,研究现代文学文本表现出的德国语境,以留德学生萧华亭与德国女郎冷荇的无望之爱为中心,考察其时的德国语境、留德学生状况和中德青年恋情,并尝试揭示其文化意涵。从本质上来说,萧华亭经历的是一种移交的过程,即留德中国学生与德国本土女郎的相遇与交融,然则“由象见道”,借助侨易思维来看,可见出中德文化相遇,乃至东西文明碰撞的大图景。
一 冷荇的我见犹怜
歌德之《少年维特之烦恼》能在德国和其他地区风靡一时,是因维特无望之爱的深及心灵追索的动人,所谓“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但又岂不知“人性本能至圣处,惨痛飞迸鬼神惊”?而陈铨的《死灰》②,讲述一个让人感念颇深的故事萧华亭与冷荇之恋,写中国留德学生萧华亭,一个表面洒脱不羁而其实懵懂困惑的青年知识人,与一个虽是青春美貌却出身下层,只知当下难见未来的德国女郎冷荇相恋的故事。
“一想到冷荇,华亭几乎一刻都不能久待”③,我们大概可以想见萧华亭和冷荇关系的密切和深情。不过虽然他们也试图谈婚论嫁,但似乎更类乎一种“情性之间”的交易关系。一战之后德国因战败而导致经济危机,民众的基本生存都有极大困难,这自然就导致了女性择偶态度的变化。冷荇是不幸的,因母亲改嫁给一个犹太商人而不得家庭之温暖。她十七岁就独立生活,依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挣钱,小说写她“自从我独立生活以后,我精神倒很快活。一个星期,虽然每天八小时的工,却可以得二十五个马克。除开房钱伙食,还有钱买新衣服,看电影,进跳舞场。那个时候,我同安丽都无拘无束地过日子”④。她对于追求自己的同厂的青年庶务也高调拒绝,可一旦有了失业的危机,冷荇就不得不降低调门,“老实说,那个时候,我要是像现在这样失业,我一定不会那样骄傲,也许嫁了他……也许不会受这两年多经济上压迫的痛苦”⑤。这其实明示了“萧冷相恋”是发生在德国经济危机时期冷荇失业的重要前提下的,而萧华亭是要给她提供经济保障的,这是当时留德学生的一般情况,不但中国人如此,日本人亦然⑥。这两者的相恋关系,实质是建立在经济关系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铨浓墨重彩地写华亭寄30马克给冷荇买新衣服、重逢时特意准备赠送红宝石金戒指⑦,就不是不重要了;而且他们一再地算账,既精打细算又尽量享乐,从这一背景出发也更易理解。当时的留学生文学中,浓墨重彩地渲染中西之间的爱恋情仇,并非新鲜。如张竞生记录和描述留法学人的各种记述或回忆,那些故事和风流仿佛天方夜谭,但经考据却确有实际出处。张竞生自己“两次在欧洲,十余年遇到许多情人”,而且“曾与一法女,同居年余,并生了一女孩;但入巴黎国立育婴院而夭殇了”。⑧按照姜亮夫的理解:“我们的留学生,多半是廿四五以前的青年,有的是国内大学毕业生,有的连大学也未进过,他们的一切内蕴如学识见解,都非常浅薄,道德修养也都未定。一到了欧、美有次序有规律也有香有色的国家,一切都震撼得非常不宁静,又在这样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地方,岂能把持得着,于是留学生第一步所被的外诱是色,色香多端,女色为甚,所以据我耳闻目见的事来说,留学生犯色欲过度的人,并不在少数,本来欧洲女性,多半是康健白皙美好,而男女风纪,又不甚严,我们的少年朋友,还有几个能自操持者呢?”⑨这是从性的角度立论,但就中外之间的男女情感而言,也未尝没有真情实意的例子,日后成婚的也不乏其人,譬如王炳南与王安娜的婚姻,乃至朱白兰对中国爱人及其国家的生死追寻等都是⑩。在这里,陈铨的妙笔不仅勾勒回肠荡气的萧冷之恋,而且顺带扫荡了那些留学生登徒子们,呼应了以上姜亮夫的判断。作者安排冷荇等在咖啡店里遇上中国著名诗人刘金龙,也是别有用意:此君乃是省派的官费生,按照旁观者的眼光,“他来玩。他请求省政府延长官费一年,说要到欧洲各国考察,其实他不过到欧洲各国来逛窑子。伦敦巴黎,他闹了半年已经有点厌倦了,所以想到柏林来换换口味,他只会讲几句简单的德文,前天来柏林,刚住下,到万牲园旁边,就去拉了一位又胖又丑的女人,带回旅馆。昨天早上起来立刻写了一首长诗。据他讲起来,这一首诗一出去,在中国爱情诗里,可以开一个新纪元”⑪。此君显然对美国、法国等也都相当熟悉:“后来又谈到女人了。诗人对于芝加哥的大腿戏与巴黎的玻璃馆,异常的叹赏。他问柏林有没有同样的设备,华亭说同样的没有,变像式的尽多,不过最好的还不应当到这种地方去找,因为她们这些人太下流了,罗罗既然是诗人,应该去找名媛闺秀,才可以配得上当代中国第一诗人的歌咏。”⑫这“当代中国第一诗人”之喻不乏讽刺。
《死灰》流露的这种面对现实社会的女性命运的惨淡和悲哀,具有普遍性、跨国别的情感意义。《死灰》中不仅有冷荇的可叹,还有德梦林的可怜,安丽的可悲。如果说冷荇因为家世的缘故,对远行有一种不自禁的畏惧感,或许更是对华亭性格认识得不够;那么安丽为了爱人而甘于出卖自己的肉体,而且不知悔悟,且振振有词,那就真的只能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⑬小说为什么取名“死灰”呢?或许在陈铨的心目中,这一命名寄托着特殊的人性意境?
二 德国形象与画卷的展开
1930年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德国无法独善其身,再加之德国长久以来遗存的犹太人问题,民族情绪被纳粹党煽动、工厂倒闭、失业人口日益增加,同时共产党的力量也在增强。德国社会充满了多元多层多方位的矛盾,表面看去或许仅是党派之争,但背后的因素却可能相当错综复杂,因为实质上饱含了利益冲突、权力争夺、资本驱动、理念之争等多重博弈,也可视为一个类乎混沌结构的系统侨易过程。
在这种背景下的中国留德学生,虽然很难完全置身真空,但却仍能享受到德国大学的学术空气和求知氛围,这不能不说是德国学术长期共同体传统的余荫和流芳在起作用。但萧华亭的心思显然不在上课,被教授点名时,也正昏昏欲睡,好不容易应付过去,却想着如何赶快赶到柏林去,因为站台上有苦苦等待的冷荇。再深邃独特的思想哲理,也敌不过恋人的楚楚动人、风姿深情。果不其然,在车站的站台上,“他忽然看见一位穿深红色大衣,压白狐皮围领的女郎,他走近一看,是冷荇”⑭。红衣白巾的妙龄女郎,不用更多言语的描述,再有趣的知识和深刻的思想在那一瞬间恐怕都已被风吹散了。
当然,对于萧华亭来说,留德的岁月并不仅都是浪漫情爱的潇洒和快乐,他也有精神上的挣扎和苦痛的一面:“这四年多来,我时时刻刻都感受一种内心的冲突,一方面常常心里想把一切科学工作抛开,提笔写点东西,但是另外一方面有时又感觉理论方面的研究,虽然明明知道同我创作没有多少直接的好处,却自有它特别的兴趣。到近一二年来,我的思想渐渐变精密了,一个问题到手,我也很自然地能够分析研究,德国大学对我科学的训练,可以说是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功。同时令人感觉到相当可怕的,就是现在我差不多已经完全失掉了我创造的习惯。”⑮这段话确实体现了德国文化中科学与文学的特殊关系,或许就是“诗与真”的冲突,一方面,文学的灵性舒展是要求一种行云流水、随意自如的境界的,而科学训练则要求人必须进入到脚踏实地、逻辑严谨的状态,即“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文德尔班区分了“存在领域”与“有效领域”的概念,自然科学属于前者,为“规律设定性科学”(normothetisch),研究的是关于知识实存的条件问题(Questio facti);文化科学属于后者,为“个别描述性科学”(idiographisch)⑯,研究的是知识有效的条件问题(Questio iuris),其目的在描述已知事实。但其论述尚未臻充分,故其弟子李凯尔特(Rickert,Heinrich,1863—1936)明确区分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概念,且认为 “对于经验的文化科学来说,无论如何直到如今还没有获得大体上近似自然科学那样广阔的哲学基础”⑰。但在歌德那里,“诗”与“真”是融为一体的(Dichtung und Wahrheit):“因为当我为了适应读者经过深思熟虑的请求,想将内心的激动,外来的影响以及自己在理论上和实际上迈出的脚步顺序加以叙述时,我便从自己狭小的私生活进入广大的世界中;直接或间接影响我的许许多多的非凡人物的形象便呈现出来。甚至那对我以及一切同时代的人有巨大影响的整个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动,也不得不加以特殊的注意。因为,把人与其时代关系加以说明,指出整个情势阻挠他到什么程度,掖助他又到什么地步,他怎样从其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作为艺术家、诗人或著作家又怎样再把他们反映出来,似乎就是传记的主要的任务,可是,这种要求差不多无法达到,要达到它,个人就得认识自己和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知道他自己在一切情况之下还是依然故我到什么程度,以及知道把人拉着一道走而不管他愿意与否、决定其倾向和予以教养的时代是怎么样。”⑱时代与个体、自传写作与时代认知、小自我与大世界、诗与真这样一种始终存在的矛盾冲突型的二元关系当然也表现在萧华亭这里:“我脑子里现在常常充满了空虚的规律,很少幻想出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我有时极力要改变又改变不来。因此我想我诗人的生活,已经寿终正寝了,这都是大学教育,害了我的。”⑲席勒也说:“常常是我在进行哲思的时候,诗人就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或而当我创作的时候,哲人的精神又占据上风。就是现在,我也常遭遇这种困惑,想象力会干扰我的抽象思维,而冷静的认知又将创造之思打断。”⑳席勒表述的是诗—哲矛盾,华亭面临的是创作—理论的冲突,基本类型是一致的,但若就一体二魂的痛苦表述而言,其实更有其普遍性价值,歌德曾借助浮士德之口道出了一个“崇高精神”与“粗鄙物欲”之间的元价值判断问题㉑,具体到两个紧密相爱的恋人之间,也有着明确的二元人生观差异,作者安排了一段对话,以表示萧华亭与冷荇这对恋人的观念之别:
“呵,冷荇!我只要一生一世不离开你,我就好了。”
“人生在世,最好过一天算一天,生活的痛苦和快乐,始终还是在现在。”
“冷荇,不只是现在,过去的回忆,同将来的恐怕,都能使你痛苦。”
“世界上最傻不过的人,就是一天到晚只想着过去将来,抛荒了现在的人。”
“冷荇,你这个人真奇怪!你也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你讲起话来,有时倒好像一位胡子通根白的哲学家一样。”.㉒
这段萧华亭对冷荇的表白以及冷荇的“及时行乐”思想颇有意趣,因为面对一个中国男性“天长地久”的诉求,浪漫的德国女郎却仅仅表示了“珍惜当下”的哲学,这似乎也一语成谶,成为这对异国恋人最后漂泊错过的结局预告。他们的观念差异巨大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恐怕多少与各自的教育背景和知识构成有关。
三 萧华亭对德国精神的把握与陈铨留德背景的印证
也因其个体蕴含的文化史意义,萧华亭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之意趣值得揣摩再三。一方面,他作为一个留德中国青年学子,与德国妙龄女郎冷荇缠绵情长,仿佛多情种子;另一方面他又仿佛是求索的中国知识青年代表,譬如阅读尼采,尤其是《苏鲁支语录》,很能见出那代人的共性特征来,华亭理解尼采的过程,似乎也由电光火石般的思想际遇所促成:
这一回他读懂了,尼采的话,平常他似很难懂的,此时他觉得没有一点困难,意义像透明的水晶那样地清楚。他自己很奇怪,为什么他突然会有这样好的悟性来?他觉得他不但了解尼采说话的意义,而且能够亲切地体贴他讲话的热情。
这种读书的遭遇困难却又曲径通幽,但最终经由思想探险而最终接近大师的过程确实精彩:
他整整读了半点钟,精神上有一种不可形容的快活。但是隔一会,他的思想又渐渐变模糊了,书上的意义他又渐渐看不懂了,再一会,书上的字,又重新上下跳跃起来。
正是这样的反反复复与坚持不懈,乃使得以萧华亭为代表的留德学生无比鲜明而形象地树立在世界文学的殿堂之中,而这样的萧华亭与冷荇之间的爱,也注定是无望的,由此可见萧华亭所代表的留德学生与冷荇所代表的德国底层工人女郎之间的精神鸿沟。
至于萧华亭本人,似乎应为陈铨本人原型。理由大致有:一是华亭的专业,按照他对佩清的说法,“你知道在德国博士考试,同时要考三样东西,德国文学是我的主科,英国文学同哲学是我的辅科”㉓,这不但反映出德国大学的主辅修专业制度,而且符合陈铨本人的基尔大学求学状况。二是华亭提及他曾在芝加哥留学㉔,这段留美经验,恰恰又是毕业于清华的陈铨所具有的,大致说来,陈铨在1928—1930年留美,在奥柏林学院毕业获得英语文学与德语文学的硕士学位㉕。1930年9月陈争取到清华之批准,将留美三年节余下的官费用于赴德深造。
陈铨的留德状况,如果辅之以陈铨本人的生活经历,则或可相互印证。当初陈铨在清华读书时,曾到青岛海滨度假,留有海滨日记,则可看出其习惯:“我每天的生活,早上到海边散步,或往烟台山读英文。……上午读中文英文,中午读韩非子及杜诗。”㉖这种侨易经验显然是有其样本可循的。《死灰》里的萧华亭形象,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作为“自叙传”来看待的。作为留德学人的陈铨的心理变化的错综复杂,再考虑到留学经验的介入,人生阅历因时空变化而更加丰富与具有融合和挑战性,也使得陈铨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变创过程,这当然有待进一步研究。总体而言,陈铨小说的艺术性无疑还有欠缺,但就《死灰》而言,却是具有相当的艺术和思想深度,可以被视作海外流易小说的代表之作;而萧华亭的出现,则标志着相当典型的一种留德学生的形象,“国家的危亡,不能激励萧华亭,萧华亭又不能自己激励自己,他只是就是这样敷衍地过活”㉗。具体地刻画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活脱脱就是“无用人的画像”:“你说他不工作吗?他每天依然地按时刻去上课读书。你说他不交朋友吗?他还是照样去拜访师长同学,赴各种集会。你说他不虑到将来吗?他常常还有许多的冥想,许多的计划。但是他时时刻刻都感觉他生活的无聊。他知道一定会有一天,他没有法子再敷衍下去的时候。”㉘但这虽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是一个中国在危难之际的在异国无所事事的“零余者”,仍是相当有典型性的。倒是那被开玩笑被称为“哲人”的冷荇,对自己恋人华亭的品质有非常到位的判断:“华亭为人心顶好,这是不错的,但是他这个人没有决断力,意志力不坚强,他不能支配环境,常常让环境去支配他。同他在德国还可以,同他到中国,我不会有好日子过。”㉙这正是非常有见地的“知己之言”,或许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作者对尼采哲学的不自觉借用,没有强力意志支配的萧华亭,只能为环境所支配,而不能强势与环境斗争,所谓“一切现象从本质上而言都是压迫的意志与反抗的意志之间的斗争……”㉚或许正道出了其中的奥义。
按照陈铨的计划,关于萧华亭的“为人,处世,品格,学问,他疯狂的原因,他同冷荇及其他女友的关系”,非得“再写一部两部”小说不能尽言。㉛而故事的发生地,很可能是以陈铨留学的基尔大学(Christian-Albrechts-Universitat zu Kiel)为模型的,这从霍夫曼女士的问话中可看出:“柏林的女孩子好看点,还是克尔的好看点?”㉜萧华亭其人,自然也多少与陈铨有些关系,我们看看他在德国文学研究课堂上的场景,其专业也是一样的。最后的“华亭跋语”无疑是饶有意趣的,“到南方来,进海岱山医院又一星期了,心里本来满怀着的希望,现在已经完全消灭了。我现在只等那一天,只虔求那一天快来,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㉝。借助重病住院的主人公的话来终结朋友涛每的小说,重温“我在德国最不能忘记”的一段感情生活㉞;希望以死亡来了结自己的痛苦,或许是肉体的、精神的都有。因为冷荇没有再见,她与别人结婚了,而华亭既不告诉她自己的病,也不告诉她自己归国的时间,所以,“我们一切的关系断绝。从前以为千难万难的事情,真正到那个时候,却有令人想象不到的容易。我现在也疲倦了……精神身体都感觉最大的疲倦……我也想休息了,世界上一切的喜怒悲哀,我都不管了,这个世界不是我理想的世界!”㉟
好一个“这个世界不是我理想的世界!”全书以这样的句子结束,似乎道尽了一种忧伤满怀和理想破灭的情绪,这当然也让我们想起德国诗人的类似表述,譬如席勒通过波沙侯爵表达的悲哀:“对于这个世纪来说,我的理想过于早熟。我只能做,未来时代的公民臣属。” (Das Jahrhundert/Ist meinem Ideal nicht reif. Ich lebe/Ein Bürger derer,welche kommen werden)㊱这是天才早产于时代的宿命悲剧,也是那代留学生的文化悲哀。按照宗白华在留德之前的说法,“在上海看见很多的青年,暮气沉沉,毫无奋斗创造的精神,终日过一种淫侈逸乐的寄生生活,恬不知耻,我见了很为中国前途悲观”㊲,担心“中国陷于文化恐慌状态”,“愈落愈甚,恐怕陷于不可恢复的境地”,强调“我们青年实负有创造中国新文化的责任”㊳。显然他是有着“为祖国文化之兴起而读书”的自觉使命感的,这一点在少年中国学会那批精英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其中一部分人到德国后更是锐身实践,创造了一个留学史上的“范式尝试”。1921年,王光祈、宗白华、魏时珍等少年中国学会留德会员发起组织了“中德文化研究会”㊴,宣称要积极地“将德国的文化介绍至中国,中国的文化介绍给德国”,“以共同发展文化为宗旨”,“我们是华人,是东方文化最古最高的国民。目下旅居德邦,是西方文化最出类拔萃的地方”,“现在东方的或西方的文化,都是片面的,还没有充分的调和。所以要谋全体人类文化的发展及进步,非从互相研究,互相孕育上着手不可”,“我们应当努力,来担任两大文化的融合及发展。从此进行,方能创造一个将来的及全人类的新文化”㊵。当然作为中国人,其内在理念仍主要放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上。这多少有些像梁启超所说的:“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吾宗也。”㊶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的文化融合和文明侨易绝非那么简单,这涉及非常复杂的文化接触、观念交锋乃至安土重迁、长期交融等层面。联姻当然是一种从根本上改变基因状况的方法,譬如李石曾就真的醉心于中法之间的通婚,因为他相信这可以改良人种。所以,我们可以视中外联姻为一种很有象征意味的文化现象,不仅有着男女两性天然相吸的自然基础,而且还涉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文化层面的相互融通之可能性。文本里的恋情让人充满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当然也带来了对其象征的文明“结婚”的期待,但正如现实中的爱情婚姻其实也很少有真正美满的,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婚恋也不例外。在文化层面上的融合说来容易,真正实现并优化者则凤毛麟角,从本质上来说,萧华亭经历的是一种移交的过程,即留德中国学生与德国本土女郎的相遇与交融,然则“由象见道”,我们借助侨易思维拓展来看,当然就可延伸出中德文化相遇,乃至东西文明碰撞的阔大图景。
萧华亭与冷荇的恋爱,或许在个体的层面能算得上是难得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但却远远见不出文化共同体层面的“有缘千里来相会”。这种侨易现象确实值得深入分析,此处不赘。“再见冷荇”是一种无望的叙述,“心如死灰”或许更可以准确地表达出作者内心的实情,这种中德之间的“联姻”向往,无论是个体还是文化,或许更多属于美好的理想憧憬,而缺乏脚踏实地的步步为营的工作。
虽然我强调,“中德文化关系史的意义,是具有两种基点文明代表性意义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而事实上,“中德文化交流是东西文化内部的两种核心子文化的互动,即作为欧洲北方文化的条顿文明与亚洲北方文化的华夏文明之间的交流”。㊷但就彼此之间的“契合”而言,显然还有漫长的道路有待跨越,这尤其需要有识见的有志之士始于脚下的千里之行,卫礼贤曾经迈出了极为建设性的步伐,可谓开辟鸿蒙,郑寿麟等留德学人显然深受感染,并且也身体力行,但无论规模和实绩都确实是相去甚远,后来也因种种限制而未能持之以恒。或许,还是要回到莱布尼茨(Leibniz,Gottfried Wilhelm,1646—1716)当初的那个预言:“鉴于我们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natürliche Theologie)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由神启示的神学(die geoffenbarte Theologie)那样,是很有必要的。”㊸如此借助莱氏立论,倒不是扬扬自得于“中国文化”可以走出去的自我满足感,而是想善意和严肃地提醒现时代和未来的中国知识精英,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再起或复兴,乃至对于世界文明共同体的建构,其实是有责任在的。
所以,重温现代留德学人坎坷荆棘的异国情感之路,也并非简单地满足一下纸上探案的猎奇之心或对文学文本情节学考索的好玩而已,我们不必去“传教”,但走出国门,敞开胸怀,让“世界都在我胸中”(“天地都在我心中”),探索文明交易之路,其实也是失航的全球之船所发出的吁求,马凯硕(Mahbubani,Kishore,1948—)将全球各国譬喻成一艘大船的若干船舱而缺乏船长,但他坚信“因为万物归一”㊹,所以我们或许应当追问,在这“归一”的过程中,中国人以及中国文明究竟该站在何样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萧华亭的疯狂也就多少有些类似维特之死,具有“文化假殉”的意味㊺,促使我们进一步追问文化侨易的可能何在。
注释:
①此文承南京工业大学张帆女士看过一遍并提示材料和意见,特此致谢。
②陈铨:《死灰》,大公报社出版部1935年版;陈铨:《再见,冷荇》,大东书局1945年版。这实际上是同一部小说,题名不同而已。也就是说,陈铨的这部小说其实是颇受欢迎的,即不仅印行一次而已,还曾再版过;而在1945年再度印行,是否有庆祝抗战胜利的意味,也值得深入考察。
③④⑤⑦⑪⑫⑬⑭⑲㉒㉔㉗㉘㉙㉜㉝㉞㉟陈铨:《死灰》,大公报社出版部1935年版,第9、36~37、37~38、28、67、70、33~34、21、133、150、126、20、20、75、4、196、196、197页。
⑥有论者指出,《舞姬》《泡沫记》《信使》是森鸥外著名的“德意志留学三部曲”。沈晓华:《浅谈森鸥外“德意志留学三部曲”》,《河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⑧《玻璃宫中》,张竞生《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4页。
⑨《欧行散记》,载姜亮夫《姜亮夫文录》,姜昆武选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7~308页。
⑩王安娜(德语原名安娜¡¤ÀûÔó,1907—1990),曾在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1年起参加反法西斯主义运动,曾两次被捕入狱。1935年与在德从事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王炳南结婚,1936年来华继续革命。1955年返回民主德国,1961年移居联邦德国。参见[德]王安娜《嫁给革命的中国》,李良健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朱白兰(德语原名Klara Blum,拼音为Dshu Bailan,1904—1971),她曾在奥地利维也纳心理学院修习心理学,大学毕业后在巴勒斯坦和维也纳从事新闻工作,后在苏联从事创作兼任教师,在法国从事文学翻译工作。1949年她重回北京,1952年担任复旦大学德语文学教授,同年9月转到南京大学任德文专业教授。“Klara Blum/Dshu Bailan Lebensweg”(朱白兰简历),南京大学档案。关于朱白兰,可参见夏瑞春《永远的陌生者——克拉拉·布鲁姆和她的中国遗作》,载印芝虹等主编《中德文化对话》第1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260页。
⑮陈铨:《死灰》,大公报社出版部1935年版,第133页。这一段萧华亭关于文学研究和创作矛盾的自白,在陈铨的自述中几乎相同:“我以前想出国学文字,只想去学一点能够帮助我创作的技巧,然而结果出去六年,所学的乃是同我初表相反的文学科学。这一种科学工作,六年来尽日磨练,欧美大学进了七八个,博士学位也骗到手了,然而我创作的生机,好像也斲丧尽了。”陈铨:《我的生活和研究》,载《清华副刊》1936年第44卷第3期。
⑯靳希平、吴增定:《十九世纪德国非主流哲学——现象学史前史札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252页。
⑰[德]李凯尔特(Rickert,Heinrich):《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Kulturwissenschaft und Naturwissenschaft),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10页。
⑱《诗与真·自序》上册,刘思慕译,载[德]歌德《歌德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⑳德文为:“denn gewöhnlich übereilte mich der Poet,wo ich philosopieren sollte,und der philosophische Geist,wo ich dichten wollte. Noch jetzt begegnet es mir häufig genug,daß die Einbildungskraft meine Abstraktionen und der klate Verstand meine Dichtung stört”。席勒1794年8月31日致歌德函,in Seidel,Siegfried: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Schiller und Goethe(席勒歌德通信集)Erster Band. München Verlag C.H.Beck,1984. S.18。
㉑[Werke: Faust. Eine Tragödie. Goethe: Werke,S. 4578 (vgl. Goethe-HA Bd. 3,S. 41)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4.htm] 此处为作者自译。《浮士德》中译本参见[德]歌德《歌德文集》第1卷,绿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㉓陈铨:《死灰》,大公报社出版部1935年版,第123页。关于陈铨的留德情况,可参见叶隽《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帆在德国基尔大学查阅了相关档案材料,提供了一些陈铨求学时的背景材料,尤其是几位重要的老师,如导师李普(Liepe,Wolfgang,1888—1962)、哲学老师克朗纳(Kroner,Richard,1884—1974)、斯坦泽(Stenzel,Julius,1883—1935)开设的课程。参见张帆《从档案看陈铨留德生涯》。
㉕Harnisch,Thomas:Chinesische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 - Geschichte und Wirkung ihrer Studienaufenthalte in den Jahren von 1860 bis 1945. Institut f. Asienkde, 1999. p.467.
㉖陈铨1924年7月10日日记,《陈铨〈海滨日记〉选录》,《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2期。
㉚尼采:《权力意志》,贺骥译,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
㉛作者志,陈铨:《死灰》,大公报社出版部1935年版,第2页。
㊱Schiller,Friedrich von: Don Carlos. In Martini, Fritz und Müller-Seidel, Walter (Hrsg.):Klassische Deutsche Dichtung. Band 13.(德国文学经典,第13册) Freiburg im Breisgau: Verlag Herder KG,1964. S.114-115. 作者自译,另可参见张威廉译《唐·卡洛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在这个问题上,诗人们是有共同语言的。尼采虽对席勒很不以为然,但也曾写诗宣称:“我的时代,尚未到来;有些人,死后方生。”
㊲㊳《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93、100页。
㊴作为留德学生的文化组织,该会成员包括王光祈、宗白华、郑寿麟、魏嗣銮(魏时珍)、孙少荆、张梦九、詹学时、陈鹤鸣、金其眉、吴屏、王达生等人,主要力量是“少年中国学会”中的一批留德学生,该会以“介绍研究中德两国文化为宗旨”,希望“东西两种文化结婚”,以“产生第三种文化”。
㊵参见翁智远主编《同济大学史》第1卷(1907—1949),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㊶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㊷《中德文化丛书》封底,叶隽:《主体的迁变——从德国传教士到留德学人群》,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㊸莱布尼茨:《〈中国近事〉序言:以中国最近情况阐释我们时代的历史》,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㊹马凯硕(Mahbubani,Kishore):《大融合:东方、西方与世界的逻辑》(The Great Convergence: Asia,the West,and the Logic of One World),丰民等译,海南出版社 2013年版,第235页。
㊺参见叶隽《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爱情悲剧后的青春迷惘与制度捆绑》,《同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