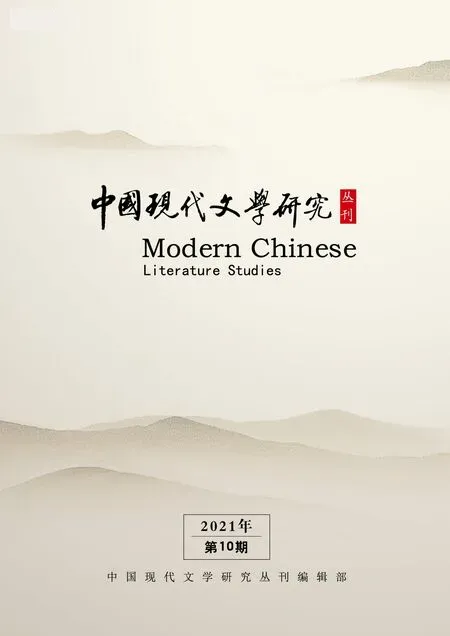论新文学中的法治省思※——以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为中心
2021-04-16董燕
董 燕
内容提要:以鲁迅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新文学并未预设关于法治的主题表达,但在其中描绘的时代沉浮、人生百态中,法治虽然缺席,却能侧面透露法治信息,如实呈现现实与法治的背道而驰,在对法律高高在上的同时又被束之高阁、平等难以实现、权利缺乏保障的批判中完成了对法治未完成的摹写,充满人文关怀。新文学作家肩负时代使命,他们以现实主义姿态,在批评和反思中,使人们得以接近时代真相,作家将对法治缺席的省思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预言了国家的前进方向。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在“德先生”“赛先生”的启蒙之外,“法治”也是不容忽视的力量。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登陆中国之初,便带着功利色彩,与救亡图存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清末修律、预备立宪起,中国逐渐开始了对现代法律制度外部形式上的追求,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展开了对法治的探索。新文学处于法治建构的历史进程中,法治缺席与古代文学的法治缺席有根本不同。古代文学处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包裹之中,诸法合体、司法行政不分、法律儒家化工具化、皇权大于法权,这一切自成体系浑然一体,偶尔出现凤毛麟角般的清官,也自诩为“看家的恶狗”(元杂剧《包待制陈州粜米》),无论现实还是文学,主导法律文化与人们的文化选择高度一致,并无矛盾与张力。如血亲复仇,在古代血亲复仇是违法的,但从统治者到普通百姓,均对占据道德优势的复仇者报以同情和认可,由此表彰孝行也是常有的事,虽然最大的矛盾是法律与复仇行为之间的冲突,但在泛道德化的法律文化与社会价值认知中,这一冲突不但不会造成困扰,反而会加强道德对法律的支配。新文学就复杂得多。血亲复仇本身的凄苦意味没变,但环境发生了改变,即便人们对复仇者心生同情,却也无法再堂而皇之地予以褒奖,认可者依然大有人在,但与此同时,多了法治层面的反思,法治就像高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迫使人们不得不追问,是否应采取如此惨烈的方式复仇,社会是否应为悲剧的产生承担责任,不如此复仇又该如何实现公平正义?诸如此类的问题纷纷涌现,主导文化倾向不是一元化的,人们的文化选择是多样化的,这就形成了更多难以解开的矛盾与冲突,丰富了文本的社会含义,也使新文学带有更鲜明的社会批判性。
考虑到新文学在3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中,各阶段的各流派、社团及作家对法治问题的呈现丰富而多元,实难通过一篇论文进行全面论证,因此,本文拟对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几位新文学作家的代表作品进行考察。之所以选择这几位作家,原因有二。第一,他们的作品能反映新文学取得的成就。第二,他们的作品虽然贯穿于民国各时期,作家并未预设关于法治的主题表达,作品也绝不是法治题材,但其中与法律至上、平等、权利等相关的情节安排和情感表达,却是侧面透露了法治信息,其中体现的法治问题具有共通性。鲁迅等人的作品揭示了法治在应然与实然层面的剥离,即法治应存在但实际不存在,反思与批判是他们创作的基调。
一 法律高高在上的同时又被束之高阁
20世纪上半叶,法律至上的观念有一个逐渐深入人心的过程。1912年1月6日孙中山在答记者问时宣称:“中华民国建设伊始,宜首重法律。”1虽然当时法律制度并不完善,但建立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却是国人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中国之当为法治国,已为全国上下所共认”2。但随着袁世凯称帝和北洋军阀割据,国内局势愈发混乱,法治发展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在新文学的法治书写中,理论层面的法治共识与现实层面的法治缺席形成鲜明对照,即法律一边高高在上,一边又被束之高阁。
说法律高高在上,是因为法律是民众在困境或纠纷中所能想到的最具权威的救济,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是有权威的;说法律被束之高阁,是因为法律并未发挥应有作用。如《离婚》中,爱姑为了不离婚,提出“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3,但在慰老爷的否定中,爱姑随即打消了这一念头。在《老张的哲学》中,孙守备为救李静,无奈之下想到了打官司,“打——官——司!跟你打——官——司!”4但随后他的心理活动是,“打官司?是中国人干的事吗?难道法厅,中国的法厅,是为打官司设的吗?……打官司?笑话!真要人们认真的打官司,法官们早另谋生活去了”5。无论老张,还是孙守备,都明了打官司的虚妄。《骆驼祥子》中,小福子的父亲二强子打伤了二强嫂,导致二强嫂死去,“二强嫂的娘家不答应,非打官司不可”6。但在旁人劝说下,娘家人让了步,最后以二强子答应好好发送二强嫂,给了娘家人十五块钱解决了纠纷。《子夜》中,吴荪甫不同意妹妹吴蕙芳读书,张素素出主意说,“我就教你跟他打官司!”7但吴蕙芳显然无法接受打官司的做法。新文学中,“打官司”出现的频率很高,但真正打官司的却少之又少,即便是《霜叶红似二月花》中,官司真正打了起来,但后来因为各种利益盘根错节,官司并未继续打下去,口头上的健讼与实际行动的畏讼形成了鲜明对照。
新文学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打官司”成为人们“挂在嘴边”的终极方案。表面看,法律成为人们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武器。这一现象的发生有深刻的时代因素。第一,诉讼主体资格的改变。古代社会是以三纲五常为原则确定诉讼主体资格的,对诉讼主体有严苛限制。以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唐律疏议》为例,其中对诉讼做了诸多限制,而诉讼主体资格深受纲常礼教制约,如卑幼告尊长,“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8;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9,可见等级关系远在是非善恶之上。这一状况在民国时代被彻底终结,取而代之的是“能独立以法律行为负义务者,有诉讼能力”10即可提起诉讼。第二,律师制的兴起保护了当事人的利益。古代社会讼师动辄得咎,如《唐律疏议》有惩罚受雇帮人诉讼者的规定:“受雇诬告人罪者,与自诬告同,赃重者坐赃论加二等,雇者从教令法。若告得实,坐赃论;雇者不坐。”111906年,沈家本主持编成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这是中国第一次开始区分实体法和诉讼法,并有关于律师的专门章节,指出“凡律师,俱准在各公堂为人辩案”12。其中对律师职责做的具体规定,在法律层面保护并制约了律师活动。自1912年公布实施的《律师暂行章程》始,民国时期的律师制度得以创立13;1927年公布施行的《律师章程》进一步明确了“律师受当事人之委讬或法院之命令,得在通常法院执行法定职务,并得依特别之规定,在特别审判机关行其职务”14。律师具备的法律知识、经验、技能,能够对民众提供更有效的保护和帮助。以严刑峻法为外在表现形式的古代律例,最终追求的是“法致中和,囹圄常空”的法律被搁置不用的无讼境界,民间百姓在礼教文化影响、律例制约、官方态度、经济条件等各因素合力作用下,形成了畏讼、厌讼、耻讼、避讼、贱讼的文化心理。无论《二十四史》等史书,还是《三言二拍》等文学作品,关于官方息讼、民间畏讼的书写屡见不鲜,由此造成的恶果便是百姓难以维护正当利益,法律权威被损害。自清末始,这一状况开始改变。
但实际上,民国法治的虚伪显而易见,罗隆基批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时说:“如今约法上的自由,都不算自由。约法上的权利,都不算权利。”15这一批评适用于民国时期各项法规。书面的法治追求,现实层面对法律的践踏,体现在新文学中,便是人们一边把“打官司”挂在嘴边,一边鲜少付之行动,如老舍的《离婚》中,小赵因感情纠纷挨打后,决定“不讲武的,讲文的,登报纸,打官司”16,而官司最终没打,因为所有人“都怕一样事,怕打官司。”17法律至上就像那个时代的华美装饰,存在,却遥不可及。
二 平等难以实现
平等是法治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孙中山的平等思想曾产生深远影响,他直接将平等视为三民主义的核心:民族主义是“中国和外国平等的主义”,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民权主义是“国家的大事人人都可以过问”,政治上人人平等,不再有特权阶层;民生主义是“把全国的财富分得很均匀”,所有人都可以平均受益。18简言之,即中外平等,国民在政治、经济层面平等。在民国法律制定中,无论宪法还是部门法,均有关于平等的明确表述。时人对平等的讨论也非常热烈,更有《平等》杂志于1931年创刊。
但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文学中,平等精神只是散落其中,偶露峥嵘,随即便如昙花一现,被淹没在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中。如《伤逝》中,涓生跟子君大谈男女平等,但在子君日渐怯弱的状态中,可知男女平等并未真正实现。《骆驼祥子》中,祥子在曹家得到的平等待遇,是他悲苦人生中最温暖的一段时光,但却非常短暂,不得已离开曹家后的祥子很快便被黑暗不公的世道吞没。《寒夜》中的曾树生追求平等、自由、独立的婚姻与人生,她与保守的婆婆,是新旧两个时代女性的象征,但最后终究守不住婚姻与孩子,只能开始另一段人生。《霜叶红似二月花》中,徐士秀等人视平等如洪水猛兽,这个细节便如其时平等思想的一个隐喻,虽已广泛传播,但平等更多停留在书本上和人们的误解、不解中。新文学中有平等精神的闪现,但不平等的现实却俯拾皆是,有身份的不平等,车夫也要分三六九等(《骆驼祥子》),卖布的儿子被人看不起(《赵子曰》),因为跟上司讲理而丢了官(《老张的哲学》);有经济的不平等,有钱有势的人可以住头等病房(《第四病室》),工人挣扎在社会最底层(《子夜》);有婚姻的不平等,少女被迫给人做小(《家》);有法律的不平等,有势力的人谋财害命死后却能上天堂(《原野》),孩子死于非命却讨不到公道(《霜叶红似二月花》)……鲁迅甚至指出,执着于平等自由会让人苦痛一生(《头发的故事》),新文学对不平等现实的批评与控诉真实再现了社会的悲苦。
人人生而平等,但人人生而不同,这决定了要实现平等,便需扶弱济贫。人人平等是理想状态,但由于人们在才智、性格、所属阶层、成长环境等诸多方面有差别,因此,“对一切人的不加区别的平等就等于不.平等”19。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建立在人生而不同、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基础上,法律对“人人平等”的强调,既表明了追求平等的决心,也说明了不平等是客观存在。为了最大限度弥补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从而实现平等,法律应向弱者有所倾斜,如保护弱小者的各项权利、为贫穷者提供生存保障等,对实际地位不平等的人,“将他们置于平等的地位的唯一方法也只能是给予他们以差别待遇”20。这是法律的人文关怀所在,即通过差别对待实现资源配置、权利保障的相对平等。
平等是法治的重要原则,但民国社会没能将写入法律的平等付诸实现,通过新文学的法治呈现,可发现弱小者、贫穷者不仅未得到法律的保护或优待,反而处于备受压迫和损害的无告境地。如《原野》中有一场阎罗审判,结果是:焦阎王上天堂,仇虎拔舌头,仇虎父亲上刀山,妹妹下地狱,仇虎的满腔悲愤化为质问:“你们这是什么法律?这是什么法律?”21这场审判意味深长。一方面,这是来自仇虎良心的不安和拷问,毕竟焦大星和小黑子都是无辜的;另一方面,这也是现实冤狱的反映,焦阎王杀人诬告,伤天害理,但无论活着还是死后,不仅未被惩罚,反而受到各种庇护,而身处最底层的仇虎一家,活着被诬告、活埋、卖身,死后还要遭受酷刑,法律不仅不能扶助弱者,反而成为压迫弱者的帮凶。《原野》发表于1937年,1931年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与193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均有保护人民财产的条款,《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还特别强调“人民有身体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或处罚”22。《原野》中压抑而浓烈的爱恨情仇,仇虎椎心泣血的质问,产生了撼人心魄的艺术效果,也凸显了法律的虚伪与无力。新文学中权势阶层依然享有特权,能得到法律庇护,底层民众处于孤苦无援的境地,平等精神便如海市蜃楼般可望而不可即。
新文学通过法律问题的不平等批判的是社会的不平等。从先秦到民国,无论政治制度如何变化,“而社会的结构却完全是一样的。然则社会的结构究竟如何?这可以一言蔽之曰:阶级的结构是也,不平等的结构是也”23。民国各宪法虽然一再强调国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却并未具体规定实现平等的保障,而现实的专制、传统的束缚则催生出各种不平等,如男女之间,女性在婚姻、经济、教育、政治等层面均未实现彻底的解放,婚姻不自主、要接受丈夫纳妾,经济不独立,教育权被剥夺,没有参政意识也缺乏参政权。再如阶级之间,自古以来便存在的“统治阶级掠夺被压迫者的经济利益”“统治阶级支配被压迫者”24等现象依然存在,社会的不平等常常以尖锐的阶级对立呈现出来,如《子夜》中的工人罢工,《家》中的鸣凤自尽等。民国法律也有对弱者的倾斜,如起到临时性宪法作用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1)中有对劳工、妇女儿童从事劳动者、因伤病废老而不能劳动之农民工人、现役军人因服务而致残废者,有施以特别保护、救济的意思表示,但通过当时的新文学作品,便可知道,劳工、妇女儿童等并没得到优待,甚至处境愈加悲惨。再加上民国立法频繁,在193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上述条款都未再出现,可见保护弱者并未成为民国法律始终如一的追求,所谓法律上的平等其实是对社会不平等的掩饰,在现实中,阶级压迫与不平等的沟壑愈发明显。新文学中平等精神的存在感比法律至上、权利意识都稍弱,不管是在书本还是口头上,出现的频次都有限,这说明残酷现实并未给人们留下太多关于平等的想象空间,但在对不平等现实的批判与法律高喊的“平等”口号之间的对比中,本身便蕴含着对不平等现实的否定,更是从反面印证了平等的必要。
三 权利缺乏保障
在权利与义务之间,权利的获得尤显重要。古代中国,民众也享有一定权利,但更强调的是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这种责任被确定后即成为义务,无论是统治者通过法律强加给民众,还是民众自觉承担,履行义务都处于核心位置,权利与义务的地位并不对等。
相较而言,新文学中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反思非常亮眼。新文学中的权利意识呈现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个体对权利的奋力争取。如《子夜》中吴蕙芳争取读书的权利;《家》中,觉民通过逃婚争取婚姻自主权,觉慧则预感到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争取权利的斗争将不会再有悲惨的结局;《伤逝》中,子君和涓生冲破封建势力的阻碍,追求婚姻自主。虽然新文学中对权利的追求大多是悲剧结局,但高涨的权利意识却是法治的重要组成,新文学作家也由此践行了“为人生”的理论建构,若能由此发挥小说的“转移世道人心之能力”25,实有促人觉悟之功。第二种,是人的权利被肆意践踏。如《伤逝》中,追求婚恋自由权利的涓生因与子君同居而失去了工作;《骆驼祥子》中,祥子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我这一辈子》中,买卖人不能保护自己的财产与货物;《家》中,鸣凤被当作礼物送人;《寒夜》中,汪文宣校对文稿时,面对其中的谎言无能为力,生病又不能得到必要的医治,最终死在了抗战胜利那天;《骆驼祥子》《老张的哲学》《子夜》中均有买卖人口的情节;还有《月牙儿》《祝福》《我这一辈子》《第四病室》等,在大量新文学作品中,个体的生存权、婚姻权、言论权、生命权等均不能得到法律保障。“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应当是良心的战士”26,新文学作家面对社会对人的压制,表现出战士的风貌,通过“家庭的惨状,社会的悲剧和兵乱的灾难”,写出了对黑暗势力的反抗。27第三种,权利被利用,有人打着权利的幌子争利。如《老张的哲学》中对选举乱象的描写,民众的选举权成为了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手段。
权利的难以实现、缺乏保障,一个原因是固有制度、传统、文化造成的。民国新旧并存,如李大钊所描绘的,过年时看见贺年的人,“有的鞠躬,有的拜跪,有的脱帽,有的作揖;有的在门首悬挂国旗,有的张贴春联”28,这是一个生动的比喻,新与旧的混杂跃然纸上。在法律层面,这种新旧的矛盾就非常突出了,比如一面禁止重婚,一面又准许纳妾,29新法既立,而旧的习俗、传统依然影响国人的心理和行动。
更何况,民国法律中关于权利的规定也缺乏诚意,这是权利难以实现、缺乏保障的另一个原因。罗隆基曾对《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1)做过统计,发现其中关于权利的条文共19条,除个别条款外,其余一切条文都有“依法律”“不依法律”字样,这样一来,“条文的实质,不是积极的受限制,就是消极的被取消。”30所以罗隆基说:“左手与之,右手取之,这是戏法,这是掩眼法,这是国民党脚快手灵的幻术。”31
四 人文关怀与出路探索
新文学中,法律至上、平等精神没能付诸现实,通过逃婚的方式追求个人婚姻权利已是社会个体追求权利的大尺度表达,这呈现了当时法治的真实面貌,是作家认清了时代真相后的批判性思考。“国家在名称上已经变为共和,但是执政的人物,依然是专制时代的旧人物,执政的思想,依然是专制的脑筋,政治的制度,依然是专制时代的旧样式,一般的人民,也依然不能脱除专制的余毒挺然独出,显出自己的真生命真价值来。”32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但从执政者、制度,到人民,均无法摆脱专制思维的控制,而这一专制的情形,在民国时期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善,反而日益严重。新文学中的法治缺席,恰是对民国时代黑暗现实的否定与批判。对于作品中的人物来讲,面对社会的不公、残害,除了顺从、忍受、妥协,并没有更好的选择。祥子面对孙侦探的敲诈只能老老实实奉上钱财,觉新面对命运的摆布只能听之任之,第四病室里的人只能听天由命,汪文宣为了养家糊口只能说违心的话……他们不能拍案而起,不能选择对簿公堂,因为这样做的结果非但于事无补,而且可能会使自己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卑微的个体无从选择。新文学呈现的是一个个苦苦挣扎却无力自救、哀告无门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汇聚在一起,就构成时代的动荡和民族的苦难。
强烈的批判性源自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与悲悯,这是新文学最宝贵的人文精神。小人物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作家写出了他们恶劣的生存环境。作品中有不对任何人负责却可以办任何事、抓人放人都无须解释的“全能”机关(《离婚》),有不让说实话的报社(《老张的哲学》),有暴力机器(警察)对工人的镇压(《子夜》),有只能靠个人手段为社会除害的无奈(《赵子曰》),有人比法律更有力的哀叹(《骆驼祥子》),有不偷不抢不害人却活不下去的悲戚(《寒夜》),作家撕开了无价值的东西,毁灭了有价值的东西,一切的痛苦与不幸都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产物。当政者以宪制之名,行的却是践踏法律之实:“国法当遵,而彼可以不遵,民权当护,而彼可以不护。不过假手于国法以抑民权,讬辞于民权以抗国法,国法民权,胥为所利用以便厥私。”33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在新文学中,为什么法律只能在口头上起到震慑对手的作用,甚至有时连这种口头上的震慑作用也没有。新文学作家哀民之苦,怜民之痛,视无尽的苦难与自己息息相关,他们对黑暗现实冷峻审视、犀利解剖的批判立场彰显的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
鲁迅等人并不将改变现状的希望寄予法律,在法律不能救民于倒悬的清醒认知中,他们提示了解决现实问题、改变不合理社会的三种方案。
第一,改造国民性。没有国民性的改变,阿Q会在糊里糊涂的状态中被处死(《阿Q正传》),祥林嫂会因被迫改嫁、不能守节而心神不宁(《祥林嫂》),鸣凤只能自尽(《家》),汪文宣只能言不由衷(《寒夜》)……在愚昧、软弱、麻木、奴性、卑怯、自私的国民面前,法条再完备也于事无补。将民众从不觉悟、不觉醒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法治观、价值观,也尤为重要。先有新民,再有新国,是贯穿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一个逻辑前提,从《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1902—1903)、《痴人说梦记》(旅生,1904—1905)、《未来世界》(春颿,1907—1908)、《新中国》(陆士谔1910)等清末立宪题材小说,再到鲁迅等人的创作,无论是对“新中国”“新世界”的想象,还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勇于反抗者的赞赏,都暗含在这一理路中。但问题也由此而生。民众认知水平的提高、道德的完善很重要,但这并不是实现法治或“新中国”绝对必要的前提。人民在现实中遭遇的种种难题,既不是国民性问题所能涵盖,也不是国民性提高便足以应对的,所以改造国民性与制度完善、法治建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也不应有先后之分。事实也证明,不从根本上改变产生国民劣根性的制度环境、法律环境,而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和宣传改造国民性,收效甚微。
第二,采取暴力手段。在无力改变不公、不幸时,以暴力手段予以回击是又一个选择。“疯子”要熄灭长明灯,要放火(《长明灯》);仇虎为复仇而越狱,并杀死仇人之子(《原野》);鲁大海带领工人罢工,敢于跟恶势力抗争(《雷雨》);李景纯对杀人如麻的军阀实施了暗杀行动,认为救国只有两条路,一是救民,二是杀军阀(《赵子曰》)……顺从麻木的国民之外,鲁迅等人的作品中也会出现充满血性甚至带有原始蛮性的人物形象,他们敢于反抗,有正义感,有冲破旧秩序的勇气和力量。当法治缺席,且找不到其他救济方式时,暴力手段能够帮助个体实现个案正义,是对抗压迫简单有效的方式。但在鲁迅等人的作品中,因力量不对等,暴力对抗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疯子被关,仇虎自杀而死,鲁大海在与周朴园谈判时工人已复工,李景纯被枪毙。缺乏先进政党领导、先进思想指导的暴力手段,是对法律异化、法治缺席的绝望反抗,但并非调整社会秩序的理想选择。
第三,寄希望于进步革命力量。改造国民性遥遥无期,个人暴力反抗代价巨大且难以成功,依靠进步革命力量成为必然选择。鲁迅等人作品中的进步革命力量包括中国共产党,先进理论指导下的革命者。《子夜》中,吴荪甫及民族工业必然失败的命运,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革命的如火如荼捷报频传,二者形成颇富象征意味的对比,茅盾以马列思想为指导,预言了中国历史的必然,不仅为中国工人革命寻找到合法性依据,而且指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和必要性。鲁迅在《药》的结尾,为革命者的坟头添了一圈红白的花,既表现了社会革命的现状,也暗示了社会革命的前景。巴金、老舍、曹禺的作品也或显或隐地写出了革命新生力量的探索、觉醒或反抗。鲁迅等人对革命的理解和态度不尽相同,处于时代动荡中的他们也并不能预见未来,但统治当局的腐朽与残酷,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使得他们转而另寻出路,他们作品中的进步革命力量,如划破黑暗夜空的一星微光,成为惨淡现实的一抹亮色。
鲁迅等人的作品抛弃了对法治的乌托邦幻想,而代之以现实主义姿态。从这个意义上,同时代的侦探小说建构的是关于法治的理想状况,侦探的主持公道、助善惩恶给民众提供了一个疏通的渠道,起到了画饼充饥的作用。虽然也有现实批判,但侦探通过科学的手段、严谨的分析、完整的证据、合理的逻辑,侦破了一个个复杂疑难案件,这本身就是对法治精神的阐释,是对法治所代表的公平正义的伸张。因此可以说,侦探小说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展示着超越于现实的法治理想。新文学则不同。鲁迅等人通过创作如实呈现了法治缺席下的水火倒悬,将对法治缺席的省思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呐喊与彷徨、挣扎与痛苦中,提示着中国的出路,他们是时代的觉醒者。
结 语
20世纪上半叶,一方面是混乱的政治环境,使得诸多法律形同虚设;另一方面是法治思潮风起云涌,法治的种子广为散播,二者的博弈构成了作家笔下不同的法治景观,清末立宪题材小说、新文学、通俗文学(侦探小说),都有关于法治的书写与表达,其中尤新文学现实主义色彩最为浓厚。鲁迅等人的创作再现了旧中国法治缺席的困境与失序,一个个社会悲剧映衬出法治的缺席,隐含着法治应该存在的线索,法治相关事件和问题渗透在作品的角角落落,比如一部《老张的哲学》,便涉及选举、债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男女平等、言论自由、特权意识等诸多法治相关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可以管窥当时的乱象。“现代的生活,它的样式,它的内容,我们要取严肃的态度,加以精密的观察与公正的批评,对于它的不公的组织因袭的罪恶,我们要加以严厉的声讨。这是文学家的重大的责任。”34新文学作家以笔代戈,奋笔疾书,誓要打破虚伪、罪孽、丑恶的现状35,他们以决绝的批判、毫不妥协的省思否定黑暗时代的非人折磨、非法残害,而正是这种批判与省思在黑暗中激励人们寻求新的方向。
注释:
1 孙中山在南京答《大陆报》记者问(1912年1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页。
2 张东荪:《法治国论》,《庸言》第一卷第二十四号,1913年。
3 鲁迅:《离婚》,《语丝》第五十四期,1925年。
4 5 老舍:《老张的哲学》,《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十二号,1926年。
6 老舍:《骆驼祥子》,《宇宙风》第四十一期,1937年。
7 茅盾:《子夜》,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549页。
8 9 11 (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3、305、311页。
10 《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1935年),《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77页。
12 《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十二号,1906年。
13 徐家力:《论民国初期律师制度的建立及特点》,《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
14 《律师章程》(1927年),《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629页。
15 16 30 31 罗隆基:《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新月》第三卷第八期,1930年。
16 17 老舍:《离婚》,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版,第185、322页。
18 参见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1924年4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十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32页。
19 [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孙增霖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20 [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4页。
21 曹禺:《原野》,《文丛》第一卷第五号,1937年。
22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1936),徐辰编著:《宪制道路与中国命运:中国近代宪法文献选编(1840—1949)》(下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8页。
23 24 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上册),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24、27页。
25 刘半农:《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346页。
26 34 35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77、177、177页。
27 叶绍钧:《创作的要素》,《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395页。
28 29 李大钊:《新的!旧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刊物目录中,文章题目为“新的!旧的”,刊物正文题目为“新的!旧的!”)
32 陶履恭:《我们政治的生命》,《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1918年。
33 李钊(李大钊):《大哀篇》,《言治》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