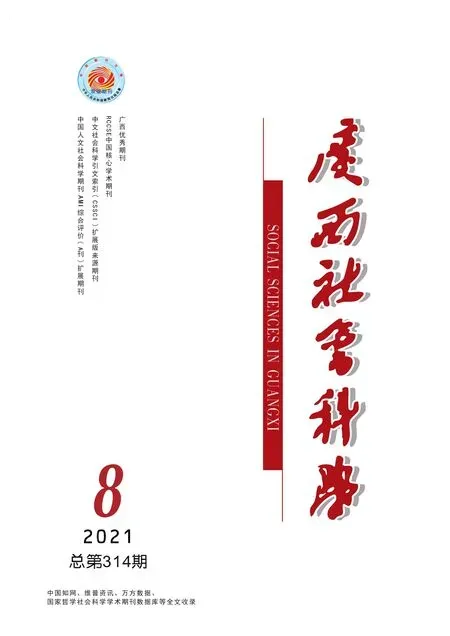《吕氏春秋》中的“公天下”思想管窥
2021-04-15张文渊
张文渊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 哲学教研部,广东 广州 510053]
公天下论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命题,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价值追求和理性期盼。启继禹立,公天下转向私天下,以君主世袭为核心的家天下成了现实。中国先贤并没有放弃对公天下理想的追求,在承认现实、认肯君主的基础上,对走向公天下作出了深刻的哲学思考和制度设计,集中体现在君道论上。因君主世袭甚至专制,公天下远离历史舞台中心,要“恢复”公天下,从限制君权、引君“向公”着手无疑是最直截了当、最关键有效的。早在先秦时期,儒、墨、法甚至道等诸家围绕君主何以产生、理想君王如何、如何做好君主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天下思想进行了相应阐释。
秦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君主专制更加凸显,家天下往前跃步。秦并六国前后,家天下现实与公天下理想之间的矛盾加剧,进一步激发了当时有识之士对公天下的思考。成书于帝国统一前夕的《吕氏春秋》,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公天下思想作了深入探讨,通过从立君、选君、为君及事君等四个方面展开分析,就解决立天下国家之主“为公”以及如何立天下国家之主“为公”、限制所立天下国家之主“为公”不“为私”以及如何限制所立天下国家之主“为公”不“为私”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说,达到了先秦公天下思想的高峰。
一、立君:为民利群
立君讨论的是君主何来、立君为何的问题。对此,无论是先秦诸子还是《吕氏春秋》都表明了君之所立因公不由私、为民不为己的立场,在君主产生之初就打下了公天下的深刻烙印,从源头上限制或规避君主私心自用、私欲横行。
《尚书》应该是现存最早讨论立君为公的文献,在《尚书·泰誓》中有这样一段话:“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1]意思是说,上天护佑下民要靠设置君师来实现;言下之意就是君主是由天所作、因民而立,其作用在于“代天佑民”。荀子承继了这一思想,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2],其意思还是上天为民立君。墨子认为,“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3],天下大乱是因为没有君主,君主的职责就在于为民平乱。主张专制集权的法家也认为立君是为了更好地治理天下,而不是为了实现君主个人之私利,“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4]。总的看来,先秦诸子对立君问题的讨论虽有所差别,但核心观点都是君主因民而立、为民而设。在这样的观点中,民先于君,民是君主得以立的前提,没有民就没有君,君不为民则不得立。
《吕氏春秋》继承了立君为民的观点,并进一步发展出更加具体现实的立君利群的思想。该书明确提出:“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5]所谓“利而物利章”,俞樾认为“章”字乃衍文,“物”即“勿”也,于是他把“利而物利章”训为“利而勿利”[6]。陈奇猷则认为“章”为语尾词,相当于“焉”,“利而物利章”应训为“利而勿利焉[7]。不管“章”是否为衍文或者语尾词,都可以把“利而物利章”理解为“利他不自利”。《吕氏春秋》对此也作了进一步阐述:“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天子利天下,国君利国,官长利官”[8]。一国之君的设立不是让天下之人瞻仰推崇,而是要有利于、造福于天下之人。
《吕氏春秋》更从君主起源的角度详细论述了立君利群的思想。首先,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远古时期,个人无法单独生存。关于个人生存能力的有限性,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9]其次,群居是人类克服自身有限性、战胜自然界危险最有效的方式。人生而柔弱,其野外的生存能力不如自然界中的诸多生物,但现实生活中人却能“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究其原因在于群居。人类群居而互助,互助则共生,这是原始人类抵御自然界危险的最大法宝,但此时人类社会与动物的群居并无多大区别:“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10]从这种无别、无道、无礼、无便、无备的特征可知,群居只是为了生存,他们还不具备人类文明社会所独有的特征,因为他们之间既没有“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分,也没有“上下、长幼”之别和“进退、揖让”之礼。最后,群居的无序性促使君主的产生,在无别、无礼的群居生活中,人们会因为各种利益产生争执、争斗,“以力为尊,少长、贤暴相颠倒”的现象比比皆是,甚至发生相互残杀的情况,正所谓“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11]。因此,“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12],设立天子、国君非为自己,而是为了天下国家的利益,即“利而物利”,所以《吕氏春秋》说:“利之出於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於群,而人备可完矣。”[13]这里强调君道乃天下之利,意在表明,在君王与天下的关系上,天下百姓是“君道”维护的价值目标,而君权王位,则是维护天下百姓利益的手段[14]。
先秦诸子提出立君为民,认为君主因民而立、为民而设,已经暗含了君主为民谋利的观念,《吕氏春秋》则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立君利群的思想,把这样的观念直接摆到了台面上,强调从君主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君主必须为民利群,清晰化具体化确立了君主的为民责任和利群使命。如果说先秦诸子的立君为民是以口号式的断论在先民心中播下了立君为公的思想种子,那么《吕氏春秋》的立君利群则通过现实考察和严密论证推动了这颗种子生根发芽,进一步在立君的层面充实了公天下思想。
二、选君:比拟圣王
立君解决为何需要君主的问题,选君则进一步讨论需要怎样的君主问题。在古代中国的人治社会中,君王个人的政治操守和政治智慧直接影响国家政治的好坏[15],甚至决定国家存亡。因此,应该选什么样的人做君主或理想君主的标准是什么,成了先秦很多思想家重点讨论的内容。总体来看,先秦诸家和《吕氏春秋》都把圣王作为理想君主,希望通过高立圣王形象来引导君主“靠近”公天下。
孔孟崇古、推三代圣王为理想君主,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为代表。如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 巍巍乎! 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16]孟子则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17]两人对这些人的评价虽不一样,但在他们看来,圣王至少应该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德性高尚,二是博施济众。荀子虽法后王、隆礼重法,但把德性和功化作为圣王的标准与孔孟一致,故他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18]
墨子认为,圣王能够从“兼爱”“非攻”“尚同”“节用”等方面进行治国理政,能够“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9]。法家指出,圣王与普通君王的区别在于其能赏罚分明,令行禁止,“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20]。韩非继承了这种观点,“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21]。道家之所以把圣王作为自己的理想君王,是因为只有圣王才能真正体道。在它这里,道是最高的价值追求,无论是养身,还是治国,不过是“道”在具体事物中的体现,而真正能体道者的是身,治国只是以道养身之后的价值延续[22]。老子云:“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23]庄子也说:“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24]在道家看来,先身后国、身国同治是道家圣王观的核心内容,所谓“内以治身,外以为国”[25]。
《吕氏春秋》也把圣王作为其理想君王。在该书看来,圣王之所以异于普通君主,在于其能够应用“静因之术”体认天道,能够法天地,进而达到去私为公的目的。“静”是指去其心智,虚静以待。在该书看来,静而去智,方可言君道,“得道者必静,静者无知,知乃无知,可以言君道也”[26],虚静去智也叫“处虚素服”,“夫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27],“处虚素服”即“处虚服素”[28],作为君王,只有以虚无为本,无爱恶之心,才能“无智”“无能”,才能行无为之道,也才能使众。“因”是指因天顺时,就是法自然,也即无为之道。在该书看来,“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29],所以“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君王何以要“为少因多”呢,原因在于人之“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既然人的心智不足恃,那就该去心智之功能,“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去三者不任则治,三者任则乱”[30],“去视”“去听”“去智”就是顺天,就是无为,故该书说“无为之道曰胜天”,胜者、任也、因也,胜天即因天、法天[31]。“静”与“因”是一体两面,“静”是为了限制君主的个人之私,是为了因天之公,而“因”是“静”的必然结果,二者都统一于无为之道,“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32]。
我们同时应当看到,在《吕氏春秋》中,“静因之术”即“无为之道”,“君也者,以无当为当,以无得为得者也”,“故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33],但“无为之道”的“无为”并非不为,它是强调君臣之间的分工,“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34],其目的是希望君王执“无为”之术获臣“有为”之功。在该书看来,“民之治乱在于有司”[35],国家之治理在于“千官尽能”[36],所以,圣王必须具有用众的能力,“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37]。能否辨别、选拔和任用贤人是圣王用众的前提:“古之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得其经也。”[38]“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39]该书还指出,为选到理想的人才,君王应该遵循“外举不避雠,内举不避子”[40]的基本原则,采用“六戚四隐”“八观六验”的识人方法,来寻找并任用真正的贤人,“此圣王之所以知人也”[41]。由此可知,《吕氏春秋》的作者更多的是从君主无为、选贤用贤及臣子有为的角度来论述其圣王观。
大一统帝国即将到来,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日益复杂的管理职能需要一个大权集于一身的君主来强力操纵与推动,但整个国家被带偏走向没落的风险也相应增大,一种能胜任国家新需要的新君王呼之欲出。在这样背景下诞生的《吕氏春秋》对选君之道的思考注定更加复杂,既有现实的考虑又有理论的建构,既吸收儒道之君道观又统摄法墨之君王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吕氏春秋》的理想君王就是适应现实需要统合道、儒、墨、法四家圣王的综合体。
三、为君:贵公去私
为君讨论的是做好君主的主要原则问题。如果说立君和选君主要还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那么为君则涉及具体实操问题。如何让大权在握的君主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持身公正不偏私,是关乎公天下理想能否落地的问题。先秦诸子和《吕氏春秋》对此问题给予高度关注、作了深入思考,形成了为君者需崇尚公而抑制私的主流观点。
儒家主张立公去私是实行王道政治的重要条件。《尚书·周官》提出君主应该“以公灭私”,才能做到“民其允怀”[42]。孔子认为,国君处事公正、以上率下,才会政通人和,“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43]。孟子认为,公正、公平、公心是实行仁政的前提,“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44],只有“正经界,均井地”[45]才能开始谈仁政,“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因为“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非仁君所为,所以“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46]。荀子认为,公既是君主必备的政治品格,也是臣子做事的榜样,因为“人主不公,人臣不忠”[47],“上公正则下易直矣”[48],如果“上好曲私,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偏”[49],所以他主张君主应该达公而息私,“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50]。墨家从兼爱的角度出发,主张君主应“举公义,辟私怨”[51],君主只有做到“不偏不党”“不党不偏”,才能“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52]。法家从法的公平性出发,倡导公而否定私,如商鞅认为,“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嫉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所以他说:“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53]韩非发扬了商鞅的观点,指出“主之道也,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54]。道家站在“以道观物”的高度,认为治理天下应该顺应自然、顺应道,“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55],因为天道是公而无私的,“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56]。
《吕氏春秋》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主张君主应该贵公去私。何谓“公”,高诱训“公”为“平”[57]。以平训公固然正确,但还不完整。在《吕氏春秋》中,“公”除了有“平”即公平之意,还有公心、公正之意,其本质是指君要以天下百姓为务。私指私心、私欲及个人好恶,实质是指君主个人的一己之利[58]。该书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时要以天下百姓之利为务,放弃个人之私利,这不仅仅是君主职责所在,也是其内在的道德品质。
该书首先指出,无私是天地万物之道。它提出了“四无私”,“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59],认为天、地、日月及四时因其无私,所以万物才得以生长。《吕氏春秋》更是以天道论人事,指出天人一体、人应该法天地[60],“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61],认为无私既是天地之大德,也是君主的最高政治品德,抑或说君主无私的政治品德源于天地无私之大德。其次,圣人治理天下的诀窍在于至公。《吕氏春秋·去私》中有这样一段话:“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62]在它看来,尧舜之所以为尧舜,之所以为圣王,在于他们至公的政治品质。是“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饰服,私利而立公,贪戾而求王,舜弗能为”[63],如果有私心,有贪戾之心,即使像舜这样的圣人也绝不可能把天下治理好,故该书得出这样的结论:“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於公。”[64]天下太平,万物安宁,源于天子的公心、公平和公正的政治品德。最后,君王治理国家必须公而无私。《吕氏春秋》指出,置天子也好,置国君也罢,其目的是为天下百姓服务的,而不是以此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65]。它进一步指出,以天下为务不仅是君王平治天下的政治准则,还是获得王位并维护自己权力的前提条件[66],“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万民之主,不阿一人”[67],一视同仁则拥有君王之职,厚此薄彼就失去君王之位,所以君主必须贵公去私。
儒、道、墨、法都倡导公而忘私,要求君主在政治实践活动中保持公心、公平与公正[68],以民利为务,只是各家具体论证的侧重点不一样,或就人事谈论人事,或着重论述天道。《吕氏春秋》则贯通天道与人事完整地阐述了贵公去私的思想,既有天道做支撑,又有人事准则可操持,对君主公私问题的阐释具有总结性。
四、事君:助势行道
禅让制的结束,意味着道与势的分离①在讨论《礼运》“天下为公”的主旨时,郑玄的解释是:“公犹共也,禅位授圣,不家之睦亲也。”孔颖达认为:“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是也。”参见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8-659页。,士君子与君王分别成了道的承担者和势的拥有者,道势关系由是复杂。伴随着道势关系而凸显的君臣观问题,成为政治哲学中的核心内容。“为君难,为臣不易”[69],因此,臣在事君过程中,是扬势还是尊道,抑或说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成了先秦思想家们探讨的重要课题。
“以道事势”是儒家处理君臣关系的态度。孔子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70]是理想的君臣关系,如不行,则“以道事君,不可则止”[71]。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认为君臣在人格上平等,应该互敬:“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72]对此,萧公权指出,孟子思想中的“君臣之间,各有尊贵。臣之于君,一视其相待之厚薄而定其相报之厚薄。恩怨分明,进退裕如”[73],在君臣平等的基础上,孟子还提出了“所就三,所去三”[74]的事君原则。荀子虽然尊君,但他却对“态臣”“篡臣”“功臣”“圣臣”作了明确区分,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谏”“争”“辅”“拂”四种佐君之方,并进一步指出:“从道不从君”是臣事君之前提[75]。
“以道迎势”是法家对待君臣关系的手段。在法家,道屈从于势,如慎到认为“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故无名而断者,权重也”[76],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更是指出君主之所以能使臣,在于其“权重位尊”[77],认为“势”是“胜众之资”[78],是“人主之渊”[79],是“人主之爪牙”[80],是不肖制贤的资本,“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故短之临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贤也以势”[81]。在法家这里,道以工具和手段的身份为势服务。
“以道避势”是道家解决君臣关系的方式。在道家这里,道既是其最高的价值追求,也是其精神慰藉。它主张君臣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老子》提倡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而《庄子》提倡“曳尾涂中”的自在与逍遥。
《吕氏春秋》“助势行道”的观点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与发挥。在它看来,臣事君是为了助君王行为公之道,是帮其完成“以民为务”的政治理想。“贤人之不远海内之路,而时往来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为务故也”[82]。因此,臣事君,必须站在立公去私的角度,以利天下为目的,辅佐君王实现其君王之道。于此,该书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助势行道”的事君问题展开论述。
第一,君寡臣众。君王虽然掌握了治国之道,但天下却不能靠君王单枪匹马去治理[83],必须有贤人的辅佐。“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84],“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国不虚存,必有贤者”[85],治天下之所以需要贤人,首先是因为君主的智能是有限的,而众人的智能是无穷的,君主要治理天下,就必须得众人之力[86],“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於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87]。其次,圣王的伟业是在贤人的帮助下取得的,“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88],像舜、禹、商汤、周武王这样“王天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仁义被后世”的圣王,也是得到贤人的辅佐,才成就其不世之功的。最后,普通君王如有贤人辅佐,也可以完成圣王的伟业,留名青史,“故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89]。
第二,恃君忠廉。《吕氏春秋》认为,士君子要实现其政治抱负,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与君王保持良好关系,这是因为“定于一”的时代与诸侯并立时期的社会政治环境完全不一样。在“系于一尊”的帝国,行道只能恃君,只能依君,换句话说,君在士君子的帮助下实现其道。《吕氏春秋》首先指出,事君必须以尽忠为前提,尽忠是人臣之本分,“为人臣弗令而忠矣”[90],“为人臣不忠贞,罪也”[91],“事君不忠,非孝也”[92]。其次,它对忠进行了区分,指出“利不可两,忠不可兼”,所谓“忠不可兼”是指忠有大忠、小忠之分,而“大忠”才是君臣所需要的,因为“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小忠,大忠之贼也”[93],所谓“大忠”就是不枉法事君,“事君枉法,不可谓忠臣”[94],就是敢于直言,“故圣王之贵豪士与忠臣也,为其敢直言而决郁塞也”[95],甚至敢于谏君之过,“故忠臣廉士,内之则谏其君之过也,外之则死人臣之义也”[96]。但该书的作者也知道,臣子能做到直言、谏过并非易事,因为“夫忠于治世易,忠于浊世难”[97],非普通人可以做到。
第三,当理缘义。《吕氏春秋》指出,士君子何以能够“助势行道”,在于其高尚的节操和独立的人格,否则就不能谏君之过,更不可能达到“以民为务”之目的。该书认为,事君之士人无论穷困与富贵,都应该志于道,以义为行动之准绳,“贤者之事也,虽贵不苟为,虽听不自阿,必中理然后动,必当义然后举,此忠臣之行也”[98],应该把对道的实现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而不是执着于物质的享受,“天下之士也者,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若也。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安虽长久,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99]。因志于道而导致穷困者并非无能之辈,反而是士君子高尚情操之表现,“君子之自行也,动必缘义,行必诚义,俗虽谓之穷,通也。行不诚义,动不缘义,俗虽谓之通,穷也”[100]。当理义与利益所产生的矛盾不可调和时,为了理义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101],非如此,不足以保证士君子助君行为公之道。
由上可见,“助势行道”是《吕氏春秋》中道势关系的核心内容,它希望君王在贤人、贤臣的帮助下,实现为公不为私的政治理想。
五、结语
《吕氏春秋》的作者会通先秦诸子,整合新的政治理念[102],希望通过限君、助君等方式,在系于天子、君主“一天下”政治框架之中,实现公天下的政治理想。正如萧公权所说:“吕氏反对专制,立论至国透辟,汉人中鲜足与之相拟者”,认为“其最大之贡献似在建议种种方法以限制君主,使其不得自恣”[103]。然在两千多年前的专制主义社会里,这种理论不会也不可能得到实践,但是这种从远古时期就流传下来的思想却成了中国思想家们几千年来的精神追求,如梁启超曾说:“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下,行民本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欧美人观中华民国粹然成立,辄疑为无源之水,非知言也。”[104]因此,《吕氏春秋》所提出的政治理论和政治理想,值得我们仔细探寻与研究,而它在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也不容抹杀[105]。
参看文献:
[1][42]十三经注疏·全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80;236.
[2][18][47][48][49][50][75]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595;481;275;379;273;282;624.
[3][19][51][52]孙诒让.墨子间诂[M].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74;115;47;278.
[4][76]许富宏.慎子集校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16;9.
[5][6][7][8][9][10][11][12][13][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59][61]62[63][64][65][67][82][84][85][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吕不韦.《吕氏春秋》新校释[M].陈奇猷,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330;1335;1335-1336;1331;1330;1330;1331;1331;1330;1059;1666;1669;933;1076;152;1103;1060;1076;719;1060;236;97;629;56;163;56;45;56;46;45;45;45;1473;1523;710;236;97;236;209;874;737;872;1256;1382;1331;585;1592;1345;1254;629.
[14][15][57][58][60][66][83][102]李宗桂,陈宏敬.《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54-59.
[16][43][69][70][7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82;127;136;30;116.
[17][44][46][72][74]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142;165;108;171;275.
[20][53]蒋礼鸿.商君书锥指[M].北京:中华书局,1986:113;85.
[21][54][77][78][79][80][81]王先谦.韩非子集解[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201;128;388;431;244;470;208.
[22]阚红艳.道家视域下的“身国同构”与“内圣外王”[J].江淮论坛,2018(3):81-85.
[23][56]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108;121.
[24][55]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800;235.
[25]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185.
[45]郭齐勇,陈乔见.孔孟儒家的公私观与公共事务伦理[J].中国社会科学,2009(1):57-64.
[68]陈乔见.先秦诸子公私之辨的本义及其政治哲学内涵[J].中原文化研究,2013(4):17-25.
[73][10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63;224.
[86]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53.
[104]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长沙:岳麓书社,2010:6.
[105]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7: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