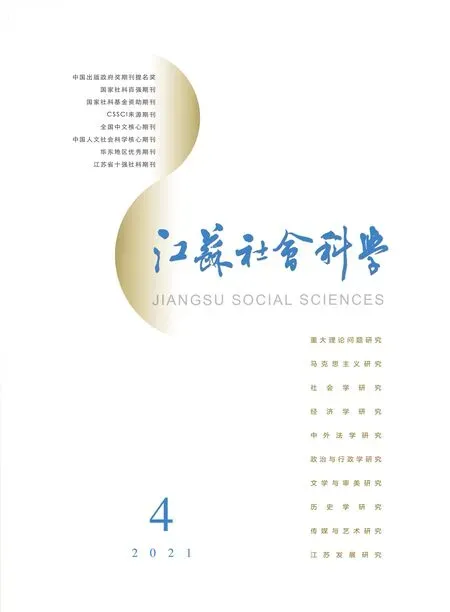青年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中的生命观及其当代价值
2021-04-15贺银垠
贺银垠
内容提要《〈伦理学原理〉批注》包含丰富的生命哲学。在其中,毛泽东主要从天人相通的自然主义视角看待人的生死问题,在中国古代生死观与近代西方哲学的碰撞交融中发展出生死自然、发达身心和超拔个人的独特的生命观。青年毛泽东的生命观源于对近代中国历史任务的深刻反思,体现出其自觉将个体生命与争取民族生存权、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紧密结合的鲜明的现实旨趣和价值关怀。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中的生命观对于青年树立理性的生命观、促进个人全面发展、实现个人和集体价值的统一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十八大以来,党将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毛泽东青年时代对生命价值的求索反映了一代优秀共产党人成长成才的心路历程,折射出青年共产党人将个人生命和民族振兴密切融合、互相促进的人生理想。1917 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而中国正经历着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西方伦理学课上,老师杨昌济用德国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作为教材。作为学生的毛泽东花了近一年时间将全书通读,留下超过12000字的批注。《〈伦理学原理〉批注》(以下简称《批注》)作为青年毛泽东独特生命观形成的关键性文本之一,对于新时代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典型教育意义。
一、生死自然:宇宙人生的基本规定性
生命问题之所以被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视为质疑问难的关键问题,是因为它不仅是个人道德锻炼的修养功夫,而且切合中华民族救亡与启蒙的紧迫现实需要。从个人修养来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及配套的旧式教育给人们灌输恪守等级尊卑、顺从家长权威的奴隶思维,使人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和积极进取之心。对此,毛泽东批评道:“惟少年亦多不顾道理之人,只欲冥行,即如上哲学讲堂,只昏昏欲睡,不能入耳。死生亦大矣,此问题都不求解释,只顾目前稊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1]《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第73页,第171页,第171页,第242页,第175—176页,第176—177页。从近代国家救亡图存的具体实践来看,鸦片战争后学习器物与文化、改革与革命、宪政与共和等各种主张,“你方唱罢我登场”,掀起一时热潮又以失败告终。毛泽东认为,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领袖既无内省之明又无外观之识,他们所领导的改革和革命运动不过是在旧有政治体制基础上进行细枝末节的修补,未能抓住世界的大本大源,因而是失却根本方向的盲目冲动。其中,大本大源即指哲学和伦理学。“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2]《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第73页,第171页,第171页,第242页,第175—176页,第176—177页。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增进个人修养和挽救民族命运都要求将生命问题视为重大的哲学、伦理学问题,进而为巩固理想信念提供根本依据。
生死自然是青年毛泽东生命观的核心。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自然属性是人之为人的第一属性。人的生命过程首先是一种自然现象,生死变化遵循着自然的普遍规律。“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3]《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第73页,第171页,第171页,第242页,第175—176页,第176—177页。由此可知,毛泽东是从宇宙自然出发来理解人的生命和生死,带有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色彩。受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影响,毛泽东认为,世界是物质和形式的结合,物质本身不生不灭,而物质存在的形式变化不居。人的生死不过是物质和精神聚与散的结果,物质聚而为人,解散以后又重新聚合为其他形式。“且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即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4]《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第73页,第171页,第171页,第242页,第175—176页,第176—177页。事物形式的聚散变化、接续构成了时间流变和人类历史的阶段性发展。“余意以为生死问题乃时间问题,成毁问题乃空间问题。世上有成毁无生死,有空间无时间。”[5]《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第73页,第171页,第171页,第242页,第175—176页,第176—177页。总之,从形式上论,人遵循自然的必然性,有生有死,不可悖逆;从物质本体上论,人同宇宙自然一样只有形式变化,实则不生不灭。此时,自然主义的生命观是毛泽东以豁达乐观心态面对生命和生死的主要哲学基础。
毛泽东关于既生既灭、不生不灭的自然生命观同样适用于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关切。在谈到民族生存时,泡尔生以人的生命类比国家发展,认为国家和民族作为宇宙的一部分必然遵循生死自然的规律,随着历史经验不断积累、社会风俗习惯逐渐固化,国家和民族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就日趋衰减,不免走向死亡。泡尔生说:“征之历史,国民皆不免有老衰萎缩之时,若思惟行为一定之习惯,若历史沿袭之思想,若构造,若权利,与时俱增。于是传说足以阻革新之气,而过去足以压制现在,对待新时代之能力,积渐销磨,而此历史界之有机体,卒不免于殄灭。”[6]《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第73页,第171页,第171页,第242页,第175—176页,第176—177页。毛泽东大为感叹,中华民族正处于此地位。但与泡尔生不同的是,毛泽东站在自然主义宇宙观的立场进一步阐述了国家死与生的辩证规律,奠定了他求解中华民族生存问题、恢复民族生命力的积极心态。“国家有灭亡,乃国家现象之变化,土地未灭亡,人民未灭亡也。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7]《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第73页,第171页,第171页,第242页,第175—176页,第176—177页。在他看来,近代以来中国面临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和封建统治分崩离析的双重压力,正处于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国灭族亡的生死问题现实地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是民族之忧。与此同时,民族危难只是国家形式和建制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征兆,制度形式的变化不仅不意味着中华民族本身的覆灭,而且是扭转民族危机、重塑民族生命的契机。通过大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设新的国家,是使中华民族无忧的道路。民族命运之忧与无忧的辩证思维,正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理论,既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又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毛泽东一方面深受德国哲学和伦理学影响因而发展出二元论的哲学观,另一方面将生死的思考牢固扎根于中国传统生命观之中,在中西哲学和伦理思想的对话碰撞中鲜明地迸发出老庄哲学的光芒。众多中国先哲主张从物质的自然聚散变化中理解宇宙和人生,早期的天命-道、五行-气等理论莫出其外。老庄哲学的道法自然和辩证思维则将古代生死自然的理念发挥到极致。毛泽东关于生死自然和生死统一的理解大多来源于此。《批注》提出:“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1]《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245页,第575页,第75页,第116—117页,第178—179页。不难看出,《批注》中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生命哲学带有显著的自然主义和相对主义色彩,距离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命观还有相当距离。
二、具足自我:个人主义的生命追求
尽管生死是人不可僭越的自然规律,但并不意味着人应该放任生死。在中国古代贵生思想和德国意志论哲学的影响下,毛泽东对自己和国人的生命主张进行了深入思考,他重视意志和自由的价值,强调精神独立和个人自决,倡导过积极有为的人生。
青年毛泽东对个体的“我”的主张并非德国意志论和康德伦理思想的复现,而是在针砭近代中国人思想弊病基础上进行的自主性发挥。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历史的国家,文化习惯和社会心理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专制统治遗留下的弊病不可能随着制度变更马上消失殆尽。梁启超提出过一个观点:“其在古代,政治之汙隆系于一帝王,教学之兴废系于一宗师,则常以一人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渐进,而重心移于少数阶级或宗派,则常以若干人之首领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益进,而重心益扩于社会之各方面,则常以大规模的团体之组织分子为‘历史的人格者’。”[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55页。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理解,国人在长期封建统治中形成了以一人为“历史人格”的国民心理,丧失了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性意识,在政治上满足于身处被治者的地位。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封建思想对个性的压抑,直指当时社会上存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3]《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245页,第575页,第75页,第116—117页,第178—179页。等问题,人们因此在纷乱交替的社会变革中失去辨别能力和主动意识,“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不亦大可哀哉!”[4]《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245页,第575页,第75页,第116—117页,第178—179页。。由此,他分析认为,近代中国数次变革的失败是由于革命是局限于少数人参与的活动,没有真正引起人民群众的理解和同情。
《批注》中对于人如何生的主张是精神上的个人主义。泡尔生原文谈到“彼等厌忌往昔之思想及生活法式,为以盲导盲,必欲以其独立之意见,别辟世界”之时,毛泽东大发感叹,“吾国二千年来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此吾国今时之现象”[5]《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245页,第575页,第75页,第116—117页,第178—179页。。毛泽东根据这段原文热烈赞扬泡尔生的个人主义主张,大有引为知己的意思,实则泡尔生的真实意图是调和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而毛泽东站在己方逻辑上视泡尔生为个人主义者,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个人之独立和自由的热烈渴盼。当然,毛泽东所倡导的个人主义虽出于近代资产阶级精神,却完全不同于自私自利的狭隘个人主义,而是指精神上的人格独立和自决。其核心观念在于“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6]《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245页,第575页,第75页,第116—117页,第178—179页。。
青年毛泽东以作为个人性主体的“我”来彰显人格的独立性,主张以“我”为中心,“我”的价值高于宇宙一切事物。“我”是指小我,即个人,与集体概念相对。毛泽东认为,从前主张无我是错误的,现在才知道一定要主张有我。“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尤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尤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尤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1]《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4页,第125页,第218页,第74页,第76页,第202页。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个人和集体是相互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既不存在抽空个人的集体,也没有脱离集体的个人。但此时毛泽东认为,必须强调个人的地位和价值优先于集体。“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2]《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4页,第125页,第218页,第74页,第76页,第202页。毛泽东主张的个人本位思想,实际上构成了对中国传统社会家庭本位、群体本位和国家本位的逆反。依照马克思以人的存在方式划分出的三大社会形态[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中国古代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制造出了人对人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家庭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抹杀了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主张国家和家庭的利益高于个人价值,片面强调个人对家庭和国家的义务责任,炮制出了“三纲五常”等虚伪道德。毛泽东坚决反对封建道德,对贬低和奴役个性的伪道德开展了猛烈抨击。他指出,个人的地位和价值高于一切,人的所有行为选择和道德评判都应以利己为唯一根本原则,奴役个体和个性的黑暗制度和封建思想应该被彻底废除。当然,毛泽东对“小我”和利己原则的肯定以恢复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为限度,并不意味着导向彻底抛弃国家和集体的无政府主义方向。在强调人具有自我保存本能的基础上,他肯定了人先天具有推己及人的良知。也就是说,利己与利他是一致的,利他作为内在良心天然地镶嵌在个人的利己原则中,利他本身也就是个人通达利己的途径。毛泽东的自利以利他、利人以利己的伦理主张实际上是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君子人格和墨家兼爱思想的新形式。
毛泽东指出:“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4]《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4页,第125页,第218页,第74页,第76页,第202页。这就是说,发达身心、具足生活就是人作为独立个体的道德律令。并且,伦理学上追寻的人生正鹄没有统一标准,每个人应当根据自身资质秉赋的实际条件来调整发展自身的目标和方式。就毛泽东个人而言,立下真志、矢志践行的就是发达身心和个性。在给师友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中,毛泽东表达了自己关于立志的愿望和苦恼。在他看来,立志不是随便的事情,盲从大流或者渴羡他人都不是真正的立志。所谓立志必须经历认真钻研,得到一种关于大本大源的真理,然后坚定对其的信仰。“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5]《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4页,第125页,第218页,第74页,第76页,第202页。正因为如此,那时毛泽东十分苦恼,“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6]《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4页,第125页,第218页,第74页,第76页,第202页。。在《批注》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追寻志向的步骤。“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7]《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4页,第125页,第218页,第74页,第76页,第202页。知之、信之、行之体现了毛泽东反对盲从、谋定后动的处世原则,也是毛泽东科学认识论的萌芽。如我们所知,尽管毛泽东对于立志有如此强烈的渴望和自觉,他实际上是在研究、比较和试验思想界各种主义后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才树立了真正的志向,并像他所说的,坚定不移地践行了社会主义理想。
三、超拔个人:舍我其谁的浪漫品格
《批注》中的生命观既与中国古代传统中贵生轻死的生死观一脉相承,又刻上了湖湘士风的深刻烙印。在面对生死大考时,毛泽东始终以贵生善生为前提强调珍惜生命和自我保存,同时将人生理想从狭隘的个人利益之中超拔出来,以理性思考赋予生死之变以丰富的浪漫色彩,并彰显出在民族国家大义面前豁达生死的态度和乐于牺牲的精神。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保存自我及延续种族是人的本能,人应该遵从生物天性保存自身、强劲身心,而不应荒废身体、轻视生命。这与儒家珍视人的生命、过积极有为生活的基本伦理取向和人生价值导向是吻合的。有学者认为:“儒家的生死观具有强烈的功利、伦理色彩,在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总要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与功名利益紧紧地交缠在一起。”[1]徐宗良:《当代生命伦理的困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儒家生死观的实用取向,一方面可以被视作世俗经验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被视为儒家君子超越生命有限性的一种途径,即借助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使有限的个体生命获得永恒价值。尽管毛泽东接受了传统生死观中贵生的基本主张,此时受近代西方思潮熏陶的他却是从人的生物性本能出发来论证自我保存的价值。《批注》提道:“人类者,兽格、人格并备。”[2]《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第219页,第5页,第58页,第175—176页,第174页。毛泽东认为,人作为智识更发达的动物保有动物自我保存的本能,因此主张非自杀、反对不珍重身体的行为。围绕长沙新娘赵女士花轿自杀事件,毛泽东提出,自杀仅在个人层面上具有自我保存的价值,即“消极之自杀,亦系为自存。因彼于遇事不能解决或愧悔其前日之罪过,以谓与其生不如死,故以一死了之。此生不如一念,即彼之自我也”[3]《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第219页,第5页,第58页,第175—176页,第174页。。但从根本上来说,自杀导致身体死亡违背了自我保存的本能,不过是由于外部环境的迫使,在社会伦理层面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体现了毛泽东把个人生命和国家社会发展联系在了一起,尝试从政治革命入手寻找个人生命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具备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现实取向。
在“非自杀”的基础上,毛泽东主张,青年人应该强健体魄、磨炼精神,达致身心具完的目标。1915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同学易昌陶因病逝世,他写作两首(其中一首篇幅长达40行)五言古风悼诗表达哀思。“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4]《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第219页,第5页,第58页,第175—176页,第174页。,明确表达了毛泽东对同学因体弱早逝、无法实现救国抱负的遗憾。这件事情促使毛泽东开始反思学校重德智轻体魄的教育方针,列举历史上许多大才大智者因身弱或早逝导致德智不显的例子来勉励自己勤加锻炼。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的著名文章《体育之研究》更把体育锻炼和个人修养与扭转民族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5]《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第219页,第5页,第58页,第175—176页,第174页。他认为,体育锻炼可以强健体魄,增强意志,改善民质,彻底改变中国国力衰弱、武风不振、民族体质孱弱的现象。为此,他还发明了一整套独特的体育锻炼方法,以达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目的。
当然,毛泽东强调的自我保存主要针对本能和实效的层面,他对待生命的基本态度无疑仍是基于理性思考基础上的浪漫主义——死又何惧。毛泽东在《批注》中对生命的长度和厚度展开了深刻思考。他提出:“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6]《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第219页,第5页,第58页,第175—176页,第174页。即是指,既然组成身体的物质永远不会灭亡,那么死后人的身体也不会消失,不过是以另外方式存在于其他物质形态中。而人之所以恐惧死亡,只不过是因为生死之间的跨度过大,且人对死亡以后的未知事物总是心生恐惧。此时,毛泽东尽管没有直陈死亡的意义,却将死亡称为奇事、奇境和奇遇。在他的奇人眼光中,死亡不仅不带有痛苦和悲情色彩,反而是雄壮奇异的景象。“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知引以为壮乎!”[7]《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第219页,第5页,第58页,第175—176页,第174页。
基于勇敢面对死亡、不惧死亡的浪漫想象,毛泽东对生死之问的回答是:敢于牺牲、乐于牺牲,在杀身成仁中发达个性。人生在世不断趋向不可避免的终点,死亡时刻警示着人之有限性。因此,人的一生始终伴随着对生命有限性的焦虑和超越个人死亡的冲动。古今中外哲人为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超越生命的有限性提出了诸多方案,却始终无法超出借助宗教、作品、事业等外物延续生命的范围。比如,泡尔生认为,个人死亡而人所留事业“不随之而俱死也,曾何憾焉”[1]《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页,第171页。。其实,将超越死亡的期望寄托于外物之上仍是一种精神固执,没有实现对生死的真正超越。毛泽东在泡尔生原文旁批注:“即随之而俱死亦何憾焉。”[2]《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页,第171页。这种豁达态度构成了毛泽东对中国人长期以来精神不独立、为外物所奴役的一种反叛。
总体上,青年毛泽东在《批注》中始终把对个人生命的思考与近代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生死存亡紧密结合,以争取民族生存权作为个人生命的道德义务,同时也将社会变革作为个人生命和自由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他从近代民族国家生死利益的角度来考量个人生命,从哲学和伦理学层面解决了泡尔生抛出的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两难问题,实现了在服从民族国家利益的实践活动中追求个人独立性和自我价值发展的贯通。尽管以个人为立足点的生命观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只占据一小段,但生死自然和生死统一的理念深刻地影响着青年毛泽东的哲学观念;精神上的个人主义则是青年毛泽东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群众史观的萌芽,具有很大的进步性,而最为根本的关于生命的乐观、自决、辩证、超然的态度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印痕。尽管《批注》时期的毛泽东尚未接触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的思想并不完全成熟正确,但是展露无遗的现实情怀决定了毛泽东的生命观必定不拘束于纯粹思维领域,而要到中国革命的风浪中践行理想。在确立个人自决基础上个体与民族命运相统一的生命价值后,毛泽东投身于中国社会大变局和民族独立振兴的试验场,寻求个人价值和民族利益的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我们应该注意,革命战争时期大我(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取代小我(个人的生命和价值)进入毛泽东的主体论域中,不应该视作大我对小我地位和价值的吞噬,而是小我发达个性、践行理想、利人以利己理念的升华。到那时,毛泽东生命观的探讨范围已经从自然意义上的生命扩展到象征意义上的生命,其生命观承载着辩证唯物主义、反教条主义、走群众路线、爱国主义教育等诸多内涵和目标,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理论资源和情感养料。
四、毛泽东青年时期生命观的当代价值
培育正确的生命观是在现代社会多元复杂的文化氛围中处理好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所特别需要的,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毛泽东青年时期的生命观是基于救亡图存之时代任务和修养身心之人生旨趣而形成的思想结晶和伦理向标,它包含的关于生命价值的普遍尺度、原则和方法,在当今时代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散发着熠熠光辉,为有志于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树立理性的生命观提供了精神导引,为青年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价值树立了榜样,为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和超拔指引了方向。
第一,为树立理性的生命观提供了精神导引。理性的生命观不仅是任何时代个人正确看待生命、追问个体同一性的内在需求,而且是现代社会中个人特别需要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现代化的高速转型和发展期,全球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使人们得以享受丰富的现代物质文化成果,与此同时也将人们充分暴露在物化、原子化、虚无化的现代性弊病之中,导致人们在多元社会中无所适从,耽于物欲横流的享乐,轻视和荒废生命,这对当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造成严重侵蚀。毛泽东在认识到生死是不可逾越的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注重以拓展生命厚度、丰富生活内涵的方式克服个人生命的有限性,形成积极有为、置生死于度外的价值导向。他主张,人即便受自然律支配仍有自由意志,可以通过遂行意志、发达个性、磨砺品行来拓展生命的厚度。人如果树立真正的志向、践行理想,活着的每一天都有价值,就无所谓留有遗憾、惧怕死亡。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上寿百年亦可也,即死亦可也”[1]《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6页,第175页。。相反的,人一旦浑浑噩噩、不对自己负责,那么生命长短与否也没有很大区别。“其未达具足生活之正鹄因有此故,因有此故而未达具足生活之正鹄,曾何憾焉?”[2]《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6页,第175页。对于当代青年人而言,应该树立理性的生命观要求——正视生命的有限性,培养健康的心理和态度,珍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尊重生命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双重客观规律性,准确认识现代社会个体成长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以踏实的自我培育和增进来回应生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和挑战;思索和确立远大的人生理想和志业,在把握时代脉搏和参与历史宏业中获得个人生命价值的延展。
第二,为青年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价值树立了榜样。社会的现代化也就是人的现代化,即人不断从物质的与精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个体和全人类自由的过程。经济政治现代化并不是人的自由解放的唯一基础,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价值实现仍是当今时代人的现代化的重要维度。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关于个人价值及其实现的主张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言仍不失其价值。人之本性大多趋利避害、喜乐恶苦,青年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善于发现抵抗的乐趣,有志于在磨砺锻炼中发达身心。相较于从战火硝烟中磨炼自我的革命先辈而言,当代青年成长于和平发展的时代,较少经历历史波澜和社会挫折的淘洗,更容易产生安于现状、趋乐避苦的软弱性格,疏于对自我成长的磨砺和锤打。毛泽东所主张的乐于和善于在磨砺中发达身心的观念对于当代青年培育坚强的自我主体意识、促进个人全面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榜样示范作用。
第三,为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和超拔指引了方向。实践证明,个人发展的方向总是与历史发展的方向保持一致,个人价值的实现只有在主动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群众的需要的基础上才具备现实可能性。毛泽东个人的成长和成就正是这一历史规律的生动体现。青年毛泽东自觉将个人的修养和生命与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结合起来,以天下兴亡、学子有责作为自己至高的道德义务。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走上革命道路后,毛泽东提倡的为民族利益而超拔个人的牺牲精神更加明确地成为拯救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义务。那时,个人生命的牺牲再次被诗化、哲学化为浪漫景象,频繁出现于毛泽东所作的诗歌和文章之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解放的革命活动本身也生动体现了毛泽东的革命浪漫主义生命哲学[3]李佑新、黄波:《伟人的终极关怀——论毛泽东的生死观》,《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这种生命经验仍向当代青年指示着,立志、求真和力行的根本方向和超拔个体生命价值的根本途径在于将个体生命价值的彰显和国家时代的发展需要结合起来,将民族复兴大业作为个人成长成才的终极指引,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