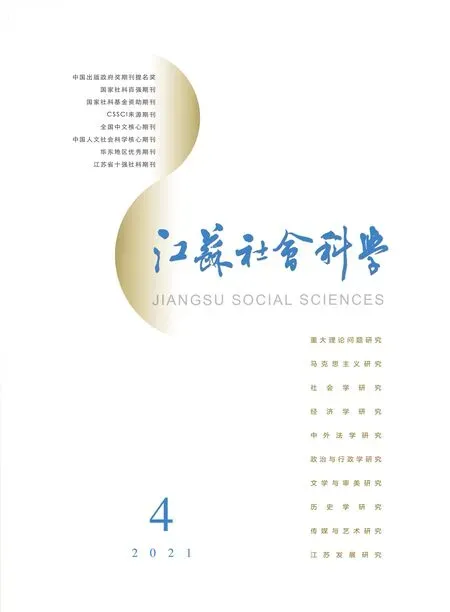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三重逻辑及当代价值
2021-04-15梅景辉骆祥慧
梅景辉 骆祥慧
内容提要 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价值逻辑”三个维度,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进行哲学维度的探讨并结合时代背景予以考察,能够深刻阐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当代的现实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精髓,是通向“真正的共同体”的重要环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对于当代社会发展的时代价值,为当代世界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维度对以“人的依赖关系”为主体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和以“物的依赖关系”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的剖析,深入挖掘了古希腊罗马城邦思想、黑格尔“国家”核心观念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乌托邦式设想的理论精髓,逐步构建了以“人的本质”为核心的共同体思想。纵观马克思经典原著,德语“Gemeinde”“Gemeinschaft”“Gemeinwesen”的含义均指向“共同体”,但此三个词在实际运用中蕴含着不同的含义。“Gemeinschaft”“Gemeinwesen”皆包含“共同”的语意,都由词根“Gemeinde”延伸而来。“Gemeinschaft”更多运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本源共同体”和未来社会的“真正的共同体”,因此,有学者从“没有异化、没有阶级所有”这一维度去理解“Gemeinschaft”的含义。“Gemeinwesen”意指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如政治社会和国家。但马克思并未在文本中直接解释何为“共同体”,因为“共同体”在词源学意义上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在马克思的思想视域中,共同体是生产力推动下的人类生存模式,其建构不仅是哲学问题,而且是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因此,只有从“历史、理论、价值”三个维度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进行文本探讨与实践分析,才能跨越时空,比较马克思所处时代语境下的共同体含义和当代社会多样化共同体的理念,契入“人类发展”的核心问题,在新时代历史坐标中充分展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启示意义。
一、历史逻辑: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渊源
想要深刻理解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就必须追根溯源,梳理其理论生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并阐述其内在逻辑。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哲学家在政治领域的探讨。
1.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共同体思想:共同体思想的萌芽
古代哲学家孕育出“共同”与“整体”的思想。赫拉克利特认为,“logos”为永恒的世界秩序,宇宙是“万物自同”的整体,这种“整体”的思想蕴含了共同体思想的萌芽。古希腊哲学家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共同体问题进行探讨,他们开始追求现实中永恒的价值——“善”,试图找到“善”的最大公约数,并在逻辑的思辨中发展共同的“善”,即从哲学的角度追求“至善”,从政治学的角度推崇“共善”。
在古希腊哲学家的眼中,维护公民共同利益的“城邦共同体”,是“共善”思想的实践形式。苏格拉底从伦理维度打开了探讨“共同体”思想的大门。他认为,“共有制度”是城邦共同体中最大的“善”,即共同占有同样的物品,建立财产公有制度,从而达到城邦的统一[1]〔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黄颖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页,第45—51页。。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城邦共同体思想中的“共善”的色彩,在《理想国》中构建了由哲人统治的小国寡民的理想城邦制度,勾勒出独具特色的“乌托邦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将城邦分为统治者、卫国者和生产者三个等级,其中统治者由极具智慧的哲学家担任。柏拉图认为,三个等级间有着各自的分工,城邦公民各司其职才能获得共同的“善”,但他对于这一共同体如何实现并未做详细说明[2]〔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黄颖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页,第45—51页。。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只有生存于“共同体”内,才有其存在的意义。他在《政治学》中指出,城邦国家是囊括一切社会团体、以实现“最高的善业”为最终目的的共同体。在辨析个人与城邦的关系时,他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城邦共同体”思想。他认为,在处理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时,既要肯定维护城邦共同利益的必要性,又要肯定维护个人私有财产的重要性。由此形成了以追求“共善”为目的、个体通过分有“共善”而拥有道德的共同体思想,即个人只有处在城邦中才具有价值和意义。他认为,在财产共有制度上不应追求绝对的整体性,而应当发扬乐善之心,追求“产业私有而财务公用”[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13页。。亚里士多德将“城邦共同体”的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虽未能挽救古希腊城邦制度的衰落,但对后人的共同体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深受古希腊“德性共同体”思想和斯多亚学派“自然法”和“世界国家”思想的影响,立足于国家的现实,从“共同体”的维度阐述了对政治国家的认知。“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权的一致性和利益的共同性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4]〔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王焕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第87页。他认为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人的天然的聚合性,将“国家”等同于“人民的事业”。国家这种共同体不是柏拉图《理想国》中任意的人群集合,而是基于法律和人民的共同利益所形成的稳定的政治共同体。西塞罗认为,国家不是由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建立的,国家的发展不应该由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决定,所以王权统治和贵族集团统治下的国家具有不稳定性。反之,“如果在一个国家里,同一事物对大家都有利,在这样的国家里最容易达到协和一致”[5]〔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王焕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第87页。。西塞罗认为,“混合政体”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人民的共同利益,从而保障了国家的稳定性。西塞罗基于罗马共和国历史对政治共同体思想的探讨,虽局限于政治领域,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宗教共同体”向“契约共同体”的转化:政治共同体的思想建构
随着中世纪宗教的兴起,基督教逐渐成为欧洲人的精神支柱,欧洲构建了以信仰“上帝”为核心的“宗教共同体”。只要归属于“宗教共同体”,不同性别、年龄、地位的信徒在上帝面前都同样渺小和平等。个人与共同体的关联基于由信徒对上帝的盲目崇拜而产生的精神联系,依托于教会举办的宗教团体仪式。此种“宗教共同体”阻碍了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但其倡导的仁爱、平等思想却一直延续至今。
近代社会“契约共同体”的思想最早源自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他提出著名的非神学形态的“自然法”概念。在他看来,“自然法”至高无上,其立法的依据不再是按照神灵的指示,而是基于“自然状态”中人的社会本性[1]〔荷〕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216页。。自然法概念奠定了“契约共同体”的理论基石。在启蒙运动时期,霍布斯、洛克、卢梭等思想家都以“自然状态”和“自然法”为切入点构建“契约共同体”。这些思想家大多认为,在人们逐渐走出原始的“自然状态”进入新型社会后,为了维护社会安定,人们签订了社会契约从而形成共同体。对人们处在何种“自然状态”、“共同体”权力如何分配等问题的不同回答,体现了启蒙运动思想家对近代政治制度设计的不同理念。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战争”源于人的本性——趋利避害的利己欲,为了结束“战争”,人们需要“共同体”来制约人的本性,所以必须让渡个人权利给代表共同意志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一集体,签订社会契约,从而形成强权共同体。“国家”的主权者(君主)拥有着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如“利维坦”(威力无比的海兽)般的国家的诞生对人们的行为起到约束作用,从而维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生命安全[2]〔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1页。。洛克认为,人生存的“自然状态”不是战争状态,而是自由和平状态,但这种自由不是肆意妄为,每个人都有捍卫私有财产和生命安全的权利。为了保障个人利益不受到伤害,大家都应共同遵循每个个体皆可使用的“自然法”,个人的行为受到理性的“自然法”的约束,从而拥有更广泛的自由。洛克在《政府论》里指出了“自然法”的主要内涵——“人民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3]〔英〕洛克:《政府论》(下册),叶启力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页。。因此,要通过契约建成“共同体”,从而更好地维护个体权利。相较于霍布斯君主集权的政治思想,洛克更倾向于君主立宪式的分权学说。卢梭是“契约共同体”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人的“自然状态”应当是原始的公有关系,没有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人生而平等且自由。但私有制的产生,打破了这种祥和的状态,人们不得不在平等的前提下签订契约,组建利益共同体,从而保障共同体成员的权益。不同于霍布斯和洛克,卢梭“契约共同体”的签订基于人人平等,提倡“主权在民”,共同体的权力掌握在每一个成员手中,共同体代表着人民的“公意”,共同体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同时,个人权益也只能在“契约共同体”内才能得到实现[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9—21页。。纵观历史,虽然并未有任何团体签订成立共同体的“契约”,但自然法派思想家关于“契约共同体”的思想极具进步意义,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对于构建“共同体”制度以保证个人利益的渴求,推动了近代政治制度的构建。
3. 黑格尔国家主义共同体思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思想逻辑建构
黑格尔在一定意义上传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共同体思想,但他也吸收了契约共同体的相关理论。他从抽象思辨的角度出发,打破市民社会与国家相统一的传统共同体解释框架,指出市民社会和国家不可混淆。一方面,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5]〔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3页。,代表作为“神”的意志的绝对理性精神。这就意味着,国家作为代表绝对精神的共同体,其制度的制定和未来的发展不受任何个人主观意志的影响和控制,具有客观合理性和普遍性。另一方面,“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5页,第254页。,国家代表着人们共同的现实利益。也就是说,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具有同一性,个体是国家的一部分,离开了国家的个体是无法界定的,“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5页,第254页。。黑格尔认为,伦理性是存在于个人意志的自由精神,也就是说,个体只有成为国家公民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按照这一思想逻辑,个人必须遵从共同体的统一意志,因为人生来就被打上了国家公民的烙印,遵从国家意志是个体与生俱来的内在属性,而国家意志不会被任何个体改变。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衍生物是其不可分割的分支,国家的属性决定市民社会的发展方向,国家是市民社会内在目标的体现。
《莱茵报》时期之前,马克思也认同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国家是代表伦理理性的共同体、个人在国家这一共同体中得到自由的思想。但在对现实进行考察后,马克思很快发现黑格尔国家观具有的矛盾性和虚假性:国家代表的不是公众的普遍利益,而是将统治者的特殊利益上升为普遍利益,具有欺骗性。这种从先验理论出发所构建的“国家共同体”思想,无法正确把握“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实质含义和现实关系。应从物质基础和人本学出发,颠倒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点[3]〔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页。。
4. 空想社会主义的蓝图:对共产主义共同体的反思与展望
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渐凸显,生活在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批判了资本发展造成的失业、贫困、贫富差距等现实问题,他们基于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从衣食住行等方面阐述了对福利共同体社会的构想,并将这些天才的想法以试验的方式付诸实践。大量涌现的“法郎吉”“新和谐公社”“乌托邦岛”“太阳城”等共产性质的理想共同体,闪耀着和谐平等的福利思想。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坚信,只有生活在共享共有、劳动自由的共产主义共同体中,人们才能拥有真正的幸福。
在现代化技术支持下,建立智慧园区的总体构想,综合考量地块信息化差异。其一,应用系统层,主要包括园区控制云、园区管理云和园区服务云;第二,应用支撑平台层;其三,网络通信层;其四,智能感知层;其五,基础设施层。
傅立叶有关“法郎吉”公社的畅想,是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共同体形式的美好设想。“法郎吉”源于希腊文,意指“有规则的矩阵”。诚如其名,这一共同体有其严格秩序,每个“法郎吉”公社的“最佳人数”为1800。公社内部明文规定选举平等、人人劳动、同工同酬、集体消费、义务教育等规章制度。这些理想制度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收入差异、分配差异和城乡差异[4]《傅立叶选集》第2卷,赵俊欣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7—236页。。这一共同体基于对未来公平社会的畅想,也凸显了对劳动本质的追求,即劳动不应是一种被剥削的行为,而应是一种主动的享乐。但是“法郎吉”公社保留了私有财产和私有制,想通过实验的方式和平进入理想共同体,这一脱离实际的理论导致美国近30个“法郎吉”公社实验均以失败告终。不同于傅立叶,英国的欧文对未来共同体社会的构建,彻底否定了私有财产[5]《欧文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56—368页。。现实中,由于大部分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统治阶级(资本家)手中,被统治者(无产者)逐步丧失劳动积极性,阶级间矛盾不断激化。唯有把生产资料彻底公有化,才能从根本上消灭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新和谐公社”是欧文理想的试验田,这一共同体取缔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压迫,劳动者回归自由自觉的劳动生活。但这一脱离物质基础的和平实验方式只存在短短数年就以失败告终。总体来说,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从政治公平、饮食公平、教育公平、住房公平、公共医疗公平乃至服装公平等各个层面详细勾勒了未来共同体社会的样貌。虽然这些理想化的设计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对市民社会共同体弊端的抨击与对未来理想共同体的天才构想,却深深影响着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灵感来源。
二、理论逻辑: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内涵
“共同体”作为一个广泛使用的概念,在不同文化、不同时代和不同语境下含义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在此探讨“共同体”,不是探究这一词汇的明确定义,而是回到马克思文本中对其进行考察。目前,学者们大多从“三种社会关系”的维度解读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但这只是切入该思想的一种理路,马克思一生都在不断完善其共同体思想。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大量使用“共同体”概念,是要突出人在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分离中实现政治解放。但政治解放不是最终的解放,政治共同体不能代表普遍利益,马克思由此揭示了国家具有“虚幻性”。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虚幻的共同体”源自市民社会所带来的人的普遍异化,“劳动是为每个人设定的天职,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1]〔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6页。,所以必须揭露“资本家共同体”的虚幻性,通过社会变革彻底消除异化,才能走向真正的共产主义,完成人的复归。《德意志意识形态》阐述了民族分工所带来社会形态的差异,描述了原始时期的“部落共同体”、奴隶社会时期的“古代古典共同体”、封建时期的“封建的共同体”等社会形态,按照社会关系将人类社会分为“自然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他在批判中构思未来社会将何去何从,由此提出走向“真正的共同体”,构建其共同体理论的基本雏形。《共产党宣言》阐述了著名的“自由人联合体”概念,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的研究重心聚焦于本源形式共同体。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深刻探讨了市民社会前的“亚细亚共同体”“古典古代共同体”“日耳曼共同体”。恩格斯也沿着这一理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详细探寻人类社会共同体的起源和古代共同体的样貌特征。
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生成脉络来看,他并非孤立静止地关注和考量人的生存,而是结合特定历史阶段并立足唯物史观,把现实的人置于不同社会关系的逻辑中予以考察研究。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逻辑对应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规律,表现为不同的“共同体”形态,我们唯有紧扣唯物史观,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种社会关系[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4—725页,第725页。和五种所有制[3]〔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5页。发展阶段的双重维度全面探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方能探究其本质内涵。
1. 前资本主义——“自然的共同体”
“自然的共同体”是马克思在论述“前资本主义形态”时提出的,是对私有制产生前不同共同体形式的概括总结。这种最初级的共同体并不是人们有意为之的,而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它证明了人类自起源至今一直依托共同体而生存,也有学者将其称为“本源共同体”。人们面对强大的自然,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维持生活,二是繁衍后代。因此,为了种族延续,人们自发形成以血缘和土地为纽带的集体,通过合作获得生存条件。在对不同形式共同体的探究中,马克思指出,这种自然生成的共同体以不发达的生产力、分工和交换为背景,以血缘、语言、习惯为纽带,以家庭为最基本单位,是“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4—725页,第725页。。人依赖于自然而存在,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必备条件来源于自在自然;人同样也依赖于共同体而存在,人的活动方式(如游牧、耕种)不由自身所决定,而是由共同体的群体性质所决定。这一共同体并非能推动社会发展,只是旨在保障自给自足和生存需要的自发联合。但“自然的共同体”的自身局限性也体现在对自然的过度依赖上,由此导致共同体具有不稳定性,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独立个体不断发展,对人的依赖关系转化为对物的依赖关系,“自然的共同体”必将走向解体。马克思晚年为探索市民社会共同体何以产生,对“自然的共同体”进行进一步探究,依托大量史料解剖出前资本主义的三种共同体形式。其一是生成于东方世界的“亚细亚共同体”。土地是共同体公有财产,人们进行自给自足的劳动生产。马克思从“单个的人”和“总和的统一体”与土地的关系深刻剖析这一共同体的实质。“单个的人”虽在共同财产——土地上劳动,但实质上不是土地的所有者,“总和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因而实际的公社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6页,第735页,第726页,第728页,第735页,第730页,第730页,第734页,第736页。。这种东方专制下的共同体,“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6页,第735页,第726页,第728页,第735页,第730页,第730页,第734页,第736页。;“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6页,第735页,第726页,第728页,第735页,第730页,第730页,第734页,第736页。。换言之,个体相对于共同体不具备独立性,只有臣服于统一体才能获得土地财产,这一因素导致个体不具备与共同体相分离的条件。在这一共同体中,如果不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那么即使统一体变迁,也不会改变其所有制关系,而且会不断加强个人同共同体的紧密联系,巩固统一体的君主专制制度,所以,此种共同体不可能过渡到市民社会共同体中。其二是以古罗马和古希腊为首的“古典古代共同体”。不同于“亚细亚共同体”,土地不再是“古典古代共同体”的根基,“耕地表现为城市的领土”[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6页,第735页,第726页,第728页,第735页,第730页,第730页,第734页,第736页。,城市则是成员的主要居住地,也是其军事组织的基础。个人和共同体关系紧密且相互依赖,但个人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自由且平等的个体联合组成共同体,共同体保障个体的生活。城市中土地财产表现为共同体公有土地和个体私有土地并存的双重形式,“存在着国有土地财产和私人土地财产相对立的形式,结果是后者以前者为中介”[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6页,第735页,第726页,第728页,第735页,第730页,第730页,第734页,第736页。。但是,个体获得土地的条件为归属于共同体,只有同时拥有私有者和共同体成员的双重身份,才能朝着共同利益进行劳动联合从而保障其集体的稳定性。这一土地财产的前提也决定了个人与共同体的不对等关系,个体(公社成员)“属于”共同体,“这种‘属于’是由他作为国家成员的存在作中介的”[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6页,第735页,第726页,第728页,第735页,第730页,第730页,第734页,第736页。。马克思指出,“属于”关系迫使公社与公社成员紧密联合,个体自由是公社赋予的,所以个体自由是相对的,“个人被置于这样一种谋生的条件下,其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6页,第735页,第726页,第728页,第735页,第730页,第730页,第734页,第736页。,个人必须维护想象中和现实中的共同利益。这种体制注定无法走向现代社会。其三是欧洲世界的“日耳曼共同体”。日耳曼人生活在森林之中,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相隔较远,公社只能通过集会的方式召集成员。相较于前两者,成员对共同体的依附程度最弱。马克思认为,这一共同体蕴含着生成市民社会的条件。语言、血统和历史是单个成员间联合的前提,但成员不再是公社的分支,而是独立的有机体,“公社便表现为一种联合而不是联合体,表现为以土地所有者为独立主体的一种统一,而不是表现为统一体”[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6页,第735页,第726页,第728页,第735页,第730页,第730页,第734页,第736页。。在这里,私人土地没有中介前提,完全属于个人所有。这种公社的形式不以国家组织的存在为前提,这种公社基于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联合,“它是被每一个个人所有者以个人所有者的身份来使用,而不是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像在罗马那样)来使用的”[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6页,第735页,第726页,第728页,第735页,第730页,第730页,第734页,第736页。。个体成员及其自由造成此共同体不具备稳定性,但也为市民社会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
2.资本主义社会——“虚幻的共同体”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的不断完善,少数人攫取越来越多的社会剩余财富,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日益尖锐,人们逐渐摆脱了对原有共同体的依赖,以人的依赖关系为根基的“自然的共同体”逐步土崩瓦解,走向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虚幻的共同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逐步转移到少部分人手中,大部人逐步转变为贫困的无产者。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实质上是虚幻虚假的,它表面上以“国家”的形式采取民主的方式捍卫国民的“共同利益”,实质上将资本家的“特殊利益”上升为国家的“共同利益”。在全面物化的社会关系中,无产阶级作为被统治阶级,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是不自由的、受限制的。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虚幻的共同体”往往代指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和社会形态。
“虚幻的共同体”根源于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不断分化,其产生是为了调和劳动分工带来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分工导致不均衡的分配(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分配在数量和质量上皆具有不对等性)和社会阶级不断分离,而个体利益与所谓的共同体利益不一致所产生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1]〔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页,第29页,第46页,第65页,第65页。。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者)为了防止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侵犯,将本阶级利益上升为普遍利益,以“国家”的名义调节日益尖锐的阶级关系。马克思从三个角度阐述了“虚幻”这一概念。第一,意识形态具有虚幻性,“普遍的东西一般来说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2]〔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页,第29页,第46页,第65页,第65页。。统治阶级为了达到统治的目的和群众的支持,必须将“共同利益”解释为“普遍的东西”并将这一解释灌输到个体的观念中。将统治阶级利益冠冕堂皇地提升为社会的整体利益,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3]〔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页,第29页,第46页,第65页,第65页。,其实质则是赤裸裸地压榨无产者们的剩余劳动。第二,市民社会中大多数人未获得真正的自由。资本家们拥有自由,而对于数目众多的被统治者而言,他们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事实上,“虚幻的共同体”的不断异化导致工人不得不屈服于“物”的统治,不仅无法分享“共同体”的利益分红,而且只能不断地把个人权益让渡给“国家”这一“虚假的共同体”。第三,多数社会成员与共同体分离。资本家的联合体捍卫的是本阶级的利益,对于广大无产者来说,这种共同体不但不能保障私人利益,而且以“国家利益”为名严重损害了无产者的利益。这种宣扬“自由平等”的共同体,甚至无法保障无产阶级的生存。诚如马克思所言,“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4]〔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页,第29页,第46页,第65页,第65页。。
从应然和实然角度可以更深层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为何“虚幻”。应然是指人们对事物发展趋势的设定,实然是指事物存在的现实状态。人们常从应然视角审视实然,甚至混淆二者。标榜“普遍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恰恰刻意混淆应然与实然,所谓的“普遍”实质是统治者们的个人利益,并未体现出分工细化所带来的个体之间不可分离、全面发展的共同利益。资本主义政党正是利用这一点将自己的私人利益上升为公共的普遍利益,所追逐的是资本主义政党的特权,其标榜的国家利益与广大无产者的利益相矛盾。这种“普遍利益”对于现实的人来说,是异己的、虚幻的、抽象的,这种共同体也具有虚幻性,不能给普罗大众带来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3.“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
“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的理论精华和价值旨趣,他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并非乌托邦式的预设,也不是空洞的伦理构想,而是基于唯物史观的通向人的最终解放的现实革命。“真正的共同体”在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的双重领域中实现了人的最终解放。其一,人在自然领域中获得自由发展。在未来社会中,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将使人们摆脱自然界的束缚,劳动分工的消灭将使个体回归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质。其二,人在共同体内获得自由发展。以往社会内的“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5]〔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页,第29页,第46页,第65页,第65页。,即使借助“国家”形式完成了政治领域的解放,实质上大多数人仍无法获得自由解放。而在未来的共同体中,不再有阶级对立,个人以自身的特殊利益为单位进行联合。这种自由人联合体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6]〔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页。。
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虚幻性”的同时,找到了走向未来社会的钥匙——消灭分工。劳动本是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分工出现后,劳动者只能在强加于他的特定范围内生产,否则会失去生活资料,“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0页。。因此,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共同体”应当打破劳动的特定范围,个体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劳动部门,而且可以选择劳动时间,生产则由社会进行宏观调控。在这一社会中,劳动回归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再受到异化的支配,个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趋于统一。因此,“真正的共同体”必须是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有机统一体。也就是说,生产资料不再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共同体的目标也不再是捍卫某一阶级的特权,而是保障每一个独立的共同体成员愿景的实现。
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共同体”应当建立于物质资料极其丰富的未来社会中,在其中,独立个体的个性、尊严、权益能够得到充分尊重。在他看来,真正的共同体应该有以下三种特征。其一,生产力高度发达,以公有制为基础,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在“真正的共同体”中,生产与分工高度发展,社会生产资料人人共享,社会按照个人自由发展的需要制定不同的生产计划。其二,社会成员自由自觉地劳动,社会财富按需分配。由于物质资料极其丰盈,在这一共同体中的人是自由的存在,其劳动不再受资本家的压榨,可以自由能动地选择职业,参与到社会生产的任一环节。劳动产品,不是按生产要素或劳动时长分配,而是按人的需求分配。其三,消除阶级和国家,人民是共同体的主人。公有制完全消除了市民社会的阶级矛盾,随着矛盾的消失,作为调节阶级矛盾工具的国家也将不复存在。个人不再作为某一阶级成员存在于不可控制的共同体内,而是作为控制着自己生存条件的独立体参与到联合体中。
三、价值逻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新性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33页。,人类共同面对现实问题,共享发展成果。在政治哲学视域中,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对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虚假共同体的超越,是引导社会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中国智慧。我们有必要探寻蕴藏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内涵和价值旨趣,从而把握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价值。
1. 以唯物史观为根基,应对全球现实挑战
唯物史观贯穿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社会的发展是由“现实个人”的实践活动所推动的,历史维度下社会关系的更替史就是共同体从低级至高级的演进史。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和三大社会关系,共同体的发展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中都有与之相对应的物质基础。按照这一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以当今世界所遭遇的挑战为历史条件,以中国腾飞发展的大国经验为实践基础,破解了人类社会面临的多方面难题。针对治理、信任、和平、发展等方面的“四大病症”,习近平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上提出“四大良方”,即建设“公正合理、互商互谅、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在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协同发展、互利共赢。
2. 以“共同体”为载体,聚焦人类发展问题
在马克思的思想视域中,“共同体”作为人类社会关系的载体永恒存在,人唯有生存于“共同体”中方能获得最终的解放。“共同体”既是人类进步的载体,又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基于对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批判,马克思提出“真正的共同体”的理想愿景。遵循马克思的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聚焦于“人”的发展前途,致力于缓解由经济发展需求导致的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破以西方为主导的传统国际治理观,以“共同体”为人类存在的实践形态,通过不断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多重联合体,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的共生共赢。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核心为“人”本身。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个体,要处理人与自在自然、人与人化自然的关系问题,获得最终的解放和自由,达到人对人本质的回归。马克思认为,“在真正的共同体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5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聚焦于民生福祉,其关切的不是某一国家或某一阶级的特殊利益,而是将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作为研究的重大命题。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政治、经济、安全、生态等各个维度聚焦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聚焦如何在当今世界创造人类美好生活这一时代命题。世界正日益紧密地连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面对资本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风险和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共同进步贡献了不一样全球治理视角,即世界各国凸显各自的优势,打破发展壁垒,共享人类发展的成果。
3. 以走向“真正的共同体”为价值旨趣
实现“人的最终解放”是马克思的毕生追求,其共同体思想指向基于唯物史观的人类解放进程。马克思认为,“最终解放”就是人对人本质的彻底复归,所以必须建立一种消灭现存共同体的联合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页。。基于此,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其出发点为“现实中的人”,落脚点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检验标准为“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但是,这种理想的共同体只能在阶级和国家消亡后产生,难以在生产力有限的今天实现。纵观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相互交融和博弈的状况仍将延续较长时间,“无产阶级时代”到来的条件尚不成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基于真理,立足现实,面对全球治理中的众多挑战,将“真正的共同体”作为价值旨趣,以“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33页。作为发展目标,构建共惠的发展环境。
我们有必要对“真正的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行学理辨析,从而把握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价值。从时空维度来看,前者提出于19世纪资产阶级主导下的市民社会,后者则是立足于解决21世纪人类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当今中国和世界的最新发展成果。从主体维度来看,前者是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联合,不是某一国家或阶级的联合;而后者是以当今社会民族国家为主体,通过国家间合作达到共赢。从内容维度来看,前者要求阶级和国家的消亡从而达到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后者着眼于不同制度、不同发展程度和发展道路的国家如何和谐发展。从实现方式维度来看,前者的实现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者的实现方式是全球各国携手共商共建共享。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时代价值,为当代世界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证明了全球治理并非只有西方“资本至上”这一条道路。 在理论维度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并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文本中描述的未来社会的联合体,但在实践维度上,它是从不同的社会制度并存的现实社会形态走向共产主义“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桥梁和绿色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