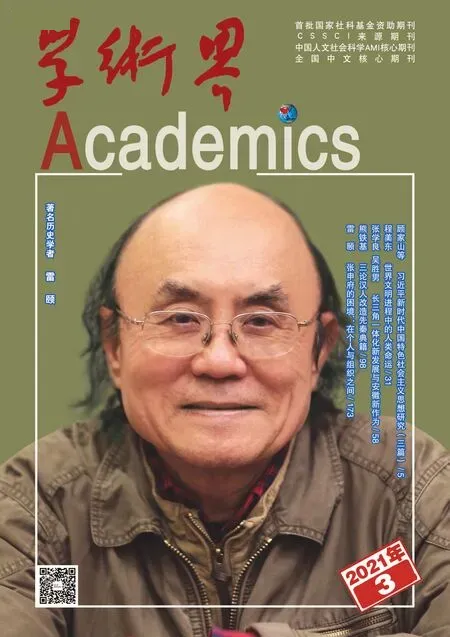析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机制〔*〕
——以洞朗事件为例
2021-04-15夏立平
夏立平
(同济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 上海 200092)
印度是当今世界新兴大国之一,印度的对外政策决策机制对其制定与推行哪种外交政策具有很大影响。印度的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本文将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并以中印洞朗事件作为案例。
一、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的发展与演变
“对外政策决策是极端复杂的,需要多重特别的专门机构、个人和机制来应对一系列不同问题。”〔1〕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的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的发展与演变可分成三阶段:
(一)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的“小集团决策”阶段(1947—1997年)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1950年1月26日始,印度宪法正式生效,自此印度开始正式成为“主权的民主共和国”。作为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的基石,印度的宪法规定了印度施行议会民主制,拥有立法、行政与司法制度这三套体系。〔2〕印度宪法虽然赋予了总统广泛的权力,但在现实的操作过程中,立法、行政与司法等实际的主要权力分别被议会、以总理为首的内阁与最高法院控制。印度总统仅仅成为国家统一的一种象征,成为类似英国女王的虚位元首。
印度总理是印度的政府首脑,也拥有最大的行政实权,其不仅拥有议会的多数支持,也牢牢把内阁操纵于自己手中,在印度政治体制中,印度总理的地位至关重要,换言之即印度总理就是印度对外政策决策的核心。〔3〕
从1947年起,尼赫鲁连续四届担任印度总理。作为印度的开国总理,尼赫鲁同时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当印度国父“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于1948年1月被暗杀后,他就变成印度的最高权威,印度现代史上“尼赫鲁时代”拉开序幕。国大党一党独大的局面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有所变化。尼赫鲁个人的领导风格不算民主,他主持内阁会议时,部长们往往是听尼赫鲁作指示,然后去办事。他不许部长们对一切重大决定有任何反对意见,他强硬的领导与工作作风也完整地体现于印度对外政策决策的过程中。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印边界争端中,尼赫鲁认为自己在对外政策制定方面的能力得天独厚,常常只听取小集团中他提拔的少数人的建议,并不接受其余同僚所提出的相左建议,以及一些高级将领的警告。在没有听取全面建议和不进行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就声称要将“麦克马洪线”看作边界,并轻易作出决策,结果招致失败。〔4〕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为了加强规划,避免国家在安全和外交政策上失误,也为了避免个人行为所带来的失误,尼赫鲁将内阁国防委员会改名为紧急委员会,主要负责处理军事和外交问题,开始制定五年防御计划。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以下简称英·甘地)于1966年成功当选印度第三任总理。直到1984年10月,英·甘地遭遇刺杀后身亡,其间绝大多数时间,印度都是由英·甘地担任印度总理。英·甘地担任总理后,一开始由于缺乏执政经验,行事风格较为小心谨慎,以至于在气势方面稍显不足。但由于英·甘地个人十分勤奋,通过各种日常实践,不断积累自己的行政经验,也掌握了很多从政方法,到后期逐渐有了自己的行事风格。她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锋芒尖锐、雷厉风行、英勇果敢。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甘地为了维护自己得之不易的权力,第二次执政后变得更加专制,手段也愈发强硬,把党政大权全部牢牢抓于自己手中。在英·甘地执政期间,印度更加强化了总理在对外政策决策中的绝对主导作用,从这点上看,她完美地继承了尼赫鲁家族的“小集团决策”传统。“她喜欢依靠由一些顾问和秘密成员组成的小团体来管理她的政策,而这个小团体后来越来越小。”〔5〕
1984年英·甘地被刺杀后,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以下简称拉·甘地)经过印度国大党推举成为印度的新总理。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极大地改善了中印之间的关系,但是拉·甘地仍沿用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机制中的“小集团决策”传统,1989年拉·甘地在印度国民大会的选举中失败,离开总理职位,并于1991年5月21日遇刺身亡。来自人民党的钱德拉·谢卡尔(Chandra Shekhar)等人在拉·甘地下台后先后担任过印度总理,但时间都不长,“小集团决策”的对外政策决策机制没有大变化。
在实践中,如果总理本人头脑清醒、小集团核心成员表现出色,“小集团决策”机制可以是有效的,并有成功的案例。例如,在1971年“东巴危机”期间,英·甘地基于局势敏感因而反应谨慎,并能接受印度军方及其所属参谋机构提出的通盘考虑局势后再动手的建议。在争取国际支持后,择机发动了对巴基斯坦的战争,并取得了胜利。
但“小集团决策”机制本身却存在明显不足,“对小集团里面合作紧密性的追求远远比不上拟定出政策的群体对于合适与公道政策的追求,由于担心或担心与其他团队成员步调不一致,许多团队成员不能或不想提出意见,导致的结果是,他们不能充分估计客观现实。所以一旦形成这样的气氛,决策小组就不能完整仔细以及充分考虑最适合与客观的政策,最终就会产生并不科学的外交政策,由此就会导致外交政策实施的失败”。〔6〕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拉·甘地政府为了维持其在南亚的霸主地位向斯里兰卡派出“维和部队”进行所谓“维和行动”。整个“出兵斯里兰卡”的政策决策过程,正是拉·甘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陆军参谋长K·桑达尔吉(K.Sundarji)将军等人参与了决策小圈子。但斯里兰卡形势发展未能如印度政府决策者所愿,印度“维和部队”在苦苦支撑2年零8个月,遭受重大伤亡后,不得不撤离斯里兰卡。这一事件实际上也标志着印度“小集团决策”机制的失败。
(二)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机制“集体决策”阶段(1998—2013年)
1962年被中国在边界反击战中打败后,印度就有人提出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但尼赫鲁及其后的几任总理对这一建议都不感兴趣。直到20世纪70年代,印度国内的社会政治力量逐渐积极参与到了印度的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这不仅提高了国家对外决策的能力,也积累了很多对外决策的经验。印度军方在应对“东巴危机”期间就有出色表现,为印度对外决策参谋机制化探索了道路。印度国内要求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呼声逐渐上升,尤其是印度“出兵斯里兰卡”失败后,印度统治集团开始慢慢发现“小集团决策”机制的弊病。维什瓦纳特·普拉塔普·辛格任总理时,印度在1990年8月24日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缩写NSC),主要目标就是尽可能改善国家安全事务的管理,但该委员会在辛格下台之前只举行过一次会议。
1998年5月,印度进行核武器试验后,其政府面临着一系列与核试验有关的重大问题——核试验的成功会对印度将要面对的国内外环境产生哪些影响——亟待找到答案。在这种情况下,1998年11月19日,印度再一次成立国家安全委员,这一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理出任主席,1999年开始正式运行。国家安全委员会最高委员会现在是内阁安全委员会(Cabinet Committee of Security,缩写CCS),由七个成员组成,印度总理本人担任主席。内阁安全委员会核心成员包括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内务部长等。其余部长与专家受到邀请之后也能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是由总理的首席秘书出任。〔7〕国家安全委员会拥有三层结构: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顶层机制为战略核心小组(Strategic Core Group,缩写SPG)。该小组主要成员17人,包括内阁秘书、国防部秘书、内政部秘书、财政部秘书、国防生产部秘书、情报局局长与调查分析局局长、陆海空三军参谋长等,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内最高的战略决策组织,负责制定印度长期和短期战略蓝图。该小组持续关注国家和国际安全环境,并采取必要步骤以解决可能的威胁。战略核心小组通常集中着眼于长期的战略,制定印度战略规划并且负责推行。〔8〕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二层机制是国家安全顾问理事会(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y Board,缩写NSAB)。其大部分成员是从政府机构之外选用的,但与政治相关。这些成员在对外政策与战略、国防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科学与技术等方面有专门的知识。印度政府设定该理事会的成员不超过30人。现在国家安全顾问理事会有23名成员。〔9〕
联合情报委员会(The combined 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缩写JIC)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底层机制。联合情报委员会又叫作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0〕联合情报委员会由印度情报系统各部门组成,包括印度情报局(Intelligence Bureau)、军事情报署、海军情报署和空军情报署,在政府需要制定与执行对外政策时,由以上这些部门提供一些必需情报。
一言以蔽之,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印度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机制进入“集体决策”阶段。在这之后,印度对外政策决策走上了相对科学与高效的道路。印度对外政策“集体决策”机制的主要特点为以下几个方面:
1.总理仍是国家对外政策决策的主导者
以“卡尔吉尔冲突”为例,1999年5—7月,印度与巴基斯坦发生“卡尔吉尔冲突”。此次冲突发生在瓦杰帕伊担任看守内阁总理期间,但却丝毫没有影响到这位即将卸任的总理在印度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在整个冲突期间,瓦杰帕伊总理主导了印度政府所有的重大决策。
2.内阁安全委员会与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制决策效果明显
内阁安全委员会自成立后,其作用越来越重要,印度政府几乎所有相关重大的决策皆是在内阁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作出的。自1999年7月第二周开始,内阁安全委员会会议几乎每天举行,除了总理与内阁安全委员会其他成员外,与会者往往还有内阁秘书、国防秘书、陆海空三军参谋长、调查分析局局长、情报局局长等。这种战时管理体制,使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与宣传手段融为一体,保证了印度决策与指挥系统的高效运转。例如,国家安全顾问理事会几位著名战略家向内阁安全委员会建议,应该允许印度军队越境作战,为决策提供了参考。各情报机构送来的情报将会送交联合情报委员会进行分析,经过研判提供给内阁安全委员会进行决策参考,再将相关情报发送给印军各军兵种和前线指挥机构用于作战。〔11〕
3.国内社会政治力量的影响力逐渐加大
冷战结束后,印度民众参政热情高涨,民主意识增强,印度议会、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都积极就印度对外政策发声,公众与印度媒体也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己对印度对外政策的看法,国内社会政治力量对印度对外政策决策的影响力开始上升,第一场通过电视媒体进入印度普通家庭的国家间冲突就是“卡尔吉尔冲突”。民众通过观看电视媒体直播的画面,视觉与心理都受到了巨大冲击,无孔不入的记者使军方和政府压力倍增,这些均对政府决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的“强人政治加集体决策”阶段(2014年至今)
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2014年5月16日当选为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与全国民主联盟在印度人民院(议会下院)543个议席中获得了334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莫迪也被世界各地的媒体冠以“作风强硬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这样一个称号。2019年5月,莫迪再次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其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在印度人民院542个议席中获得了303个议席,其所在的执政联盟获得345个议席,超过组阁所需要的272个议席。
莫迪一向被印度媒体称为“非典型印度政治家”,不仅是由于莫迪是印度极少数未陷入过受贿或其他丑闻的官僚,还因为他“是一位坚定的实干家领袖,果断、廉洁、高效、以解决问题为己任”。〔12〕莫迪有独断专行的强人风格,以暴脾气闻名,工作勤勉。如今在印度,莫迪的威信很高,他的人气也是十分高,不仅获得许多同僚的支持,在民众中威望也很高,有些人甚至把他当作偶像,将他认作“半个神明”,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印度历史上最强有力的总理”。〔13〕
莫迪把他的强人风格也用于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机制中,使该机制转变为“强人政治加集体决策”。其主要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莫迪总理以强势风格推进外交政策
“印度教特性”(Hindutava)〔14〕逐渐在印度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印度人民党在国内政治架构中“一党独大”的地位也得以巩固。以上条件都使得莫迪总理可以更强势地推进他授权与同意下的外交议程。莫迪上台后,提出将印度打造为世界“领导性强国”(leading power)的战略目标,突出“邻国优先”,以战略自主取代之前的“不结盟”政策等。〔15〕莫迪凭借强势的有浓烈个人特色的执政风格、从基层做起慢慢积累下来的政治人脉和威望、在执政联盟内的主导地位以及成功让党内元老“靠边站”的手腕等,提高了他在对外政策上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虽然印度人民党内批评莫迪过于强势的声音络绎不绝,但莫迪超高的人气对印度人民党至关重要,他的总理办公室也曾被形容为“历史上最具有权势的总理办公室”。〔16〕《外交政策》杂志曾经发表文章将莫迪描述为“帝王”,认为莫迪已终结曾经荣耀一时的“甘地王朝”。〔17〕
2.莫迪总理运用推特等新媒体技术推动公共外交发展
莫迪上任后不仅加大了新科技手段在外交中的运用,还提出了“数字外交倡议”,专门建立公共外交网站,利用推特(Twittwe)等社交工具宣传印度的外交政策与外交理念。莫迪外交的一大特色就是公共外交与数字外交的结合。包含莫迪在内的印度政府高层,主动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宣传,他们都非常重视社交媒体的作用。在2015年的统计中,超过1000万人关注了莫迪的推特账户,这样的关注人数仅次于时任美国总统的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和教皇。莫迪在全世界的受欢迎程度与其个人魅力在某种程度上对印度的国家形象有正面作用。
3.以内阁安全委员会为主制定对外政策与国家安全决策
印度议会2016年11月批准印度陆军购买新型坦克,但购买何种坦克一直未决,可以说效率非常低。但2019年12月底,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却能很快批准采购“巴拉克”—8反导系统的远程舰对空导弹,以及“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的反舰型号,配备给4艘排水量为7300吨的“维沙卡帕特南”级导弹驱逐舰以对付沿海、海上及空中目标。全部资金达到615亿卢比(1美元约为71卢比),由坐落于孟买的印度国企马扎冈造船厂为印海军制造4艘导弹驱逐舰。再如,2020年2月,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批准以26亿美元为印海军购买24架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配备鱼雷和飞弹的MH-60R型“海鹰”反潜直升机等。相比之下内阁安全委员会的决策效率要高很多,莫迪政府对其也更加倚重。
二、影响印度对外政策决策的主要因素
美国专家瓦莱丽·哈德森(Valerie Hudson)认为:“如果要对外交决策进行深入研究,需要研究影响外交决策与决策者的相关因素。”〔18〕目前影响印度对外政策决策的主要因素包括:印度国家安全战略、印度战略文化、国会和反对党、公众舆论等。
(一)印度国家安全战略对印度对外政策决策的影响
虽然现在印度政府还没有发布正式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但印度的国家安全战略最终目标可归纳为“争当世界一流强国,主导南亚,控制印度洋”。印度一直以来都想在世界上成为“一流强国”,印度对于这个目标的执念很深。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曾就渴望印度成为一流大国表达过他的憧憬:“凭借印度身处的位置与地位,印度不可以在当今时代扮演二流角色,要么就销声匿迹,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超一流大国。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19〕印度独立以来的历届政府都以这一目标作为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虽然印度在冷战时期国力并不强,但印度仍通过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来树立自己的形象,并保障自身安全。
印度国家安全战略在冷战结束后将注重传统军事的安全战略转为注重包括军事、政治、科技、经济等在内的综合性安全战略。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1.谋求世界大国地位
印度一直在争取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设法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其已经通过进行核试验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家,这使得印度认为可以在全球安全问题上拥有更多发言权,并借此试图成为多中心世界的其中一个中心,由此来保证印度安全。
2.主导南亚和控制印度洋
印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将实现其主导南亚目标所涉及的地区统称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地区”,并将“核心地区”划了两个圈:第一圈是内圈,包含东南亚到波斯湾地区,从阿富汗和英属印度的国界线杜兰线至缅甸;第二圈是外圈,这一圈为印度洋周边的国家,在后期还加上中国和中亚。印度实际上一直在不断扩展印度国家安全的外部空间,其以“印度中心论”为理论依据,战略意图是阻止其他大国插手南亚和印度洋事务。保卫西北边界,不允许其他大国对其周围的小国施加影响,不允许其他国家在其西北部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扩展势力,也不同意其他大国扩大在印度洋的影响,意图把对印度洋的控制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不仅如此,印度还主张“印太”构想。印度专家认为,“印太”构想可以极大提升印度在亚洲安全战略领域的话语权,可以扩大其稍显落后的亚太战略版图,印度也能够从中获得相应的好处。〔20〕
3.保持足够的军事竞争力
在军事发展目标上,印度紧紧对标中国的国防力量,明确表示过其国防现代化水平要与中国保持同步;同时,印度还需要保持战略核威慑,来应对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的常规战争与有限核战争威胁。除此之外,印度不仅加强了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合作,着眼于整体作战能力的提高,还开发了远程导弹系统,其导弹射程已覆盖中国上海、武汉等大城市。
4.借助大国力量牵制中国
首先,印度自冷战结束以来,逐渐恢复了其与俄罗斯的传统关系,是俄式武器的主要采购方。其次,针对目前中国发展势头很强的局面,印度深知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崛起,对其在印太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为了实现地区力量“均势”,美国更乐意选择联合印度来牵制中国。在牵制中国这一方面,美国的利益需求恰好迎合了印度借助其他大国力量的需要。可见,印度国家安全战略可以决定印度对外政策决策的主要逻辑和基本方向。
(二)印度战略文化对印度对外政策决策的影响
在印度战略文化中不仅存在现实主义战略文化的传统,与之相对应的还有理想主义战略文化的传统,但现实主义战略文化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除此之外,印度战略文化也深受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文化的影响。对印度对外政策决策影响较大的印度战略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理想主义战略文化对印度对外政策决策的影响
早在古印度孔雀王朝时期,王朝第三代国王阿育王在统一印度的过程中眼身目睹,并经历了屠杀的场面,刹那间顿悟成为虔诚的佛教徒,接受了“法胜”思想。阿育王公开宣布佛教为国教,停止武力扩张,以后不以战争作为王国对外政策的工具。“法胜”思想也影响到了近代以来的印度对外政策决策,〔21〕如“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提倡的非暴力抵抗的现代政治学说与“非暴力”的哲学思想,也源于阿育王接受的“法胜”思想和其推行的对其他宗教宽容与和平共处的政策。不仅如此,尼赫鲁与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以及缅甸领导人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受到了阿育王“法胜”思想的影响。
2.现实主义战略文化对印度对外政策决策的影响
古印度孔雀王朝时期的大臣考底利耶曾经提出“曼荼罗”体系的主张。“曼荼罗”理论认为:与自己最相近的邻国最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敌对者,或者是真实与潜在的敌人,而紧靠着自己周边国家的国家则是有很大的可能性能够成为自己的朋友。在考底利耶的“曼荼罗”体系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每个国家都将自己邻国设定为非友好的、贪婪的和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因此印度国王首先必须要清楚自己在“曼荼罗”体系中的位置才能获得成功。在此基础上作出战略上的选择包括和平共处、中立、进攻、联盟、战争与双重政策六种。在《政事论》中,考底利耶提出遵循“鱼的法则”,国王能够存活下来的途径就是拥有最高,或者说是顶尖的权力,只有当自身的势力足够强大,才能遏制“大鱼”的吞食。〔22〕“这些现实主义战略文化长此以往慢慢成为影响印度对外政策决策的主流。”〔23〕“曼荼罗”理论在提供了判断敌友的基本标准的同时,还提出了整体战略观。除此之外,印度国内的种姓制度文化更强化了印度对世界持有等级观念的看法。很多印度人都认同的观点是“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理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一种‘婆罗门’式的世界观”。〔24〕
3.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文化对印度对外政策决策的影响
160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批船只抵达印度,其后英国逐渐开始通过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在印度次大陆开辟殖民地。英国政府从1858年开始接管英属东印度公司,英国正式进入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时代。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国除了在印度掠夺财富大搞殖民扩张外,也对印度民众进行殖民文化教育。特别是印度的一些精英人士,在接受英国殖民文化教育后,既不满英国的殖民统治,又接受了英国殖民统治的许多观念。例如,印度在被殖民统治前是由许多土邦组成的,它们对海洋基本上没有战略概念,但在印度独立后,部分印度精英人士开始对印度洋持有一定战略理念。“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开始思考我们与大海之间的紧密关系了。”〔25〕印度著名的外交家潘尼迦的说法更加明确:“谁把控住了印度洋,谁就能把控住整个印度。”〔26〕印度独立后,实际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印度有些邻国的某些宗主国权力。以上的主张决定了印度的地区战略目标主要包括:第一,使地区的其他国家接受印度的领导国地位或印度某种程度上的宗主国地位;第二,促使区外主要大国对印度这一领导国地位的认可;第三,确保印度在南亚地区的领导国地位。
(三)印度国会与反对党对印度对外政策决策的影响
印度国会与反对党对印度对外政策决策具有一定影响。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来自英国,其议会民主制在整个政治过程上和英国非常相近,即当总理行使国家权力时受到国内政治力量的制约。由于总理是议会中的多数党领袖,因此多数党内部尽管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意见,一般都是支持总理决策的,但也会有多数党主流派迫使政府调整政策的情况发生。例如,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前,印度执政党国大党内部主流对华态度基本上是强硬和不妥协的,他们主要来源于国大党的右翼,排挤了对华持温和观点的一派,对尼赫鲁形成强大的压力,加快了尼赫鲁政府向对华采取敌对政策转变的速度。〔27〕
印度反对党及其议员需要扮演好“忠诚国家的反对党”角色。如1959年印度人民社会党领袖在德里举办的一次民众大会中表示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印度”的举措进行攻击,明确要求印度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击退“在印度领土上的”中国军队。〔28〕中央邦人民社会党主席卡马特宣称,他始终认为,如果个人或国家必须在懦弱和暴力二者之间作一抉择,那应当选择暴力,“让我们在边境地区把民兵组织起来。如果我们希望的话,让我们组织另外一支印度国民军”。〔29〕这些言论助推了尼赫鲁政府对华采取敌对政策。
(四)印度公众舆论对印度对外政策决策的影响
印度公众舆论可以分为印度国内媒体和印度思想库两大部分,都对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有一定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末期,由于尼赫鲁政府实施外交开放政策,印度国内媒体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力逐步上升。特别是1959年后,印度国内媒体对中印边界事务的关注度高涨。印度国内各大媒体利用“空喀山口事件”和“朗久事件”向政府施加压力。鼓动政府不与中国谈判,而是加强边境防御,“重新评估”中印关系;支持尼赫鲁拒绝中国关于中印各自撤军的建议。
印度对外政策决策受印度思想库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例如,印度思想库在1971年“东巴危机”期间首次参与到广泛的政治活动中,时任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所长的K·苏布拉曼亚姆(K.Subrhamanyam)代表了印度国内要求立即发动“解放”东巴基斯坦战争一派的观点。他主张东巴事态发展可以为印度肢解巴基斯坦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而解体巴基斯坦恰恰符合印度利益。〔30〕这些智库的观点对英·甘地政府作出军事肢解巴基斯坦的决定产生了影响。又如,印度思想库的一些专家积极鼓吹印度拥核的必要性。经济学家拉贾·克里希纳(Raj Krishna)1965年发表文章《印度与核弹》,提出为了制衡中国,印度唯一的选择是获取核能力。〔31〕1973年苏布拉曼亚姆表示印度应当掌握核武器,以此来敦促核武器大国裁减核武器,以确保印度不受核讹诈和威胁。〔32〕另一位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所长贾斯吉特·辛格(Jasjit Singh)宣称,只要拥有核武器,无论是否部署,都算有了安全保护伞。以上这些来自智库专家的观点,对瓦杰帕伊政府作出核试验的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三、双层博弈理论视阈下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机制在洞朗事件中的运作
本文借鉴了双层博弈理论,构建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机制在洞朗事件中的运作框架。1988年,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Putnam)最早将“双层博弈”的概念带入国际关系研究之中,以此来分析国际谈判中国际与国内因素之间的互动。〔33〕根据这一概念,政治领导人们会在国内与国际这两个舞台上同时进行着自己的“演出”。政治领导人们努力运用国际与国内这两个舞台来实现不同的目标,但与此同时也会面临着来自两个舞台不同的——有时会是相反的——压力与制约。普特南指出:“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通过强迫政府采用有利(favorable)政策以此寻求符合自己的利益,但是政治家会通过建立联盟在这些集团中寻求权力。在国际层次上,国家通过寻求利益最大化以提髙自身满足囯内需要的必要能力。因此,只要主权国家存在,还处于相互依赖的状态中,位置处于中心的决策者(central decision-makers)就不可以将这两层中的任何一层博弈忽视掉。”〔34〕
通过双层博弈理论可以得知,印度在洞朗事件中的对外政策决策,源自印度政府首脑在国际层面博弈与国内层面博弈,以及这两个层面相互博弈之下妥协的结果。从这一理论出发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洞朗事件中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有如下主要特点:
(一)莫迪政府的“强人政治与集体决策”机制在内外因素博弈下作出派遣印度边防人员进入中国境内干预中国边防部队在洞朗地区正常活动的决策
2017年6月18日,印度300多名边防人员携两台工程机械以及数十支枪械于中印边界锡金段越过边界线,进入中国境内。干扰中国的施工人员进行正常作业,由此引发中印洞朗对峙事件。〔35〕此次印度越过的是中印共同承认的锡金段边界线,此边界线是中国与印度到现在为止唯一已划定过的。相比此前印方在未正式划定的东、中、西段边界的越界行为,这次的洞朗越界行为具有明显的挑衅性,对抗程度更高。中国在西藏洞朗地区进行施工之前,已将计划提前告知印方。洞朗事件是自1987年以来,中国与印度两国所碰到的最紧急的边界对立与僵持。
从印度内部因素来看,2014年莫迪不仅凭借民众高支持率赢得大选就任印度总理,而且莫迪领导印度人民党在议会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政府和支持性政党合二为一,由此“悬浮议会”结束了,政府不再轻易受到变幻莫测的联盟政治的左右与影响。具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莫迪在上台后接连推出新的改革措施,莫迪的新政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经济指标不能兑现其最初的竞选承诺的情况,国家债台高筑的同时印度国内形势也十分动荡,各方矛盾处于不断被激化的状态。种种压力之下的印度政府选择在洞朗制造事端,这样做不仅可以转移国内矛盾的焦点,也可以刺激国内民族主义,以便于保持自己较高的支持率。因此此次对峙对莫迪政府来说,最好的结果是占有洞朗地区,次之是将洞朗地区转变成为有争议的“三国交界区”。
从印度外部因素来说,莫迪上台以后,将成为“领导性强国”(leading power),当“世界领导”(world leader)和“全球领导”(global leader)作为印度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36〕不断充实并完善“领导性强国”这一概念的实质和内涵。在洞朗制造事端也是在这一战略指导下,在国际上谋取利益的先手棋。
美国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就想要将印度拉入美国“印太战略”的战略伙伴国网络。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2015年1月受莫迪邀请,以主宾身份出席了印度共和国日庆祝活动,奥巴马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受邀参与印度国庆活动的美国总统。除此之外,他也是唯一一位在自己任期内两次访问印度的美国总统。在印度访问期间,美国与印度共同发表《美印关于亚太与印度洋地区的战略视角联合声明》。〔37〕特朗普上台后,在2017年底推出“印太战略”,美国想要成功实施“印太战略”的关键就是拉拢印度。〔38〕日本和澳大利亚也在拉拢印度,企图形成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印度相当于将在洞朗挑事当作是递交给美国的投名状。
但印度对中印实力对比作出了错误的评估。印度认为自己经济这几年发展势头快,印度国内经济实力大幅增强;印度加强山地部队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中印边境印军占有较大优势;中国军队正在军改过程中,减少了驻西藏山地战精锐部队的编制和数量,实力处于下风。莫迪政府选择洞朗制造事端在战术上也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他认为,印度在洞朗附近地区兵力相对占优,洞朗的地形又有利于印度增兵;中国在此地区的国防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人员和装备不足以对印度形成足够优势,增兵只能利用唯一的道路,还要克服1400米的海拔差。印度宣称,由于洞朗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中方修路行为不但单方面地改变了三国交界点的现状,还对印度境内连接本土与东北部七邦的西里古里走廊构成了一定的战略威胁。
历史上,1998—2013年,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机制处于“集体决策”阶段,印度政府在对待中印边界问题上相对谨慎。而在1947—1997年,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机制处于“小集团决策”阶段,出现了1962年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界推行的“前进”挑衅政策和1987年5月印军主动越过边境中方实控线对我桑多洛河谷哨所进行武力试探事件。洞朗事件则是莫迪政府“强人政治加集体决策”机制在评估了印度国内外因素后作出的决策,企图以此提升国内支持率,并在国际上捞取好处。可以肯定的是,印度在强势政府掌权时,在中印边界主动挑事的可能性大于印度对外政策处于“集体决策”机制时。
(二)莫迪政府妄图通过双层博弈在中印洞朗对峙中向中方施加重大压力
印度边防人员越过边界线进入中方境内的行为是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威胁中国安全利益的不端行为。对于这样的冒犯,中方本着最大善意,保持高度冷静与克制,迅速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与底线。但在此基础上,中印边防部队仍在洞朗地区维持了72天的对峙。
印度派遣军事人员越过边界线阻止中方施工,本质上是以一种制造事前成本的方式,对外展示对抗的决心。在对峙形成后,莫迪政府一方面在国际层面博弈,另一方面在国内层面博弈。在国际层面,为了进一步展示决心和迫使中国让步,印度做出了一系列展示武力的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军在洞朗地区附近印度境内部署了众多军力,也做好了在短时间内迅速调动军力的准备。驻扎在该区域的印度陆军第17、20和27山地师以及其他山地作战部队保持高度戒备,可随时应付突发状况。7月初印方从其驻不丹部队向洞朗地区增援2500名士兵,同时对驻扎在锡金东部和北部的印度第63、112旅,各有超过3000人的作战部队分别作了必要的动员。〔39〕印度政府、政要拉高调门,其目的是要让世界“重视”印度的“实力”和“决心”。
同时,印度媒体不断向世界宣传,企图证明派遣军队进入洞朗地区中方境内的正当性。例如,《印度时报》提出五点证据:第一,印度认为该地区属于不丹,在不丹皇家军队的求助下,印度才出面让中国军队“撤离不丹领土”;第二,即使中印就锡金地区边界达成一致意见,但仍在涉及印度、不丹与中国的三国交接点处有分歧,尽管三国在2012年签署了有关三国交界点问题处理的谅解文件,要求通过协商来解决三方的边界事务;第三,印度单方面认为《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属于“无效”条约,原因是那时的中国政府对西藏没有控制权;第四,印度认为中国外交部有刻意隐瞒事实的行为,虽然中国外交部从印度前总理尼赫鲁的信中摘取了部分内容,该内容表明印度政府已接受1890《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其中洞朗地区也包括在内;第五,中国还未与不丹建交,在没有与不丹取得联系的前提下中国就认为洞朗地区属于自己的是错误的。〔40〕这些论据似是而非,但企图蒙蔽世界舆论。
在国内层面,印度罗织以上这些论据,也是因为其有欺骗国内民众的需要。2017年8月15日,在印度第71个独立日,莫迪总理宣称“国家安全是首要任务”,要在2022年之前建成“新印度”。他也借此给民众鼓励即“要有改变国家的决心”,他还声称印军“不容外界小觑”,“不管是在网上还是现实、海上或陆上,印度都强大到足以扭转局面,印度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对抗任何层面上的外敌”。〔41〕这是为了提高印度人的士气,当然,这些话也是说给国际社会听的。
印度在中印边境争议地区之外发起对峙,是向国际、国内观众表明印度对抗中国的决心。总体来说,印度采取的是弱者的策略,为了对抗实力强大的对手,必须展现出更强硬的决心。
(三)在双层博弈中渐处下风的莫迪政府不得不将印方越界人员与设备撤回边界线的印方一侧
实际上,莫迪政府在中印洞朗对峙的双层博弈中屡遭挫折,未能到达预期目的。从国际层面上看,在现场的中国边防部队对越境印军采取了十分紧迫的应对措施。同时,中方紧急通过外交途径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对印方不法的越界行为表示了强烈抗议与斥责,要求印度在第一时间内将仍处越界位置的印度边防部队撤退到边界线印方一侧。中国国防部2017年6月29日表示,“希望印度个别人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发表这种叫嚣战争的危险言论”。〔42〕中国国防部同时也承认解放军新式坦克正在西藏进行实验。〔43〕7月4日,解放军公布西藏军区某旅开赴海拔5100米陌生地域进行实弹演习的画面,该旅装备有自行防空炮、主战坦克等重型装备。解放军西部战区西宁联勤保障基地组织了横跨中国西部的大规模军队后勤保障演习,其间数百辆军车将上万吨战备物资运往昆仑山南麓。〔44〕7月24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提醒印方“不要心存幻想,勿抱有不切实际的空想”,“撼山易,撼解放军难”。〔45〕8月3日上午至4日凌晨,新华社、外交部等先后对印方的越界行为发表声明,在揭露印方非法越界的恶劣性质的同时,强调中国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印度在洞朗制造的事端,也有对中国“秀肌肉”以及对不丹和尼泊尔施加压力的意涵。来自“不丹新闻网”的旺查·桑杰(Wangcha Sangey)2017年7月6日发表署名文章,公开谴责印度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过“铁腕政策”对不丹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控制,阻止中国与不丹进行边界谈判,“归根结底是由于印度政府担心,签署边界协议后,中国与不丹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会正常化”;一旦不丹与中国建立起稳固的外交关系,“这将增强不丹的主权地位,不丹也就会不再很容易地成为印度的代理人,尤其是在国际政治的敏感问题中”。〔46〕
莫迪政府在国内层面博弈中也一筹莫展。〔47〕2017年7月8日反对党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前往中国大使馆与中方官员会面,还会见了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了解有关洞朗对峙的信息。〔48〕站在反对党的角度,他们不希望印度在此类问题上一再挑战中国的底线。不仅如此,印度国内问题也让莫迪政府焦头烂额。印度本来以为可以通过在洞朗制造事端,以此来缓解国内存在的矛盾,但是国内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普通民众的不满却让各种危机频发。8月上旬,印度大约3800名公共汽车司机举行罢工;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因失业率高和农村经济发展不景气,民众多次走上首府孟买街头抗议;印度近百万银行职员举行了全国的大规模的罢工游行示威,反对印度当局所推广的银行变革政策,由此造成印度国有银行业务大面积停摆;印度西北部宗教组织“社会福利和精神组织”头目古尔米特·拉希姆·辛格事件引发的社会骚乱不断发酵,造成30多人死亡与300多人受伤;印度首都新德里等多个地方的局势十分紧张,纷纷进入紧急状态。〔49〕
在中国表示了坚定立场、发出严厉警告,并进行武力威慑的情况下,加上印度国内的这种形势,莫迪政府不得不考虑撤走进入中国领土的印军。其实,莫迪本人从一开始就留有后路,他没有就事件发布任何公开的强硬声明,这为后续策略选择保留了灵活性,为印度政府后续更改政策目标留有转圜余地,也可以在谈判策略选择上减轻来自国内层面的压力。在洞朗危机期间,当时担任印度外长的苏诗马·斯瓦拉吉(Sushma Swaraj)不断强调战争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耐心和言语克制对问题的解决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失去耐心只会激怒对方”。〔50〕时任印度内政部长拉杰纳特·辛格(Rajnath Singh)通过印度新闻信息局也对洞朗对峙发表自己的观点,“希望印度和中国可以尽快解决洞朗对峙,……印度没有扩张的打算,也不会攻击别国。冲突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和平才是我们一直所渴望的”。〔51〕
当洞朗对峙进入第三周,2017年7月初,印方开始试探通过谈判缓和危机。印度媒体曝出莫迪希望在7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汉堡峰会期间与中方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7月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及是否有相关安排时,没有作出正面回应。〔52〕援引中方消息人士的印度媒体称,中方认为当下并不具备举行中印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气氛”。〔53〕7月8日,印度外交部官方推特发布了中印两国领导人在汉堡峰会大厅握手的照片。〔54〕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拒绝认为中印领导人在汉堡峰会期间举行了双边会晤,并就洞朗问题再次重申中方的主张,“越界的印方边防人员应当即刻撤退回到边界线的印方一侧,这一切行动都将是中国与印度两个国家之间展开一切有意义对话的条件与基础”。〔55〕时任印度外交国务秘书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表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密,不能让边界争端导致中印两国留下永久性伤害。苏杰生的举动被认为是试着给两国当时的紧张关系降温。
随着洞朗对峙的持续,印度政府多次公开表示,希望通过外交渠道解决中印边境部队在洞朗对峙的问题。〔56〕7月27—28日,时任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Ajit Kumar Doval)来北京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由于此时印方主动缓和危机,中国领导人最终决定接见多瓦尔。〔57〕这次会见是为双方能够和平解决洞朗对峙问题所做出的努力。
2017年8月28日,洞朗对峙以印方同意撤离越界人员,中方同意暂停施工结束。就在28日当天,中方公布“印方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中方现场人员对此进行了确认”。〔58〕印度外交部的简短声明称,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双方保持外交接触,双方同意现场人员“相互脱离接触”(Disengagement)。〔59〕9月3—5日莫迪总理参加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以此来应对洞朗对峙结束所产生的影响。莫迪政府在中印洞朗对峙内外双层博弈中遭到的挫折和困难,促使其从中方领土撤军而结束这场危机。
注释:
〔1〕〔7〕〔8〕〔9〕〔10〕V.P.Dutt,India’s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Delhi: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Ltd,1999,pp.80,107,109,110,141.
〔2〕张历历:《新兴国家外交决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2页。
〔3〕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428-429页。
〔4〕吴永年、赵干成、马孆:《21世纪印度外交新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81页。
〔5〕Steven A.Hoffmann,“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47.
〔6〕张清敏:《“小集团思维”:外交政策分析的特殊模式》,《国际论坛》2004年第2期。
〔11〕〔27〕〔28〕〔29〕宋海啸:《印度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与模式》,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第218-219、79、84、84页。
〔12〕Milan Vaishnav, “Opinion:2019 general election will be no cakewalk for Narendra Modi,BJP”,Hindustan Times,April 16,2018,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the-2019-general-election-will-be-no-cakewalk-for-narendra-modi-bjp/story-TVxD2ZavgoAHWwBhbZc8pI.html.
〔13〕“Modi-led BJP wins Indian elections:Election Commission”,Xinhua New Delhi,May 24,2019,http://english.sina.com/news/2019-05-24/detail-ihvhiews4145262.shtml.
〔14〕“印度教特性”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最初由印度思想家萨瓦卡(Savarkar)于1923年提出,认为印度是共同地理、种族联系和共同文化结合起来的政治共同体,是“印度教、印地语、印度斯坦”(Hindu,Hindi,Hindustan)的结合。
〔15〕C.Raja Mohan,Modi’s World:Expanding India’s Sphere of Influence,Noida: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India,June 2015.
〔16〕Sanjay Kumar,Pranav Gupta,“Why PM Modi Remains Critical to BJP’s Fortunes”,March 4,2019,https://www.livemint.com/news/india/why-pm-modi-remains-critical-to-bjp-s-fortunes-1551718226157.html;“The Most Powerful PMO in India’s History”,October 10,2017,https://www.rediff.com/news/special/the-most-powerful-pmo-in-indias-history/20171010.htm.
〔17〕Kanchan Chandra,“Emperor Modi Ended the Gandhi Dynasty”,Foreign Policy,August 8,2016.
〔18〕Valerie M.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Theory”,Lanham·Boulder·New York·Toronto·Plymouth,UK: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7,p.5.
〔19〕〔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文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16页。
〔20〕张力:《“印太”构想对亚太地区多边格局的影响》,《南亚研究季刊》2013年第4期。
〔21〕〔英〕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徐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3-206页。
〔22〕〔印度〕潘尼迦:《印度简史》,吴之椿、欧阳采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228-238页。
〔23〕Imtiaz Ahmed,State and Foreign Policy:India’s Role in South Asia,New Delhi:Vikas Publishing House,1993,p.223.
〔24〕George Tanham, “India’s Strategic Culture”,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1992,p.130.
〔25〕Kousar J.Azam,ed.,India’s Defence Policy for the 1990s,New Delhi:Sterling Publishers,1992,p.70.
〔26〕〔印度〕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德隆、望蜀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81、89页。
〔30〕〔印度〕S.辛格:《喋血孟加拉》,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94页。
〔31〕章节根:《印度的核战略》,2007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第27页。
〔32〕〔美〕斯蒂芬·科亨:《大象和孔雀:解读印度大战略》,刘满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82页。
〔33〕〔34〕Robert D. 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ummer 1988,Vol.42,No.3,pp.75,434.
〔3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http://www.fmprc.gov.cn/web/zyxw/P02017070802541371281020.pdf。
〔36〕任远喆:《印度外交理念的演进与莫迪政府外交变革初探》,《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10期。
〔37〕U.S.-India Joint Statement,“US-India Joint Strategic Vision for the Asia-Pacific and Indian Ocean Region”,January 25,2015,available at: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4728/USIndia_Joint_Strategic_Vision_for_the_AsiaPacific_and_Indian_Ocean_Region.
〔38〕门洪华:《新时代的中国对美方略》,《中国战略报告》(第7辑),上海:格致出版社,2020年,第233-243页。
〔39〕“India Boosts Troop Presence Near Face-Off Site with China”,The Times of India,July 11,2017,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ndia-boosts-troop-presence-near-face-off-sitewith-china/articleshowprint/59536954.cms.
〔41〕《莫迪独立日演讲:5年内打造“新印度”,国家安全是首要任务》,Sina新闻中心,http://news.sina.com.cn/o/2017-08-15/doc-ifyixcaw5052535.shtml。
〔42〕《2017年6月国防部例行记者会文字实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http://www.mod.gov.cn/jzhzt/2017-06/29/content_4784102_3.htm。
〔43〕《外交部霸气回应印防长:2017年的中国也与1962年不同》,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154398809_601268。
〔44〕《西宁联勤保障中心紧贴实战开展跨地域机动演练》,《解放军报》2017年7月17日。
〔45〕张茜:《国防部回应中印对峙问题:撼山易,撼解放军难》,《中国青年报》2017年7月25日。
〔46〕查希、张骜、李德意、刘洋:《印度你在越界事件中的小算盘被不丹学者揭露了》,Sina新闻中心,http://news.sina.com.cn/o/2017-07-07/doc-ifyhweua4194429.shtml。
〔47〕〔49〕孟庆龙:《从印度的心态看洞朗事件》,《边界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5期。
〔48〕Aurangzeb Naqshbandi,“After Morning of Denials,Congress Accepts Rahul Gandhi Met Chinese Envoy”,Hindustan Tmes,July 11,2017,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amid-sikkim-standoff-rahul-gandhi-met-chinese-envoy-congress-confirms/story-uy38DjacYfBCb6xkVIhyQN.html.
〔50〕Doklam Row,“India Reasonably Sure China Does Not Want War despite Angry Rhetoric”,Hindustan Times,August 4,2017,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india-saysborder-stanoff-with-china-can-be-resolved-through-talks/story-sezoSO74OK1b4Xq81s8i1N.html.
〔51〕Press Information Bureau,Government of India, “Hope Doklam Standoff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to be Resolved Soon:Shri Rajnath Singh”,August 21,2017,http://pib.nic.in/newsite/PrintRelease.aspx?relid=170125.
〔52〕《2017年7月6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ipc.fmprc.gov.cn/chn/fyrth/t1475878.htm。
〔53〕“Atmosphere not Right for a Xi-Modi meet in Hamburg:China”,The Times of India,https://www.dnaindia.com/world/report-atmosphere-not-right-for-a-xi-modi-meet-in-hamburg-china-2493685.
〔54〕“PM Modi meet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SCO Sidelines”,The Times of India,July 9,2017,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pm-modi-chinese-president-xi-jinping-on-scosidelines/articlehowprint/59064282.cms.
〔55〕《2017年7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ipc.fmprc.gov.cn/chn/fyrth/t1476699.htm。
〔56〕谢超:《观众成本理论的局限及批判:以洞朗对峙中的印度为例》,《南亚研究》2019年第1期。
〔57〕印度此时主动减少在对峙现场的士兵人数和设备数量。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http://www.fmprc.gov.cn/web/zyxw/P02017070802541371281020.pdf。
〔58〕《2017年8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487864.shtml。
〔59〕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Government of India,“Press Statement on Doklam Disengagement Understanding”,August 28,2017,https://www.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28893/Press-Statement_on_Doklam_disengagement_understa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