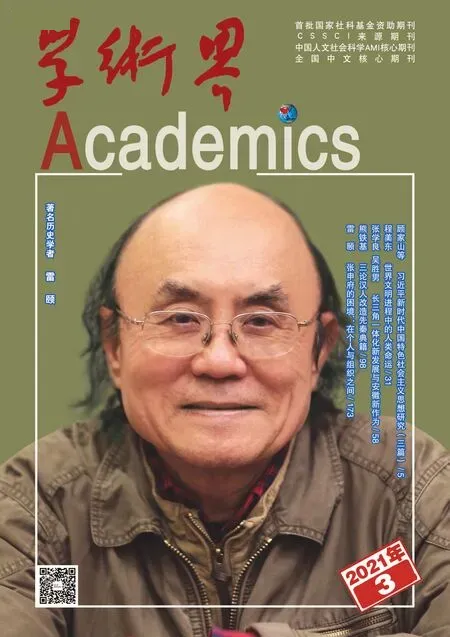中国政府承认与继承史考〔*〕
2021-04-15罗国强
罗国强
(武汉大学 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在中国未被纳入国际法体系而是实施自成一体的朝贡体系的古代,并不存在国际法意义上的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尽管改朝换代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基于朝贡体系的特点,其他国家与中国并非平等的主体,而是名义上臣服中国皇帝的藩国或贡国;“中国”也只是大一统情况下的泛称而非正式的国家名称,有关政权无论是否实现大一统都更为强调中央政府(朝代)而非国家的“正名”,这些情况与西方国际法的逻辑虽然不能说毫无类似之处,但也确实基本上难以融合。因此,考察中国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之历史,只能从中国被纳入国际法体系的近代时期开始。
自清政府统治后期,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建王朝所主导的延续千年的传统朝贡体系,并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纳入国际法体系,客观上使得国际法开始调整中国政府的更迭问题,这就导致了国际法意义上的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在中国开始出现。
从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到中华民国政府的成立,及至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成为“中华民国”正统,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虽然曾经有过形式上的统一,但实质上处于长期的内战与分治状态之中。这其中除了个别情况涉及到国家承认问题(外蒙古)〔1〕之外,其他情况所涉及的都是政府承认问题。为此,本文拟从政府承认与继承的角度,来考证其大致的历史脉络。
一、中华民国政府取代清政府
(一)政府更迭之历史进程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发表对外照会,明确要求各国承认军政府为交战团体。起初列强对此态度暧昧,鲜有明确表态。列强虽然对照会予以回复,并先后表示中立,但并未明确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英国等默认驻汉领事与军政府的交往,并未对军政府的照会提出有针对性的否定声明,这些举措虽然不能等同于正式承认军政府,但隐约已经有了暗示承认的意思。也就是说,列强考虑给予军政府作为交战团体事实上的承认,但尚未作出此项决定。
有学者指出,英国等国的态度主要是基于三点原因:一是革命进展迅速,在各国尚未来得及作出反应时,军政府已经有了自立的基础,不但控制了相当的地域,而且拥有了稳固的军事力量,这些因素已经构成了一个交战团体的基本要素;二是革命军处处照顾了各国在华的利益,可谓“举动文明”,地方秩序良好,并无排外性质,这些举动无疑赢得了列强采取暂时观望的态度;三是清政府仍然是名义上的全国性合法政府,在形势并未完全明朗以前,如果贸然承认军政府为交战团体,必然会引起清政府的抗议,并最终损及他们的在华利益。〔2〕
但此后不久,武昌起义的影响力席卷全国,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5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尽管宣布中立不仅意味着列强不干涉中国内战,还意味着其不会主动改变法律上承认清政府的既有状态,但对于列强而言,其至少要在事实上承认辛亥革命军为中国内战的交战团体,并在事实上与之交往,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1月5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呼吁“深望吾国得列入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不徒享有种种之利益与特权,亦且与各国交相提挈”,〔3〕这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次通过其国家元首要求获得列强的承认,在此,虽然孙中山是以“吾国”的名义提出主张,在其严格法律意义上,这一主张的实质是要求经由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政府取代清政府获得各国正式的、法律上的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上述主张虽经多方提出,但未获得英、法、俄、日等列强的明确答复。〔4〕
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次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外务部致电原清政府派遣的各驻外使臣,“所有出使大臣改称临时外交代表,接续办事”。〔5〕袁世凯接替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不久,临时政府外交部致电各外交代表称,“所有满清前与各国缔结各项国际条约,均由中华民国政府担任实行上之效力,凡已结未结及将来开议各项交涉案件,均即由驻在国之临时外交代表继续接办。”〔6〕
由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虽然名为“临时”,听起来似乎不符合法律上的政府承认的条件,但实际上已经顺利推翻清政府并取而代之,中国的政权已然不存在两个以上的争夺者,这就满足了一般情况下的法律上的政府承认所需要的条件;而无论是临时政府主导政治力量的转变(从辛亥革命军到北洋军)、国家元首的交替(从孙中山到袁世凯),还是国家首都的变迁(从南京到北京),都并不影响临时政府本身的唯一代表中国之政权的属性;与此同时,临时政府开始明确提出了全面继承清政府国内外权利义务的主张。
(二)政府承认与继承之落实
然而,在法律上的政府承认与继承的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其得到落实的情况是有差异的。
美国积极推动中华民国政府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英、俄、日等国则以延迟承认为要挟,乘机勒索中华民国政府,指望获取更大利益,这其中又以日本最甚;〔7〕法、德以及其他的欧洲和美洲国家则大致上采取跟风观望的态度。〔8〕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正式召开,此后数月内依法选举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议长等国家元首和政府主要官员。由于共和政体得到了明确的确立和正式的运作,并去掉了“临时”二字,英国等国延迟给予中华民国政府法律上承认的主要表面理由〔9〕也烟消云散。于是在1913年3月,美国使馆致电本国政府建议迅速承认中华民国,美国国会和政府很快作出了承认中华民国的决定,并告知了巴西、古巴、墨西哥、秘鲁等四个南美国家。于是巴西于4月9日、秘鲁于4月10日相继宣布承认中华民国,美国则于5月2日宣布无条件正式承认中华民国。〔10〕5月31日,中华民国政府“决定在向各国驻北京公使通告大总统选举结果之同时发一声明,言明中国政府将严格尊重其所承担之一切条约义务以及外国人根据既成惯例所享有之一切在华特权与豁免权等”,〔11〕从而获得了更多国家的支持。1913年10月6日,英、俄、法、日等13国宣布承认中华民国。
可见,尽管存在某些国家趁火打劫的情况,但基于对法律上的政府承认条件的充分满足,中华民国获得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认乃是必然,在美洲各国的推动之下,这一进程得以加快推进。及至袁世凯正式当选大总统后,中华民国政府在国际社会获得正式的、法律上的承认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由此中华民国政府也得以顺利继承了清政府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全部权利义务。
在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及至1928年期间,政府由北洋军阀所控制,故而又被称为北洋政府。因国力有限,且在那个“构成说”占主流的时代亟需获得国际承认,故而北洋政府对于列强此前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采取了全面继承的态度。但违反强行法的不平等条约被废弃乃是大势所趋,北洋政府也并非一以贯之地“卖国”,对不平等条约听之任之,而是在站稳脚跟后逐步提出了废止旧的不平等条约、订立新的平等条约的主张,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2〕此外北洋政府还代表中国,以国际社会平等一员的姿态,加入了《国际联盟盟约》(1920年加入)、《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1925年加入)〔13〕等多边性的国际公约。但不可否认,北洋政府也缔结了一些不平等条约。〔14〕
不过从条约继承的角度上讲,这里考察的只是政府更迭前后的情况,新政府获得承认并继承国际权利义务之后,不论是进一步修订旧有条约,还是订立新约的举措,都是一个新的国与国之间协商和讨价还价的过程,属于新的国家合意能否达成和落实的问题,并不属于政府继承的范畴。
大致说来,从1911年武昌起义掀起推翻清政府的内战,到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获得法律上的承认,中国政府的更迭历经两年左右的时间有了一个明确的结果,这属于比较典型的一般政府承认与继承的情况,其经过虽然是曲折的,但从法律上讲是较为简单的。然而,之后中国的政局越发动荡和复杂,使得政府承认与继承的问题不仅再次出现,而且越来越显现出特殊的属性。
二、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
(一)政府更迭之历史进程
袁世凯时期北洋政府的一系列独裁与阴谋举措引发了革命者的不满,“善后大借款”引发了国民党的反对,“宋教仁遇刺案”更是激起武力反抗。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号召各省宣布独立、武力讨袁,其实质是要推翻北洋政府的统治。这一主张一度得到南方数省军阀的响应,讨袁军与北洋军展开了内战,由此也就在理论上导致了一个叛乱团体的承认问题。但因“二次革命”不到两月即宣告失败,故而这一问题基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不可否认,“二次革命”揭开了中国军阀混战的序幕,从而使得涉及中国政府的承认问题有可能反复出现,甚至可能具有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的属性。
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实行事实上的终身总统制,并于1915年12月宣布准备实行帝制,其将在次年元旦登基并改元“洪宪”。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属于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主动修改宪法、改变政体,而并不属于革命性或者叛乱性的政府更迭,若顺利实施,并不会再次导致政府承认的问题。但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引发了另一次中国内战。12月25日云南首先宣布独立,接着,贵州、广西也响应,组成“护国军”进行讨袁战争,北洋军内部分化且战事不利,南方各省相继宣布独立。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不得不在1916年2月25日下令缓办帝制,3月22日又宣布取消帝制,并于6月6日病逝。此后数年间,北洋政府由国务总理段祺瑞实际掌权,其一度推举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并恢复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尽管各派势力仍然纷争不止,〔15〕但至少护国战争就此得以结束。由于袁世凯并未“登基”,此次中国政体的改变并未落实,加之护国战争短期内就取得了胜利,且其主要诉求不仅不是推翻现有政府或者改变政体,反而恰恰是维护“中华民国”、反对“中华帝国”,讨伐所针对的对象不是北洋政府而是袁世凯个人,故而此次内战并不会导致政府承认问题的出现。
在此后数年间,出现过数次大大小小的试图颠覆北洋政府的行动,包括1917年7月间张勋复辟清政府、1917—1918年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并自任大元帅)、1921—1922年“第二次护法运动”(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但这些行动影响范围较小且在短期内以失败告终。尽管孙中山主张自己所建立的广州政府才是真正符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政权并应获得国际社会承认,〔16〕但显然,国内法上的合法性最多只是一个各国考虑是否给予承认过程中的道义因素,并不是构成政府承认的要素——政府承认的合法性原则只要求不违反国际法,即便其他国家同意孙中山的主张,但基于有效统治原则,对于没有长期稳定有效控制至少部分领土的政治组织,是不可能给予政府承认的。因此,对于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列强基本上持不予承认的态度。〔17〕
而与北洋政府分庭抗礼、取而代之,并将政府承认问题真正摆上台面的,乃是以改组后的国民党为政治主导力量的“国民政府”。1923年底,孙中山完成国民党改组准备工作;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此后开始酝酿北伐。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汪兆铭(汪精卫)任主席。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随着北伐的进展,同年12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武汉国民政府不设主席,以汪精卫等五人为常务委员。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胡汉民为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7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合并。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占北京,各地(除东北外)军阀归顺,北洋政府的统治实质上被终结,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全国统一的宣言;同年10月,蒋介石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并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同年12月,掌控东北的北洋奉系军阀张学良通电全国,宣称接受国民政府管辖,取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挂上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由此北伐取得成功,北洋政权彻底寿终正寝,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取代北洋政府成为新的“中华民国”政府。
可见,此次历时两年多的中国内战,以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北洋政府土崩瓦解、国民政府取而代之而告终。尽管内战双方皆宣称自己是“中华民国”政府,〔18〕政权名称看似未变,但斗争的本质乃是国民党以暴力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并取而代之,属于非宪法性的政权更迭。这也说明,是否属于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不依赖于政权的名称,而主要是看政权更迭的方式,只要属于非宪法性的革命、叛乱、内战等以强制力量打破既有权力架构的情况,那么即便新政权使用跟旧政权一样的名称,也会存在政府承认的问题;而像袁世凯主动改行帝制那种情况,如果成功的话,即便新旧政权名称不同,也不会存在政府承认的问题。由此,在此次中国内战期间,国际社会必然面临着一个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之间作出政府承认选择的问题。
(二)政府承认与继承之落实
1.国民政府的政策
国民政府自广州时期起就始终积极主张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并一直尝试将有条件地继承此前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承认问题捆绑在一起解决。应该说,这一主张是符合国际法原则和规则、顺应时代潮流、契合中国民意的,有利于争取国内斗争的胜利和国际外交的成绩。
国民政府最初的主张是较为激进的“废除”或“取消”不平等条约而另订新约,但之后为争取列强的国际承认,其基调有所软化,对于维持旧约而“修正”或“更正”不平等条约的替代做法,在实践中也予以接受。实际上,这两种做法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首先因为都是在获取国际承认的时候作出的,故而都属于政府继承的范畴;其次因为在政府继承的情况下,不论是另订新约还是延续旧约,都会部分继承、部分否弃和修正原有条约内容,只是前者名义上更加彰显新政府的独立性,后者名义上更加体现新旧政府之间的承继性而已,而实际上有的时候,新政府为了尽快为自己正名而选择另订新约,其所承担的对价较之修订旧约更高。〔19〕此外,北洋政府时期签订的条约,也存在属于平等条约(如《中德协约》《中奥商约》等)的情况,但国民政府仍然主张废止和重订,甚至不惜付出更高对价,其实主要还是为了“正名”的问题。而像《国际联盟盟约》这样的平等基础上缔结的多边条约,由于既不需要修订不平等的内容,又不存在为了国民政府“正名”而重订的可能,国民政府就直接全盘继承了,压根没有提出与政府承认捆绑解决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上讲,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口号所针对的,原本应该是清政府签订、北洋政府继承的大量双边条约和少量多边条约(如《辛丑条约》),以及北洋政府签订的某些不平等条约(如《中日民四条约》),但实际上北洋政府签订的某些并非不平等条约的双边条约也被纳入“废约”的对象之中。但即便如此,作为新政府,国民政府确实有权选择自己继承条约的政策与方式,这样做也无可厚非。相当一段时期内主持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王正廷,是将废除旧约、另订新约作为原则和口号,但根本上其所主张的是一种刚性的修约,即在正当的外交手续中坚持废约的目标和立场;修约与废约是两种不同的手段,其目标是一致的,实是殊途而同归。〔20〕这就大致概括了国民政府的条约继承政策。
1926年12月,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日、美等国使节进行非正式谈话,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承认国民政府等问题,他强调:“国民政府现时所管辖之区域虽尚未及全国,但已统治大多数之省份,设未统治之省份举行总投票,则该区域人民亦必赞成归向国民政府,毫无疑义……英国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关于全国之问题,即不能同时与北京政府交涉此项问题。”〔21〕1927年1月,武汉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再次声明自己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同时不再坚持必须采用废约和另订新约的方式处理条约继承问题。而意欲建立独裁统治的蒋介石则深深感到,其所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必须得到帝国主义支持和外交承认。〔22〕为了得到列强的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不断根据形势需要调整外交方针和政策并积极向列强展示;当然,其所宣传的口径仍然是废约和另订新约,但在具体操作中具有灵活性,即能废止则废止和新订,不能废止则修订和更正。1927年12月,蒋介石在上海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强调北伐完成后最紧要的工作是外交方针的急速改定,将循外交常轨和国际公法正常进行,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23〕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发表宣言,要求同各国“应进一步而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同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专门发布了《重订新约宣言》《中华民国与各外国旧约已废新约未订前适用之临时办法》,其核心主张,就是只对业已期满之条约会明确予以废弃,而对于其他条约则事实上采取承认和修约的做法。〔24〕
2.列强的态度
列强对国民政府的承认态度是逐步演进的。北伐胜利进军后,列强开始尝试与国民政府接触,并考虑给予事实上的承认。1926年11月,英国国会议员崔威廉、工党首领马克多纳等都提出,广州政府已经达到了可以承认的程度;同年12月初,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在武汉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举行了多次非正式会谈,但蓝普森以中国尚未统一为由拒绝了陈友仁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正式承认国民政府的要求。蓝普森还表示,国民政府至少承认现行条约,取消反英运动,才能谋求承认;陈友仁对此表示同意,之后武汉国民政府确定了要求英方在修正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承认国民政府的方针。〔25〕美国虽然维持了对北洋政府的法律上的承认,但也于1926年底派代表迈尔前往武汉与国民政府接触。1927年3月,英国外相张伯伦表示,是否承认南京政府将视事实而定;同年5月他又指出,南京政府将是一个新的政府。
尽管1927年3月“宁案”〔26〕的发生一度造成了南京国民政府与列强关系的紧张,但后续的交涉也验证了列强给予南京国民政府事实上承认的必要性与可行性。1928年3月,中美双方就解决“宁案”达成协议,互换照会,美方在换文中用“南京当局”来指代国民政府,事实上的承认意味浓烈;此后不久,英、意、法等国也与国民政府分别以互换照会的方式达成了解决“宁案”的协议。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场交涉的成功意味着美英列强给予南京国民政府以事实上的外交关系,即“已承认中国之国民政府为一法律的实体”。〔27〕
而北伐军在内战中节节胜利并攻占北京之后,列强看到中国内战大局已定,遂加快了给予国民政府法律上承认的步伐,并开始正视国民政府提出的废止旧约、另订新约的主张。
1928年7月,美国政府代表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在北平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可见在美国政府的配合下,南京国民政府开启了在获取国际承认的同时,依据国际法部分继承(即重订或修订)不平等条约的进程——尽管国民政府修订的并非所有不平等条约,亦不涵盖条约内容之全部,但较之北洋政府起初为获取国际承认而全面继承不平等条约,之后要求重订或修订条约但进展缓慢、成效有限的状况,还是有了相当的进步;另一方面,这种订立正式条约的方式表明,美国虽然尚未声明给予国民政府法律上的承认,但通过其行动,已经默示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由此美国成为首个给予国民政府法律上承认的国家。同年11月,美国又以明示的方式,正式给予南京国民政府法律上的承认。
在美国的带动下,国民政府与德国签订了《中德条约》,与挪威、荷兰、瑞典、英国、法国订立《关税条约》,与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西班牙订立《友好通商条约》,也就等于这些缔约国默示地给予了国民政府法律上的承认。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12月的《中英关税条约》虽然采用另订新约的方式,但其附件明确规定,中方只能采用1925年关税会议所暂时议定的税率,且一年内不得更改之,可见虽是另订新约,但实际上仍会部分继承旧约的规定;此后英国于1929年1月正式给予南京国民政府法律上的承认。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撤废领事裁判权问题照会英、法、美、荷、挪等国驻华公使,上述各国均未明确反对。
日本原本打算再次借承认之机在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之间敲诈勒索、从中渔利,故而一再拖延给予南京国民政府法律上的承认,但在中国内战形势已经明朗无疑,其他列强均已顺应形势对国民政府作出法律上承认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在1929年6月,通过驻华公使向国民政府主席呈递国书的方式,正式承认了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5月,中日政府签署《关税协定》,为中国实现关税自主扫除了最后一个障碍。
而对于《国际联盟盟约》,南京国民政府予以全面继承,并在北洋政府倒台后顺利继承了在国际联盟中代表中国的权利。
可见,随着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进军,国民政府对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土实施了有效统治,这就使得列强承认国民政府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列强一开始维持了对北洋政府法律上的承认,而给予国民政府事实上的承认;而在北伐大局已定,北洋政府土崩瓦解,国民政府稳定地控制中国绝大多数领土之后,列强给予了国民政府法律上的承认,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撤销了对已经失去统治权的北洋政府的法律上的承认。应该说,这一进程基本上是符合国际法关于政府承认的条件的,即当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能够与北洋政府分庭抗礼的时候给予事实上的承认,而当国民政府实质上击败北洋政府并控制包括首都在内的全国大部分领土之后给予法律上的承认。当然,南京国民政府多次表态不采取激进方式废止或修订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也是一个促使列强放心作出法律上承认的因素。南京国民政府针对不同的条约采取了不同的继承政策,即全面继承平等的多边条约、部分继承(重订或修订)不平等的多边条约和双边条约,这种方式较为灵活,容易为政府承认与条约继承的捆绑解决带来突破,但同时也导致部分不平等条约义务在中国长期存在,直到抗战前后才基本废除。〔28〕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中华民国政府
(一)蒋介石政府的众多反叛者
蒋介石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创建者和实际控制者,因此“中华民国政府”又被称为“蒋介石政府”。蒋介石政府统治期间,实际上不断有意欲取而代之的反叛者。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汪精卫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出席,会议决议于9月9日在北平成立“国民政府”,阎锡山任主席。但支持蒋介石的张学良于9月23日进驻北平,北平“国民政府”被迫迁往太原,并于11月随着阎、冯宣告下野而解散。由于这个北平“国民政府”严格意义上的寿命只有十几天,往宽了说也只有一个多月,只能在理论上勉强算作叛乱团体,而实际上并无予以政府承认的必要。
1931年,国民党内不满蒋介石的胡派、汪派、桂系、孙科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于5月28日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汪精卫任主席。之后国民党内达成妥协,广州政府于12月22日取消。蒋介石虽一度下野且复出后仅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仍然实际掌控南京国民政府的大权,尤其是军权。此次另立政府虽然时间达到半年多,但却是以党内和平斗争的形式展开,没有引发内战,最终也因党内达成和解而平息了争端,故而实际上也没有作出政府承认的必要。
1933年,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不满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并与之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的做法,遂于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并发表《人民权利宣言》;11月21日,李济深等通电脱离国民党,随后发起成立“生产人民党”,以陈铭枢为总书记;11月22日,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担任主席,以福州为首都,废除南京政府年号并另立新国旗;12月下旬,蒋介石政府派军镇压;1934年1月上、中旬,延平、古田、福州先后被占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迁往漳州;21日,泉州、漳州相继失守,“福建事变”失败。这是一次国民党抗日派和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主导的政变,尽管采取了另立新党和国号的激进方式,但其实际控制区域仅限于福建省的部分地区,而且在极短的时间内宣告失败,影响范围和时间非常有限,难以引发事实上的政府承认。
抗战爆发后,日本在所占中国领土上策划了多个伪政权。包括1937年12月在北平建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在南京建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9年9月在张家口建立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40年这些傀儡政权名义上合并到汪精卫任“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的伪“南京国民政府”之中,但华北和蒙疆地区实际上不受伪南京政府的管辖。根据国际法,此种傀儡政权,不具备政府承认的构成要素,不符合有效统治原则中的独立性、合法性等要求,且同盟国政府对此负有不承认的义务,故而不应被承认为政府。〔29〕事实上,伪政府仅获得了日本、德国、意大利以及“轴心国”在二战中所建立的傀儡政权〔30〕的承认,并随着日本的战败于1945年土崩瓦解。因此,对于这些伪政权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存在政府承认的问题。
抗战期间,蒋介石政府一度迁都重庆,抗战胜利后还都南京。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宣布正式立宪,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迈入“宪政”时期。1948年5月20日,国民政府改行总统制,蒋介石担任中华民国总统,组建一府五院的中华民国政府。但上述变化,都是在同一个政权主导下,在其政治运作轨道内主动采取的措施,均不发生政府承认的问题。
可见,上述与蒋介石政府针锋相对的政权,除了“福建事变”中李济深政权被动宣告脱党以外,〔31〕基本在名义上仍然是属于中国国民党的政权,其本质是党内各派争权夺利。尽管是否属于党内斗争并不是衡量政府更迭是否正常的标准,但当时国民党的党内斗争具有习以为常、敌友态势多变、既对立又合作的特点,客观上减弱了斗争的对立程度;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争权夺利的斗争要么达成妥协,要么被外国侵略者操控和利用,未能真正地引发至少是可能的政府非宪法性更迭,故而并不符合政府承认的构成要素,不会在真正意义上带来政府承认的问题。
(二)中共政权对国民党政权的取代
而真正引发了中国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的,乃是中国共产党通过针对蒋介石政府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国民党的革命斗争所建立起来的政权。
从政府承认的角度来分析中共政权取代国民党政权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叛乱团体时期
在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是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反对北洋政府统治的重要政治力量,并对北伐的顺利进军发挥了积极作用。1927年4月和7月,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先后开始“清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斗争目标直指蒋介石政权。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由其掌控的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武装起义。尽管起义最初是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发动,但实际主导者为中共,因此本次起义可算作中共武装反叛国民政府的开端,由此也就为政府承认问题的提出创造了一个基本前提。当然,由于南昌起义之后,这支武装力量转战多地、频频受挫,未能对其所经过的领土建立较为稳定和有效的统治,实际上并不能导致事实上的政府承认问题的发生。而之后爆发的一系列中共领导的反对蒋介石政府的暴力革命(如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等),都具有类似的特征。
1928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整合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剩余工农革命军和当地的农民自卫军,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尽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地处偏远落后的山区且占地面积有限,但毕竟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而在其带动之下,其他大大小小的革命根据地也在中共的领导下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32〕尽管与国民政府派遣的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长期交战,且根据地初创时期的规模较小,即便发展壮大之后也往往只能局限在地方军阀彼此地盘的交界区域而很难扩展到中心城市地区,但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中共在这些革命根据地都能够维持较为稳定的统治。如此一来,从政府承认的角度来看,这就符合了事实上被承认为叛乱团体的条件,而由于这些根据地都归中共中央领导和统辖,故而被承认的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共及其建立的革命武装割据政权。
但确实,由于中共军队数量少、装备差,多数时候都在为生存搏杀而无暇顾及对外交往问题;根据地远离城市(包括辐射力较强的大城市和至少存在某些工业化设施、信息流通基本顺畅的普通城市),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经济落后、产业机构单一),较之同一时期与蒋介石政府针锋相对的政治势力及反叛者而言,影响力非常有限,国际社会对这一政权基本上采取了忽视的态度;即便是作为中共当时的指导者和主要国际支持力量的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给予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热情关注和真诚支持,〔33〕但也并未对中共所领导的这个散布在大大小小偏远山村的割据政权给予充分的重视,不认为有给予其事实上的政府承认的必要,而主要是从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角度去看待中共及其武装割据政权,并从党的层面给予指导和支持。
2.交战团体时期
至1931年,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13块革命根据地。其中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被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中央苏区鼎盛时期下辖60个行政县,人口435万,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根据会议决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毛泽东任主席,以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临时中央政府相继制定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等一系列法律文件。
中华苏维埃政权体制是借鉴和学习苏联的做法和经验而来的,是由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人民委员会、最高法院、审计委员会等机构组成。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机关。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选举主席团为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最高法院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司法机关。依据《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第六号训令)和《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等法律、法令的规定,基本按照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的要求,创立和完善了司法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临时最高法庭和各级裁判机构等人民司法机关;制定和规范了公开审判、便民诉讼等一整套司法制度。〔34〕
由此一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为一个事实上的政权形式已经成立,并具备了较为完备的政权组织结构,且其在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中国领土的部分区域(革命根据地)实施了较为稳固的统治,〔35〕颁布了宪法等基本法律文件,设立了各级政府机构,建立了统一的工农革命武装力量,并正式与蒋介石主导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尽管其所占据的地域仍然为中国领土上的边穷地区,国内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较小,但此种斗争已经具备相当的规模并且维持了相当时间的稳定统治,已经符合了事实上被承认为交战团体的条件。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使得中央苏区成为中共当时领导的所有根据地的中枢,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是中共领导的武装割据力量的国家政府形式之表现。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该政权改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取消了“临时”二字,更加彰显了政权的正式性和完备性。
在具备了完整的政府形态并达到交战团体的承认标准之后,中共领导的革命政权开始重视外交问题。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提出与苏联结盟;主张实行公开外交,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外债,收回租借地,驱赶帝国主义派驻中国的军队,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产业;不反对与世界各帝国资本主义的政府重新订立完全平等的条约,在苏维埃区域内,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不违犯苏维埃一切法令的条件之下,可以有经营工商业的自由。1932年4月15日,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对日本宣战。1937年5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了《告西班牙人民书》,对西班牙民主政府领导的武装斗争表示称赞和支持。当然不难发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其后续革命政权的上述外交政策,都只是单方面的主张和宣告,除了获得共产国际及其背后的苏联政府以及各国共产党从党的层面给予支持以外,〔36〕并没有在政府层面得到任何国家的公开回应;而在国民政府早已获得国际社会广泛的法律上承认,苏区规模小且位置偏远,与外界交流不畅,国际影响十分有限,且当时的中共革命政权忙于“反围剿”、内部斗争等生死攸关问题的局面之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其后续革命政权实际上没有精力和资源从事外交实务运作,也没有向国外派出任何外交使节。
而之后的历史发展,使得中共武装割据力量的交战团体属性有所变化,但同时也使得该政权获得国际承认的状况有所变化。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被迫放弃中央苏区,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同月,组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统一领导中央苏区留守军民的斗争。1935年5月,中共西北特委组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抵达陕甘苏区;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更名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12月,中华苏维埃政权改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宣布迁都延安。1936年,政权再度改名为“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对外继续沿用“中央西北办事处”的名义。尽管中央苏区以及南方各苏区失去了原有的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一度不再较为稳定地控制任何领土,交战团体的属性受到极大弱化;但陕北等少数革命根据地作为武装割据政权的一部分,仍然对其所辖区域维持了较为稳定的统治,使得中共革命政权的交战团体属性不至于完全丧失;而中共中央在陕北站稳脚跟之后,陕甘苏区实际上演变为新的中央苏区,这就使得中共武装割据政权的交战团体属性再次得以明确。而中共革命政权以长征的胜利、反对日本法西斯侵华战争为主题的国际宣传工作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取得了卓著的成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介绍长征的报告文学集《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记》)一经出版就震撼了世界;〔37〕更多的外国友人到苏区和抗日根据地访问和考察,并撰写了众多报道和著作;美国总统罗斯福也秘密派遣卡尔逊到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与毛泽东等人进行非正式的交流。〔38〕中共革命政权广泛对外交往的大门由此开启,从而为之后获得国际社会事实上的承认创造了有利条件。
而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为此,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22日,正式结束苏维埃国家政权形式,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国民政府所辖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中国工农红军所辖部队(包括在陕北的中央红军和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相继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至此,历时5年零10个月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共武装割据政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由于形式上被纳入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管辖范围,不再主张“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武装暴动推翻蒋介石政府,中共武装割据政权的交战团体属性就在质的层面出现了变化,成为受国民政府统辖并与之合作抗日的地方政权,不再具有交战团体的地位。这一状态一直维持到1946年国共内战再度爆发。
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中共不再作为从属于共产国际的支部存在,而明确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致力于参与或夺取国家政权的中国国内政党。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客观上导致国共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为避免内战再起,国共双方代表曾先后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美国也曾积极调停,但内战仍然于1946年6月再次爆发。而此时,中共政权经过多年的革命斗争和抗日战争的洗礼,不断发展壮大,其实际控制的领土面积大大扩展,人口数量大大增加,军队数量、质量和装备大大改善;虽然尚未占领中心城市,但也不再局限于边远山村,而是开始在广大农村乃至普通城市站稳脚跟;可以说,该政权无论是国内综合实力还是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都突飞猛进、今非昔比了。尽管此前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但中共革命政权在中国内部斗争中作为唯一能够与蒋介石政权分庭抗礼的另一派政治势力的地位,在国际上已经广为人知。因此,如果不爆发内战,国际社会还可以暂时不去正式讨论和面对事实上的政府承认的问题,一旦爆发内战,国际社会即刻就会根据中共革命政权对交战团体构成要素的满足,给予其事实上的政府承认,并进行事实上的交往。
当时中国的对外关系局势主要取决于跟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的关系。美国方面,1941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私人代表居里来华,其与周恩来在英国驻华使馆进行了会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与英美等国的联系和交往更为广泛,罗斯福在制定“扶蒋联共”政策之时就曾经指出,“我一直在同那里的两个政府合作”;〔39〕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同年11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访问延安并同毛泽东签订了有利于协调国共关系的协议草案;〔40〕而抗战胜利之后的美国的居中调停,本身也就意味着对于中国内部政权分立格局的承认,意味着若调停失败中共政权就将是内战中与蒋介石政府针锋相对的另一方。苏联方面,斯大林政府历来秉持从法律上承认蒋介石政府的政策,并通过1945年8月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以较小的代价攫取了不小的利益,〔41〕此项条约的签订本身也说明苏联给予蒋介石政府的乃是正式的、法律上的承认;而对于中共革命政权,尽管对斯大林政府的支持力度和影响,学术界存在争议,〔42〕但不可否认,苏联政府确实给予了某种程度上的援助和交流,〔43〕而这种援助和交流显然是以事实上的承认为基础的。
上述这些情况都说明,与井冈山和瑞金时期不同,国际社会已经清楚地知悉了中国政权内部斗争的局势,明白了中共所领导的革命政权在中国政局中的份量,故而内战一旦正式爆发,对中共革命政权作为中共内战的交战团体的事实上的政府承认就是水到渠成的了。当然,此种事实上的承认数量有限,且基本采用的都是默示的方式,既不会明确地、专门地去提及这个承认的问题,但也不会令其成为实践交往的障碍,事实上需要交往的时候就会去交往。这一是由于中共政权在内战基本胜利之前都没有提出明确的建政主张,而只是将其所辖军队由“国民革命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并表示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急于提出自己的国号明显不同);二是由于世界各国早就给予并仍然维持了蒋介石政府法律上的承认,在此情况下通常没有必要去刻意强调自己会给予内战中的另一方事实上的承认;三是由于中共政权地处农村,除了美苏两个大国之外,真正需要与之打交道的国家并不多,这对于多数国家来讲都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3.中央政府时期
解放战争爆发后,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分出了胜负。1948年三大战役结束后,战场走势逐渐明朗;1949年4月,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蒋介石政府对全中国的统治实质上被终结,大局已定。〔44〕中共政权开始从此前的交战团体,转变为取代蒋介石政府的新的中国中央政府,即通常所称的“新中国政府”。
1949年9月,带有制宪会议性质的由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及爱国人士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会议通过了带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决定将政权名称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至此,中共政权已经基本上符合政府承认的要素,能够被承认为新的中国中央政府,且基于当时占主流的承认性质“宣告说”,无论其他国家是否承认,一旦符合了有效统治的条件和有关国际法的原则规则,中共政权作为新中国政府的性质都能够得以确立,并应当被承认为新的中国中央政府,而即便有的国家不予承认,这一性质也不会因他国的态度而有所改变。
其实在南京解放之后,其他国家就已经在考虑给予新中国政府明示的事实上承认乃至法律上承认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经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建议,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了“共同阵线”政策,主张各盟友与其采取共同行动,不主动承认中共将要建立的新中国政权。〔45〕但英国的主张是从现实出发,承认中共的新政权,因为国民党政府“再也代表不了什么了”,这一主张得到了部分采取务实态度的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的响应。〔46〕新中国政府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成立后,不仅此前不去专门和明确触及中国政府承认问题的理由已经消失,而且新中国政府已经基本具备了取代旧中国政府获得法律上承认的条件,对此各国就必须作出明确的选择了。
1949年10月2日,苏联给予了新中国政府法律上的承认,并与旧中国政府断交;在此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民主德国、越南等)也相继给予了新中国政府法律上的承认。10月5日,英国外交部照会新中国政府外交部,表示愿意“建立非正式关系”,即先对新中国政府作出事实上的承认;12月25日,英国外交大臣照会称,将于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法律上的政府,愿与其建立外交关系、互换使节、在未任命大使前先派驻临时代办,并声明撤销对国民党集团的外交承认。〔47〕尽管由于冷战和朝鲜战争等原因,中英此后直到1972年才正式建交,但这并不妨碍英方所作的法律上承认的有效性;承认和建交虽有紧密联系(承认奠定建交的基础,建交进一步明确法律上的承认),但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发生的时间可以有所间隔。因此,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政府的西方国家,而瑞典则是第一个与新中国政府建交的西方国家(1950年1月14日承认、1950年5月9日建交),这在逻辑上并不矛盾。在上述国家的带动之下,仅在1949年12月到1950年1月之间,有相当一批国家给予了新中国政府法律上的承认。〔48〕
此后新中国政府获得正式承认的数量稳步上升。尤其是20世纪中后期的民族解放浪潮,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摆脱了殖民压迫而取得独立,并与新中国政府相互承认和建交,尤其是在70年代形成了一个承认与建交的高潮。〔49〕但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政府给予这些新独立国家的是国家承认,而后者给予新中国政府的则是政府承认,两者虽然能够被有关国家拿来进行这样的操作,但稍不注意就会引发混淆;加之这些新独立国家成立之时,新中国政府已经成立,其对于中国政权更迭的历史没有清晰的概念,这就导致了一些与新中国政府建交的发展中国家及其民众,对于与新中国政府之间相互给予承认性质之不同,存在概念上的理解偏差,从而留下某些法律隐患。
尽管因为意识形态和冷战阵营等问题,新中国政府在早已具备获得正式的法律上承认的资质的情况下,却迟迟未得到美国为首的多数西方国家的承认,也未能顺利继承旧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但尊重事实,给予符合了承认要素和条件的新中国政府法律上的承认乃是大势所趋。1971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新中国政府继承了旧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权利;1972年,中英建交,中日邦交正常化;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给予新中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法律上的承认并撤销了对旧中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法律上的承认。截至2019年9月底,与新中国政府建交的国家达到180个,〔50〕约占全世界国家总数的92.3%。
作为旧中国政府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分别迁往广州、重庆、成都、西昌之后,最终于1949年12月7日迁往台北,故而从此被称为“台湾当局”。1950年,解放军进驻大西南,解放海南岛、万山群岛与舟山群岛;1955年解放军相继攻占一江山岛和大陈岛。此后,虽未签订任何停战协定或者和平协议,但双方事实上未再开启战端,新中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旧中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都再无变动,即前者实际控制中国大陆、周边沿海地区以及部分南海岛礁,约占中国领土总面积的96%;后者实际控制中国台湾岛、澎湖群岛、金门、马祖以及部分南海岛礁(东沙群岛、南沙的太平岛和中洲岛),约占中国领土总面积的4%。
在台湾当局维持或者取得法律承认方面,1949年底其尚有“邦交国”47个;受朝鲜战争和冷战以及西方对中国中央政府封锁的影响,1969年其“邦交国”数量一度升至70个的历史高位;但随着新中国政府与西方关系解冻以及继承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台湾当局的“邦交国”数量持续下滑。截至2020年,台湾当局的“邦交国”为15个,〔51〕约占全世界195个国家总数的7.7%,这些“邦交国”无论是国家数量还是综合实力都处于绝对劣势,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极为有限;该政权在国际组织中不得代表中国,也不得使用其“中华民国”的官方正式名称,而只能以“中国台北”(Chinese Taipei)、“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Penghu,Kinmen and Matsu)等称谓从事经济与教科文卫等交流活动,不得涉足国际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国际组织及其活动。
在解放战争短期定局、长期延续、对峙而不战的局势下,一方面,新中国政府有效统治绝大多数中国领土,是毫无疑问的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另一方面,新中国政府的有效统治并非100%,毕竟有少数中国领土仍处于旧中国政府的实际控制之下,旧中国政府虽然失去了中国中央政府的地位,但仍得以作为中国内战一方的交战团体或地方割据政权而存在。而由此,就导致了涉及中国的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52〕——台湾问题,并引发了一系列法律上的难题。〔53〕
注释:
〔1〕1945年8月,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又称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取得苏联的支持,中方同意了诸多苛刻的条件,其中就包括同意承认外蒙古公民投票的结果。据此,在苏联的操纵下,外蒙古于同年10月举行“独立公投”,以零票反对的罕见票数通过独立案。中华民国政府于1946年1月公告表示接受公投结果,承认外蒙古“独立”。尽管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投”和“独立”,但由于这属于母国不反对的分离,故而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新国家并获得国际社会承认,成为了既定事实。尽管到了1953年,已经失去中央政府地位的“中华民国”政府(台湾当局)援引上述条约中苏联并未做到“不援助中共”等条件,宣布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并把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版图。但是,该条约中的有关条款早已履行,双方依约对有关领土所作的处分不会自动改变;更何况当时的台湾当局已经不具备代表中国签订、修改或者废止条约的资格,而实际上该条约是在新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于1950年2月另订新约之时被废止的——当然该条约被废止之前已经履行的权利义务和已经处分的领土并不会自动回转。为此,尽管长期占据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台湾当局曾经于1955年否决外蒙古分离后成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但在1961年未再行使否决权,蒙古国得以入联;2002年台湾当局也不再将外蒙古列入“中华民国”版图。
〔2〕侯中军:《“成立在我,承认在人”——辛亥革命期间中华民国承认问题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3〕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0-251页。
〔4〕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88页;陈三井:《法国与辛亥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7-148页。
〔5〕1911年,清政府派有驻外使臣的国家有英国、俄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美国、秘鲁、墨西哥、古巴、日本等15国;在中国驻有公使的国家有英国、俄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瑞典、挪威、丹麦、美国、秘鲁、墨西哥、巴西、古巴、日本等19国。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6页。
〔7〕日本一度力图主导中国政府的承认问题,并主张各国采取一致行动。其于1912年2月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政府承认问题的备忘录,后又于3月草拟了《关于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条件细目》,其最初提出承认中华民国的前提条件,是中华民国全盘接受清政府时期的全部债务和条约,外国保留在中国所享有之一切权利、特权及豁免;这一倡议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赞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也没有表示异议;但之后日本又进一步提出要一并解决中国政府向外国贷款的问题和满蒙问题等超越既有不平等条约的、损害中国主权、满足其自身利益的种种要求。参见郭宁:《寻求主导:日本与承认中华民国问题(1912—1913)》,《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3期。
〔8〕比如,1912年4月3日,北京政府令驻法外交代表向法国政府要求承认,但法国以中国政府未能达到日本所提出的承认条件为由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参见陈三井:《法国与辛亥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1年第2期。
〔9〕英国最初提出了加强西藏自治权的要求,在获得袁世凯政府的部分满足后,就给予中华民国政府法律上的承认提出了召开国会,制定宪法,根据宪法选出大总统,临时政府成为永久政府等形式条件。The American chargé d' 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rch 18,1913,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13 (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0),p.98。
〔10〕顾则徐:《美国率先承认中华民国背后的国际争斗》,腾讯网,http://cul.qq.com/a/20160305/022144.htm。
〔11〕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446页。
〔12〕北洋政府借参加一战之机废止了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条约,收回了两国的不平等特权,之后订立了平等的《中德协约》和《中奥商约》;在巴黎和会上要求修改条约;对无约及新成立诸国坚持平等订约,不愿再给予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由此与玻利维亚、波斯、希腊、芬兰、波兰等国订立了平等的条约。参见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6、82、309页。
〔13〕该条约由美国、英国、丹麦、法国、意大利、日本、挪威、荷兰、瑞典在1920年于巴黎签订,之后又有数国加入,其规定挪威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连同熊岛等“具有充分和完全的主权”,但各缔约国的公民可以自由进入,在遵守挪威法律的范围内从事正当的生产和商业以及科学考察等活动。
〔14〕比如,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同年5月,袁世凯政府在与日本政府讨价还价后,在北京签署《中日民四条约》,并于同年6月在东京换文。又如,1915年6月,北洋政府与沙俄政府签订《中俄蒙协约》,导致中国丧失对外蒙古的实际统治权;但在1919年11月北洋政府趁苏俄政权立足未稳之际收回了外蒙古主权,并将《中俄蒙协约》废止。
〔15〕仅北洋军阀内部就有皖系、直系、奉系等派,并两次爆发“府院之争”。
〔16〕孙中山在1921年发表《呼吁列强承认南方政府的对外宣言》,提出“1913年,国会组织之民国政府,曾经友邦之承认;本政府亦为此国会所组织者,应请各友邦政府援此先例,承认为中华民国唯一之政府”。参见程道德等:《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73页。
〔17〕英国先后制造关余问题、白鹅潭事件及商团叛乱事件,欲推翻广州政府;五卅运动期间,英国对广州政府的废约等要求置之不理,北京公使团以未承认广州政府为由,拒绝答复广州政府的抗议照会而只与北京政府交涉。参见李斌:《关于国民政府“国际承认”问题的探讨》,《求索》2009年第9期。
〔18〕这是由于“中华民国”实际上是由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在达成相互妥协的情况下共同缔造的,其与两派政治势力均有历史渊源和客观联系,故而成为了两派政治势力都接受、维护和争夺的政权名称。
〔19〕比如南京政府与比利时、德国签订的新约,都因出于政治需要而未对其内容认真推敲,较之此前北京政府与两国签订的旧约,中方所作的妥协更大、承担的义务更多。参见曾友豪:《从国际法学的观点批评中外新约》,载《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十四号,北京: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4-23页。
〔20〕〔28〕李育民:《中国废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46-650、915页。
〔21〕〔27〕程道德等:《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88、440页。
〔22〕史全生等:《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0页;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24页。
〔23〕李斌:《关于国民政府“国际承认”问题的探讨》,《求索》2009年第9期。
〔24〕王芸生:《中国国民党外交之回顾》,《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一期,1932年。
〔25〕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48-450页。
〔26〕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进入南京之时,南京城内在外国驻宁领馆、洋行和外人住宅曾有劫案与毙伤外领、外侨之事发生,美、英停泊下关江面的军舰以此为由,借保护侨民之名,向下关及南京城内发炮,毙伤中国军民多人,损毁公私房屋、各种设施、家什、器具等无算,此一事件,史称“南京事件”或“宁案”。参见孔庆泰:《1927年宁案与宁案处理始末》,《历史档案》1987年第2期。
〔29〕罗国强:《政府承认的性质及其所适用的原则》,《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30〕包括日本建立和扶持的伪满洲国、泰国伪政权、“自由印度”政府、缅甸巴莫政权、菲律宾劳雷尔政权,以及德国的若干仆从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等。
〔31〕在李济深宣告脱党之前,已被蒋介石第二次开除党籍;1937年起,李济深再次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直至1947年被蒋介石第三次开除党籍。
〔32〕包括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琼崖革命根据地等。
〔33〕余伯流:《共产国际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关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34〕杨木生:《中央苏区法制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七十周年》,《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12期。
〔35〕理论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应集中统一领导所有苏区,但由于根据地之间交通不便、联系不畅,各地情况又异常变化复杂,故而临时中央政府对各地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临时中央政府实际只能直接领导中央苏区,对其他苏区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大。参见何善川、王庆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刍议》,《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但笔者认为从交战团体承认的要件上讲,只要各根据地自身实现了较为稳固的统治并至少在理论上服从中央的领导,临时中央政府是否直接领导并不妨碍这一要素的认定。
〔36〕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提供了军事援助。西欧各国共产党发出告工人劳动群众书,号召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及被压迫群众用全副力量来打破国际反革命的凶恶计划,保护中国苏维埃及苏联;要求码头工人、海员、兵工厂工人及一切化学工人阻止及反对资本主义国家运输军火及军队去中国战场。美国和日本共产党也发表社论和宣言,支持中共的主张。参见万建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述略》,《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37〕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Victor Gollancz Ltd London,1937。此书一问世便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10万册以上。以后此书多次再版,并以近二十种文字翻译出版,几十年间几乎传遍了世界,成了著名的畅销书,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和共产党人的主要来源之一。
〔38〕〔40〕赵佳楹编著:《中国现代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710-712,829、921页。
〔39〕〔美〕伊利·雅克·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徐隋林、刘润生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年,第148页。
〔41〕苏联承诺给予国民政府援助、尊重中国东三省主权、不干涉中国内政,但实际上迫使中国同意外蒙古分离,并承继了帝俄时代的条约特权。参见李育民:《中国废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51-953页。
〔42〕王志刚:《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的研究进展及评估》,《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0期。
〔43〕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44〕中共政权在短期内迅速以少胜多奠定胜局的原因可谓纷繁复杂,但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无疑在于国家内部——蒋介石政府统治中国期间,其内政外交虽然不能说没有政绩和值得称道之处,但在最为关键的国计民生事务上中国都深陷泥潭(长期遭受日本侵略致大半国土沦陷、通货膨胀、经济崩溃、治安混乱),人民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水深火热,从而导致民心尽失,人民出于对该政权的失望,本能地期望有一个新政权来取而代之,给国家一个新的选择、新的希望。正是在这种普遍社会心态之下,解放战争一爆发就呈现出“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城市市民抗议游行示威蒋当局、农村农民支持土改参加和援助解放军、国民党内斗激烈、各派与蒋当局貌合神离、大批国民党军队投诚起义或放弃抵抗、蒋当局内部大量情报尤其是军事机密外泄……),从而使得苦心经营多年、积累了强大面上实力的蒋介石政权及其军队不堪一击。
〔45〕Francis C,Prescott,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The Far East:China,Volume IX,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4,p.13.
〔46〕法国、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比利时、印度等国也都对美国的政策提出了异议。参见赵佳楹编著:《中国现代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1321-1323页。
〔47〕魏敬民:《建国初期的中英外交关系》,《党史天地》2002年第6期。
〔48〕这些国家包括: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英国、挪威、丹麦、以色列、印尼、阿富汗、芬兰、瑞典、瑞士。
〔49〕吴白乙:《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政治关系的再思考》,《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第4期。
〔50〕《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2193_674977/。
〔51〕包括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伯利兹、海地、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巴拉圭、帕劳、马绍尔群岛、瑙鲁、图瓦卢、斯威士兰、梵蒂冈。
〔52〕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出现的原因在于实现一般政府承认与继承所需要的有效统治未能百分之百地得到实现。交战团体或叛乱团体的存在是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产生的直接原因。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具有跟一般政府承认与继承相同的共性,同时具有后者所没有的特性。参见罗国强:《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的性质分析》,《政法论丛》2018年第1期。
〔53〕相关例证可参见罗国强:《论〈台湾旅行法〉对国际法的违反》,《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