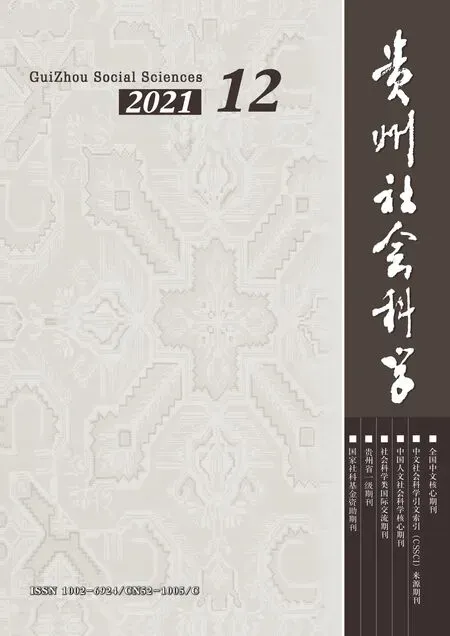西方中世纪学的嬗演路径
——基于《剑桥中世纪学指南》的述析
2021-04-15王云龙
王云龙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024)
在西方,中世纪早已不是历史学的“禁脔”。大学等学术机构中世纪史研究日渐式微,与此同时,大众文化的中世纪叙事方兴未艾。[1]中世纪学标举革故鼎新,呈方兴未艾之势。剑桥学科指南系列丛书是西方学术研究的风向标,也是某一学科或跨学科论域学术成熟的刻度尺。“一个领域的学术研究达到值得拥有剑桥指南的程度,是多么令人激动。(剑桥指南)是一个研究领域拥有足够多的标志性成果和高度成熟,表现在学术进展、研究主题集成、发展路径和批判性方法。中世纪学研究就是这样的典型,在后中世纪文化语境中研究欧洲中世纪的认知、阐释与再创造。”[2]12016年出版的《剑桥中世纪学指南》(TheCambridgeCompaniontoMediev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既是《剑桥文化研究指南》丛书之一,亦是中世纪学成为西方学术界“显学”的标志。《剑桥中世纪学指南》由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Australia)英语文献学教授阿森斯主编,全书由主编撰写的导论和各领域权威学者撰写的14章专题论文构成。专题论文标举了当代西方中世纪学的不同论域:英国诗歌中的中世纪学、中世纪学与建筑、中世纪学与电影、音乐中世纪学与和弦、参与式中世纪学:角色扮演和电子游戏、现代早期中世纪学、浪漫主义中世纪学、中世纪学与民族主义、中世纪学与战争意识形态、西属美洲独立后的中世纪学、新中世纪主义与国际关系、世界中世纪学与翻译、中世纪学与时间理论、酷儿中世纪学:蒙提·派森与圣杯。阿森斯教授在导论中说,《剑桥中世纪学指南》“聚焦热门议题,不仅揭示那些学科过去与现在的态势,而且预测未来可能产生更大成果的学科发展方向”。[2]11中世纪学学术辐射性是跨学科、多论域的,具有学理穿透性,“中世纪学研究对人文学科最具影响的贡献是为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的关键对话提供差异化安排。本书(《剑桥中世纪学指南》)一些内容包括重要的元分析,揭示了鲜为人知的中世纪学理念对于先锋艺术、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的重要启示作用。(本书未收录的)中世纪学家设置了广泛的议题,从历史辐射到性学、时间知识学、认知与情感史学、后人文主义、生态批评、动物学、客观性理论。确保中世纪学研究发展的关键机制之一,是不断补充进新的、善于运用主流理论方法和复杂概念化术语体系研讨中世纪学的研究人员”。[2]11
一、跨域性(Interdisciplinary):中世纪何以成学
在西方学术界,中世纪学(medievalism)被界定为在中世纪之后的文化中对欧洲中世纪的接受、阐释与再创造的研究。[3]1979年,莱斯利·沃克曼创办《中世纪学研究》(MedievalismStudies)杂志。西方学术界公认,中世纪学研究的大行其道应归功于莱斯利·沃克曼和凯思琳·薇都茵伉俪。1981年起,莱斯利·沃克曼与时任密执安希望学院文学教授的妻子凯思琳·薇都茵共同编辑《中世纪学研究》。1986年起,莱斯利·沃克曼和凯思琳·薇都茵组织中世纪学系列国际研讨会,出版《中世纪学年鉴》(TheYear`sWorkinMedievalism)。在西方学术界,以《中世纪学研究》、《中世纪学年鉴》和中世纪学国际学术会议为平台,论文与专著层出不穷,中世纪学终成20世纪显学(the venerable twentieth-century discipline of “Medievalism Studies”)。[4]在西方学术语境中,中世纪学(medievalism)与中世纪研究(medieval studies)异名同旨,相映成趣;与中世纪史(medieval historiography)形似神殊,大异其趣。在汉语学术语境中,中世纪学名号冷僻,且被中世纪史遮蔽,不见经传。
西方中世纪学肇端于早期现代性阶段的浪漫主义运动时期,传统的中世纪学是浪漫主义反对理性主义的学术结晶。启蒙思想家为了给新时代开辟新的道路,以理性取代神性,以科学破除迷信,以线性取代轮回,以进步破除天定。启蒙思想家秉持理性的绝对律令,运用科学的绝对思维,构造线性的绝对路径,笃行进步的绝对理念,中世纪就成为了启蒙思想合法性言说的绝对否定的对立面。由于启蒙运动,“千年黑暗”的中世纪就成为了常识性话语。在启蒙运动的话语霸权主导下,中世纪也就成为了线性进步、科学理性的对立面。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中世纪自然地等同于蒙昧无知、落后腐朽。即使在启蒙运动风起云涌的18世纪,理性主义就已遭遇到浪漫主义的挑战。浪漫主义进攻理性主义的主战场,就是应用人文学(humanities)的学理体系,构造反理性至上的中世纪学。[5]3-4
德意志浪漫主义思想大师、文化民族主义与传统中世纪学的创立者之一赫尔德指出,传统中世纪学侧重“再现”,重在构造与理性主义双峰对峙的浪漫主义的中世纪意象,他尤其反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思想家关于中世纪“千年黑暗”的论断。赫尔德认为,中世纪与其说是历史的实在,不如说是历史的传奇。他从浪漫主义语境出发,把中世纪看作浪漫主义意象的源泉,中世纪是以“北欧骑士”为独特审美符号的历史时段。他指出:“人们经常把‘北欧骑士’精神与古希腊英雄时代相比较,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不具有可比性,是唯一的。中世纪是历史的独特形态,它的优长与缺欠之处,既不可与其前的时代相比较,又在其后的时代被无休止地改头换面,因而,中世纪是唯一的。我们阅读关于这一时期的著作,都集中于揭示它的黑暗面。每一位在我们这个世纪主导地位的经典作家,都把整个中世纪看作野蛮、蒙昧、迷信、宗教狂热与极度匮乏充斥的时段。……欧洲被构造完成了……我只想指出中世纪是其后时代精神和人类行为方式的源泉。”[5]4
中世纪学(mediaevalismmedievalism)英文名词始现于1853年,中世纪学(medievalism)指涉时段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世纪末,意蕴中世纪信仰与实践的特质,涉及中世纪思想、宗教、艺术等领域,推崇中世纪理念与话语。[6]中世纪学是跨学科研究中世纪西欧历史的论域,但不囿于中世纪历史学(beyond the medieval historiography)。因而,“试图总结中世纪学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任务。首先,中世纪学涵盖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时段、地理与文化的广博范畴的文化实践、话语和器物”。[2]2当代英语学术语境的中世纪学,肇兴于中世纪研究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展现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19世纪中世纪学研究精品力作开始面世”。[2]119世纪中期,随着英国工业革命深入发展,阶级分化与阶层固化日益明显,部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转化为“有闲阶级”(The Leisure Class)。中世纪学契合了“有闲阶级”慕古之幽思,应运而生。最早的中世纪学家(medievalists)大多出身于“有闲阶级”,这使得中世纪学家超越中世纪史家(medieval historiographers)学术视域,不囿于史料(historical resources),不眈于兰克历史学的方法论(methodology of historiography),而是把中世纪作为历史语料(medieval corpus),基于历史语文学(philology),构建中世纪学。或曰,在19世纪学术语境中,中世纪学家等同于中世纪历史语文学家(medieval philologists)。“这影响到盛行或引人注目的人性的保守取向,(1)通过阶级传承和有闲阶级与其他阶级血统融合,(2)通过保存和保护古代制度,使得古代遗存能够在有闲阶级血统融合之外更广泛地存续。”[7]在“有闲阶级”引领下,维多利亚时代追慕中世纪,蔚为“高风所泊,薄俗以敦”。[8]
启蒙运动以降,中世纪不可避免地落入后塑性历史书写的辉格窠臼,“遍及欧洲的中世纪史料文献的编辑、出版,奥援民族优越论。中世纪学是罗曼语、特别是欧洲那些具有漫长中世纪的民族历史书写最具持续性的特质之一”。[9]“中世纪学被视为奠基伟大的大学和支撑学术、艺术和文学的(中世纪)宗教奉献范式和道德献身精神的研究领域。”[10]
与此同时,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区位与独特的文化地理区间,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古典文明核心地域——亚平宁半岛,“法国大革命及其在意大利的影响对于‘历史世纪’的意大利历史学家至关重要。大众登上政治舞台,引发了基于中世纪的大量阶级斗争研究。因为阶级源于中世纪的社会阶层”。[11]227“因而,历史探究与分析的焦点聚焦于中世纪论域。”[11]228其中,希蒙德·德·西斯蒙第的著述堪称“越世高谈,自开户牖”。[12]
希蒙德·德·西斯蒙第是出生于瑞士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当过银行职员,经营过农场,是有闲阶级一员,还是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13]655在政治经济学颇有建树,得到马克思的肯定。马克思指出:“西斯蒙第比较理解资本的特殊的局限性。……不但强调生产会遇到限制,而且强调这个限制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于是资本陷入矛盾之中,他由此预言,这些矛盾必然导致资本的毁灭。”[13]91-92“希蒙德·德·西斯蒙第是意大利中世纪学的核心人物。他的《中世纪意大利共和国历史》(Histoiredesrépuliquesitaliennesdumoyenge),1807—1818年间陆续出版。期后多次再版,并出版两卷本简编版。……德西斯蒙第的研究是新教式的,揭露天主教在意大利历史上的消极作用,特别是阻碍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这一著作读者众多,讨论持续很长时间,盛誉有加,特别是中世纪意大利自由黄金时代的叙事,当时诸微型共和国守护自由和高度的文明,击败了巴巴罗萨皇帝。”[11]228-229由于《中世纪意大利共和国历史》把中世纪意大利看作现代欧洲的起源,襄赞意大利统一,与其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定位相反,西方学术界将希蒙德·德西斯蒙第的意大利历史著作归入非浪漫主义的中世纪学(Medievalism without Romanticism)。[11]228
1870年,萨伏伊王室(House of Savoy)统一亚平宁半岛,现代意义民族国家——意大利王国应时而生。意大利历史研究取向由地方实体转向民族国家,这也辐射到中世纪领域,“19世纪末,中世纪学不再把意大利公社作为现代自由的摇篮来研究,同时历史语文学方法也式微了。(意大利)知识和精神氛围发生变化,服膺桑巴特(Sombart)的理念,把中世纪意大利城镇视为现代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源头”。[11]235相对于悠长的中世纪学术研究,意大利大学里相关教席则先发而后至,“尽管对于中世纪有着长久的兴趣,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大学才设置第一批中世纪史教席”。[11]234意大利中世纪史学术建制化,晚于中世纪学很长时间,展示了从跨域性中世纪学向专业性中世纪史缮演的学理进路。
二、互文性:中世纪学何以可能
中世纪学学理设定与中世纪历史实然形成了阐释性张力,即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中世纪学的学理设定是中世纪历史实然符号化学理再生产机制,以解构—重构的阐释性为圭臬,“这就是中世纪学的学术本质。学者们用自己的方式揭示他者的中世纪学。……中世纪人们不会像我们那样去思考与享乐的理念被学术界与其他群体,以不计其数的方式迂回传播着”。[14]“直到20世纪中叶,中世纪被视为民族与宗教的神话般源头,是持续到当下的牢不可破的共同体意识形态的基因。呈现为日常习俗与习惯的中世纪之源,从节日、民间服饰到民族国家,事实上是19世纪的发明。历史学家没有低估这些大众趣味的中世纪学,相反认为这有助于中世纪历史的趣味化与普及化。”[15]例如,中世纪学视域的中世纪战争叙事,充分展现了学理应然与历史实然的张力,“几百年来,中世纪战争传统自我滋生,蕴育出主题丛——大众文化主角;重铸宝剑——开发出特殊的武士品牌——十字军、撒克逊人、维京人,重新形塑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亚瑟王、熙德、萨拉丁、华莱士。这些演进过程把中世纪浓缩和化约为并非实然的战争状态”。[16]但是,无论如何变化,(实然)中世纪都提供了权威性与真实性,以满足新的语境和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需求。[17]
中世纪学研究突破了中世纪史学科边界,深入到中世纪史不可能覆盖的领域。通过完美的画面和复杂的互动呈现故事情节,作为中世纪学时髦的形态——电子游戏成熟到了新的境界。中世纪角色扮演游戏和“参与式中世纪学”并非试图回到“真实的”中世纪,流量通过另外的方式,在角色扮演上和游戏范围内,创造一个从未存在的中世纪,名曰:“新中世纪”(the neomedieval)。[18]76新中世纪魔幻世界的诉求和角色扮演的画面,把在当代文化中差异如此之大的不同人群聚合起来:富人与穷人、青年人与老年人、异性恋与同性恋、土著与移民、男人和女人、运动员和极客、身姿婀娜者和矮粗胖者,他们都在参与式中世纪学的角色扮演世界里有一席之地。魔幻的中世纪世界可能是社会化的新形式,把拒绝其他社会化途径的人们组织起来,只关注游戏的趣味性,无视历史的准确性。海量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实体标志、转喻、仿造的前现代腔调,制造了历史的大杂烩、中世纪能指的共时性特写。[18]8020世纪70年代以来,“再现历史”团体如雨后春笋出现在欧美各国,其中“再造历史协会”(the Society for Creative Anachronism, SCA)最为名声显赫。“再造历史协会”“致力于研究与再造17世纪之前的欧洲艺术与技艺,是从未存在的浪漫中世纪的维多利亚意象好莱坞版本的后现代建构”。[19]在角色扮演的电子游戏世界,中世纪实然变成天马行空意象构建的虚拟世界应然。“再造历史协会”通过仪式重演、个人角色扮演和物质文明造物,模仿前现代欧洲的骑士精神的英雄气概,再现中世纪社会结构。“再造历史协会”一方面反主流文化,联袂激进主义政治议程和罗斯金式(Ruskinesque)工业社会批判;另一方面采纳通常的性别角色和传统的等级制度,又凸显出保守性。“再造历史协会”的中世纪世界分为19个王国,全球3万多注册会员。每个王国由国王和王后统治,王国实行半封建制:大公和女大公统治公国,伯爵和女伯爵统治伯爵领地,地方分别由郡守、县令、区丞、学长、要塞长、市政官统领,注册会员有资格充任上述官位并领有装备。除了忠诚,各级官爵均由电子游戏竞赛获胜者担任。“再造历史协会”在模拟中世纪行政系统中,总管是行政长官,纹章院主管统领军事(the earl marshal who oversees all martial activities),艺术与科学大臣负责前现代艺术与技术研究,财政大臣执掌国库,太史令掌管出版事宜(the chronicler who oversees publications),外科医生负责紧急救援(chirurgeon who administers first aid)。角色扮演超越了个体再现的范畴,融入了中世纪以后的社会与政治等级。尽管如此,“再造历史协会”模拟的中世纪,眈于乡愁,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拥抱前工业社会,无视现代社会急剧变迁。[18]81-82
玩以致学,手工再现中世纪。参与式中世纪游戏,把中世纪由皓首穷经的象牙塔扁平化为共享性游戏世界。相对于其他中世纪参与式游戏,“再造历史协会”相关游戏的参与者更加广泛。“再造历史协会”游戏参与者兴致盎然地研究自己扮演的角色在中世纪的历史、考古和物质环境。例如,为了缝制自己角色的服装,潜心研究中世纪真确的裁剪方法,使用中世纪工具制造自己的装备、家什和用于交换的产品。在王国纹章院主管监管下,“再造历史协会”游戏竞技严格遵循规则定制。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东王国与中王国间的年度潘希科战争(the annual Pennsic War),剑由藤条缠制而成,盔甲有皮革的,有链锁的,还有全身铠胄的,尽最大可能重现特定历史时段的真切场景,参与者按照规则激战。在碎片化的当代文化,寻觅共同体,“再造历史协会”是一个跨历史的异托邦(a transhistorical heterotopia),聚合各种各样的前现代文化碎片,依照中世纪先人的意象,凝练为一个整体。[18]81-82参与到这些新中世纪虚拟场景,中世纪角色扮演展示了当下与中世纪的跨时间亲和力,共时性地融合了当下报刊关于过去的转喻与面向即将到来的未来。[18]87虚拟中世纪与文本中世纪之间的学理张力(academical tension),形成了突破历史学(historiography)刚性边界的互文性。这种学理张力导致中世纪学既基于互文性,又丰富了互文性。“莎士比亚名剧《伯里克利》中的合唱队表现的不仅是中世纪生活的连续性,而且是中世纪学(对中世纪生活)创造。(根据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改编的)莎剧《两贵亲·序幕》是现代早期中世纪学缩影的完美意象。”[20]“来自学术界与学术性小说的互文世界的长辈冥思,能够娱乐和肤浅地启发大众。”[21]
如果参与式角色扮演是虚拟化共时性中世纪文本语境的载体,那么,经籍重勘则是中世纪文本语境阐释化历时性的进路。中世纪经籍,既含蓄史籍(historical resources),又含蕴文籍(literary books)。
三、后塑性:中世纪学何以如此
作者运用史料语料化编撰范式,从事当下取向的历史叙事话语建构,语境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22]是为后塑性(post-figurative)。“解散修道院运动”(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作为重大事件的国教化改革,开启了英语范式的后塑性中世纪学建构。“解散修道院运动”压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修道院,并将其财富转到王权名下,以增加王室财力。1536—1540年,由托马斯·克伦威尔组织实施。1535—1536年,巡视所有的修道院,发现其失当行为,为“解散修道院”政策提供道义依据,大约800座修道院受到波及。9000名修道士的申诉通过“求恩巡礼”(the Pilgrimage of Grace)得到赔偿。亨利八世的“解散修道院”政策,额外带来9万多磅的岁入。大部分修道院财富通过增收法庭(the Court of Augmentation)转售给英格兰贵族。[23]在文籍与史籍解构—重构的语境化运作过程中,包括“解散修道院运动”在内的国教化改革作为中世纪学构建的后塑性母题,后塑性阐释的多向度叙事特质得以凸显。
“解散修道院运动”是英格兰教会国教化改革(Reformation)的重要一环,“国教化改革通常被视为长时段西方拉丁基督教传统与互为独立且用民族语言礼拜并时常处于交战状态的现代民族国家教会的宗教文化的分水岭”。[24]89而且,现代早期的中世纪学是国教化改革的学术产物。[24]901549年,英格兰教会《公祷书》(TheBookofCommonPrayer)首版印行,发出了国教化改革的呐喊:“千百年来,古代教父圣洁如上帝般的传统被扭曲、遮蔽和漠视”。[25]英格兰宗教改革家、《圣经》(钦定《圣经》詹姆斯国王版TheHolyBibleKingJamesVersion的母本)英译本译者威廉·廷德尔,抨击罗马天主教罔顾教父传统的圣誉。他指出,几百年来,罗马教会体系通过诡辩和晦涩的迷局,把教父传统湮灭在“无底深渊的迷雾中”,教士们用《圣经》蒙蔽、欺骗、恫吓信众,将信众引进黑暗。[26]从宗教改革谱系出发,在英格兰的历史语境中,廷德尔较早地把罗马教庭执掌西欧教会的长时段界定为“黑暗”(darken)。廷德尔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宗教改革,为国教化改革提供了合法性资源,而且预兆了其后的启蒙(enlightened),为启蒙运动恶谥中世纪为“千年黑暗”提供了原话语(meta-discourse)。廷德尔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蔑视中世纪精神文化,有的蔑视中世纪拉丁范式,有的蔑视托马斯经院哲学,或两者都蔑视。吊诡的是,国教化改革集成的反中世纪话语,一方面推动了“解散修道院运动”,另一方面促发了第一波后中世纪的中世纪学。英格兰国教化改革肇兴了欣赏中世纪历史的汲古风尚(antiquarianism),这种汲古风尚致力于再现中世纪,但也模糊了发现、发明、附会的界限。都铎王朝早期和中期,民族历史与宗教历史的认同断裂,繁盛了汲古风尚。[24]92-93英格兰第一波中世纪学充分体现了后塑性,即以应然话语建构遮蔽了中世纪实然历史。中世纪历史实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整个历史进程——指重大事件——到现在为止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7]
16世纪前期,在中世纪文化、特别是古英语文献整理领域,呈现出针锋相对的中世纪学取向。由于古腾堡印刷术传遍西欧,古英语版本典籍第一次大量印行,1571年古英语版《福音书》印行,1574年威尔士教士阿塞尔的《阿尔弗烈德大王传》(LifeofAlfred)出版。坎特伯雷大主教马修·帕克是英格兰国教化改革的旗手,“运用盎格鲁—撒克逊的学术资源巩固安立甘教会的教理与机构的合法性。(通过印行乔叟和朗格兰的作品)申明国教化改革关切合法性的根源”。[28]国教化改革者将改革的合法性诉诸于英格兰古籍,天主教虔信者亦将反国教化改革的合法性诉诸于英格兰古籍。1565年,流亡在低地国家的英格兰天主教徒托马斯·特普尔顿的《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HistoryoftheEnglishPeople)的英译本印行。在该书的献辞中,托马斯·特普尔顿批驳国教化改革,劝谏秉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从这部《历史》中可以看出,您的尊贵的国王是在哪一种信仰里施洗的,它持续了几千年,使天主荣耀,君王光彩,国泰民安。在这部《历史》中,陛下您会看到,在多少重大问题上,虚伪的教会改革派(国教化改革派)已经背离了那由我们的使徒——神圣的奥古斯丁和他品德高尚的同伴首先在英吉利人中传播的正确的普世信仰。本书的作者——可敬的比德真实而诚挚地描述了这种信仰,他以其非凡的德行和罕见的博识被整个基督教界称为‘可敬的比德’”。可是,伊丽莎白所乘的“可恶的分裂主义轻舟”(国教化改革)却背离了“坚固的诺亚方舟”(罗马天主教),越驶越远。[29]《英吉利教会史》被托马斯·特普尔顿后塑化为秉持罗马天主教,反对国教化改革的历史合法性文本,进而为反国教化改革的汲古风尚的中世纪学文本。
与《英吉利教会史》托马斯·特普尔顿英译本针锋相对的,是襄赞国教化改革的历史叙事文本——《殉教者英名录》(ActesandMounments)或名曰《殉教者书》(BookofMartyrs)。《殉教者英名录》“是整个现代早期中世纪学最具影响力的文本之一”,[24]95标识着“这样形态的中世纪学兴起——寻觅诉诸祖先、长辈和真实性的意识形态偏好”。[24]95《殉教者英名录》的作者约翰·福克斯是国教化改革活动家。约翰·福克斯毕业于牛津大学,1539年就职于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Magdalin College),后因秉持宗教改革信念被迫辞职。1547年,约翰·福克斯任迁居伦敦,担任圣公会助祭(a deacon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1553年,宗奉天主教的玛丽一世女王即位,大肆迫害国教化改革人士,约翰·福克斯被迫流亡西欧。1554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约翰·福克斯发表《殉教者英名录》拉丁文版部分内容。流亡期间,约翰·福克斯著文呼吁英格兰贵族奋起反抗玛丽一世迫害国教化改革派,同时,完成《殉教者英名录》,借古喻今。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后,约翰·福克斯返回英格兰,1560年担任牧师。1563年,《殉教者英名录》英文首版印行,并题献给伊丽莎白一世。《殉教者英名录》强调,英格兰是神选之国,无须借助罗马教廷。“这部鸿篇巨制是早期国教化改革最重要的文献,是这一时段公认的中世纪学著作,对从民谣歌集到莎士比亚戏剧的现代早期文学影响巨大。融汇中世纪学、学术与意识形态冲突是这部著作鲜明特色。福克斯致力于论证为了国教化改革而改造中世纪历史。”[24]95-96在《殉教者英名录》中,约翰·福克斯把罗拉德派(Lollardy)及其首领约翰·奥尔德卡斯特爵士后塑为16世纪50年代殉教者的“完美的中世纪先驱”。[24]961414年,约翰·奥尔德卡斯特爵士发动罗拉德派暴动。史料表明,这次暴动与异端的煽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1563年版《殉教者英名录》中,约翰·福克斯回避奥尔德卡斯特爵士发动罗拉德派暴动的史实,写道:“有人向国王控告奥尔德卡斯特及其党羽,在伦敦召开大会,谋划摧毁王国,颠覆公序良俗。国王亨利五世到达集会地点,并未发现这样的集会”。[24]96
无论约翰·福克斯的《殉教者英名录》还是托马斯·特普尔顿的《英吉利教会史》英译本,国教化改革生发的后塑性历史言说,深深地嵌入了中世纪历史叙事话语构建。“十分明显,16世纪出现的原始中世纪学形态(the first forms of medievalism),基础是矛盾与不稳固的,是政治—宗教力量强力形塑的,是极易受到攻击与反诘的新的民族—宗教认同的形成中的状态。”[24]96
以中世纪史料语料化学理立基的跨域性,以学理应然与历史实然张力构建的互文性,以当下取向与历史叙事话语建构的后塑性,西方中世纪学创造性阐释与再创造欧洲中世纪时段,已经是当代西方文化记忆的主要形态,并且日益成为全球现象。西方中世纪学将西欧中世纪的特质性(Medieval Characters)形塑为现代性的母体(Matrix of Modernity),其学理体系与话语的价值取向不可不察。当然,这超出了本文的范畴,是一个更加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