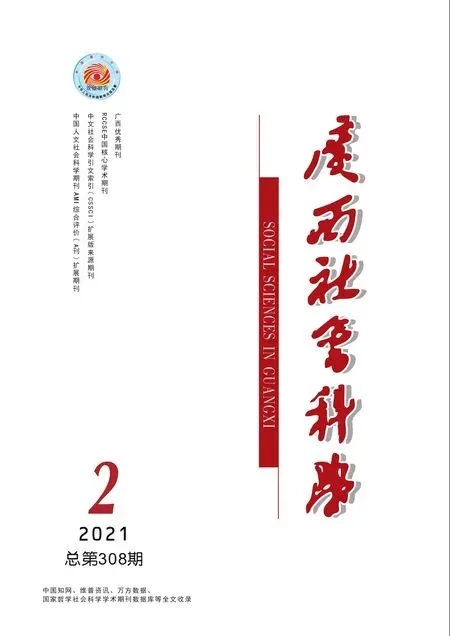《民法典》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法理基础
——兼论近亲属权益保护说的理论困境及其解释论分析
2021-04-15
(浙江大学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浙江 杭州 310000)
一、导言:背景与问题
人格权是一项古老且重要的权利①公元前20世纪的《苏美尔法典》、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中就有使用损害赔偿的方式来保护生命、健康等人格权的例子。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对死者人格的保护在我国经历了从判例到司法解释再到制定法的漫长过程,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人格权编”的重要内容。1987年的“荷花女案”可以说是法院保护死者名誉的首个案件,它体现了社会实践对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要求,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填补了此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的立法空白①分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亡人的名誉权应依法保护的复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范应莲诉敬永祥等侵害海灯法师名誉权一案有关诉讼程序问题的复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范应莲诉敬永祥侵害海灯名誉一案如何处理的复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近年来随着《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五条“英烈条款”的规定又重新激发人们的讨论,立法者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和学理讨论的基础上,在《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四条中正式规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但是保护死者在理论上存在的争议并没有随着《民法典》的制定而消失。一来是由于《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四条并没有新增有关一般性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内容,例如《民法典》在“人格权编”第六章新规定了自然人的隐私权与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但是涉及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则基本上沿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和第七条的内容,并没有实现新的突破。二来是由于近亲属权益保护说一直占据解释论的核心,但实际上近亲属权益保护说自身存在诸多问题。有学者在研究英烈问题时认为,英烈条款的核心就在于确定它与一般死者人格利益条款之间的关系[1]。因此,研究一般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规则对于英烈条款的解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民法典》如何协调好对自然人和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也具有重要意义。
而研究对死者人格的保护涉及如下一般性问题:死者是否有人格权?死者近亲属在保护死者的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自然人死后,其人格权或人格利益是否仍然存续?死者人格利益可以被损害吗?还是说损害的是其近亲属的利益?近亲属对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提起诉讼的权利基础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通行教义学解释以近亲属权益保护说为主(即通说观点)。在近亲属权益保护说看来,保护死者实质上是为了保护死者仍然活着的近亲属,因为一个人死后无法被伤害并且也不能作为权利主体来提起诉讼。近亲属权益保护说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如下难题:一方面,民法所应负担某种保护死者的道德要求与社会政策需求;另一方面,保护死者可能与民法中现行权利能力制度相冲突。为论述的方便,本文试将人的生前与死后的时间节点分为t1(出生时刻点)、t2(死亡时刻点)、t3②本文仅仅讨论死后是否存在人格利益的问题,而不涉及人格利益在实定法内保护期限多长的问题,所以t3的具体期限范围在本文不作讨论。(死后的任一时刻点),重点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论证近亲属权益保护说不能作为《民法典》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理论基础。首先揭示了摆在民法学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如何弥补因保护死者与维系民法体系的完整而产生的裂缝。通说通过语义扩张的方式对该裂缝予以解释,即把“保护死者人格”理解为“保护死者近亲属人格”,但实际上裂缝的产生可能与对权利概念的混淆相关。二是论证近亲属权益保护说成立的两大基石“利益幸存问题”与“主体问题”并不可靠。通过合理解释“死者”概念同时区分“利益幸存于t3”与“在t3拥有利益”可以回应这一问题。三是论证近亲属权益保护说为什么是失败的。实际上它存在如下一系列问题:预设错误前提、背离对死者的保护、难以融贯解释法律与实践,然后对近亲属权益保护说陷入上述理论困境进行解释论上的分析。
二、死者人格权:司法难题与概念澄清
笔者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中检索“死者人格权”“死者权利”“死者名誉权”等关键词,截至2020年10月3日,发现有55份裁判文书中出现“死者人格权”的表述,有34份裁判文书中出现“死者权利”这一表述,有36份裁判文书中出现“死者名誉权”的表述。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第一,死者拥有包括人格权在内的权利;第二,在司法实践中,对死者的权利予以保护。但是,在民法中谈死者的权利乍一看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因为一直以来法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只以活着的自然人为刻画对象——此即民法的“现世性”特征,一个证据就是权利能力制度规定“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新颁布的《民法典》第十三条也规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可见,如何在保护死者与维持民法体系的完整性之间寻求平衡,就成了摆在法律人面前的一道难题。笔者认为,这个难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不同权利概念的混乱导致的,在法理上分析厘定概念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待民法问题中的争论,下面我们作进一步解释。
(一)区分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
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对于解释“权利所有者基于什么拥有权利”这一问题的回答存在分歧。二者对于权利根据的理解是不同的,道德权利主张权利的根据来自道德理由,而法律权利认为权利的根据在于法律权威的规定这一事实(即法律理由)。法律理由是以来源为基础的,当被问及做某事的法律理由时,人们总会说法律是如此规定的,而不会去考虑做此事的道德价值,后者恰恰是道德理由的落脚点①但是有学者认为虽然对法律权利的识别依赖于事实上实在法体系是否有所规定,但实际上对法律权利的证成则依赖于道德主张(如功利主义),因此法律权利是以道德权利为基础的,由于篇幅限制对此不作进一步讨论。对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一般性讨论,参见陈景辉《法律权利的性质:它与道德权利必然相关吗?》,载《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第4-12页。。毫无疑问,法律权利是一种事实权利,对它的识别仅仅依赖于法体系如何规定,而道德权利通常是基于权利主体的道德地位而享有的权利,理论家常常认为未来的人类、高等动物、死者等具有类似的道德地位因此主张动物权利、代际权利、死者权利等新型权利,但是我国现有法体系并没有对这些权利进行规定,所以它们不是法律权利。当我们把一个事物称作某人的权利时,我们似乎都是在主张该权利的所有者对社会具有某种有效请求,以保护他所拥有的选择或利益。但是对法律权利与道德权利的保护方式是不同的:在法律体系内部,对权利的保护是以权利所有者提起诉讼等公力救济的方式进行的,民法上的实体请求权通常对应程序法上的诉权,此之谓“有权利必有救济”,但是道德权利至少不能以这种方式获得保护。
在区分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之后,我们发现如果想要融贯地解释对死者人格的保护以及现行民法中的权利能力制度,那么死者人格权就应该被理解为一种道德权利而非法律权利。因此,在与死者人格权相关的讨论中,判决书里的“死者权利”与民法中权利能力的“权利”不是同一个概念,前者实际上是指道德权利,而后者是法律权利,在讨论死者人格权时应该警惕混淆二者。
(二)法律对死者人格的保护
如果死者权利是一种道德权利,并且基于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在保护方式上的差异,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法律保护死者人格,仅仅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如果存在)而非其人格权利。此外,如何理解死者存在人格利益呢?一般认为自然人死后,其生前的某些人格利益会继续存在于他死后的世界,这些人格利益可以包括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数据信息等具体人格利益,也包括死后尊严等一般性人格利益,它主要涉及对死者遗体的妥当处置。但是这种观点遭到通说的反对,对此笔者将在下一部分回应通说的理论挑战时进行具体论证。
而死者受保护的人格利益通常可以分为财产利益与精神利益,对于死者财产利益的保护是通过保护死者的继承人来实现的②对保护死者财产利益的讨论,可参见张红《死者生前人格上财产利益之保护》,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100-112页。,但是由于人格的精神利益具有专属性,所以对它的保护在理论上产生诸多争议。自1949年以来,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对死者的著作人格权有作出规定外,包括《民法通则》在内的民事法律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此后是在对一系列案件所作出的司法解释中逐步确立的(即法官的造法活动),然后通过立法的形式在《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四条予以再次确认。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死者精神利益的保护主要以保护死者名誉为契机。但是从2001年的司法解释起,死者人格利益的范围从名誉扩展到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遗骨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我国现行法律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并且法律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不再限于名誉方面。
(三)司法实践中混淆权利概念的原因和危害
笔者认为对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混淆与权利泛化现象有关。所谓的“权利泛化”,就是指在法治实践中,“泛化者将一些法定权利以外的得受法律保护的正当利益,未经法定程序,扩大、推广到法定权利形态,以法定权利的救济方式来寻求救济的现象”[2]。那么实践中是如何将利益升格为权利的呢?这就涉及对权利的性质与功能的不同理解,一种理解认为权利保护的是权利所有者的选择与自由意志,通常把这种观点称之为权利的意志论;另一种理解认为权利保护的是权利所有者的切身利益,通常把它称之为权利的利益论①一般性讨论,see Kramer M H.A debate over rights:philosophical enquirie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95-232,239-302.McBride,M.(Ed.).(2017).New Essays on the Nature of Rights.Bloomsbury Publishing.相比意志论而言,利益理论对权利主体的解释更加宽泛——只要权利主体其福祉或利益具有最终价值即可,这会使得那些因不具有自主能力而被意志论者排除出去的对象(如部分残疾人、婴儿)可以成为权利所有者,而且还能将动物作为权利的所有者,因为高等动物具有体验快乐的能力,而快乐是具有最终价值的利益。。因利益论在解释权利主体问题上的包容性,新型权利通常会与它具有天然亲和力。根据利益论的解释,如果陈某可以从王某对其义务的履行中获益,那么似乎就可以在概念上证成陈某相对于王某拥有某项权利。而一个无法作出意思表示或选择的人或动物也能成为权利主体,因为他/它们能在他人相对义务的履行中享有利益。因此,由于死者可以在他人不侵害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人格利益中获益,他就拥有相对于他人履行其尊重死者义务的权利。可见,权利泛化现象中的新型权利是在对权利性质作利益论理解后,通过升格利益得到的。跟其他新型权利一样,死者人格权也是通过升格利益得到的。
之所以造成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混淆,这是因为:首先,我们会基于某些道德理由通过确立道德权利的方式来保护死者人格,例如我们认为应该尊重死者的道德主体地位或者认为保护一个人的身后名誉在道德上是好的,等等;其次,民法本身应当负担起某种保护死者人格的社会道德要求和社会政策需求,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当死者人格利益受到侵犯时法律通常会予以保护;最后,人们就自然而然地认为法律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就意味着存在死者人格权,但这是错误的。在此要注意的是,虽然法律可以保护道德权利所保护的利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利益能升格成为法律权利。因为法律权利的性质要求: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想要升格为法律权利,必须要法律在事实上作出规定。由于我国现有民法体系规定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如果承认死者具有法律上的人格权,就会与这条一般性的规定相冲突。对权利能力制度进行修改将面临一系列从逻辑到社会效果上的问题,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影响,因此不主张为了保护死者人格权而对现行权利能力制度进行修改[3]。因此,如前所述,原则上法律只对死者人格利益予以保护,而主张法律保护死者权利则是不恰当的,这一点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前后立场的变化是一致的。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1993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范应莲诉敬永祥侵害海灯名誉一案如何处理的复函》中最高人民法院刻意将此前两个司法解释(分别于1989年与1990年实施)中死者“名誉权”的表述删去“权”字改成“死者名誉”[4]。北大法宝中不少判决书将死者与权利联系在一起,是由于混淆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这对概念。
混淆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进而损害司法实践。例如,不少人在实践中将具有重要道德价值的利益升格为权利以后,基于对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混淆试图通过起诉获得某种救济。这点已经为部分学者所揭示:“‘泛化’者往往忽视或不知法定权利与自然权利的区别,同时也忽视或不知法定权利的限定性,而任意逾越法定权利的边界,从而戏剧性地创造出前述‘权利’。普通人可以轻易地制造出权利名目去法院起诉和应诉”[5]。以同性恋婚姻权、亲吻权等新型权利为例,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以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未对它们进行规定而不予以支持,在2016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之一的“孙文麟等同性婚姻登记案”中,一审、二审法院都以孙文麟、胡明亮均为男性,其结婚登记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关于结婚必须是男女双方的规定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②孙文麟等与长沙市芙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行政纠纷案——同性婚姻登记案,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行终452号行政判决书。。而在亲吻权一案中法院甚至明确说:“一切权利必有法律依据,任何一种人格权,不论是一般人格权还是具体人格权,都源于法律的确认,即权利法定。纵观我国现有的法律、行政法规,均无亲吻权之规定,故亲吻权的提出于法无据……原告嘴唇裂伤,亲吻不能或变成一种痛苦的心理体验,属于情感上的利益损失,当属精神性人格利益。但利益不等于权利,利益并非都能得到司法救济。”[6]
由以上可见,司法实践中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概念界定的问题。以司法实践中对死者人格的保护为例,一方面要对死者人格权予以保护,另一方面对死者人格权予以保护将导致与现有权利能力制度相冲突。死者权利或死者人格权表述中的“权利”是指道德权利,而民事权利能力中的“权利”是指法律权利。通过揭示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不同,可以化解这个两难问题,即应保护死者人格利益而非死者人格权。
三、死者人格利益法律保护的通说立场:理论挑战与回应
如前所述,保护死者人格将与现行民法规定的权利能力制度相冲突。面对这个难题,支持近亲属权益保护说的学者通过把“保护死者人格”本质上理解为“保护死者近亲属人格”来化解与现行权利能力制度的冲突。为了实现其理论目的,该主张的支持者提出如下两个理论挑战:利益幸存问题与主体问题。只有这两个理论挑战成立,我们才有理由接受近亲属权益保护说。但实际上,对它们的接受并不像通说的支持者们所设想的那样理所应当。
(一)作为间接说的近亲属权益保护说
最高人民法院在保护死者名誉的立场上曾经历“直接说—混合说—直接说”的摇摆[7],但是,目前无论是在实务界还是在理论界,我国保护死者名誉的通行主张都是间接说①笔者将在下文论证其实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场不是近亲属权益保护说,而更接近于法益保护说,将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场理解为近亲属权益保护说是由于二者在表面上看都保护死者近亲属。。直接说与间接说的主要差别在于是否直接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直接说),还是通过保护死者近亲属利益来保护死者利益(间接说)②直接说与间接说都有诸多不同版本,直接说包括死者法益保护说、死者权利保护说、死者人身权益延伸说等,间接说包括近亲属利益保护说、近亲属利益关联说、近亲属权利保护兼采社会利益说等。参见刘颖《〈民法总则〉中英雄烈士条款的解释论研究》,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101页。。间接说认为,在涉及名誉侵权的案件中,近亲属因名誉受损导致的精神损害通常源自死者名誉受损,所以近亲属因其名誉权或人格尊严受损而获得法律上的救济,可以申请法院判决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在保护自身人格利益的同时保护死者生前的人格利益,因此也叫“近亲属权益保护说”③主张近亲属权益保护说的学者,可参见魏振瀛《侵害名誉权的认定》,载《中外法学》1990第1期,第9页;张新宝《名誉权的法律保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37页;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葛云松《死者生前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载《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4期,第24页;张红《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护:案例比较与法官造法》,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4期,第147-151页。。魏振瀛可谓国内最早主张近亲属权益保护说的学者之一,他率先指出:“保护死者名誉的实质与作用是保护死者的配偶、子女和父母(以下简称近亲属)的利益……与其说对死者的名誉(这里说的是名誉,不是名誉权)需要民法保护,不如说是对死者的近亲属的利益或人身权的民法保护。对死者名誉的损害,可视为对其近亲属的利益或人身权的侵害。”[8]这种主张曾影响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场[9]。
(二)近亲属权益保护说提出的理论挑战:利益幸存问题与主体问题
在近亲属权益保护说的支持者中,葛云松说:“死者有何利益可言?”[10]又说:“只要是法律保护的利益,不论是不是权利,都须归属于权利主体。所以,只要认为死者的‘法益’受法律保护,那么就等于认为死者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或者至少和某些学者主张的一样,具有‘部分’民事权利能力。”[11]张红认为:“‘近亲属利益说’认为,死者已去,名誉权即告消灭,再无人格精神痛苦,他人侮辱、诽谤死者侵害的只是生者的名誉,导致生者精神痛苦”[12]。张善斌认为:“人死亡之后不再是民事主体,既不可能享有权利也不可能享有利益,而且死者不可能因侵害行为有任何损害”[13]。杨巍说:“人格之精神利益随自然人死亡而消灭”[14]。在此不一一列举,但是近亲属权益保护说的逻辑已清晰可见:为了不与民法体系中有关权利能力的规定相冲突,近亲属权益保护说认为自然人死后精神利益也随之消失,因为自然人死后原本承载其利益的主体消失,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利益可以通过继承找到新的承载者,但是由于精神利益具有专属性,无所依附,因而只能随着死者肉身的消灭一道消灭。进而,我们可以将近亲属权益保护说提出的理论挑战归纳如下:(1)自然人死后再无精神利益;(2)因为精神利益依附的主体不存在了。前者称之为“利益幸存问题”,后者称之为“主体问题”。
(三)对利益幸存问题的回应
笔者认为近亲属权益保护说的上述主张都是不成立的。首先,针对自然人死后精神利益一同消灭的主张,这里涉及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的精神利益与这个人的自然存活时间是必然吻合的吗?如前所分t1、t2、t3时间节点,一个生存于t1—t2时段的人其精神利益也只能存在于这个时间段吗?如果是必然吻合的,那么自然人死后再无精神利益的主张就是成立的。但是答案是否定的,笔者认为一个生活在t1—t2时段的人,他的人格精神利益可以存在于t2以后的t3。我们可以根据自身利益内容所涉及的对象不同分为“涉及自我的自身利益”与“涉及他人的自身利益”[15],前者的例子如“我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险受益人是自己”,后者的例子如“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我的心愿”。事实上,随着一个人死亡而消灭的是那些不再能够被身后事件所影响的利益,这些利益包括涉自利益中的绝大多数,例如所有依附于我们的感官和心理特征而获得的利益将随着死亡不存在,因此身后事件好的坏的也都不会影响它们。涉自利益里面还有一小部分利益是可以幸存于t2以后利益主体已不存在的世界,例如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精神利益,以及遗产和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利益,这些大部分也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还有一些涉他利益也是可以幸存于t2以后的世界的,如某人生前愿望就是死后世界和平、消灭贫穷等,但是这些涉他利益不受法律保护。与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相关的精神利益为什么能够幸存于t2以后权利主体不存在的世界?这是由这些精神利益的性质决定的。以名誉为例,一个人的名誉通常涉及社会与他人对他的评价,而社会评价是独立于权利主体而存在的。换言之,自然人死亡之后对他的社会评价依然存在,因此与这些社会评价相关的名誉利益当然也就存在。此外,法律对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保护事实上也变相地承认了精神利益幸存于自然人死亡之后。我们还是通过法条来进行分析。《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四条规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如果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不存在,那么也就不存在对死者姓名、名誉、隐私等的侵害,进而也就不存在死者近亲属作为有权原告起诉一事了。所以,自然人死后,部分生前利益可以幸存于死后。
(四)对主体问题的回应
近亲属权益保护说提出的主体问题也是不成立的。主体问题与利益幸存问题存在密切联系,因为近亲属权益保护说正是因为权利或利益主体不存在所以主张利益不存在。为了明晰自然人死后精神利益无所依附这一问题的症结,我们应该对“死者”这一概念进行解释,并将它与尸体或遗体等概念区分开来①对遗体或尸体法律属性的讨论也是民法中一个重要的话题,但并非本文探讨的对象,在此不赘述。相关讨论参见杨立新、曹艳春《论尸体的法律属性及其处置规则》,载《法学家》2005年第4期,第76-83页;申卫星《论遗体在民法教义学体系中的地位——兼谈民法总则相关条文的立法建议》,载《法学家》2016年第6期,第162-174页。。尸体或遗体指自然人死后遗留下来由一堆原子构成的并且会随着时间变化在物理上产生变化的事物,但是死者是那个“生活在t1—t2时间段现在已逝去的人”,悼念死者不是悼念在棺材中的骨灰或衣物(t2以后与死者相关的事物),而是悼念他记忆中活在t1—t2时间段的那个人[16]。遗体上的人格利益(如死者生前的意愿)是t1—t2时间段人格利益的表达和投射,我们设想一具尸体成为侮辱、诽谤、贬损、丑化的对象时,实际上指的是死者生前的意愿(如死后遗体完整的意愿)和人格利益(如名誉利益)受到侵害。总之,对死者人格利益的损害指的是对在后人记忆中存在于t1—t2时段那个人的损害而非对遗体或尸体的损害,后者是物,不能作为主体。但是死者与自然人唯一的差别是,死者不能作为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主体,但是能够作为概念上的主体。很多民法学者认为一个人死后自然其利益也就不存在了,是因为他们混淆了在概念上至关重要的一个区分:“利益幸存于t3”与“在t3拥有利益”,前者不需要利益的主体同时存在于t3,而后者要求主体存在于t3。而当我们说保护死者利益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保护“幸存于t3的利益”,而不是保护“某人在t3拥有利益”,并不预设在t2以后存在利益主体,也就不会与权利能力制度相冲突。
四、近亲属权益保护说的理论困境与解释论分析
近亲属权益保护说在如下方面存在问题:第一,近亲属权益保护说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理论基石之上,即为其一众支持者所共享的如下理论前提是值得商榷的:对精神利益的损害必须以感受到精神痛苦为前提;第二,依据近亲属权益保护说进行法律制度的设计将在保护死者利益上产生“乌龙”现象,即从保护死者利益这一初始目的出发最终却无法立足对死者利益的保护;第三,近亲属权益保护说还存在无法融贯解释的各种情形。以下笔者将在揭示近亲属权益保护说存在的上述困境后,从解释论的角度来分析并找出通说陷入这些困境的原因。
(一)近亲属权益保护说的理论困境
1. 近亲属权益保护说建立在错误的理论预设之上。结合上述对近亲属权益保护说的讨论,我们发现近亲属权益保护说的支持者预设如下立场:对精神利益的损害必须以感受到精神痛苦为前提。近亲属权益保护说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人死后不再具有感知到精神痛苦的能力,所以即使死者存在精神利益,那么侮辱、诽谤也无法造成损害。
笔者认为,近亲属权益保护说所预设的上述立场是不成立的,在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先厘清精神痛苦、精神损害、精神利益受损三者之间的关系,因为近亲属权益保护说持有上述立场正是由于忽略了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别。笔者认为精神损害应该被理解为包含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受损这两个要素,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之为对精神损害的广义理解[17]。精神利益受损是指利益主体关于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遗骨等的意愿因侵权行为而被损害,而精神痛苦则是自然人的主观心理感受,死者无此感受。精神利益受损是精神损害的客观维度,而精神痛苦是精神损害的主观维度,精神利益受损可以被理解为精神痛苦的原因,精神痛苦是知晓自身利益受损后的表现。精神痛苦以知晓(即心理意识存在)为必要条件,但是精神利益受损不以知晓为必要条件。例如,某人被造谣与儿媳妇有不正当关系,但是全世界除了他自己外都知道这个消息,因此他经常看到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但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在这个情形中,此人的名誉利益肯定受到了损害,因为对他的社会评价降低了,但是由于不知晓原因他就不会有精神痛苦,因此他也就不会去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果将精神损害等同于精神痛苦,会导致实务中对精神损害很难认定,而且将无法融贯地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和第八条中的相关规定。该解释在第三条中规定“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可见精神痛苦与精神损害是两个不同概念。同时,第八条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从中可以看出,精神损害另外还涉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这一要素,如果精神损害没有造成严重后果,那么就是精神损害中的精神利益受损这类要素受到赔偿,对应当事人要承担的民事责任是: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这是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遗骨等精神利益遭受损害后可以请求主张的;而如果精神损害造成了严重后果,那么除了上述赔偿外,精神损害中精神痛苦及其引发的身体损害这类要素就要额外受到赔偿,因此此类要素对应当事人要承担的民事责任是: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民法学家王泽鉴就持有这一立场,他说:“抚慰金赔偿的是精神利益受损产生的精神痛苦”[18]。因此,我们不应该将精神损害等同于精神痛苦,而应该将精神损害理解为包含精神利益的损害与精神痛苦这两个要素。
2. 近亲属权益保护说将背离保护死者利益的初衷。通过把“保护死者人格”本质上理解为“保护死者近亲属人格”,近亲属权益保护说虽然可能避免与现行法律体系中有关权利能力制度的规定相冲突,但是实际上它也很可能背离法律保护死者的初衷而转向保护生者(即死者近亲属)。我们分两种情况来讨论:第一种情况,死者存在近亲属;第二种情况,死者不存在近亲属。就第一种情况而言,当死者尚存在近亲属的时候,对于近亲属权益保护说而言对死者利益的保护需要证明其近亲属精神利益受损。因为就像近亲属权益保护说的代表葛云松所言:“损害死者名誉并不必然侵害死者亲属的名誉权或者人格尊严,死者亲属仅仅证明死者名誉受损害是不够的,还必须证明自己的名誉或者人格尊严也因此而受到损害。”[19]这意味着万一近亲属人格尊严没有受损,那么就无法适用近亲属权益保护说去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可见将对死者的保护依附于对死者近亲属的保护将导致死者利益经常会无法获得保护。此外,从法律制度设计上来看,现实中死者近亲属证明其精神利益或人格尊严因死者而受损往往是困难的,这就在制度上给保护死者利益增加了障碍,最终可能导致死者及其近亲属的人格利益都无法得到保障。而在第二种情况中,当死者不存在近亲属时,坚持近亲属权利保护说就意味着死者人格尊严在制度层面全然不能得到保护,这显然是违反“法律在道德上负有保护死者的义务”这一初衷的。
为了能够融贯一致地理解法律保护死者人格利益以及现行法律对“近亲属”概念的理解,我们应该区分对待死者无近亲属的两种不同情形:一种情况是因死者生活的年代久远其近亲属自然也就不存在,如曾在我国台湾地区轰动一时的“诽韩案”[20]主角韩愈,因为韩愈离我们生活的时代太远,无法对现行法律保护其人格尊严和人格发展形成合理的预期,而法律保护死者就在于让生者形成这种预期——自己死后人格利益会受到法律保护,因此对于这种距离我们生活年代太久远的情况现行法律实无保护之必要。另一种情况是死者近亲属都先于他离世或死者因某些原因与近亲属断绝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死者仍然是我们共同体的成员,仍会对法律如何对待无近亲属的死者形成预期,我们应该在法律制度上考虑对他的保护,目前对于这一方面的立法是欠缺的。因此,笔者认为立法者对于保护死者利益的态度与法律制度的配套存在不一致性,而近亲属权益保护说又迎合了这种不一致性。因为在近亲属权益保护说看来,既然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实质在于保护死者近亲属的人格利益,那么对这类无近亲属的死者就不应该加以保护。
3. 近亲属权益保护说无法融贯解释的诸情形。第一,近亲属权益保护说无法解释死者生前名誉受损时为何近亲属没有诉权。如果真像近亲属权益保护说主张的那样,死者的近亲属是基于其自身人格权利受损而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当死者A还是活着的自然人时,对A名誉侵犯也同样会损害到近亲属B的名誉权,为什么此时法律没有规定B可以基于自己的名誉权受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呢?对此,近亲属权益保护说无法解释。第二,近亲属权益保护说无法解释法律应该平等对待英烈与普通死者。假设英烈和普通死者都没有近亲属,此时按照近亲属权益保护说的立场二者都不应该予以保护,但是由于对英烈生前人格利益的保护还涉及保护公共利益,因此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来保护英烈。但是正如很多人对“英烈条款”的担忧,认为此前《民法总则》对英雄烈士的特别规定意味着对英烈人格利益相较于普通死者的特别保护,通过对比同样没有近亲属的英烈和普通死者,近亲属权益保护说恰恰坐实了这个“特别保护英烈”的说法。第三,近亲属权益保护说无法解释如下日常直觉。当我们说保护死者人格尊严,尊重死者的时候,我们谈论和尊重的对象是死者而非死者的近亲属,因此当我们说法律要保护死者的时候应该指对死者本人而非其近亲属的保护。所以接受近亲属权益保护说将违反我们的日常语言表达习惯。第四,近亲属权益保护说无法融贯一致地解释死者名誉利益与死者其他人格利益。如果说死者名誉受损会导致其近亲属名誉权受损,进而近亲属可因自身人格权受损导致精神痛苦而提起诉讼,那么对于其他同样受法律保护的死者人格利益(如姓名、肖像、荣誉、隐私、遗体等)而言,近亲属权益保护说似乎难以融贯地作类似主张。因为对除名誉外其他人格利益的损害完全有可能不损害到死者近亲属的人格精神利益,事实上其他人格利益的确不像名誉利益那样具有联动性(即死者名誉受损的同时很可能近亲属名誉也受损)。基于笔者在前文已经论证了精神痛苦与人格精神利益受损是两码事,虽然死者近亲属仍然可能因死者上述人格利益受损而遭受精神痛苦进而提起诉讼,但是此时近亲属的人格精神利益可能并没有受损。换言之,此时近亲属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姓名、肖像、荣誉、隐私等利益受损而提起的诉讼,而仅仅因为自己遭受到了精神痛苦,在涉及除名誉利益以外的人格利益时近亲属权益保护说很可能是自我挫败的。
(二)从解释论角度理解近亲属权益保护说的理论困境
笔者认为,近亲属权益保护说的内容基本上属于一种理论推理,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报案例(彭家惠诉《中国故事》杂志社名誉权纠纷案)和后来的指导性案例(“狼牙山五壮士”名誉侵权案)来看,近亲属权益保护说对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理解是有瑕疵的,应当被放弃。
通过考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和第七条,我们可以确定如下事实:法律对死者人格利益进行保护,同时法律也对死者近亲属人格权益进行保护。该解释第三条表明:“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显然这是对死者近亲属的保护。但是法律到底保护死者近亲属的什么,这是值得讨论的。笔者认为,从解释论角度看,至少可以有以下几种理解:(1)保护死者近亲属免受因侵权导致的精神痛苦,这是文义的最直接表达;(2)在保护死者近亲属免受精神痛苦的同时,也保护死者近亲属的人格利益不因死者而受到侵犯。正如前文所述,精神痛苦与人格精神利益受损是相互独立、相异的两个概念,在逻辑上完全可以设想一个人人格精神利益①有必要再次对“人格精神利益”这一概念予以强调,它是指利益主体关于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遗骨等非财产性精神利益受到合理对待的意愿(无论生前还是身后),它不以知晓为前提。例如,一个人死后遗体不受玷污的意愿,一个人死后名誉不受侮辱、诽谤的意愿,等等。受损但是没有精神痛苦。因此,在死者近亲属身上,精神痛苦与人格精神利益受损进一步可以有如下两种关系:第一种关系,由于死者人格精神利益受损导致近亲属自身人格精神利益受损害继而导致的精神痛苦;第二种关系,由于死者人格精神利益受损导致自身精神痛苦,此时近亲属自身人格精神利益可能受损也可能没受损。显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对应的应该是第二种关系的内容。换言之,近亲属提起诉讼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并不以自身人格精神利益受损为要件。
由于近亲属权益保护说将精神痛苦等同于人格精神利益受损,因此在近亲属权益保护说看来保护死者近亲属免遭精神痛苦也就是保护死者近亲属的人格精神利益免于损害。然后基于上述谈到的错误前见(即精神利益受损以利益主体知晓为前提),该学说认为死者无法感受精神痛苦,因此死者人格精神利益无法受损。进而就进一步推论出保护死者其实是保护死者近亲属的方便说法,因为死者无从保护,所以从来只有对死者近亲属的保护。进一步地,因为近亲属权益保护说将精神痛苦等同于人格精神利益受损,所以会认为当死者近亲属因精神痛苦而提起诉讼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时,是基于自身的人格权益受损请求赔偿。
在实践中,近亲属权益保护说也无法与后来的司法实践融贯一致。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保护死者的立场前后有变化,但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之后,立场基本无大变化。从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报案例“彭家惠诉《中国故事》杂志社名誉权纠纷案”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场,在该案判决书中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彭家惠作为彭家珍烈士的近亲属对杂志社提起诉讼,是维护彭家珍烈士的名誉,而非自身的名誉权受到侵害。一审法院将侵权人实施侵害死者名誉权的行为,认定同时对死者的近亲属也构成了侵权,没有法律依据。”[21]虽然这不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直接观点,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将其作为公报案例或许默认其观点。再从更近的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指导性案例的“狼牙山五壮士”名誉侵权案来看,其裁判理由中明确:“案涉文章通过刊物发行和网络传播,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仅损害了葛振林的个人名誉和荣誉,损害了葛长生的个人感情,也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情感……洪振快作为具有一定研究能力和熟练使用互联网工具的人,应当认识到案涉文章的发表及其传播将会损害到‘狼牙山五壮士’的名誉及荣誉,也会对其近亲属造成感情和精神上的伤害,更会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②葛长生诉洪振快名誉权、荣誉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99 号(2018年)。从“损害了葛振林的个人名誉和荣誉”“损害到‘狼牙山五壮士’的名誉及荣誉”等表述中我们可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场与近亲属权益保护说不同,最高人民法院主张死者人格利益可以受到损害,也并非如近亲属权益保护说主张的那样单凭死者近亲属自身权益受损就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在此死者并非多余的一环。
所以,近亲属权益保护说是一种不当的理论推论,它混淆了“精神痛苦”与“人格精神利益受损”这对概念,然后基于错误前见对司法解释进行了不当解释。由于近亲属权益保护说将精神痛苦等同于人格精神利益受损,并且错误地把保护死者利益与保护近亲属人格权益等同起来,这一切共同导致上述理论困境。
五、结论
在我国,死者人格权最多算作一种道德权利而非法律权利,因此法律不对死者人格权进行保护,最多保护的是死者的人格利益。近亲属权益保护说(通说)认为在保护死者人格过程中存在如下理论挑战:自然人死后再无精神利益,因为精神利益依附的主体不存在了。事实上,通过合理解释“死者”概念以及区分“利益幸存于t3”与“在t3拥有利益”我们就能回应这些挑战。此外,近亲属权益保护说存在一系列理论问题:第一,它预设某种错误的前提假设,认为精神损害必须以感受到精神痛苦为前提;第二,坚持近亲属权益保护说将背离保护死者利益的初衷;第三,近亲属权益保护说还存在一系列无法融贯解释的情形。而存在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亲属权益保护说基于错误前见对法律作出的不当解释,并在概念上错误地将精神痛苦等同于人格精神利益受损,并且错误地把保护死者利益与保护近亲属人格权益等同起来。因此,笔者认为,近亲属权益保护说不应成为《民法典》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阿基米德支点,立法者应采取行动回应通说的理论困境,而不是沿袭20年前的陈规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