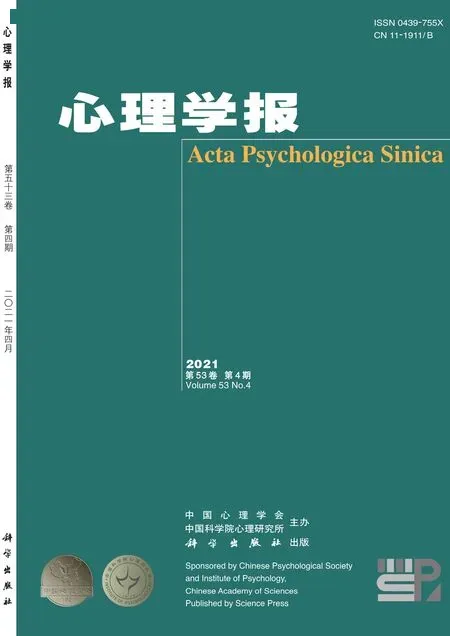性别化名字对个体印象评价及人际交往的影响*
2021-04-14温芳芳谢志杰
佐 斌 刘 晨 温芳芳 谭 潇 谢志杰
性别化名字对个体印象评价及人际交往的影响
佐 斌刘 晨温芳芳谭 潇谢志杰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社会心理研究中心) (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9)
名字在个体印象评价和人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结合刻板印象内容模型, 从刻板印象维护视角出发, 通过3个研究考察了性别化名字的热情能力感知, 基于此探究性别化名字对不同性别个体的印象评价及人际交往的影响。结果发现:(1)人们对男性化名字的能力评价高于女性化名字, 对女性化名字的热情评价高于男性化名字; (2)性别化名字影响男性的能力评价和女性的热情评价; (3)性别化名字影响人们对女性的交友偏好, 热情评价在其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性别化名字影响人们和男性的共事偏好, 能力评价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研究揭示了性别化名字影响印象评价的模式, 并为理解人际交往中名字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性别化名字, 印象评价, 热情, 能力, 人际交往
1 引言
在社会发展中, 人们逐渐形成了关于不同性别对象所具有的典型特征、行为的观念。一般而言, 人们认为男性比女性更有能力, 而女性比男性更具热情(Glick & Fiske, 2011)。这种相对稳定的认识也体现在人们对姓名这一社会符号的感知上。比如对英文名的研究发现, 典型男性名字往往被感知为高能力, 女性名字被感知为高热情(Newman et al., 2018)。中国人的名字也具有鲜明的性别色彩。但有意思的是, 中国也存在男性使用女名或者女性使用男名的情况。对名字的知觉会影响人们对名字主人的评价和交往意向(Mehrabian, 2001; 包寒吴霜等, 2016)。这就引发了一系列有趣的问题:隐含性别线索的名字和个体的性别会如何影响印象评价?进一步, 这种评价会对个体的人际交往有何影响?本研究结合刻板印象内容模型(Fiske et al., 2002; 佐斌等, 2015),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考察性别化名字的热情与能力感知, 并从刻板印象维护的视角探究性别化名字和性别对个体印象评价和人际交往的影响, 为理解人际知觉中名字的作用模式提供参考。
1.1 性别化名字的热情能力特质感知
名字作为一种语言符号, 具有社会分类的功能。大量研究表明, 英文名和中文名大多有明确的性别定向(Lindsay & Dempsey, 2017; Pilcher, 2016; 苏红, 任孝鹏, 2015)。依据名字的性别典型性程度, 可将名字分为性别化名字(包括男性化名字、女性化名字)和中性化名字(包寒吴霜等, 2016; Duffy & Ridinger, 1981)。名字隐含的性别信息影响名字的特质感知。根据刻板印象内容模型, 人们主要在热情和能力维度感知他人(Abele & Wojciszke, 2007; 佐斌等, 2014)。人们持有男性高能力、低热情以及女性高热情、低能力的刻板印象(Clough et al., 2017; Glick & Fiske, 2011)。以往研究发现, 性别化名字能激活性别刻板印象(Cotton et al., 2008; Smith et al., 2005)。因此, 性别化名字的特质感知与性别刻板印象存在紧密关联。对英文名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人们对常用男性名字的能力评价高于女性名字, 而对女性名字的热情评价高于男性名字(Etaugh & Geraghty, 2018; Newman et al., 2018)。
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 很多英文名字具有明显的性别定向(Pilcher, 2016)。中国文化讲求男女有别, 男性的名字强调阳刚之气, 女性的名字则蕴含阴柔之美(苏红, 任孝鹏, 2015)。不过, 目前关于性别化名字的特质感知研究较少。包寒吴霜等(2016)考察了人们对性别化名字持有者的评价, 发现人们对性别化名字持有者的评价存在性别角色差异。但是对名字持有者的评价不同于对名字的感知。另一方面, 尽管性别角色的测量项目(男性化与女性化)与刻板印象内容(能力与热情)存在交叠(佐斌等, 2014), 然而热情与能力涵盖的内容更为广泛, 两维度对于社会知觉中的变异也具有较高的解释力(Wojciszke et al., 1998)。因此有必要对名字的热情能力感知进行本土化检验。
1.2 性别化名字对个体评价的影响
他人对名字的知觉影响对名字主人的评价。有研究发现, 男性化名字的个体被感知为更有能力(Etaugh & Geraghty, 2018), 女性化名字的个体被感知为更具热情(Mehrabian, 2001), 因为人们认为名字隐含的性别与个体性别相一致, 会依据名字的性别线索评价他人。然而, 现实中存在名字性别信息和个体性别不一致的现象。在中国, 使用女性化名字的男性与使用男性化名字的女性不在少数。既然男性化名字和女性化名字分别被感知为“高能力”和“高热情”, 男性和女性分别给人以“高能力”和“高热情”的印象, 那么在热情和能力维度上, 隐含性别信息的名字和生理性别会对名字主人的评价产生怎样的影响?
社会角色理论(social role theory)指出, 性别刻板印象源于人们对两性传统的职业角色的观察, 对两性“应该具有”的特质进行了严格规定(Eagly, 1987), 即男性“应该”是成就定向、高能力的, 而女性“应该”是关怀取向、高热情的(Ellemers, 2018; Prentice & Carranza, 2002)。若个体缺乏“应有”的性别特质则违反了刻板印象, 人们会在认知和行为层面抵制那些反刻板的个体, 以维护性别刻板印象(Bosak, Kulich et al., 2018; 刘晅, 佐斌, 2006)。在认知层面, 人们会对违反刻板预期的个体做出负面评价, 比如缺乏亲和力、不够温柔的女性被评价为低热情, 优柔寡断、缺乏竞争力的男性被评价为低能力(Bosak, Eagly et al., 2018; Eagly et al., 2020)。
以往研究发现, 相较于名字和性别一致的个体,人们对名字和性别不一致个体的外显与内隐评价都更消极(包寒吴霜等, 2016; Fox et al., 2002; 张积家等, 2006)。这一现象可被概括为“人−名匹配效应”, 指名字和性别一致的个体能获得更积极的评价也因此更受欢迎。这种偏好反映了人们对违反性别刻板印象个体的抵制, 暗示着名字和性别不一致的个体可能被感知为具有反刻板的特质(包寒吴霜等, 2016; Etaugh & Geraghty, 2018; 杨婷, 任孝鹏, 2016)。从刻板印象维护视角出发, 我们推断在个体 “应有”的评价维度(能力之于男性, 热情之于女性), 名字和性别不一致的个体可能会受到负面评价。具体而言, 男性被认为是高能力的群体, 而人们对女性化名字的能力评价可能低于男性化名字, 使用女性化名字的男性也就违反了男性高能力的刻板印象, 人们对女性化名字男性的能力评价可能低于男性化名字的男性; 同理, 男性化名字被感知为低热情, 男性化名字的女性可能违反了高热情的刻板印象, 人们对男性化名字女性的热情评价也就低于女性化名字的女性。
1.3 性别化名字对人际交往的影响
名字知觉对人际交往具有深远影响。在社会互动中, 人们同他人沟通情感以满足亲和需要, 同时也希望通过与他人协作实现个人难以达成的目标(Carrier et al., 2019)。根据这两种社会动机, 人际交往情境也可相应地分为交友情境和任务情境。特质与情境之间的匹配关系影响人际交往(Deaux & Major, 1987; Spence, 1985), 在交友和任务导向的社会互动中, 人们选择交往对象所关注的特质不同(Benson et al., 2019; Fiske, 2018)。比如在郊游情境下, 人们更关心交往对象是否友善(Kervyn et al., 2012); 而需要选择谈判代表时, 人们更关注交往对象是否具备目标达成有关的能力特质(McCroskey & McCain, 1974; Wojciszke et al., 1998)。
名字对不同情境下的人际交往有何影响呢?结合名字的知觉特征以及情境和特质的匹配关系, 人们在交友情境更关注潜在交往对象的热情特质。如果使用男性化名字会降低女性的热情感知, 那么使用女性化名字的女性就更可能被选为伙伴。而对于使用女性化名字的男性, 虽然热情特质在交友中备受重视, 但西方研究发现, 网络交友中人们也更喜欢能力突出的男性(Whitty & Buchanan, 2010)。不同于西方的“男性化”文化, 中国文化偏“女性化” (王登峰, 崔红, 2007)。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影响个体对男性面孔的感知与审美(李朝旭等, 2017; 温芳芳, 佐斌, 2012)。据此推测个体对不同性别化名字男性的交友偏好或许也存在文化差异。在任务导向情境, 人们更关注同伴的能力特质, 若女性化名字会降低男性的能力感知, 则男性化名字的男性更可能被选作共事搭档。对于使用男性化名字的女性, 有研究表明男性化名字有助于女性在理工科、法律等男性传统优势领域获得良好发展(Coffey & Mclaughlin, 2016; Coffey& Mclaughlin,2009), 但这些研究并未探讨名字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的机制。因此, 名字对人际交往的影响及其机制仍需研究加以深入探讨。
1.4 本研究目的与假设
以往研究关注名字对个体评价的影响, 但并不清楚名字本身给人留下的印象, 而明晰名字的知觉特征有助于揭示名字影响印象评价的内部机制。另外, 从名字影响个体评价的行为后效来看, 先前研究探讨了名字对人际信任、人际吸引和人事决策的影响(辛志勇等, 2015; 郭凤等, 2020), 但对于人际交往中名字作用机制的认识非常有限。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本研究拟基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 通过3个研究, 探究性别化名字在热情能力维度的感知特征, 以此为基础探索名字对不同性别个体印象评价和人际交往的影响及内部机制。研究1考察性别化名字的热情与能力感知。研究2探究名字和性别对个体印象评价的影响。研究3分别在交友和任务情境下探究名字对人际交往的影响及机制。研究提出以下假设:(1)人们对男性化名字的能力评价高于女性化名字, 对女性化名字的热情评价高于男性化名字。(2)相较于女性化名字的女性,男性化名字的女性给人以低热情的印象; 相较于男性化名字的男性, 女性化名字的男性给人以低能力的印象。(3)在交友情境中, 人们倾向于选择女性化名字的女性为伙伴, 热情评价在名字和选择结果中起到中介作用; 在任务情境下, 人们倾向于选择男性化名字的男性为搭档, 能力评价起到中介作用。
2 研究1:性别化名字的热情与能力感知
2.1 目的
结合刻板印象内容模型, 采用特质评价法, 在热情与能力维度比较人们对男性化名字和女性化名字的感知差异。
2.2 方法
2.2.1 被试
招募大学生被试176名, 其中6人选项重复或有明显作答规律, 可能存在不认真作答的情况, 故剔除其数据, 最终有效被试170人(男性73名, 女性97名, 平均年龄21.7岁,= 3.06岁)。所有被试自愿参与研究, 问卷作答完毕获得一定报酬。采用问卷星的题目随机设置, 随机抽取70~100个名字请被试进行热情和能力评价。
2.2.2 研究材料与程序
研究材料为名字评价问卷, 包括性别化名字和热情能力特质词。名字源于高校花名册, 剔除名字姓氏仅保留名, 由39名本科生在性别化、熟悉度和吸引力方面进行1~7分评定。性别化评定采用双维评价法, 每名评价者需要分别评价名字在多大程度上适合男性和女性, 用适合男性分数减去适合女性分数, 男性化名字的取值范围[4, 6], 女性化名字的取值范围[−6, −4]。最终得到50个男性化名字和50个女性化名字, 两类名字在熟悉度、吸引力方面无差异。热情、能力维度特质词参考Fiske等(2002)的研究。由于名字的寓意通常偏积极, 本研究采用积极的特质词。热情维度特质词为热情友好、真诚可信, 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0; 能力维度特质词为聪明能干、做事高效, 内部一致性信度0.82。
被试被告知参与一个名字评价研究, 首先填写性别、年龄基本信息, 接着请被试尽量凭借直觉, 在热情和能力维度对名字进行1~7分的评价。
2.3 结果
为检验性别化名字在热情和能力维度的感知特点, 以性别化名字为单位进行方差分析, 比较不同被试对同一个名字的热情能力评分。结果发现, 评价维度主效应显著,(1, 49) = 29.48,< 0.001, 偏η= 0.38; 性别化名字主效应不显著,(1, 49) = 0.02,0.88; 性别化名字和评价维度的交互效应显著,(1, 49) = 46.35,< 0.001, 偏η= 0.49。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在热情维度, 女性化名字的热情得分(= 4.69,= 0.20)高于男性化名字(= 4.52,= 0.18),(1, 49) = 24.44,< 0.001; 在能力维度, 男性化名字的能力得分(= 4.56,= 0.28)高于女性化名字(= 4.41,= 0.22),(1, 49) = 11.14,< 0.05。
2.4 讨论
研究1发现, 人们对男性化名字的能力评价高于女性化名字, 对女性化名字的热情评价高于男性化名字。鉴于名字的维度感知差异, 结合男性“高能力”以及女性“高热情”的性别刻板印象, 在热情与能力维度上, 性别化名字会对不同性别的名字主人的评价产生什么影响?研究2将探究名字对男性与女性印象评价的影响。
3 研究2:名字和性别对个体印象评价的影响
3.1 目的
操纵名字性别化和名字主人性别, 探究名字对不同性别个体的热情和能力评价的影响。
3.2 方法
3.2.1 被试
140名大学生参与线上实验, 19人未通过问卷中的操纵性检验被剔除, 最终有效被试121名(男生57名, 女生64名, 平均年龄22.6岁,= 3.14岁)。问卷按照名字主人性别分为两个版本, 问卷1中的人物均为男性, 问卷2的人物均为女性。被试随机填答一个版本的问卷, 其中62人作答问卷1(男生27人, 女生35人), 59人作答问卷2(男生30人, 女生29人)。所有被试自愿参加实验, 实验结束后获得一定报酬。
3.2.2 实验设计
采用2(名字性别化:男性化, 女性化) × 2(名字主人性别:男, 女) × 2(被试性别:男, 女) × 2(评价维度:热情, 能力)的混合实验设计, 名字主人性别和被试性别为被试间变量, 因变量为被试对名字主人的热情和能力评价得分。
3.2.3 实验材料与程序
研究采用想象情境范式, 实验材料改编自包寒吴霜等(2016)研究2的情境指导语。首先, 告知被试将参加一个印象评价研究。接着, 向被试介绍有两位交换生将进入班级进行交流学习, 且均为男生(另一批被试被告知为女生)。但因信息有限只能呈现两个人的名字, 男性化名字和女性化名字为研究一中的“余铭辉”和“杜惠敏”。随后, 为确保被试已掌握交换生信息, 需回答操纵性检验题:根据前面的人物信息, 判断人物性别。该题答错自动停止作答, 问卷作废。通过操纵性检验的被试随后在“热情的、友好的、真诚的”3个热情特质词以及“聪明的、能干的、高效的”3个能力特质词上, 对两名交换生进行1~7分的评价。3个热情特质词的评分均值以及3个能力特质词的评分均值分别作为热情和能力评价指标。本实验中热情测量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4, 能力测量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2。
3.3 结果
被试对不同性别化名字个体的热情和能力评价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评价维度主效应显著,(1, 117) = 5.21,< 0.05, 偏η= 0.04; 名字和名字主人性别的交互效应显著,(1, 117) = 15.92,< 0.001, 偏η= 0.12; 名字和评价维度交互效应显著,(1, 117) = 16.41,< 0.001, 偏η= 0.12; 名字和被试性别的交互效应显著,(1, 117) = 4.99,< 0.05, 偏η= 0.04。其他主效应以及交互效应均不显著。

表1 对不同性别化名字的男性和女性的热情与能力评价(M ± SD)
对名字和名字主人性别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1)对男性的评价在名字上存在显著差异,(1, 119) = 13.08,< 0.001; 对女性的评价在性别化名字上存在显著差异,(1, 119) = 4.76,< 0.05。(2)对女性化名字主人的评价存在性别差异,(1, 119) = 7.23,< 0.05, 女性化名字的男性评价(= 4.87,= 0.89)低于女性(= 5.29,= 0.80)。对名字和评价维度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性别化名字在热情评价上存在显著差异,(1, 120) = 5.86,< 0.05; 性别化名字在能力评价上存在显著差异,(1, 120) = 10.63,< 0.001。对名字和被试性别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女被试对男性化名字个体的评价(= 5.18,= 0.60)显著高于女性化名字个体(= 4.96,= 0.82),(1, 119) = 5.67,< 0.05。
分别比较性别化名字对男性和女性名字主人的热情和能力评价的影响, 结果见图1。(1)对男性名字主人的方差分析发现, 名字主效应显著,(1, 60) = 12.54,< 0.001, 偏η= 0.17; 名字和评价维度的交互效应显著,(1, 60) = 8.91,< 0.01, 偏η= 0.13。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被试对男性的能力评价在名字上差异显著,(1, 61) = 16.69,< 0.001。(2)对女性名字主人的分析发现, 名字主效应显著,(1, 57) = 4.57,< 0.05, 偏η= 0.07; 名字和评价维度的交互效应显著,(1, 57) = 7.54,< 0.01, 偏η= 0.12。其他主效应及交互效应均不显著。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被试对女性的热情评价在名字上存在显著差异,(1, 58) = 12.90,< 0.001。

图1 对不同性别化名字男女个体的热情能力评分
注:*表示< 0.05, **表示< 0.01, ***表示< 0.001,“男名”为“男性化名字”, “女名”为“女性化名字”, 下图同
采用独立样本检验, 分别比较性别化名字与名字主人性别一致、不一致两种条件下个体的热情与能力评价分数, 进一步检验名字和性别对个体评价的影响。结果发现, 在名字和名字主人性别一致条件下, 被试对男性化名字男性的热情评价低于女性化名字的女性,(119) = −1.94,= 0.055,= −0.36; 而名字和名字主人性别不一致时, 被试对使用女性化名字的男性的能力评价显著低于男性化名字的女性,(119) = −2.77,< 0.01,= −0.51。
3.4 讨论
研究2发现, 男性化名字主人被感知为高能力、低热情, 女性化名字主人被感知为高热情、低能力, 表明性别化名字影响他人对名字主人的热情和能力评价。名字和性别一致的个体获得了更积极的评价, 验证了人−名匹配效应。对不同性别人物的名字和维度交互作用分析发现, 女性取男性化名字被认为低热情, 男性取女性化名字被认为低能力。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2, 同时也揭示出人−名匹配效应背后的原因:使用相反性别化名字的个体会被认为缺乏“应有”的特质, 从而受到较为负面的评价。而人们对女性化名字的男性评价更消极, 对男性化名字主人的评价则无性别差异, 这体现了名字影响个体评价的性别不对称性, 原因可能在于人们通常认为男性的地位比女性更高(Moss-Racusin & Johnson, 2016),容易将具有异性特质的男性和低地位联系起来(Rudman et al., 2012)。因此相较于男性化名字的女性, 女性化名字的男性会受到更消极的评价。
不同于男性能力高于女性的传统性别观念, 本研究发现, 人们认为使用相反性别化名字的女性比男性更具能力。以男性化名字的男性为参照, 可以发现女性化名字降低了对男性的能力感知, 而被试对男性化名字女性的能力评价较高, 导致了男性化名字的女性比女性化名字的男性被感知为更有能力。该结果表明, 相较于个体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别, 性别化名字表征的社会性别在个体评价中可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研究2中采用一个名字代表一类性别化名字, 研究结论的推广性可能受到限制。研究3通过两个子研究, 创设交友、任务两类更具生态性的情境, 关注性别化名字影响个体评价的行为后效, 考察名字和性别对人际交往的影响及其内部机制。同时, 通过增设名字数量, 提升研究的外部效度, 并进一步检验研究2的发现。
4 研究3:名字和性别对人际交往的影响
4.1 研究3a:交友情境下性别化名字和性别对人际交往的影响
4.1.1 目的
在交友情境下考察不同性别化名字对人际交往的影响, 并探究印象评价的中介作用。
4.1.2 方法
(1)被试
在网上招募大学生被试159名。23名被试未通过操纵性检验被剔除, 有效被试136名(男62名, 女74名, 平均年龄21.65岁,= 2.94岁)。按照名字主人性别将问卷分为两组, 每组问卷有5个版本, 每个版本中人物的名字不同。其中问卷1~5中的人物均为男性, 问卷6~10的人物均为女性。被试随机填答一个版本的问卷, 其中71人作答第一组问卷(男生32人, 女生39人), 65人作答第二组问卷(男生30人, 女生35人)。所有被试均自愿参与实验, 通过操纵性检验的被试获得一定的实验报酬。
(2)实验设计
采用2(名字性别化:男性化, 女性化) × 2(名字主人性别:男, 女) × 2(被试性别:男, 女) × 2(评价维度:热情, 能力)的混合实验设计, 名字主人性别、被试性别为被试间变量。因变量为被试对名字主人的热情与能力维度评价以及交往选择结果。
(3)实验材料与程序
创设“交友”情境, 实验材料参考Kervyn等人(2012)研究中热情取向的情境。被试被告知参与一项情境想象研究, 首先阅读指导语:您将乘坐大巴去郊游。由于您报名时间晚, 车上只剩下两个空位, 这两个空位的位置差不多。您可以在报名系统看到客车座位预约旅客的名字和性别信息。接着, 被试需根据游客的名字和性别信息, 在热情和能力特质词上对两名游客进行1~7分评价, 之后在百分制量表上分别评价与两名旅客的同座意向。最后, 被试需回答一道操纵性检验题:根据游客信息, 判断下列游客的性别。此题答错问卷作废。
在名字的选择上, 选用研究1中5个男性化名字(余铭辉、范坤鸿、任鸣涛、谭振康、姜宏韬)和5个女性化名字(杜惠敏、汪玥萱、戴雪纯、钟思莹、姚钰静), 在Excel中进行随机分组, 具体过程如下:在Excel中按照性别化将名字列为两组并编号, 之后采用“RANDBETWEEN”公式在1到5的范围内生成随机整数, 两列名字中数值最接近的名字分为一组, 生成5组研究材料。结合名字主人的性别, 最终形成10套版本的问卷。特质词以及性别的操纵方式同研究2。实验3a热情、能力测量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66和0.80。5个男性化名字热情和能力评分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1和0.69, 5个女性化名字热情和能力评分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61和0.68。
4.1.3 结果
研究3a、3b中, 被试对使用男性化名字、女性化名字的男性、女性的热情和能力评价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研究3a、3b不同性别化名字人物的热情、能力评价(M ± SD)
(1)交友情境下性别化名字对评价的影响
5个版本的名字在热情和能力维度的评分一致性信度较好, 可忽略材料对结果的影响。以性别化名字、维度作为被试内变量, 人物性别和被试性别为被试间变量, 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见图2。名字、维度和目标性别交互效应显著,(1, 132) = 4.52,< 0.05, 偏η= 0.03; 名字和人物性别交互效应显著,(1, 132) = 14.10,< 0.001, 偏η= 0.10; 名字和维度交互效应显著,(1, 132) = 23.11,< 0.001, 偏η= 0.15。其他主效应、交互效应均不显著。
性别化名字、评价维度和名字主人性别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不同名字的女性人物在热情评价上存在显著差异,(1, 134) = 29.80,< 0.001; 不同名字的男性人物在能力评价上存在显著差异,(1, 134) = 7.23,< 0.01。名字和名字主人性别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对女性人物的评价在名字上差异显著,(1, 134) = 15.25,< 0.001; 对女性化名字人物的评价存在性别差异,(1, 134) = 20.07,< 0.001。名字和维度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对两类名字的热情评价存在显著差异,(1, 135) = 14.61,< 0.001; 两类名字在能力评价上存在显著差异,(1, 135) = 5.21,< 0.05。
采用独立样本检验, 分别比较了名字与名字主人性别一致、不一致两种条件下个体的热情与能力评价。结果发现, 在名字和名字主人性别一致条件下, 被试对男性化名字男性的热情评价低于女性化名字的女性,(134) = −4.38,< 0.001,= −0.76; 而在性别化名字和名字主人性别不一致条件, 被试对女性化名字的男性的能力评价显著低于男性化名字的女性,(134) = −3.25,< 0.01,= −0.56; 被试对女性化名字的男性的热情评价略高于男性化名字的女性,(134) = 1.83,= 0.07。

图2 交友、任务情境下被试对不同性别化名字男女个体的热情、能力评分
(2)性别化名字对交友意向的影响及中介效应检验
以被试对名字主人的选择结果作为被试内变量, 名字主人性别和被试性别作为被试间变量,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 名字主效应显著,(1, 132) = 5.38,< 0.05, 偏η= 0.04, 被试对女性化名字主人的交往意愿(= 54.11,= 22.07)高于男性化名字主人(= 45.89,= 22.07)。性别化名字和人物性别的交互效应显著,(1, 132) = 24.34,< 0.001, 偏η= 0.16。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对女性人物的交往意向在名字上存在差异,(1, 134) = 25.16,< 0.001, 被试对女性化名字女性的交往意向(= 62.72,= 20.20)显著高于男性化名字的女性(= 32.28,= 20.20); 对男性人物的交往意向在名字上的差异边缘显著,(1, 134) = 3.05,0.08, 被试对男性化名字男性的交往意向(= 54.24,= 20.67)略高于女性化名字的男性(= 45.76,= 20.67)。
为进一步解释性别化名字影响人际交往的机制, 使用SPSS的MEMORE插件(Montoya & Hayes, 2017; 王阳, 温忠麟, 2018), 建立热情、能力维度在名字性别化和交友意向之间的中介模型。由于名字影响被试对女性人物的交往意向, 故建立以女性人物选择结果为预测变量的中介模型, 纳入评价维度、名字性别化和交友意向评分后的回归方程显著(= 0.44,(4, 60) = 11.64,< 0.001; 见图3), 女性化名字的女性比男性化名字的女性得到更高的热情评价(= 0.48,= 0.17;(64) = 2.90,< 0.01, 95% CI = [0.15, 0.81]); 而不同名字女性的能力评价差异不显著(= 0.20,= 0.14;(64) = 1.40,> 0.05, 95% CI = [−0.09, 0.49])。对女性的热情评价能够正向预测交往意愿(= 0.91,= 0.14;(60) = 6.69,< 0.001, 95% CI = [0.64, 1.18])。对女性的能力评价无法预测交往意愿(= 0.11,= 0.15;(60) = 0.73,> 0.05, 95% CI = [−0.20, 0.42])。热情在性别化名字对女性交友意向的预测模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间接效应 = 0.44, 95% CI = [0.16, 0.71]; 直接效应 = 0.34, 95% CI = [−0.04, 0.72])。

图3 名字性别化对女性人物交友意向的中介模型图
4.2 研究3b:任务情境下性别化名字和性别对人际交往的影响
4.2.1 目的
在任务情境下考察性别化名字对人际交往的影响, 并探究印象评价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4.2.2 方法
(1)被试
线上招募大学生144人。13名被试未通过操纵性检验被剔除, 最终有效被试131名(男52人, 女79人, 平均年龄21.95岁,= 2.41岁)。按照名字主人性别将问卷分为两组。被试随机填答一个版本的问卷, 其中67人作答第一组问卷(男生27人, 女生40人), 64人作答第二组问卷(男生25人, 女生39人)。所有被试均自愿参与实验, 通过操纵性检验的被试获得一定的实验报酬。
(2)实验设计与程序
实验设计与流程同实验3a。不同之处在于情境指导语。实验3b的任务情境指导语:您参加了一个知识竞赛, 其中一个环节要求两人组队完成一项困难任务。赛制组为您随机安排了两位参赛选手, 您可以看到选手的名字和性别信息。接着, 被试需根据选手的名字和性别信息, 在热情和能力特质词上对两位选手进行1~7分评价, 之后在百分制量表上分别评价与两位选手的搭档意向。名字的选择同实验3a。实验3b热情与能力测量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78和0.72。5个男性化名字热情和能力评分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69和0.75, 5个女性化名字热情和能力评分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7和0.72。
4.2.3 结果
(1)任务情境下性别化名字对评价的影响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 性别化名字和名字主人性别的交互效应显著,(1, 127) = 4.97,< 0.05, 偏η= 0.04; 性别化名字和评价维度的交互效应显著,(1, 127) = 41.22,< 0.001, 偏η= 0.25; 评价维度主效应显著,(1, 127) = 22.07,< 0.001, 偏η= 0.15, 被试对性别化名字主人的能力评价(= 5.04,= 0.68)高于热情(= 4.86,= 0.70)。其他主效应、交互效应均不显著。
性别化名字和人物性别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对女性人物的评价在名字上存在差异,(1, 129) = 7.14,< 0.01; 对女性化名字人物的评价存在性别差异,(1, 129) = 12.73,< 0.001。性别化名字和评价维度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两类名字在热情维度上的评价差异显著,(1, 130) = 30.23,< 0.001; 两类名字在能力维度上的评价差异显著,(1, 130) = 6.95,< 0.01。
分别比较名字对男性和女性名字主人的热情和能力评价的差异。对男性名字主人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 评价维度的主效应显著,(1, 65) = 13.97,< 0.001, 偏η= 0.18; 性别化名字和评价维度的交互效应显著,(1, 65) = 11.83,< 0.001, 偏η= 0.15。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男性的热情评价在名字上存在差异,(1, 66) = 4.43,< 0.05; 男性的能力评价在名字上存在差异,(1, 66) = 5.22,< 0.05。对女性名字主人的分析发现, 名字主效应显著,(1, 62) = 6.62,< 0.05, 偏η= 0.10; 评价维度主效应显著,(1, 62)=8.81,< 0.01, η= 0.12; 性别化名字和评价维度的交互效应显著,(1, 62) = 31.67,< 0.001, 偏η= 0.34。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在热情维度, 被试对不同名字的女性评价存在显著差异,(1, 63) = 33.44,< 0.001。
对名字与名字主人性别一致、不一致条件下个体的热情与能力评价的独立样本检验发现, 在名字和性别一致条件下, 被试对男性化名字男性的热情评价低于女性化名字的女性,(129) = −5.53,< 0.001,= −0.97; 而在性别化名字和名字主人性别不一致条件, 被试对女性化名字的男性的能力评价显著低于男性化名字的女性,(129) = −3.79,< 0.001,= −0.67; 被试对女性化名字的男性的热情评价略高于男性化名字的女性,(129) = 1.92,= 0.057。
(2)性别化名字对搭档选择的影响及中介效应检验
以不同名字人物的选择结果为被试内变量, 名字主人性别和被试性别作为被试间变量,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 性别化名字主效应显著,(1, 127) = 15.78,< 0.001, 偏η= 0.11, 被试对男性化名字主人的搭档意向(= 58.18,= 22.49)高于女性化名字主人(= 41.82,= 22.49)。名字和人物性别的交互效应不显著,(1, 127) = 1.73,= 0.22。性别化名字和被试性别交互效应显著,(1, 127) = 4.82,< 0.05, 偏η= 0.04, 二者的简单效应不显著。
使用SPSS的MEMORE插件, 建立特质评价在名字和搭档选择之间的中介模型。尽管任务情境中名字和人物性别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说明男性化名字对于男性和女性搭档选择的影响可能是相同的, 但为了检验假设3(能力维度在性别化名字和男性搭档选择间的中介作用), 将分别建立男性、女性搭档选择的中介模型:
纳入评价维度、名字性别化和对女性搭档意向评分后的回归方程显著(= 0.52,(4, 59) = 15.88,< 0.001), 男性化名字的女性比女性化名字的女性得到更低的热情评价(= −0.35,= 0.16;(63) = −2.11,< 0.05, 95% CI = [−0.68, −0.02]); 而不同名字女性的能力评价差异不显著(= −0.10,= 0.17;(63) = −0.59,= 0.55, 95% CI = [−0.44, 0.24])。对女性的能力评价能够正向预测搭档意愿(= 1.03,= 0.15;(59) = 7.08,< 0.001, 95% CI = [0.74, 1.32]), 而对女性的热情评价无法预测搭档意愿(= 0.23,= 0.15;(59) = 1.52,= 0.13, 95% CI = [−0.07, 0.54])。评价维度在名字到女性搭档选择意向的中介模型不成立。
纳入评价维度、名字性别化和对男性搭档意向评分后的回归方程显著(= 0.50,(4, 62) =15.78,< 0.001; 见图4), 男性化名字的男性比女性化名字的男性得到更低的热情评价(= −0.29,= 0.14;(66) = −2.11,< 0.05, 95% CI = [−0.56, −0.01]); 男性化名字的男性比女性化名字的男性得到更高的能力评价(= 0.39,= 0.17;(66) = 2.28,< 0.05, 95% CI = [0.05, 0.73])。对男性的热情评价无法预测搭档意愿(= −0.03,= 0.15;(62) = −0.22,=0.82, 95% CI = [−0.33, 0.27]), 对男性的能力评价正向预测搭档意愿(= 0.77,= 0.13;(62) = 6.13,< 0.001, 95% CI = [0.52, 1.03])。能力在性别化名字对男性搭档意向的预测模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间接效应 = 0.30, 95% CI = [0.04, 0.60]; 直接效应 = −0.08, 95% CI = [−0.43, 0.28])。

图4 名字性别化对男性人物合作意向的中介模型
4.4 讨论
研究3对性别化名字的热情能力感知特点, 以及名字对不同性别个体的印象评价进行了检验, 结果与研究1、2的发现吻合。根据研究3b, 名字不仅影响男性的能力感知和女性的热情感知, 还会影响男性的热情评价。这是名字印象评价研究中的首次发现。从现实影响上看, 虽然热情、友善是积极的特质, 但在研究3b这一任务情境中, 评价者更关注潜在搭档的能力特质。尽管人们认为女性化名字的男性比男性化名字的男性更富热情, 然而因为前者被感知为能力不足, 最终影响人们与之搭档的意愿。
人们更愿意与女性化名字的女性成为朋友, 热情评价在名字和交友结果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人们倾向于和男性化名字的男性组队完成任务, 能力评价完全中介了名字对搭档选择的影响。该结果表明, 人们对名字和性别一致个体的偏好具有情境特异性。结合人际交往中特质和情境的匹配关系, 在交友情境, 人们注重交往对象的热情特质, 认为女性化名字的女性比男性化名字的女性更为热情, 是合适的交往对象; 在任务情境, 人们更关注交往对象的能力特质, 认为男性化名字的男性比女性化名字的男性更有能力, 是合作的良好人选。
5 总讨论
从性别化名字的热情和能力感知入手, 本研究从性别刻板印象维护视角探讨了名字和性别影响个体评价的模式, 首次从评价者动机的角度考察了名字对人际交往的影响及心理机制, 为名字的社会心理认知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支持。研究在发现了男性化名字被感知为高能力、低热情, 女性化名字被感知为高热情、低能力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现性别化名字影响名字主人“本应具有”的特质评价, 而且名字主人给人留下的印象和评价者动机能共同影响个体的人际交往。
5.1 名字热情能力知觉的稳定性
研究发现人们对男性化名字的能力评价高于女性化名字, 对女性化名字的热情评价高于男性化名字, 与西方研究结果一致(Nett et al., 2020; Newman et al., 2018)。这说明人们对名字这一社会符号的知觉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此外, 相较于女性化名字的个体, 男性化名字的个体被认为高能力低热情; 女性化名字的个体比男性化名字个体被认为高热情低能力。这些结果表明性别化名字对个体知觉的影响非常稳定。名字能够激活性别刻板印象(韩燕等, 2008; Karniol et al., 2016), 影响人们对性别化名字的热情与能力感知。上述结果印证了名字作为一种身份标识对社会知觉的重要影响。
5.2 名字影响个体“本应具有”的特质评价
本研究发现, 使用相反性别化名字的个体会被认为缺乏“应有”的性别特质。对于使用相反性别化名字的个体, 名字传递的特质违反了人们对名字主人的性别预期。而对于缺乏“应有”性别特质的个体, 人们会在其对应的刻板印象维度给出较低的评价(Hansen et al., 2017; Vaidis & Bran, 2018), 从而维护刻板印象。也正因为此, 使用相反性别化名字的个体给人留下比较消极的印象。本研究中不同性别人物的名字和评价维度交互作用的效应量在0.1~0.25之间, 属于低效应量, 原因在于被试做出评价时参考的线索非常有限, 并且人们往往抱以谨慎的态度来评价他人。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会整合多种线索评价他人, 名字在评价中的作用可能会被其他线索冲淡。不过, 本研究通过考察名字影响印象评价的可能模式, 揭示出人际知觉中名字的作用机制, 丰富了名字人际知觉的理论。
5.3 名字改变个体的刻板化评价
名字通过影响个体“本应具有”的特质评价, 能够改变个体的刻板化评价。具体而言, 男性化名字的女性比女性化名字的男性被感知为更有能力; 在研究3中, 女性化名字的男性比男性化名字的女性被感知为更富热情。总的来看, 男性化名字对女性能力评价的影响非常稳定, 且使用相反性别化名字的女性和男性个体在能力评价上差异的效应量均高于0.5。事实上, 如果将名字与性别一致者的评价视作一般意义上的性别刻板印象, 可以发现被试对女性的能力评价不低于男性。伴随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 人们的性别观念已然发生变化。Eagly及其同事(2020)的研究发现, 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的能力感知不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的结果也揭示出人们对女性能力感知的变化。
研究3b发现人们认为女性化名字的男性比男性化名字的男性更热情, 其原因可能和中国的文化环境有关。西方文化偏“男性化”, 人们对男性的热情等社会性特质并未抱有太大期许(Bosak, Kulich et al., 2018; Croft et al., 2015)。而东方属于“女性化”文化, 温润如玉的君子形象蕴含了中国文化“刚柔相济”的思想理念。名字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 具有维持和传递社会观念的功能。女性化名字中蕴含的友好、亲和等特质, 同人们对东方男性“宽厚仁爱”的期许相符合, 名字主人会受到名字的影响被感知为具有高热情的特质。
5.4 人−名匹配效应的情境特异性
从评价者动机的角度出发, 本研究首次发现了人−名匹配效应存在情境特异性, 即在特定情境下, 被试对人−名匹配个体的偏好在某一性别上有所凸显。名字影响男性和女性个体“应有”的特质感知, 而受到动机的驱使, 人们在不同情境下选择交往对象时所关注的特质也不尽相同(Spence, 1985), 这种特质与情境间的匹配关系, 影响特定情境下人们对某一性别人物的偏好。综上, 性别化名字对人际交往的影响, 不仅受制于名字主人性别和名字的匹配关系, 还会受到评价者动机的影响。本研究结合情境和特质的匹配关系, 从评价者和评价对象两个方面考察名字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 拓展了名字的社会知觉研究。
研究发现, 相较于女性化名字的女性, 人们在任务情境中更青睐男性化名字的女性, 印证了男性化名字助力女性职业发展的结论(Coffey & Mclaughlin, 2016; 郭凤等, 2020)。但值得注意的是, 性别化名字不影响对女性的能力感知, 女性的能力特质在性别化名字和搭档选择结果之间的中介路径并不成立。此外, 被试能够准确判断名字主人的性别, 这就排除了被试将男性化名字的女性误认为男性进而做出选择的可能。或许在竞赛这一任务导向情境下, 存在能力以外的因素影响人们对男性化名字女性的偏好。另外, 研究并未发现女性化名字能够帮助男性获得友谊, 也就是说, 使用相反性别化名字的个体能否从名字中获益取决于性别。有研究表明拥有异性名字的个体使人感到惊奇、怪异(Pilcher, 2016)。或许使用相反性别化名字的男性给人带来的并非是“刚柔相济”的和谐感, 而是一种“不阴不阳”的失调感。后续研究可以将情绪与认知相结合来考察名字对人际互动的影响。
5.5 本研究的应用启示
中国的姓名文化历史悠久, 姓名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本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应用启示。个体自出生以来被赋予的名字对社会知觉具有重要影响, 应该正确认识名字的功能, 避免因名字而对他人形成先入之见, 妨碍人际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 名字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印象管理工具。在一些功能性团体和组织中, 允许人们使用非实名(昵称或小名)以更好地实现互动目标, 人们可以根据互动目标给自己取一个合适的假名, 助力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此外, 本研究通过考察人们对不同性别化名字主人的评价, 揭示出当代中国社会性别观念的转变, 名字能够为研究社会变迁背景下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规律提供一种有效的工具。
5.6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结合刻板印象内容维度, 为名字热情能力知觉的稳定性和跨文化一致性提供有力证据, 提出了名字影响个体印象评价的可能模式, 并从评价者动机的角度探索了名字影响人际交往的内部机制。但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 值得未来进一步探索。首先, 中国存在大量男女通用的“中性化”名字, 中性化名字或许被感知为具有适度的热情和能力, 拥有中性化名字的个体可能给人留下“刚柔并济”的印象也因此更受欢迎, 未来可以考察对中性化名字主人的印象评价及影响(包寒吴霜等, 2016)。其次, 本研究考察了他人对名字主人印象评价的影响, 那么从名字主人本身具有的特质来看, 持有不同性别化名字的个体是否在热情与能力维度上存在差异?未来有必要探讨名字影响印象评价的准确性。再者, 线上交友已成为当今人际交往的重要形式, 人们希望通过网名给他人留下好印象(Whitty & Buchanan, 2010)。今后可探讨网名或昵称的性别化感知对印象评价的影响。
6 结论
(1)人们对男性化名字的能力评价高于女性化名字, 对女性化名字的热情评价高于男性化名字。
(2)性别化名字影响个体“应有”的特质评价, 名字与性别不一致的女性和男性分别给人以“低热情”和“低能力”的印象。
(3)性别化名字通过改变对女性的热情评价进而影响人们与女性的交友意愿, 通过改变对男性的能力评价进而影响人们与男性的共事意向。
Abele, A. E., & Wojciszke, B. (2007). Agency and commun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f versus others.(5), 751–763.
Bao, H. W. S., Chen, J. L., Lin, J. L., & Li, L. (2016). Effects of name and gender on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Gender role evaluation as a mediator.(4), 596–600.
[包寒吴霜, 陈俊霖, 林俊利, 刘力. (2016). 名字与性别的人际吸引机制:性别角色评价的中介作用.(4), 596–600.]
Benson, A. J., Azizi, E., Evans, M. B., Eys, M. A., & Bray, S. R. (2019). How innuendo shapes impressions of task and intimacy groups.,, 1038–1054.
Bosak, J., Eagly, A. H., Diekman, A. B., & Sczesny, S. (2018). Women and men of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Evidence of dynamic gender stereotypes in Ghana.(1), 115–129.
Bosak, J., Kulich, C., Rudman, L., & Kinahan, M. (2018). Be an advocate for others, unless you are a man: Backlash against gender-atypical male job candidates.,(1), 156–165.
Carrier, A., Dompnier, B., & Yzerbyt, V. (2019). Of nice and mean: The personal relevance of others’ competence drives perceptions of warmth.(11), 1549–1562.
Clough, P. D., Bates, J., & Otterbacher, J. (2017). Competent men and warm women: Gender stereotypes and backlash in image search results., 6620–6631.
Coffey, B., & Mclaughlin, P. A. (2009). Do masculine names help female lawyers become judges? Evidence from south carolina.(1), 112–133.
Coffey, B., & Mclaughlin, P. A. (2016). The effect on lawyers income of gender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first names.(1), 57–76.
Cotton, J. L., O'neill, B. S., & Griffin, A. (2008). The “name game”: Affective and hiring reactions to first names.,(1), 18–39.
Croft, A., Schmader, T., & Block, K. (2015). An underexamined inequality: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barriers to men’s engagement with communal roles.,(4), 343–370.
Deaux, K., & Major, B. (1987). Putting gender into context: An interactive model of gender-related behavior.,(3), 369–389.
Duffy, J. C., & Ridinger, B. (1981). Stereotyped connotations of masculine and feminine names.(1), 25–33.
Eagly, A. H. (1987)..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Eagly, A. H., Nater, C., Miller, D. I., Kaufmann, M., & Sczesny, S. (2020). Gender stereotypes have changed: 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of U.S. public opinion polls from 1946 to 2018.(3), 301–315.
Ellemers, N. (2018). Gender stereotypes.(1), 275–298.
Etaugh, C., & Geraghty, C. (2018). Both gender and cohort affect perceptions of forenames, but are 25-year-old standards still valid?(11-12), 726–737.
Fiske, S. T. (2018). Stereotype content: Warmth and competence endure.(2), 67–73.
Fiske, S. T., Cuddy, A. J. C., Glick, P., & Xu, J. (2002). A model of (often mixed) stereotype content: Competence and warmth respectively follow from perceived status and competition.(6), 878–902.
Fox, E, Russo, R, & Dutton, K. (2002). Attentional bias for threat: Evidence for delayed disengagement from emotional faces.(3), 355–379.
Glick, P., & Fiske, S. T. (2011). Ambivalent sexism revisited.,(3), 530–535.
Guo, F., Ren, X. P., & Su, H. (2020). The impact of gender orientation of names on the female applicants' interview opportunity.(5), 46–58.
[郭凤, 任孝鹏, 苏红. (2020). 不同性别定向的名字对女性获得面试机会的影响.(5), 46–58.]
Han, Y., Qiu, J., & Zhang, Q. L. (2008). Conflict effect of gender-stereotypical names and pronouns.(10), 164–168.
[韩燕, 邱江, 张庆林. (2008). 性别刻板化人名推测判断中的冲突效应.(10), 164–168.]
Hansen, K., Rakić, T., & Steffens, M. C. (2017). Competent and warm?(1), 27–36.
Karniol, R., Artzi, S., & Ludmer, M. (2016). Children’s production of subject-verb agreement in Hebrew when gender and context are ambiguous.,(6), 1515–1532.
Kervyn, N., Bergsieker, H. B., & Fiske, S. T. (2012). The innuendo effect: Hearing the positive but inferring the negative.,(1), 77–85.
Li, Z. X., Zhao, K. B., & Pan, W. J. (2017). The first survey to folk imagination of emperor face in Confucianism.(3), 547–552.
[李朝旭, 赵凯宾, 潘文静. (2017). 基于儒家文化的“帝王相”之民间意象的首次探索.(3), 547–552.]
Lindsay, J. M., & Dempsey, D. (2017). First names and social distinction: Middle-class naming practices in Australia.(3), 577–591.
Liu, X., & Zuo, B. (2006).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maintaining gender stereotypes.(03), 456–461.
[刘晅, 佐斌. (2006). 性别刻板印象维护的心理机制.,(03), 456–461.]
Mccroskey, J. C., & Mccain, T. A. (1974).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3), 261–266.
Mehrabian, A. (2001). Characteristics attributed to individuals on the basis of their first names.,(1), 59–88.
Montoya, A. K., & Hayes, A. F. (2017). Two-condition within-participant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alysis: A path-analytic framework.(1), 6–27.
Moss‐Racusin, C. A., & Johnson, E. R. (2016). Backlash against male elementary educators.(7), 379–393.
Nett, T., Dorrough, A., Jekel, M., & Glöckner, A. (2020). Perceived biological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a representative set of German first names.(1), 17–34.
Newman, L. S., Tan, M., Caldwell, T. L., Duff, K. J., & Winer, E. S. (2018). Name norms: A guide to casting your next experiment.(10), 1435–1448.
Pilcher, J. (2016). Names, bodies and identities.,(4), 764–779.
Prentice, D. A., & Carranza, E. (2002). What women and men should be, shouldn't be, are allowed to be, and don't have to be: The contents of prescriptive gender stereotypes.,(4), 269–281.
Rudman, L. A., Moss-Racusin, C. A., Phelan, J. E., & Nauts, S. (2012). Status incongruity and backlash effects: Defending the gender hierarchy motivates prejudice against female leaders(1), 165–179.
Smith, F. I., Tabak, F., Showail, S., Parks, J. M., & Kleist, J. S. (2005). The name game: Employability evaluations of prototypical applicants with stereotypical feminine and masculine first names.,(1), 63–82.
Spence, J. T., & Sawin, L. L. (1985). Images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A reconceptualization. In V. E. O'Leary, R. K. Unger, & B. S. Wallston (Eds.),(pp. 35–66). Hillsdale, NJ: Erlbaum.
Su, H., & Ren, X. P. (2015).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first names: Individual level and group level evidence.,(5), 879–887.
[苏红, 任孝鹏. (2015). 名字的心理效应:来自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的证据.(5), 879–887.]
Vaidis, D., & Bran, A. (2018). Some prior considerations about dissonance to understand its reduction: Comment on McGrath (2017).(9). doi: 10.1111/spc3.12411.
Wang, D. F., & Cui, H. (2007).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ex role scale and relations between sex role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1–9.
[王登峰, 崔红. (2007). 中国人性别角色量表的建构及其与心理社会适应的关系., 1–9.]
Wang, Y., & Wen, Z. L. (2018). The analyses of mediation effects based on two-condition within-participant design.(5), 1233–1239.
[王阳, 温忠麟. (2018). 基于两水平被试内设计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5), 1233–1239.]
Wen, F. F., & Zuo, B. (2012). The effects of transformed gender facial features on face prefer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the test of computer graphics and eye movement tracks.(1), 14–29.
[温芳芳, 佐斌. (2012). 男性化与女性化对面孔偏好的影响——基于图像处理技术和眼动的检验.(1), 14–29.]
Wojciszke, B., Bazinska, R., & Jaworski, M. (1998). On the dominance of moral categories in impression formation.,(12), 1251–1263.
Xin, Z. Y., Du, X. P., & Sha, L. (2015). The influence of trustees’ name recognizability on their trustworthiness.(6), 1438–1444.
[辛志勇, 杜晓鹏, 沙璐. (2015). 名字易识认性对被信任者的可信性的影响.(6), 1438–1444.]
Yang, T., & Ren, X. P. (2016). The impact of gender orientation of names on female mate preferences.(5), 1190–1196.
[杨婷, 任孝鹏. (2016). 不同性别定向的名字对女性择偶偏好的影响.(5), 1190–1196.]
Zhang, J. J., Liu, H.Y., & Ye, Q. Y. (2006). The influence of names on perceptions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2), 127–134.
[张积家, 刘红艳, 叶倩仪. (2006). 名字对个体吸引力的影响.(2), 127–134.]
Zuo, B., Dai, T. T., Wen, F. F., & Suo Y. X. (2015). The big two model in social cognition.(4), 1019–1023.
[佐斌, 代涛涛, 温芳芳, 索玉贤. (2015). 社会认知内容的“大二”模型.(4), 1019–1023.]
Zuo, B., Dai, T. T., Wen, F. F., & Teng T. T. (20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rmth and competence in social cognition.(9), 1467–1474.
[佐斌, 代涛涛, 温芳芳, 滕婷婷. (2014). 热情与能力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9), 1467–1474.]
The impact of gender orientation of names on individuals’ evaluation of impressions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ZUO Bin, LIU Chen, WEN Fangfang, TAN Xiao, XIE Zhijie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Ministry of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People can infer personal traits from names and, thus, the impressions of an individual can be influenced by how others perceive his or her name. Previou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people have a distinctive perception of masculine and feminine names. This raises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How do people evaluate individuals with opposite gender-oriented names, and how will this evaluation affect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based on the main two dimensions of social cognition (i.e., warmth and competence).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e first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perception of warmth and competence of names withi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examine the effects of an individual’s gender and name-gender orientation on impression formation. The second aim was to explore the behavioral aftereffects of evaluation of impressions based on individual’s names.
Four studies were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questions. In Study 1, a total of 100 masculine and feminine names were presented to 176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ho were asked to rate these names according to four traits: two traits for each dimension of warmth and competence. In Study 2, 121 undergraduate participants were presented with information about target genders and names.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rate these targets based on warmth and competence. In Study 3a, 136 undergraduate participants were presented with two targets that had masculine or feminine nam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imagining going on a trip with them. Furthermore, in Study 3b, 131 undergraduat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imagine that they would meet two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nam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finishing a difficult task. Participants in Study 3a and Study 3b were then asked to evaluate these individuals based on their warmth and competence traits and choose one of them as their partner to complete the corresponding activitie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Feminine names were rated higher on warmth than masculine names, and masculine names were rated higher on competence than feminine names; (2) Individuals with gender-consistent names were considered to have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gender: women with feminine names were perceived as warmer than women with masculine names, and men with masculine names were perceived more competent than men with feminine names; (3) Individuals with gender-inconsistent names were considered to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pposite sex: men with feminine names were perceived less competent than women with masculine names, whereas women with masculine names were perceived less warm than men with feminine names; (4) Participants intended to make friends with women whose name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ir gender, and the perception of warmth completely mediated the effect of name-gender orientation on willingness to interact; and 5) Participants preferred to finish difficult tasks with men whose name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ir gender, and the perception of competence completely mediated the effect of name gender orientation on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to explore how gender and name gender orientation affect individuals’ impressions by applying stereotype content in China. We examined the influence of name gender orientation on individuals’ perceptions about others, as well as their behavior intention and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rceiver’s motiv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and empirical support for impression evaluation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based on names, and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he social cognition of names. Further studies should explore the content of gender-ambiguous names and their effects on individuals’ impressions and behavioral aftereffects. The effects of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on names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should also be assessed.
gender orientation of names, impression evaluation, warmth, competenc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2020-05-25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331)和华中师范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CCNU19ZN021)资助。
温芳芳, E-mail: wenff@mail.ccnu.edu.cn
B849: C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