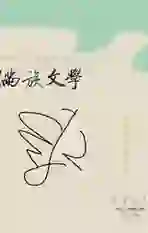谁在静坐喜床
2021-04-12孙惠芬
孙惠芬
朋友打来电话,约写一篇“回顾处女作”的随笔,我当即答应。虽然那是时间银行里储蓄久远的存单,但关于这张存单的存款日期、存款来源、以及存款形式,永远都不会忘记。可想不到的是,真正动笔,却遇到了困难,原因似乎很简单:“回顾”的路口,朝向的是深远的过去,而我,不喜欢怀旧,当逝去的一切蓄意风起云涌,钩沉起曾经的伤痛,情感的通道,瞬间就竖起了墙壁。
为了践行诺言,用了近半个月时间,我推倒了障碍,让自己顺“回顾”的路口,向三十八年前走去——那是处女作发表的时间,1982年;向比三十八年前又早了四年那个上午走去——那是处女作写作的时间,1978年。那是一个秋天的上午,十八岁的我坐在一辆陪嫁的马车上,从一个叫山咀子的村庄出发,朝着一个叫青堆子的小镇驶去。我十七岁辍学,在大田里干了近一年农活,最盼望的事情就是谁结婚找我陪嫁,那样的一天,可以不干活,可以穿上漂亮衣服,可以像在舞台上一样被人们围观。可因为刚刚下学,又性格内向,与年龄稍大一点有可能结婚的女子攀不上朋友,这一天一直没有到来。终于得到机会,是两年以后,堂姐结婚,沾了亲戚的光。那是怎样的上午,有过怎样的心绪,如今全然记不得了,不忘的是,午后回来,下午上班的哨声还没吹响——山咀子离青堆子只有十里路,太近了!这意味着,我需要脱下漂亮衣服(那不过是一套蓝色学生制服)下大田干活。我自然没去干活,我让逍遥的时光在写字台前拉长(那也不是什么写字台,一张带抽屉的桌子),我用一个下午时间,写了一篇题为《新嫁娘》的日记。
这篇日记尘封在笔记本中间的地方,它的前一篇是《希望》,后一篇是什么我忘了。我的日记都有题目,不但有题目,还要有插图,还要有版式设计——后来知道,这是我为自己创办的一份杂志,用以发表我的心绪——后来知道,日记里记录的不仅仅是我的心绪,更是我在某种心绪作用下创作的作品,因为在那里,往往写的是别人的心绪。《新嫁娘》就写了一个生长于乡村的女子,结婚这天坐在喜床上,看着小镇上的新夫和婆婆,决心做一个贤妻孝媳的情绪波动。
就这样,它和所有日记一样,被尘封在了厚厚的蓝皮横格笔记本里。那时候,并不知道它会有什么价值,只是为了倾诉,日记本,可以说是我心灵的垃圾筒。只不过,这个垃圾筒没有垃圾气味,可以翻阅;每每翻阅,还会感受到某种生机,那种逝去的一切重又复活的生机,那种心灵的历史得以鲜活的生机。而这生机里,时常闪烁一星火花,像在草丛里划着了火柴,你心底里某些不可名状的东西被噼里啪啦点燃,它们虽然无比短暂,几乎是稍纵即逝,但它们让你压抑、痛苦、不堪疲惫的青春荒野,闪现出一丝神秘的希望。
那不可名状的东西,自然是文学,是艺术,是被我记录在案的现实里蕴藏着的审美意趣,它们构成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生活的全部希望。它们是希望,我却并不自知,这正是它的神秘所在——我從未觉得自己会做一辈子农民,但我并不知道出路就在日记尘封的心灵历史里。
神秘的事情,发生在1979年,那一年十月,公社召开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就是如今的劳模会,小队队长让我代表我的和睦大家庭去公社“讲用”。队长并不知道我有写日记的训练,出于什么原因把任务交给我,并不清楚。我写了十页稿纸,把对母亲如何处理十八口人大家庭复杂关系的观察条分缕析。“讲用”结束,一个男生冲到我面前,他说你讲得太好了,你有当作家的天赋。他说县文化馆最近有一个文学班,我把你报上去。
当作家的天赋,我当然有啦,我在小学升初中时就写过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可我没有说出来,只是激动得浑身打颤。
后来知道,这个男生,是公社文化站站长,二十几岁的样子。后来知道,参加学习班,必须带作品。我因为没有作品,只能带去日记。
尘封在日记里的心灵,就在这样的时刻得以打开,它们曾是我隐秘的心事,现在却要公布于光天化日;它们是我倾诉的废墟,却被冠以散文或小说的名义,吸引了文化馆的老师,让他们纷纷伸出帮教之手,帮我修改并投稿,第二年五月,日记里曾低眉顺眼的《新嫁娘》,便理直气壮地《静坐喜床》了!骨子里,这位新嫁娘仍然低眉顺眼,但她一旦登上了大连《海燕》杂志,换成了《静坐喜床》的题目,便拥有了登堂入室的做派了。
实际上,同是这个月份,我的日记《希望》,也在河北《无名文学》杂志发表,但因为它没有《静坐喜床》那么隆重(《海燕》同期配发了评论),也就和杂志的名字一样,在后来的时光,永远寂寂无名了,许多时候,连我自己都不承认它才是我文学银行里的第一张存单——在日记里,它可是排在《新嫁娘》前边。
一位作家说过:逝去的一切,总被后来的人们视为如今一切的源泉。这也同样是我的心声。可是此刻,打量这张存单,我并不能读出它的全部密码。比如,那个十八岁的我,渴望陪嫁,在终于可以陪嫁的时光,对嫁到小镇的女子有了近距离接触,从而更深地体会了新嫁娘的感受,可是,我当真愿意新嫁娘只因为从农村嫁到小镇,就甘愿一辈子做贤妻孝媳?要知道,当时的我,在封建礼教严重的大家庭里长大,通过奶奶、母亲、三个嫂子,看到了太多做女人的压抑和痛苦,我当时深陷大田里的压抑和痛苦,包含着这所有女人的痛苦!可以说,在我对未来的期许里,从就没有做人妻媳的想法,我曾下决心绝不结婚!我的那篇《希望》的散文,写的就是这种希望,我希望去远方,希望远走高飞,希望远离结婚、生子、关系复杂的家庭!我为什么要让那个嫁到小镇的女子下一个和写作的我完全相反的决心?是我在真实的新嫁娘那里观察到了这一点?还是家庭教育潜移默化了我的价值取向?
如果是前者,那么就说明,我在写日记时,就已经拥有了作家的洞察和圣者的慈悲,能够全然放下自我去拥抱他人,我不认为当时的我有这样的能力;如果是后者,就证明我是一个懦弱无能又虚伪的家伙,暗地里,每时每刻都在抗争女性命运,而一旦诉诸文字,哪怕只在日记里,都不敢吐露心声,可我,也不觉得自己会懦弱虚伪到如此境地。要知道,我的大家庭外边,是一片一望无际的野地,从童年到少年,当我忍受不住家庭礼教的羁绊,动辄就带着侄子侄女在野地里疯跑时,曾无数次挨过母亲的打!虽然到了青春时代,野地变成牢笼,用劳累锁住了肢体,可正因为如此,那个能够在日记里逃离肢体的想象,才更应该信马由缰无拘无束……我是说,到底谁在静坐喜床?如果她既不是那个新嫁娘,又不是那个写作的我,那么,她究竟是谁?
实际上,十年之后,我真的和小镇男子结婚了——我不想结婚,但这个念头无法阻止恋爱,而只要恋爱,那扇传统的门就没办法不被打开。只是结婚那天,我坐的不是马车,而是130汽车,我也没有找陪嫁,坐在我旁边的,是自家侄女;而推开婆家的门,我也没有下那个做贤妻孝媳的决心,我是因为没考上北大作家班,才无望地答应结婚——无望,证明我还没有为结婚后面的事情做好任何准备……
实际上,当后来有了创作的自觉,可以用虚构和想象来建立一个世界,那世界里,走出了一系列这样的女人。她们不管如何在生活中挣扎、抗争,最后都归顺了女性的命运,而在这样的命运里,她们不是变得颓萎、懦弱、消沉,而是无声地强大,就像《歇马山庄》里的月月,《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李平,《秉德女人》里的秉德女人……
一晃四十年过去,翻开我的处女作,揣测这张存单的密码,猛然发现,它仿佛是在揭示我的宿命,曾决心坚决不结婚的我,不但做了贤妻,做了孝顺儿媳,还做了好母亲——虽然还谈不上良母。然而,正因为这一点,我似乎看到了存单密码更隐秘的部分,那就是:当那个写作者以审美而不仅仅是新嫁娘的视角看待生活,那个来自生活的巨大源流,如同从天而降的幕布,瞬间就上演了来自天地自然的生命消息,那消息关乎包容、忍耐、付出,关乎更广大世界的存在实相和逻辑;而写作的我,只要虔诚,凭直觉就能触摸到实相的一角,那便是:只有接受命运,包容、忍耐、付出,才能抵达内心的安详?
如果是这样,那是不是意味着,那个写作的我,青春年代渴望的远方,其实不是什么远方,仅仅是内心的安详,只不过那安详,藏在生命的直觉中,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而已呢?
如果是,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不知道,可广阔、无穷、复杂而深邃的生活知道,只要你站在她的源流,抱持一颗虔诚的心,她便会毫无保留地赐予你真相的启示呢?!
一直以来,都觉得《静坐喜床》是一篇要多单薄有多单薄的小说,此刻,却解读出更多的维度。难免,我在过分解讀,但既是过分,也是必然,因为每个年龄,都能看到过去年龄看不到的东西。此刻,当我看到过去的一切从未过去,它储蓄了现在、储蓄了未来,我想起里尔克那个著名的诗句,“过去的一切还在前头”。
过去的一切,是一笔储蓄,它不可变现,不可花取,可它一直都在宣示生活的本来面目。并且愈是将时间拉长,那面目便愈加清晰。
2020年12月6日于海南陵水
【责任编辑】大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