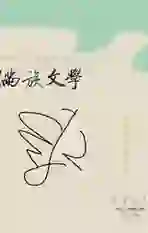声声呼唤
2021-04-12女真
在我们家,准确称呼老辈人,是一门艺术。
话说我姥爷不是光达、不是我爷,仅仅只是我姥爷的时候——这话乍听别扭、让人困惑,但没有毛病,我可不是酒喝高了说胡话。
且听我慢慢道来。
那一年,姥姥被确诊为白血病,我妈建议姥姥、姥爷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爸和我,都不反对。我跟姥姥、姥爷有感情。小时候,我妈经常出差远行,一走十天半个月。每次我妈出远门之前,会把已经退休的姥姥、姥爷请到我们家。姥姥做饭好吃,擅长面食,包子、饺子、烧卖、各种饼,我点什么她都会做;姥爷手巧,他做的大蜈蚣风筝带彩灯,放飞到天上亮闪闪,在北陵公园傍晚的风筝群里独一份,明显与那些花钱就能买到的金鱼、蜻蜓风筝不同,让我骄傲得不行。我当然欢迎他们过来长住。我爸也明确表示赞成,但我心里暗自寻思,他欢迎的程度肯定不如我。我觉得自私是人的本能——我爷身体还行,我奶体格软弱,作为儿子,按理说我爸也应该接他们过来跟我们同住,但既然姥姥生了大病,姥爷自己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我妈作为独生女儿又不可能辞掉工作专门回老家去照看他们,把姥姥、姥爷接到我们家,就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我爷、我奶,暂时还不能排在前面。
为了让姥姥、姥爷下决心,我爸妈把家里三好街电脑城旁边的那套两居室卖了,在当时房价相对便宜的北陵公园东门附近,沈阳体育学院没搬迁之前的老地方,买了一套带电梯的三居室,以最快速度装修完毕。考虑到姥姥的身体状况,我家装修极简,精心挑选了高档环保材料。
姥姥、姥爷,找不到理由不来了。
姥姥的最后岁月,我们都尽了孝。
两年后,姥姥归天。
再过半年,我姥爷却坚决要回老家自己生活,怎么也留不住。说是要回去侍弄花。姥爷家一楼小院,栽了木槿、百合、月季、芍药、凌霄,年年花开绚烂,他说院子里花开了没人欣赏、没人看,是罪过。我姥爷说他身体棒,生活自理没问题。他当了多年中学语文老师,后来还当过校长,学生多得数不清,远到世界各地,近到左邻右舍,有事情需要帮忙,随便打个电话,能招呼来一大帮。我妈说姥爷明显夸大了自己的影响力,但她也没办法留住他。有一种人,老了死犟死犟的。譬如我姥爷。
姥爷搬走一个月,我爷、我奶就来了。
我爷、我奶两个孩子。我爸还有个妹,也就是我姑。我姑念书比我爸厉害,她是学霸型的,考上清华,去美国留学后定居旧金山,嫁了一个当地码农,给我添了三个酷毕帅呆的混血金发表弟。我爷、我奶到旧金山去过三次,每次都因为我姑生孩子。奶奶听说外国女人生娃不坐月子,她怕我姑跟着学,她得到旧金山去亲自看着自己的闺女。我爷年轻时当兵,打过辽沈战役,跨过鸭绿江,真枪实弹打过仗,他不乐意我姑嫁当地人,不愿意去旧金山,但我奶不得不去,他不放心,只好跟着去当保镖。当我姑明确告诉我爷、我奶,她年纪大不准备再生了,把我爷乐坏了,一次喝了半斤茅台,从此不让我奶出国门:你闺女要是还惦记你,她应该经常回来看你!
我爷不乐意去美国。姑姑嫁的那个杰克,除了“你好”“好吃”,其他汉语不会。那三个小混血儿,汉语也都不灵。奶奶作为中学特级语文老师,在教混血外孙语言方面,最大的成就,是教会老大哈里、老二比尔一句玩笑话:姥爷爱放屁。我爷直性子,属于有屁就放那伙儿的,从身体到性格高度统一,从来就没学会掩饰,我奶跟他念叨好几十年,一直念叨到旧金山。哈里、比尔发现我奶一说“姥爷爱放屁”,他们的妈咪就呵呵笑,后来便开始竞相模仿,他们把这句话说得越顺溜,我奶就笑得越厉害,和我姑笑成一团,他俩越发起劲说,就把这句话练出来了。我爷耳听俩小外孙把讥讽他的一句粗话说得越来越顺溜,却打也不得、骂也不得,一点辙都没有。他不知道怎么用美国大兵的话教训俩小金毛。我爷说他到了美国,跟聋哑人没什么区别。他最高兴的时刻是抱着小不点托尼往天上扔,看眼睛瓦蓝的托尼一脸惊恐然后又咯咯傻乐。托尼还小,不会说话。中国话、美国话都不会。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却没办法说话交流,那还算一家人吗?
事实上,即使我姑想生第四个孩子,我奶也不会去看她了。我奶记性没了,明白时少,糊涂时多。到我家长住以后,她喊我梅梅。梅梅是我姑的名字,我奶拿孙女当闺女了。乱喊我名字只是她糊涂的症状之一。一开始我还跟她认真掰扯,告诉她我是妮子,不是梅梅。后来我干脆不提这茬儿,她喊什么我都答应。她要能把我也喊进清华、喊来个听话的老公、喊出几个可爱小倍比,也行!我不反对。
奶奶和爷爷年纪都大了,糊涂,记不清人和事,我猜这是我姥爷坚持离开的主要原因。姥爷虽然只有我妈一个闺女,但他骨子里很中国、很传统,还有那么一点儿重男輕女。他闺女还有年迈的公婆呢,为闺女考虑,他得走。他不能影响我爸、他女婿当孝顺儿子。
我爷、我奶,住进给姥姥、姥爷准备的那个大房间。房间朝南,有独立卫浴,光线好,还有一个封闭大阳台,赶上刮风下雨,在阳台上就能活动腿脚、晒太阳,很适合老年人。我妈请木匠在阳台用防腐木钉了花架子,摆了丽格海棠、非洲茉莉、大岩桐、长寿花、月季、米兰,一年四季都有花开,香喷喷,养眼睛。买房子的时候,除了价钱合适,这个带阳台的房间,也是我们家考虑的因素。
但那几年,很不幸,老天爷在我们家收人。
姥姥得白血病,把她和我姥爷攒了一辈子的家底,折腾差不多了,没治好。然后,我爷突然又没了。我爷在我们家住了不到一年,某天早晨起床,站着穿裤子时,让裤腿绊了一跤,突发脑溢血,送医院虽挺及时,那也没抢救过来。
我爸、我妈,他们俩好像商量好了,差不多同时长了白头发。我妈偶尔还把头发焗成棕色、烫出点型,我爸干脆就那么让头发花白,面皮却还没怎么沧桑,像影视剧组里的小鲜肉非得演老先生,妆没化好,看上去假,越瞅越别扭。
我刚懂事时,我爷就跟我讲过他年轻时候的事。我爷当兵前给有钱人家放猪。有一年夏天,他放猪时打了盹儿,猪淘气,把人家已经坐穗儿的苞米地祸害一大片。我爷清楚自己家穷,赔不起,我太爷性子又刚烈,为这事,能把他屁股打开花。刚巧村子里正过队伍,他没跟我太爷、太奶告别,自作主张跑去当兵,成了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兵,让我太爷、太奶成了光荣的军属。我爷当兵十年养成了好习惯,身板笔挺,走路姿式标准,八十多时,头发雪白,走街上还有回头率。虽然脾气大点儿,但他是个好心眼儿的帅老头儿。
我奶体格软弱。她比我爷年纪小,身体却比我爷差很多,我爷常挂嘴边一句话:毕竟是娇小姐。退休以后,我奶几次住医院大修。肺子发炎,心脏搭桥,骨股头换过。她怎么也不相信我爷比她先走。
爷爷走了以后,奶奶经常问我:梅梅,你爸呢?他怎么还不回来吃饭?
我知道她其实在说我爷。我不知道去哪儿把我爷喊回来吃饭。她这么说话,我心悲伤。
那段时间,照顾好我奶,是我家大事。我爸、我妈白天上班,非周末时间,我得住校,留我奶老太太一个人在家,全家人提心吊胆不放心。一點不夸张,她能把我们家放把火点着。我眼见着她把煤气开关拧开,没做任何点火动作,转身就去干别的。多悬哪!遇见明火,那就得爆炸!就是不爆炸,时间长了,人也得让煤气熏坏喽。所以,家里至少得请个钟点工。
你们都知道现如今找个合适的钟点工有多难。面对钟点工,我奶一点不像娇小姐出身,凡事爱自己动手,好像天生跟钟点工有仇,好不容易过了我妈那道关的钟点工,待不了俩礼拜都被她找各种理由打发了。所有的钟点工,她都嫌人家干活不利索。我爸、我妈,为踅摸合适的钟点工,白头发继续噌噌往外冒。他俩每天上班提心吊胆,只要能早回家,无论谁,都赶紧往家跑。
这种情况下,我姥爷偶然重来我家,简直就像天神下凡,把我爸、我妈喜坏了。
我姥爷、我奶,一对亲家公母,以前当然见过面,但次数不多。他们到我们家,差不多都是轮流来。即使偶尔撞车,也就是一起吃个饭,没有更多交流的机会。这次,不一样。
我姥爷这次来,有件特殊的事情。
他毕业的那所师范学院,历史悠久,据说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底子是一所教会学校。一位久居海外发了财的热心校友,赞助一笔钱,用于学院编撰口述校史。我姥爷是六十多年前从学院毕业、头脑清晰、还能写字的少数几个老学生之一。学院搬迁到沈北新校区,院方请他回来参观。本来安排他住学院宾馆,到家跟前了,我们哪能让姥爷住外面呢,直接接到家里。老话说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学院见我们把姥爷接回家住,人家巴不得,改成派人到我家来录音访谈。就这样,我家白天很热闹了。
姥爷这次来我家,我妈安排他住我房间。我平时住校,周末回家,住大房间陪我奶。我奶半夜经常起夜,给她开灯倒水,我力所能及。
哈哈,姥爷这次来,我又一次看出来,我奶是真糊涂了——她管我姥爷不叫亲家,而是一口一个光达。一开始我姥爷还纠正她,跟她说:亲家母,我是妮子姥爷!见我奶总不改口,跟我一样,索性我奶胡乱喊什么,他都答应了。
姥爷来了以后,我奶变化巨大。每天吃完早饭,她都把家居服换掉,认真穿上外出的体面新衣服。我奶的新衣服,多是我梅姑邮寄回来的,大红大绿、鲜亮花哨。我姑说:外国老太太年纪越大穿得越新鲜。我奶以前拒绝穿这种花哨的衣服,她说:不习惯、太扎眼,中国老太太哪有这么穿的?家里来了录音的年轻客人,她把这些花哨衣服都披挂上,屋子里一下子亮堂起来,像花朵盛开了在行走。我奶穿着鲜亮的衣服,跟我姥爷一起并排坐在客厅,听我姥爷跟人家讲他还记得的从前。我奶乖乖地听,一句话不多说,偶尔还能想起来给客人添茶水、削苹果。校报记者小田,每天一大早过来录音,中午请我姥爷去楼下的餐馆吃饭。怕我姥爷累着,他们下午不工作。我奶也跟着他们到外面去吃饭。她好像很高兴跟我姥爷一起下楼。自从我爷走了,动员我奶下一次楼费牛大的劲,我不知道姥爷用了什么招法,不但让她愿意跟着一起下馆子,还在饭后跟他一起去北陵公园散步、晒太阳。我奶走路超慢,我偶尔陪她一起走走停停,总感觉自己腿不好使,经常顺拐,接近崩溃,但我姥爷有耐心陪她倒碎步,过公园门口的红绿灯时还搀扶她,不知道的人,准以为他们是一对恩爱的老夫妻。北陵公园林子密、空气好,夏天进去,温度比外面低好几度,有的老头、老太太,备上点心、水,在北陵公园一待半天。我姥爷、我奶待不了那么久,他们总是一个小时以后就回家。我奶下午得眯上个把钟头,这个雷打不动。
我爸、我妈难得轻松。他们白天上班不用提心吊胆,晚上下班不用着急往家赶了。我姥爷身体好,睡完午觉,还能把晚饭煮上,和我奶一起把菜摘好、洗净,只等着我爸、我妈下班回家后煎炒烹炸。我周末回家,看见我爸、我妈,感觉他们年轻了,那时候我心里就想,我们家永远这样多好。
可惜呀,姥爷在我们家只待一个月,录音一结束,他又要走。我妈强留他又住了半个月,再留不住了,只能让我爸开车送他回去。
从此,我奶又开始不下楼,谁动员都没用。一天二十四小时穿睡衣。我妈早晨上班走时给她做好饭,放进保温筒,好几次晚上下班回家,发现留下的饭菜一点没动,家里别的吃食也没少。我奶一个白天一丁点儿食物没进肚。你问她:吃没吃饭?她信誓旦旦地说:吃了。你再问她:饿不?她回说:快饿昏了,有窝头没?
总这么下去不行啊。
把我妈、我爸愁的!
接着找钟点工吧。
得能找到合适的呀。
我开动脑筋,给我爸妈出主意:还是把姥爷请回来吧。
我爸、我妈,他们的表情,五彩缤纷。
我没问过他们怎么想的,但我能猜个大概齐。
我奶管我姥爷叫光达,我爸脸色难看,这我还能瞧不出来。我爷大名徐土根,一听就苦大仇深,穷人家出身。徐家祖上从山东蓬莱闯关东过来的,好几辈子没人读过书,不可能给下一代起个名字叫什么文绉绉的光达。我姥爷家上辈人给孩子起洋名。我姥爷大名宋约翰,从小念教会学校。说远了,还说我奶。我心里琢磨,我奶年轻时会不会有个相好的,也许是婚前好友,也许是多少年的梦中情人,那个人姓什么不知道,反正名字里有俩字:光达。我奶明白时把光达埋在心里,埋了一辈子,糊涂时没心眼儿了,不知道隐藏,不打自招全说出来了。我这样琢磨不是没根由的。我奶比我爷年轻得多,她跟我爷结婚时,我爷已经从部队转业地方有些年了,他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最可爱的人,根正苗红,虽然没有多高文化,年纪也偏大,政治上绝对可靠。我奶不行。我爷说她毕竟是娇小姐,那不是乱说的。我奶家以前是城市小业主,早年间在奉天城里四平街开酱园子的。四平街就是现在的中街,沈阳城里最繁华的地界之一,有历史——清朝留守奉天的王爷、贝勒,民国时的大帅、少帅,都经常在那一带活动。在老沈阳人的观念里,那一带,包括四平街南面的故宫,老城墙里面才是真正的城里。我奶从小生活在城里,念过书、有文化,要不然她能当教师吗?她嫁给我爷时已经二十八岁,这在她嫁人的那个年代,绝对算是晚婚。一个出身小康之家、念过书、有体面工作的漂亮姑娘,拖到二十八岁才嫁人,不会无缘无故吧?
不管我奶有过婚前好友还是梦中情人,我爸肯定心情复杂——我爷虽然已经作古,但我爸肯定想维护我爷的声誉;作为儿子,恐怕他也不希望自己的老妈古稀之年再曝出个情人吧?那样他在媳妇儿、在我这个闺女、在任何亲朋好友面前,都会觉得尴尬、没面子。
我妈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她在我面前从来不说婆婆的闲话。我妈不是一般战士——以后有机会我会单独说她。我妈城府深,在这一点上,我比她差远了。
想到我奶可能有过相好,我倒是不在意。自从我懂事,尤其上大學以后,我开始渐渐觉得,奶奶嫁给我爷其实挺委屈的。他们俩不般配,文化差距太大。除了吃喝拉撒,我觉着他们不会有什么共同语言。我奶果真曾经有个相好的,我甚至会替她高兴,说明她这辈子活得挺丰富的,哈哈。当然,这些想法我只会暗自动动心眼儿,我既不能去问我奶,她已经糊涂了,我趁她糊涂时套长辈的话,不厚道;我也不能去问我爸、我妈。我爸急眼扇我耳光不至于,他瞪几眼我也犯不上。我妈会保持沉默。我太了解他们了。
话说,我是这么给他们出主意的:干脆你们把我姥爷接回来吧。
我妈不吱声,她只是看了我爸一眼,然后我爸又看了她一眼。他们当我面没马上回应,但我知道他们会重视我的意见。他们当然不会当我面商量这么敏感的事情。
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式动员我姥爷回来的。
合理化建议得以落实,我享受结果就行了。
正像我设想的那样,自从姥爷再次回来,我奶重新开始换新衣服,又开始下楼去北陵公园散步。我为自己拥有聪明才智感到自豪。
我只是没想到,有一天,姥爷会正式成为我爷。
我爸、我妈去接我姥爷时,我在家陪伴我奶。陪伴一个老年痴呆、失忆的长辈人不容易。我奶真比小孩儿还难侍候。穿衣服得哄,吃饭得哄。小孩儿你可以硬穿、硬喂,老人不行。骨头都硬了、脆了,万一你不小心弄骨折了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姥爷很伟大,很了不起。他能让我奶乖乖地换上花衣服、按时吃饭、下楼溜达。这些事情我做不到,我爸妈也没做到。但其实细想,也不是我姥爷有多伟大,而是那个叫光达的人伟大。在我奶眼里,我姥爷就是光达。尽管这样,还得说姥爷也了不起——我奶喊他光达时,他好像一点不纠结,好像他从来不叫那个被批斗都没让他改变的宋约翰,他就是那个姓氏不详的光达。
而我对那个叫光达的人越来越感兴趣。张王李赵遍地刘,我把百家姓从前往后一个一个往光达前面安,试图找出点感觉,找出点线索。
我奶没事愿意翻老照片。我爸征得我姑梅梅同意,把老房子卖掉,连同家具、电器都处理了,只把老照片搬回来十好几摞。我琢磨着,她那些照相册里也许有那个叫光达的人。老年人的记忆真是奇葩,你问我奶中午吃没吃饭她记不得,但你问她照相册上的某张照片,她不但能说出那些发黄照片上不用放大镜已经看不出模样的小人儿是三姑奶还是四爷爷,而且经常连拍照片的时间、地点都还记得。她是选择性失忆、选择性记忆。老照片上大多是我奶家族的亲属,包括不少我奶年轻时的影像。四平街有照相馆,我奶家当年也算小康,照相对她来说应该不是难事。我奶的老照片,有穿布衣的小家碧玉学生装扮,也有时她穿着华丽的旗袍,贵家小姐一般倚在黑轿车旁边,是那个时代的香车美人照。我奶年轻时也是个时尚美人呢。照片是黑白的,摆拍,脸上的表情不自然、做作,但你能感觉出来相片上的人对照相这件事的重视。
我爷年轻时的照片只有两张,他穿军装,一眼就能认出来。
我在那些老照片中研究另外一些年轻的男人。我问我奶那些年轻的很有历史感的男人都是谁。他们有的穿中山装,有的穿西服,有的穿绸缎对襟衣裳。很遗憾,她没管任何一个照片上的人叫光达。
姥爷成为我爷——话说这是他被我爸、我妈请回来一年以后的事情,那时候我奶已经离不开人,或者说她不但白天离不开我姥爷,晚上也拉着我姥爷在身边陪伴她。有一天我半夜醒来上厕所,发现我奶和我姥爷的卧室门敞开着,房间里有灯光。卧室里有两张单人床,我奶躺在她自己的床上已经睡着,她现在睡觉手指头经常含在嘴里,像婴儿一样。我小时候,有含手指头的毛病,我奶为我纠正过好多回。现如今,她自己也变回小孩了哈。姥爷坐在我的旧书桌前,台灯开着,他在翻一本线装书。我知道他在看什么。姥爷研究《易经》。他研究这个有些年头了,在老家时,经常有人找他算卦。我真想问一问姥爷,他能凭着《易经》算出那个叫光达的人是谁不。想过不止一次,终于还是忍住了。
我奶和姥爷,他们到民政部门登过记。我爸、我妈陪他们一起去的。
从此,姥爷成为我爷。换个说法,也可以说姥爷仍旧是我的姥爷,然后我奶我也可以叫她姥姥。我爸既是他们的儿子,也是他们的女婿。我妈既是他们的闺女,也是他们的儿媳妇。我既是他们的孙女,也是他们的外孙女。哈哈哈哈……
我姑梅梅对姥爷和我奶这事居然非常赞成,她视频里跟我说:你知道英语里只要是爸妈的长辈,称呼都是一样的,就没有爷爷、姥爷之分,也没有奶奶、姥姥之分,你要跟在这边长大的咱家那几个小倍比说姑姥姥、姑奶奶、姨姥姥、姨奶奶,绝对能把他们绕腾迷糊!
我对她的感想深以为然,记得小时候看《红楼梦》,里面的人物关系就让我犯迷糊,但我又想,我们家复杂的关系,又不是简单的姥爷、爷爷之分——这里面可是还掺着一个光达呀!
一个除我奶以外我们谁都没见过、不认识的人,把我们家本来已经够复杂的关系,整得格外扑朔迷离。
我在照相册上没发现子丑寅卯,开始踅摸从姥爷那儿能不能有所突破。姥爷比我奶大四岁,他们都是念师范的出身,虽然念的不是同一所学校,毕竟,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也许,天天跟我奶在一起,姥爷会发现一点我奶的秘密?
我用各种方式企图套姥爷的话。我姥爷以他老年人的城府和狡狯,也许还有善良,每次都打马虎眼,装糊涂,不接我茬儿,让我不好意思再多问。成为我爷这件事,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他不但是一个手巧的人,一个教过书的人,研究《易经》几十年,还是一个真正富有牺牲精神的人——如果能让亲家母正常穿衣吃饭,他可以牺牲自己的名份。
是这样吧?
我奶现在基本上就管姥爷叫光达了。我姥爷,喊她关老师,而不是从前的亲家母。
我对光达却仍旧充满了好奇。生命不息,好奇不止。
一个重大发现是,不久前,我在准备博士论文、查阅民国时的旧报纸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叫闫光达的人——因为我奶,我对光达两个字格外敏感,这两个字就像我博士论文开篇写下的那几个关键词一样,多少次出现在我梦境中。闫光达比我奶大四岁,跟姥爷同庚,是奉天女子师范学校的青年教师,他当教师的那个时间段,我奶恰恰是奉天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闫光达能被我查到,因为他的名字上了当时的报纸。后来我又去档案馆查旧警署档案,发现他还出现在当时的官方通缉令上。但当我往后查找时,再没发现他的任何消息。这个当年的赤色嫌疑份子,最后不知所踪。他,会不会是我奶生命中的那个光达?
有一天,帮我奶洗澡搓背,我没忍住,趴她耳边,有点残酷地小声问她:闫光达是谁?
别有用心仔细观察我奶的反应——如果我的猜想、推测靠谱儿,我想,她会有一些反应。既然能想起来光达,能把光达挂在嘴上,如果我把完整名字说出来,她也应该有反应吧?
好吧,我得说,我很失望。我奶好像没听见我说话,聋子打岔,回我:后背搓干凈了吗?再帮我冲一冲。
听到她的回答,再看一眼岁月在她皮肤上雕刻出的苍老和松驰,我忽然开始自责:从此,也许,我真的不应该再去跟她纠缠光达是谁?作为已经度过人生最美好岁月的曾经年轻、如花的我奶奶,这个我生命源头之一的女人,她经历过战乱、政权更迭,经历过主义的纷争,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她的一生,一定不是我能够想象出来的那样简单。人生不易,如果她的生活中曾经有过一个男人至今还能让她有记忆、有感觉、活在心中,老年痴呆了也没能遗忘,那个男人,一定不是一般地让她心动,甚至可能支撑过她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生命中有过这样一个男人,我奶奶这一生,她就是幸福的。至于光达到底是谁,是真名还是化名,他信仰过什么,最后做了高官还是早已经命归黄泉或者做了别的女人的丈夫,其实跟我半毛关系都没有。他只跟我奶奶一个人有关。
岁月这条河按自己的节奏向未来流逝,不会给任何人留下情面。没有人能长生不老。虽然我奶奶从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学生、娇小姐变成了记忆模糊的沧桑老太太,但我其实还有那么一点羡慕她——我迄今为止的生活,仍旧没有一个像光达那样的男人能够让我铭记。
我愿岁月之刀最终能够在我的记忆中刻下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人。就像它曾经在我奶奶心头铭刻过。
【责任编辑】王雪茜
女 真
女真,本名张颖,中国作协会员。编审、一级作家。写作小说、散文、评论等多种文体,曾获中国图书奖、《小说选刊》年度优秀作品奖、辽宁文学奖等多种奖项。现居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