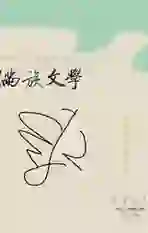眩晕
2021-04-12马金莲
班车有些年头了,行李舱挺脏的,上班车前于丽娜再三看看已经塞进几个箱子之间的行李包,确定它卡得比较紧,不会中途跌滚下来沾染一身泥土,里头的几瓶化妆品也应该不会打碎,她有些气恼地转身上车。刚才她本来要拎着包上车,被司机拦住了,说包大,车厢里挤,放下头行李舱里。于丽娜有点不情愿,她打算把包带到最后一排,等车出发上了高速以后,如果乘客不是满员,后排一般是有空座的,到时候她就可以枕着她的大包舒舒服服睡一觉了。长途累,加上她血压低,坐四个钟头的班车很受罪,她可能会晕车,只要一晕就会吐。没想到司机不允许大包上车,说人满了,这么大的包没处放。她有点不甘心,试图解释。司机看上去很不耐烦,匆匆收了她的票,撕去结算联,说26号,按座儿坐!他不理于丽娜了。于丽娜瞅瞅这个人,一个中年男人,五官不分明,被一种中年就要结束正在滑向老年的模糊气氛统一到了一张脸上,这模糊没有营造出和善,相反显得有几分暴戾。可能因为于丽娜是带着情绪打量的,所以她感觉这个人不好说话,再纠缠的话她会吃亏。她断了妄想,气鼓鼓把包塞进下头的箱子之间。
26号是一个不前不后的座位,靠通道。于丽娜提着手里的皮包找到了座位。同座的乘客已经到位了,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青年,一副不打算与任何人交往的样子,耳朵里塞着耳机,身子斜躺着,眼睛一直在看手机。于丽娜把身子塞在自己的座位上。座位显得很挤,给人一种挺逼仄的压迫感。她扭头看后面,看到连最后那排座位也满座,她心里才不那么堵了。看来司机说得没错,并非有意刁难她。今天只能全程坐着了,没有躺下歇歇的待遇了。她扣上安全带,有些疲惫地闭上眼睛,逼着自己小睡一会儿。眼皮挺沉的,闭上了就没力气再往开睁。耳边听到司机在做发车前的最后安全要求,安全带,安全带,都系上安全带!
还得捆这么个驴肚带啊,勒得人难受。左边一个妇女,用有些搞笑的语调抱怨。她是老家口音。于丽娜懒得睁眼看。这样的口音刚刚教训过她,余音似乎还在耳畔回绕。她带着一丝微怒,说娜呀不是妈抱怨,庄里人都笑话我哩,说我女子吃着公家饭,是公家人,咋还给我保不住一个低保?人老刘的儿子也工作哩,老刘一家子吃低保多少年了,也没见哪个村干部敢把低保给取了去!说到这里她的声音压低了,似乎她要传播的是一个世界级秘密,说主要是人家晓得走后门,把后门走好,啥事都不难!
发牢骚的是于丽娜的老娘。六十五岁了,这两年吃着一份低保,吃得提心吊胆的,天天担心忽然就被取消了低保。现在确定要取消了,老太太求告无门,干脆对女儿发起了脾气。她的意思是,让女儿快寻门路找人,哪怕是花几百块钱走一下后门,只要保住低保就好。在她看来,女儿既然有工作,那就和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都是一家人,都能说上话,应该是能帮老娘保住一个低保名额的。早在半年前她听到风声说有可能取她的低保,她就慌得连夜找过女儿。于丽娜只能一再地哄,拖,告诉老娘事情想办法办着哩,后门也马上就走,凡事有个过程嘛,急是不能急的。老娘被她哄着拖了三五个月,现在是真到了悬崖边上了,眼前无路了,才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于丽娜悄悄叹一口气,跟老娘解释不清楚,因为老娘拒绝往清楚的方向去想,她觉得女儿完全可以给乡上管低保的干部打个电话,让他(她)给村干部下命令,村干部敢不听?她的低保也就保住了。这就是她指给女儿的光明大道。偏偏于丽娜笨,不沿着这条路去走,这不,就把老太太的好事耽误到了没路可走的地步了。
于丽娜觉得头怪大的,也挺好笑,不要说她没勇气给老家的民政办公室打电话,就算她豁出去打了,那又如何,自己仅仅仗着同为行政单位干部的身份,就能跟乡民政办公室干部说她是某某某,她要她妈享受一份低保?不成千古笑话才怪!再说为一份低保,值吗?她已经跟老妈反复强调过,就当不要这个低保了,每个月她掏二百元补给老妈。老妈不干,说这就不是一二百块钱的事情,而是牵扯到了面子。面子啊娃娃——老妈语重心长起来,要哭了,说你就不知道现在的人,都看重面子得很,庄里差不多的都吃低保,支书她妈也吃哩,李有财老两口三个娃工作哩,也吃着低保,你说我一没老伴儿,二没工作的儿子,就你一个人工作,还是个女子么,嫁出去就成了旁人家一口子人,凭啥我就不能吃低保?
这已经不是于丽娜每月给老太太二百元就能解决的问题了。这背后牵扯得很多,比如一个乡村寡居妇人的尊严,还有哥哥一家人,甚至于家这个门户在村里的身份地位等问题。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生计问题。就算不多的一点钱,如果占着不被拿掉,那也是钱么,苍蝇腿也是肉,每个月领着,一袋米一袋面一桶油至少是够买的吧。白白得來的,谁不爱占便宜。如果公家的拿着,女儿再每月给老太太从工资里抽出几百,岂不是更美的事!母亲不好明着让女儿周济当农民的儿子,如果女儿愿意每月给她一二百元,也等于周济了她的儿子。人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老太太也不例外。
可于丽娜不是泼妇,也不是贵妇人。前者有勇气豁出去四处跑动,求人,跟村干部骂架,为母亲保全低保;后者的话,之所以成为贵妇人,婆家的资源自然是雄厚的,雄厚到一个电话,就可能解决如今的难题。话说回来,如果真是贵妇人,比如某个大官富豪的老婆,或者官二代富二代的女人,还会为一份低保熬煎吗?有熬煎的必要吗?于丽娜想到这里,噗嗤笑了。属于苦笑,无可奈何,又觉得好笑。要说多少遍才能跟老太太解释得清楚呢,她只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是吃着公家饭,可吃公家饭的不等于就能管着低保,或者和管低保的人熟稔到开口说一下就能把老妈的低保给保住。
老妈固执地认为,她既然是公家人,那就和天下的公家人都熟络,公家人没有不认公家人的理,除非女儿如今翅膀硬了,眼界高了,只顾着自己飞,自己过舒坦日子,不管老妈了。可是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的啊,供养你念书,也花了不少钱,光那馍馍疙瘩,叫你背了多少呀,半袋子半袋子地往学校背哩,十几年下来,能背几麻袋哩,能堆一个小山哩,把本事是喂大了,可没把良心喂大,现如今连老妈都不管了——
于丽娜闭上眼,把头抵在前座上,吃力地驱赶着脑子里的凌乱。老妈的事回去再面对吧。现在她急需养神,休息。有一股汽油味在空气中弥散。她感觉有些恶心想吐。运气不好,这趟班车是个旧车,在漏油。味儿够冲的。她昨夜没睡好,会议结束得很迟,为了便利就在会场附近住了个小旅社,空间很狭小,没窗户,睡在单人床上她觉得喘不过气来,墙壁还不隔音,左右两边都是人语声,吵得严重,等到十二点过了,邻居休息了,轮到她睡不着了,一直失眠到天亮。她从包里取一个塑料袋捏在手里,准备随时迎接呕吐物。
车上了高速,行驶平稳起来,颠簸感稍减了一些,汽油味也没那么逼人了。她昏昏沉沉睡着,眩晕感像水浪,一波一波荡漾着,在心头冲击,要突破堤坝,她一边忍着,一边转移注意力,尽量让难受感快点过去——根据经验,只要能压制住最初的眩晕,就不会吐,要是压不住就肯定要吐。在车里当众呕吐是很伤脸的,不到万不得已她才不愿丢人呢。她回头看了几次,后座上依旧满员,她今天是不能躺一会儿了。运气真不好。
有女声引起了她的注意。确切地讲,是两个妇女的声音。她们的交谈开始得很早,也许于丽娜上车之前,她们就在说话了。于丽娜好奇自己为啥迟迟没留意到这一点呢。再说为什么要留意这一点呢?她说不清楚。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竖起了耳朵,用心听她们的声音。应该是前排传来的,她发现抬起头听,声音有点远,头低下顶在前排座椅背上,语声就近了,嗡嗡嘤嘤地响着。两个嗓音,一个稍微沙哑,低沉,似乎是个疲惫的人,话不多,只是发出简短的回应,哦,嗷,嗯,哟,几乎全是单音节词,要不是尾音里拖着一点女性的感觉,还真像个男的。另一个相反,嗓音很好听,话多,热情,活络,话几乎全是由她说出来的,交谈的节奏和气氛也正是她在营造并不断推动。
多少年没见了!嗯。七年了!哦。整整七年啊!哦。都有变化!嗯。哎呀,谁说我没变化,还是有的,哪能逆生长哩!哦。主要是我心态好,我朋友都羡慕我有个好心态!哦。主要是要保养,得舍得对自己好!嗷。看你,舍不得穿也舍不得用吧,跟从前一样,没进步!哟。你记着我的话,女人就要对自己好!自己都不对自己好,还能指望旁人对你好!嗯。我啥秘诀啊?皮肤这么好,一点不显老!嗯。我跟你说这个也有秘诀的,主要是化妆品用对了!
于丽娜两只手抓住座椅背,本来软塌塌的身子绷紧了,眩晕感也轻微多了,她在注意收听前排接下来的对话。她已经断断续续听出大意来了,两个闲聊的女人,从前是旧相识,后来分开,多年不见,今天不期而遇地坐到了一辆车上,自然有太多话儿要拉呱。现在哑嗓子在夸尖嗓子年轻,不显老,皮肤好。尖嗓子也没隐瞒自己的秘诀,她用对了化妆品。是什么样的化妆品,有这样神奇的效果?于丽娜的心顿时被吊起来了,满满的都是好奇。她太想知道答案了。自从进入三十岁,她每天的事情除了工作和家庭,忙忙碌碌,吃喝拉撒,再就是关注自己的脸,具体说是覆盖在脸上的这张皮。这张皮在衰老。夸张点说,她都能看到它每天衰老的痕迹。这个月和上个月不是一个样,今年和上一年更不是一个样。时间不能倒流,自然是越来越老,越来越难看。尤其这两年,被单位派下去做扶贫,村里吃不好睡不好,风土硬,紫外线强,她这张脸已经呈现出要超越年龄的沧桑来。
据说女人的脸要年轻,除了狠狠地整容,像某些明星一样,再就是保养,心态好是一方面,好的化妆品也重要,所以于丽娜现在开始进美容院了,半个月做一次护理,化妆品也从几百块钱一套换到了一套上千。闹心的是,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看不到逆生长哪怕是紧急刹车的迹象。她何尝不懂得呢,说到底还是和个人心态、生活处境等有关系。她太忙了,忙得鸡飞狗跳昏天黑地,每天从睁开眼到闭眼睡觉,醒着的时间里就很少能清闲,不是赶往帮扶村的路上,就是趴在村部填表,要么在接送娃娃上下学,要么陪老人去住院,反正时间好像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也没心思对自己好一会儿,让自己清闲一会儿。
哑嗓子似乎轻轻一笑。却没问。于丽娜着急,她应该问呀,问清楚究竟是什么化妆品,真有那么好的效果?这几年她密切关注化妆品,什么国内的国际的,二线的一线的,好多品牌都涉猎了,一样一样买回来往脸上抹,可结果令她失望。她一直都渴望遇到一种真正能立竿见影的好化妆品,哪怕贵点也没关系,她愿意忍痛割肉,为自己的脸投资。
哑嗓子是个蔫性子人,要等她来推动剧情,是指望不上的。于丽娜抬头望前头,试图看清楚说话的人,可能的话,也搭腔上去问她一嗓子。女人对化妆品的热情,那是天然的,也不用怕遭人笑话。可惜座位之间距离太近,她被卡在座位上,只能保持一个坐姿,根本站不起来,也就看不见前头的人。只能看到两个背影。她斜着身子,趴在两个座位间的豁口上,这姿势有点怪,再使劲就把自己楔进这豁口了。
好在尖嗓子的声音适时响了起来。她好像知道有人在急切等待下文。她说这个油好得很,洗的,拍的,抹的,补水的,防护的,抗皱的,美白的,提拉的,扣弹的,还有祛红血丝的,祛斑的,都不错,我用着呢,十年了,质量没得说。
于丽娜觉得失望,她的热情有所减退,因為她听出来了,这尖嗓子就是个卖化妆品的,很可能是走街头串巷子见人就推销化妆品的那种人。这种人最擅长的就是说辞,一套一套的,能把死的说成活的,公的说成母的。这种人的化妆品,于丽娜不考虑,看都不看,绕着走。她身子靠后,闭上眼浅睡。为自己刚才的冲动和失态,觉得懊恼。
那对女人的声音一直没有停,噪噪切切,高了低了,重了轻了,落下去,又浮上来,深一句浅一句,总旋绕在耳畔。于丽娜累,想把座位调低一点,但她这个座位的调节手柄是坏的,扳弄了几回都没作用。只能一个姿势坐到死了。她觉得悲哀。昨天坐四个钟头到省里,开会开到黑,今天上午又开会一上午,会散后匆匆吃碗面,又要连续坐四个钟头的班车返回去。这腰腿实在是不堪蜷缩之苦。她想不通,尖嗓子哪来这么好的精力,能一直说话,就算久别重逢,内心很喜悦,可表达也需要精力来支撑啊,难道她就不累吗。
尽管于丽娜不再留意,尽量把她们的交谈当做某种没法消除的背景存在,却还是零星注意到话题的大致走向。现在不说化妆品了,换成说男人。哑嗓子的男人。尖嗓子的男人。哑嗓子的男人“老样子,没啥出息”。就这么被一句概括并带过。尖嗓子的男人被夸了一阵。由尖嗓子自己提及,自己夸,然后又抱怨了一小下。于丽娜没听清他是干什么的。反正听上去挺不错,尖嗓子抱怨的语气里难掩宠溺,所以他应该是那种因为宠溺女人,从而被女人反过来宠溺的男人。雇了个保姆。尖嗓子说。做饭,搞卫生,接送娃,都归保姆管。
于丽娜喘了一口气。她知道自己的心因为嫉妒,而在抽搐。居然雇佣保姆,保姆承包了一切家务,那么她这个女主人做什么呢,还有什么可做的呢,照这么说,她回到家只要脱鞋换衣服,然后躺着睡美容觉就可以了。能用得起保姆的,应该是有钱人家。既然有钱,花点小钱雇个保姆,把自家女人从家务里解脱出来,何乐而不为呢。于丽娜禁不住想象,这个有钱雇佣保姆伺候的女人,究竟是个怎样的女人。
说实话,除了在影视剧里看到使唤佣人的女人,实际生活当中,她还真没有亲眼看到谁家里在使用保姆。她单位的一把手正好是女的,一个风风火火的女人,工作上一丝不苟,稍有不满会对下属瞪白眼,在于丽娜心中,她应该是单位最权威的女人,但就是这样的女人,家里也没用保姆,据说当年坐月子是婆婆伺候,婆媳脾气不合,加上她没生出婆婆期待的孙子,一个月时间,婆婆给她各种零碎气受,出了月子要上班,娃娃没人看,每天抱到亲戚家,晚上再接回来,遇到发烧感冒,娃娃哭,她也哭。女领导至今说起来心有余悸,好像是终于从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里逃离了出来。
于丽娜没女领导这样惨,她的娃是婆婆帮忙看。婆婆做得仁至义尽,表面上看不出任何破绽,是慈祥人儿,滴水不漏。但于丽娜挺熬煎的,婆婆在不方便,她就是说个话,出口气,放个屁,走个路,穿个衣服,都要考虑到婆婆在这个家里的存在,婆婆会怎么看,怎么想,会不会多心,会不会生气,这样天长日久日积月累地过下来,挺累的。她就偷偷地盼着娃快点长大,婆婆早日离开,渴望过几天没有婆婆的舒展日子。她也曾暗暗地滋生过一个念头,不用婆婆,雇个人,只要看孩子就可以了。当然,这念头奢侈,背后牵引的那根神经叫经济收入,保姆不便宜,一个月能拿走她三分之二的收入,而她家还供着一套房子的公积金贷款呢。所以说,想想可以,真要实践么,现实骨感,马高镫短,够不上。
即便是偶尔想想,于丽娜想的也只是看孩子的保姆,至于做饭洗衣搞家务伺候人等全方位服务型的那种保姆,于丽娜想象的触角从来都没敢往那个方向伸展过。那种家政人员,只怕她得花掉每月的全部工资。就算是不切实际的奢望,她也只是在太累的时候,在低层次上幻想一下。
她们在讨论驾驭保姆的经验和技巧。还是尖嗓子在说。尖嗓子是主演,哑嗓子是配角,念唱作打全是尖嗓子,配角只负责嗯嗯哦哦。我给你说,这种人你得留个心眼——尖嗓子说。她们也有她们的圈子,还建了群,叫个“姐妹齐心协力群”。其实我家阿姨很老实,没啥心眼儿,但那个群里都是狐狸精,尤其那些年轻女子,你知道一个个的都在图谋啥?
谋着勾引雇主家的男人哩!
“啪!”一个巴掌拍在了一个肩膀上。于丽娜的心不由得跟着跳荡了一下。好在这一巴掌是落在哑嗓子身上了。也多亏哑嗓子沉稳,对这忽然的袭击也能接受。于丽娜知道,有些女人就这性子,跟你说话,说着说着高兴了,激动了,就有了肢体语言,拍你一巴掌,捏你一指头,摸摸你的脸,揪一把小辫子,都在这个范畴里。看来尖嗓子有这样的习惯。
思绪稍微不集中,就跟不上前头的思路了。尖嗓子已经跳开了刚才的事,在说她家阿姨的厨艺了。手艺不错,变着花样做,她的胃口都被吃刁了,出来就不适应,尤其宾馆的自助餐,温吞吞的,千篇一律,跟工厂流水线饲养动物一样!她居然这样表述。车剧烈晃荡了几下。于丽娜被颠得心里难过。快到服务区了。这段路有些破损,车每次到这里都晃荡。好像在提醒乘客做好下去解手的准备。于丽娜开会的时候,如果主办方管饭,就会吃到自助餐,每次于丽娜都把减肥大业暂缓一边,忍不住吃到撑。她挺喜欢吃自助餐的。可现在她怪想吐的——谁叫这破车这样颠呢。
车门一开,凉风扑面。于丽娜跟在几个女人身后跑,这个服务区的卫生间很简陋,还小,女厕八个蹲坑,居然总是锁着三两个,剩下几个就很紧张。于丽娜印象里,每次到了这里都要排好一阵子的队。她恰好尿憋,顾不得别的,一头冲向厕所。等解完手出来,到隔壁便利店接了一保温杯开水,端着水上车。车里空著,人都还没回来。她慢悠悠走,路过前头的座位,留意看,座位空着,包被随身带走了,两个座位和满车别的座位没啥区别,都是千篇一律的客车座,包了一层化纤布外皮,靠背上套了一样的人造革套子,白套子上打着红字广告,内容来自某野鸡医院,不孕不育,早泄阳痿,性生活不和谐。好像全天下的女性都怀孕困难,好像全天下的男性都阳痿不举,好像去了这野鸡医院就能百病包除。
一抹烦躁在心头弥漫。作为一个女人,活到了中年,于丽娜感觉她把自己活得越来越不像人,倒像是鬼了。总渴望着把日子过好,把生活理顺,从里到外有个理想的状态,可到了实际当中,如愿的时候少了又少,一直都乱糟糟的,不是这里不顺意,就是那里不随心。有时候她也渴望发一顿猛力,把这一切从根本上给弄齐整了,可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任何快刀到了具体的生活纷扰面前,也会变钝,变老,面对乱麻是那么无力。慢慢地人就麻木了,习惯了,妥协了,投降了,就在这样的日子里熬着,泡着,扛着,跋涉着。还能怎么做呢,都已经人到中年了,就像赶一段路,现在正好是走到了半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前路还远,回头嘛,去路也已经被岁月的利刃斩断,你还能怎么办,除了继续闷头向前,再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
她们上来了。前头一个稍胖,矮墩墩的,面相挺饱满,慈眉善目的,一看就是那种话不多,却有涵养的女子,有四十来岁吧,不急不慢地过来,不着急入座,等后面的。后面跟着的是位高挑个子,比前者年轻,也漂亮,远远一眼就能抓住你的眼球,让你把她划归到漂亮行列去的那种感觉。她笑笑地走来,穿得挺时髦,驼色毛呢大衣,里面是黑色打底衫,下面配半裙,脚上蹬一双网布短靴。一股既年轻又漂亮的气息,扑面而来,逼人后退。
于丽娜赶紧坐下,装作在扣安全带,眼睛余光却笼罩着这个女人。高个的进去坐下,胖点的坐在边上。高个买了一包吃的,两个人窸窸窣窣地开瓶子,拆袋子,吃了起来。于丽娜后悔自己没买点啥。就吸溜吸溜地喝开水。本来不饿,也不馋,前头这么一吃,倒惹得她又馋又饿。人都上来了,司机点完数,车重新跑了起来。下次吧,下回出差,也买一包,饮料,辣条,鸡爪子,笋片,开心果。她甚至有一个打算,下次出差的话,抽空去一趟省里的大商场,买件毛呢大衣,配短裙,短靴,再买个脖子里带花边的打底衫。她还没发现自己隐秘的内心里,已经在渴望拥有某位女人的外貌了,长相是天生的,做不到了,穿着打扮可以做到。
于丽娜挺直身子,看侧前方。高个女人完全吸引住她了。她的模样好看,声音也动听。娓娓的,潺潺的,像一阵风在吹,像一股水在流,交映,叠加,清澈,柔和。也不年轻了吧,听口气上四十了,因为她们的话题说到了孩子,她有个儿子,上大学呢。她说起儿子的口气,好像在说一个小情夫,口齿间缠绕着甜蜜。列举了一些琐碎的事,咯咯地笑。于丽娜边听边在脑子里拼凑语言的碎片,拼凑出一个帅气、调皮又懂事的大学生。每周都视频一次,有一回我忙,关机早睡了,第二天一开机他就打过来,发了一顿脾气,眼泪都出来了,说担心我有事,一夜没睡踏实。胖女人说嗯,嗯嗯。
有那么个儿子多好。于丽娜暗暗羡慕。只有活到了四十岁的年纪,你才能明白,女人的成功不仅仅是保持漂亮年轻,嫁个好男人,还有孩子呢,孩子养得好,有出息,懂事,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于丽娜的大儿子刚上初一,早熟,叛逆,天天跟她斗智斗勇。想起来就累啊。其实她的累,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孩子。偏偏这个尖嗓子女人,啥都有,啥好都让她占全了。于丽娜说不清楚是什么心情,反正不是好心情,越来越不好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她都有点后悔一开始注意收听了前头的对话。何苦呢,坐趟班车还能给自己找些不自在出来。
话题又回到化妆品上了。于丽娜回头看后面,思量着哪个乘客会愿意跟自己调一下座位。大家都昏昏沉沉的,长途坐车的疲累挂在脸上,身体松松垮垮地沉陷着,好像这么快就和座位融为一体了。随便打扰谁都不好,于丽娜踟蹰了。尖嗓子的声音钻进耳朵来。这个在于个人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说是骗子,在骗人。有的就相信。相信是因为用了咱家的产品。用过你就会知道咱家这油有多好。
哑嗓子似乎累了,想休息,又不得不应付尖嗓子,缓缓地嗯着。于丽娜又想问一下化妆品。啥牌子的,能这么好。真有这么好的话,她回去了就买。可哑嗓子掉线,剧情没法推进。于丽娜扯着脖子瞅前头,渴望看到。尖嗓子从包里拿出几个瓶瓶罐罐来了,肯定是化妆品。
不知道哑嗓子问了句什么。尖嗓子咯咯地笑了起来。说没有没有真没有,我才不给脸上随便动刀子呢。也没啥秘诀,就用它,坚持十年了,别人也都说我逆生长呢。于丽娜只能看到她抬起手在抚摸脸,她的脸蛋本来就好看,再加上抹了一层粉,显得更白了。是粉遮盖了瑕疵,还是本身就细腻白嫩,说实话不好判断。又不是熟人,不能凑近去细看。社交距离,只能看到外表。
得坚持用。那些杂牌子就不要用了,钱一样花,没效果的。为啥毛孔越来越粗大,黑头清不干净,还下垂,出皱纹,就是用油不当。它不吸收呀,你给它再好的,不吸收啥也不顶。别听那些广告上说得好听!我给你说,咱家的产品不打广告,省了广告费,为消费者留个实惠。更新换代也快,一年基本上出一套新品。根据每个人的皮肤配油,不像专柜上,你糊里糊涂买着哩,不一定适合你。
于丽娜悄然点头。尖嗓子的话她听懂了,入心了,感觉很在理。化妆品对于每个女人来说,都必不可少,可用来用去,这么些年就跟瞎子摸象一样,摸是一直在摸,可没摸到真相,也没摸出个一二三来。就跟吸毒一样,吸上就离不开了,不敢离,明知道很贵,明知道可能没什么效果,明知道用法错误,却还得一直用,停不下来。明明知道有个问题在里头,却没有能力去挑破和面对。今天尖嗓子把症结说出来了。原来用错了,方法错了,产品本身也选错了。试问四十岁的女人,有几十年如一日用儿童油的吗?肯定少。谁不是越换越贵,越换越高级。自认为钱多的就好。在一条不归路上走。慢慢迷失了自己。明知道需要回头,返璞归真,可真要实践又根本做不到。
你啥时节到我店里来,体验一下,你就知道咱家东西好不好了。我亲自给你做脸。叫我们最优秀的美容师给你做身体。很放松的。女人嘛,就要对自己好。钱攒着没用,花了才是你的,花在你的身上脸上,才算你的。哑嗓子可能睡着了。剩下尖嗓子一个人在说。也可能哑嗓子在看着尖嗓子的眼睛,给她点头,才让交谈能够一直进行。
于丽娜对尖嗓子的认识深入了一层,她在某地有个美容院,还不小呢,还雇佣了人手。那么尖嗓子本人就是老板了。美容界的老板,怪不得呢,衣着打扮都很不俗,尤其是气质,和一车女性比,她分外地与众不同。小时候于丽娜看到一句话不太懂,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现在于丽娜的总结是,女更怕入错行。职业太累的话,一辈子都搭进去了。有段子说现如今公务员也是高危行业。于丽娜没觉得有多高危,但累是实实在在的。闻着前排时不时飘来的幽香,毋庸置疑,是从尖嗓子身上发出来的,香水的味道,于丽娜觉得悲哀,自己活成了啥呀,甚至感觉不像女人,更像风风火火的男人,早就没有了给自己喷洒香水的情致。
微信响了。是老妈,在打视频。于丽娜赶紧压了,她怕老妈一接通就追问低保的事情。于丽娜还没给乡里打电话呢,母亲在等结果。挺难的。她又不在老家工作。这隔空办一件事,得需要能量,她是个能量不足甚至还不具备什么能量的小公务员,母亲又不懂这些。心里烦,对化妆品什么的顿时没了兴趣。其实年轻的时候她还是挺有生活情趣的,插花,摆草,泡茶,喝咖啡,戴着英伦风的帽子,时光是慢的,节奏是悠然的,小心情天天晴晴朗朗,小日子云淡风轻。是生活里的鸡零狗碎鸡毛蒜皮,零敲碎打地磨秃了她,心迟钝了,神经老了,蒙上了尘垢,太厚的一层,如今想抖落,想逃离,想回到过去,都不可能了。她心灰意冷,闭上眼睛,想睡一会儿。
你说我为啥回去了啊?是去办个事。低保的事!要补个材料哩。好几年没回去了,那些信息都旧了,回去给补了一下。对话声又响起来了。于丽娜猛地抬起头。车速依旧,车里的人还是老状态。要么打瞌睡,要么看手机。前头两个女人确实在说低保。这个问题看来哑嗓子也感兴趣,她终于肯在嗯啊之外多问一半句了。你也吃低保啊?是啊,不像吗?呵呵,说出来很多人都不信。好几年了,吃上就一直吃着。于丽娜抬起来的头没法再低下来,也没办法装作听不到。她很吃惊,这个女人吃低保?这怎么可能?可她没听错,她还在说低保的事。口气淡淡的,又有点得意,好像那低保既是个可有可无的事情,又还是值得拿出来给好朋友说说的。所以她就有些遮掩和保留地说着这件事。你不是在外头做生意吗?哑嗓子问。是啊,生意就要到处跑,不跑没生意嘛,低保是老家的,我户口还在老家。
于丽娜在心里骂了一声娘。谁的娘该骂,她没想,就是很想骂娘。手机微信上,她拒绝了她妈打来的视频通話,她妈就发了好几条语音,方言说的语音没办法转换为文字,她先不听,回到家再听吧,老太太铁定又在催低保的事。
尖嗓子居然也吃低保。于丽娜没法接受这样的信息。印象里,吃低保的不应该是老妈那样的,又老又穷或者身患残疾和重病的吗?这个女的她凭什么吃上了,还吃了很多年!据她的了解,吃低保得有条件,收入低于一定的水准才能申请。这个尖嗓子,看穿戴,打扮,口气,吃喝,还有手里的手机,都应该远超出了低保对象的层面。而且,听她自己说,她还开美容院做老板呢。这世上有需要和穷人抢低保的老板?难道她们那个地方,人人都富裕,都比她还富有,所以她算是个穷人了?
于丽娜在心里冷冷偷笑。骂娘。反复骂。她在骂管低保的人,乡干部,村干部,不仅是这个女人户口所在地的干部,她在骂所有和低保有关系的干部。她也遗憾自己没什么本事,给老妈连个低保都保不住。老妈说你知道低保都叫啥人吃了吗,叫有钱人吃了,叫村干部的亲门党家吃了。她每次都开解母亲,说不会的,事情是公平的,低保就是给穷人的,富汉家不能要,也看不上要。每次母亲都气得骂她实心眼,是个老实疙瘩。
于丽娜觉得尖嗓子的声音越来越难听。说话难听,笑起来更难听,有一股淫荡的味道。真是把没脸当有脸啊,满世界跑生意,嫌弃宾馆的自助餐像动物饲料,打扮得阔太太一样,居然吃低保,也好意思啊,就算家里有人帮忙弄的,这个也不应该占。占了就悄悄偷着笑吧,还好意思拿出来显摆。老话说精沟子撵狼哩,把没羞当胆大哩,说的不正是她这种人吗?家里还雇了保姆,一个月那一二百元低保金,还不够保姆工资的零头吧。
于丽娜头疼起来了,后面脖子里一股大筋抽着,硬成了一根棍。肯定是颈椎病犯了,这病残的颈椎啊,只要空调风一吹就犯,而班车里吹了一路的空调。前头话题还在说低保。尖嗓子在为哑嗓子解释,怎么申请,要交啥材料,需要多长时间。于丽娜举起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她要发朋友圈,发微博,要告诉世人,这个富婆一样有钱有楼有生意,家里雇着保姆的女人,她吃着低保。低保所在地,就是她户口所在地。她老家是甘肃的。请大家转发,认认,甘肃哪里出了这样的美人,顺带再查查那个地方的村干部,这里头肯定有一条腐败链。
可惜都是后背,应该拍脸,越清晰越好。?那就等下车时拍吧,一定拍个正面的。网络的力量现代人没有不知道的,只要真的爆出这个料去,也算是替穷人除了一害呢。于丽娜越构想越兴奋,好像已经把这个女人从一个高高的神坛上拉了下来,让她露出了本来面目,让大家都看清楚,她的年轻美貌和优雅气质,都是怎么得来的,都是建立在挤占社会有限的救助资源基础之上的。
两个女人肯定做梦都不知道,身后一座之隔,有一颗心里正在翻涌着恶毒的汁液,正在图谋着一个大阴招。于丽娜手机没多少电了。她暂时停用手机,留点电下车时做抓拍。她感到很累,是那种濒临虚脱边缘的累,好像一路上的累都是小累,刚才这个计划,才是耗费精力的大事。她闭上眼假睡,养精蓄锐,为后面的行动做准备。
车进站了。像个一直憋着气的人,终于舒展了身子,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于丽娜赶紧站起来,只要尖嗓子转过半个脸她就拍,能抓多少就抓多少。她的坤包还在头顶高处。她赶紧拿包。卡住了。她使劲拽了几下才拽出来。哑嗓子和尖嗓子下去了。她们有箱子,着急去拿箱子。
于丽娜几乎是冲下车的,箱子已经被抽走了好几个,她的大包被压在一个箱子下面。于丽娜愤怒,包终究还是沾满了尘土。这时候人都慌,乱纷纷的,好像时间忽然就变得分秒必争了,每个人都想抢在前头把行李拿上掉头离开。于丽娜提上包,再找尖嗓子。那高挑出众的身影很好找,已经拉着箱子离开了,远远在前头走着,短靴的高跟在地上打出一串脆响,噔噔噔,节奏明快。
于丽娜举着手机,小跑着拍,一张又一张。全是后背,一个窈窕淑女的背影。没有脸不行,她继续追。出站口有个旋转挡杆,出一个人转一下,于丽娜被挡住了。等转出门,外头是车站广场,前方是马路,马路边停满了排队载客的出租车,左右是停车场,零零散散停着私家车。人呢,咋转眼就不见了?上了哪辆车,还是转个弯不见了?于丽娜不甘心,前后左右跑步,找,找了半圈,看到了另一个身影,胖乎乎的那个哑嗓子,她上了1路公交车。
公交车就要开了,于丽娜飞跑着追了上去。
车摇摇晃晃启动了,于丽娜满车看,没看到那个美貌又窈窕的身影,只有哑嗓子一个人。
那个女的呢?就是跟你坐一起的?于丽娜喘吁吁问。刚才一阵跑,她累得够呛。同时脑子里飞速盘算着,自己想好的那条信息不能就此放弃,照片正面没拍到,那就打听一下她姓甚名谁家在哪里,这些信息也挺有用的,发出去让网友们人肉去吧。她甚至有种在努力为社会剜除毒瘤和恶疮的快意。揭露腐败,人人有责。
哑嗓子用疑惑的眼神打量于丽娜。那意思是,你谁呀,我们认识吗?
于丽娜赶紧解释,我跟你们坐一路班车回来的,就坐你后面,哎呀,你那个姐妹,她把东西忘车上了,你快帮忙联系下。
这个借口是临时冒出来的。在于丽娜的人生中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她平时说谎就脸红,也说不像。今天急中生智,居然说得很像。
先套出信息,至于下一步,边走边看吧。
哑嗓子的大眼睛看着于丽娜。和善地笑了,摇头,她呀,我也不认识呀——
于丽娜急了,你们不是老乡吗,很早就认识!
哑嗓子缓缓摇头,显得很有涵养——我说了你肯定不信,她我真不认识,缠着我说了一路化妆品,要卖给我,她应该是推销化妆品的。
还有,我看她是想钱想疯了,这儿都想出问题来了。哑嗓子说着抬手指了下她自己的脑门。公交到新的站点了,她不再理睬于丽娜,拎起包下车走了。
于丽娜站在车里,像个傻子一样茫然,茫然中抬手看,她手心里紧紧攥着一个塑料袋,早就攥出汗了,被汗水浸湿的塑料袋旧兮兮脏乎乎的。于丽娜现在才猛然发现,自己这一路上居然没有吐,只是犯过一阵子眩晕。
【责任编辑】邹 军
馬金莲
马金莲,女,回族,宁夏西吉人,八零后,中国作协会员,民盟盟员。从事文学创作二十年,在各级文学刊物发表作品四百余万字,出版小说集《长河》《1987的浆水和酸菜》《我的母亲喜进花》等十部,长篇小说《马兰花开》等3部。小说集《长河》被翻译为英文在国外出版,多篇作品入选外文选本。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郁达夫奖、中国出版协会优秀图书奖、《小说选刊》年度奖、《民族文学》年度奖、《朔方》文学奖、《飞天》十年奖、《长江文艺》双年奖等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