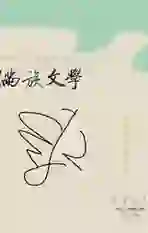鄱阳湖上的训鸟人
2021-04-12塞壬
一
那一天,鄱阳湖上的渔民跟相依为命了八百年的鸬鹚告别。邹水义说,它们黑压压地蹲挤在船边一动不动,仿佛钉在那里一般,它们知晓了那离别的命运。有人痛哭,有人哀叹,鄱阳湖也呜咽着。那一天,作为渔民的邹水义,完成了对鄱阳湖的告别。一转身,六十年过去了,鄱阳湖上不再有训鸟人,这古老的行当,这浩渺的水域,不再有一群驾一叶小舟,赤脚,持着长篙,嘴里喊出一长串口令的训鸟人。他们回到岸上,告别了生生世世的水上生涯。他做着大幅度的手势,对着我学了几声训鸟口令:喔嗬喔嗬喔嗬,呼嗬呼嗬呼嗬……那声音高亢,孤寂,竟有一股悲壮的味道。在他瞳孔的深处,我看见了泪光。“我死之后,再也不会有人惦记鸬鹚了,在我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这些跟我一起在湖上风里来雨里去的好兄弟。”他说,鸬鹚贱价卖掉了,船也砸了,我忽然成了一个手足无措的人,一个多余的人。世界忽然变得无比阔大与虚无,人生变得空荡荡的。只有遥远的回响。
如果你习惯性地回头望向身边,发现这个位置已空,如果你叫一个名字,却无人应和。如果你的梦里只有它与你相濡以沫的点滴,如果你大醉却无人猜中你的心事。那么我想,鸬鹚之于邹水义就是这样的存在。
2020年1月1日起,国家对鄱阳湖实施了十年禁捕的政策。为的是生态的休养生息。邹水义说,有政策补贴,活不是问题。但活,不是有饭吃,有衣穿就足够了的。活是要笑,要醉,要与人抱头痛哭,要有心心念念的物件儿。七十岁的邹水义是鄱阳湖上的一个传奇,他是唯一能够孵养鸬鹚的人。他九岁上船,有六十多年的捕鱼生涯。邹氏一脉在鄱阳湖以鸬鸟捕鱼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他说十年之后,鄱阳湖上以鸬鸟捕鱼为生的人将会永久消失。自他儿子这代起,他们已开始慢慢上岸,去外地打工。孙辈则考上了大学,去了外面的城市。即使十年之后鄱阳湖开禁,大部分渔民,也都转向了更高级的现代捕猎手段。邹氏传统的鸬鸟捕鱼,即将被历史掩埋。
当我在鄱阳湖见到这位老人时,他因为表达的急促与焦虑时常陷入一种词不达意的慌乱中。他对于“我死之后”这个话语尤为焦虑。他念叨着:我得出本书才行啊,我得出本书啊。这种见识,不是一个普通渔民能有的。而我,一个作家面对他的困境只能一筹莫展。即便我写出了三五千字,这细弱的力量,如何能扛动这几百年历史的厚重与壮丽?更何况,此次我跟他,也只是匆匆一见。
二
此时的鄱阳湖正是枯水季,它露出了平坦的湖底,竟是葱绿的草原模样。放眼望去,碧草连天。在近处的水域,候鸟成群地觅食。我们认识了各种雁、鹳、鹭、天鹅,还有传说中的隼。它们有的队列着飞向天空,有的扇动翅膀互戏,隔着距离,人类只能赞叹这绝美的奇景。鸟群是一种意象,它来自于我们的想象。而面对洁白、长腿、曲项的高贵物种,它那冷漠的美,挑战着所有的修辞。因为文学,作家们相约鄱阳湖。而我,认识了这位鄱阳湖上的训鸟人,邹水义。在饶河调百转千回的唱腔里,人们跟我谈起了这位鄱阳奇人。鸬鹚之父。
他有着奇特的长相。长着一双跟鸬鹚一样的耷眉,脸上的表情也跟鸬鹚一样,看人,就像看着湖面,专注而机敏。尤其他缩着脖子,耸着肩的时候简直跟鸬鹚一模一样。我深信,这是长期与鸬鹚形影不离的结果。一身黑衣,步履稳健,身体藏着大的力气与迅猛的应变能力。我想,这个人应该就是鸬鹚化成人形的样子。用水上漂、浪里白条来形容他是不为过的。他没有进学堂念过书,如今却能写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他能说出近百年鄱阳湖上的沧桑人事与流变,他是某种文化的传承者与缔造者。他说,我死之后……
我能理解他的焦虑。那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
我对一生沉迷于一种活法的人总是感佩,就像我自己之于写作这种人生。一旦说起鸬鹚,邹水义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整个人都在发着光。甚至唱念起来,时而吆喝,时而站起身做着手势。这才是真正的邹水义。他说起公鸬鹚求偶的场景:那鸟把头往后一仰,尾巴往上一翘,双翅一张,好像在说,看,我多漂亮啊,如果有另一个公的过来了,它就嘎嘎嘎,仿佛在说你过来试试看!立即拉出一幅决斗的架式来。说罢,停了一会,而后他就黯然起来。我觉得他在未来的人生里是走不出水上的鸬鸟捕猎生涯的:我们人上了岸还有自己的生活,可是鸬鹚除了我们,它什么也没有。你是它的全部,全部。它不是你的奴役,不是宠物,不是你谋生的工具,不是牲口不是禽獸,它是你相依为命的兄弟。
在这大段的独白里,一个人裸露出他战栗的灵魂。类似无望的告白,淹在滂沱的泪水里。听的人觉得心口一痛。他担心他的鸬鹚被人买走后会遭受厄运。
他给我铺开了一张地图。这是邹水义画出的整个鄱阳湖水域的地图。我很震惊。这是航拍的视角。绘出张图,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地图里标注着各种山名、岛名、湖汊、港、洲、村落以及大大小小的湖的名称、形状与流向。六十年,他熟悉湖里的一切。水文、气候、渔汛、鱼类的洄游、产卵,鱼的种类与习性。至于鸬鹚,他一个眼神鸬鹚就能读懂,分毫不差。人与鸟的这种默契除了情感,应该还有一种彼此相通的意识。我能想象,邹水义披着棕衣,拿着长烟杆蹲在鸟船上指挥鸬鹚的样子,那个时候,湖、鸟、船,与他这个人构成了不可分割的完美生态。他跟我说起他的祖父,那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啊。
邹水义在鄱阳湖的岛上出生。九岁时就跟着祖父在船上训鸟捕鱼。祖父教给这个少年朴素的做人道理。在湖上,不可见死不救,六十年来,邹水义已记不清救了多少溺水者。卖鱼的斤两、价格,零钱的找赎不得有半点欺诈。他说,祖父在1942年曾救过两名降落在湖里的美国飞行员。即使是未分清敌友,但救人是首要的。虽然被白肤蓝眼的人种吓住了,虽然不知为何人会从天而降,祖父还是义无反顾地去救人。邹水义眼中的祖父是一个训鸟高手。这一片水域,唯有祖父会孵蛋。他手把手地教会了邹水义如何把一只鸬鹚从蛋里孵出来、精心养大,直到下水捕猎。因此,邹家是做卖鸬鹚生意的。阔过。邹水义回忆,1959年,家里有几千斤谷子、几缸盐,祖父死后,囤的煤还烧了好几年。在那样一个宽裕的环境里,祖父请人教邹水义读书识字。邹水义说,他能做所有的渔具,一看就会。还能详细地把制作过程写出来。回忆那段时光,邹水义满脸的笑意,仿佛那样的好日子谁也比不了。
在水上生活的人生老病死都是在船上。他们在船上如履平地,风浪再大,脚盘都是稳的。水上的万家灯火是什么样子的?孩子们在船上追逐嬉戏是什么样子的?女人们相互串门吗?她们在夕阳中补网唱歌吗?如果有浪,那是不是枕着涛声入眠?晨起的阳光、晚霞、落日,还有船上的炊烟,是不是美得令人震颤?所有的,都只能是我以一种陆地对水域文化的想象与猎奇,那种神秘感在我看来,缘于湖上傳说与地方戏曲吧。在那样一个世界里,有没有只言片语的文字记录它,留存它?
他自豪地说,从古至今,我们渔民的日子是要比农民强的。因为掌握了孵蛋技术,邹水义理所应当地成为了邹氏鸬鸟捕鱼的族长。在电鱼、炸鱼、毒鱼盛行的鄱阳湖,他带领族人签订了永不涉电的协议。邹氏爱这一片水域,爱这生生世世生老病死的家园,他们恪守着古老的祖训,守着这片水域的生灵与生态。每一艘鸟船里都供着菩萨,除了求神护佑,还有一种敬畏。
三
我试着走进邹水义的鸬鸟世界。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流遍全身。仿佛亲历了一遭。他说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细节,都太有画面感了。他与鸬鸟之间营造了某种氛围,包括语言、形体、呼吸,甚至是一个语调、一个手势和一些细微的情绪。即使是沉默,他们都彼此懂得。我在邹水义身上看到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他们合谋完成一次次漂亮的狩猎。因为鸬鸟全部都卖掉了,所以那天我没有见到一只真正的鸬鹚。在邹水义的手机相片里,他一张一张地翻给我看:拍击水花怒啄活鱼,敛脚直坠深水,迅疾如同一枚弹头,鸬鸟衔鱼冲出水面,因为速度和强大的力量使照片模糊成一团光影,却斑澜闪耀。它的喙,它的眼,它的翅,还有它的蹼足,都有各种姿势的特写。邹水义珍藏着它们,用手指一帧帧划过,我能感受到他的呼吸里,有一丝丝的悸动。那是他放在心尖尖上的宝贝。
看了一个一分钟的小视频。到了预定水域,渔夫划着船盯着水面,一发现鸬鸟咬鱼出来,立即放桨,脚踏着不到两寸宽的船舷,身轻如燕,噔噔噔三个箭步,跃到船头,操起一丈多长的竹篙,捅向鸬鸟,篙端装有捞箕,篙到鸟嘴一松,鱼落入箕中。不到一分钟,整个过程完美流畅,一气呵成。
我注意到,渔夫钉在船上的双脚,那脚趾五趾张开,呈扇型,壁虎一般,牢牢吸在船面的木板上,那持篙的手,擘力惊人,那纵身一跃,除了肢体的平衡感,还有多年的水上功夫。邹水义说,要练好这功夫七八岁就得上船,不然,等骨头硬了就练不成,他说,即便是现在七十高龄,他能平地一跃登上八仙桌。
可是孩子们都是要去岸上读书的。这绝技只能失传。
我想起电影《加勒比海盗》中的杰克船长,他是“黑珍珠”号的灵魂,他是它的王,他在船上飞来飞去,唯有大海才是他人生的主场。鄱阳湖之于邹水义,鸬鹚之于邹水义,是他人生的全部。而如今,他最终会死在岸上。
“每一只鸬鹚都有名字。我们给它取名:赵子龙、张飞、罗成,金大力……这是英雄的名字,五虎上将啊,我们是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他说,在一般人眼里,所有的鸬鹚都长得一样,可是在我们看来,它们千差万别,即使是空中远远的背影,我们都能分辨出是哪一只鸬鹚。你只要一叫它的名字,它就会回应你,冲你嘎嘎嘎,好像在说,你叫我做什么呀?
如果那一天收成好,它就很高兴,晚上你在舱里喝酒,它就一颠一颠地跑过来依在你身边撒娇,挨着你的脸,要亲亲。如果你让它不高兴了,它就耷着眉毛,把咬的鱼故意放走气你。它们会争风吃醋,报复,还会立功讨你欢心。邹水义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比鸬鹚更聪明的鸟儿。
一个家庭有两只鸬鹚就足以生存。市面上,一只鸬鹚要卖到三千块。一船一人六鸟,不到三小时可以咬到八百多斤鱼。它能捕咬到三十多斤的鲤鱼、八斤重的甲鱼。在十几米深的水域,这猛禽的力量与智慧不可思议,奋力与大鱼博斗,周旋,追逐,厮杀,最终衔鱼破水而出,像一个将军挟着俘虏胜利归来。它上来后还会告诉你,下面有一个深洞,它探不进去,或者是一个树蔸,蔸底藏着好多鱼,它无能为力,它用钩子在船上划圈圈,然后朝你点头,告诉你它在水下看到的一切。如果它看到不可知物,它会发出恐怖的惨叫,用以警示你,水下有可怕的东西。咬上来的鱼,它能按鱼的种类堆放在一起。从没有混淆过。
最鼎盛时期,邹水义雇了四十八个人,他有两张网,五条船,二十六只鸟。一网十万斤凤尾鱼。我对一网十万斤凤尾鱼毫无概念。无法想象。我对于一只鸬鹚能捕到九十斤重的杆鱼也无法想象。但他跟我说起那段人生的快乐逍遥,上岸卖鱼,停在周边的村落,去喝酒,听戏,兄弟们去找女人。恍惚间,我仿佛进入了沈从文的边城。那种人间的多情与风流,多少往事尽在这浩渺的鄱阳湖上了。
邹水义说,如果不是跟它朝夕相处,是读不懂这一切的。看了一些专家写的关于鸬鹚的文章,很多都是错误的。鸬鹚不吃螺、蛤、贝,它只吃肉。他了解它的全部,从一只蛋开始,在它六十天的成长过程里,睁眼,长出第一根毛翅,到开胸,最后到合翦,邹水义甚至清楚今天相比昨天,一只小鸬鹚长了多少肉,手一掂就知道。这是极有仪式感的一种成长。当小鸟出壳睁眼、齐毛到能下水,每一个重要的日子都会放鞭庆祝。初一、十五要拜菩萨祈福。对于他们来说,鸬鹚就像农民的牛一样,而它们却又成活艰难。跨级式的成长阶梯,都是重要纪念日,像婴孩,剃毛、满月、百日,周岁,都会纪念一番。我对这样的隆重感到不可思议。但我还是懂了,在手心长大的鸟,如同掌上明珠,那是心头肉般的存在了。
所以,鸬鹚是他的家人。
失去它们,就如同失去……后面的话,我无法说出。
四
下元节祭水神。拜菩萨、大比武、巡游、放河灯。这盛大的节日如今还能怎么办呢?这古老的习俗,传承八百年的水上节日,没有了鸬鹚,没有了船,它将如何延续?
我没有问。只剩下饶河调在孤独地唱响。只剩下一个孤独的身影在落日中暗淡。
邹水义为此痛哭。湖里的鱼大量死亡,因为有人乱排化学污染物;有人扒螺蛳,拖网破坏水底绿植,挖沙船翻起湖底陈年垃圾,毒化水质,有人赶鱼,连同江肫一起赶,在闸口处活活闷死江肫,一天几十头,整船整船的尸体被拉出。电鱼、炸鱼屡禁不止,鱼的产量每年剧减,渔业萎缩,填湖导致湖面变小,鱼的种类灭绝,生态堪忧。
他悲愤地发出:可是这关我们鸬鸟营生的人何事?我们为什么要为此买单?禁渔,也把鸬鹚给禁了。一同禁断的还有它的文化与传承,那些无法续写的故事与传奇。
他说,在他多年的渔民生涯里,海鱼灌入鄱阳湖是常有的事,比目鱼、大黄鱼、小黄鱼都曾现身。但现在,从未看到过了。他还说了件奇事,火烈鸟也曾来鄱阳湖过冬。那种红色的鸟,单腿直立,成群结队。他见过丹顶鹤盘旋飞到高处垒窝,孵蛋。他说,鄱阳湖的大闸蟹两三斤重,野菱角、莲蓬、茨实无人采摘,泛滥成灾,他说,今后十年,我们都吃不到鄱阳湖的鱼了。
再也不会重现开河的盛事。那一天,湖面上,千百条渔船,千帆竞发,百舟争渡,场面尤为壮观。一声令下,渔船像离弦之箭,争先恐后,在渔歌、吆喝声里,撒网、打镣、走钩、划钩,放鸬鹚,各显神通,热闹非凡,那一天捕鱼可达十几万斤。至于那首渔歌何时再能唱起:
喜气洋洋赛龙船,我船划得出头尖,红颜鸬鸟咬得好,一船鱼来几船粮。
当一个事件进入了博物馆,成为历史,当一个人守着回忆孤独度过余生。我知道句号就要划上了。邹水义,鄱阳湖上最后的训鸟人,这活化石般的存在,我能留下的仅这微弱的文字罢了。终究,我只是一个无力的人。太多事,大抵如此。
【责任编辑】王雪茜
塞壬,原名黄红艳,现居东莞长安。已出版散文集四部。两度获《人民文学》年度散文奖、第七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新人奖、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第六届、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提名奖、第四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第六届冰心散文奖、第十一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