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托邦·医生书写·文化协商
2021-04-01王彦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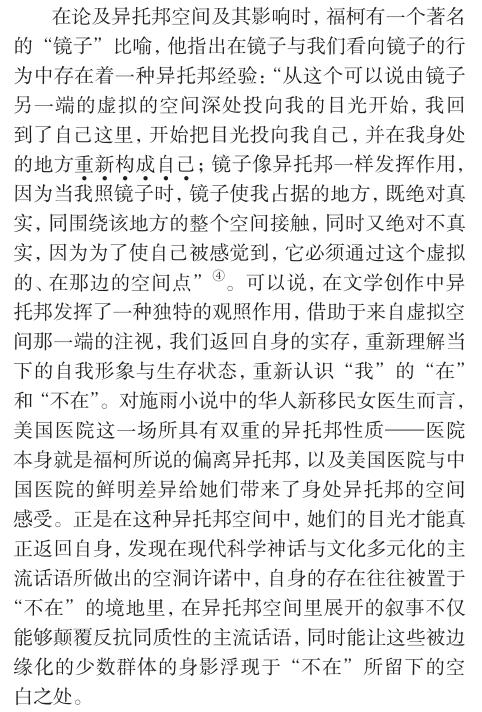
摘 要:作为医生作家,施雨的小说创作在新移民文学中独树一帜。她的小说描绘新移民的跨文化体验,展示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及新移民进行文化协商的过程。她笔下的医生叙事将文化表现置于医院这一异托邦空间中,将异托邦空间叙事与文化叙事相融合,从而写出了新移民群体独特的文化伦理困境及其文化协商策略。
关键词: 新移民小说 异托邦 医生书写 文化伦理 文化协商
《下城急诊室》与《刀锋下的盲点》是新移民女作家施雨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作品面世后得到广泛的关注,论者指出这两部作品从文化表现深度而言,展现出作者对于中美文化的深刻把握和了解;从文化视野的广度来说,其中对美国其他少数族裔文化的展示在新移民文学中是一种突破。a和其他新移民小说一样,两部作品以新移民人物作为联结,展示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新移民进行文化协商的过程,但施雨的作品予人深刻印象的地方在于,作家不仅对差异性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包容度和深入的理解,而且将文化表现置于医院这一特殊空间之中,形成独特的异托邦空间叙事与文化叙事相融合的手法,并展示新移民独特的文化伦理困境及其协商策略。
一、异托邦空间叙事
异托邦概念是福柯提出的,出于对空间与个人主体性之间关系的敏感,他认为空間对个人有着隐蔽的规训能力,空间的安排布局中伴随着一种微观的权力机制,这一机制与不断扩张的社会制度复合体沆瀣一气,通过作用于人的身体及生存方式,将人锻造为一种新的主体。而异托邦则提供了对抗这种权力机制的场所,它是一个容纳异质性的空间,是“能够出离中心的场所”,“相对于日常处所而言,承载着某种强烈的相异性和某种对立或对照的标志”,“其功能和效果是质疑,即质疑被看作自然和合法的空间所有不证自明的样式,质疑这些自然和合法空间之权力和权威的所有不证自明的样式。异托邦的本质就是向权力关系、知识传播的场所和空间分布提出争议”。b因此,就个人主体性而言,异托邦提供了一个逃离社会规训的可能性,正如布洛萨所强调的,其根本目的并非“反抗”一词能概括的,而是重在对差异的显现,异托邦空间能够打破我们对社会统一性同质性的习以为常,从而跳出这一麻木状态。
医院作为一种异托邦空间,其首要特征是对异质性的容纳。福柯所谈论的异质性,是相对于社会的“正常”而言的,是一种“边缘性”。就此意义来说,医院内的人群同时也是社会中边缘化的人群:就患者而言,他们因为自身的伤病处于“健康”社会的边缘地带,需要在医院里恢复健康以便回归社会;就医生而言,他们在这一空间中主要以职业身份出现,由于职业的特殊性(现代医学要求医生具有强大的理性,而将普通人所具有的感性倾向均视为软弱和缺陷),他们被推到“正常”社会的边缘地带。异质性容纳的第二个方面,是指最大限度地容纳差异性的共存。无论个体间在政治、文化、种族、信仰等各个方面存在多么巨大的差异,医生与患者都因为“疾病—医疗”而聚集到医院空间内,并在这一框架下抛开差异,为同一个目标(即治愈)而共同努力。
异托邦空间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是颠覆性。医院空间汇聚了大量的异质性人群,他们却在这一空间内展现出某种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压倒了异质性差异的现象本身颠覆了日常生活中由同质性幻觉带来的稳定感。其次,“医院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地方,生与死每天都在眼前发生,人在接近死亡的时候,人性会表现得很彻底,病人、家属,医生、护士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感受也格外强烈。一般人在一生中不会有几次接近死亡的机会,而医生则是无数次,而且是各种各样的,在这样反复刺激和考问之下,不做深度思考的人很少”c。这些极端性情境往往展现出偶然性带来的无可预测的后果,打破了我们关于生活的“恒常”性质的幻觉。
异托邦空间的第三个特征是去(主流)政治化。异托邦往往表现为对主流政治的拒绝与疏离,虽然根据福柯的权力渗透理论,完全去政治化是绝无可能的,但在医院这类异托邦空间中,仍然在整体上与政治保持相当距离。例如医生在面对病人时,不以其阶级地位、种族性别等因素为考查依据,就是一种去政治化态度。
作为一种典型的异托邦空间,医院空间的特征不仅表现在与其他“正常”空间相比较时具有异质性、颠覆性、和去政治化的特征,也表现在这一空间自身就具有多元性的特征。医院空间内部并非是同一特质的,而是具有自身的差异性,施雨小说医院空间叙事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向我们展现了医院空间的内部差异。在《下城急诊室》中,作家主要描绘了急诊室这一空间,在其中发生的都是紧急情况,各种极端情境往往同时在此上演,而面对这些纷乱的情况,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患者,甚至那些并非患者但却来到这一空间内的人们,他们都最大限度地忽略了彼此的差异性,在面对生死考验的时候,他们都还原为最原初的人类。因此,这一空间的异质容纳程度、颠覆性特征比医院的其他区域表现得更为突出,具有直观的震撼感。《刀锋下的盲点》主要描写叶桑进入普通科室后的生活,在这一空间中急诊室的应急状态消退,“正常”社会的秩序往往能在其中发挥作用,而工作于其间的医生们也多数会以“正常”社会的标准行事,因此,由个体差异所带来的分歧和斗争就会浮现出来。
《刀锋下的盲点》还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医院空间——私人诊所。私人诊所与普通医院在服务于“病人”、享有现代科技赋予的权威等方面是相似的,但“私人化”特征使这一空间具有更鲜明的异托邦色彩。首先,私人诊所的权威性更多来自病人的认可而不是由官方赋予的,诊所里的医生不仅需要在知识技能上得到病人的服膺,还需要与病人之间建立起长期而稳固的、兼有信任与喜爱的感情联系,因此在空间布置上更具有人情味。在安德森医生的私人诊所里,等候室里有各种杂志供等候者翻阅,还有沙发茶几,与普通医院候诊区相比空间条件十分舒适,鱼缸里热带鱼浮游景象带来的度假联想,更暗示了一种对痊愈的期待和痊愈后生活的想象,熟悉的老歌唤起等候者的记忆,在情感上与这一空间容易产生一种共鸣。
其次,私人诊所的运转、支持都主要与私人有关,这也决定了它与“正常”社会之间保有一定距离,具有更浓厚的私人色彩。如来到这里的人们会更多地展示出私人生活和个性,此外还包括诊所对于前来的人们负有保守秘密的义务。小说中的关键人物纳尔逊夫人之所以选择安德森的诊所做整容手术,就在于这些手术需要对外保密,以便维护自己和丈夫的公众形象。这种私人色彩同时导致医生与病患之间的界限很容易趋于模糊暧昧,带来私人情感的联系:如安德森医生与纳尔逊夫人既是医患也是情人。
施雨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作为异托邦空间,无论是普通医院还是私人诊所,其边界都不是那么牢固。在普通医院中,由于医生们的权威是来自官方的授予,其服务得以产生的动力是被规定了的——即他们除了应遵守医生职业道德标准、人道主义精神之外,还必须服从此类机构自身的运作规则,在医院的整体利益面前,医生个体或病人个体的利益往往被轻易放弃:小说中为了医院的利益,病人因误诊而死亡的真相被隐瞒下来;为了得到大额的资助,医院对于叶桑的蒙冤受屈视而不见,甚至落井下石。可见医院作为异托邦,其对“正常”社会及其权力的拒绝往往表现为一种不连续性。而在私人诊所里,其所有者的个人品质往往决定了诊所工作人员及患者的命运,如果没有安德森医生的善良无私,叶桑在纳尔逊夫人遗体已经火化,而手术时采集的血样消失不见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证明自身的清白,这个故事的完美结局几乎完全取决于安德森医生的个人良心这一偶然性因素。偶然性同时意味着无法把握,私人诊所作为一个异托邦空间,其脆弱和不稳定显露无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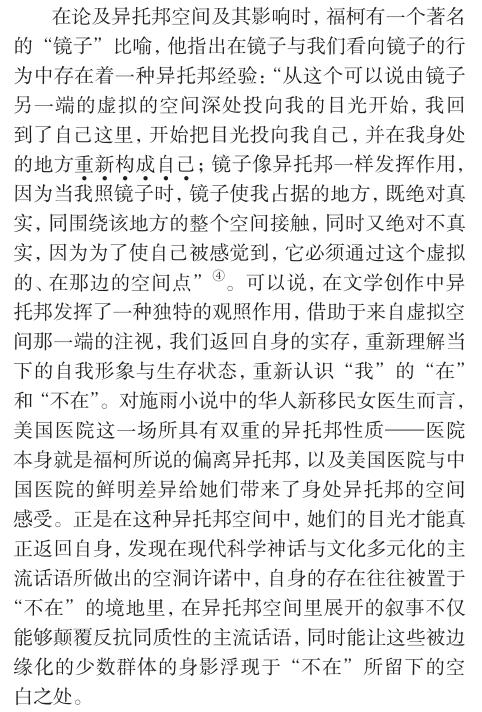
二、文化叙事与文化伦理困境
在异托邦空间所容纳的各种异质性中,福柯最为关注的是文化异质性;换言之,福柯主要讨论了异托邦在文化领域中发挥的作用。在“正常”社会里,主流文化将异质文化排挤到边缘地带,对它们进行遮蔽或者压迫,异质文化因此不能进入大众视野,或是以异常和反面的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而异托邦空间为这些文化提供了存在和被认可的可能性,从而颠覆了主流文化话语霸权,对主流文化进行反抗。
在施雨的两部长篇小说中,作者有意识地建构自己的文化表现主题,正如她在访谈中所说:“‘生存和‘文化或许是新移民文学,甚至更早的台湾留学生文学永远摆脱不了的母题,《刀锋下的盲点》自然也是如此,但在这部小说里,我试图摆脱华裔文化的窠臼,以全球化这样更高、更大的视域来处理小说中的人和事。”e之所以“生存”与“文化”能够并举,不仅因为二者均为移民初到移居国时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而且也是因为二者之间往往彼此交织紧密联系的。文化上的不能适应最终会带来生存困境,同时也是困境体验的重要内容。
《下城急诊室》主要描写实习医生何小寒的爱情生活,这种生活与她的职业生涯交织在一起,并以职业生涯为背景来展开。小说着重对比了中美文化中婚恋文化的差异,并展现了新移民群体所面对的文化伦理困境。何小寒的三段爱情中,在国内与高凡伟的恋爱是一个基础性的情节:它既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动力(因为恋爱的失败,何小寒才离乡去国),也是人物命运的成因(对这场恋爱的反复怀悼与反思,直接影响着何小寒接下来对爱情甚至生活的抉择)。这段爱情显示,恋爱双方深受当时国内社会性别文化的影响,如婚姻重于爱情、男主动—女被动的情感模式等。小说通过何小寒的回忆来讲述这一段爱情故事,回溯性的叙述与她的当下经验交织,由此构成中美两国性别文化间的对话。对美国婚恋文化中的爱情至上、婚姻家庭观念相对淡薄以及女性也可以是爱情中的主导者等内容,何小寒并不能接受,她拒绝白人追求者而选择同为新移民的施杰,说明她在公共生活领域(如医生职业生活)里能适应美国社会的文化要求,但在私人生活领域(如爱情生活)却依旧以她所熟悉的中国文化标准行事。这一背离性的文化体验正是新移民所面对的文化困境:个体的内外统一的文化感受似乎遥不可及。
在两部小说之中,显然施雨认为《刀锋下的盲点》在文化主题上有更出色的表现,是“以全球化这样更高、更大的视域来处理小说中的人和事”,“花很大的笔墨大胆、细腻地描写本民族之外的西方文化”f,从而避免了新移民作家写作常常停留在本民族文化领域的缺憾。
小说对美国文化的表现是立体式、具体化的。
首先,作者在对叶桑生活的环境进行描写时,不仅对于所写城市的历史、各种轶事掌故了如指掌,同时也能对相关的文学、音乐及其他艺术创作等旁征博引,表现出对美国文化传统的深入了解。在这样的写作中,美国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异域符号:作为一个空间形象,由于作家对城市布局的清晰展示,这一空间得到立体化展示;而历史及文化因素的引入,也赋予了这一空间时间的深度及文化的深度。
第二,小说展示的美国文化并未停留在表面印象上,而是深入介绍了其文化的内在构成,主要是美国独特的法律文化和医疗文化。在对这两个方面进行展示时,作家既写出它们合理甚至进步的一面,也写出其中存在的漏洞乃至不合情理之处;既写它们的整体构成、运作机制,也写具体的操作细节和施行策略;既写医生护士、法官律师,也描摹患者表现、被告心态。在这样的处理中,美国文化以一种多层次、多面向、多角度的方式得到呈现,不再是一种单一化的僵硬整体。
第三,小说通过对美国少数族裔的深入刻画充分展示了美国文化的多元化构成。在刻画美国华裔这一群体时,作者的笔触从新移民延伸到华裔的另一部分——华人移民后代身上,小说中另一重要人物王大卫即为华人移民后代的代表。在叶桑等新移民看来,华人移民后代与自己只有人种学上的共同点,因此以诸如“ABC”“香蕉人”等称呼他们,小说让王大卫向叶桑指出在寻求白人社会认同等方面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性差别:“在这个移民的国家,大家都差不多,只不过有的人是生为白人;有的人是学做白人;有的人则是不自觉地成为白人。”只不过华人移民后代的一部分认同之路是由移民父母代为完成的。对王大卫所代表的移民后代之心理及其文化意识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作家出色的文化敏感性。
小说中还描写了美国其他少数族裔的人物,在叶桑被当作医疗事故的替罪羊时,她的支持者包括同样来自中国的施杰、白人导师、朋友,以及一些其他少数族裔的医生;但反对她最为激烈的,恰恰是一位印度裔的女性医生,同为少数族裔或同为女性并没有使得这位医生对叶桑产生同情心,相反让她看到叶桑所具有的巨大威胁——从少数族裔角度而言,叶桑的事为少数族裔不可靠提供了新的证据;从女性角度而言,叶桑的事为女性不适合从医提供了证据。这样的描写让我们意识到,美国少数族裔群体及其文化是一个团结与分裂共存、相似与差异同在的复杂构成,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去单一地看待这些少数族裔群体及其文化,都只能带来僵化和错误的认識。
小说让我们意识到,不仅美国对中国有刻板印象,新移民也有对美国的刻板印象,在这种单一同质化的认知被彻底打破之前,新移民是不可能真正适应美国文化的。
三、医生叙事与文化协商
近年来,由于叙事理论在美国医学界长期的渗透与发展,出现了医生书写这一新的文学类型。在医生书写中,医院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场所,它是“医生故事发生的场所,更是促成故事发展的原因和动力”,医生书写同时十分关注医院作为现代医学话语霸权及其权力实践场所的一面,借助于文学叙事,“医生作家实际上是在医院这个异托邦中建构起另一个异托邦”,从而对理性崇拜和科技至上的狭隘理念进行反抗。美国医生书写的价值还不仅于此,在由医生作家们建构的文学与医学的交叉叙事空间中,因这一空间“非此非彼”的特性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其间,“医生作家可以把理性社会中种种非人化的规定推翻”,“并以此来颠覆医生英雄形象的宏大叙事和质疑医疗话语霸权的规训作用”g。
与美国医生书写比较,施雨的医生叙事有着自己独特的之处。首先,在美国医生书写中,本土医生作家们关注的主要是医院作为一种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的权威性机构,以及其间所包蕴的权力关系网络及医生在这一网络中的位置,通过对这一权力网络的揭示,批判其在科学及理性的名义下所形成的种种非人化的规定。而施雨关注的是在医院空间内包容的种种边缘化文化,如少数族裔文化、同性恋者文化、无产者文化等,描写这些边缘性文化在医院这一空间内部所产生的碰撞。正是医院空间的特殊功能一方面为这些文化的共存提供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也为这些不同文化的碰撞增加了戏剧性。在面对生死的紧要时刻,文化间的差异性一方面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弥合——为了拯救生命,无论医者还是患者往往都会暂时放下对于文化差异的敏感;另一方面,恰恰是生死之际最能使个体表现出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对待死亡的态度常常是不同文化产生差异的根源所在。由此,施雨通过文学叙事與医学交叉所创立的异托邦空间成为异质文化多元共存、彼此对话的文化空间,但在其中,医生与医院权力网络的关系却隐退到幕后。
其次,美国本土医生作家的文学书写是为了对抗理性崇拜和科技至上观念,致力于恢复被医学话语取消的医者身体性,并从感性的角度对患者进行还原与再现。在施雨的小说中医学空间不只具备科学理性,同时也被赋予了感性内涵,这一感性内涵主要通过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的私人情感和个人生活进行展现,对这些感性内容的表达并非为了反抗医学话语中的理性科技至上,而是服务于对人物心灵世界的刻画。实际上作家借人物之口对于美国医学中的理性色彩做了许多的赞美与肯定,尤其在《刀锋下的盲点》中,作家在医院之外又着力描写了法庭这一特殊空间,从而与医院空间构成鲜明的对比。从表面上看,法庭空间与医院空间一样都具有权威性特点,它的布局简单明确、功能性强、严守规范,这一空间设立的目的是尽量让不同的人们获得共同的正义,正是在这一理想目标之下法律事务的从业者发展出众多策略和技巧,当这些策略技巧被过度使用时往往会给人一种感觉,似乎策略技巧取代了正义成为追求的目标,而有罪与无罪之间不仅界限模糊暧昧,甚至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与之相比,医院空间里具有明确的操作过程、清晰的结果判断、可逆的反思程序等,无一不在显示现代理性的权威性和正义性,而且空间内部大多数医者对职业道德、人道主义精神的坚守,也是对现代精神的一种正面描述。因此,施雨的医生书写在对现代科技理性的态度上正与美国的医生书写背道而驰。
可以看出,与美国本土医生作家相比较,作为新移民的施雨显然更加关注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与沟通问题,正因为新移民所属的美国华裔在文化上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地带,作家的目光才会进一步投射到同属边缘文化的同性恋亚文化、无产者亚文化领域,对这些文化产生了解和表现的兴味,并进一步寻找不同文化间沟通对话的可能性。而美国本土医生作家受到了西方世界内部文化自我反思思潮的影响,其写作对于医院权力关系网络的揭露、医学话语霸权的颠覆等都是这一反思带来的结果,这种反思的关注点仍然是在于西方世界的自我纠正自我更新,即使在写作中带入其他亚文化内容,其努力的目标仍旧是令西方文化恢复更健全的状态。
施雨小说的医生叙事立足于自己在美国多年从医的经验,在小说中充分调动医院这一异托邦空间的文化潜能,使得各种异质文化在其中共存,并在彼此的冲撞中激发出文化对话,最终导向文化协商。在施雨这两部作品中,文化协商有两个向度:一个向度指向美国主流社会,医院作为重要的协商空间,不仅容纳了各种异质文化,而且在这些文化的彼此冲撞之中建立起一道联结主流强势文化与边缘弱势文化的桥梁;一个向度指向中国国内,其策略是文化翻译,小说中大量对美国社会文化、历史乃至制度的介绍,不仅是理解人物故事所必需的背景,也帮助国内的读者真正了解新移民的生存环境。这两个协商向度为我们指出,新移民作家的双重跨域经验给他们带来的独特文化处境,即他们需要同时面对移居国文化和中国国内文化进行身份构建。意识到这一点,能帮助我们认识到新移民写作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立体性,意识到新移民作家的文化策略所具有的层次性和丰富性,甚至能够理解其中的矛盾之处。
a 见刘俊:《“单纯/中国”与“丰富/美国”的融合》,《华文文学》2009年第4期;陈涵平:《跨域的情愫与复杂的认同——对施雨两部长篇的比较阅读》,《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b 〔法〕阿兰·布洛萨:《福柯的异托邦哲学及其问题》,汤明洁译,《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cef江少川:《弃医从文 用母语坚守精神家园——施雨访谈录》,《世界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d 〔法〕福柯: 《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引文中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g 孙杰娜:《异托邦中的异托邦:当代美国医生书写中的空间叙事》,《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1期。
基金项目: 甘肃省教育厅一般项目(2017A-019),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资助
作 者: 王彦彦,博士,兰州交通大学文学与国际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