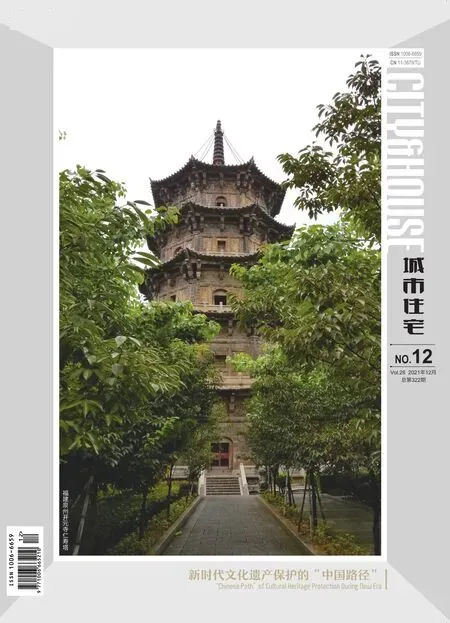新陈代谢运动影响下的建筑设计与城市设计的延续
2021-03-31陈素云
陈素云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0 引言
国际现代主义失败之后,与“十次小组”和“Archigram”同一时期出现新陈代谢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掀起了一股试图突破现代主义统一性现状的浪潮。由丹下健三作为领头人,黑川纪章、大高正人、菊竹清训、川添登和槙文彦等人作为主要“新陈代谢”理论研究和实际验证人[1],为日本战后政治转变、经济崛起的时期增添了对未来社会充满激进的尝试与幻想。新陈代谢主义是现代主义的最后一场运动,以建筑实践加宣言的单一设计模式就此逐渐消失,并使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该理论的领头人丹下健三深受柯布西耶设计语言的影响,故在新陈代谢代谢主义发展的早期,设计手法多利用现代主义的几何框架与日本传统建筑相结合的形式。本文回顾和探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盛行的新陈代谢主义建筑空间的表现形式以及建筑与城市的关系。在新时代背景下,建筑设计理念依旧趋于地域生态和传统文化的结合发展,我国建筑设计中也依旧存在现代与传统、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故当代建筑与城市空间仍然可以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理论中吸取经验与教训。
1 研究意义
现代城市在国际现代主义遗风的影响下,产生了高密度、形体单一的“方盒子”城市景象。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国际现代主义的兴起到由史密森夫妇为首的“十次小组”,尖锐地指出当时的设计中功能城市规划思想的不足,率先打破了当时国际建筑学领域单一的范式和组织模式[2]。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逐渐瓦解,意味着“现代主义”(Modernism)建筑以功能至上的设计理念再也无法契合人们的实际需求,多元化的历史文化与民族主义渐渐得到了人们的重视。新陈代谢理论学习和发展了“十次小组”及“Archigram”强调的流动和变化的建筑形式,并将其与本土建筑哲学思想结合。除了研究新陈代谢主义短短十年的建筑与城市设计理念的变化外,本文还将对比同一时代下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讨论同是经济高速发展、人文精神和民族意识高涨的现在,传统观念与现代理念的碰撞在设计中该何去何从。
2 新陈代谢主义背景与含义
2.1 形成背景
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在欧洲发展正盛,多数国家对“现代主义”都是以先“移植”再“吸收”的形式代替自发性创造。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日本将“现代主义”本土化创造了时机。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增长,1955年实行的“55年体制”增加了人们的生活福利,其日常生活趋于安定。但正是由于现代主义在日本的稳步发展,以及国际现代主义受到文化冲击的刺激日益瓦解的双重条件下,促使日本为缓解传统与现代冲突进行多次探索。例如丹下健三在1951年设计的东京自宅,以传统的木质建筑材料为基础,平滑屋顶、方形细柱以及外廊道结构在传承“桂离宫”日式美感的同时,又结合了柯布西耶的几何设计元素。同样的设计理念也体现在这一时期丹下健三设计的广岛和平纪念馆,虽然深受柯布西耶的影响,并出于纪念性形象的需求,该建筑通过简单的轴线关系和裸露的混凝土建筑外立面,加之竖向水泥柱的粗细、排列和朝向的变化,体现出废墟重生的原始状态。
战后的城市成了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对抗的重要场所,大多数城市都选择了以复原的形式重建,但城市发展不似以往,工业化为城市带来大量劳动力,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过度拥挤的状况导致城市用地无法满足人口激增。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大多向海洋和高空探索。1960年,在东京湾规划中丹下健三提出跨越东京湾的“城市轴”方案。整个城市规划为线性“有机”生长结构,以一条横跨东京湾的海上高速公路作为中脊结构,被中脊环绕的建筑结构是政治枢纽、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区,次级交通连接于中脊骨架上,分层降级至居住使用的建筑群体,形成一套完整的、以汽车交通为主的城市框架。其城市设计原型可追溯至柯布西耶设计的阿尔及尔高速公路巨构建筑。在丹下健三的东京湾规划中,交通系统被比作身体的神经系统,流动方向决定了城市结构。“新陈代谢运动是一场有乌托邦诉求的现代艺术和建筑运动的最后范例”,为日本现代建筑努力与现代主义全球发展趋势进行联系提供了重要的立足点。虽说新陈代谢运动有具体的理论宣言但模式单一,参与其中的设计师都有各自偏好和发展。同是新陈代谢主义维护者的矶崎新认为“未来的城市就是废墟”,在1960年为日本东京新宿地区设想的“空中城市”,其城市规划外表看起来更像是巨大斗拱样式,是一种大胆的、纯粹形式主义的畅想预言。矶崎新提出,事物从开始到结束这种简单的直线型变化方式是欧洲的、西方的概念,东方的概念则认为事物消失还会再生,所以“废墟”既是消亡也是再生。如日本的伊势神宫,通过设定两处对等的场地和建筑材料的使用周期,以20年更迭的形式,在两处相同场地中的另一片场地中复原以前场地的建筑形式。经历了近1 400年的不断变迁与重生,以现代的目光再去评判它,既可以说是旧建筑具体存在的消亡,又可以说是一种传统历史建筑结构的延续。在这种日本建筑传统形制的影响下,以“有机生长”为主题的新陈代谢主义的出现便更加显得有迹可循。
2.2 理论含义
新陈代谢主义反对过去把城市和建筑看成是固定的、自然净化的观点[3],认为城市就像生物体内的新陈代谢,是将能量不断吸收转化排出的动态生长的过程。建筑和城市作为有机体,新陈代谢将时间因素引进建筑和城市设计中,认为建筑与城市是有使用周期限制的,通过自主地掌握其时间周期,在原本的时间周期上不断增加相较周期更短的因素,形成以主要周期为主导,由短周期作为附加部件形式的设计体系。时间较长的周期因素为主体结构,时间较短的周期因素可以根据主体因素的需求更改或增减,以此影响和维护主体。
作为新陈代谢主义领导人的丹下健三,其设计的东京自宅和广岛和平纪念馆的空间形式,实际上就是传统建筑形式与柯布西耶设计语言的结合体。而新陈代谢主义代表建筑则是由黑川纪章设计的中银舱体大厦[4]。该建筑同样利用了路易斯·康的服务空间和被服务空间的设计理念,以2个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楼为中心,包括了楼梯间和电梯间以及各种管道设施作为服务空间。将普通的楼层以穿插的舱体形方盒代替,通过高强度螺栓将尺寸为2.7m×4.0m的舱体固定在中心的塔楼上,仅容纳了通风、睡觉、洗漱等基础起居要素。除了受到当时日本城市发展,建筑面积急剧缩小的影响,也受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航空航天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影响。大厦中心的2座大楼可以不断向上衍生,穿插的舱体也可以根据家庭生活人数的需求进行多次组装和更改。1958年,菊竹清训设计的天空住宅也是通过减少硬件,增加房屋中的可活动部分,在设计之初就设定了可承受房屋格局变化的结构和灵活的平面布局,故居住者根据使用需求可以增加或删减天空住宅的房间形式,在时间上实现建筑的“生长性”,这样的设计使建筑能够在原本的物质基础上不断发展。
3 新陈代谢运动发展后期影响
新陈代谢主义倡导者所建议的是非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和城市结构,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尝试去猜测未来将会怎么样,而是应该为哪些无法预测的作好准备”[5]。新陈代谢理论虽然起始的初衷是肯定事物的变化以及有关各种元素的不同生命周期,但设计者对建筑或城市组成部分的自我限定又与其推崇的“生长性”形成冲突。该理论影响下的建筑虽然受到相应的工业技术和材料的影响,呈向前发展的趋势,但永久性的基础和转瞬变化的建筑建设依旧对立,并且在后期的发展中过于商业化和对未来数字时代的预判错误,导致这时期大部分建筑都被拆除。上述讨论的建筑和城市规划方式是一种巨构的设计形式,巨构即自上而下的综合体,具有线性发展和序列化组织的特征。槙文彦设计的东京代官山居住综合体,从1969年始建第一期,直至1998年的第七期,都通过从局部到整体的设计方法,利用建筑与建筑之间模糊的开放性空间,增加社会场所,通过“人居”视角将建筑室内室外相互联系,将独立建筑本身的历史文化脉络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在当地文化和人居习惯的引导下,上述社区建筑发展是具有承接性、延续性。槙文彦作为新陈代谢论的倡导者之一则提出了自下而上、完整有机的人性化城市系统设想,同是对城市与建筑设计“生长性”的诠释,却有不同的解读。
郑州郑东新区规划是黑川纪章在20世纪80年代将新城代谢主义与共生思想结合后的作品[6]。经过新陈代谢运动后,黑川纪章综合并发展了早期的设计理念,提出了共生思想[7]。在新陈代谢运动中,他的设计作品体现了异质文化的共生、人与技术的共生、整体与部分的共生。在郑东新区的规划中,他又强调了内部与外部的共生、历史与未来的共生,以及人与自然的共生。利用生物学相关概念,郑东新区规划延续了早期新陈代谢理论,但新区规划重视城市的历史延续性和生态保护,根据使用功能清晰界定,建筑组团式发展,各功能分区又通过绿道、湖水等室外空间相互联系,以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新陈代谢运动的最终结果即便是失败,但也没有影响到人们对它具有积极意义一面的肯定。
在新陈代谢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1960—1970年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艰难中挣扎的一段历程。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不可避免地受到斯大林主义的艺术方法的影响[8]。在建筑领域,苏联并没有超越简单的产业主义和功能主义,并且,赫鲁晓夫为了去除斯大林主义的神话色彩,反对早期俄国前卫艺术的形式主义,上述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深深影响了新中国同时代建筑风格的形成,中国的近当代建筑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停滞发展许久。中国早年的城市规划也受到了《雅典宪章》和柯布西耶《光辉城市》的影响[9]。1933年的《雅典宪章》定义了现代城市“居住、工作、交通与休闲”四大功能分类,这种规划原则在“二战”之后百废俱兴的欧洲迅速成为指导性纲领。早期中国城市也就此形成了能够满足其中每个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机械化体系。
4 结语
新陈代谢派实际上就是致力于重工业化的纯粹形式表现,将建筑与城市拟作有机体的同时,利用技术手段适应以变化为常态的环境,但正是适应性和流动性的核心思想证明了新陈代谢主义的短暂。不论是丹下健三的都市轴理论、矶崎新的“未来城市就是废墟”,还是黑川纪章的共生理论,即使是在单一宣言的运动模式之下,都是各有特点的现代主义本土化试验。城市规划理论中新陈代谢派超前的预估并不适应未来的发展,建筑的生物性使用周期若无法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也将遭遇淘汰。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现代主义尝试与铺垫,才将日本后现代主义的设计引向独具传统和人文特色的发展。在经济飞速发展、民生稳定的当下,将传统哲学、构筑元素与当代设计大胆结合是未来创造力的体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