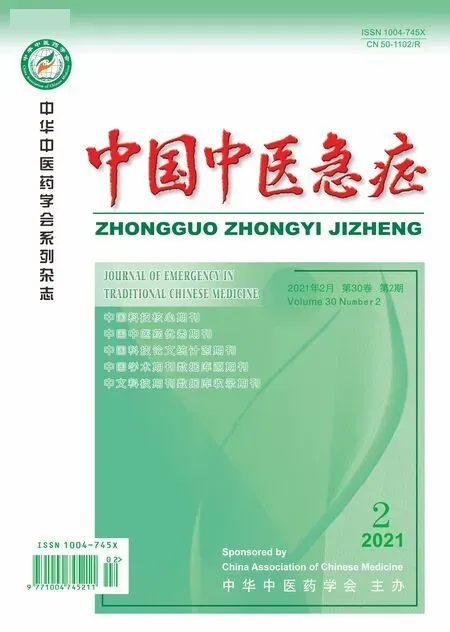“风毒”立论治疗吉兰-巴雷综合征∗
2021-03-28刘涌涛石鉴泉石志超
王 达 刘涌涛 张 洋 石鉴泉 石志超
(1.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中医医院,辽宁 大连 116100;2.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辽宁大连 116000;3.石志超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辽宁 大连 116000;4.辽宁省大连市中医医院,辽宁 大连116013)
吉兰-巴雷综合征(GBS)又称急性炎症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病,表现为急性对称性弛缓性肢体瘫痪,严重可累及肋间肌和膈肌导致呼吸麻痹死亡,少数患者遗留持久的神经功能障碍,是神经内科常见的临床危重急症。可以归属于中医学“痿证”范畴。本章主要讨论中医以“风毒”论治痿证,对其病因病机的认识和临床体会,主张病证结合,衷中参西,标本兼顾,可以拓展临床痿证辨证的新思路。
1 中西医治疗方式及其缺点
GBS又称急性炎症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病,一组急性起病的自身免疫性周围神经病,主要累及神经根、周围神经甚至颅神经,以四肢对称性无力,反射减退或消失为主要临床表现。病理改变是由于病原体的某些组分与周围神经髓鞘的某些组分相似,机体免疫系统发生了错误识别,产生自身免疫性T细胞和自身抗体,针对周围神经组分发生免疫应答,引起周围神经髓鞘脱失。并且周围神经组织中小血管周围淋巴细胞侵润与巨噬细胞浸润,神经纤维出现节段性脱髓鞘和轴突变性,主要损害多数脊神经根和周围神经,也常累及脑神经。GBS主要特点:脑脊液检查见蛋白-细胞分离特征;神经电生理则表现为周围神经传导速度减慢,传导阻滞和波形离散。金标准为病理诊断,包括有髓鞘纤维多灶性脱髓鞘炎性细胞浸润等。临床主要表现为:急性四肢远端对称性无力,很快加重并向近端发展,颅神经可受累,甚至为首发症状,可合并心动过速、自汗、血压异常等自主神经功能障碍,严重可累及肋间肌和膈肌导致呼吸麻痹,死因主要为呼吸功能不全、肺部感染、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和心脏骤停,死亡率在3%~7%。发病后6个月仍有20%GBS患者在无辅助下仍不能走动,成人患者常遗留持久的神经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日常活动和生活质量。
临床常见的西医治疗包含多学科的医疗照顾和免疫治疗(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及糖皮质激素治疗等),虽然能够有效抑制免疫反应,同时清除致病因子,预防疾病持续发展,但部分患者长时间治疗后可能产生一定局限性,甚至增加并发症发生率,提升对患者的伤害,同时延长康复时长。随后中医技术快速发展,中医学认为本病归于“痿证”范畴,《素问玄机原病式·五运主病》云“痿,谓手足痿弱,无力以运行也”[1]。痿证指肢体筋脉弛缓、软弱无力,不能随意运动或伴有肌肉萎缩的一种病证,临床以下肢痿弱常见,亦称痿躄。中医学认为痿证总以虚为本,以起病急、发展快归属于感受燥热毒邪或湿热浸淫;起病与发展较慢归属于脾胃肝肾亏虚,久病入络。另寒邪也可致萎,魏荔彤云“有冷之萎,如霜杀之则干矣”。《素问·痿论篇》提出“治痿独取阳明”成为临床治疗痿证的重要原则,即补益后天方法。“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利,故足痿不用也”[2]。人体全身的肌肉、筋脉都需要脾胃所运化的水谷精微来营养,肺热伤津,耗灼胃液,胃火清则肺金肃,也是独取阳明的临床体现,故有“五痿皆由肺热生,阳明无病不能成”之说[3]。此外《素问·生气通天论》又有“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朱丹溪亦提出“泻南方、补北方”[2],清热利湿和清热滋肾也为治痿常用大法。但相关报道中曾指出,GBS除少数患者发病前1~3周有发热、呼吸道、胃肠道等前驱感染史,或劳累、受凉、创伤、外科手术等非特异诱因,大多仅有上感病史且无发热又无药物接触史,甚至仅仅有一过性尿、便障碍为主要症状,亦无他症。因此中医临床以肺热、湿热、脾虚、肝肾不足等辨证论治,难免牵强附会,削足适履,疗效大都不尽人意。
2 “风毒”立论治疗
2.1 “风毒”病机与用药原则
笔者认为此类疾病的直接致病因素为风邪挟毒外袭、风邪内蕴郁滞成毒。风毒瘀浊胶结于肺更能反映其病理实质,更能反映其病性。“盖六气之中惟风能全兼五气”,风寒、风火、风湿、风温、风燥之邪挟毒侵袭于肺,多为本病发生的诱因,是为外因[4]。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卷四》指出“肺位居最高,受脏腑上朝之清气,秉清肃之体,性主乎降。又为娇脏,不耐邪侵,六淫之气一有所著,即能致病。其性恶寒、恶热、恶燥、恶湿,最畏风火。邪著则失其清肃,降令遂痹塞不通爽矣”。且“肺主百脉,为病最多,肺与大肠相表里,又与膀胱通气化,故二便之通闭,肺实有关系焉”,临证可见尿便障碍,亦是临床提壶揭盖治法机理[4]。“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不足风邪易袭,不能驱邪外出,是为内因。
《素问·太阴阳明论》曰“伤于风者,上先受之”,风为阳邪善行而数变为百病之长,易袭阳位[2]。邪毒多依附于风而侵袭肺表,或内蕴久滞成风毒,郁而发热。《灵枢·经脉篇》云“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胃肠道感冒亦可责之肺受风毒所致[5]。方星岩说“肺为清虚之脏,喜通利,恶壅塞,毫发不可干之”。肺叶娇嫩,易被邪侵[6]。程国彭《医学心悟》曰“且肺为娇脏,攻击之剂,既不任受,而外主皮毛,最易受邪,不行表散则邪气留连而不解”。肺为华盖,主皮毛,主宣发肃降,朝百脉,与他脏关系密切。肺伤则肝木无制约,木无制就会反侮土,脾土不足则后天之精无以化源,肾气不能充盈[7]。肾水无土承制,水无制就会泛滥克火,心火不能下交肾水,肾水则不能独化;心火无肾水制约,又火旺灼金,肺伤亦甚。可见风毒伤肺在本病的发生举足轻重。风毒侵袭人体,损伤正气,宣发失职,不能将脾所输津液和水谷精微布散全身,外达于皮毛;肃降失常,不能将肺吸入清气和水谷精微向下布散。肺为水上之源,肾为主水之脏。金水相生,经络上密切相关,肺通调水道失职水液代谢失常,肾精不能蒸腾气化致津液代谢障碍。肺主降而肝主升,肺降不及则肝升太过,相火上亢下劫肾阴,水不涵木筋失所养;兼肝失条达疏泄,气机郁滞导致津液输布障碍。肺主气心主血,肺气不足不能助心行血致津血运行失常。致此五脏不能润泽,四肢筋脉、肌肉失养而弛纵,不能束骨而利关节,发为痿证。
中医上关于痿病辨证要点包含以下几点,其中辨虚实中起病较急,且病情发展较为迅速,患者通常肢体力弱,拘急麻木,肌肉萎缩现象不明显,可判定成实证;而起病较为缓慢,且呈现不断加重现象,通常患者病程较长,肢体弛缓,肌肉萎缩显著,可判定成虚症。另外辨脏腑发生是在热病过程中,或者热病后,患者伴有咳嗽咽干现象,其病变则在肺部;而患者面色萎黄不华,食少便溏,其病变在于脾胃;而起病缓慢,月经不调,腰脊酸软,遗精耳鸣,其病变则处于肝肾。但既往治疗中不论选方用药,而利用针灸选穴,增加对脾胃调理的重视程度,但随着医疗技术的改进,临床应给予辨证论治,其中实邪突出者,应提供祛瘀、清热及化湿方式达到以祛邪实目的;而正虚突出者,可提供滋补肝肾、健脾褴气方式来恢复止气;虚实夹杂者则扶正与祛邪兼顾。另外在邪实祛除后,应进行补虚养脏,调和气血,濡养筋脉的治疗。近年来随着中医水平的不断提升,临床经过分证论治后发现,针对肺热津伤证,其身热退净、食欲衰退、口燥咽干较为严重者,可判定为肺胃阴伤,应选择益胃汤加薏苡仁、山药、谷芽等,达到益胃生津的功效,切不可使用苦寒燥湿辛温之品。针对湿热浸淫证,主要是由凶湿热浸淫引起,不可急于填补,预防助湿。除湿之外还应兼施清养,不可使用辛温苦燥之品,一旦发现患者湿热伤阴后,可转清滋善后。针对脾胃虚弱证,实发在中焦,若出现食滞后,可给予谷麦芽、山楂、神曲等。针对肝肾亏损证,应以补肾清热为治疗原则。针对瘀阻络脉证,尤其是瘀血较重者,可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入地龙、水蛭、蜈蚣、全蝎等虫类,已达到搜剔经络、痛经活络的作用。随后在临床辨治过程中,考虑GBS发病及病机衍化皆以风邪挟毒侵袭肺表,或正气虚弱不能逐风邪于外,内蕴成风毒最为得当,故以“风毒”立论,而其治疗原则应以搜风剔毒,滋补肝肾,活血通络为主,例如桑寄生、黄芪、柴胡、牛膝、桑枝、地龙等中药均可运用其中,达到发散邪热、通经活络、益气固表、疏肝解郁的作用。
2.2 临床用药对中医辨证和治疗的影响
2.2.1 激素类药物对本病的影响 激素类药物按中医理论分析为补阳药物的范畴,此类药物久用必有助火升阳、耗竭肺肾阴液之弊。故在补阳的同时必须考虑到阳损及阴的一面,治疗必用养阴之品。石师认为病患久用激素,阴阳失调,应补阴配阳,既减少激素之燥热不良反应,又为激素替代疗法,缓撤激素,应时时以顾护阴精为念。
2.2.2 β受体阻滞剂对本病脉证的影响 β受体阻滞剂主要治疗高血压、心绞痛及心律失常。抗心律失常基本药理是阻滞β受体可以使心肌收缩力下降,收缩速度以及传导速度减慢,并且通过阻止儿茶酚对窦房结、心房起搏点及浦肯野纤维4期自发除极,减慢房室结及浦肯纤维传导速度纠正快速室上性、室性心律失常。此类药物按中医理论分析可归为收敛药物的范畴,此类药物有收敛气机作用,减弱心脏鼓动气血力量,必见有沉迟、沉缓等表现为虚寒脉象。故在辨证尤其脉证方面可以舍脉从证。
2.2.3 宣肺搜风剔毒之品的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注意 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上讲,本病发病机理主要是感染后自身免疫性疾病,与机体的免疫反应、淋巴细胞浸润、炎症反应、髓鞘脱失等密切有关。中药宣肺疏风剔毒之品大都具有调节免疫、抗变态反应、抗过敏之功。从“风毒”立论治疗,“风毒”辨治亦当贯彻始终。故选用宣肺搜风剔毒的药物如:桑寄生、地龙、蝉蜕、僵蚕、乌梢蛇、蛇蜕、桑枝、牛蒡子等之品,一者取其走窜之性搜风剔毒,二者又有取虫药之以毒攻毒之意,每获良效。痿证多虚实夹杂互见,兼夹之证不可等闲视之,“至于活血化瘀通络之法,近代医家每以久病入络立论,而实质是风毒胶结,新病即夹瘀,不单纯久病而入络”,必辅以活血化瘀通络等法及时救治免成痼疾。然搜风剔毒、化瘀通络之法,终属正治八法中之“消”法范畴,正治当以“补”法为主,搜风剔毒、化瘀通络之药可用,只宜当作必不可少的治标之品贯穿病程始终。祛邪而不犯无过之地,刻刻以顾护正气为念[8]。
3 病案举隅
患某,男性,80岁。2019年5月20日初诊。患者既往高血压病、冠心病、心律失常房颤、心衰病史。于1个月前因突发排尿困难予导尿后现双手麻木,左上肢疼痛,逐渐出现四肢麻木无力疼痛剧烈,于某医院住院治疗,确诊为“GBS,急性炎症性脱髓鞘性周围神经病”。予糖皮质激素、免疫球蛋白、营养神经、抗凝,扩冠、利尿、β受体阻滞剂稳定心室率治疗后,能自行排尿,四诊无力症状略改善,麻木疼痛症状略减轻,出院后仍卧床不能翻身活动。入院前3 d患者又复感风寒后出现四肢麻木无力疼痛加重,呼吸困难,为求中医系统治疗遂来我院。入院神经系统查体:神清,言语流利,颅神级未见异常。左侧上肢肌力2级,右侧上肢肌力3-级,双侧下肢肌力2级。四肢痛觉减退,腱反射未引出。西医予抗凝、降压、降糖、减轻心脏负荷稳定心室率(酒石酸美托洛尔50 mg/片,每次50 mg,每日2次口服)、糖皮质激素(强的松5 mg/片,每周减5 mg)、营养神经(维生素B1100 mg/支、维生素B12500 mg/支,每日1次,各1支肌注)对症治疗。刻下:精神亢奋,颜面潮红,偶有发热(37.4℃),口干不欲饮,胸窒如塞,四肢麻木无力,左肩背疼痛,稍动即疼痛剧烈难忍,纳寐可,大便干。舌红苔薄白少津,舌下络脉瘀紫,脉结代沉迟无力。诊断:痿证(GBS急性期)。辨证:风毒瘀滞,肝肾阴虚,瘀血阻络。治法:搜风剔毒,滋补肝肾,活血通络。方药:桑寄生30 g,桑枝6 g,地龙15 g,丹参20 g,柴胡6 g,牛膝 15 g,桃仁15 g,炒白术30 g,黄芪 20 g,黄柏 15 g,当归 15 g,白芍 15 g,生地黄 15 g,熟地黄15 g,龟板10 g,川芎6 g,生杜仲15 g,鸡血藤30 g,炙甘草15 g。7剂,每日1剂,水煎早晚温服。二诊2019年5月27日:麻木无力症状改善,口和,疼痛缓解,纳少,时有发作性胸闷气短,五心烦热,二便调。舌淡红苔薄白,脉结代迟缓。去黄芪加知母10 g,党参15 g。7剂,日1剂,水煎早晚温服。汤药未尽,患者能自行站立,可缓步慢走,限于体力不能步远。三诊2019年6月3日:患者疼痛症状基本消失,四肢麻木无力症状明显改善。去党参、黄柏,加生山药30 g,桃仁6 g。14剂,出院带药继服。2月余后,患者可以杖助步独自行动。
按语:治病必求其本,治疗危重疑难,更当辨证求因求其本。诊治之时,“审查病机,勿失病机”,以法立方。“从毒立论,顽疾皆由毒作祟”治疗本病[8]。方中桑寄生、桑枝、地龙宣肺搜风剔毒,调节免疫、抗过敏、抗变态反应,地龙性寒解诸热疾,下行能利小便兼通经络。所谓补其肺者益其气,予黄芪益气固表,从太阴托里之邪毒外出,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四物补血活血止痛;风之为患,肝木主之,两相感召,同气相求,归、芍、芎和肝血,柔肝降逆,先安未受邪之地;补其肾者益其精,二地、龟板、杜仲、黄柏补肾填精,滋阴潜阳,引浮阳龙火归宅,金水相生,肺金得润,其令可行,能固其卫气,阳气外达;柴胡者,气质轻清,苦味最薄,可和解表里,发散邪热,亦能疏肝解郁,调畅情志,从少阳领邪外出;《甲乙经》曰“夫胆者,中精之腑,五脏取决于胆”[9],正邪相争必取少阳,少阳为枢机,斡旋上下,攘外安内,能恢复中轴升降之职,使清阳自升,浊阴能降,阴阳调和,液道运行;柴胡、牛膝法血府逐瘀汤之义,升降气机,活血通络,丹参活血养血凉血,安神止痛,一味丹参功同四物;《日华子》云“通利关节”[10],现代药理表明能抗动脉粥样硬化,降低心肌耗氧量,增加冠脉流量[11],改善泵血功能;藤类入络,鸡血藤行血补血,舒筋活络止痛;桃仁流通凝滞气血止痛;使瘀祛新生;另桑枝、牛膝引药入四肢。最后入山药者,补益肺脾肾三脏,概因其不寒不热,不燥不滑,有补虚祛风之长,意徐徐缓图之,谓必得正气至后风气可去也;“土常不足,最无有余”[12],术、草和胃气而健脾,补益后天,助精气化源,培土生金,调和诸药;先后两天同补,诸药相辅相成而建功。方中理法方药直中病机,面面俱到,药证和拍,故能获效,体现了中医治病谨守病机和辨证论治奥义。故依此法辨证论治,多可获效良佳,不独此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