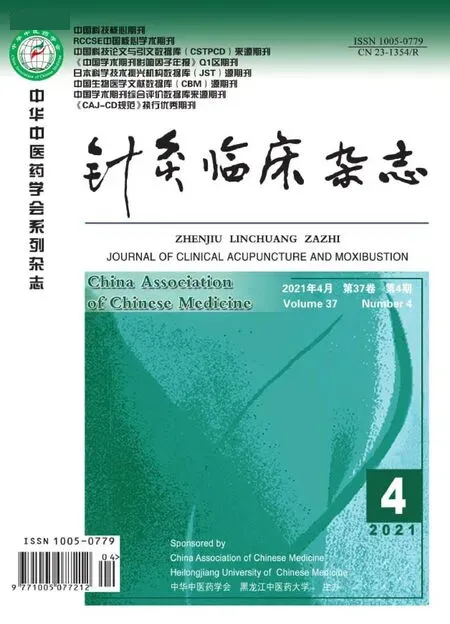针灸通过调控微生物-肠-脑轴防治阿尔茨海默病的可行性分析*
2021-03-28黄重生孔立红余超超王雪松
黄重生,孔立红,余超超,王雪松,何 川
(湖北中医药大学 针灸治未病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湖北 武汉 430061)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是中枢神经退行性疾病,临床主要表现为学习记忆及认知功能障碍,其病情呈进行性变化,晚期患者卧床不起,需专人陪护[1]。研究数据表明,全球AD患者数量预计在本世纪中叶将达到1.315亿[2],因此导致的全球医疗资源及经济成本预计将高达9.12万亿美元[3]。现阶段临床上对于AD并无有效治愈的药物和方法,临床常用的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和天冬氨酸受体抑制剂也仅仅是改善AD的症状,效果十分有限[4]。AD的主要病理特征是β淀粉样蛋白(Aβ)沉积形成老年斑和过度磷酸化的tau蛋白形成神经原纤维缠结以及脑内弥漫性慢性炎症[1]。有研究显示,AD患者肠道微生物群会发生改变[5],而肠道微生物群会产生与中枢神经Aβ类似的细菌Aβ及可诱导神经炎症及老年斑形成的内毒素,最终通过微生物-肠-脑轴而诱发神经性炎症[6]。因此微生物-肠-脑轴可能是针灸治疗AD的作用机制之一,现论述如下。
1 微生物-肠-脑轴与AD的关系
1.1 微生物-肠-脑轴
肠脑轴(GBA)是连接脑和胃肠道的桥梁,其组成包括中枢神经系统(CNS)、自主神经系统(ANS)、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和脑肠肽[7]。肠神经系统(ENS)是胃肠道的自主神经系统,被称为人类的“第二大脑”,由迷走神经和椎前神经节支配。迷走神经属于ANS,起自脑干,向肠神经节和孤束核传入,构成CNS和ENS之间的初级双向连接,是GBA的重要组成部分[8]。迷走神经在炎症的调控中起重要作用。可通过HPA的神经内分泌途径和胆碱能抗炎通路(CAP)途径发挥抗炎效应。
人类胃肠道拥有丰富且复杂微生物种群,其数量预计超过1 000种[6]。肠道微生物的动态平衡对人类的健康极其重要。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群可通过GBA与大脑相互影响,学术界称之为“微生物-肠-脑轴”[9]。肠道微生物通过微生物-肠-脑轴影响大脑功能和行为,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参与抑郁、焦虑、疼痛和认知等方面的调节[10]。这在抑郁症、自闭症、中风与帕金森病等多种神经系统疾病中已得到证实[11]。肠道微生物群还可通过炎性小体介导脑部炎症的调控[12],一些益生菌甚至可以调节大脑中特定基因的表达以改善年龄所导致的突触可塑性降低[13]。肠道微生物群还影响胎儿的神经发育[9]。最新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与AD之间存在密切联系,AD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发生了改变[5]。
1.2 AD患者存在肠道微生物群紊乱
研究发现,AD患者与正常者相比,肠道微生物中产生丁酸盐的菌种的相对丰度较低,如丁酸弧菌属、真杆菌属和梭状芽胞杆菌属等[14]。丁酸盐是人体结肠的重要代谢物,是结肠上皮细胞重要的能量来源,有助于肠道屏障的维持,并且具有免疫调节和抗炎的特性,其比例过低会导致结肠上皮出现炎性状态[15]。研究发现AD患者肠道微生物中与AD有关联的相关菌群的丰度有所增加:如克雷伯氏菌能分泌淀粉样蛋白,可诱导AD患者产生类似淀粉样蛋白的病理性细胞毒性反应[16];如脆弱拟杆菌可产生脂多糖(LPS),导致AD的神经性炎症[17]。
一项研究分析了AD患者和非AD患者的粪便微生物基因组成,发现 AD患者微生物的丰度和多样性发生改变,双歧杆菌丰度降低,类杆菌丰度增加,并且这与AD患者脑脊液中病理性标志物的升高呈相关性[5]。Zhuang ZQ等[18]研究发现,与对照组比较,AD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组成和多样性发生改变,如放线杆菌、类杆菌、瘤胃球菌科、硒单胞菌和梭状芽孢杆菌等菌群。并且有研究发现,出现认知受损和脑淀粉样变性的AD患者肠道微生物中类杆菌的丰度较低[19]。
LPS是革兰氏阴性菌细胞壁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毒性物质,也存在于肠道微生物群中,在健康状态下,肠道屏障会阻止LPS进入血液,但如果肠道微生物群紊乱,肠上皮细胞紧密连接受损,肠通透性增加,LPS就会进入血液,引发炎症反应[20]。一项研究发现,AD患者的血液LPS水平是健康者的3倍[21]。钙保护素是白细胞释放到炎症区域的一种蛋白质,粪便钙保护素升高可作为肠道炎症的标志。Leblhuber F等[22]检测了22名AD患者的粪便,发现患者的钙保护素浓度都超过正常水平。血浆LPS和粪便钙保护素浓度升高提示AD患者肠道微生物群紊乱及肠道炎症的存在,这些结果进一步提示肠道微生物与AD可能存在密切联系。
1.3 肠道微生物群可能是AD脑内Aβ的来源之一
Aβ沉积形成老年斑是AD的主要病理特征之一[1]。正常生理状态下,由血管内皮细胞和星形细胞组成的血脑屏障(BBB)会将中枢神经系统与血源性大分子、病原体和有害蛋白隔开,以保护脑组织[23]。而由迷走神经所构成的肠脑连接可绕过血脑屏障的保护将大分子物质从肠道逆向运输到大脑。这在动物实验中已得到验证,在该实验动物模型中,作为帕金森病标志物路易小体的蛋白成分α-突触核蛋白(α-SYN)通过迷走神经轴突从肠道运输到脑干背侧运动核[24]。迷走神经是微生物-肠-脑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为异常的潜在致病蛋白从肠道传递到大脑提供了证据。
肠道微生物可产生大量Aβ,细菌之间通过分泌的Aβ相互结合形成生物膜,以抵抗物理、免疫等因素造成的伤害[25]。细菌Aβ与人类中枢神经系统Aβ在一级结构上有所不同,但在三级结构上类似,也可激活小胶质细胞诱导神经炎性反应[26-27],并且被细菌Aβ激活过的小胶质细胞对大脑生理性Aβ反应更敏感[28]。细菌Aβ还可能会刺激肠道激活免疫系统,增强对内源性Aβ的免疫反应,加重神经炎性反应[26]。并且细菌淀粉样蛋白还表现出朊蛋白传播特征,即可以在细胞间扩散传播,并可诱导正常蛋白转变为不可溶性病变蛋白,最终聚集而引发疾病[27]。结合迷走神经的运输功能,这预示着肠道微生物可以将Aβ传输到中枢神经系统。因此,肠道微生物可能是AD脑内病理性Aβ的来源之一。
1.4 肠道微生物及其衍生物LPS可能是导致AD神经炎性反应的因素之一
Aβ斑块诱导小胶质细胞、星形胶质细胞和补体激活所导致的神经性炎症是AD重要的病理表现[29]。在AD前期,激活的小胶质细胞会促进低浓度Aβ的清除,但随着病程的发展,持续性高浓度的Aβ会导致小胶质细胞过度激活,加重神经炎性反应,导致神经损伤和凋亡[30]。神经炎症还会下调髓系细胞触发受体-2(TREM-2)的表达,抑制小胶质细胞的吞噬功能,进一步导致Aβ-42的积聚,加重炎性反应[31]。
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和稳定性会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一些益生菌的比例会降低,而有害菌群比例上升,这将导致老年人肠道系统受到刺激而表现为慢性低度炎症状态[32-33],而持续慢性炎症会导致肠道屏障被破坏、血液循环中促炎细胞因子和细菌衍生物的进一步增加、血脑屏障的损害和神经炎症[34]。一项研究发现,高浓度的大肠杆菌会导致大鼠脑中神经元α-SYN沉积增加、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增生增强,诱发神经元损伤和炎症[35]。而在AD患者的尸检中发现,患者血脑屏障受损,脑内出现细菌感染,这为细菌可能导致神经性炎症提供了证据[36]。由肠道微生物导诱的全身性感染会激活大脑的先天免疫系统,导致作为抗菌肽的Aβ病理性聚集,触发蛋白级联效应,而病理性聚集的Aβ反过来又会激活小胶质细胞导致中枢神经炎性反应,最终形成恶性循环[36]。
肠道微生物群产生的衍生物LPS和AD神经炎症关系密切。研究发现,将细菌LPS注入大鼠大脑第四脑室可再现AD的脑内炎症和病理特征[37],将LPS注入小鼠腹腔会导致海马区Aβ含量升高和小鼠认知功能障碍[38]。LPS不仅能促进淀粉样纤维的生成,还可以诱导更具致病性的朊蛋白样的片状淀粉样蛋白的形成[39-40]。在AD患者的海马和新皮质中已检测到LPS的存在[41],患者血浆中LPS浓度也显著高于健康人[21],患者脑中血管周围也发现了LPS与Aβ1-40/42的共定位表达,这表明细菌LPS与AD存在相关性[42]。LPS还可以激活TLR4受体,诱发小胶质细胞的活化,促进神经炎症反应[27]。
2 针灸调控微生物-肠-脑轴防治AD的可行性
2.1 理论基础
AD在中医学上属“呆病”“神呆”“健忘”等范畴,其病因多为年老体虚、七情内伤和久病耗损,基本病机为本虚标实,其本虚主要表现为肾精不足、髓海亏虚和神机失用;其标实主要表现为痰浊蒙窍、瘀阻脑络。本虚可导致痰浊、瘀血内生,因虚而致实;痰浊、瘀血等标实又会阻碍气血的化生、输布,导致本虚更甚,因实而致虚,形成恶性循环。临床上主要分为髓海不足、脾肾两虚、痰浊蒙窍、瘀血内阻和心肝火旺等5个证型。中医学强调“治病求本”,各个医家治疗AD多注重补虚。AD病机表现为髓海亏虚、神机失用,何谓神?《灵枢·平人绝谷》篇曰:“神者,水谷之精气也。” 《素问·六节藏象论》曰:“五味入口, 藏于肠胃, 味有所藏, 以养五气, 气和而生, 津液相成, 神乃自生。”都指出神与脏腑气血盛衰密切相关。脏精充足、气血旺盛,则神气充足,机能协调;脏精衰竭、气血衰败,则神气枯竭、神机失用。而益精填髓首先注重补益气血,《灵枢·五瘾津液别》曰:“五谷之精微和合而膏者, 内渗入于骨空, 补益脑髓。”历代医家治疗呆病多从补益气血、填精益神出发,重视脾胃补益后天之本的功能。临床针灸治疗AD,取穴频率排名前5 位的分别是百会、足三里、四神聪、神门和太溪[43]。足三里穴为胃经下合穴,是胃腑之气血汇聚之地,常用来调理脾胃、补益气血,脾胃健康、气血充足自然会“精神”充沛,这也支持了补益脾胃后天之本在AD治疗中的重要性。
《灵枢·经脉》记载胃足阳明之脉“循发际,至额颅”“足阳明之别……上络头项”,与脑联系十分紧密。《灵枢·动输》曰:“胃气上注于肺,其悍气上冲头者,循咽,上走空窍,循眼系,入络脑”,胃经之经气上输于脑窍,脑窍得养,则神清目明。而手阳明大肠经与胃经相表里,“从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中……上挟鼻孔”,循行至头面部,主头面、五官和神志病,与脑的联系同样紧密。因此,调理胃肠经气,维护脏腑功能,使髓海有源、清阳得升和脑窍得养对AD至关重要。
肠道微生物群定居于胃肠道,与胃肠功能相互影响。研究表明,胃肠道可通过神经系统控制肠蠕动、肠通透性和肠激素的释放,从而控制肠道微生物的密度[44]。肠道粘膜还可通过内分泌调节肠道微生物的丰度和组成,例如肠上皮细胞表达先天性免疫受体,可以释放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而肠相关淋巴组织则可通过淋巴细胞产生特异性免疫反应,而潘氏细胞则可分泌抗菌素调控细菌多样性,各组织间相互协同维持肠道微生物群的平衡[45]。胃肠功能和肠道微生物群的协调统一为针灸调节微生物-肠-脑轴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以中医理论为指导,通过针灸调理脾胃治疗AD切实可行。
2.2 针灸治疗AD疗效肯定
临床研究表明,针灸在治疗AD上有其独特优势且方法众多[46]。如王月花等[47]通过针药结合治疗AD患者后发现相比于单纯服用西药安理申,针药结合治疗总有效率高,患者多种评分量表得分显著改善。又如王以申等[48]搜集大量文献进行系统性研究表明针刺结合药物能促进AD患者认知功能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并且对于由AD引起的睡眠、情绪等相关问题针灸也都有不错的治疗效果,能有效提升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例如一项研究表明针灸对于AD脑神经受损导致的抑郁和焦虑的精神症状有明显的改善作用[49]。而且相比于口服多奈哌齐,针灸治疗AD不仅效果不错,在长期应用上也更具备优势。如有研究表明,对AD患者采用针刺治疗后,患者总体功能状态及生活能力都有明显改善,其多项评分量表得分均优于口服多奈哌齐组,并且在治疗过程中相比于药物组出现多例胃肠道不良反应,针刺组仅有少量患者出现针刺轻微出血和疼痛反应[50]。另一项研究也证明,相比于口服多奈哌齐,针刺治疗AD耐受性更强,且副作用小,这对长期治疗是很有必要的[51]。
2.3 针灸可调节微生物-肠-脑轴
针灸可以通过调节GBA来调节人体功能。研究发现,电针能降低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D-IBS)大鼠脑肠轴5-羟色胺(5-HT)和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含量,增加脑肠肽Y(NPY)含量,改善D-IBS的临床症状。5-HT和NPY是GBA、ENS的重要神经递质,二者通过影响海马、下丘脑和肠粘膜下神经节的胆碱能传递,调节应激和情绪[52]。研究还发现,电针足三里穴可激活胆碱能抗炎通路和肠胶质细胞,抑制炎症因子的分泌,促进肠上皮的修复,保护失血大鼠的肠道损伤和粘膜屏障功能[53],而胆碱抗炎通路是GBA的组成部分。一项采用静息态fMRI研究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研究发现,针刺治疗后患者的脑功能连通性发生改变,接近健康对照组,其机制可能与针刺治疗使患者脑肠轴正常化有关[54]。
针灸可以调节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和丰度。肥胖模型大鼠经电针治疗后,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逐渐接近正常小鼠[55]。电针天枢穴和足三里穴后,改善了IBS模型大鼠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和组成,降低了变形杆菌、梭杆菌等与IBS相关的有害菌群丰度[56]。司原成等[57]应用健脾益气针法治疗肥胖模型大鼠后,纠正了大鼠肠道微生物群的失衡状态,改善了大鼠肥胖程度及脑组织和肠道的炎症。李湘力等[58]发现,针刺可使IBS-D模型大鼠肠道微生物群的α多样性上调,纠正大鼠的肠道微生物群紊乱。吴生兵等[59]用电针治疗心肌缺血大鼠,使大鼠肠道微生物中厚壁菌门的丰度上升,拟杆菌门、变形菌门、梭杆菌门和放线菌门等有害菌群丰度下降。临床研究也表明,针灸可提高IBS患者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等益生菌的数量,降低大肠杆菌数量,改善双歧杆菌/大肠杆菌比值,提升肠道益生菌定植力[60-61]。这些研究表明,针灸调节肠道微生物激活肠-脑轴以治疗脑与肠的一些疾病具备一定可行性。
3 小结
临床众多研究表明,针灸可改善AD的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并且副作用小、耐受性强,因此针灸作为AD的补充疗法值得研究和推广。鉴于AD机制尚未完全阐明,针灸与之相关的研究也陷入瓶颈,微生物-肠-脑轴的发现可能为研究针灸治疗AD的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群可能是AD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分泌的淀粉样蛋白或可通过脑肠轴传输到大脑,这可能是AD病理性Aβ的来源之一,并且细菌及其衍生物可刺激免疫细胞,上调炎症因子,破坏血脑屏障,激活小胶质细胞,这可能是导致AD神经炎性反应的关键因素之一。研究发现,AD患者肠道微生物群发生紊乱,菌群多样性降低,益生菌丰度下降,有害细菌丰度升高,而针灸可以调节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和丰度,纠正肠道微生物群紊乱状态,激活微生物-肠-脑轴。因此,推测针灸或许能通过调节微生物-肠-脑轴,下调炎症因子,保护血脑屏障,减少大脑淀粉样蛋白含量,改善大脑慢性炎症,从而改善AD患者的临床症状。
综上,本研究分析并探讨了针灸、微生物-肠-脑轴和AD三者的关系,以期为研究针灸防治AD的具体机制提供思路,但受相关研究质量及相关机制不明确的限制,因此本研究还有不足之处,如:①肠道微生物所产生的细菌性Aβ与AD病理性Aβ具体关系有待确定;②AD神经性炎症与肠道微生物及其衍生物LPS之间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也有待研究;③针灸治疗AD的临床研究纳入及评价标准多样,质量参差不齐。因此,更加深入对微生物-肠-脑轴的研究,加强针灸治疗AD 研究的标准化,提高统一性和实验设计的专业性,扩大临床多中心研究的样本量,建立更客观有效的评价标准,这对研究针灸治疗AD的具体作用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微生物-肠-脑轴在治疗AD中的作用以及针灸对其具体的调控机制终将明了,从而为针灸临床防治AD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