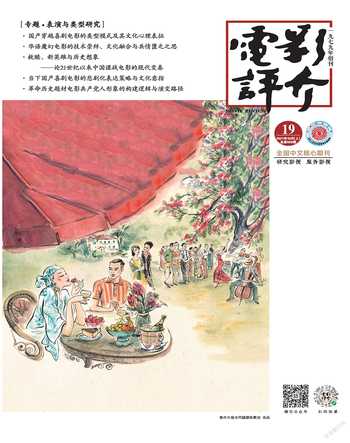结构、观念与重述: 由《盛夏未来》观照中国青春片新语态
2021-03-27徐江涛
徐江涛
自21世纪一批引起观众热议的青春片上映以来,青春片成为大陆电影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中文化主题的探究,也成为电影研究与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内容。2021年7月底上映的《盛夏未来》(陈正道,2021)以两名高中生为主要人物,在呈现青春故事的同时展现两名高中生背后的文化结构与社会热点问题。
一、青春故事后的文化结构
在中国大陆乃至整个华语青春电影谱系中,《盛夏未来》都是其中普通而稍显特殊的一部。普通之处在于,《盛夏未来》以少男少女的成长成熟故事为基本线索,承袭了青春片中青春有遗憾(恋爱的遗憾、考试的遗憾)但青春无悔(年轻人对于自由不计代价的追求、毫无保留地相互帮助等)的情感基调;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部拍给“90后”乃至“00后”等“数码原住民”的青春电影,它并不站在《夏洛特烦恼》(闫非、彭大魔,2015),《乘风破浪》(韩寒,2017),《后来的我们》(刘若英,2018)等重返青春、追忆青春的中年人视角感慨青春不再,也不像《送你一朵小红花》(韩延,2020)和《少年的你》(曾国祥,2019)一样以身心病痛、校园霸凌事件等先在于故事结构与人物角色之外的矛盾点推动叙事的戏剧性,令电影整体向成熟的类型化方向发展。在影片的整体故事与风格基调上,《盛夏未来》沿袭了导演在“精神前作”《盛夏光年》(陈正道,2006)的基本风格,以平淡朴实的日常叙事承载了感情与精力充沛的青春故事,虽然几乎没有刻意营造的喜剧包袱与催泪点,也没有颇具戏剧性的小概率事件,甚至男女主角在校园中都是平凡的,却在缓缓流淌的时间与情绪之流中给国产青春片带来了不一样的风格色彩。《盛夏未来》讲述即将高考的女孩陈辰意外发现妈妈与卖水果的王叔叔的“外遇”而心情低落,她发现父母早已离婚,只是为了不影响自己高考才继续同居。陈辰为了保护三口之家的存续在高考时交白卷,并谎称自己与校园网红郑宇星早恋才影响了成绩,却不料在复读班中真正对郑宇星产生了感情。《盛夏未来》中,观众不仅能从陈辰与郑宇星像朋友又像情侣的有趣互动中重新体会青春的乐趣和悲伤,而且能从陈辰父母对待情感关系的副线中,站在成人的角度对少年情感的追寻进行有趣的佐证与补充。这样一来,影片就在内容层面上饱含多重内涵:既有对青春少年们真实情感的关注,对当下性别议题的探索,对应试教育得失的微妙辩证关系,又包含两个互相辨认为“同类”的灵魂是如何在未解的青春里携手面对成长的种种难题,勇敢地面对真实的自己,同时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见证彼此的成长和蜕变。影片从陈辰与郑宇星相识相知的感情入手,拿捏得当地展示了当下青少年在家庭中与父母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学校中与老师“亦敌亦友”的师生感情,以及对LIVE音乐、摇滚乐队、社交网络、新媒体等新兴事物的关联,从而将电影主题从“青春”或“青春期人群”有效辐射到家庭与社会。片尾处电音节上,郑宇星和陈辰的台词与动作,更是令影片的故事不再拘泥于二人之间的暧昧感情,有效升华了影片的整体立意。
与同题材、同基调的《盛夏光年》相比,《盛夏未来》同样是在简单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反复渲染角色感情的,每个片段都欲言又止。这样的写法令陈正道的两部青春片将青年人的恋爱故事引向更广泛的文化结构。《盛夏未来》中,朝夕相处的陈辰与郑宇星同样含含混混地享受着以“友情”为名的青春时光,他们在上课时候偷偷聊天,放学之后一起学习,分享同一个耳机中的歌曲,在闲暇时间一起散步、一起吃饭、一起唱歌、一起过生日,一切都是鲜活而简单青春片“类型”;《盛夏光年》中的慧嘉、正行和守恒也是一样,在阳光照进矮墙,小雨、斑驳的校舍、篮球场的器材屋中,“青春”主题在电影美术风格中的描叙分外凸显。尽管对青年主体的塑造与对青春想象的呈现在早期电影中已有体现,但战后的西方电影却首次以青春作为叙事主题与影片美术基调,使得青春电影成了一个明确的、以青少年为主角、以高度年轻化的观众为对象的商业片类型。“战后好莱坞电影的‘青春化’连接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潮流,这一阶段的青春片所呈现出的反叛、对抗与迷茫为世界电影史意义上的青春片划定了一个基本坐标系,从国别电影的发展来看,青春片不仅意味着前面所说的演员和观众的‘青春(吸引力)’,更体现为创作者的青春(反叛与挑战),其在题材和电影语言上的突破可能会形成一种电影新浪潮。”[1]《盛夏未来》片尾处,慧嘉、正行和守恒三人之间同样充满无法宣诸于口的感情。海边滚动着躁动不安的雷声,对峙的三人之间弥漫着山雨欲来风满楼般的沉默,最后守恒宣泄般地喊出“康正行,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宣告了这段感情的无疾而终。《盛夏光年》则以高考与表白这两个“事件”标记着“青春”的终结:高考意味着分离,表白意味着少年在性别上成为成熟的青年,陈辰与郑宇星成为他们让彼此开始正视自己心意的契机。随着故事平缓地推进,故事中的“年轻人”到了不得不告别青春故事,为了进入更广阔的未来做出选择的时候。其选择的结局,就是从青春故事走向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结构,一如陈辰终于理解了父母的苦衷,同意了母亲与王叔叔的恋爱,并重新认识了已经身为知名DJ的郑宇星。与《夏洛特烦恼》《乘风破浪》等影片相比,《盛夏光年》与《盛夏未来》的语时与语态是更为当下化的,男女主角在当下已经体会到长大成人过程中的遗憾与怅惘;与《盛夏光年》相比,《盛夏未来》更加重视当下文化语境的影响。短视频平台上的网红在同龄人中格外受到欢迎、靠对音乐的喜好寻找“同类”,都是当下“00后”青少年群体中司空见惯的生存习惯与生存方式。《盛夏未来》将这些元素纳入叙事,不仅更为贴近当下主流观众的现实生活,而且成功在文化结构的意义上实现了青春片的有效重写。
二、青春与“青春片”观念的倒错与更新
青春片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意义的片种,当我们对其加以讨论时,不能在空泛的扁平历史背景下谈论相关议题,必须圈定一个确定的文化、伦理与历史范围,赋予青春片以具体的年代背景。从宣扬将青春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青春之歌》(崔嵬,1959)开始,无论是具有“伤痕文学”特性与建设新时代热情的《青春祭》(张暖忻,1985),还是受到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在时代剧变中显示出困惑与迷茫的《顽主》(米家山,1989)与《十七岁的单车》(王小帅,2001),中国的青春电影始终勇敢地触及与表达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历程。它们不仅从独特的批判与反思角度发掘了一代代中国人多年来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而且提供了一种很优美而独特的形式来表现这些独特的内容。不同的时代思想与青春经验具有不同的特性,每一部青春片都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范围与思想观念,因此,“青春片”这一语词的所指也是非常具体的。中国当下的青春片首先是有着商业特性的类型片,有着特定的叙事成规与对特定市场的吸引。以《盛夏未来》为例,这部影片采用了一种淡淡的忧伤情感基调,在当下时空中显示出从挥洒青春激情到思念与怀旧的轉变;叙事空间从校园空间向外辐射,涉及主人公的家庭、与主人公爱好相关的场所如音乐节等。从2013年开始,《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夏洛特烦恼》《乘风破浪》《后来的我们》等影片在院线相继亮相,“青春片”成为新的文化议题与阅读症候。“青春”这一话题似乎总是指向令人向往的赤子之心、年轻人不计回报的付出以及对光明前途的美好向往。反过来看,这一意象也作为一种空洞的能指被不同时代的电影创作者反复构成和填充,在看似相近的大光圈摄影、近距离面部特写、对光线与环境的考究摄影下,是“青春”概念本身的反复倒错。这些同义反复的叙述圆圈构成一系列关于“生命”“爱”“幸福”“唯美”“浪漫”“时代”“新”“未来”等所指的、空洞的能指符号,“因其空洞而激动人心,因其空洞而获得强大的解释力量,并最终成就一个完满的现代意识形态神话”[2]。那么,关于“青春”的话题在何种意义上在这些超高票房的商业片中发挥作用,这些被称为“青春片”的电影又具有怎样的电影形式、叙述方法和电影观念?
学理上的“青春期”与“少年”“儿童”等概念一样,都是近代以来社会文化结构变形产生出的、关于“人”的话语。“青春期”这一概念在美国发展心理学中最早被提出时,描绘的是13~17岁之间人的心理发生迅速成长变化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全球范围内的青年反文化运动与青年主导的民权运动,在肯尼迪政府的推动下被全面赋予了叛逆、左翼、激进等意味,“青春期”“代沟”等概念也真正借由大众文化等渠道在全球社会中流行起来[3]。可以说,所有青春电影都遥远地呼应着“青春”最早产生的文化语境,这些青春电影在大众文化的回收与融合中不断促使观念的叛逆、更改、倒错与更新,一边以电影商业市场所定义的“青春吸引力”与“青春反叛性”生出诸多可能存在脱离现实问题的景观,一边保持着愤怒、反叛与反思的色彩。即使是看似平缓发展的《盛夏未来》,在情绪色彩上也依然抱有反叛与愤怒的情绪。无论是陈辰离经叛道、以交白卷对抗家庭分裂的举动,还是颇具自由色彩的、在同学们起哄和围观下的奔跑、上课时一人一只耳机偷偷捂着耳朵听歌“开小差”、在高考前说走就走到海南听电音节的旅行,都充满了青少年亚文化中仪式抵抗的色彩;陈辰与郑宇星通过抖音平台“秀恩爱”、郑宇星将两人喜欢的歌做成Remix版本,在DJ台上作为定制的生日礼物送给陈辰,都在高考将近的背景前显得离经叛道、随心所欲。而电影中父母和班主任的存在,仿佛作为一切现实主义、击垮理想的反面力量站在主人公一切行动的对面。“美国青春片从不是孤立的电影类型,而是在生产、制作、流通、发行及接受各方面都依托其他类型片及其电影史的书写发展而成的混杂集合”“是关于类型的类型,同时也是一种具有高度连续性的‘再类型’。其不但不拒绝各种类型传统中的模式化叙事结构、人物类别、脸谱化造型,甚至充分利用这些‘刻板印象’来创建冲突、强化效果”[4]。看似循规蹈矩的青年对父辈与集体的反叛与挑战,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功利观念与追逐激情之间的对抗成为贯穿《盛夏光年》的重要旋律。如果将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现实视作最初孕育现代意义上青春观念以及青春电影的土壤,那么在远离全球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社会现实之后,青春片必然面临在何处落地的问题。
三、青春角度的观察视角与现实重述
当青春与青春片离开其原生的文化与社会土壤之后,就会逐渐成为一种价值表现与现实叙述上越来越趋于多元化的亚类型和混类型。在中国青春电影谱系中,《盛夏光年》以一种不同于之前青春片的姿态呈现了青春叙述背后的社会结构问题,从而对现实进行了从独特“青春”位置出发的有效重述。对于一般观众而言,《盛夏未来》在观感上首先是一部十分新鲜和新潮的电影:抖音、音乐网红、Live与DJ、电子音乐、酒吧、音乐节都能成功唤起新一代观众的共鸣,“我一首特别喜欢的电子乐下面只有两个人评论,特别好奇这两位是谁”“去电音节可以遇到自己的同类”“我们要拒绝虚伪拒绝撒谎,直面自己的内心不好吗”,这些台词都是当下新一代高中生生活的写照。陈辰和郑宇星之所以会成为朋友,而且彼此引为同听一首歌的知己,不仅因为他们根据音乐寻找同类,而且因为音乐成为他们对抗现实压力的重要资源。对于当前的青少年人群来说,追求棱角分明的鲜明个性、特立独行且对世界有强烈好奇心非常重要,他们以流行文化与网络媒介上的虚拟偶像为理想形象,希望活成自己梦想中的样子。导演陈正道虽然出身中国台湾,却对大陆青年学生的生活相当了解,在影片中对陈辰与郑宇星生活的诸多细节进行了充满趣味的展现,像是集体跑步时同学们的起哄、考试后会根据排名调整座位、下课后复读生还在坚持做题、老师将学生的手机收集起来、男女间用社交平台的互动来揣测对方的心意、孤独时只能和Siri对话等情景,都是当下年轻人生活中触手可得却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这些细节让整部电影的现实叙述具有了落地的真实。在影像上,《盛夏未来》也十分考究:郑宇星和陈辰偷听音乐时,当歌词唱到“in this moment I lose focus”时,镜头做了变焦处理,“focus”即“焦点”,在电影语言与自然语言层面同时映射出两人的情感变化。在郑宇星崩溃的一场戏中,他在音乐节上给暗恋已久的明打电话,音乐节的彩色灯光投影了点点光斑,打在他悲伤的脸上,像眼泪一般在迷幻的氛围中渲染出悲伤的氛围;在结尾闪回的泳池戏份中,把陈辰从水中拉出来的另一双手实际上是水面上陈辰自己的倒影,倒影中实像与虚像的对照关联,呈现了陈辰从逃避现实到直面内心的转变,也揭示了陈辰的情感没有得到回应的孤独状态,以及只有她自己能将自己从悲伤中解救出来的心灵景况。导演仅用了这样一个镜头就呈现了她与自我的和解,可见对镜头语言的把握与操控力度之强。《盛夏未来》在看似精致的画面与浪漫的情绪之流之外,有力地袒露出青春的不同面向。作为一部青春电影,它暴露出了年轻人似乎不那么“温顺”和循规蹈矩的一面,而观众也应该通过对电影的反思勇敢地向真实的生活袒露自身,感受青春最真切的现在时态。
在现实生活的面向上,郑宇星和陈辰的家庭在社会结构中具有相近的位置。在两人撞见陈辰母亲和海南水果王见面的那场戏中,原本只有两个人的对话中,第3和第4个人的加入制造了有趣的节奏点;陈辰和郑宇星试图为上一辈人的对话“配音”也显示出现实中年轻一代与长辈之间的关系。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中,孩子天然具有言说父母的立场与能力。这部电影不只试图言说传统核心家庭中的新一代,或是某一特定社会文化中成长的新一代的成长,而是试图以当代年轻人的情感为路径,探讨与触摸当代中国的某一段现实,它在青春故事的叙述之下提出和解决的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问题。其中多元化的青春与青春片内涵,正在作为一种“动态的文化调解机制”发挥出调节个人、家庭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之间问题的作用。
结语
作为二战后伴随青年亚文化兴起的产物,青春片经历了文化结构、故事主题、思想观念等多层面的变化后,终于在当下的中国被固定為一种具有稳定意义生产功能的叙事系统。《盛夏未来》在对青春片的电影表述和电影时态进行了富有意义的探索,参与了大众文化对社会的观察与反馈。
参考文献:
[1]陈琰娇.《过春天》重新定义青春片了吗?——兼谈国产青春片的命名焦虑[ J ].戏剧与影视评论,2019(03):78.
[2]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45.
[3]陈犀禾,吴小丽.影视批评[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71.
[4]白惠元.“后青春期”与“暮气青春”:中国青春片的情动视野及其性别政治[ J ].文艺研究,2019(3):15.
[5][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