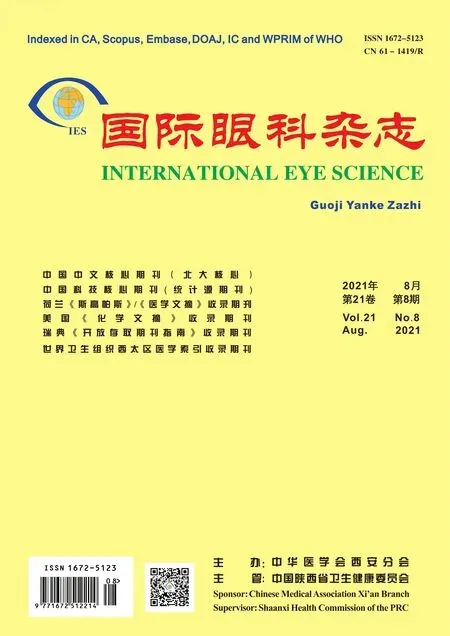近视性视网膜劈裂研究进展
2021-03-26纪海峰宋继科毕宏生2
纪海峰,宋继科,2,张 浩,温 莹,毕宏生2,
0引言
近视性视网膜劈裂(myopic retinoschisis,MRS)是指近视患者视网膜神经上皮层发生层间分离,形成一个或多个囊样空隙,高发于病理性近视。1958年,Phillips[1]通过对近视黄斑区视网膜脱离的病例进行眼底观察,发现部分视网膜脱离病例观察不到视网膜裂孔,可能与近视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有关,从而提出近视性视网膜劈裂的概念。随着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技术(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的发展,1999年Takano等[2]首次在显微结构上观察到高度近视患者黄斑部视网膜内层的分裂。根据黄斑劈裂在神经上皮层的位置分为内层和外层劈裂。内层视网膜劈裂多发生于神经纤维层和神经节细胞层,外层视网膜劈裂多发生于外丛状层和外颗粒层[3-4]。位于黄斑区的MRS称为黄斑劈裂(myopic foveoschisis,MF)。
目前,全球近视人数高达19.5亿[5],有数据预计到2050年,全球近视人数将增至47.58亿,占世界人口的49.8%,其中高度近视人数9.38亿,占世界人口的9.8%[6]。而MRS在病理性近视中的发病率约为9%~34%[2,7-10],在自然人群中的发病率约是0.83%[11]。随着MRS越来越高的发病率及发病人数,以及其对视力的长期损害,MRS需引起高度重视。
1近视性视网膜劈裂发病机制
目前,MRS发病机制并不十分明确,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参与的结果。
1.1外部牵拉因素近视性眼轴的伸长和巩膜的扩张是MRS发生的主要外部牵拉因素。病理性近视眼轴延长,巩膜向后扩展,同时牵拉相应的视网膜一起延伸,由此对视网膜产生了垂直于切线方向的外向牵拉,使视网膜伸展变薄,眼轴增长至一定程度下,视网膜的延伸不能适应巩膜的扩展,导致视网膜层间分离。Wu等[10]发现眼轴长度与MRS有显著的相关性。而后巩膜葡萄肿在此基础上,后极部巩膜向外突出,且突出部分的曲率半径小于周围眼壁的曲率半径,致使对视网膜的外向牵拉力更大。Wakazono等[12]研究发现,在高度近视眼中,眼球后极部曲率的尖锐化会促进MRS的发生。Akiba等[13]研究表明后巩膜葡萄肿可能促使MRS的发展。游启生等[11]研究发现后巩膜葡萄肿是MRS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后巩膜葡萄肿患者MRS的发生率是正常人的4倍。Shinohara等[14]进一步研究显示,视网膜劈裂和巩膜葡萄肿的位置在空间上是相互关联的,且后巩膜葡萄肿产生的外部牵拉主要引起的是外层视网膜劈裂。
1.2内部牵拉因素内部牵拉因素主要包括玻璃体皮质、内界膜及视网膜动脉的内向牵拉。高度近视眼轴的增长倾向于在30岁之前稳定下来,而MRS的发生通常是50岁以后。因此,MRS的发生可能与玻璃体不完全后脱离以及玻璃体后皮质收缩产生的内向牵拉力相关。玻璃体后皮质和内界膜(internal limiting membranes,ILM)之间与其下的视网膜Müller细胞黏连紧密,玻璃体与ILM的黏连和玻璃体不完全后脱离产生的牵拉力以及ILM自身的收缩可引起内层视网膜劈裂,通常发生在外丛状层,形成较薄的外层和较厚的内层[9,15-16]。Wu等[10]发现眼轴长度大于31mm的高度近视眼中,玻璃体视网膜界面是MRS的独立相关因素。
临床观察发现玻璃体切除术(pars plana vitrectomy,PPV)联合ILM剥除术治疗黄斑裂孔(macular hole,MH)后出现沿视网膜动脉走形的微小皱褶。内向的视网膜动脉牵引产生皱褶,该牵引力是由于视网膜动脉缺乏弹性不能适应高度近视眼轴的增长而产生。Ikuno等[4]认为高度近视眼由于视网膜血管在延长过程中缺乏弹性而形成视网膜血管微皱褶,硬化的视网膜血管阻止了视网膜的拉伸,以保持视网膜与色素上皮(retinal pigment epithelium,RPE)层的黏附,从而导致了视网膜在不同层面上的分离。另有研究发现高度近视患者中2.9%的患眼存在与视网膜血管相关的微皱褶,这些微皱褶的存在表明在高度近视眼中存在内向的血管牵引力[17]。
1.3视网膜自身因素病理性近视视网膜进行性萎缩与变薄是MRS发生的主要视网膜自身因素。高度近视视网膜电图显示a波和b波波幅降低、波峰潜伏期延迟[18],这是由于萎缩变性的视网膜各层之间的联系削弱。在此情况下,外力牵拉更容易造成视网膜层间分离,形成劈裂。此外,病理性近视视网膜内层受损变薄,液化的玻璃体通过视网膜微小孔进入视网膜下或积蓄在视网膜层间,导致视网膜劈裂的形成,且极薄的网状劈裂内层对液化玻璃体具体渗透性,加重视网膜劈裂[19]。
总之,外层视网膜劈裂主要由外部牵拉,即后巩膜葡萄肿引起。内层视网膜劈裂主要由内部牵拉,即玻璃体、内界膜牵引及视网膜血管微皱褶牵拉引起。目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解剖层面,对其潜在的分子机制以及视网膜各层细胞间的联系减弱的机制研究仍存在空白。
2近视性视网膜劈裂的检查方法
2.1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技术MRS在常规的眼底检查中难以察觉,易被误诊为黄斑水肿或视网膜浅脱离。既往研究普遍达成共识,OCT是确诊MRS的主要工具[2,8-9]。MRS在OCT上表现为后极部视网膜神经上皮增厚,在神经上皮层间有裂隙样的光学空间,其间有斜形垂直的桥状或柱状光带相连,以及RPE层前细的中等程度反射[20-21]。1999年,Takano等[2]首先使用OCT详细描述了视网膜劈裂症的出现,认为视网膜劈裂症的特征是视网膜内囊肿分裂或形成。Benhamou等[7]也使用OCT描述了在裂开的视网膜内层和外层之间观察到桥接柱的存在。
Shimada等[22]根据频域OCT将外层视网膜劈裂的范围和微结构变化分为S0~S4级。S0:无黄斑视网膜劈裂症;S1:黄斑中心凹以外视网膜劈裂症;S2:仅黄斑中心凹视网膜劈裂症;S3:黄斑中心凹但不波及整个黄斑区域黄斑视网膜劈裂症;S4:整个黄斑区视网膜劈裂症。Shinohara等[14]使用广域扫频OCT观察MRS,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分级。S4D(dome-shaped):圆顶状黄斑和除中心凹区域外的整个黄斑外侧视网膜劈裂症;S5S(staphyloma):伴有后巩膜葡萄肿且一侧视网膜劈裂超过葡萄肿边缘;S5D:无后巩膜葡萄肿且超出广域扫频OCT扫描长度范围的外侧视网膜劈裂症。
2.2眼部B超当屈光间质混浊或屈光间质干扰条件下,难以通过OCT检测到清晰准确的图像,此时需要借助B超检查。刘茜等[23]研究发现86.15%视网膜劈裂能够通过B超检查发现。MRS的B超影像表现为后巩膜葡萄肿后部眼球壁内表面欠光滑或纤细膜状回声带附着球壁。不同于视网膜脱离后界与视盘相连,且存在后运动,视网膜劈裂呈膜状物隆起时,带状回声强且纤细缺乏后运动[24-25]。
2.3超广角眼底自发荧光超广角眼底自发荧光(ultra-wide field fundus autofluorescence,UWF-FAF)成像是一种新近发展起来的无创性视网膜成像技术,具有广泛的成像范围,可以定位传统眼底自发荧光无法定位的周围眼底病变。UWF-FAF是反映RPE细胞中荧光团(脂褐素)的含量和分布,依靠荧光团的光激发产生自发荧光,评估各种视网膜和脉络膜疾病中RPE的代谢状态[26]。在MRS中,神经上皮层的分离以及脱落的感光细胞的积累可能会改变RPE的代谢状态从而导致自发荧光信号的改变。视网膜劈裂的区域表现为界限分明的颗粒状或斑片状的超自发荧光,可形成清晰的高荧光边缘[27-29]。临床工作中,OCT和UWF-FAF的结合使用可以客观评估MRS的病程进展,进而帮助临床医师进行长期监测和管理MRS患者。
3近视性视网膜劈裂的自然病程与转归
MRS是一种缓慢进展的疾病,是(尤其是黄斑劈裂)高度近视患者视力丧失的主要原因。通常情况下多数患者视力在长达数年内保持稳定,但也会进展导致视力严重丧失。目前研究已经确定了一些视力预后相关因素,包括视网膜劈裂的位置和程度及其并发症,如MH、椭圆体带断裂和中央凹的感光细胞脱离等[7,30-33]。根据Shimada等[22]对MRS的分级,研究表明多数视网膜劈裂(S0~S2)患者视力或最佳矫正视力长期保持稳定,而视力严重下降的患者多数发展至整个黄斑的视网膜劈裂(S4),其视力及最佳矫正视力下降显著[34]。除了视网膜劈裂程度,黄斑显微结构变化也与视力下降相关,包括感光细胞的脱离、椭圆体带断裂、全层MH和中央视网膜厚度>300μm。椭圆体带断裂可导致MRS发展为MH和视网膜脱离,原因是视网膜内液通过椭圆体带断裂缺损处从视网膜裂隙向视网膜下迁移[35]。除此之外,有研究表明年龄、屈光不正或眼轴长度与MRS的程度没有显著相关性[34]。MRS病程长,进展缓慢。目前的研究缺少对其自然病程进展长期监管的队列研究,需要对其进行大样本、长周期的随访观察,进一步明确其自然病程及转归。
4近视性视网膜劈裂的治疗
PPV、黄斑扣带术(macular buckle technique,MB)是治疗MRS的有效方法,但目前尚不清楚手术的最佳时机和结果预测指标。发生整个黄斑视网膜劈裂(S4)的患者应该频繁追踪病情,当中心视力明显下降或者OCT图像中发现病情进展(发生MH或视网膜脱离)最好及时进行玻璃体手术防止进一步发展。另外,如果初次就诊检查出内界膜受到干扰,建议随访,不进行手术治疗。
4.1玻璃体切除术目前PPV是治疗视网膜劈裂的有效方法,通常采用经睫状体平坦部三切口。然而,ILM剥除(部分剥除)或气体填塞是否必要仍存在争议,未达成共识。
Ikuno等[36]对6例因MRS进行性视力损害而无MH的患者采用PPV联合ILM剥除和气体填塞术,结果显示术后6mo所有患者视力至少提高两行。另一项研究中40例MRS患者接受了PPV联合ILM剥除术,术后所有患者视网膜中心凹实现再附着,视力预后与症状的持续时间和术前视力密切相关[37]。Zhang等[38]对50例67眼MF患者行PPV联合ILM剥除术,80%的患者术后最佳矫正视力得到改善,并在3a的随访中,视力和解剖结构保持稳定。Mao等[39]对60例MF患者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评价ILM剥除术的有效性,结果显示PPV术联合ILM剥除组的视力及解剖效果优于单纯PPV组。上述研究认为剥除ILM可以释放玻璃体视网膜界面的牵引力,故更愿意剥除ILM。但是,PPV联合ILM剥除术可能与术后MH形成有关。Kwok等[40]报道8例MRS患者进行单纯PPV,随访6~30mo,视力平均改善3.6行。Qi等[41]在一项回顾性研究中纳入MRS患者84例112眼,发现单纯PPV术对MRS的治疗效果满意,无需ILM剥除。近年较多研究报道在剥除ILM时保留黄斑中心凹的ILM,可以最大程度降低MH及其他并发症发生的风险[42-46],这也为临床医师手术选择提供了新思路。
相对于ILM剥除,气体填塞是否必须也存在争议。Zheng等[47]研究表明采用全氟丙烷(C3F8)进行填塞可使黄斑中心凹视网膜再附着更快。与空气填塞相比,C3F8在黄斑中心凹厚度>400μm的患者中更有效[48]。Yun等[31]在一项回顾性研究中发现,不伴气体填塞与伴有气体填塞的PPV术同样有效。上述研究表明,多数MRS患者无需填塞剂即可治愈,而气体填塞使得恢复周期缩短。
总之,虽然PPV术对重新连接中心凹是有效的,但可能增加对椭圆体带的破坏,并且功能改善有限。另外,手术治疗MRS的最佳时机尚未明确,仍需要大量的临床研究证实。
4.2黄斑扣带术尽管PPV术可以减除玻璃体内界膜界面的牵拉,但是后巩膜葡萄肿、视网膜血管硬化等整体牵拉因素并不能完全消除。相比之下,MB可能有助于解除这些牵引力。Baba等[49]将由Fumitaka Ando设计的MB用于MRS与MH相关的视网膜脱离,5例患者术前视力降低了0.2~0.6,术后视力均得到改善。OCT显示平均术后1.8(0.5~3.0)mo后,MRS和中央凹再附着得以解决。Mateo等[50]研究在16例进展中的MRS患者中使用了PPV联合MB,术后视敏度提高了87.5%。Zhao等[51]对28例MF患者进行改良MB联合或不联合PPV治疗,术后视网膜再附着率达100%,平均眼轴降低2.09mm,最佳矫正视力得到显著改善。MB联合PPV不仅有效解除了玻璃体视网膜界面的牵拉力,而且释放了由眼轴增长引起的整体牵拉力,从而使视网膜解剖复位,最终改善视力。
4.3视网膜光凝术激光治疗主要适用于周边部MRS,作用于病变部位或在病变周围预防性的激光,加强劈裂处内外层视网膜黏附,阻止视网膜劈裂进展。但对于病变程度严重的MRS,激光治疗可能会加速视网膜脱离[52]。并且激光治疗会损伤黄斑区神经上皮细胞,最终影响视力预后。
目前,MRS的手术时机多选择在患者视力明显下降或视网膜劈裂明显进展时期,通常出现这些情况时视力预后较差。未来随着微创手术的发展,或可提前手术干预解除玻璃体视网膜牵拉等因素,可以延缓病程进展,改善视力预后。
5总结与展望
MRS及其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视力,其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明确。通常MRS患者视力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可以定期使用OCT联合UWF-FAF检查观察其显微结构变化,长期随访监测病情。对于视力下降显著或进展期患者,PPV术和MB术治疗MRS均有良好效果,但对于ILM剥除(部分剥除)或气体填塞是否有必要仍没有统一标准。MRS的防治策略、最佳手术时机选择及结果预测指标还需要大量临床研究证实。此外,目前并未见到MRS相关动物实验模型的报道,需要建立相应的动物模型对其发病机制、自然病程及治疗进行进一步研究,为MRS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