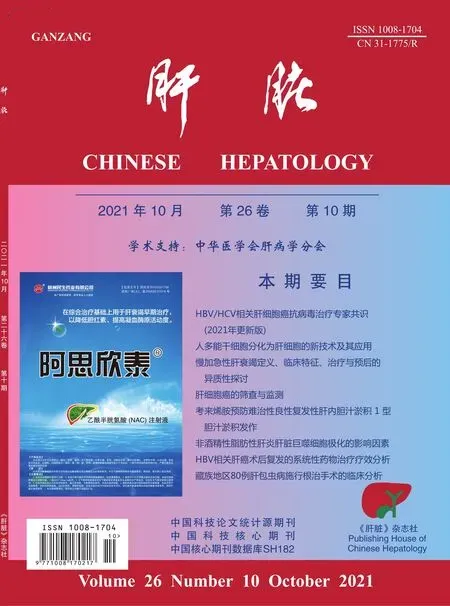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肝脏巨噬细胞极化的影响因素
2021-03-26刘百怡饶慧瑛
刘百怡 饶慧瑛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一个炎症阶段,常伴有代谢紊乱,如肥胖、2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以及血脂异常[1]。NASH以肝脏炎症和肝细胞损伤为特征,可进一步发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癌。NAFLD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慢性肝病病因,其全球患病率约25%,NASH在普通人群中的患病率为1.5%~6.5%。研究估计,2016年至2030年,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英国和美国NASH患者数量在NAFLD患者中的占比将高达56%,将会加重医疗负担[2- 3]。巨噬细胞是机体固有免疫系统的关键,参与多种炎症反应和免疫调节。肝脏巨噬细胞约占肝脏细胞总数的15%,包括肝脏固有巨噬细胞(库普弗细胞)和单核细胞来源的巨噬细胞,参与肝脏免疫稳态的调节以及多种肝脏疾病(如NAFLD、慢性病毒性肝炎、肝癌)的发展[4-5]。肝脏巨噬细胞具有异质性和可塑性特点,在NAFLD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呈现动态性变化。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巨噬细胞可以通过调节基因和蛋白的表达而呈现出不同的表型。然而,肝脏巨噬细胞在NASH中动态变化的潜在机制仍未完全明确。本文旨在更深入地了解巨噬细胞激活在NASH中的作用以及NASH的发病机制。
一、肝脏巨噬细胞的分布情况
肝脏巨噬细胞由不同的细胞亚群组成。其中,库普弗细胞来源于卵黄囊红系-髓系祖细胞,随后聚集和迁移到肝脏并进一步分化为成熟的肝脏固有巨噬细胞[6]。单核细胞来源的巨噬细胞源于骨髓造血干细胞,随血液循环募集到肝脏[7]。在健康人群中,库普弗细胞是肝内主要的免疫细胞。在健康的啮齿动物肝脏中,库普弗细胞占肝脏所有非实质细胞的20%~35%[8]。库普弗细胞大部分存在于肝血窦内,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可抵御外来危险入侵。受肝脏微环境的影响,巨噬细胞通常可极化为两种亚型,包括“促炎”的M1型巨噬细胞和参与“免疫调节”的M2型巨噬细胞[9]。在NAFLD肝脏中,库普弗细胞被脂多糖(LPS)或过量的游离脂肪酸(FFA)激活,释放大量促炎性细胞因子(TNF-α、TNF-β、NF-κB等),并通过旁分泌的作用促进肝细胞内脂质堆积以及氧化应激反应,推动肝脏的组织学由单纯性脂肪变性向NASH甚至纤维化进展。在这个过程中,M1型巨噬细胞数量明显增加,M2型巨噬细胞数量显著减少。M1/M2比例之间存在动态平衡,M1/M2比例失衡可能是NAFLD发病的关键。
二、NASH肝脏巨噬细胞向M1型极化的机制
经典的M1型巨噬细胞主要由脂多糖(LPS)或Th1细胞因子(如干扰素γ)激活,引起促炎反应和杀菌作用。影响肝脏巨噬细胞向M1型极化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细菌、microRNA、细胞因子、热休克蛋白等。
有研究发现,大肠杆菌 NF73-1易位到肝脏,通过TLR2/NLRP3途径导致肝脏M1型巨噬细胞增加,并进一步激活肝细胞mTOR-S6K1-SREBP-1/PPAR-α信号通路,引起小鼠肝细胞由甘油三酯氧化向甘油三酯合成的代谢转变。肝细胞内脂质堆积和炎症反应促使肝脏由单纯性脂肪变性发展为NASH[10]。肠道菌群通过移位到肝脏而对巨噬细胞极化产生影响,提示肝-肠轴可能在NASH发病机制中发挥作用。
microRNA是短链非编码RNA,参与转录后基因表达的调控。microRNA还可以参与肝脏的稳态调节,例如miR-552-3p通过调节胆汁酸受体(FXR)和肝脏X受体(LXR)的转录活性以改善肝脏糖脂代谢紊乱[11]。此外,有研究团队在动物实验中发现,肝细胞胆固醇负荷使溶酶体功能受损,诱导肝细胞释放外泌体,外泌体以microRNA-122-5依赖的方式影响巨噬细胞向M1型极化并诱导炎症发生[12]。
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参与经典的MAPK信号通路,是重要的炎症因子,包括p38α(p38)、p38β1、p38β2、p38γ、p38δ五个异构体,与细胞炎症、凋亡和生长相关。在高脂饮食(HFD)喂养的小鼠肝脏中,巨噬细胞p38α通过诱导促炎细胞因子(TNF-α、CXCL10和IL-6)的分泌介导巨噬细胞向M1型极化。向p38α缺失的巨噬细胞与正常肝脏细胞共培养体系中加入TNF-α、CXCL10和IL-6,可以诱导肝脏细胞脂质积累和炎症反应。p38抑制剂可抑制HFD诱导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13]。
热休克蛋白12A(HSPA12A)是HSP70家族的一个成员。有研究验证了HSPA12A 的表达与肝细胞癌患者的生存期缩短有关,提示HSPA12A可能参与了肝脏稳态的调节。在NAFLD小鼠模型中,肝脏巨噬细胞内的HSPA12A通过基因表达上调和核移位与丙酮酸激酶M2(PKM2)形成复合物,介导巨噬细胞向M1型极化,进一步通过旁分泌作用调节肝细胞脂肪变性和损伤[14]。在体内和体外实验中,骨形态发生蛋白(BMP)9可以增强NF-κB的核移位,诱导巨噬细胞向M1型极化,并促进LPS介导的巨噬细胞NF-κB通路的激活,进而引起肝细胞损伤并促进NASH发展[15]。
除了有机影响因素外,无机物同样可以引起巨噬细胞向M1型极化。Handa等[16]证实,无论是在NAFLD患者还是小鼠肝脏中,肝网状内皮系统细胞(RES)中的铁超载会使M1型巨噬细胞的生物标记物(CCL2、CD14、iNOS、IL-1β、IL-6、TNF-α)表达水平升高。这提示铁超载会增加M1巨噬细胞的数量,破坏了M1/M2巨噬细胞极化之间的平衡,导致促炎型巨噬细胞加速肝脏炎症和纤维化的形成。另外,有研究发现在小鼠肝脏中,M2型巨噬细胞分泌的IL-10可以促进M1型巨噬细胞凋亡,从而抵抗NASH[17]。
三、NASH肝脏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的机制
M2型巨噬细胞在肝脏微环境免疫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可以促进肝脏组织修复以及参与结构重建。在NAFLD中,M2型巨噬细胞起到对肝脏的保护作用,该亚型的细胞增多可以改善NASH。
Han等[18]发现在HFD喂养的小鼠肝脏中,维甲酸相关孤儿受体α(RORα)可以通过诱导klf4(kruppel-like factor 4)增强库普弗细胞向M2极化,在肝细胞中发挥抗脂肪生成和抗氧化作用,从而改善小鼠NASH进展。膜联蛋白A5作为细胞凋亡、组织修复、抗磷脂综合征和炎症反应的参与者,可以直接与PKM2相互作用,促进巨噬细胞表型由促炎的M1型向抗炎的M2型转变,降低M1型巨噬细胞的糖酵解反应,同时增强氧化磷酸化反应,从而改善HFD诱导小鼠的NASH肝脏表现[19]。氧化物酶体增殖激活受体γ(PPAR-γ)是一种配体激活的核受体,通过调节脂肪细胞基因表达和胰岛素细胞间信号转导来调控脂肪细胞的分化和糖脂代谢。已有研究发现,PPAR-γ活化在巨噬细胞极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NAFLD小鼠模型中,PPAR-γ上调使脂质诱导的巨噬细胞极化从M1型向M2型转变。提示调控PPAR-γ活性可能会平衡脂质诱导的M1/M2巨噬细胞极化,从而阻止NAFLD的发展[20]。
在脂肪组织中,IL-25通过诱导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来促进巨噬细胞脂质代谢[21]。该结果也在HFD诱导的小鼠肝脏中得到证实。IL-25可以激活肝脏巨噬细胞和肝细胞中的IL-13/STAT6轴。在肝脏巨噬细胞中,IL-25/IL-13/STAT6轴诱导M2a型巨噬细胞的产生;在肝细胞中,IL-25可以恢复IL-25/IL-13/STAT6/IL-25正反馈回路,从而对肝脏脂肪变性起到保护作用[22]。另外,番红素通过提高信号传导及转录激活因子(STAT6)和蛋白激酶B(Akt)的磷酸化水平来促进IL-4诱导的M2极化,进而加速脂肪组织细胞内脂肪的分解反应[23]。
虽然目前仍没有治疗NAFLD的特效药,但是已有研究发现可以改善NAFLD的药物。国内的研究团队对NAFLD小鼠模型进行为期4周的利拉鲁肽腹腔注射,发现小鼠的体质量下降,肝脏炎症、ALT、AST、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均得到显著改善,M2/M1 库普弗细胞的比率升高。体外实验进一步验证得出,利拉鲁肽通过cAMP-PKA-STAT3信号通路调节库普弗细胞向M2型极化,从而减轻HFD引起的肝脏脂肪变性和炎症[24]。另一研究团队发现,对HFD诱导的小鼠模型进行吡非尼酮治疗,可以降低脂肪生成和脂肪酸合成相关基因(Srebp1c、Chrebp、Fasn、Scd1)的表达并增加脂肪酸氧化相关基因(Acc、Ppara、Cpt1a、Lcad)的表达来减弱肝脏脂质过度积累和过氧化。此外,吡非尼酮还减少了肝脏巨噬细胞的数量,特别是“促炎”的M1型巨噬细胞,增加了“抗炎”的M2型巨噬细胞的数量,从而改善了NASH小鼠的胰岛素抵抗、肝脏炎症和纤维化。这提示吡非尼酮可能是治疗NASH的潜在候选药物[25]。
四、 小结
肝脏巨噬细胞参与NAFLD的发生和发展,巨噬细胞极化在NAFLD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M1型巨噬细胞增加是导致NASH进展的关键因素,M2型巨噬细胞增加会改善NASH,M1/M2之间的平衡可能是NAFLD发病机制和治疗策略的切入点。因此,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巨噬细胞的极化机制以及M1/M2在NAFLD各阶段的动态变化,这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NAFLD的发病机制,为临床治疗提供更新型、更有效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