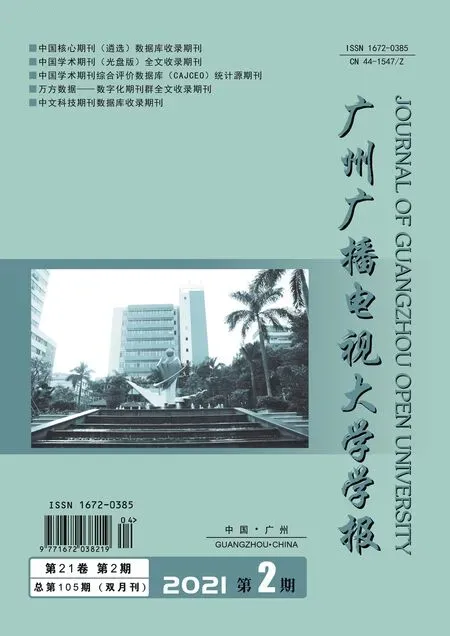论晁补之词中的“桃源”意象
2021-03-25姚家欣
姚家欣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7)
“桃源”意象最早源于东晋陶渊明在《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中营造的一个宁静优美、远离尘嚣的隐逸世界,唐代王维又创作了《桃源行》,将桃源理解为“仙源”“灵境”,后“桃源”便作为一种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意象固定下来,代表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中刘晨阮肇入天台的故事则具有探访仙界和男女爱情的双重意味。在后世的文学书写中,桃源意象的种种象征意义逐渐交错融合,并在宋词中呈现出追慕隐逸、向往仙界、描写爱情及社会享乐等特点。晁补之词中的“桃源”意象,主要吸收了陶渊明隐逸安宁的桃源主题,注重书写当下和过去的美好生活,强调了“桃源”的现实性与追忆性,暗示了晁补之纠结于过去和现在的矛盾心态。
一、词中的“桃源”指向
晁补之词中的桃源意象并不是直接出现的,而是多以陶渊明桃花源隐逸世界中的“武陵”“花洞”指代:“鸥起苹中,鱼惊荷底,画船天上来时。翠湾红渚,宛似武陵迷”(《满庭芳·赴信日,舟中别次膺十二叔》)。[1]该词作于元符二年(1099年)晁补之赴任信州盐酒税使途中与其叔晁端礼留别之时。苹中鸥鹭,荷底戏鱼,水上画船,碧波红花,一派宁静甜美,使他感觉如置身于“武陵”桃源仙境之中。其后则以竹林名士喻指其叔晁次膺的高逸风神,并在词末以“天际片帆归”表达了对隐逸生活的赞赏之情。这种隐逸之情同样见于该年作者途经庐山所作的《尾犯·庐山》中,“花洞里、杳然渔艇。别是个、潇洒乾坤,世情尘土休问”。[2]但考虑到该年是章惇等新党得势后的第六年,也是晁补之服除后担任的第一个官职,正如他在守制期间所作的诗歌而言,“先君余庆期之子,吾驾如今不可还”,[3]此时他更多是对仕途的担忧,归隐对他而言为时尚早。故而,此处的“桃源”并非是他的心灵栖息之地,更多是一个风景之喻。
贬逐信州时期,晁补之又在词中间接化用了“桃源”意象:“清狂、扬州一梦,中山千日,名利都忘。细数从前,眼中欢事尽成伤。去船迷、乱花流水,遗佩悄、寒草空江。黯愁肠。暮云吟断,青鬓成霜”(《玉蝴蝶》)。[4]“去船迷、乱花流水”。暗用陶渊明《桃花源记》“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之事,[5]充斥着少年欢乐不可追寻,仕途起伏难以琢磨的悲凉伤感。而词的上阙却是另一番面貌:“暗忆少年豪气,烂南国、蓬岛风光”(《玉蝴蝶》),晁补之12岁时,随父亲晁端友仕于会稽(越州),此后山清水秀的江南风光便深深地烙在了他的记忆中。醉倚吴宫,歌舞登临,意兴何等豪盛!正如他在《求志赋》中写道:“横武林之大江兮,往始宁之南邑。路会稽以周流兮,求历山之所在”。[6]然而正是回忆中欢乐与现实中的苦痛相互交织所形成的强大落差,不仅加深了晁补之此刻的悲凉,也是这种悲凉形成的深层原因。“清狂、扬州一梦”情感陡然下跌,感叹往事如梦,再也回不到少年恣意欢畅的时光,过往种种快乐,皆如武陵人无意中探访桃花源,后来再寻却不得的失落与感伤。如果说秦观的“桃源”是在追寻的过程中发现虚幻性,那么晁补之的“桃源”便是“细数从前”,沉浸在曾经拥有的回忆中。但欢事成空,而今只能独对寒草空江,悲怆黯淡的心境不言自明。
即使是退居东皋归来园时期,晁补之也仍将“桃源”理解为曾经得到而如今却无法再得的快乐,并发出了“迷路桃源了”的感慨!依然是上阙欢乐与下阕悲凉的强烈对比,《安公子·和次膺叔》开篇直接以“少日狂游好”表现任职京城时期的欢畅,花间游宴,不惜千金,歌舞沉醉;归去卧眠,竟未觉日上三竿,“从市人、拍手拦街笑”[7]何等潇洒畅快!但下片却以“迷路桃源了”陡然一转,情绪由乐转悲,发出了“乱山沈水何由到?”的疑问,运用伯牙子期“拨断朱弦”之典暗示自己无知音赏识,又借“青鸟传信”“弄玉吹箫”表达自己归隐的愿望,最后以刘晨阮肇入天台事,指明仙境桃源难以再次寻找。全词结构分明,上片极力铺写旧日京城盛事,气势充沛,酣畅淋漓,过片转笔宕开,以“迷路桃源了”将退居心事和盘托出:再也回不到游宴京城的快乐时光了。
然而,京城何乐之有?自晁补之元丰八年(1084年)任京城太学正以来,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人也渐渐齐聚京师,形成了以苏轼为首的文人集团,他们极尽交游之乐。南宋金华人邵浩的《坡门酬唱集》收录有苏轼兄弟及苏门六君子8人660首作品,其中多有同体共韵之作,可见苏门酬唱的盛况。此外,他们也常集聚于风雅的士大夫家,饮酒高歌,赏花看舞,尽显名士风范。如元丰初年(1078年),驸马都尉王洗曾在府中宴请当时名士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李之仪、李公麟、晁补之、张来、秦观、圆通大师等十六人游园,被世人称为“西园雅集”。
这些聚会在晁补之的词中也有生动的记载:“满槛煌煌看霜晓。唤金钱翠雨,不称标容,潇洒意、陶潜诗中能道”(《洞仙歌·菊》);[8]“偶来恰值,半谢妖饶犹好。便呼诗酒伴,同倾倒”(《感皇恩·海棠》);[9]“送出灯前,婀娜腰肢柳细。步蹙香裀,红浪随鸳履。梁州紧,凤翘坠。悚轻体”(《碧牡丹·王晋卿都尉宅观舞》)。[10]无论是赏花还是看舞,词中皆洋溢着满足与惬意之情。京城任职的八年,是晁补之一生中的巅峰时期。绍圣之后,新党掌权,元佑旧党被打压,那些把酒弄盏、赏花看舞、吟诗唱词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但京城的回忆已镌刻在生命中,成为晁补之无时无刻的精神“桃源”。
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晁补之的“桃源”常象征着曾经的快乐,但仍具有现实性。退居东皋归来园(今山东巨野)的宁静生活,与他追慕的恬美桃源相似,使他从中收获了不少的快乐。“旧游应未改,武陵花似锦,笑语相逢”(《凤箫吟·永嘉郡君生日》)。[11]妻子生日之时,恰逢春暖花开,桃杏盛放,万物一派安宁祥和。晁补之便以“蕊宫金丹”和“芝田仙乡”的典故,表现归隐生活的惬意,即夫妇二人如同生活于桃源仙境一般,共驻容颜,归隐庐山。整首词洋溢着一种热烈喜悦的气氛,除了庆贺妻子生辰,也直接表明了他退居东皋的喜悦。在他看来,现实居住的归来园就是“桃源”,他十分满足这种宁静恬淡的生活。
晁补之词中的“桃源”意象涉及他少年随父宦居浙东、青年任职京城、晚年退居东皋归来园三个时期,是他对过去美好生活的追忆和对当下宁静生活的享受,也是他在坎坷宦途中不断探寻的心灵栖息地。
二、追慕“桃源”之因
青年时期的晁补之具有强烈的功业理想“男儿三十四方身,布衣不化京洛尘”(《答陈履常秀才谑赠》),[12]“男儿业就可以行,桃李荣时腰缓灿”(《送石梁赴举》),[13]而中晚年的晁补之却以具有隐逸意味的“桃源”作为自己的心灵栖息地,这是为何?
首先这与晁补之宦途的坎坷有关。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亲政,任用新党,旧党人物纷纷被贬。此后他的心理便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过程:
绍圣元年,晁补之出知齐州。他在《齐州谢到任表》中言“从臣之欲,获奉亲与;便臣之私,使近乡邑”,[14]表达了对朝廷满足自己专城独居,侍亲身侧愿望的感念;绍圣二年(1095年),晁补之因扬州任上修葺摘星楼之事被贬为应天府通判,但《宋史》却载“坐修《神宗实录》失实,降通判应天府”,[15]各中缘由不过党争。晁补之十分愤怒,在谢表中言“庶几孤余不越分量。而偶弼臣之一荐,滥文馆者十年”,[16]讽刺与不满之意溢于纸上。到任半年后,他又被改任亳州通判。
绍圣四年(1097年),朝廷再次爆发整治元佑旧臣风潮。晁补之因“力附奸恶之党,表里倡和,阿附导谀”的险邪之资,[17]被贬为处州盐酒税监。宦途的贬谪和名节的诋毁,再加上母亲的猝然离世,使他“毁脊几不胜”。元符二年,晁补之服丧期满,改监信州酒税。不同于前期的消沉,他的心情更加轻快和洒脱。“要过香垆双履步,却从彭蠡一帆飞。它年笑向张公子,应带烟霞满客衣”(《巳卯六月赴上饶之谪醇臣以诗送行次韵留别》),[18]像范蠡和张良一样在功成名就后归隐田园,正是他的人生理想。元符三年(1100年)还京师著作佐郎。因《神宗实录》与时局的复杂关系,多次请辞,未果。
靖国元年秋(1101年),党论再起,晁补之出知河中府,“莫嫌马上过春风,得句桃溪柳涧中”(《赴蒲道中寄洛倅王定国》)。[19]但次年三月,刚刚到任的晁补之又被改知湖州,“冲寒到郡待花开,花未开时却遣回”(《罢蒲干濠道中寄府教授之道弟》),[20]而抵达湖州后,又被徙知密州,不久便完全落职,只以管勾江州天平观的祠禄罢职家居。靖国二年(1102年),他便退居金乡故园。
一方面,从仕途生涯来看,相比于苏轼、黄庭坚与秦观,晁补之与张耒的仕途虽不算坎坷,但朝廷的党争、名节的毁坏使具有强烈经世理想的晁补之对官场心灰意冷,产生了隐退的想法;另一方面,他对仕途的打击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在创作中寻找精神寄托。但不幸的是,这些努力都失败了。
贬谪应天府与亳州是晁补之词的创作初期,他常提及唐代刘禹锡、白居易被贬之事:“应记狂吟司马,去年时、黄花高宴。竹枝苦怨,琵琶多泪,新年鬓换”(《水龙吟·寄留守无愧文》);[21]“刘郎莫问,去后桃花事。司马更堪怜,掩金觞、琵琶催泪”(《蓦山溪·谯园饮酒为守令作》)。[22]一方面,晁补之能与同样被贬的刘白共情,同时也设想到自己今后可能遇到的艰难与挫折,表达了贬谪的悲伤和对未来的忧虑之情;另一方面,也有汲取刘禹锡屡折不挠的超迈精神力量之意。但此期的晁补之更注重与刘白贬谪经历的共鸣,对二人的精神力量汲取较少,这使得他不能脱离悲伤的心境。
贬谪信州的创作中期,晁补之词中的刘白逐渐退场,阮籍、阮咸开始出现。“竹林高晋阮,阿咸潇散,犹愧风期”(《满庭芳·赴信日舟中别次膺十二钗》);[23]“有多才南阮,自为知己。不似朱公江海去,未成陶令田园计”(《满江红·赴玉山之谪,与诸父泛舟大泽,分题为别》);[24]“觉阮途穷,归心阻。断魂素月,一千里、伤平楚”(《迷神引·贬玉溪对江山作》)。[25]晁补之羡慕魏晋士人风流潇洒的风度,但他更看到了阮籍穷途痛哭的一面,阮籍、阮咸所面对的魏晋易代的政治压迫与晁补之所面对的朝廷内部严峻的党争形势相似,人人自危,不得不谨言慎行。相比而言,后者的精神痛苦远远大于对魏晋风度的追慕。故而魏晋风度仍旧不能抚慰他的内心,以真挚的感情抒发贬谪之痛仍是此期晁补之词中的主调。
而随着学习刘禹锡、白居易、阮籍、阮咸等积极精神的失败,晁补之继续寻找着能抚慰心灵的力量,象征安宁美好的“桃源”便走入了他的世界。其实,宋词中“桃源”意象,不仅继承了前代隐逸的思想和对仙界的向往,还诉说着男女爱情,描绘着社会宴乐的场景。但不同于黄庭坚词具有艳情色彩的“桃源”,“宋玉短墙东畔,桃源落日西斜。浓妆下着绣帘遮。鼓笛相催清夜”(《西江月·宋玉短墙东畔》),[26]和秦观词具有强烈个人绝望色彩的虚幻“桃源”,“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踏莎行·郴州旅舍》),[27]晁补之词中的“桃源”具有隐逸思想、宁静生活的意味。这一点的形成除了现实的因素和晁补之个人心灵的追寻,亲友对他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一)亲人
晁补之的父亲晁端友虽为官不显,却是一个淡泊名利又喜爱山水的人。“先君……喜宾客,家居不绝酒,不乐为吏,至累岁不调,乏无檐石,亦不以经意,旷达乐山水,意所欲往”,[28]晁补之少年时便追随父亲宦游浙东,常年的陪伴自然使他耳濡目染地受到父亲品格的影响。
晁补之成年后,十二叔晁端礼对他影响较大。试看他与晁补之赴信州途中留别的酬唱之作:“人生事,谁如意。剩拼取,尊前醉。想升沉重有命,去来非己”(《满江红》)。[29]不同于晁补之词中对未来的隐隐担忧,晁端礼在退居的几十年间看破了世事起伏。他于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举进士,担任过单州城武主簿、瀛州防御推官等官职,但因得罪上司,被废徙达30年之久。晁端礼在词中也表达了对世事的看法:宦途的起伏自有安排,并非个人所能左右,并在词尾以“菊老松深三径在,田园已有归来计”的实际经历劝勉侄子,为他舒缓着宦途的不平之气。而这次酬唱,也是晁补之词中第一次出现“桃源”意象的源起。
(二)苏轼
自熙宁五年(1072年)上书投拜苏轼门下,至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卒于常州,晁补之的人生便与苏轼紧紧相连。苏轼在元丰二年(1079年)经历“乌台诗案”和贬谪黄州后,心态发生了较大转折,隐逸思想在他心中不断生长。“师渊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诗。赋归来之清引,我其后身盖无疑”(《和陶归去来兮辞》),[30]他心中的理想人物就是陶渊明。苏轼一生中共作120多首和陶诗,实现了与陶渊明精神的完美融合,达到了超旷放达的境界。在晁补之与苏轼会面的最后一个阶段——宦居扬州期间,二人往来唱和,度过了相对快乐的一段时光。这一时期苏轼开始作《和陶饮酒二十首并序》,并“示舍酒弟子由、晁无咎学士”,[31]而且第十九首就是写给晁补之的,“晁子天麒麟,结交未及仕。高才故难及,雅志或类己……。行乐当及时,绿发不可恃”。[32]另外,晁补之也作了《饮酒二十首同苏翰林先生辞韵追和陶渊明》唱和。由此可知,晁补之退居金乡时期对陶渊明的直接追慕很大程度上是受苏轼影响,而这也是晁词“桃源”意象大量指向隐逸思想的直接原因。
(三)好友
除了师长,晁补之的好友也对他的隐逸思想产生了不小影响。廖正一,号竹林居士,与晁补之同于元丰二年中进士,元佑年间又同在馆阁任职,后又皆因党藉而被贬谪。廖明略心直口快,“廖君愤世谈刺口”(《答明略并呈鲁直》),[33]在贬谪后多次表示退隐,并有竹林之风,晁补之称其“竹林风来虚自赏”(《答明略并呈鲁直》);[34]李昭汜,自号乐郡先生,与晁补之是同乡,二人少年齐名,关系非同一般,入党藉后,李昭汜居闲十五年,晁补之对他的闲居情况很是了解,“居贫少烟火,饘食尚须旰。出门兀何之,踉跄从欵段。吾人古遗隐,凫足闵同患”(《次韵李成季感事》);[35]胡戢,被晁补之称为“逸民”,根据晁补之《苏门居士胡君墓志铭》可知,二人少年便已结识,但胡戢的隐逸思想萌生较早,“时叔文方壮,浩然已有遗世深隐之意矣。后八年,补之教授北京,以书来曰:‘戢不复仕’”。[36]这些志趣相投的朋友皆与晁补之有相似遭遇,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隐逸作为自己的存身之道,必然会影响到晁补之。
由此可知,晁补之对“桃源”意象的追慕是在现实仕途的打击下形成的,他苦苦追寻着自己的精神“良药”,与贬谪的刘禹锡、白居易共情失败了,对魏晋士人潇洒风度的追慕也失败了,在师长、亲友,尤其在苏轼对陶渊明大力提倡的影响下,隐逸思想在晁补之的心中不断生长,最终发现了“桃源”乐土。
三、何以“迷路桃源了”
退居金乡之后,晁补之开始了真正的隐逸生活,并打造了自己的现实“桃源”。他心中的理想人物就是陶渊明。据《宋史》所记,晁补之“还家,葺归来园,自号归来子,忘情仕进,慕陶潜为人”,[37]他追慕陶潜的力度可谓不小。在重新修葺了归来园后,皆以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语句如“松菊”“舒啸”“临赋”“遐观”“流憩”“寄傲”“倦飞”“窈窕”等命名园中的轩室楼亭,以“致归去来之意”,他急切地营造了一个充斥着“陶渊明”的日常环境,认为这可以达到“若渊明卧起与俱”“与渊明晤语接”“踌躇自得,无往而不归来矣”[38](《归来子名缗城所居记》)的效果。
而在晁补之的后期词中,举目可见他对陶渊明的学习以及对自己心中“桃源”的打造。“我似渊明逃社,怡颜盼、百尺庭柯”(《满庭芳·用东坡,韵题自画莲社图》);[39]“松菊堂深,芰荷池小,长夏清暑”“听衡宇、欣欣童稚,共说夜来初雨”(《永遇乐·东皋寓居》),[40]而晁补之也确实获得了不小的闲居愉悦,其词作中充斥着一股自由散漫、轻松淡然的气息,“南园住致偏宜暑。两两三三修篁,新笋出初齐,猗猗过檐侵户。听乱飐芰荷风,细洒梧桐雨”(《黄莺儿·东皋寓居》);[41]“燕引雏还,鸠呼妇往,人静郊原趣。麦天已过,薄衣轻扇,试起绕园徐步”(《永遇乐·东皋寓居》)。[42]
故而,在晁补之看来,他的“桃源”便是充满着惬意与安宁的归来园,是能够让他忘怀贬谪之痛的心灵场所。但即便如此,晁补之依旧发出了“迷路桃源了”的感慨,这又是为何?恐怕要归结于“矛盾”二字。
首先,从“桃源”意象的本质而言,无论是陶渊明的武陵桃源,还是刘义庆的天台桃源,都蕴含着希冀美好生活的未来指向,但晁补之的“桃源”却是对过去美好生活的追忆和对当下宁静生活的享受,在精神上指向过去和现在,独独没有涉及未来。贬逐信州时期,晁补之深知少年漫游浙东、青年任职京城、扬州的美好时光皆是从前往事,但他依然将其视为“桃源”,可见他内心对过去的深深眷恋;东皋退居,他本就处于与陶渊明一般的隐居状态,但归隐田间之乐依旧不能抚平他内心对往日生活的留恋,可见他在仕宦与隐逸中的纠结与矛盾。从这个角度而言,晁补之的“桃源”虽美好,却与现实形成了强大的反差。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难以跳出,终究使他的心灵不能安然栖息于“桃源”。即便晁补之的桃源依旧包含着享受宁静生活的现实指向,但“桃源”意象本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引导着世人对未来充满期望,而晁补之的“桃源”却完全没有这一层意味。故而,晁补之的“桃源”和传统意义上的桃源是存在本质矛盾的。
其次,虽然晁补之的后期词中作为“桃源”精神核心的陶渊明及其相关的意象大量出现,但也不可忽视“李广冯唐”意象的存在。“射虎山边寻旧迹,骑鲸海上追前约”(《满江红·次韵吊汶阳李诚之待制》);[43]“只愁恐、轻鞭犯夜,灞陵旧路”(《永遇乐·东皋寓居》);[44]“应怀得隽大明宫,无事老冯公”(《一丛花·再呈十二叔》)。[45]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却未被封侯的“飞将军”李广,因年老出征迷失道路,只能以“不能复对刀笔之吏”自刎;冯唐,多年担任小官,武帝欲用之时,他已九十岁,不能为官。晁补之取李广善射赋闲与冯唐空耗年华之意,寄托自身的怀才不遇之感。这种悲慨犹如一团乌云弥漫在他心头,即使是归隐山林之乐也不能驱散。这两类意象的矛盾性似乎可以解释“桃源”意象缺乏未来指向的原因。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慨叹自己怀才不遇正暗示了晁补之心中继续为国效力的想法。纠结于出仕与入仕之间,也正是冯煦所言晁词“无子瞻之高华,而沉咽过之”的内在原因。[46]
最后,晁补之的本志与“桃源”理想也是相矛盾的。一则,他与“桃源”的精神人物陶渊明并无相似,也未学得其精神内核。“读陶潜《归去来词》,觉己不似,而愿师之”,[47]他近乎“疯狂”地学陶,努力营造“归去来兮”的氛围,“犹相观左右,意不自足,惧失渊明一语也”,[48]但越刻意越难以实现。晁补之从田园形似的角度出发仿效陶渊明,却未彻底体会陶渊明超脱潇洒的田园之神韵,最终导致了看似超逸闲适,却将怨愤郁结实于内的矛盾心理。二则,晁补之更乐于做官,“桃源”理想更多是他基于现实压迫的无奈选择。晁补之也认识到学陶是有困难的,“而余遭盛时,尝见识拔,污台省,国恩未报,而决然去之,以若所歉,为渊明固难”,[49]他始终对国家朝廷念念不忘,中途隐退,心中歉疚。这样的心理使得他有了做官机会后,便马上放下了现实“桃源”,不顾年龄、身体的状况赴任,并在《泗州谢上表》表达了“誓报更生之恩,终捐九死之命”[50]的决心,又写下《泗州谢执政启》《谢泗州教授启》等一系列书启。可见他再度为官的欣喜。
综上而言,无论是晁补之对“桃源”意象本质的认识,还是退居金乡后追慕陶渊明与悲慨李广冯唐的矛盾,亦或是晁补之的本志与“桃源”理想的矛盾,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即使晁补之已生活在了他心中的“桃源”,他也无法完全让自己“安”于其中,“迷路桃源了”是必然导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