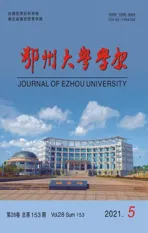鄂豫皖苏区红色政权政治权威建设研究
——社会身份认同、利益认同化为政权认同
2021-03-25王兵
王兵
(中共亳州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研室,安徽亳州236800)
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的仅次于中央苏区的革命根据地,铸就了“28年红旗不倒”的辉煌成就。恩格斯讲“革命是最权威的东西”,任何政权建设与长期存续都需要政治权威。为何鄂豫皖红色政权维持这么久,并且在红军撤去之后仍与敌人进行百折不挠抗争,皆因鄂豫皖红色政权具有政治权威,是建立在群众理性选择基础之上的,因此,获得了群众认同与支持。政治权威的形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有具体的来源的,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深化对政权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一、西方学者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政治权威理论的阐释
政治权威是政治权力合法化的形式,是政治权力符合政治共同体普遍约定的一种 “正当性”,认同性与合法性是其应有之义,易言之,政治权威是使得客体自愿服从的能力。阶级社会中政治权力所具有的强制性不言自明无需赘言,但权力来源于哪里? 为何三岁的娃娃当上皇帝,普天之下却莫敢不从。最早关注和探讨这个问题且结果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韦伯认为合法性是权力产生、客体自愿服从的根本所在,即为政治权力变为政治权威的原因,所谓合法性指促使人们自愿服从命令的动机[1]。他从经验事实分析入手,利用自己开创的理念类型分析法,将合法性来源分为传统型、法理型和克里斯玛型三种。传统型是指合法性建立在社会群体敬畏传统且社会传统痕迹浓重基础之上的,如风俗习惯、传统惯例在群体中具有无上权威性,那么符合以上传统的权力就会得到成员遵从。法理型是合法性建立在社会群体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基础之上,如: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即使有些选民不喜欢,也未投票给他,但都得承认他是总统,因为他的出任是符合法律的。克里斯玛型亦称为魅力型,是指合法性建立在领袖个人魅力基础之上,因群体信服他的能力,而心甘情愿遵从。[2]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抑或是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期,韦伯的合法性理论阐述皆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影响深远。随着社会发展,政治领域新问题的不断涌现,合法性理论也不断被各国学者丰富和延伸,以提升对新问题的解释力。
一些学者强调政治权力转为政治权威是执政者与社会大众双向互动的结果,而意识形态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论断对于分析现实政治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认同性与合法性是政治权威的应有之义,合法性蕴含着社会成员对政权的认同与自愿遵从,这虽与统治者自身努力说教和传输“奴化思想”关系巨大,但是促使政权认同因素落地生根与合法性建立并非仅此一方之功,其源自统治者与社会大众的双向互动,并且社会大众一方也非机械被动接收认知,而是依靠理性自觉进行认知活动。斯特恩伯格提出合法性的考察须从政府和社会大众两方面着手,而且强调政府和社会大众在互动中满足社会大众同意授予政府权力,政府能自觉拥有权力并以此施政时合法性才能建立。而罗思切尔德则更加强调,社会大众同意授予政府权力背后的因果密码,他认为其中认知和信仰是重要原因,即只有社会大众认为政治系统是符合其认知所得“正当”时,才会承认和决定赋予政治系统权力。戴维·伊斯顿在继承韦伯合法性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突出强调了意识形态在政治权威(政治权力合法性)建设中的地位,他将合法性来源概括为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三方面[3]。在伊斯顿那里,意识形态为合法性的建立提供了道义上的诊释,为社会大众与政治系统之间搭建了一架情感桥梁,有助于培养社会大众对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情感。结构和个人品质两方面是辩证继承了韦伯的合法性理论,并进行了新的归纳。合法性来源结构,强调的是具有稳定的政治结构能够提供合法性,如:韦伯的传统型和法理学就是一种稳定的结构,虽然稳定的结构形成的原因各异,但稳定的结构有助于合法性的传授。合法性来源个人品质方面,伊斯顿在这里淡化了韦伯所强调的魅力型人物的作用,强调了普通个体也能够通过某种手段赢得大批拥护者。可以说,以上政治学者合法性理论对于分析现实政治合法性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我国学术界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进行梳理发现,在韦伯之前,马克思著作中已经谈及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问题,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文中强调:“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它的官僚不再需要道义上的权威,便可以合法存在。”[4]很明显这段话论述了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及来源,强调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传统主要源自道义。恩格斯在《论权威》中则更加强调了工业时代合法性来源多数表决人的意志等。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话语体系中,政治权威同样是合法性与认同性的辩证统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是由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构成,被统治阶级因信服而“臣服”于统治阶级,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为何被统治阶级自愿服从?马克思主义给出了与韦伯截然不同的解读,他认为合法性根本来源是“现实的人”理性选择。“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现实的人”是置身于历史发展中的人,指通过对具体的人的需求出发考察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样,对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活的考察,必须从“现实的人”出发考察。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强调政治权威“是根据劳动各部门代表决定,或多数表决的办法”。具体到政治生活中,就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政治权威是人民群众基于现实需求而做出的理性选择。
二、社会身份认同化为政权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实践及新意识形态构建,从而实现社会个体身份重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传统社会下个体社会身份转变的一种革命实践和政治文化重构的社会变革,革命实践重塑了农民社会身份,新的政治文化颠覆了农民对政权性质传统认知,在此过程中,促发农民新的社会身份认同转化为政权认同,现实中展现出农民支持中国共产党及红色政权建设生动历史画面,鄂豫皖苏区红色政权建设就是在这样的逻辑支配下获得了政治权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重塑了农民社会身份。农民社会身份由社会阶级结构所决定,传统封建社会下农民是被统治阶级,这决定了农民社会身份首先是服从者、附属者,农民是排除于政权之外的。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所建设的红色政权赋予了农民新的社会身份,使得农民从社会的附属者一跃成为了社会的主人。从1929年至1931年,鄂豫皖多个县建立苏维埃政权,1931年鄂豫皖边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 《鄂豫皖苏区苏维埃临时组织大纲》明确提出苏维埃政权的性质,“苏维埃是工农代表会议,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是彻底替工农兵谋解放的政权”①,并且规定了具体的选举办法“凡满16 岁之男女而非剥削的劳动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②。此外,中国共产党通过动员和帮助鄂豫皖苏区农民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如:工会、青年团、妇女会。这些群众性组织功能上既为争取群体利益提供了组织保障,同时也塑造了新的社会身份,而新的身份则是与红色政权连为一体的。就鄂豫皖苏区工会来讲,有店员工会、手工业工会、雇农工会等,1931年成立了鄂豫皖特区总工会。工会的职责就是巩固苏维埃政权与反动政权作斗争,在此基础上积极为工人改善生活而努力等。青年团、妇女会也是同样赋予了青年和妇女新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而这些身份和地位的获得都是与红色政权的建立分不开的。鄂豫皖苏区红色政权通过法律和制度形式确立了政权性质和群众的社会地位,制度具有可预测性,尤其是在社会变革中作用明显,有助于群众对未来做出理性选择。苏维埃红色政权一方面对人民实行广泛和充分的民主,另一方面对剥削阶级及一切反动派实行专政,将剥削阶级及反动派排除于政权之外,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实践从而强化了人民新的社会身份,最终实现了群众身份认同向政权认同的转化。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通过构建新的政治文化重塑个体身份,具体实现方式是将民众政治和经济利益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使得民众与中国共产党成为利益共同体,并将国民党和地主豪绅等塑造成危害共同利益的敌人,动员民众进行革命反对国民党。意识形态宣传是鄂豫皖红色政权能够获得民众支持的重要原因,通过向民众宣传革命、阶级、国家、人民和敌人等政治概念,使当地民众能够认清自身新的社会定位和身份,从而在民众间建构起革命意识和价值观念[5]。
革命中意识形态主导着人们的认知体系,革命政党通过政治理论宣传来塑造政治权威。对于社会大众,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着自身身份和社会定位,这关乎政权认同。社会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多重身份,不同的身份认知会直接影响到个体行为。传统社会下,统治者以儒家文化为内核构建了庞大的维护皇权权威的意识形态体系,社会个体均被囊括其中,个体身份、社会定位清晰,其中“三纲五常”是人们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家长制成为应然群体管理之道,臣民文化被塑造。新民主主义革命理想是要构建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新的政权,革命过程与结果皆要求社会个体具有主体意识,广泛参与,这显然是反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革命,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鄂豫皖红色政权的建立就是伴随着基层传统意识形态的不断解构,中国共产党进行新的意识形态构建,农民身份发生转变,从而个体身份认同化为红色政权认同。新意识形态是相对中国基层传统意识形态,指马克思列宁主义。
自19 世纪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陷入全面危机之中,传统社会意识形态所维护的清王朝,在面对殖民主义侵略中的无能,人民生活不断恶化中已难以自圆其说,统治合法性消失殆尽,意识形态根基动摇。进入20 世纪,传统意识形态已处于全面解构的过程当中。新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是个全面和复杂的过程,需要采用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的对社会个体进行宣传的策略,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就是高度抽象化的知识体系,面对文盲居多、知识水平不高的群众现实,这种宣传策略可谓最佳选择。基于此,一些学者以概念来分解意识形态构成,以此视角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对新意识形态构建颇有新意和合理性。如:邹容将新意识形态解构为“革命”、“群众”、“阶级”、“共产主义”等关键概念来透析中国共产党的新意识形态的构建[6]。本文参考这种方法来阐释鄂豫皖苏区新意识形态构建如何实现农民新身份认同化为红色政权认同。首先这些概念向农民传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是其改造社会的根本途径,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之路,中国共产党尤其注重对革命的宣传,而革命的宣传是结合“群众”和“阶级”等概念一并进行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阶级的暴烈行动。”[7]那么革命是哪个阶级推翻哪个阶级? 哪些人是群众,哪些人是敌人? 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克思主义系统阐释了以上问题,对不同的社会个体皆赋予了新的社会身份,以此实现个体身份重塑。对中国阶级的划分和分析,最权威最详细的莫过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之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指导原则。毛泽东将中国的阶级划分为六大阶级,而且明确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群众,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是中间力量,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革命对象,很明显各个社会个体在其中都被赋予了新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在赋予社会个体新的身份同时,并进行了社会动员,从中实现了个体身份认同化为政权认同。在鄂豫皖苏区中国共产党常用歌谣的方式进行宣传和社会动员,如:当时鄂豫皖地区流传的《赤色苏俄歌》里面唱到“工人农人万众一条心……推翻反动的统治建立苏维埃。”[8]流传在河南信阳工人间的战斗歌谣“我们工人创造世界人类衣食住,不工作的资产阶级反把我们欺,起来! 起来! 赶快起来结成个大团体,努力奋斗,最后胜利都是我们的”③。还有广大社会个体间流传的“土豪和劣绅,压迫我穷人,火热又水深。这时候,我穷人赶快来革命,调转枪头杀尽那豪绅”等④。
三、利益认同化为政权认同——中国共产党始终为民谋利从而赢得民心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权威来源于 “现实的人”理性选择的基本理论,勘探鄂豫皖苏区红色政权建设需要回置于鲜活历史背景之中。任何政权的建设、稳固与发展都需要有夯实的群众基础,鄂豫皖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存续且在危难之时仍获得群众大力支持,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与民一条心,为群众谋利益而不懈地与反动势力作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鄂豫皖边界地区及周围频繁爆发战争,局势的动荡与反动势力的盘剥使得鄂豫皖地区民众生活可谓水生火热,如同鄂豫皖地区流传的歌谣唱的那样 “穷人身上两把刀、租子重,利息高,夹在中间吃不消。穷人眼前三条路,逃荒、上吊、坐监牢”[9]133。据统计仅1927年10月—1930年11月,3年间鄂豫皖边界地区先后经受了多次大小规模军阀混战,如:宁汉战争、蒋桂战争、蒋冯阎大战及冯玉祥部在河南与地方小军阀之间的战争等。频繁的战争得利的是战胜方的军阀,但“失败方”始终是民众,战争使得本身不那么景气的经济更加凋敝异常,群众生活秩序混乱失常。混乱的秩序所造成的不安全感,使得民众难以正常生活,热兵器时代的战争留下的创伤则是民众心中始终擦不去的泪痕。如同全国土地状况一样,鄂豫皖边区农村土地大部分集中于少数军阀、官僚、豪绅地主之手,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长期承受反动阶级的经济剥削。1927年以后鄂豫皖地区地租普遍增加,有些地方甚至增加了数倍,例如:黄梅县有些村地租翻了一番,黄破的田赋增加将近10 倍。光山、信阳等县的地租率基本在70%左右。同时,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无孔不入,多如牛毛,如霍邱,霍山、潜山等县,苛捐杂税种类均超过了60 种。高田赋多杂税使得当地群众生活面临破产边缘,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除此之外,国民党还多次对鄂豫皖苏区实行竭泽而渔战略[10]进行“围剿”红军,极大损害了群众利益。据万耀煌日记和访问录中记载,国民党将民众比作水,红军比作水里的鱼,认为通过抽干水的办法,可以将鱼一网打尽,这就是所谓的竭泽而渔战略。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国民党对鄂豫皖地区采取了竭泽而渔战略,给苏区群众带来了巨大人祸。国民党军队在鄂豫皖苏区“见房就烧”,觉得可疑的人全部抓走,期间错杀误杀的人不在少数。以红安一些地区经历四次围剿之后的数据可窥鄂豫皖苏区之惨状,红安七里区大斛乡1927年—1933年间,人口下降将近79%,房屋近70%被摧毁。⑤
为何在反动势力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国民党多次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红军,鄂豫皖苏区反而不断巩固和发展。通过对1927年以后鄂豫皖苏区民众生活的惨状,以及反动势力的所作所为,我们易得出鄂豫皖苏区不断巩固和发展的原因在于,相比于反动政府,鄂豫皖苏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红色政权始终回应群众需求,为群众谋利益,给了穷人除了逃荒、上吊、坐监牢三条路外的第四条路,就是有饭吃,将来还会过上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从而赢得了民心,红色政权树立了政治权威。
为农民谋利益,领导土地革命,恢复和发展生产。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是农民主要生产资料,农民拥有土地就等于有了生活保障,因此,土地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鄂豫皖苏区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抓住这一关键点,满足农民需求,领导土地革命,发展生产。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黄麻起义掀开了鄂豫皖苏区土地革命的序幕。《临时土地政纲》和《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是鄂豫皖地区早期的区域性土地法规。两个法规中明确提出,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有效回应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激发了农民革命的积极性,但是这个时期,土体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在确定农民土地所有权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正如王全营在《鄂豫皖苏区土地政策的演进》文中评价的那样,鄂豫皖地区土地政策起步是稳的,也是正确和成功的,但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解决的并不是很好,之后李立三、王明左倾错误也对鄂豫皖苏区土地政策起到了反面影响。[11]但是总体上鄂豫皖苏区土地革命回应了群众的需求,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群众生活大大改善。通过土地革命,获得土地的农民,深知个人利益与红色政权之间的关系,积极参加红军,保卫红色政权,这对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起了巨大推动作用。此外,一些农民虽然拥有了一定土地,但因其他因素导致难以恢复生产,如:缺少劳动力、种子、农耕工具等。针对于此,鄂豫皖苏区政府一方面帮助农民建立农民生产队、共耕队等组织互助生产,另一方面组织和号召妇女儿童,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帮助生产。鄂豫皖苏区各级政府还通过财政信贷渠道,给农业发放贷款,帮助贫苦农民解决耕牛、农具、资金等困难。鄂豫皖苏区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和方法,有针对性地帮助农民恢复农业生产,为群众谋实实在在的利益。
为弱势群体谋利益,提高社会地位,改善生存状况。传统社会中妇女地位偏低,处于弱势地位,在社会和家庭中并无权利可言,如:妇女不能进入宗族祠堂,不能参与家庭事务处理等。随着中国共产党对男女平等思想的传播,鄂豫皖妇女群体逐渐开始走向社会,成为社会的主人。鄂豫皖苏区积极引导和帮助妇女建立自己的组织——妇女会,妇女会是维护和保障妇女权利的群众性组织。同时,1929年《苏维埃问题决议案》中明确规定满足一定条件的妇女也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而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妇女的政治地位。随后通过的《婚姻问题决议案》中严令禁止一夫多妻、童养媳、蓄裨、强迫守寡等行为,拆除了传统封建伦理思想的压迫,根本上改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激发了妇女对于革命和支持红色政权的热情。妇女在社会中既是弱势群体,也是庞大的社会群体,人数占了总人口的一半,妇女积极性的调动,大大支持了红色政权的建设。为了支持红色政权,妇女会逐渐将组织广大妇女参加土地革命,拥护红军,保护鄂豫皖苏区作为中心工作。她们在红军作战时,帮助做好战争后勤保障工作,如:抬担架救治伤员,做军鞋送红军等。她们积极相应鄂豫皖红色政权的号召,积极支持红军队伍,如勉励自己的亲人当红军上战场杀敌,如鄂豫皖苏区当时歌谣所唱“我郎年纪轻,革命要认真;作战上前线,勇敢杀敌人”[9]130。同时,鄂豫皖苏区政府针对孤寡老人等生活困难群体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扶助政策,保障基本民生,如:1929年,《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政纲》规定要建立养老、育幼,保护残疾等事业。
鄂豫皖苏区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一条心,为群众谋利益,这与国民党对群众的利益损害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讲话中指出“鄂豫皖苏区能够28年红旗不倒……根本原因是我们党同人民一条心、军民团结如一人”,在鄂豫皖苏区群众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比中选择了支持和拥护红色政权。
注释:
①《鄂豫皖苏区苏维埃临时组织大纲》,1931年.
②《鄂东北各县第二次联席会议关于苏维埃问题决议案》,1929年.
③中共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肖章同志谈平民工厂[M].信阳党史资料汇编:52.
④陈降普.《革命歌词抄本》,红安县革命博物馆藏,档号:革360.
⑤红安县革命史编辑委员会.红安县革命史汇编(下册)[M].武汉:湖北省档案馆,196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