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诗与画
2021-03-22李方木李晓玮
李方木 李晓玮
巴赫金(Mikhai Bakhtin,1895—1975)在《对话的想象》(The Dialogic Imagination,1982)中曾经指出,小说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文类,“任何一种体裁都能够镶嵌到小说的结构中去”,无论是抒情诗、短剧等文学体裁,还是日常演说、宗教文章等非文学体裁。诚然,小说具有足够的开放性,如若我们跨过文学体裁的边界,放眼于跨媒介、跨艺术的文学表现手法时,巴赫金的这一论断仍然是有效的,尤其对于19世紀后期以来的小说作品而言。美国现代作家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1896—1940)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悲婉凄凉的爱情故事。盖茨比爱上了家境殷实的黛西,“一战”的到来暂时拆散了这对年轻的情侣,而战后盖茨比发现黛西已嫁作他人妇,他悲伤之余决定发愤图强。在五年左右的时间之内,盖茨比迅速跃升为纽约长岛的一位富豪大亨,通过举办大型宴会吸引黛西前来。她最终来了,但带来的却非幸福,而是杀身之祸:黛西驾车撞人,嫁祸于他,受害者的丈夫在一腔怒火中将盖茨比枪杀。这部小说一直被认为是20世纪20年代 “美国梦”幻灭的典范之作,代表着一种表面繁荣、暗藏危机的时代症候。然而,更加优美的是作家运用了语言与叙事技巧,以及跨媒介、跨艺术的表现手法。

正如英语中小说(novel)一词的形容词含义所示,小说叙事需要变换手法,以求新意。然而,小说家也会在作品中公开或隐蔽借用他人的诗歌片段或意象,这在文论家看来不过是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手段。根据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词典》(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中的界定,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事实上都是由其他不同形式的文本组合而成,对先前我们业已积累的语言、文学惯例以及表现手法不可避免的重复与改造,构成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话语本身。虽然菲茨杰拉德的这部小说着力再现的是纽约上层社会的奢靡生活,但作家还将目光转向了威尔逊等下层人的悲惨生活境遇,仿佛从对立面进一步展示了纽约社会阶层的分裂与对垒。作家在描写盖茨比豪宅之前,利用第二章开篇讲述了“灰谷”的恶劣生存条件:“那里的灰尘像小麦一样生长在山峦上和奇形怪状的花园里”,“唯一的建筑就是一排坐落在荒原边缘上的黄砖房”。这里的“荒原”意象最为直白地表明了这部小说与著名现代主义诗人托·斯·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的长诗《荒原》(The Wasteland)互文性,前一句也令人联想起长诗中诡异的诗句——“去年你种在花园里的尸首,/ 它发芽了吗?今年会开花吗?”如果说艾略特的“荒原”揭示了“一战”之后人类社会的文化贫瘠与生存困境,那么菲茨杰拉德的“荒原”则预示了小说人物(黛西丈夫布坎南及其情妇的丈夫威尔逊)之间不可避免的阶层冲突,预示了小说的悲剧性结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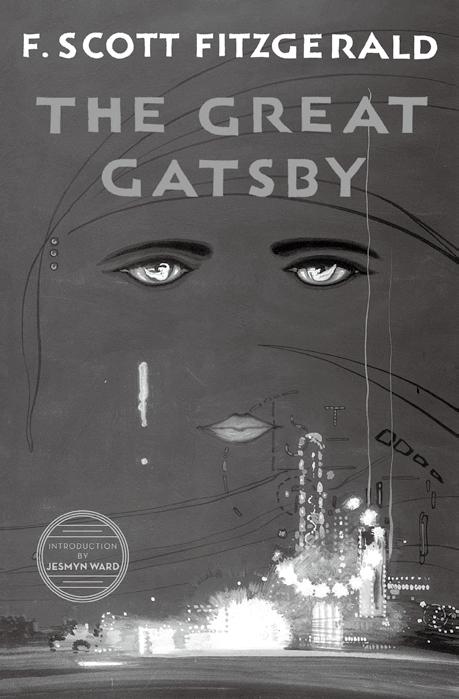
其实,菲茨杰拉德小说中艾略特的影子远不止于此,后者的另一首代表性诗作《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便是其中之一。这首诗中的主人公普鲁弗洛克是一位优柔寡断的求爱者,他一边直言“让我们快点去做客”,又在一遍遍地重复“总还有时间”,后来演变成 “我怎敢开口”这样的自我质疑,理由无非是“我有点害怕”。这样的反偶像形象俨然不同于中世纪骑士传奇中的男主人公,也无可堪比于19世纪维多利亚小说中男子气概十足的绅士,而是沦落为唯唯诺诺、碌碌无为的小人物!反观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盖茨比,当他历经五年艰辛与等待,终于再见旧日情人之时,“脸色像死灰一样苍白,两只手插在衣兜里,鼓鼓囊囊地像是装着沉重的东西”,甚至“像着了魔一样,一转身逃到客厅里”!显而易见,盖茨比紧张至极,这不就是另一个普鲁弗洛克吗?
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曾说,菲茨杰拉德的背后站着一个济慈(John Keats,1795—1821),此言不虚,尤其是在这部《了不起的盖茨比》之中。小说第六章中盖茨比向小说叙述者尼克深情讲述了自己与黛西的恋爱经历,在某个秋夜“他亲吻了她”,“他的嘴唇一沾她的唇边,她立刻就像一朵鲜花为他绽开花苞,于是他的理想便化为现实了。”这化腐朽为神奇的“一吻”,切实回应了济慈名诗《希腊古瓮颂》(Ode on a Grecian Urn)中的诗行——“鲁莽的恋人呵,你永远,永远也无法亲吻到 / 虽然只是一步之遥”。济慈笔下的古瓮将这幅情人之间欲吻不能的场景定格,是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在《拉奥孔》一文中所谓包孕性瞬间(pregnant moment)的典型代表,成为永恒美的表征,而这种略带缺憾的美,在盖茨比记忆中却成了现实。
也许我们还可以联想到华莱士·史蒂芬斯(Wallace Stevens,1879—1955)那首著名的意象诗《坛子轶事》(Anecdote of the Jar),其中有只缩影了人类全部艺术品的神奇坛子。“我”把这只圆形坛子放在田纳西州一座小山顶上,发现“它使得散乱的荒野 / 都以此小山为中心”。这里,人造物或艺术品与“散乱的荒野”形成鲜明的对比,甚至可以影响到后者的存在秩序和生存法则。诗人突出强调了人类艺术及想象的重要性,正因为它迥异于周遭世界的无序,才能成为值得保存或珍藏之物。菲茨杰拉德笔下茕茕孑立的盖茨比,矗立于纽约繁华都市的灯红酒绿而不染,全身心等待着自己心爱的黛西,虽然她已经不是往昔的模样。
我们还要看到,菲茨杰拉德在形式安排上的独具匠心。首先,小说共包含九章,这一幕出现于第六章,基本上位于全书的中间位置,如此一来前后形成一个总体的对称结构。菲茨杰拉德有意由此将这部小说的章节构成设计成为一个具象化的艺术品,恰好应和了济慈的古瓮和史蒂文斯的坛子外形,文字媒介因而在作家和读者想象中幻化成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其次,从叙事顺序上看,盖茨比青春之吻的这段回忆出现于这对恋人再次相遇之后,显然是现实并未如理想一样完美,或者并未如记忆中的过去一样完美,因而才会有了他对尼克的深情倾诉。可见,盖茨比将这一吻视作极其珍贵的记忆,宛如一颗镶嵌于王冠上的钻石。小说形式与主题内涵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統一,而作者有意使用两个省略号将这两段与前述内容隔开,更加突出了它在这一章节、甚至整部小说中占据的核心位置。
盖茨比被人射杀在自家游泳池之后,菲茨杰拉德给出了如下一段描写:“一阵微风拂过,水面波澜不惊,竟足以扰乱盖茨比躺着使用的充气垫偶然负重而变幻莫测的航程。一团落叶簇拥着,它便缓缓地旋转起来,像经纬仪的一只脚一样,在水面上划出一个细细的红色圆圈。”在这一幕中,落叶簇拥着气垫及其上的盖茨比尸体,显然是汩汩流出的鲜血随着气垫的微微转动,划了一个血色的圆圈。经纬仪(transit)可以看成现代意义上的圆规,而圆规正是英国玄学派诗人多恩 (John Donne,1572—1631)的名诗《离别辞:莫悲伤》(A Valediction: Forbidding Mourning)中的主导意象:“即使我俩的灵魂不一,/也只是圆规的两只脚而已;/ 你的灵魂,那只固定的脚不想动”,“然而当另一只脚向远处漂移,/ 它就会侧身过去附耳倾听”。这首诗中多恩用圆规的两只脚描绘恋人之间的别离与重聚,生动再现了爱情的伟大与温馨,而菲茨杰拉德将之转移到经纬仪和盖茨比身上,诗与小说的互文达至最大化。另外,落叶簇拥尸首的画面也是对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奥菲莉亚溺水而亡之景的再现,尤其回应了19世纪英国拉斐尔前派画家米雷斯(Sir John Everett Millais,1829—1896)的著名油画《水中的奥菲莉亚》。

值得注意的是,盖茨比的血液流入池水这一景象,还可以看作是一种晕染画(vignette)。根据《新编牛津艺术词典》的解释,这个术语自法语中的“葡萄藤”(vigne)一词演变而来,最常用于指代无明确边界的图样,画面边缘虚化而融入背景之中,也可以指建筑装饰中的蔓叶花饰,后来逐渐拓展至手抄本和书籍装帧设计领域,用来指称所有在书籍或章节末尾填充空白的小插图。我们完全从图书装帧的角度来理解盖茨比初吻以及去世这两幕的美学内涵。图书设计者往往会在某一章节的首尾放置一张小型的插图,尤其是结尾出现大片空白的时候。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e,1832—1883)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插画师,受出版社邀请曾为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以及弥尔顿的《失乐园》等多部文学名著创作铜版插图,虽然他的这些画作尚不能称之为补白插图,却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很多出版社利用小型插图实现多雷作品达到的效果。当然,《了不起的盖茨比》多个版本中并未出现此类的补白插图,这里是从隐喻意义上将主人公脑海中最美好的回忆以及盖茨比死亡视作书籍制作中的此类插图,两幕出现的位置也正好是在章节的尾部。
事实上,菲茨杰拉德也明确提到过绘画,小说最后尼克描述了盖茨比死后的心境,发现纽约的生活“简直就像艾尔·格列柯描绘的一幅夜景:阴霾的苍穹笼罩着大地,天边的月亮暗淡无光,上百座粗俗不堪、奇形怪状的房子一股脑儿簇拥在一起。”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一位伟大的画家,他对光线、色彩和人体姿势的运用都带有独特的个人风格。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细致描述一幅画,这样的手法在艺术领域被称为艺格符换(ekphrasis),即对艺术品的修辞性描绘,显然他将纽约的夜景艺术化,目的并非是美化,反而是利用人们心目中的格列柯艺术形象丑化纽约的夜生活:正是人们对金钱和欲望的不懈追逐造成了人的异化。小说中有画,画中有真相,这就是菲茨杰拉德通过跨媒介、跨艺术呈现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毋庸置疑的是,身为20世纪20年代的一位经典作家,菲茨杰拉德受到来自欧洲印象画派表现技法的强烈影响。后印象主义绘画的一大特色就是利用光影变换与色彩冲突表现画家内心的主观情感,菲茨杰拉德在描述到盖茨比首次开车载尼克出城会友时,后者看到窗外的景色:“阳光透过大桥上一根根钢梁透射过来,穿行而过的车辆全带上了一闪而过的光影,河对岸的城市迅速映入眼帘,一排排白色的高楼大厦像方糖一样整齐,如此宏伟的建筑是吝啬金钱的建造者根本无法想象的。”这里的画面感很强,正类似于后印象画派的典型作品:大桥上疾驰而过的汽车与阳光与钢梁共同营造了不停变换的光影效果,和煦的阳光普照着冰冷的汽车与大桥钢梁,冷暖两种色调制衡与调和于一处。这与尼克的心境不谋而合,独自置身于纽约,形似方糖的白色建筑线条感极强,充盈着城市的凌厉和锐气,给人以莫名的疏离之感;然而,尼克有幸结识了大人物盖茨比,内心自感温暖与慰藉。
结识盖茨比那个夜晚,尼克反思了自己孤身闯荡纽约这段时间的生活,时常孤独地走在夜晚的街头,看到“那些坐在车里等待离开的人物轮廓依偎在一起,情语绵绵,虽不知他们在窃窃私语什么,但却能听见他们从车窗里传出来的嬉笑声,还能隐约看到手指夹着燃烧的烟头随意画着圈圈”。当时的尼克刚到纽约不久,大都市的喧嚣无法掩饰内心的孤独与落寞,显然大街上的匆匆过客他并不认识。有鉴于此,作家借用了后印象画派模糊化的表现手法,隐去人物的典型外表特征,使其成为“人物轮廓”,虽然“情语”传来却“不知他们在窃窃私语什么”,这种看似矛盾的修辞暗含了尼克与人交际的欲望以及周遭世界的冷漠。最后一个意象也带有深意,尼克远离坐在车中的乘客,显然无法看清乘客的外貌,只有手中点燃的香烟随着车子的行进而上下左右晃动,仿佛是在画“圈圈”。这些乘车之人经历一番外出之旅,会回到温馨的家中,赢得手中烟圈一般的闭环式生活,而对面的尼克则身无所依,孤独地寻找自己的归宿。
其实,小说中找不到归宿的并非尼克一人。黛西丈夫布坎南的婚外情人茉特尔被丈夫关押在二楼卧室,室外的尼克透过窗户看到了她:“脸上的表情迅速地变化着,仿佛冲洗胶卷时,底片上的物景逐渐显影一样”。迅速变化的表情暗示了茉特尔当时五味杂陈的心态,或许正在谋划如何逃出丈夫威尔逊设置的囹圄,甚至打乱他的搬迁计划,成功逃至布坎南身边,而后者正不明就里地站在楼下。这里,自由和爱情占据了茉特尔的大脑,而机器的形象则统摄了尼克的想象空间,这里冲洗胶卷的过程被用来比喻茉特尔的表情变化,再合适不过。显然,叙述者的这一联想也暗示着他内心深处的偏见,即纽约都市民众的生活都已被机器同化,个人对自由和爱情的本真追求也可以像机器一样计算得出,而这样的情形在尼克的故乡则并未出现,那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过着朴实纯真的生活。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曾在《摄影小史》(A Short History of Photography,1931)中指出,摄影术的发明以“极为笨拙”的方式冲击了油画等传统艺术形式的统治地位,也可以说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革新了艺术的本质概念,拓展了艺术的领域范畴。换句话说,摄影以操作简单便捷见长,完全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而代表过去与传统的绘画技艺则需要大量时间、熟练技艺甚至是社会地位和金钱。由此看来,尼克对茉特尔等人的不屑其实昭示了他骨子里暗含的对新兴技术发明的不敏感、不感兴趣。作为一位现代主义作家的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以微妙的笔触写尽了20世纪前期美国民众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惶惑与内心纠结,他们挣扎于传统与现代、艺术与科技、都市与乡村、真情实感与金钱财富的夹缝,对这些人物的逼真刻画也成就了作家本人娴熟的叙事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