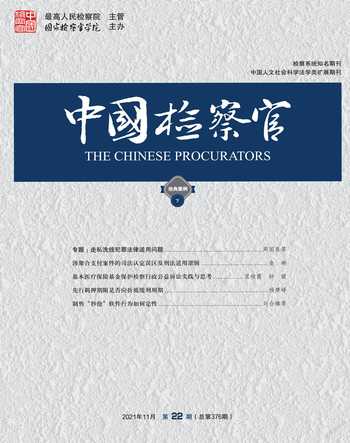追诉时效制度问题探析
2021-03-22刘文霞
刘文霞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陈某某与同案犯王某某系朋友关系,王某某对妻子吴某某公然出轨他人怀恨在心,多次向陈某某诉苦,请陈某某帮忙杀死吴某某,陈某某应允。1995年3月14日上午,王某某将吴某某骗至案发现场,劝说回心转意无果后手掐吴某某颈部,陈某某身处现场未予制止,直至吴某某死亡。之后,王某某与陈某某共同将吴某某的尸体捆绑装入纸箱,用三轮车运至附近江边。为防止尸体胀气上浮,该二人连续捅刺尸体四十余刀再捆绑石头沉入江中。作案后王某某潜逃异地,陈某某在当地正常生活。4月19日,被害人尸体被群众发现。
案发后,王某某被列为重大犯罪嫌疑人上网追逃,包含陈某某在内的五人因与王某某关系密切被公安机关采取监视居住措施,后因嫌疑排除均被撤銷监视居住。监视居住期间,陈某某做笔录一份,简单陈述了与王某某的日常往来,对其涉案情况予以隐瞒。25年后,王某某被抓归案,供述了陈某某涉案的事实,陈某某因此被抓。公安机关对陈某某启动报请核准追诉程序。
二、分歧意见
本案系报请核准追诉案件,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否满足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或死刑的启动报请核准条件;第二,是否属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情形。
1.本案对法定最高刑的理解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根据行为人所犯基本罪行结合自首、立功、从犯等从宽量刑情节,综合评估实际可能判处的刑罚,在此基础上确定法定最高刑。“所谓法定最高刑,是指和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法定情节相对应的刑法条款或者量刑幅度中的最高刑。”[1]具体到本案,陈某某只在现场旁观助阵,不存在故意杀人的实行行为,系从犯,且被害人对引发本案存在过错,应对陈某某减轻处罚在3到10年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本案法定最高刑未达无期徒刑,不符合启动报请核准的条件,且已过15年追诉期限,不应再予追诉,逐级退回公安机关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曾于1985年作出答复认为“刑法第76条按照罪与刑相适应的原则,将追诉期限分别规定为长短不同的四档,因此,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应当分别适用刑法规定的不同条款或相应的量刑幅度,按其法定最高刑来计算追诉期限。……虽然案件尚未开庭审判,但是,经过认真审查案卷材料和必要的核实案情,在基本事实查清的情况下,已可估量刑期,计算追诉期限”[2],基本上认同此观点,虽该答复现已失效,但蕴含的法律精神仍有参考意义。
第二种意见认为,法定最高刑的确定不应计入从轻、减轻或从重等刑法总则量刑情节,不应根据实际可能判处的宣告刑确定法定最高刑,而应以犯罪行为的一般情形为判断标准,即数额犯根据刑法分则相应条款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确定应当适用的量刑幅度取最高刑,情节犯根据情节较轻、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确定相应量刑幅度取最高刑,自首、立功、累犯、未成年人等情节虽因从轻、减轻或从重处罚而影响实际量刑,从而影响追诉必要性的判断,但并非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定量刑幅度时应予考虑的内容[3]。本案中基本犯罪行为是故意杀人并致1人死亡,应当适用的法定量刑幅度是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符合报请核准追诉的相应条件。
2.本案对陈某某是否存在“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限制”情形存在三种意见。本案发生在1995年,法定最高刑为死刑,已明显超过20年追诉期限。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4]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本案应适用1979年《刑法》第77条“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关于本案中陈某某是否存在逃避侦查的行为,第一种意见认为,只要开具过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文书,行为人不自动归案或不主动如实供述罪行的行为就是逃避侦查行为,陈某某曾因本案被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却未如实供述罪行,导致公安机关未能及时有效侦破案件,存在逃避侦查行为,不受追诉期限保护,应对其直接追诉,不需报请核准[5]。本案中陈某不如实供述即是典型的逃避侦查。
第二种意见虽然同样认为陈某某的行为应认定为逃避侦查行为,但提出不同观点。“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不应泛化,应限于更为积极、明显的逃避行为,根据期待可能性理论,对于出具了强制措施手续但行为人没自动到案的情况,不应评价为积极的逃避侦查行为,但对于已经被实际羁押却仍不如实交代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是一种积极对抗、逃避侦查的行为。
本案中,第三种意见认为,“逃避侦查或审判”的具体表现和把握标准应限于积极的、明显的、致使侦查或审判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的对抗行为,主要表现为司法机关已经告知其不得逃跑、藏匿甚至实际执行强制措施后而刻意逃跑或藏匿的情形,行为人是否实际到案受到羁押只是其行为是否达到“明显”“积极”逃避程度的判断要素之一,而非充分条件、绝对标准。对行为人犯罪后实施情节一般的毁灭证据、轻微串供、不主动如实供述等行为,即便是在人身羁押状态下,依然不宜认定为此处的“逃避侦查或者审判”[6],否则追诉时效制度会丧失应有的意义。
三、评析意见
(一)关于法定最高刑的确定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即在核准追诉程序中,确定犯罪行为应当适用的法定最高刑时,仅需确定行为一般情形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款和对应的量刑幅度,不宜计入从轻、减轻等量刑情节。虽然本案中陈某某没有实行行为,其帮助作用亦十分有限,减轻处罚后实际可能判处的刑期应在有期徒刑范围,启动报请核准程序确实浪费司法资源,但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文义解释“法定最高刑”应是指法定刑,与实际可能判处的宣告刑存在不同,本案中陈某某、王某某2人地位、作用差异悬殊,量刑情节容易判断,但司法实践中大量案件情节比较复杂,是否从轻或减轻处罚,幅度多大,往往因案件尚未进行追诉和审判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计入这些情节就会导致各司法机关自由裁量空间较大,扩大追诉与否的随意性,不利于追诉尺度的统一把握。
具体到本案,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本案不属于“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情形。1979年《刑法》第1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1997年《刑法》第232条的规定与此一致。可见故意杀人罪的条文规定了两个量刑幅度,以是否属于“情节较轻”作为适用的界限。对第二个量刑幅度“情节较轻”的情形,法律和司法解释未作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限于大义灭亲、防卫过当等能够让人报以极大宽恕的特定情形。显而易见,本案不属于此类,法定基准刑应适用第一个量刑幅度,即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符合报请核准条件。
其次,陈某某虽系从犯,但“对于共同犯罪,确定从犯追诉期限时所适用的法律条款与确定主犯追诉期限所适用的法律条款应当同一。这是共同犯罪追诉的一体性以及保证诉讼程序完整性的要求”[7]。这一立场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六批指导性案例“丁国山等故意伤害核准追诉案”中也得到了体现。[8]有学者认为,共同犯罪并非适用统一的追诉时效标准,而应按照各共犯人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分别计算追诉期限。[9]这一观点虽然考虑到了各共犯人之间在责任程度上的差异从而可以很好地贯彻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但该观点忽视了共同犯罪的整体性特征,不利于对共同犯罪的追诉。在共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阶段,就根据各共犯人的量刑情节确定不同的量刑幅度对应的法定最高刑,进而确定不同的追诉期限明显不具有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自首、是否属于从犯等量刑情节以及究竟应从轻还是减轻处罚争执不下的情况下,由公安机关决定不同共犯人各自的追诉时效难免流于恣意,也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最终可能会损害刑事追诉的公正性。
此外,如果采取共犯的从属性原理,对于共犯也应当根据正犯行为的违法性程度所对应的法定刑幅度确定追诉期限。[10]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从犯和主犯在责任程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也决定了对从犯应当判处的刑罚较之主犯可能显著为轻。鉴于追诉时效期限的确定与罪行、刑罚的轻重息息相关,对于从犯虽然原则上应当适用与主犯相同的追诉期限,但根据其罪行的轻重以及犯罪后的表现综合考量不是必须追诉的,仍然可以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不予追诉来实现,或基于节约司法资源的考量,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核准追诉规定进行修改,赋予下级检察机关在追诉必要性方面的部分决定权。
(二)对“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理解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即本案不属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情形,已过追诉期限。“法不强人所难”“不得自证其罪”是刑法的基本价值立场,如果将犯罪后不主动归案、归案后未如实供述视为追诉时效制度中规定的“逃避侦查或者审判”情形,则实践中几乎所有的犯罪人都存在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行为,“不受追诉期限限制”就成了僵尸法条、一纸空文,明显违背期待可能性等基本的刑法理论。因此,“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不应以是否实际羁押为判断标准,而应统一理解为积极的、明显的毁灭罪证、指使他人作伪证、串供、潜逃、隐匿等明显因行为人的原因致使侦查、审判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的行为。
本案中,陈某某被采取强制措施后虽未如实供述,但公安机在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只对陈某某进行了一次讯问,并未就其是否涉案进行重点讯问,而是围绕王某某案发前后的踪迹进行了解,之后即将陈某某释放,此后25年陈某某都正常生活,无毁证、串供等其他妨碍侦查的行为,更无潜逃或隐匿表现,不属于可延长追诉期限的情形。
[1] 黎宏:《刑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12页。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三)》(1985年8月21日颁布),2013年1月18日已失效。
[3] 参见李剑弢、江晓燕:《杨伟故意伤害案——如何确定犯罪行为对应的法定最高刑及追诉期限》,《刑事审判参考》2012年第1集。
[4] 对追诉时效规定的溯及力问题,理论及司法实务界几多争鸣,本文持“从旧兼从轻”立场,因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内容,在此不做展开。
[5] 参见王勇:《从南医大女生被害案看追诉时效之运用》,新浪网http://k.sina.com.cn/article_5510098095_1486d6caf01900vshv.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10月8日。
[6]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51页。
[7] 同前注[3]。
[8] 参见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批指导性案例“丁国山等(故意伤害)核准追诉案”(检例第21号)。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涉嫌共同故意伤害罪的四名犯罪嫌疑人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决定一并核准追诉;从犯闫立军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9] 同前注[6],第649页。张明楷教授举例认为,甲和乙共同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甲为主犯,乙为从犯,对乙应当按照减轻处罚后适用的法定量刑幅度的最高刑即3年来确定追诉期限;A和B共同故意杀人,根据案情,对A应适用“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对B(从犯)应当适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以此法定最高刑作為确定对乙追诉期限的判断标准。
[10] 参见陈洪兵:《追诉时效的正当性根据及其适用》,《法治研究》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