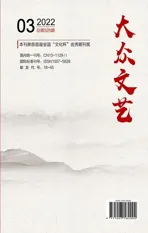蒋春霖战争词之赋笔特质小议
2021-03-16吉映澄
吉映澄
(南昌理工学院,江西南昌 330044)
一、“赋笔”在诗词中的表现
词学界对“赋笔为词”的讨论, 主要集中在“赋笔”铺陈直述的特点。刘勰在《文心雕龙》言:“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这种特征,使“赋笔”带有很强的纪实性。这一点上,杜甫开“以赋入诗”之先河,对后世诗词的创作都有着深远影响。宋词人柳永专力慢词,也大量使用了赋笔手法,对词境亦有着极大的开辟之功。
朱庸斋《分春馆词话》评价鹿潭词:“鹿潭长调多用赋体。赋体笔力需健挺,积健为雄,始无拖沓之弊”。蒋春霖早期专力诗作,所剩百余首诗稿大多取法老杜而深得其髓,风格恢雄沉厚。尽管中年蒋春霖因感于“无以蕲胜于古人之外”而焚弃诗稿,但取法老杜的经历是成就鹿潭词中“真实力量”的重要因素。
(一)杜甫之“以赋为诗”
郑倖朱《苏轼以赋为诗研究》中曾对“以赋为诗”有如此定义:“凡在形象上运用赋的重视空间表现的铺陈技法, 在结构上参酌汉赋之主客问答及曲终奏雅的形式, 在语言艺术技巧的表现上参考赋的大量用比喻、铺排、夸张、白描等特色, 在风格上呈现汉赋铺张扬厉的巨丽之美, 则称之为‘以赋为诗’”。这一定义同样可以评价“以赋入词”。不管是子美诗还是鹿潭战争词,皆注重正面描写,直言本事,因而能够将战时的生灵涂炭、众生凋敝刻画得淋漓尽致。相较子美诗,词这一载体赋予了蒋春霖更多的抒情空间,能够在直言本事的同时,又充分发挥出赋笔融情于景的优势。以蒋春霖《水龙吟·癸丑除夕》和杜甫《哀江头》为对比,二作皆是感怀曾经繁华的城市在战乱后的满目疮痍,杜诗由于诗律限制,多化用典故,如“明眸皓齿今安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来展现而今长安的物是人非,所蕴含的悲剧力量更加厚重。反观鹿潭词,“旧游嬉处,而今何在,城闉空锁。小市春声,深门笑语,不听犹可”同样是感叹物是人非,但由于词的音乐性和更灵活的节奏,能够以更直白的笔法来展现悲叹之情。
杜甫在赋的造诣极高,他本人也颇为自负,曾言“赋或似相如”(《进雕赋表》)、“赋料扬雄敌”(《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也正因如此,杜甫才能够驱赋入诗,达到“以赋为诗”的极致。在诗创作中,杜甫之排律和长篇古诗受赋笔影响最深保留了赋体长于铺叙、丽辞雅义的艺术特点,又讲究练字,将浩大繁杂的社会事件融入诗作,从而将“以赋为诗”真正在内容、体裁和技巧上都熔铸一炉,达到诗歌表现方法的一种突破。通过赋笔,杜诗能够将所见的事件、场景、人物的种种复杂状态展现地细腻周至,富于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以《北征》为例,胡小石在《杜甫〈北征〉小笺》中说:“《北征》,变赋入诗者也,题名《北征》,即可见之,其结构出赋……”。《北征》从开头“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简单明了地点明全诗因由,而后到“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句,整段叙述自己在政治上有抱负却无法作为的苦闷,正契合了作赋之“序以建言,首引情本”的结构。此外,不同于比兴手法多有隐晦描写,《北征》全诗对“流血”“白骨”等意象直言不讳,这种对战争惨相赤裸裸的描写不独《北征》,《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悲青坂》(青是烽烟白是骨)等都同样以这种直接的描写凸显出战争的残酷。章法结构上,杜诗“长篇必分段落,每段必用提顿以见起,用结束以见止”,体现了赋体开合跌宕、起伏跳跃的特点。不难发现,赋笔是杜诗之所以成就诗史的重要一环。而蒋春霖效法老杜,自然学到了“赋笔入词”的特质。
(二)柳永“以赋入词”
后世对蒋春霖和柳永词作的评价有诸多相似,谭献分别在《箧中词》中评蒋春霖为“倚声家老杜”、《复堂词话》中评柳永“耆卿正锋,以当老杜”;又如金武祥评鹿潭词“盖几几有饮水处,无不唱鹿潭词”,而叶梦得称屯田词“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这与他们多用便于铺陈的慢词,且长于赋笔的特质是分不开的。
柳永虽放笔慢词,但是章法精严。在叙事写景方面,吸收汉大赋铺张扬厉的文法,其词关于宫殿堂皇、都市繁华的描写极多,极尽夸张铺排之能事。且看《望海潮(东南形胜)》: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此词为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柳永至杭州干谒知杭州孙沔时所作。全诗纵览杭州,上片极力铺排西湖之富庶繁华,下片则描绘出游杭州的盛景。此外,《破阵乐(露花倒影)》写京都气象,《一寸金(井络天开)》写蜀地风土,以及其他展现都邑风光、投献达官贵人的词,无不是层层铺叙,笔墨酣畅,不管是内容抑或笔法,屯田词皆可谓与汉大赋一脉相合。
在写景抒情方面,柳永更是深谙此道,直接以六朝赋笔入词,不但长于摹写景物,更能够以极细腻的笔触融情于景。以《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上片为例: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首两句化用诗经《风雨》“风雨潇潇”,通过视觉、听觉营造出清冷的秋意,“暮”字点出时间的同时,更加深了苍茫之感。而后以“渐”引领时间变化,“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三段三景,以眼见之苍凉抒发词人心中无限的萧瑟。《文献雕龙·诠赋》云:“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八声甘州》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而蒋春霖在这一点上,可谓不输柳永。
二、蒋春霖战争词之赋笔
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对当时中国整个时局造成了剧烈动荡。蒋春霖出身宦官世家,又作为传统的中国文人,对于这种极大打击地主阶级的革命团体有着本能的阶级敌视,其词作中,多有战乱惨相的描写,保留的文学现场在开辟词境的同时,亦为史家提供了研究依据,故后人赞蒋春霖为“倚声家杜老”,认为其词是“词史”的代表。
在上文中我们讨论了“赋笔”在杜诗和屯田词中的“词心”和“词史”体现。而对于鹿潭词来说,前人多讨论的是其“词人之词”的艺术价值或“词史”的历史意义。关于蒋春霖以“赋笔”将“词心”和“词史”二者有机合一的探讨仍不多见。在我看来,“词心”更注重词抒发感情的功能,以身外之境触动身内之境,以内心真实的情感体验诉之笔端,“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也”,进而以一人之愁苦,写一国之愁苦,这也就注定了“词心”更注重感官上的刺激。而“词史”则是词学发展到一定高度后,倚声家不满词的微末地位,赋予词更多纪事、议政的功能的要求,更注重指向社会时局,多以“大题目、大意义”出词。因此,“词心”和“词史”,有一个根本意义上的不同,即创作冲动的来源不同,“词心”之创作冲动,来源于个人的所见所闻,是词人的“身内之境”受到“身外之境”引动而萌生的“不自觉之一念”,驱使着词人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来释放个人的情感。而“词史”则是词人在历经世事后,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以词的方式记录下来,以达到“存经存史”、针砭时弊的目的。
(一) 鹿潭战争词的赋笔特质
1.“词史”之赋笔
宗源瀚《水云楼词续序》载有鹿潭一段自述:“欲以骚经为骨,类情指事,意内言外,造词人之极致”。可以看出,蒋春霖继承了“骚经”的传统,在词作创作当中有意识地托兴深微,引类譬喻,这一点,与常州词派的词学观念几为同出一辙。但鹿潭又标榜“词祖乐府,与诗同源”,故鹿潭之战争词亦多感于世事而作,在立足常州词派词学观的同时,又能够摆脱比兴的局限。因此,鹿潭之战争词,能够尽致地展现出战争后民生的苦难、凋敝,直击读者的心灵。以《扬州慢》(癸丑十一月二十七日,贼趋京口,报官军收扬州)为例,1853年,太平军一月下武昌,二月沿长江连克九江、安庆、芜湖,三月破金陵,定都南京。清朝廷军事上的一系列失利,使包括蒋春霖在内的众多文人都生出社稷破碎的仿徨。回望宋朝年间金人马踏扬州,姜夔也是在同样的心绪下,创作了《扬州慢》这一词牌。我们可将两首词一同比较:
姜夔《扬州慢》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
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
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
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
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
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蒋春霖《扬州慢》
野幕巢乌,旗门噪鹊,谯楼吹断笳声。
过沧桑一霎,又旧时芜城。
怕双燕归来恨晚,斜阳颓阁,不忍重登。
但红桥,风雨梅花,开落空营。
劫灰到处,便司空见惯都惊。
问障扇遮尘,围棋赌墅,可奈苍生。
月黑流萤何处?西风黯、鬼火星星。
更伤心南望,隔江无数峰青
可以看出,蒋春霖之《扬州慢》应该是有意识的模仿姜夔词。两者皆是以遭受兵燹后的扬州为起兴对象,于第二句尽写扬州如今的沧桑,第三、四句则抒发时过境迁之感。到了下阕则又些许不同,姜夔是寄情杜牧,遥想杜郎若是看到一梦十年的扬州变成如今狼藉会是何等惊怖。而蒋春霖则是用自己的切实经历痛诉苍生的苦难。若说千岩老人以为姜夔之《扬州慢》有《黍离》之悲,蒋春霖《扬州慢》结尾处化用了辛弃疾“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与钱起“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两句又何尝不是如此!谭献《箧中词》评其为“赋体至此,高于比兴矣”,可谓善评。
2.“词心”之赋笔
鹿潭之战争词,沉郁顿挫有之,凄壮清雄有之,悲壮激越有之,幽涩皱瘦亦有之。总的来说,鹿潭战争词是以细腻的笔触,将自己最真实的情感注入苍凉的悲歌。谭献将容若、莲生、鹿潭并称为“词人之词”,便是由于此三家皆是以情真语真胜。鹿潭之战争词,以性灵之笔,写出战争种种凄惨现状,又因赋笔特有的细腻,所叙所讲,无不跃然纸上,使人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乃至于到了哀切至极之处,则使人释卷掩面,不忍卒读。我们且看一首《台城路》:
金丽生自金陵围城出,为述沙洲避雨光景,感成此解。时画角咽秋,灯焰惨绿,如有鬼声在纸上也。
惊飞燕子魂无定,荒洲坠如残叶。树影疑人,鸮声幻鬼,欹侧春冰途滑。颓云万叠。又雨击寒沙,乱鸣金铁。似引宵程,隔溪燐火乍明灭。
江间奔浪怒涌,断笳时隐隐,相和呜咽。野渡舟危,空村草湿,一饭芦中凄绝。孤城雾结。剩罥网离鸿,怨啼昏月。险梦愁题,杜鹃枝上血。
在我看来,这首词的叙事手法若比之电影,像极了纪录片《女巫布莱尔》,此二者皆取真景,叙真事,景事结合,便令人生出毛骨悚然之感受。读此词,惊燕、荒州、树影、颓云、燐火、野舟、孤城,历历眼前;画角、鸮叫、落雨、奔浪、断笳、离鸿、杜鹃,声声耳边。无怪乎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评曰:“绘声绘影,字字阴森,绿人毛发,真乃笔端有鬼。”而这一切,虽非作者亲历亲见,乃是听金丽生所叙逃亡历程想象而得,但依旧传神地描摹出好友一路惶惶然而草木皆兵的心理状态,足见鹿潭心思细腻之至,赋笔手法之深厚。全词的创作手法,则突破了传统词的局限,取象自好友的一路见闻,却不局限于这些意象,直写金陵兵乱,不啻于是一篇《哀金陵赋》。吴梅言:“鹿潭不专尚比兴,《木兰花慢》《台城路》固全是赋体,即一二小词,亦直言本事,绝不寄意帏闼,是真实力量,他人极力为之,不能工也”,这种真实力量,也正是鹿潭战争词中以赋笔写词心的体现。
(二)“词心”“词史”于赋笔中的融合
蒋春霖曾批判当时的词学创作有“偎薄破琐,失风雅之旨”之弊,提出“欲以骚经为骨,类情指事,意内言外,造词人之极致”,将骚经的传统作为填词的中心。而在创作实践中,蒋春霖则要求“情至韵会,溯泻风流,极温深怨慕之意”。“情至韵会”似可以《文心雕龙》之“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相印证,即创作冲动来源于词人对外界(“风雨山川”)的感触。由此推及“类情指事”便能明白其真正含义是以真情(“赤子之心”)来感受、反映身外之境。另一方面,“意内言外”由张惠言首次用于词学评论,言“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将词比于《诗》之比、兴、变风之义,肯定了“词”实际上是近乎“骚人之歌”的。蒋春霖对此深以为然,同样在作品中多有寄寓人生感怀,即“溯泻风流,极温深怨慕之意”。这一特点,又与冯熙评秦观之“故所为词,寄慨身世……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不谋而合。
同样以《台城路》(惊飞燕子魂无定)为例,这首词被认为是鹿潭“词史”之代表作,固然词中对于金陵战乱有着极为详细的描写,但是我们同样要注意的是,序言中说:“金丽生自金陵围城出,为述沙洲避雨光景,感成此解”,这个“感成此解”很重要,按照创作冲动来源来说,这首词是由于蒋春霖听闻朋友一路的见闻有感而发。而从词心特质来说,《台城路》代友人而言心事,若没有一颗敏感细腻的赤子之心,断无可能如鹿潭一般写得如此传神而扣人心弦。情真同时,全诗直写金陵战乱,其景亦真。正如况周颐所言“真字是词骨”。从“词之穆境”来说,蒋春霖在作词过程中,感同身受友人所说之景,可谓“斯时若有无端哀怨枨触于万不得已”,而词序末尾之“画角咽秋,灯焰惨绿,如有鬼声在纸上也”,不正如“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虚晃、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之说?
求诸鹿潭之大多战争词,几可皆为所观所闻有感而作,如《木兰花慢》(甲寅四月,客有自金陵来者,感成此阕),《淡黄柳》(扬州兵后,平山诸园皆成榛莽。为赋数词,以寄哀怨。诒园索稿,作此谢之,悲从中来,更不能已)等词,皆可看出是“感成此阕”或“更不能已”而写就,这都可看作是蒋春霖赋笔中“词心”的流露。
如前文所说,“词心”是蒋春霖创作冲动的来源,战争带来的惨相无时不刻不触动着蒋春霖敏感的心灵,人生的失意,乱世的艰难,种种郁结之气梗在肺腑,使他时刻有着“无端哀怨”需吐之而后快,加之蒋春霖对词创作的要求和早年的诗功,蒋春霖“以赋入词”的结果似乎也可以说是一种必然。而“赋笔”直言本事的特质,使鹿潭词自然而然地被烙上时代的印记,折射出太平天国的时局变迁,因而成就了“词史”。
注释
:①朱庸斋.《分春馆词话》.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92页.
②王京州.《杜甫以赋为诗论》.湖南:中国韵文学刊,2006年12月,第20卷,第4期,43页.
③胡小石.《胡小石文录》.南京:南京大学,1979,10页.
④况周颐.《蕙风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卷一,10页.
⑤刘永刚.《水云楼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附录二·序跋,337页.
⑥谭献.《箧中词》.“或曰:(鹿潭)何以与成项并论?应之曰:阮亭葆馚一流,为才人之词.宛邻止庵一派,为学人之词.惟三家是词人之词……”.台北:鼎文书局,1971年,292页.
⑦刘永刚.《水云楼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卷二,108页.
⑧陈延焯.《白雨斋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五章,110页.
⑨吴梅.《词学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九章,177页.
⑩况周颐.《蕙风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卷一,6页.
(11)况周颐.《蕙风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卷一,10页.
(12)况周颐.《蕙风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卷一,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