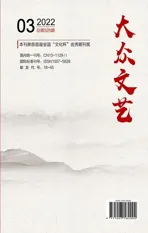论小川洋子《妊娠日历》中的女性自我意识
2021-03-16谢小洁
谢小洁
(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通 226000)
《妊娠日历》以妹妹的视角通过日记的形式记录姐姐的妊娠过程,姐姐和姐夫对妊娠没有表现出初为人父母应有的喜悦,而“我”则将可能致癌的葡萄柚做成果酱给姐姐吃,企图伤害胎儿的染色体。
围绕小说《妊娠日历》,一种研究方向着重关注“我”对胎儿没来由的恶意,另一种研究方向则从母性反转的角度分析姐姐对胎儿的冷漠态度,这一类分析都指出姐姐的态度区别于传统观念上被神圣化的母性,强调以医学、客观的视角描写妊娠过程是为了表达对母性的一种反抗。《芥川赏选评》中对《妊娠日历》有以下评论:“在妊娠、分娩的女性更深层次的生理和心理过程中有着男性所无法窥视的部分”“只能说这是只有女性才能理解的心理行动”。这说明“妊娠”作为女性独特的体验,由女性来描写具有其创新性和不可替代性。本文将尝试结合第二次女性主义解放、反母性文学潮流等背景以及对姐姐、“我”、姐夫三个人物行为分析,廓清小说中对待妊娠的反常表现与女性自我意识的关联。
一、注重体验独有的妊娠过程
通读小说以后不难发现,姐姐不同于寻常的孕妇,她的反常之处归结起来有两点:超声诊断时的表现、临产前的恐惧。
第一点反常之处表现在超声诊断时对胎儿照片的冷漠。她喜欢被诊断用的透明软膏抚摩肌肤时的奇妙感觉,当检查结束后,护士擦拭肚子的速度过快让她觉得不过瘾,出诊室之后,发现肚子上的软膏被擦拭的一干二净,这让她感到很失望。透过“奇妙”“过瘾”“失望”这些字眼,姐姐始终在描述一个神奇的体验过程,这个体验过程包含软膏抚摩肌肤的奇妙、护士用刚刚洗过的纱布为其擦拭肚子的触感。这些全都是姐姐对身体的感知过程。姐姐对身体的触觉如此敏感,却对胎儿的感知视而不见。本来作为监测胎儿发育状况的超声诊断,姐姐重视其带来的美妙触觉更甚于从中得知的胎儿的状况。换言之,她关注自己更甚于腹中胎儿。
在人们的印象中,符合常理的妊娠女性应当是充满母爱的。从姐姐得知自己怀孕时的反应和做超声诊断时的关注点,可以推测她对新生命的降生并没有太大的期待,更谈不上母爱,这就表现出了与传统母亲形象的冲突。波伏娃在著作《第二性》中曾经指出根本没有与生俱来的、神秘的母性本能,所谓“母亲”的天职和使命感,皆由后天教育、经历所形成。照此逻辑来看,母性本能只是传统父权制度为女性套上的枷锁,笔者认为姐姐的反常表现不只是对母性的反抗,更多的是姐姐作为女性的主体想要拥有体验的权力。
回溯日本的女性文学史,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女性文学显著出现了强烈的反母性特征,挑战生育、母爱。例如大庭美奈子表达对妊娠的憎恶,“在20世纪的今天,妊娠不再是结果的象征,而是不毛与破灭的代名词”;三枝和子彻底否定生育,“我,闭上眼睛。出于一种憎恶,无论如何我也得将这个孩子杀掉。出于一种憎恶,出于一种对生命渐次形成的恐惧。人生人,世上没有比这种行为更丑恶的了”;高桥多贺子描写一个厌恶、甚至想杀死自己女儿的母亲,“我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笔的中间, 将笔的末端举到右眼前, 闭上左眼, 将笔尖丝毫不差地向初子指去”。这些作品都站在父权制的极端对立面,鲜明地表现出女性摆脱母性束缚的强烈意识,反观《妊娠日历》,姐姐面对妊娠这件事,并没有刻意回避、厌恶妊娠。她认真地坚持每天早晨测量体温、食欲不振时想象摆放着玫瑰花的餐桌上的葡萄酒杯、冒着热气的汤和肉菜、妊娠反应过后任性地提出想吃枇杷雪葩、担心难产等等。姐姐更像在认真体验女性独有的妊娠过程,她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体感受和精神体验中,因此可以说作为妊娠主体的姐姐,在这种与常相悖的表现下积极意识到自我。这是一个将自己看作主体,注重体验自己人生经历的过程。
综上,姐姐对待妊娠的反常举动反映女性的自我意识,具体表现为关注女性主体而并非胎儿主体,注重体验女性特有的人生经验。除此之外,姐姐的女性自我意识还体现在苦恼对孩子没有选择权上。
二、注重女性自由支配身体的权力
在七月二日的日记中,姐姐从医院回来后一脸不悦,向“我”描述对分娩、未出世的孩子的恐惧。
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样美好的。只要从我的肚子里生出来,他便注定是我的孩子了,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哪怕孩子半边脸上都是红斑,或者手指全连载一起,或者是无脑儿,或者是连体儿……
姐姐的第二点反常之处在于她说出一连串可怕的词语“红斑”“无脑儿”“连体儿”,表达害怕这些可怕的词语将会成为她的孩子,却没有担忧孩子将会有缺陷。姐姐所表达的“选择孩子”是一种从她自身出发的单向选择,换言之,是母亲选择孩子的权利。母亲选择孩子的权利与兴起于20世纪早期的女权主义中女性选择堕胎的权力有异曲同工之处。波伏娃认为女性之所以长期社会地位低下,是因为男性通过劳动创造价值,成为主体,女性则无法摆脱生育这一生物功能而成为依附者。她把生育看作是女性受到的生殖奴役,如果女性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这对女性解放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怀孕也可以成为一个合理的、可以支配的部分,而不是受到它的奴役。无论是“堕胎权”还是小说中姐姐想要“选择孩子”的权力,其实本质上都体现“妊娠”是女性可以自由支配的部分。因此,姐姐的这个反常现象可以说是以女性为主体,自由支配身体的女性自我意识的一种表象。
总的来说,姐姐是妊娠的主体,在妊娠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不是神圣的母亲形象,将一切注意力集中在自我体验身上,并且意识到自己和胎儿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
三、追求自我价值
(一) 妹妹关注姐姐的个体性
“我”作为妹妹,也没有对姐姐妊娠表现出兴奋,首先,“我”的反常之处在于没有将胎儿看作是作为“人”的生命体的存在;其次,“我”比姐姐更关注她身体的变形。
“我”第一次从姐姐那儿看到照片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胎儿影像,认为是“蚕豆状的空洞”。在脑子里试图理解婴儿时,使用的关键词是“染色体”,由“染色体”联想到婴儿的形状。“我”观察着姐姐身体的变形,脑子里在想着“胎儿的染色体是否在正常的增加?在她隆起的肚子里,蝴蝶双胞胎幼虫是否正连在一起蠕动着”? “我”理解的婴儿是“染色体”,杂志上的“染色体”看起来像是蝴蝶双胞胎幼虫,每当“我”联想起胎儿,就会想到蝴蝶双胞胎幼虫。此外,“我”还觉得姐姐的身体就像是一个“大脓包”。胎儿的这些在我心里的印象,除了非生命体就是“蝴蝶双胞胎幼虫”,我从未把胎儿视作人类、具有生命现象。非人类、没有生命现象的胎儿在我眼中是姐姐寄宿在身体里的一个“大脓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表现存在着否认女性妊娠的意味。否认妊娠,否认姐姐是孕育生命的媒介,即承认姐姐的个体性,因此,“我”这一对妊娠的反常行为体现了女性意识到自我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价值。
“我”兴趣盎然地观察着姐姐身体的变形,表现出比姐姐自己更关心的态度。姐姐的身体从胸部到下腹部大胆地鼓了起来,进入到第三十周时,姐姐的脸颊、脖子、手指和脚脖子等地方也长起了没有弹力的脂肪。她的身体所有部位的组合都失去了应有的比例。在“我”看来,妊娠反应过后,姐姐变得食欲大增,姐姐对自己的身体变形一点都不关心,只是一味地吃东西,“我”看着姐姐狼吞虎咽地吃果酱,试着劝她不吃,但没有任何效果,姐姐依旧快速地吞咽果酱。姐姐妊娠反应时无法忍受食物的味道,妊娠反应结束后导致暴食,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发胖,身体轮廓被松弛的脂肪包裹着。因此,与其说“我”关注的是姐姐因为妊娠变形的身体,不如说是姐姐因为妊娠丧失的“自我”。
对待姐姐妊娠这一件事,“我”没有说出表示恭喜的话语,反而将胎儿视作非人类、无生命现象的存在,一直注视着姐姐发胖的身体,“我”的反常背后,或许意识到女性个体的自我价值以及深藏着对女性因妊娠有可能丧失“自我”的敏锐嗅觉。
(二)降低男性的价值
姐夫这一人物既担任了胎儿父亲的角色,同时又是家庭中唯一的男性成员。在父亲的角色中,关于胎儿的事情,“我”在日记中两次提到,姐姐和姐夫两人都没有谈论妊娠一事的意思,姐姐和姐夫从不提婴儿的事情。作为父亲的姐夫,同样没有表达出对胎儿应有的关注。“我”眼里的姐夫是个无趣、自以为温柔、没有主见的男性。姐妹俩父母病逝之后,家里的过节气氛越发淡薄,然而姐夫的到来并没有任何的改观、姐姐半夜提出想吃枇杷雪葩的要求,姐夫不想出门只是 怯怯地看着姐姐,姐姐心情不好时,他“无计可施地抱住姐姐的肩膀,并勉强做出自认为这是姐姐最希望看到的温柔的表情”。“我”甚至怀疑姐夫对姐姐妊娠所起的作用。姐夫代表着一个无所作为的男性形象,在家庭生活中,其他两个女性都不谈及妊娠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开口谈论。他就像是一个对照形象,代表无主见和家庭地位被弱化的男性,凸显小说中另外两个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
四、结语
奥野健男曾经指出,现代已经是女性叙述自身的时代了。女性书写自己的体验、反映女性的隐私、心声,正如芥川赏选评中所说,《妊娠日历》中真实的妊娠体验非女性不能懂。人们普遍认为,符合常的妊娠时期的女性理所应当充满母爱,但《妊娠日历》中却充斥着对妊娠的冷漠态度。对于《妊娠日历》中表现出的反常式的妊娠态度,以往的研究大多认为其追随反母性文学潮流。但反母性文学笔下的女性对母性所持的否定态度强烈且极端,而《妊娠日历》中的女性虽不推崇母性,但也没有刻意回避母性甚至憎恶母性,反而在用自己的方式认真体验妊娠这一女性独有的过程。因此,笔者认为,与其说小说中反映了女性对母性的反抗思想,不如说反映了女性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她们更注重女性独有经验的自我体验过程,重视探讨自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