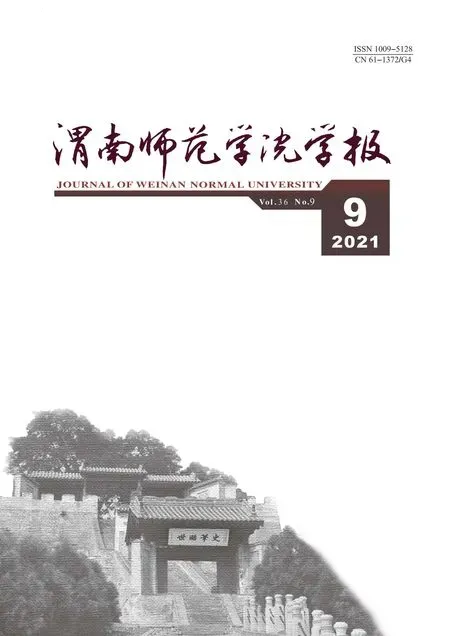乡村题材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收获
——评王旺山长篇小说《铁花》
2021-03-08任葆华
任 葆 华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714099)
陕西作家王旺山的长篇小说《铁花》以实证的精神真实地还原了一个世俗化的乡村世界,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乡下人的现实存在状态和精神世界。作为一部地方性写作的典型文本,《铁花》充满了丰富而鲜明的文化内涵,犹如一桌地域文化的盛宴。尤为值得称道的是,该小说以舒缓的叙事节奏建构了一种慢的小说美学,并且在艺术上做了一些探索。依我个人多年的阅读经验和审美感受来判断,《铁花》应该是一部比较优秀且富有特色的乡村题材现实主义小说,值得阅读和研究。
一、真实地还原了一个世俗化的乡村世界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1所以,要想真正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就必须先理解中国社会的乡土本色。王旺山的小说《铁花》真实地还原了一个世俗化的乡村世界,为我们理解乡土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中国传统上是个农业大国,靠土地吃饭,底层乡下人的生存、生活与土地密不可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耕作繁衍于斯,最后也多终老于斯。因此,中国底层的乡下人对于土地大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眷恋乡土,安土重迁,生活的环境多是熟人社会。然而,随着社会时代的变革,乡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昔日土地在他们心目中至尊的地位渐已动摇,甚或在新一代人心目中已难以为继。小说《铁花》以实证的精神真实地还原了一个世俗化的乡村世界,写出了三代人对于土地的不同态度,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古城村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以王银海、杨木匠和杨毛子等为代表的老一辈人对土地充满了敬畏之情。借用小说中贫协主席的话来说,他们把自己的地当娃哩,日夜侍弄,生怕走了墒,泄了劲,耽误了农事。在他们这一代人的眼里,地就是命根子,甚至为了争地界,不惜拼命。以王天赐和黑蛋等为代表的第二代人,对于土地则是若即若离,虽然他们仍生活在家乡这块土地上,但他们已不满足于仅在土里刨食了,农闲或去打猎,或去外搞副业——跑运输、开农家乐等,尝试寻求发家致富的新路径。而以平安为代表的第三代人,精神面貌迥异于前两代人,他们已不再恋土,不再安土重迁,而是渴望走出家乡这块土地,到外面的世界闯荡,去寻求别样的人生。三代人对于土地不同态度的背后,折射的是社会时代的历史变迁和乡民生活观念的嬗变。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乡村作为中国后发区域,从某种意义上讲,其现代化变革都有一定的被动性,这一点尤为明显地表现在农民精神心理的变化上。当土地不再是制约人们自由“折腾”的枷锁,也不再是羁绊人远行的镣铐,农民也渐由被动适应到开始主动寻求变革。小说《铁花》以细腻的笔触真实地记述了这一变化过程及农民的精神疑难。因此,可以说,《铁花》不仅是一部关中乡村社会生活的实录,更是一部农民被动适应社会的心灵史。
一个好的小说家,应该是生活的专家。什么是专家?沈从文说,专家就是有常识的人。一件瓷器,到了文物专家的手里,他很快就能判断出它的年代、产地,是官窑,还是民窑。因为他有这方面的常识。我们说作家应该是生活的专家,指的是他应该尽可能多地精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要熟悉他所描绘的生活领域。即便之前不熟悉,也要通过调查研究和分析论证,建立起关于这些生活的常识。小说不能只写生活中的极端和偶然的部分,还应该写生活中的常识部分。因为生活中常识的部分积淀着人类丰厚的生活经验和智慧,而且也只有生活中的常识部分才具有普遍性。当一个作家有了关于某种生活的常识,他写起来,才会得心应手,精细传神。读旺山的《铁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那就是,他对于自己所写的生活是有常识、有专门研究的。小说中有关乡村生活的许多描写,和实际生活严丝合缝,经得起反复推敲。如他写过去年月的批斗会,开会的一般议程是怎样的,如何捆绑犯人,犯人胸前挂的牌子,上面一般都写着什么样的内容,牌子上名字同样是打叉,但颜色有些是红色的,有些是黑色的。一般红叉是枪毙,而黑叉则是批斗。若无相关的知识经验,是写不出来的。同样,他写打猎,猎人怎么排兵布阵,什么狗做探哨,什么狗担任追逐,什么狗负责撕咬?撵野猪和抓獾又有什么不同?以及打完猎物回家不能走前门,要先隔后墙把猎物扔进去后,人才可以从正门进入院子的禁忌等,都写得细致入微。读到这些内容,你可能会怀疑他曾当过猎人,不然的话,何以写得如此精微细腻!还有,他写驯牲口,讲驯牛有两个关键环节,一是戴刹环,即穿牛鼻子、带铁环,牛鼻如果穿不正,将会影响牛犁地拉耱的方向感。二是套犁,驾驭牛的口令:嘚是前行,喔是左行,唷是右行,喂是停止。驾驭马的口令基本和牛一样,不同在于马前行,用的口令是“驾”,后退则是“稍”。所有这些叙写,一看就是行家里手。因为其中是有不少技术含量的,没有相关常识,肯定是写不好的。旺山之所以写得这么精细入微,这么生动逼真,一方面源于他过去的乡村生活经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下了笨功夫,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我曾陪同旺山做过有关乡民祈雨的田野调查,深知其中的付出和艰辛。祈雨民俗中包含着繁杂的礼仪轨制和禁忌,不做调查和案头工作,肯定是写不好的。正是因为旺山秉持了实证的科学态度,才给我们真实地还原了一个世俗化的乡村世界,为揭示乡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不能只停留在世俗生活和物质世界的叙写之上,它不仅要讲述人们的生存状态,还应挖掘人的精神世界,探索人的心灵疑难。作家铁凝关于小说写作有过一个说法,大意是,短篇小说写的是景象,中篇小说写的是故事,而长篇小说写的是命运。这种说法,固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把写人物命运视作长篇小说使命的看法,却非常有道理。读旺山的《铁花》,在作品中人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里,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一种属于命运感的东西。军嫂月季是村里的贫协委员,也是古城村长得最美的女人。她有文化、知识,聪明能干,在村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可就是这样一位女性,由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感情淡漠,难耐寂寞孤独的她,先后与村里的民兵连长胡章娃、王银海和赵魁等人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赵魁唆使她从保管员王银海那里窃取并私配了保管室的钥匙,偷走了保管室的粮油。结果导致王银海被关押,受尽折磨,并含冤离世。月季为此颇感愧疚,内心饱受良心折磨。她与赵魁的奸情及合谋之事暴露后,面对村里人的白眼,她更是抬不起头来,精神渐渐失常,最后跳水而亡。巧珍的男人赵九娃为村里祈雨累死了,留下巧珍和儿子备战相依为命。后来,她和苦命的黑蛋相好了,并冲破各种阻力,结了婚。他们夫妻起早贪黑,跑运输,发了家,致了富。本以为生活从此进入幸福坦途,可谁料巧珍却在生孩子时因难产而死。作品中那个叫玲珍的女性,发现丈夫赵魁与月季私通,一气之下,跟着一个走村串户的货郎跑了。多年后,货郎死了,她生计无着、逼迫无奈又跑了回来。可此时赵魁死活不让她进门,无奈之下,只好栖身于饲养室,和王天赐一起过着不清不白的日子。直至赵魁瘫倒之后,才得以归家。山里的红莲被人贩子卖给了老六,却又和车马店老板老董及王天赐不清不白,她顺天从命,满腔苦楚,更是无人诉说;红英嫁给了王天赐,生了孩子,按说日子应该顺风顺水,可突发的癫痫使她后来变得半疯半傻了,丈夫也渐渐疏远了她。旺山笔下的女性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人有好的归宿,她们都是生活中的不幸者,命运似乎对她们充满了不公。
与女性人物相比,作品中的男性人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天赐他三爸早年参加革命,未婚妻却跟了别人,自己也因曾被国民党俘虏过,怕家人受牵连,隐居深山,孤老终生;队长王银海因组织村民搞副业和祈雨活动等,几上几下,后因保管室被盗,冤屈而死;黑蛋父亲黑老四因地界与人发生冲突,失手打死方被判刑入狱,姐姐黑娥跟一个唱灯影戏的私奔了,留下黑蛋一人孤苦伶仃,艰难度日,后费尽周折才与村里的寡妇巧珍结了婚。正当他们日子越过越好,巧珍却难产而死。这一巨大的打击让黑蛋一蹶不振,甚至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在好友天赐的帮助下,他才逐渐缓过劲来。后来,他又遇到了一个叫春梅的女人,虽因她不能生育颇感遗憾,但搭伙的日子过得还算滋润。可好景不长,他因车祸意外而亡。旺山笔下这些人物的身上,似乎都有一种叫作宿命的因素在作祟。面对生活的不幸遭遇时,他们虽感痛苦,但大都乐天知命。“乐天知命”是他们信奉的座右铭。对此,朱光潜先生曾经有过深入的分析,他说:“(中国人)是一个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他们不大进行抽象的思辨,也不想去费力解决那些和现实生活好像没有明显的直接关系的终极问题。……当他们遇到人的命运这个问题时,是既不会在智能方面表现出特别好奇,也不会在感情上骚动不安。在遭遇不幸的时候,他们的确也把痛苦归之于天命,但他们的宿命论不是导致悲观,倒是产生乐观。”[2]215只要归之于天命,“事情就算了结,也不用再多忧愁。中国人实在不怎么多探究命运,也不觉得这当中有什么违反自然或者值得怀疑的”[2]216。旺山的《铁花》写出了中国人的这种生活观,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乡下人的现实存在状态和精神困境,是一部关于人的命运叙述的厚重之作。
二、一部典型的“地方性写作”
地方性写作一直是世界文学中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福克纳写邮票一样大小的故乡,马尔克斯写马孔多,沈从文写湘西,贾平凹写商州,莫言写高密东北乡,都是比较典型的地方性写作。进入21世纪以来,地方性写作在中国更是蔚为大观,涌现出贾平凹的《秦腔》、金宇澄的《繁花》、王安忆的《天香》等长篇力作。这一不容忽视的写作潮流背后隐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意旨,值得探究。旺山的小说《铁花》也是一部比较典型的地方性写作。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书中大量有关陕西韩城的地理景观、民俗文化、历史传说以及方言土语等的书写。
首先,小说以作者的故乡韩城(古称夏阳)作为书写的对象,就地理景观而言,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皆与韩城这个地方息息相关。前者如芝川、澽水、黄河、龙门、禹山、梁山等,后者如司马坡、禹王庙、后土祠、圣母庙、毓秀桥、少梁国,甚至还包括一些村庄、地名等。著名的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认为:“地理景观不是一种个体特征,它们反映了一种社会的——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信仰、实践、技术。地理景观就像文化一样,是这些因素的集中体现。”[3]13-14因此,读小说《铁花》时,我们不能仅仅把小说中写到的地理景观看作是当地的物质外貌,而当作可以解读的“文本”,因为它们寄寓着有关韩城当地的历史故事、观念信仰,甚至可以说,它们是韩城当地的文化表情,具有无限丰厚的意蕴。
其次,小说中写到的民俗文化、历史传说等,也充斥着韩城的元素。文化学者在谈到文化时,往往把文化分为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器物文化三种类型。在这里,我想采用社会上更为通俗的文化分类方法。就小说《铁花》写到的地域文化而言,主要有建筑文化、戏曲文化、鼓乐文化、神秘文化、社会礼俗和饮食文化等方面。在建筑文化方面,小说写到具有鲜明韩城地域特色的民居、门楣、戏楼、祠堂、庙宇等;戏曲文化方面,小说写到了木偶戏、灯影戏,剧种有秦腔、蒲戏等,这方面主要围绕被称为是“古城村的戏胆”的杨木匠这个人物来叙写的,写他一生爱看戏、演戏和排戏;鼓乐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中关于赛鼓的情节部分,其中既有具体表演场景的描写,还穿插介绍了多部鼓乐曲调的特点,让人自然联想到富于韩城地域特色的行鼓表演;而神秘文化则以杨毛子、高瘸子和范先生等人为代表,小说写到算卦、看风水、驱鬼、立柱子、贴神符、剪纸止雨、祈雨等;社会礼俗文化方面,则写到了祠堂祭祀以及给孩子过满月、十二岁下抻(全灯)礼、丧葬以及打铁花、岁时节令等习俗;至于有关韩城的历史文化内容更多,如赵廉坟、赵氏孤儿、秦晋之好、状元王杰等,仅有关芝川渡(夏阳渡)一地,小说里就写到韩信木罂渡河、闯王渡河,八路军东渡黄河等历史事件;此外,小说还写到富有韩城地域特色的饮食文化,如羊肉糊饽、饸饹和芝麻烧饼等。
在地方性写作中,不少作者企图通过叙写各种地方性的山川风物和历史民俗等,增加作品的地域色彩。这样写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若不能将它们巧妙地融化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之中,地域文化与小说情节往往会是油水两张皮,融不到一起。这样就像做成了一锅夹生饭,尽管看起来不错,但生硬难吃,没人会喜欢的。值得称道的是,小说《铁花》的作者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把地域性的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合到小说的故事情节之中,显得比较自然。读者阅读小说《铁花》,犹如品享地域文化的盛宴。
最后,小说还适度使用了当地的方言土语。语言是小说的第一要素。有作家甚至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若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便会让人难以卒读。一般而言,人物对话可适当运用方言,而叙述语言则要求规范、雅驯,向规范性的现代汉语靠拢。但是小说《铁花》无论是人物对话,还是叙述语言,都大量使用了关中东部的方言土语。如,“咥”与“挕”,前者指“吃”,后者指“打”;再如,“脚底里”指的房间炕下面的地方;又如,“像木桩一样戳在那儿”中的“戳”,指的是“站”。方言土语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在地性”和“地方感”。[4]但是由于关中方言与普通话同属北方语系,适度地使用丝毫不会影响阅读效果。而且,这些方言土语的采用,体现的不仅仅是作者对故乡农民的尊重,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对故乡和故乡人的深厚情感。因此可以这样说,运用方言土语,既是一种思想、情感的选择,也是一种对地域文化的选择。
小说《铁花》作为一部典型的地方性写作,从表面上看,其地方性叙事是为了表现特定地域风物人情、民俗文化等特征,追求一种独特写作风貌。但若是把它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其深层意旨恐怕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在全球化潮流的冲击下,地方性知识面临着被同化和消解的风险。地方性写作的背后往往有一个隐而不彰的辩论对象,即全球化。全球化要求一体化、无差别化,强调共通性,地方性写作则凸显地域性、在野性,强调差异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地方性写作实质上就是对强势的全球化潮流的一种抵抗。当然,在抵抗的同时,也有尝试以地方性和差异性寻求与世界对话的努力。文学评论家岳雯认为:“到了新时代,逆全球化潮流开始抬头,民族主义复苏,并对各国的文明与文化形成冲击。在这里,地方性写作不单成为某个地方的文化象征,而是指向了民族国家,由此,地方成为民族国家的一种隐喻。”[5]王旺山的小说《铁花》作为一部比较典型的地方性写作,其深远的意义和价值或许就在这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若是作者能在地方性知识的书写中更多地发掘出具有普遍价值的人类学经验、因素,那么它就不仅只是展示地方文化,而且能凸显本土经验的价值,对于反抗全球文化霸权也可能会有更为积极的意义。
三、建构了一种慢的小说美学
读旺山的《铁花》,你会发现,小说几乎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主线,只有自始至终的人物。在整体结构上采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两种叙述视角交替进行的方式。在叙事上,变幻多端,既有顺时序,也有逆时序,即顺叙、倒叙、插叙等交叉使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作者以一种近乎原生态的写实手法,着力于日常生活的叙事,而且在叙事时总是喜欢旁逸斜出,节外生枝,穿插叙写相关人物事件,或山川地理、历史传说、风物民俗等,情节发展整体推进比较缓慢。作者并不急于讲故事,就像走路的人并不急于赶路,而是走走停停,随意驻足,欣赏一会路边的风景。甚至有时还会走进路旁的田地里,去逛一圈,再回到大路上,继续前行。我很佩服王旺山写作过程中的耐心和对叙事节奏的把握。进入写作的状态时,他便一反日常生活中的雷厉风行、果断干脆的行事风格,叙事时变得很耐心,很从容,不慌不忙。有时甚至觉得他仿佛是在考验读者的耐心。这样一种缺乏故事情节主线,叙事又枝枝蔓蔓的写法,对于快节奏、碎片化阅读时代的读者来说,可能是一种挑战。
当代大多数作家写小说,总是急于讲故事,一门心思地构造紧张的情节,制造悬念,快速地推进情节发展,生怕稍不留神抓不住读者的心,从而失去了阅读的兴趣。这样的写作,显然是缺少叙事的耐心。小说故事虽然很好看,但总让人觉得缺少点什么。正是因为如此,评论家谢有顺说:“在当代小说家的笔下,几乎很少能看到传神的风景描写了。”[6]51大家都忙于讲故事了,谁还有耐心去描写风景呢!值得欣喜的是,旺山的《铁花》里却有大量的风景描写,包括地方风物和建筑的描写,而且写景时很少单独采用描写的语言,而是融叙事与描写为一体,这样的操作大大地增加了写景部分的可读性,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有些读者看作品,遇到写景部分便跳着读的现象。如下面这段:
雨已经下了三天了。看样子,没有立马要停的意思。淅淅沥沥的一会大,一会小。雨的大小,天赐是根据四周雨滴落在灌木丛、野草和树叶上的回声判断的,山里的雨天和川道里不一样。川道里的雨天是混沌的,容易让人腻烦,但在大山里听雨是一种享受。因为四周的远山近峰,高低不同,山上植被也同样是错落有致。所以,无论雨滴大小,传到耳朵里的声音同样有高有低,有强有弱,有远有近,有大有小,像音乐一样好听。山里的雨天,大部分时间都是通透的,散发着植物清新的气息,甚至充满了诱惑人的神秘感。现在,天赐就坐在车马店一间马厩的石槽上,独自享受这场持续的秋雨交响乐。置身其中,他觉得自己被雨水一层一层地浸透,一遍一遍过滤,大脑一片清爽,胸口在被一种无形的力量不断填充、膨胀着。劳作的疲惫,往日的烦心事儿早随着雨水流走了。[7]130-131
作者不是为了写景而写景,而是将人事与景物融合起来写。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就喜欢采用这种写法。作家沈从文曾对此非常欣赏,并在自己的作品中予以借鉴。小说《铁花》开始写天赐打猎一章,大量的景物描写,浪漫抒情的文风,让我想到了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等抒情化的小说。小说的其他章节也一样,尤其是有关山中打猎的部分,叙事之中也有大段大段的写景文字。这样的写景抒情性文字,也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小说的节奏。当然,慢不是目的,其背后应该有着作者观察和透析生活的心路历程。这样一种别有用心的写法,实际上建构了一种慢的小说美学,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过去中国乡村的那种很琐碎很无聊的日常生活,把人物心情、感觉写进去,而且把乡村生活的味道氛围写了出来。在这个人心浮躁、灵魂挂空的快节奏时代,人们生活的目的性太强,总是急匆匆地低头赶路,直奔目的地。小说《铁花》以一种舒缓的叙事节奏,建构了一种慢的小说美学,试图让我们在文学阅读中慢下来,静下来,并不忙着奔向目的地,而是不时驻足,欣赏一下沿途上的风景。
像大多数作家的小说一样,旺山的小说也存在一些尚需精进的地方。小说《铁花》,虽说很接地气,但更多还停留在写经验讲故事的层面,他的精神视野还不够开阔,小说的精神底子容易被读者一眼看穿,而缺少一个沉默的层面、未明的区域,特别是缺少一个统摄全作的精魂,无法让人做更多的想象和沉思,也很少能引发人产生形而上的思考。当然,这对于几乎所有的作家来说,都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了。另外,小说的结尾显得过于仓促,或者说在本该结束的地方,他却补充交代了许多,给人留下想象思考的空间不多。
尽管存在些许不足,但笔者认为《铁花》仍不失为一部比较优秀的乡土小说,甚至可以说是近年来我们渭南文学最美的收获,也是陕西乡村题材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收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