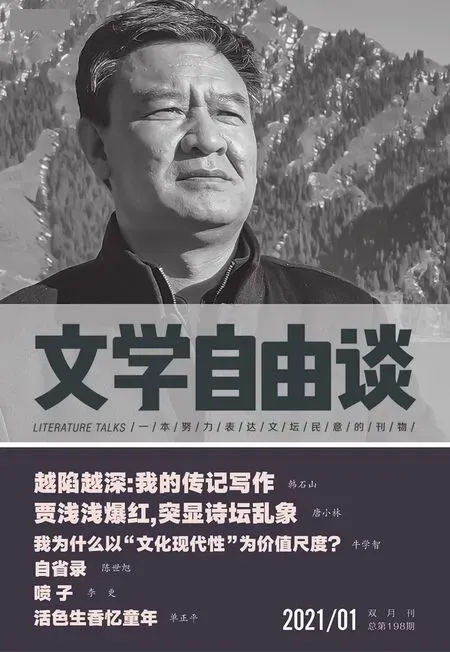“三人行”与《诗探索》
2021-03-08古远清
□古远清
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北大、首都师大等机构主办的《诗探索》,是中国文坛上鲜见的老年人办的刊物。从2019年第四期所刊登的编委会名单上看,三位主任,最年轻的吴思敬已“坐七望八”,谢冕则“坐八望九”,而杨匡汉初度八十时就在北京某会议的主席台上亮出了拐棍。如果说撰写发刊词《我们需要探索》的谢冕是《诗探索》这辆汽车的发动机,那为创刊号设计要目和专栏的匡汉和后来任主编的思敬,则属于方向盘。
这三人堪称“黄金组合”,美中不足的是,只有“诗翁”而没有“诗媪”。不过,这三人的个性倒也十分戏剧化,如谢冕嗜酒,匡汉嗜烟,思敬大概就嗜赌了。2006年10月15日,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的“新世纪中国新诗学术研讨会”上,有人问“《诗探索》会不会停刊”时,刹那间“牌桌变赌桌”,不再伺候“牌局”的思敬,没有捶胸顿足,而是气定神闲地和大伙打赌:“我敢说,《诗探索》会一直办下去!”舍我其谁的得意和浑身是劲的魄力,跃然“嘴”上。
《诗探索》的三位主任平均年龄超过八十岁,说它是耄耋老人办的刊物,不如说是“大孩子”或“大朋友”办的刊物,或者说是年长的“青年”学者办的刊物。不能以貌取人,这个刊物的主持人年迈,但不等于老气横秋,而在气质上倒是充满着青春朝气。比如谢冕,其“学官”履历也就止于空壳(无经费无实体)的北大新诗研究院院长。正因为无官一身轻,也就没有沾上官僚习气,故他待人没有城府,酒醉后更是天真如赤子。这位望之俨然、仰之弥高的学者,在桑榆晚年,奋笔力书专著《中国新诗史略》,只见灵气、才气,再加上“酒气”,而不见书卷气。他热情、奔放,有一颗年轻的心。为人写序是他写作生活的重要一环。他总是不嫌麻烦地阅读那些“不修边幅”的稿件,由此,索序者便多了起来。这时,他会像余光中那样抱怨:“我从未与人借过钱,怎么一下就冒出这么多债务,永远还不清呢?”不过,如果没有人请他写序,他大概就感到自己真的老了。为避免衰老,他下决心“还债”。他为拙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写的序言,不是应景之作,而是有深情的关怀和期待,不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让人触摸到中华文化的血脉和学人的风骨。
自称是“反季节写作”的谢冕,在生命的严冬就这样书写着春意盎然的篇章。孙绍振八十大寿时,这位醉眼朦胧的诗翁为同窗写了《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开一个美丽的会——黄山奇墅湖祝词》,说绍振的生命“犹如黄山上面的奇松、怪石、云海,非常美丽,不仅是一般的秀美,而且是极美,是奇美”。谢冕的生命同样是一道奇美的风景。在诗歌的探索道路上,他不仅为新潮诗大声喝彩,而且利用《诗探索》这个园圃努力栽培,尽管前进的道路上有礁石和深坑,但一旦行过生命的低谷,便迎来了一片灿若黄金的诗歌时代。典型的是他在《光明日报》发出为初看不免有些古怪的作品叫好的声音,让“守成派”读后愕然失色。这无异是一声狮吼,同时又是一把燎原烈火,和舒婷们的创作燃成一景。这位虎虎生风的启蒙者、改革者、探索者,心态一直像初出茅庐的“青椒”。有这样以童趣与好奇窥探人生种种现象和诗坛百态的“大孩子”,以“精卫之坚韧,刑天之勇猛”捍卫诗的探索性、纯洁性的“大朋友”,陪伴《诗探索》的作者和读者,怎能不是刊物的幸运呢?
烟不离手的匡汉,其颜值不可能呈红润状。他不似其胞弟匡满以诗闻于世,但一直“暗恋”旅美诗人纪弦:吞云吐雾代表了他的灵感,这是追求浪漫的;手杖是他儒雅风度的体现,这是面对现实的。不久前有朋友向我感叹:在近年召开的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怎么看不见逢会必到的“监事长”匡汉敦厚的身影?或许他戒烟(此说存疑)的同时又“戒会”了?遥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他解除教条的桎梏,提倡更新新诗研究方法,不能老停留在拿“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做文章的层面,引发时任《诗探索》资深编委宋垒的强烈不满而大“闹”起来,对号入座,为文反驳。《诗探索》内部发生两位名家对峙的“闹春”动态,非常“新闻”。这种毫无诗意可言的不迷人局面,由自称为“中间派”而不承认自己是“守成派”的宋垒退隐江湖而落下惟幕。现在重读宋、杨两人的论争文章,感到当时诗坛实力明显是“宋”消“杨”长。即使这样,宋垒怎能说放手就放手?一个与卞之琳对垒过——卞在《诗刊》1958年第十一期发表《分歧在哪里》,宋在《诗刊》1958年第十二期发表《分歧在这里》——的雄辩评论家,怎么可以不打声招呼就人间蒸发了?让人感到庆幸的是,匡汉这颗星至今依然熠熠生辉,文论诗论仍滔滔滚滚。2015年在广州召开的诗学研讨会上,主事者请他坐着讲,他坚持站着说。不到二十分钟的发言,不敢说是出口成章,但至少不是高头讲章,其中引人深思的内容不少。曾有人批评匡汉的文章有玄学化的倾向,可他于2018年8月在《名作欣赏》上发表的《长亭谢师录》,没有时下学报上出现的某些文章“骨头很少,水分甚多”的弊端,堪称思辨与文采俱佳的学者散文。
我和匡汉均从事华文文学研究,每次由“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举办的大型研讨会,会长饶芃子都点名要他做“学术总结”。他没有“把破帽,年年拈出”,每次的“总结”从标题到内容,都有一定的新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资深编审白舒荣谑称他为“杨总结”,简称“杨总”。“杨总”的论著和一般学者不同之处,是充满思辨性和语言的生动性。他的书法更是灵动,古文功底也厚实。在我迈向古稀之年时,香港的曾敏之写给我的是七律,别出心裁的匡汉却用短句为我庆生。他收起学问的锋芒,以一支生花妙笔吟出四言诗,虽然语多溢美,但说我“小节不拘”“快嘴快语”“嬉笑怒骂”“盘马争鸣”“广交友朋”等,不愧是知音之论。
我认识思敬,谈不上一些“小朋友”对心仪的学者那样情怯。夸张一点说,我们一见面,是从“吵架”开始的。我于1984年开始撰写《中国当代诗论50家》,在我的“黑名单”里,就有思敬,可他于1985年元月30日回信说:“我的诗论研究还处在学步阶段。”我说不能把朦胧诗看成是新诗的发展方向,他说作为新生事物就应无条件地支持。在1980年秋天召开的“定福庄诗会”(全国诗歌理论座谈会)上,他和绍振、钟文等人一起手执“新诗潮”之刀,以夷变夏,拆解中国诗坛之肌体,连带向暮气沉沉的文坛挑战。近乎迂腐冬烘的我,在他们遭到围攻时没有厕身其间,不似他以诗人的激情和评论家的敏锐,敢于和谢冕一道,批评僵化的诗坛,联手吹起“新诗潮”的号角。那时我慑于老作家的名流威望,游走在举剑对击的“新潮派”和“守成派”之间。在“非常时期”未能成为“战友”的思敬,“平常时期”毕竟是同行、同道,何况那时他也没有像现在有那么多“铁粉”,故1985年我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第二届新诗评奖的评审工作时,在满山红叶的秋天,到他位于菜厂胡同7号的府上拜访。从全国各地来的书刊占据了逼仄的斗室空间,书斋成了“书灾”,他苦中作乐,以诗意地栖居在可以养生怡神、称心惬意的菜厂胡同而沾沾自喜。当时我觉得奇怪,《诗刊》为什么不请颇有名气的思敬参加“读诗班”做评审工作?原来,主事者为了保持立场中立,请的清一色是介于“新潮派”与“守成派”之间的“上园派”诗论家。我在北京上园饭店和号称“西南一霸”的吕进、《诗刊》理论组组长朱先树等一起住过半月之久,虽没有名正言顺地参加“上园派”,却也是这派观点的支持者。思敬并不因为我与他观点相左而疏远我。记得那次两人促膝私语,我真正感受到他家作为文化沙龙的愉悦。
我和颇具老辈风范的《诗探索》的主任或主编的友谊,不像闺蜜那样腻在一起,更不可能泡在一起。尤其是在“少外出,莫聚会”的疫情期间,我们实行的是无接触社交。即使没有这场天灾,我和思敬大概每年也只能见一次面。前几年在山东开会时,我惊奇地发现,见证过文坛风云、经历过人生阴晴圆缺的他,走起路来已有点老态龙钟。即使这样,他和谢冕一样,也是一位老得漂亮——勤而不老、严而不老、人老心不老—的“大孩子”,始终保持着犹如赤子的眼神,纯净而澄明,有一股年轻人的傻劲与冲力。我听过他主持一些重要会议的主题发言,他都不念讲稿,文思泉涌地娓娓道来,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我最佩服的是,他寻找新的学术点比别人敏锐、迅捷。他主持的《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竣工后,又主持《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近年他更奋自淬砺,大幅刷新已有的研究思路,申报教育部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又奏凯歌。他不愧为目光远大的新潮评论家。每次做课题,他都不忘把台港澳新诗写进去,把中国当代新诗经营成一座大花园,这对把“中国当代新诗史”处理成“中国大陆当代新诗史”或“共和国新诗史”的某些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反拨。而台港澳新诗部分,他每次都点名要我加盟,我也很乐意和这位年龄比我小、学问比我大的人合作。合作时他不摆“主编”架子,而是平易近人地与大家商讨课题应如何写,论争时能做到口舌平等交锋,所以比思敬年轻的学者也就成了不大不小的朋友。本来,他有自己的想法,但决不强加于人,而是尊重别人的选择,更不干预别人的写作。在他麾下做课题,我感到自由、宽松,深深体会到他是一位可敬又可亲的“兵团司令”。
诗歌理论刊物如何参与中国当代诗坛的建构,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曾经叱咤风云、主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诗歌潮流的《诗探索》,如今的“镇刊之石”,非思敬莫属。他近年精心设计了“诗学研究”“中国新诗:新世纪十年回顾和反思”“姿态与尺度”“诗论家研究”“中生代诗人研究”“诗人谈诗”“新诗文本细读”“结识一位诗人”“台湾诗歌研究”“外国诗论译丛”等众多栏目,还有不少专题,使诗歌评论不再是诗歌创作的附属物,而在诗学研究上显出自己的前瞻性。以我有限的阅读,我感到《诗刊》和《诗探索》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堪称双子星座,功不可没。标榜“探索”的《诗探索》,立足于中国当代诗歌的时空结构,把探索作为研究和影响创作的路径。通过多次不同风格诗人的“结识”和探讨,阐发诗歌的探索性、实验性与传统性的交互关系,发掘诗坛最新动态对诗歌研究的价值,尤其是通过台港澳新诗特性的归纳和总结,重绘中国新诗的空间地图。感到荣幸的是,我为《诗探索》提供的《台湾三大诗社互动和冲突的关系》《戴望舒“附逆”辨》等论文,参与了“重绘中国新诗地图”的工作。可见,《诗探索》的胸襟是宽广的,而不是狭隘的;其诗学观念是开放的,而不是保守的。
我这辈子阅读和投稿的文学评论杂志多矣。在市场经济时代,商风似伤风一样流行,有的刊物暗箱操作收取好处费,有的杂志明码实价收取版面费,而锐气十足的《诗探索》洁身自好,从不收好处费和版面费,是一份品位不低、招牌超硬、声誉甚隆的杂志。有人开玩笑,说它是“中央级”刊物,可它从不居高临下,而是放下身段,注重诗歌研究空间的转换,经常发现来自各省市的新人,扶助基层作者的成长,为诗歌研究的“在地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向。这在为武汉诗人田禾所制作的专辑中,谢冕所写的《田禾的村庄》体现得特别明显。谢冕所说的“村庄”,是指具体的地理空间和诗歌场域,它有着自己的自然环境、社会构成和新乡土诗的价值体系,在田禾的写作经验和身份认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他评论家的文章,同样也体现了这一点。
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现当代诗歌领域,立足于两岸四地大一统诗歌史观,和以时间演进为内在逻辑的诗歌史建构方式,发现和推出诗歌写作以及理论研究新人,培养创作和研究兼备的复合型诗歌人才,坚持探索性和前卫性,不断扩展刊物的有效读者群,办好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的诗歌研讨会以及有特色的诗歌奖项——所有这些,成就了《诗探索》的理论品格。尽管诗歌巨宅堂奥甚多,无人敢打赌说只有自己的探索才是正路,但《诗探索》的主编们坚守自己的诗学观念毫不动摇。它躲避宏大历史叙事的牵绊,不断推动中国新诗研究的深耕细作。他们的个人成就尽管大于刊物成就,但这份杂志毕竟像一座波澜不惊的桥梁,始终保持本色,屹立在首善之区。笔者相信这也是众多评论家和读者,对《诗探索》在当代诗坛所起重要作用的评价。
在当代学界,诗学研究之于《诗探索》的主任或主编们,不是产业,而是职业、事业。他们不走视学术为产业的道路,更不把目光牢牢盯在编杂志如何成为C刊的转换中。他们在处理来稿时,远离亲名校、亲名人的浅碟学风,不过分追求发表文章的“规范化”,无论是序跋还是格言式的诗论,只要有真知灼见,就加以发表。他们是诗潮的弄潮儿,将自己的志趣、才华、生命与诗的探索融为一体;不旁鹜自己办的刊物属何等级,更不计较利益得失,只求对诗歌创作有用、有补;不软媚乡愿,不屑逢迎手握刊物等级大权的“学阀”。他们集稿有方,编刊甚力,又乐此不疲。这是只知道埋头苦干的一群发烧友。
无论是已退居二线的精英耆宿谢冕、匡汉,以及至今还在为当年的“赌誓”拼打在一线的思敬,均是书痴型的评论家和编辑家,是地地道道的本色派学者。2016年11月,我在《当代文坛》发表《“北大新诗学派”的形成和贡献》,提出“北大新诗学派”的概念,把并非北大出身但与谢冕经常同进同出、与“新诗潮”论者联袂合拍的思敬,定位为“北大新诗学派”的掌门人。耿直孤高、也是北大人的刘登翰,对此提出异议:“大作把非北大出身的学者,也放入‘北大新诗学派’来讨论,我不知道当事人感觉如何,是否愿意,这好像有点‘拉夫’,以壮大声威,给人感觉是将之放于‘从属’的地位。与其如此,不如另外命名,例如‘诗探索’派或别的什么,给人以更多的平等和尊重。”(见拙编《谢冕评说三十年》,第204页,海天出版社,2014年)其实,“北大新诗学派”不是“同乡会”,研究者把某人算成“北大新诗学派”成员,用不着左顾右盼考虑他人的感受,更不必征求本人同意,这样才能体现研究者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但同是“大朋友”的登翰说的“诗探索派”是否存在,这倒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
犹记得《诗探索》于1980年创刊时,我满心期待到了兴奋莫名的地步:除了可以有真正属于诗评家自己的园地外,还可以与嗜酒的谢冕、嗜烟的匡汉、嗜赌的思敬进行诗学交流。可到了1985年秋,《诗探索》“放假”,形成只有招牌而无营业的状态。它究竟是这群“大孩子”戏弄我们的幽默,还是幕后另有读者所不知道的隐情?这只好等待文学史家去考证了。那时碰巧我在北京出差,在一家小邮局里买到一份上海出版的《社会科学报》,上有匡汉写的《救救〈诗探索〉》的短文,读之不禁失落怅然。忽然想起木心说的“文学在于玩笑”“文学在于胡闹”“文学在于悲伤”这几句戏言,内心深处竟燃起一股挥之不去的依恋之情。我虽然从未“胡闹”过,在《诗探索》发表的文章不似我最近在《中华读书报》刊登的以“玩笑”为主的《野味北大文坛》,但毕竟是它的支持者,尤其是一位长期订阅的读者。我已将自己生命中那么一段宝贵的时光与《诗探索》主编及其刊物在精神上紧密相连,阅读此刊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习惯。正是在这种心态和情绪中,尤其是在杜鹃花开的端午节,我衷心希望一群嗜酒嗜烟嗜赌的“大孩子”所办的《诗探索》,从此不用再打赌,它一定有龟寿鹤龄,而不会降下半旗再度“放假”;衷心期望那些魅力万千的现役诗评家、退休教授的主任们,永葆学术青春,生命不息,探索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