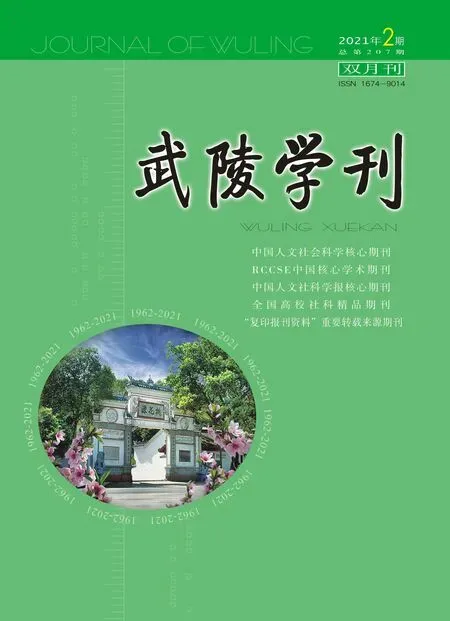唤起与重构:抗战动员中的“坚守西安”记忆
2021-03-07叶欣明
叶欣明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1926 年4 月至11 月,直系军阀刘镇华率十万“镇嵩军”围攻西安,西安军民在李虎臣、杨虎城的率领下坚守八月之久,直至冯玉祥五原誓师后方才解围,《大公报》称之为“千古未有之奇闻,近代未有之惨劫”[1]。“九一八”事变后,西安各界于每年11 月28 日的解围日举行纪念活动,“二虎守长安”的英雄事迹被广为传颂,“其气弥励忠烈之慨,拟诸张巡许达之守睢阳,史可法之守扬州,殆无愧色”[2]。一个伟大的民族总是在对历史的庄重回望中汲取前进的力量,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坚守西安”的记忆一方面融入了“巩固革命基础,促北伐之成功”[3]240的革命意义,另一方面又与抗日卫国主题相关联,同心协力的守土防边之责和以一当百、誓死拼命的坚韧精神不断被发掘出来,记忆的对象遂从战祸绵延、民不聊生的“围城”暴行演变为承载历史苦难的“坚守”义举,反映了“适合社会需要的文化符号的建构过程”[4]。关于这一事件目前学界多聚焦于历史史实和个人回忆,笔者拟以事件亲历者、知识分子和陕西地方政府的集体记忆为切入口,考察时人如何重塑“坚守西安”的历史记忆,并将此运用于抗战救亡。
一、“苦难”记忆:崇扬民族精神共赴国难
事件发生之初,“一般人民尚认定为军阀家自相鱼肉”[1],着重凸显西安被军阀戕害的腥风血雨,聚焦于对加害者刘镇华和“镇嵩军”的声讨以及对受害者惨况的同情,或悲痛于“饿殍触目皆是,血肉狼藉、满目惨状”;或指摘刘镇华“极人生之恶事,无所不作”;或惊骇于“环城数十里战壕埦埏、深可丈余、宽可丈余”[1]。在西北大学黄成垙的记叙中,攻守双方不过是各为其野心所驱使,“个人争权利竟殃及全城人民,使其受莫大之痛苦,最巨之惨灾”[5]。在抗战中,这种记忆被重新检视,事件的亲历亲闻者抛开个人的恩怨得失,站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之下,力图彰显中华民族的艰苦奋斗精神和中国人民竭力守城的历史伟绩。
(一)“油渣”与不畏强权、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员
西安围城时,由于粮运不通,罗掘俱穷,加之斗粟百元,一餐数金,犬马食尽,油渣即成上珍。据冯钦哉回忆,“十月以后,城内粮食即形缺乏,人民多以油渣充饥”[3]239。因而有人形象地将“坚守西安”纪念日比喻为“油渣节”[3]357。在抗战中,油渣如同一块“纪念碑”,其上铭刻的是令人“思之犹觉心悸”[6]的围城往事,启示、鞭策着国人以苦难意识和坚定信念,冲出日寇围困,复兴民族。
忍饥耐苦的“油渣”记忆激发了守城将士誓死不屈的抗日斗志。中共派往杨虎城军部的宋绮云就指出,当时的守城将士“油渣尽则宁愿殉城以死,鲜屈服于暴力之下”,正是这种精神的感召使民众“革命之情绪,慨奋之热情,益趋高涨,且具铁似的坚决之意志”[7]。薛镇东认为吃油渣咬菜根充分体现出“茹苦含辛,甘之如饴”的民族历史文化精神,堪称“孔子所称‘见危授命’的成人,孟子所赞许‘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8]。一首《无题》的纪念诗这样写道:“任凭你残暴者攻击围困,强烈的炮火怎敌民众热情!”在民族受日寇暴力侵迫之时,国家之危殆也如同置于重围之中,高昂的民情化作馑腹中呐喊的呼号:“啊残暴,不除残暴不回头!”[9]西安政府也借助《公祭宣传纲要》向世人宣示:“中国民族有坚守西安的精神,即有坚守国土的毅力。”[10]
惨烈牺牲的“油渣”记忆激励了军民裹创杀敌。在宋绮云的叙述中,坚守西安之于中国如同《最后一课》之于法国[7],是国民陷于垂死之绝境必奋起而觉醒的重要记忆,象征着“粮尽则嘴及油渣,裹创犹起而杀敌”[11]的革命斗志。当秋粮已尽,油渣无存之时,便是“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最后关头,必须“俯敌垒为墉垣,共油渣为性命”[12]。署名“秋平”的作者感慨于当时“冒白刃,与敌人肉搏!万众一心,齐呼着打出去!或者就死在这里!”[13]在他的描述中,民众丝毫没有绝望和悲切,眼中只升腾起革命的火焰,勇往直前。
饥兵羸卒的“油渣”记忆警醒了时人发展生产、充实国防的热情。围城前西安虽获丰收,但“入秋粮渐尽,人民之饿毙者,尤无可数计”[14]。郭英夫对当时坚守西安的情形十分惊叹:“少数的兵力,残缺的枪械,储存无隔宿之粮,守城的士兵仅随身佩带着数排药弹,在严重时局以此种单薄的力量,自卫不遑,何堪言战?”[15]他呼吁今后更要惨淡经营,努力发展生产建设,完善交通,充实国防,方能恢复民族自信精神[15]。当下如何看待历史是记忆重构的重要方式,民族危亡背景下的“油渣”记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蕴含了直面苦难、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精神,成为振奋人民意志的精神象征。
(二)“军阀祸国”和与民更始、团结统一的精神动员
西安罹难的祸首是当时依附于吴佩孚的地方军阀刘镇华,抗战之中,对刘镇华暴酷惨无人道的罪行刻画,不单是对其个人罪恶行径的声讨,更是对独裁专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有人这样描述当时围城的场景:“村社为虚,鸡犬全无,死尸遍野,骨暴沙砾,至为惨痛!此为陕西亘古未有之浩劫,亦军阀祸国之现象也。”[3]246造成这一惨况的祸源则是长久以来的军阀内战与争斗,“吴佩孚挟期重定中原之余威,驱其精锐,摧关西指,意欲征服西北,实现其武力统一之大梦”[16]。
因之,必须首先铲除军阀余孽,与民更始、整军修政。张学良认为坚守西安最为痛念的“是由于军阀野心致此惨剧,牺牲无数中国人性命,中国人金钱,亦即在内战中消耗仅有的国力、人力、财力”[17]。封建势力的故态复萌是三十年代中国的一大社会弊病,军阀余孽、劣绅土豪、政客官僚“横作淫威,民众痛苦有增无已,地方糜烂时刻加剧,社会现象,日趋险恶”,加之国民党这个“革命政府比军阀政府还残酷多少倍”,民族危机的根源在于政治,惟有“积极扶植民众势力,涤清政治,方能解救中国的劫运”[18]。
其次,必须反对同室操戈,要团结统一、众志成城。西安围城虽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直接结果,却是民初以来帝国主义操控下“争权夺利自相鱼肉之恶风”[19]的产物,曹冷泉就对当时“酣歌恒舞,忘国难于九霄,或拥巨兵以自固,视危亡而不救,甚或甘为倭奴臣妾,以同胞为敌仇”[20]的国人大加挞伐。《告全陕同志书》则对同室操戈者深表痛心,并告诫全国上下“再不同心一德,精诚团结,以国家民族前途为愿念,我恐不惟国亡,而人民将在毒气与炮弹下绝尽矣”[21]。批评的最终目的在于激发爱国之心,雪耻复兴,昭告国人“精诚团结,一致争取国家胜利”[19],“以枕戈待旦的志气,肩起复地雪耻的重任”[22]。
抗战之中坚守西安的记忆被不约而同地升华为体现民族坚强意志和反抗精神的绝佳素材,守城之悲壮的“油渣”记忆是崇扬民族精神的重要符号,代表着一种知耻后勇的决心和勇气;同仇敌忾的守城精神,既是刻骨铭心的历史鉴镜,又是中华民族摆脱困境、迎接光明的希望之光和取胜之道。对苦难的反思在抗日救亡时期成为民族复兴的时代呼唤,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和道德追求,号召人们“以坚守西安忍饥耐苦的精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3]。
二、“光荣”记忆:恪尽守土之责坚守中国
西安坚守历八月而不破,解围之初,基于牺牲四万余众的惨烈现实和对“新旧军阀之争”的认识,时人对守城的意义还颇有争议。西北大学教授黄成垙将其视为“孤注一掷以争一己之地盘”,而国民党人则推此举为“大有造于西北革命,从而盛称其丰功伟烈”[24]。抗战之中,坚守西安“保全西北、策应北伐”的光荣记忆因时代需要而被各界追认,如纪念歌中所唱“固守西安援助了北伐胜利革命成功……荣中华民族于东亚”[25],又如祭文所写“厥功伟矣,勋被全民,岂独梓里”[26]。由此,坚守西安保卫战的记忆成为召唤全国军民保家卫国、捍卫疆土的号角,并借以成为反对投降主义,强化守土之责的一面旗帜。
(一)“西京依旧金瓯无缺”与保卫国土收复东北
西安坚守中曾发生多次大型攻守之战,东北城角“以手榴弹、大刀相肉搏”,小雁塔“陷两次,克复两次,敌终未得据”[3]244。在军民的共同抵御之下,西安城坚如金瓯,镇嵩军未越雷池一步,后人常以“金汤永固”褒扬坚守西安之绩。抗战之中坚守西安保全西北革命策源地、襄助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意义使这段记忆历久弥新,“光荣”记忆的生成与收复东北四省、坚守中华民族国土的时代诉求密切相关,寄托了时人重整河山,恢复故土的夙愿和理想。
强调保全西北革命策源地的意义旨在激励将士守国之信念。坚守西安保全了秦川半壁山河免于枪林弹雨之下,“于一线危机中保持了全陕数百千万之生命财产”[27],使民众明了今日抵抗日寇自求解放,“中华民族才有生存希望”[28]。渗透着国难意识和解放意义的坚守记忆被唤起和加强,激励着国人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家园。坚守西安还使当时危如累卵的西北形势重现生机,促使革命运动澎湃发展,杨幼炯在纪念文章中指出:“北方革命局势之转变,既以是役为枢纽。在反革命势力重重围迫之中而突出,为爱护国家民族而努力。”危城坚守,即是为了“维系革命军民之信念”[29],勉励危难中的民众始终保持斗志。
强调促北伐成功的意义旨在维护统一,收复失地。坚守西安,“国民革命军方能摧毁孙传芳、吴佩孚等联合之师,而肃清长江,奠都金陵”[30]。西安解围使南北革命军会师中原,提振了革命信心,特别是冲出重围、兵合一处、主动出击更为国人收复东北、维护统一提供了重要参照。杨虎城强调:“守城与守国,并没有怎样的不同,一寸一分都是不让与人的。”[31]守城与守国的象征性比拟旨在警醒人们只有“以扫荡军阀的勇气收复失地”,才能“使十年前璀璨的革命重复照耀在锦绣河山上”[32]。郭乐三进一步指出,守国的关键在于东北将士、国防军及民众“本着守西安的革命信念、奋斗决心、牺牲精神,冲出中国的重围,收复东北失地”[33]。
奠邦基、固西北、促北伐是镌刻在坚守西安丰碑上闪耀的时代记忆,在救亡图存、爱国主义的主旋律渲染和激发下,坚守西安成为坚守中国的历史印证,彰显出炎黄子孙英勇不屈的民族自豪和自信,即相信能守、相信能胜、相信军民能共守斯城[15],对全民族联合抗战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二)“捍一城而卫天下”与反对弃城避敌
西安围城中,刘镇华曾利用城中“和平期成会”进行诱降活动,杨虎城为表守城决心,将首恶毙杀于西华门,乞和投降活动始告敛迹。宋联奎有诗言此:“共传诸将语,城下耻言盟。”[34]此外,有人因目睹惨状,声称坚守西安是“不恤民艰”[3]379-380。抗战之中,正义与非正义的判断变得泾渭分明,“捍一城而卫天下”的记忆逐渐生成和凸显,并被赋予“惕刷现在和启发未来斗争的历史发展性”[35]价值,借以批判弃城投降之策。
一是利用西安坚守所折射的正义价值进行驳斥。国民军将领刘润民声称坚守西安的价值在于“为正义而奋斗,决不为利害打算”,体现了“中华民族为正义而战的最大决心”[36]。在抗战现实的投射下,坚守西安成为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反抗暴虐奴役、捍卫民族国家正义的壮举。“九一八”事变后,张仞鸣便坚决反对放弃抵抗,“坚城不守,任敌长入,则宰割践踏,陕民为状,又将奚若?”张氏视“以孤城死守为非计”者为“浅识者流”,并呼吁继西安之大义,“以增长其光荣”[37]。西安纪念大会通过《宣传大纲》向民众传达:“西安不守,西北各省无疑地变成军阀的俎上肉了,为祸之惨更不堪言了。”[3]379-380
二是利用守一城与保一国的历史经验进行驳斥。《塘沽协定》签订及华北危机后,日本的“渐进蚕食”更使国人深感守土守城之必要。杨虎城坦言:“倘国人一遇敌,皆以不抵抗得计,则吾民前途尚堪问耶!”[3]388原本主张中日交涉的胡适也转变了对日态度,开始强调“守”对国家和主权的重要性[38]。受胡适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文谴责“不抵抗”的思想,并质问避敌者:“设使九年以前守西安的将士们,也像今日的一走了事,不但国民革命难以顺利进行,而今日国家的主人,究是谁何?”诘问国民政府及军政要员:“倘使中枢主持者责令疆吏坚守,负守土责任的将士知道‘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勿去’的大义,能造成今日不可收拾的局面吗?”[39]放眼中外,守国的策略亦体现在守城之中,“比利时固守列日要塞一月,弹丸之比利时得以不亡,法兰西坚守凡尔登要塞卒能复兴。辛亥革命图一时之和平,此后全国各省几无日不在战争中”[40]。七七事变后,“保卫一个角落,就是保卫全省,保卫全省,就是保卫全国”的记忆不断警醒着时人不可心存苟安,必须“要坚守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河流”[41]。
坚守西安对保卫西北、策应北伐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段荣耀的记忆为后人的不断言说提供了丰富的解读空间,在抗战中成为凝聚民族情感、呼唤个人与国家命运共振的教育资源。对“弃城而图存者”的强烈愤慨,彰显了国人的民族救亡意识,汇聚了抗战守土、匹夫有责的时代强音,更体现出自古以来中华儿女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追溯北伐成功、感怀国土沦丧、思考守城意义和批判不抵抗策略,无不衬托出时人为守卫疆土而不辞艰危的壮志。
三、“英雄”记忆:高昂抗战情绪加强军民合作
1927 年杨虎城在公祭死难军民的挽联中写道“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6]。哀痛之中尽显愧疚之情,抗战之中,“怨”逐渐为“誉”所替代,凝聚着英雄记忆的石碑与热血沸腾的文字,成为对守城者由衷的赞誉和真切的历史评价。无论是对杨虎城的个人尊崇,还是对坚守军民的讴歌,无一不是在塑造坚毅、威武又充满胜利信念的“抵抗者”形象,以激起民族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为与侵略者进行斗争做准备。
(一)对“人民的英雄”与国之干城的呼唤
坚守西安中的杨虎城团结了李虎臣等各方力量,率众抵抗,发挥了核心作用,相较于诸多英雄高蹈于民众之上的圣贤化,时人对其形象塑造更为立体,既表现了其英雄性格,也描述了杨虎城作为普通陕人的品格特征,使之成为时代所呼唤的具有爱国情感的军人和领袖,激人奋进。
作为抵抗者和指挥者,人们多褒扬杨氏“力持抵抗主义”的“独具卓识”[6]。镇嵩军曾雇用飞机散发投降传单,致使民心不稳,经杨虎城“会衔布告,晓以中国革命之趋势,及坚守西安之重要,而市面照常,秩序不紊”[3]245。杨虎城的部下姬汇百回忆说:“杨公终日血战,冲锋陷阵,胆益豪,气益劲,全体官兵感杨公忠勇坚毅,咸一德一心,无怀二志者。”[42]炮火威逼、物资缺乏,杨公仍“百般劝慰于镇静,千方设计于不穷”,终使“落日孤城,不被恶魔所吞噬”[43]。英雄是历史叙事成为集体记忆的重要符号和结晶,为国家争生存,为民众谋解放的杨虎城得到时人的青睐,既是人民对英雄的褒奖和呼唤,更是对抗战救国领袖的渴望与期盼。
作为秦人的表率和楷模,杨虎城是“关西大汉”的典范,与民同甘苦、共患难。魏炳文述其“气不稍馁,风夕雪夜,愈加振奋,虽矢穷弹绝,尤以瓯瓦相搏,苦心鏖战,毅力擎持”[43]。杨氏的形象在秦人彪悍豪迈的民风映衬下,具体表现为“壮志雄魄、凛若冰霜”[43]的卓绝勇气;“不惧强敌、不怕强虏”[44]的革命魄力;“四千年来养成的朴实刚毅、机敏坚韧的特性”以及象征“秦人之敌忾”的古风[45]。其形象建构恰好符合抗战救国所需的“坚决意志,持久力量”[46],彰显出秦人执戟而战、振臂高呼的如歌情怀。
作为为国尽忠者,时人着重刻画杨虎城“始终服从,效命国家”的军人形象。郭则沉称赞其“历二十余年,无役不从,每战必先,为西北革命之中坚”[47]。西安解围后,他只身离开隐居,“谦虚而明大业”[43]。抗战中,如何激起全民族同仇敌忾的决心是时人最为瞻念的,以英雄品质灌注人民心灵,焕发出救国生机是最有效的号召方式,因而杨虎城被塑造为“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一切绝不以个人利益为向背”的“民族国家之干城”[43],其满腔的忠忱激励着人们坚忍迈进,赴身疆场。1936 年在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坚守西安十周年纪念大会成为十七路军团结抗日的动员大会。西安事变中,杨虎城响应中共的号召,秉持“为大局之需要,且以保障陕民之安全”[48]的原则,促使事件和平解决,此后杨虽被蒋介石长期囚禁,但其英雄形象却长留时人心中。
(二)号召“英雄的人民”与军民合作抗敌
坚守西安事件不仅承载了英雄个体的记忆,也展现了守城将士的光辉形象,建构出军民合作守城的抗敌记忆。从杨虎城到守城官兵,直至延伸为英勇抵抗的军民,英雄群像契合了全民族团结御辱的抗战需要,增进了民族认同感和战斗热情,为抗战动员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源。
坚守西安的记忆再现了革命军人与革命民众的合作,成为全陕民众迎击敌人的总动员。“军民一心,誓死无二”的共同撑持成就了西安“封垒坚守”之功,1934 年杨虎城于《告民众书》中肯定了守城及牺牲民众的卓越勋劳:“可歌可泣之伟绩,亦壮亦烈之奇勋。”[49]《中央日报》称所纪念者乃“守城将领”,所哀思者乃“牺牲的四万民众”,他们“坚守与救助之精诚苦行,交相辉映,如日月之光芒,照耀天理”[29]。
坚守西安中的军民合作一方面使民众知晓“效死勿去”,从而倍感其所肩负的重大使命,踏上先烈血路;同时也使军队战斗力最大化,其效用“能使万众一心,动如掣电,静如山岳”[49]。冲锋陷阵、壮烈牺牲的守城将士形象体现的是凛然的侠气和守土卫国的志向。1933 年杨虎城在祭文中盛赞守城“六千君子”当“填海同心,百二河山,铭功纪绩”[50]。而与杨虎城并肩守城的李虎臣、冯钦哉、卫定一等均被纳入英雄行列,孙蔚如、赵寿珊、李与中、许权中、李振西的勇敢善战也得到时人关注和纪念[51]。此外,西安的求援者于右任和解围者冯玉祥也成为英雄的代表,“于公间关重澜,奔走乞援,日夜兼程,濒死者数。冯副委员长不待包胥之哭,即兴救楚之师,衔枚疾走,破釜沉舟”[11],以此鼓舞将士“如守西安之忠贞,如援西安之热烈”[11]。
另一方面也肯定了民众武力的重要性。抗战以来所积蓄的民众力量逐渐充实与勃兴,胡毓威指出,“坚守西安中的军民合作便是全民族的真表现”[46],民众不仅充当军队的后勤和运输,更是亲身参与战斗,军队在与民众的共同奋战中受到拥护[32],从“人民的英雄”到“英雄的人民”,反映出民众抗战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的觉醒与增强。民众的广泛动员是抗战胜利的主要条件,军民结合的目的在于“动员民众,组织自卫军保卫国土”[41]。在这一话语中,“无役不参加,无役无坚持到底”的陕西民众及其“长久之革命历史及坚毅之革命精神”构成了坚守西安记忆的底色。
历史记忆的建构离不开对“人”的塑造,其中英雄形象是历史记忆在现实中的投影和延续,壮怀激烈的英雄赞歌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阐述,更是将民族共同的价值观投射于对现实人物的称颂之中。西安民众匹夫有责的自我觉悟,杨虎城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大义情怀,守城将士马革裹尸的壮志豪情,都使这一记忆具有了无穷的崇高性,深刻影响抗战时人。爱国热情的鼓荡,使中华民族齐集在抗战的旌旗之下,义无反顾地拼杀在浴血沙场,“军民合作力量之伟大,只要有决心,则一切苦难无不可以渡过”[52]。
坚守西安是抵抗军阀围城,保卫西安古城的正义斗争,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悲壮而辉煌的历史篇章。在此过程中,西安军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守城的英勇、军阀的残暴、人民的苦难理应长存史册,鉴往训今。时人所塑造的坚守西安的历史记忆在抗战中成为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共识,“苦难”记忆的呈现,深刻透视出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古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独立解放的价值观融合在一起,成为激励民族不断前行的内在驱动力;辉煌历程的“光荣”记忆,使爱国意识、奉献意识、团结意识、尊严意识不断被唤醒和激发;不畏牺牲、视死如归的“英雄”谱写号召人民在风雨如晦的救亡岁月里视死如归,用意志化作枪炮,用血肉铸就长城,共同投身于抗战之中。“坚守西安”既是民族悲情的寄托,也是民族奋起的源泉。正是这种自信而坚毅态度的注入,才使饱经战乱洗礼、政权更迭的人们依旧对胜利充满信心,在战火中重燃斗志,在废墟中重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