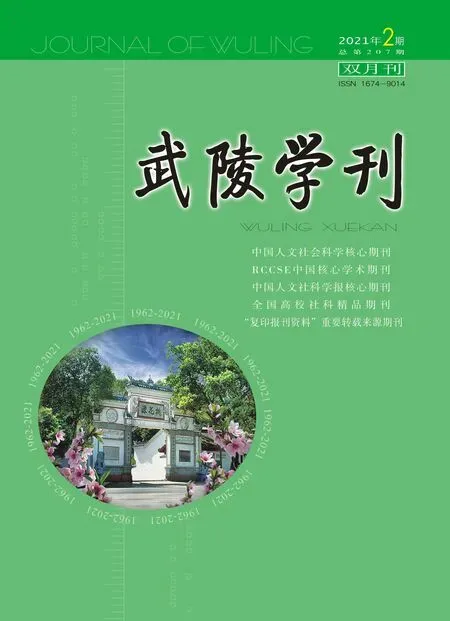身体现象学视角下课堂“举手”体验研究
2021-03-07孙洪涛
赵 娟,孙洪涛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对常识①问题的反思,是教育社会学对教育活动互动研究的基础。本文从课堂“举手”这一教育活动出发,反思课堂常识,发现课堂教学过分注重认知,忽视了身体对思维的重要影响,降低了教师的有效教学与学生的深度学习。“举手”这一身体动作,并非常识观念中的与课堂认知、思维无关,而是个体“自我”概念形成、个体“印象”维持管理、课堂“关系”联结等思维活动顺利进行的关键。通过“举手”体验研究,揭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及课堂里身体在场的重要性,为理解师生互动与交往,深度理解课堂教学意义,提高教学效率献言建议。
一、 “举手”的身体价值
(一)身体纳入理论视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 年发布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身体健康和智力健全之间的密切关系已被提及,指出神经科学在改善教学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特别是描述了大脑在各个阶段如何发育和运转,这有助于人们选择学习的最佳时间和方法[1]。刘铁芳曾指出:“人活在世界中,首先是作为身体的存在,身体在世之存在方式乃是个体存在的基础性存在方式,换言之,个体的一切活动都是基于身体在世之存在,并且最终回返到身体之存在。……任何教育形式都是以身体为基础,并且从身体出发,最终又体现为个体身体在世状态的转变与自我提升。”[2]
对身体的关注,从身体现象学就已经开始,但一直未得到该有的重视。现象学研究的一次重大转向来自于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胡塞尔的经典现象学关注意识体验,沿袭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身心二元论倾向,强调意识才是“我”成为“我”的绝对确实性。但是到了后期,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开始萌发了意识体验中的身体参与知觉意向的苗头,梅洛-庞蒂在此基础上开启了身体现象学转向,改变了传统的身心二元对立局面,他通过对知觉的本质探讨,将认识的本质还原为“身体—主体”相统一的身体上,即身体才是世界奠基性的存在。
(二)身体回归教学本身
首先,课堂教学改革呼吁一种新的探索模式。吴康宁等分析和归类课改背景下的课堂教学改革,发现绝大部分课堂教学模式都是哲学模式、心理学模式,或两者兼而有之的综合性模式,“社会模式或真正将社会学视野与策略融入其中的统整性模式几乎没有。”[3]而课堂教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除了让学生高效率、高质量的学习和掌握知识与技能,更要揭示课堂教学的社会学特征,使个体的社会化得以顺畅发展。
其次,课堂教学情境关注一种新的身体实践。在以往的研究中,高洁认为课堂“举手”现象是隐性的教育机会,体现出教师的一种偏好与价值选择[4]。苏崇武对比香港、台湾、上海和美国硅谷求学的亲身经历,叙述女儿上课“举手”发言的不同情境,观察美国与中国基础教育中不同的德育教学方法,认为教师对待学生举手的首要目的是“发展学生创造力”,而不是“维持秩序”[5]。因此,“举手”现象作为一种身体实践,正在逐渐进入教学研究视域。杨晓认为,课堂教学中的身体具有认知能力,具有主体性和意义,身体与自然、社会、他人和自我的相互作用是教学的起点,人回到教学的根本就是让“身体”回到教学[6]。
二、 “举手”的体验描述
范梅南在《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一书中,认为现象学研究遵循一定的研究传统,具有一定的知识体系,其写作手法尽力以直观了当的语言来描述当时的体验,而不作任何原因阐释,把反思与装饰语言“悬置”起来。这种白描的生活体验所挖掘的意义就是研究的重点:“现象学研究的意义就是‘借用’他人的经验及其对经验的反思”[7]78。受此启发,研究首先对“举手”体验进行描述,还原学生“举手”当下的时空。
(一)不同个体“举手”体验描述
根据不同个体对课堂“举手”体验的描述,可以大致把“举手”分为主动式举手、从众式举手、被动式举手三种方式。
1.主动式举手。主动式举手的学生在低年级表现比较活跃,有些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想“插嘴”又碍于课堂要求,不敢随意插嘴,只有高高举手,身体和视线都跟着老师移动,表现出强烈的表达欲望,享受“举手”回答问题后被老师鼓励和同学赞许的感受。有学者这样描述“举手”的体验:“在我们班级里有几位同学在课堂上的表现很积极,他们将课堂的气氛带动起来。老师们也不止一次的鼓励大家要多多举手发言,……也许是受到了同学和老师的影响,在课堂上我也变得积极起来,每一次回答完一个问题,我心中都会增加一份自信和自豪。”[8]
2.从众式举手。从众式举手指一些平常不爱举手的学生,看到旁边的人都举手,或者认为举手才能被老师认为是“好学生”,不管内心是否情愿,都随着“从众效应”而举手。也有学者对此作了描述:“课堂回答问题,教师要求要先举手,而且五指要并拢伸直。但是仍有少数学生身体向前倾,甚至站起来把右手高高举起,希望老师看到能够点他。有些平时纪律不好的学生也表现得非常积极,举手发言,坐得笔直,表现出一个‘好学生’的样子。”[9]
3.被动式举手。被动式举手发生在公开示范课上。老师为了保证课堂顺利完成,在短时间内提高课堂效率,会提前指定一些同学,特别是成绩好的同学“举手”发言回答问题。被动式举手还存在另外一种现象,即当班级其它人都已经举手回答问题后,只有个别人还没有举手,属于老师筛查的对象,迫不得已需要举手来回答老师的问题,例如后文中《让梦想起飞》里的主人公诚诚。
(二)同一个体“举手”体验描述
同一个体的“举手”体验在不同阶段表现不同:从幼儿园、小学初期“举手”时的热情高涨、争先恐后,到小学中后期、中学阶段的犹豫不决,思虑再三,甚至大学阶段的沉默不语,躲闪逃避。因此,“举手”体验不仅包含着共时性的原因,也反应出历时性的发展变化,刘云杉教授在著作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那时候同学们上课总是很积极。老师提出一个问题,无数只小手会立刻举起来,这还是不积极的了;倘若积极起来,小手会举得高高的,同学们都从座位上站起来,把手不停的摇着,嘴里还会或高或低地喊着:“老师,老师!”。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上课举手的人越来越少,是老师提的问题太难吗?不,每次被点到的同学都会回答呀。那么为什么呢?我不明白,依然我行我素的积极发言。
直到有一天,当我举起手时,我发现周围同学的眼神都怪怪的,我竟有点胆怯了。我听到有人说:“哼,出风头!”我的心仿佛被什么狠狠的扎了一下,举起的手也缩了回来。如今我已上了高二,却再也没有举过手。其实老师的问题我都会,可是我的手就是举不起来;身边的同学也都会,可他们谁也不举手。我搞不懂这到底是为什么,一度我行我素,如今也再难潇洒,我是怎么了?
现在的课堂变得很滑稽。上课了师生互礼后,同学们纷纷坐下,就开始了45 分钟的听课过程。老师在台上讲,同学们在下面听,老师讲什么同学就听什么、记什么,气氛虽不活跃,但至少还不像夜一般的寂静。“下面我问个问题。”本来十分安静的课堂一下子变得十二分的寂静。人人都低着头,手里转笔的,此时笔也静止了;本来写字的,不敢停笔,依旧在纸上瞎划着;坐的高的往下缩了缩,坐的低的赶紧趴在桌上,每个人的心脏的跳动都听得见,每一息轻微的呼吸。
老师终于开了金口,叫了一位同学的名字,教室里突然有了声音,——那不是人讲话的声音,是缩下去的同学重新坐高,趴在桌上的重新做直的声音混合而成,间或还夹着几声舒气声,闭闭眼睛,拍拍胸口,教师重又恢复了安静。真希望有一天,课堂上能毅然举起许多手,像无数只帆船,在人生的海洋里迎风破浪!(高二学生随笔节选)[10]
(三)概括体验描述的主题
对体验描述的意义探寻,需要用核心概念或者意义凝结的固化表达方式——主题来概括和理解。“主题就像一颗颗星星,构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意义星空,靠着主题之光,我们能遨游并探索这个星空。当我们进行现象学描述时,主题给了我们一种现象学力量”[7]11。基于上述有关“举手”的详尽体验描述,从身体现象学的角度来审视,可以概括出以下主题词:“自我”“印象”与“关系”。
首先,身体现象学认为,身体是我们理解和领会世界的中介,“自我”是身体的互动产物。那么,从“举手”体验中,我们通过身体理解什么?领会什么?学生的举手姿势,并不仅仅是躯体动作,而是与个体的自我意识紧密相关,是个体理解自己与领会世界的桥梁。
其次,“举手”是学生维持“印象”的身体管理方式。在课堂场域中,“举手”是身体转换前台与后台的一种教育性表演,通过身体表演,与他人的互动,让个体更加理解“我是谁”;通过“举手”体验,生动描绘出身体管理的“戏剧化”效果,每个学生都在扮演角色,以维持个体的整体印象。
最后,身体现象学主张,身体是课堂场域里各种“关系”的联结。通过身体,获得与主体体验者生活世界直接而原初的联系。身体不仅联结课堂教学中的物理、地理、心理环境,还联结时间、空间、人际等综合环境,联结物质与精神、个体与群体、普遍与特殊的综合实践。正如维特根斯坦描述的“身体是灵魂最好的图画”,课堂中的“举手”现象,通过身体在场与参与联结思维。
三、“举手”的意义探寻
体验描述和主题概括的目的是为了探寻意义。现象学研究注重参与者相对完整的体验,以及体验所负载的意义,因为“现象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获得对我们日常生活体验的本性或意义更深刻的理解”[11]。因此,研究从“举手”体验文本的理解开始,思考主题所蕴含的意义。
(一)举手:“自我”形成的身体产物
“举手”的意义之一,在于通过“举手”这一外显动作,揭示内在“自我”概念的形成,以及他人对“主我”和“客我”的影响。“自我”概念,不是和“社会”相对立的概念,也不是单纯的心理学概念,它实际上指的是个体在与他人进行交往时,所产生的自我感觉和认识[12]349。这种个体的“自我”,离不开交往和与他人的互动,与美国威廉·詹姆斯提出的“社会自我”有着直接的血缘亲属关系,即人们对于自己的各种感情与感觉,是通过与别人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个人通过想象他人如何评价他,以及他所看重的那些人对他的某种期待,产生自我认同感。”[12]349
米德把“自我”分为“主我”(I)和“客我”(Me)。“客我”是外在部分,“是来自外部、来自它周围的社会的那一部分,呈现的形态为需要满足的要求和被学习的榜样”[13]8。在“自我”的形成中,群体所起的作用是由“客我”这部分完成的。上文体验描述中的学生,其“客我”就是来自他人对自己期待的一种映像经验:刚入学时家长的叮嘱“要积极举手发言”,家长的期待“深深的印在脑海中”;再到小学,老师倾向性的选择期待,让学生的举手“发生了变化”;当周围同学的举手期待是“怪异”,学生从他人的眼神中区分正当行为和不正当行为,对于奖惩或者赞许的记忆,逐渐形成对规则或者他人期待准则的认识,就是“客我”的形成。
“主我”则是自我分裂出来的另外一部分,和“客我”一起代表了自我的双重性。“主我”是自我的内在核心,“所有外在的社会要求和期待都要经过‘主我’的细察、评价、推断和理解”[13]8。上文体验描述中“主我”的作用体现在:当面临外在的期待以及上课举手的人越来越少,“主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经历了对外在“客我”的仔细审查、思考,出现了“依然我行我素的积极发言”到“如今再难潇洒”的局面,这一过程并不是心理学意义上从众心理的顺利过渡,而是经过了“主我”不断对“客我”的反思、衡量、理解、调整,体现了“主我”主动性的调节功能。
“自我”概念在社会互动中怎样产生?换句话说,个体自我在社会互动中的形成机制是什么?库利提出的“镜中我”理论进一步做出了表述。库利认为,个体在与他人的交往中,通过互相解释对方的姿态,根据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等,把别人的语言和反映当作一面“镜子”,从而获得自己的认识,形成自我的概念。体验中的“我”,原本是热爱举手,积极发言的一个“我”,可是当发现“周围同学的眼神都怪怪的”,“我”就变得有点胆怯,再加上听到有人说“哼,出风头”,“我”的心仿佛被什么狠狠扎了一下,举起的手也缩了回来,再也没有举过手。不再举手的原因不是因为题目太难不会,而是因为他人对“我”的看法和评价,“他人”成了一面镜子,使“我”对原来的“自我”产生了怀疑,为了适应他人对我“不举手”的期望,形成了新的自我形象,不再积极举手发言。
(二)举手:“印象”维持的身体管理
“举手”的意义之二,在于个体为维持他人“印象”,对自我进行的身体管理。用戈夫曼的“剧场理论”来形容,课堂就是一个剧场,“自我”为顺利进行角色定位和扮演,实现印象管理的自我保护功能,不断在紧张化“前台”与隐秘化“后台”之间切换。
当学生身体和行为暴露在老师和其它个体面前,处在一举一动都会有人关注的“前台”情境中,为维持自身印象,会进行身体管理,呈现一个能被别人接受的形象。上文体验描述中的老师用“下面我问个问题”定义“前台”情境,犹如抛出演员台词,设定布景。学生为扮演好角色,将一些事或者身体隐藏起来:停笔、低头、缩身、趴着,试图连呼吸都要隐藏起来,没有人想“出风头”来破坏自身的印象管理,招来他人的不好评价。
这种情景定义一旦消除,“前台”的紧张立马回到“后台”的放松。“后台就是各种非正式行动出现的地方。”[14]当老师叫了一名同学回答问题后,大家就消除前台的紧张感,恢复后台的自由感:缩下去的同学重新坐高,趴在桌上的同学重新坐直,甚至还有舒气声,教室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因此,“前台”与“后台”的身体变化,是身体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的过程。
课堂教学中的“前台”和“后台”既相连也有分隔,并相互转换。正在举手回答问题的同学,会有“前台”的紧张感,他所要说的话和身体动作,不一定出于内心的真实想法,而是为了维持角色形象、符合角色期待、经过主体选择后的行为。如果他的所言所行打破了所期望的角色扮演,就会被当做笑话或者“不正常”行为。与此同时,其它没有回答问题的同学,就处在隐秘化的“后台”中,不用按照角色期待去行动,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比如转笔玩、瞎画纸等。
(三)举手:“关系”联结的身体表达
“举手”的意义之三,在于“举手”这一身体符号是课堂各种“关系”的联结。换句话说,课堂中学生对“自我”的认识离不开他人的期望,而联结自我和他人的关系,则离不开身体;另外,课堂中学生对知识与情感的联结,也离不开身体。个体从婴幼儿开始,当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影像时,就会脱离实际体验的“我”,而趋向由“镜子”所提供的那个想象的“我”。当我们看到他人时,也只不过与镜中看到的“我”的形象类似,他人只是我的外在形象。这是自我以及自我分化的最原初的反思,被梅洛庞蒂称为“沉默的我思”,产生于婴儿的镜像阶段,却一直伴随我们成人,发展成为一种知觉反思。原初反思会把他人的面孔不再单纯的当作视觉材料的“看”,而是当作情感的表达,与身体密切相关。
我和他人的关系,就是一种身体间的关系。“是我的身体在感知他人的身体,在他人的身体中看到自己的意向的奇妙延伸,看到一种看待世界的熟悉方式。”[15]梅洛庞蒂举了一个和婴儿做游戏的例子:我把婴儿的一个手指放到我的嘴里,装出要咬的样子,婴儿也会随之张开嘴。这并不是婴儿有意识的想学习我的动作,而是因为他从内部感觉到他自己的嘴巴和牙齿就是“咬”的器官,这样当他从外部看到我张开嘴的动作,他也感受到了同样的意向。因此,“咬”本身就有一种主体间的意义。
这种主体间的意义在“举手”体验中同样存在。当我们进入课堂教学场景时,我们能感受到周围的环境变化,并且被周围环境感染或者“传染”别人。虽然没有人给出积极或者消极指令,身体却跟着环境意向而改变,做出举手或者不举手的动作。例如环境描述中的无数、怪异、寂静、安静等词,身体也跟着变化,这说明它们都具有一种主体间的意义,都是身体性共在的体现。正如我的身体是一个系统,各部分相互蕴涵,我和他人的身体也是一个单一的整体,我同时栖居在我的系统身体和与他人共存的整体身体之中,用梅洛庞蒂的话来说,“我”这个词用于了复数,变成了“我们”。
从单数“我”到复数“我们”,身体的联结意义何在?答案是我们运用身体进行思考和记忆。研究表明,再现一个场景比其他任何记忆术都更有助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由这类证据推出的结论被称为具身化(Embodiment)[16]。具身化主张身体在认知处理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幼童时期用手指帮助我们数数,增加加减的感性直观,到长大后身体对某件事物的痛苦或者愉悦情绪,能让我们避免或者倾向于引起这种情绪的行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甚至在某些文化中,人的整个身体被当作一套数字系统。例如新几内亚的澳客萨普明人,将身体各部位依序对应27个数字,因此他们的计数系统是二十七进制。当然,我们对十进制的运用也有可能我们有10 个手指。也就是说,在认知过程中,我们把身体当做了存储器,身体帮助思考和记忆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总结与启示
根据对“举手”体验的现象学意义挖掘、研究,我们发现:一是课堂教学不能过分依赖经验常识,把“举手”仅看成躯体动作,而应打破常识,反思身体动作背后的深层原因;二是课堂教学并非纯认知训练,而是以身体为中介的一种社会互动与交往。三是课堂教学应重视学生的具身体验,运用身体帮助思考和记忆。
(一)打破“常识”,提高课堂对身体的反思性
课堂教学就是日常生活,课堂教学中的“举手”体验研究只是揭示了日常生活中一种你我共有的、未经加工过的知识——常识。当我们接受日常生活中的常识,也就是接受了常规的习惯性,不需要更多的自我审查和自我分析。“举手”体验研究中,小学生对举手的热情高涨,到中高年级的躲闪逃避,“本来就是这样”,“人本来就是如此”的常识性思维方式,使“举手”事件变得顺其自然,缺乏理性的分析,影响个体的自我成长与社会化。
置疑常规、打破常规,使常识陌生化才能鼓励我们重新评定经验,发现更多阐释经验的可能性,增加对问题反思的敏感性,产生教学机智。当然,反思问题并不是要“改正”常识,而是要“扩充”常识;不是用真理去代替“错误”,而是鼓励老师用批判的眼光去审查自己,提倡自我分析的习惯和质疑;反思教育教学过程中一些“墨守成规”的现象,解读课堂教学中,学生身体的变化对其社会化的影响与作用。
如何通过“举手”的身体动作,提高课堂对身体的反思性?让我们来看一段案例:这是一堂被我命名为《让梦想起飞》的励志课。首先,我让同学们面对大家,大声地告诉别人自己的梦想……我用举手的方式检查了谁有没有说,不出意料,坐在教室最后面的诚诚没有举手,也没有发言。我轻轻地走到他身边,告诉他,我知道你有梦想,只是不敢让全部人听到,那么,你把梦想写到纸条上,老师替你告诉全班同学,可以吗?
当他拿起笔准备写的时候,我有意识的走开了,又给全班布置了一项课堂任务,转移课堂的焦点。不一会儿,教室最后排的诚诚举手了,他给我一张撕下来的小纸条,歪歪斜斜地写着一行小字:我没有梦想,我将来只想做好一个平凡人[17]。
在这个案例中,诚诚属于被动式举手,原因是他缺乏安全感,害怕自己“平凡的梦想”会引来同学的嘲笑。而同学们的嘲笑将影响诚诚“自我”的认同与成长。故事中的老师,不是用常识经验来对待,而是运用教学机智,抓住了问题的敏感性,积极保护诚诚的“平凡”,用巧妙的比喻让同学们理解梦想的层次,要达到高层次,必须从最低的台阶开始,每个人的起点都是“平凡的人”,能坚持到达高台阶的人,也就是“做好一个平凡人”。这样,从身体“举手”的胆怯,经过微妙的反思处理,经过意识又返回到身体,下课后的诚诚“腰挺的很直,头抬的很高,眼神中也多了一丝自信。”
(二)理解“互动”,增强课堂中身体的参与
课堂教学中的交往和互动形式多种多样,这些交往模式放在身体现象学的理论背景下来理解,就是师生和生生之间,存在以身体为基础的初级群体关系。初级群体,是社会学家库利在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中提出来的概念,库利指出:“个人最早、最完全的社会生活经验时源于这里。”[18]他认为,人不是生下来就具有人性,人性是在初级群体中逐渐形成的,如果没有亲密的人际交往,人性就无法形成,在孤立中人性将会消失。
同一课堂中,老师和学生的身体固定在同一个时空,面对面的交往和合作,形成亲密关系,共同组成了初级群体。且生生之间的初级群体关系整合度更高,与个体的自我成长关系更密切,对个体人性的成长影响更大,即同辈群体对个体成长的影响更大,甚至超过家长和教师的影响。例如体验描述中的学生状态,共同保持沉默已经成为群体不需言明的规则,各自躲避举手回答问题已经成为群体的亚文化,且这种规则和亚文化的形成,都来自于学生身体之间的互动。
因此,课堂教学需要在关注认知的基础上,理解学生身体互动的社会学意义。刘旭等提出,学生的身体在教育场域中具有和心智同等重要的价值,课堂教学需要一场理解身体重要性的转向[19]。而传统的教育提倡“身体坐直,小手放后面,小嘴巴不说话”的方式,这种对身体的规训禁锢,对认知的过渡追求,带来对育人的片面理解。
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增强身体参与?佐藤学提供了一个通过观察“举手”的身体参与,完成课堂“静悄悄革命”的案例。佐藤学记载静冈县富士市广见小学,八木静代老师的改革:三年前的课堂,八木老师抱怨“我们班吵吵闹闹的,没办法”,因此上课只是一种教师独白的应付。而三年后的课堂,发生了变化。八木老师开始关注学生的身体参与,在鼓励并肯定“小修”同学举手发言,增加课堂互动,改善课堂行为后,悄悄改变以前“独白式”的教学场面:“在这个课堂里,八木老师的点名,并不受儿童举手的束缚。她琢磨每一个儿童的表情,侧耳倾听他们的低语,不举手的儿童也每每被点名,并静静的等待那些不知如何表达的女生们组织语言。”[20]
(三)创设“情境”,关注课堂的具身体验
随着具身认知科学的发展,在教育活动中,越来越关注身体的在场,个体的身体不是被动的机器,单纯地执行着大脑的指令,而是身体以及动作会以一种强有力并且可以预测的方式在影响我们的思考和推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用手势或者其它肢体语言来释放我们的大脑,贝洛克(Beilock,S.)这样举例:打电话的时候,虽然对方并没有看到我们的手势或者动作,但是我们依然在移动双手或者身体的某个部位,通过空出更多的脑力来掌握其他重要信息[21]。当然,这并不是凭空猜测,而是基于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家大卫·麦克尼尔(David McNeill)和苏珊·戈尔丁- 梅多(Susan Goldin-Meadow)对手势和思考之间的关系,长时间实验而提出来的观点。因此,对身体与教育的关系,正逐步走入研究者的视野。
国内首先用身体现象学来消除身体与教学关系二元论的尝试来自于唐松林等人,虽然当时还没有提出具身这个词,但是他们的研究已经在以“身体”为中心,认为“身体—教学”的关系特征是整体性、建构性、道德性和艺术性[22]。邱关军在对比传统教学思维方式和现代教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认为传统教学中,身体和身体经验在教学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扮演的只是“机器”的角色,身体是被动的,经验是缺场的。对身体和经验的忽视,导致教师和研究者在教学改革中没有交集,各做各的。因此,现代教学思维方式开始转变,在教学中重视具身化教学,即关注教学的情境性、生成性、动态化以及教学研究方式的身体化[23]。
在课程方面,张永飞明确提出,身体不再是物化的,身体是主体最核心的内容,课程主体就是“身体—主体”,课程活动是主体间具身性的表达、理解和感知[24]。以上研究只是从课堂教学的宏观层面或者中观层面来研究具身化教学,而对“举手”体验的研究,可以从微观角度解释身体在场对教学的影响,在微观中关注具身体验。
为何要关注具身体验?首先,教育即体验,爱因斯坦曾经呼吁:学习是一种体验,其它一切都只是信息②。我国最早对具身(Embodied)进行国外引进的刘光正,在其对雷柯夫和约翰逊合著的“Philosi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一书的翻译和概括性介绍的时候,就把具身思想翻译为“体验哲学”[24],其实这样翻译也是关注到了身体的经验,即对体验的重视,人对世界的认知是一种切身实践与切身体验的状态,教育活动是身体的切身活动。
其次,课堂教学中的身体不是孤立的,而是“嵌入”在课堂情境中、与周围环境和外在他人共同作用的身体。梅洛-庞蒂曾指出:“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入一个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于其中。”[25]例如“举手”体验研究中的个体,他的身体动作,举手、站起来、缩下去、趴着等身体变化,都与周围环境和他人的期望息息相关,每个人的身体都嵌入到了其他人共同在场的情境中。
最后,课堂教学还要关注身体的动态性变化,身体的动态性表现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不断修正认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曾经与《少年儿童研究》杂志社联合组成调查组,抽取了10 个省市的3 737 名10—18 岁学生,并对其进行调查,统计出上课主动举手回答问题的学生,其中小学生占13.8%,初中生占5.7%,高中生占2.9%。可见,课堂上主动举手回答问题的积极性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降低[26]。这种变化缘于学生对“举手”这一身体动作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当认为应该积极举手时,手高高举起,甚至站起来,随着年龄的长大,身体为了适应周围的环境,认知也改变为“缩下去”才是合群的,因此不再举手。
总之,在课堂教学中要从身体现象学的视角,打破常识,反思教育教学,并运用教学机智关注学生身体,理解学生自我成长的因素及其途径,以更好的达到育人目的;其次,课堂教学就是一个互动的场域,观察群体互动中个体身体的互动方式与特征,“举手”并不是个体的身体姿态,而是结合意识和思维的一种打开方式;最后,关注课堂教学中的身体在场,发挥身体在影响思维方式的积极作用,更好得实现身心合一的全面发展。
注 释:
①常识,在这时指你我的“原始”生活知识。社会学与“常识”保持密切而又有区分的联系,在方法和手段上存在以下四点差异:1.社会学(与常识不同)努力遵守负责地言说的严格规则,这些规则被认为是科学的特性。2. 社会学与常识所做判断的材料来源,范围的大小不同,社会学家研究的视角比个人生活世界提供的视角更为宽广。3.方法上的差别,社会学通过分析人类相互依赖的多重关系网络来理解人类处境。4. 社会学使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对常识所体现的日常生活方式进行细致的审查。总之,当社会学提出并质疑我们共有的常识性知识时,它会促使并鼓励我们重新评定我们的经验,去发现更多的阐释这些经验的可能性。——参见齐尔格特·鲍曼著,高华,吕东,徐庆,薛晓源译. 《通过社会学去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
②此句的英语是:learning is an experience, everything else is just information。——Albert Einstein. 原文用的是experience. 这里的经验既包括生理身体和物理世界的互动,也包括社会和文化经验。雷柯夫认为“具身”表现为两种状态:一种是基于肉身的身体;另一种是基于各种经验的身体。因此,本文把experience 翻译为第二种具身状态的体验。——参见张永飞著《具身化的课程:基于具身认知的课程观建构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