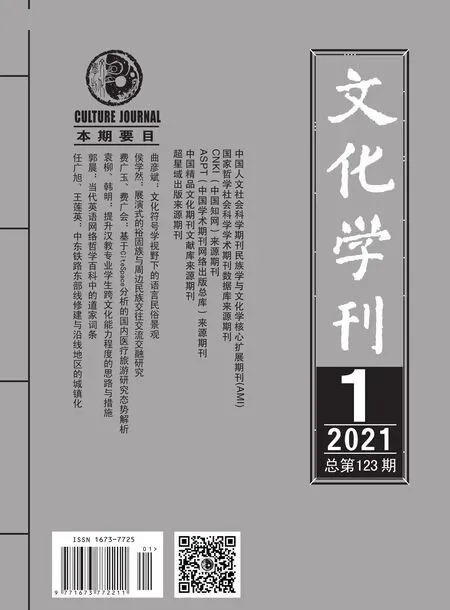《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爱米丽扭曲人生的心理原型解读
2021-03-07李爱宁
李爱宁
在20世纪的美国文坛上,南方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因对美国文坛的突出贡献及其高尚的人文情怀而被誉为“美国的莎士比亚”。1949年,瑞典学院在授予福克纳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这样评价:“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1]作为一位南方作家,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Yoknapatawpha County)百科全书式地反映了美国南方的历史、文化、种族及社会现实,他以犀利的笔调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战败后(美国内战)的美国南方,深刻揭露了战败阴影笼罩下美国南方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异化。《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福克纳于1930年发表的一篇哥特式短篇小说,主人公爱米丽出身于南方贵族世家,母亲早逝,父亲森严的门第观念及其落后的清教式教育使得爱米丽从小就养成孤傲的性格,与现实脱离。父亲去世后,作为镇上唯一的一位贵族后裔,从小深受父亲“关爱”的爱米丽年近三十仍待字闺中。一次偶然的机会,爱米丽与荷默·伯隆相识,两人出双入对,当镇上的人都以为爱米丽要嫁给荷默的时候,爱米丽却将荷默毒死并且与其尸体同床共枕几十年,不禁让人汗毛倒立。这部哥特式的短篇小说引起了国内外评论家的极大关注,评论界研究方兴未艾。有些学者从爱米丽的家庭教育入手探讨其悲剧根源;有些学者认为爱米丽“变态”,杀死爱人,守着一具干尸了却残生;还有学者认为爱米丽是封建礼制的替罪羔羊[2]。但是,鲜有学者对爱米丽这些看似疯狂的甚至变态的行为进行原型心理解读,以追溯其行为的根源。对此,本文以荣格的心理原型理论为依据,解读爱米丽扭曲的悲剧人生。
一、荣格的心理原型理论
受弗洛伊德个体潜意识的影响和启发,荣格提出集体无意识,用它来表示人类心灵中所包含的共同的精神遗传。关于到底什么是集体无意识,荣格曾经这样说过:“与个体无意识不同的是,一个人的各种情结组成了个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而集体无意识则是精神的一部分,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主要表达形式。”[3]荣格指出理解原型意象(archetypical images)是理解原型的存在及其意义的关键。人格面具(persona)、阴影(shadow)、阿尼玛(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及自性(self)是对人的性格形成和行为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主要心理原型。人格面具实际上就是“我”,处于人格的最表面,是一个人为了立足社会所必须具备的社会属性,属于社会性人格;阴影是隐藏于人内心最深处的,属于无意识层面的心理表现,一般来讲,自我意识的压抑或者尚未被认识到的自我是形成阴影的主要原因;阿尼姆斯是与阿尼玛对应的一个概念,象征女性内存的男性成分;自性是荣格分析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是组织、协调、统一原则,用来协调人格中的其他原型,实现自我价值,达到人格的协调发展,在一个健康的人格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一过程也称之为自性化过程[4]。
二、爱米丽的扭曲人生的心理原型解读
爱米丽的人生是悲剧的,也是扭曲的。究其原因,爱米丽的悲剧人生与其扭曲的人格、扭曲的爱情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荣格心理原型理论为更好地分析这一点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爱米丽的扭曲人格:人格面具与阴影之间矛盾冲突的必然产物
荣格心理原型理论认为,作为一对相互对应而存在的意象,人格面具与阴影是不可分割的。正如一个人不愿意把自己心中不可告人的秘密告诉他人一样,很多时候阴影都被人们隐藏了起来;反之亦然,人格面具就如同一个人最美的一面,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人们总是倾向于把这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他人,并且加以粉饰。古语云,有阳光的地方就有阴影。当一个人总是试图粉饰自己的时候(美化人格面具),那么他的心理就愈加阴暗,许多心理问题与障碍正是因为两者的不协调或者冲突而引起的。人格的完善需要两者协调统一,任何一方失调都会导致人格扭曲。爱米丽的人生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自幼受父亲森严门第观念及清教文化教育的影响,爱米丽不可避免地沦为父亲思想的傀儡。福克纳在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身段苗条,身着白衣的爱米丽小姐立在身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爱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5]43白色裙子包裹下的爱米丽是苍白无助的;父亲手里的马鞭,向后开的门,象征着父亲对爱米丽的专制,也说明爱米丽终其一生都无法摆脱傀儡的命运。人格面具是指人为了能在社会上与他人友好相处所扮演的角色,其目的是给人一个好的印象以便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接受。人格面具不是人的真正人格。在父亲面前,爱米丽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人格面具,她对父亲唯命是从,不敢对父亲有半点不敬。这使得父亲认为爱米丽认同自己的专横,因此才会变本加厉地把去家里的年轻男子都赶了出去。为了顾全父亲及其家族在小镇上的声望,在镇上的所有人面前,爱米丽也很好地利用着自己的人格面具。她是贵族的象征,她桀骜不驯、不苟言笑却又彬彬有礼。每当听到或看到镇上的人们关切地议论她为何年近三十还尚未婚配,爱米丽亦不予理会。爱米丽宽容的态度换来的是镇上的人们对爱米丽的同情与理解,每每看到爱米丽,镇上的老人们总是报以同情地说句“可怜的爱米丽”。爱米丽的人格面具使得爱米丽与父亲及镇上的人们保持着正常的人际关系。
然而,如前所述,当一个人总是试图粉饰自己的时候,他的心理就愈加阴暗,许多心理问题与障碍也因为两者的不协调或者冲突而出现。人格面具不是一个人的真实人格,人应该勇敢面对真实的自己(阴影),也只有当一个人适时地摘下人格面具,面对真实的自己时,一个人的人格才能得到健康发展。而爱米丽却不敢摘下自己的人格面具,面对那个懦弱的真实的自己。父亲的去世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突然之间爱米丽的人格面具被撕去,她不得不以真面目(阴影)示人,这时爱米丽显得无所适从,甚至有些冷漠:“她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天,所有的妇女都准备到她家拜望,表示哀悼和愿意接济的心意,这是我们的习俗。爱米丽小姐在家门口接待她们,衣着和平日一样,脸上没有一丝哀愁。她告诉她们,她的父亲并未死,一连三天她都是这样。”[5]43爱米丽的人格面具与其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真实的自己(阴影)在父亲去世之后发生了巨大冲突。如果说爱米丽在父亲活着的时候戴着人格面具去与镇上的人们交往是顾忌父亲那贵族的面子,那么父亲去世后就使得爱米丽内心长期被压抑的那个真实的自己(阴影)因重获自由而变得无所适从。“她病了好长一段时间。再见到她时,她的头发已经剪短,看上去像个姑娘,和教堂里彩色玻璃窗上的天使像不无相似之处——有几分悲怆肃穆。”[5]44就在这时,爱米丽遇到了那个叫荷默·伯隆的北方佬。于是,每个礼拜天的下午镇上的人都能看见他们一同驾着马车出游,爱米丽小姐的头总是抬得高高的[5]44。这时的爱米丽内心那个被压抑已久的自己已经完全释放,镇上的人都以为爱米丽小姐是在自甘堕落了。在镇上的人们看来,爱米丽与北方佬在一起甚至要结婚是多么荒唐的一件事,所以每每看到他们驾着马车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过时人们总是禁不住说一句“可怜的爱米丽”。但是,爱米丽并没有理会镇上人们的议论,依然我行我素。在撕下了人格面具之后,爱米丽却没有正视自己(阴影),爱米丽似乎摆脱了父亲的钳制,可以为所欲为。但是,荣格认为,当一个人的人格面具与他的阴影发生冲突且不可调和时,其人格就会扭曲。父亲去世后,爱米丽便在人格面具与阴影的冲突中苦苦挣扎而觅不到出路,这就给爱米丽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
(二)爱米丽阿尼姆斯原型的缺失
荣格认为,阿尼姆斯是女性心理结构中的男性化特征。荣格在解释集体无意识时曾说过,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会一直潜藏在集体无意识中,无法抹去。
爱米丽心理结构中的阿尼姆斯的消失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面对父亲去世。父亲的去世,对自幼在父亲的呵护下长大的爱米丽来说如同一座大山坍塌,爱米丽不知如何面对也没有能力面对。因此,她先否认父亲去世这一事实,把自己关起来不与外界联系,再次出现时却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与北方佬谈恋爱,甚至结婚,而这一切在镇上的人们看来就是堕落。从父亲去世到爱米丽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爱米丽的变化是很明显的,但这种变化恰恰说明了爱米丽独自面对生活的无助。其二,与北方佬的爱情。正是这段看似给了爱米丽一个可能开始新生活的爱情,成为把爱米丽推向人格扭曲深渊的致命一击。正当爱米丽不管不顾打算与北方佬结婚时,却得知这个北方佬压根没想过跟自己结婚,甚至打算路修好之后就回北方。于是,当镇上的人们开始讨论他们什么时候结婚,甚至有人看见爱米丽去买男性盥洗用品,并且每一件器皿上都刻上了“荷·伯”。此时,爱米丽却向药剂师买了砒霜,当药剂师问爱米丽小姐买砒霜做何用时,爱米丽怒目而视,吓得药剂师不敢多问。不久之后人们就看见爱米丽家的大门紧锁,每天只看到那个黑人仆人挎着篮子进出,爱米丽小姐完全消失在了人们的生活中。让人们感到更好奇的是,那个北方佬也销声匿迹,再后来就是人们闻到阵阵恶臭从爱米丽小姐的家里散发出来,而爱米丽却淡淡地回应了一句“可能是死老鼠的恶臭”,人们便不敢再多言。其实,爱米丽已经用在药剂师那里买来的砒霜将自己的爱人毒死在他们新婚燕尔的床上,并且每晚拥着这具尸体入眠。爱米丽爱而不得于是毒死爱人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爱米丽在面对爱情尤其是爱情中的背叛时的阿尼姆斯的缺失。在父亲长期的压制中,爱米丽心理结构中的阿尼姆斯并没有从父亲那里获得,反而,这种环境抑制了这种男性特征的获取,因此,在第一次独立处理人生中的大事时爱米丽是非常极端疯狂的,这是父亲的长期压制埋下的恶果,也是爱米丽扭曲人格的恶果。
(三)爱米丽无法实现的自性
自性,处于人格结构的核心位置,如同弗洛伊德的“超我”,起到协调其他原型的作用,最终实现人格的完善。
母亲早逝,使得父亲成为爱米丽唯一可以依靠的血亲,然而父亲的专制把爱米丽一步步推向了扭曲人生的深渊,无法自拔。诚然,父亲在世时,爱米丽的人格面具帮助爱米丽保持与镇上人们正常的人际交往,但是正如荣格所说,人格面具不是真正的人格,人要想达到人格的完美,必须适时脱下自己的人格面具,看到自己隐藏在人格深处的阴影,只有这样,人才不会出现性格障碍或者扭曲人格。爱米丽在父亲去世后脱下了人格面具,但却不是爱米丽自愿的,长期的压抑使得爱米丽无法正视那个真实的自己(阴影),阴影就与人格面具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父亲去世后,爱米丽看到了自己内心的恐惧(阴影),但是爱米丽却没有利用人格面具让镇上的人对她施以援手,对阴影不断加深的恐惧让爱米丽不知所措,自性也没能在此时协调阴影与人格面具的冲突,爱米丽就这样一步步走向她一开始就注定的结局。
三、结语
福克纳作为美国南方作家,对南方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结。战败后的南方人似乎陷入了一场梦魇中而无法醒来,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岌岌可危。自性原型已经无力将他们拉回到现实,爱米丽的悲剧也就发生了。1949年,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中曾这样说道:“我们今天的悲剧是人们普遍存在一种生理上的恐惧,这种恐惧存在已久,以致我们已经习惯了。现在不存在精神上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我什么时候会被炸得粉身碎骨?’正因如此,今天从事写作的男女青年已经忘记了人类内心的冲突。而这本身就是好作品。因为这是唯一值得写、值得呕心沥血地去写的题材。”[1]或许这就是福克纳作品的伟大之处吧。爱米丽是爱米丽,又不仅仅是爱米丽,而是每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深受精神问题困扰的人。